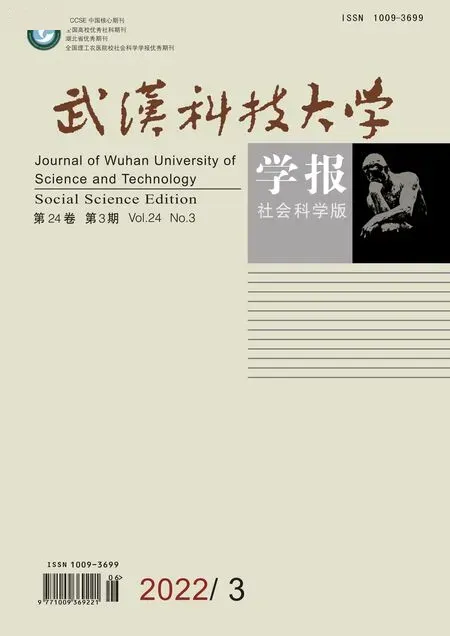今天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形而上学
——阿多诺对于形而上学经验的分析及其启示
王 晓 升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精神和肉体对立的基础上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所出现的问题已经受到了海德格尔等人的批判。阿多诺在批判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了奥斯维辛之后究竟需要怎样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形而上学构想,这就是要拯救形而上学经验,这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精神和肉体的统一的身体为根基的形而上学。对于他来说,形而上学经验的消蚀也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文化基础,因此,拯救形而上学经验不仅对于我们重新建构形而上学而且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同一性逻辑与人自身自然的扭曲
从文明的一开始,人就开始为了自我生存而不断地强化对于自然的征服。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必须控制自己的内在自然,对于内在自然的控制越来越成为人控制外部自然、提升控制的水平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人对于内在自然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越来越习惯于用同一性逻辑来思考自然;另一方面,人对自身自然的控制导致自身自然被扭曲。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通过同一性思维,人越来越能够有效地把握自然的规律,看到自然现象的同一性,并根据这种同一性来控制自然,从而使被控制的自然服务于人类的福祉。通过对人的内在自然的控制,人摆脱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对待他自己和其他人。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被概括在启蒙的概念之下,有了这种启蒙,人类才能有今天的文明和进步,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文明的这种进步同时也带来了难于避免的灾难,就同一性思维方式来说,虽然这种同一性思维方式对于把握外部世界的规律是必要的,但是一旦这种思维方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那么它就会无法容忍那些无法被纳入同一性思维框架中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存在者都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而成为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本质:一个是按照同一性逻辑所说的本质,比如,人的本质就是指人的最核心的共同点,即理性;另一个就是每个人自身的特殊本质,对于每个人来说,那种使他成为其自身而区别于一切其他人的东西就是他的本质。正如人和其他动物的最根本差别构成了人的本质一样,一个人与其他人的最根本差别构成了这个人的本质,而这个意义上的本质是不能按照同一性逻辑用概念来加以概括的,它不是某种共同性,不是抽象的一般特性。一个艺术鉴赏家能够非常容易把艺术上的真品和赝品区分开来,而把这两者区分开来的是一些非常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有时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那个使人成为他自己的特殊东西也是难于用语言来描述的,这是非同一的东西,而在同一性的思维框架中人们有时虽然也认识到非同一的东西,但是在同一性的思维框架中非同一的东西就直接与同一的东西对立起来,并被纳入到同一性(二元对立的)的思维框架之中。本来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但是,人却被概括在“白人”或者“黑人”这样的一般特征之下,这两类人甚至由于人种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
而就人自身的自然来说,人必须控制自己的自然,这是一般文明的标志,但是如果人类的文明走向了极端,把对人自身的自然控制建立在对自身自然的恐惧上,甚至彻底否定人自身的自然,那么人自身的自然就会被扭曲。这就是说,人不能和他自身的自然取得一种和解,而这种和解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比如,在中国历史中就有人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可是,凡是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在灭人欲的背后,人的欲望就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导致人自身自然的扭曲。
本来,人是要通过征服自然而实现自我持存的,但是为了实现自我持存,人居然要消灭人的欲望,消灭人自身的自然,于是,在人的自我持存中就包含了一种自暴自弃、自我否定的倾向[1]25。在恐惧和敌视人自身自然的情况下,一个人即使享受美食,也会带着内疚,这种内疚的心态如同一个人带着和尚的心态吃猪肉,虽然他能够品尝到猪肉的美味,但是他也会不断地诅咒自己,感觉自己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自然,在这里,人在一定程度上抱着一种自我憎恨的心态,对于这样一种状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描述说:从荷马时代一直到今天,统治精神都力图在斯库拉返回到简单再生产和卡律布狄斯无限满足需求之间的两难处境中校准方向,它也从来不相信,任何一种指路明星能使它少走弯路。德国的新享乐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们就试图再让人们失去欢乐,但他们在数百年的劳动压迫中学会了自我憎恨,因此他们在极权主义肆虐横行的国家里,只有靠粗鄙丑陋和自暴自弃才能获得解脱[1]24-25,在这里,人没有一种对待自己的正确态度,他们或者极端享乐或者自我憎恨。
当一个人用这样一种态度对待他自己的时候,他或者把自己变成一种纯粹的抽象自我,是纯粹的精神自我,或者纯粹肉体上的自我。如果他把自己变成纯粹精神上的自我,那么他就不能容忍经验的内容,肉体上的体验受到排斥。如果他把自己只是当成肉体上自我,那么精神上的超越性受到排斥。从哲学上来说,他或者是抽象的唯理论,或者是粗陋的经验论。当梅洛·庞蒂把肉体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批判了这两种理论。同一性逻辑强化了人们思想中的这种两极对立,而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这两者之间表面上是两极对立的,其实它们是相通的,它们都根源于人对于自己肉体的矛盾态度,根源于自身自然的扭曲。在阿多诺看来,人类文明之中长期发展起来的这种观念与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关联。
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西斯主义者用同一性逻辑来理解他人和世界,于是,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可以不被当作人来对待。阿多诺指出,“集中营里的施虐狂对他们的被害者说:明天你们就化作烟雾从这个烟囱中升腾到天空之中。这就是说每个鲜活生命在这里是无差别的,而历史正在走向生命的无差别性:每一个人在其享有形式的自由之中就已经是在清算者的脚下的可互换、可替代的东西了”[2]355。本来,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这些法西斯主义者对于犹太人也应该有最起码的人类情感,但是,这些人把所有的人都抽象化,好像他们所面对的犹太人是没有肉体的精神存在,他们在纯粹的精神意义上都是抽象的自我,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在对待肉体的态度上表现出一种两极对立的倾向,虽然他们自己享受着肉体的快乐,但是又排斥肉体上的快乐,对其他人缺乏起码的同情,这些人甚至对自己的肉体的享受都表现出某种敌视态度。
二、精神和肉体的对立:形而上学经验的消蚀
在这里,人们必然会问,这与形而上学经验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阿多诺所提出的形而上学经验是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是肉体的人,都是有情感的人,这些人哪怕再残忍也会有那么一点情感,只要他有一点点情感,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敬畏生命,不至于像法西斯主义那样滥杀无辜,而法西斯主义为什么竟然会如此无情无义呢?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不能把他自己所保留的那一点点情感向外扩展到其他人身上呢?如果用学术的话语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人的这样一种情感不能有超越性呢?为什么这种情感只能是一个人内在的而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呢?
在《否定辩证法》的最后一部分,阿多诺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再残忍的人都会是有感觉的人,是有情感的人,但是这些人却可能缺乏“形而上学的能力”,缺乏超越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他没有形而上学能力,他就无法对他人表现出同情和关爱,而这又与现代社会变成了“第二自然”这个状况联系在一起。用阿多诺的话来说:这个第二自然从人类之恶中构造了一个真正的地狱,并由此而剥夺了人的想象力。人的形而上学的能力被扭曲了,因为,已发生的事件摧毁了思辨形而上学思维和与经验之间共存的基础[2]354,这就是说,在社会变成第二自然的时候,人进入了一种精神和肉体二元对立,当这两者对立起来的时候,一个人作为精神的人就会是进行思辨形而上学思维的人,而作为经验的人是具有肉体体验的人。如果一个人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人就能够把自己的肉体上的体验超出个人之外,而对其他人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而当我们的社会变成第二自然的时候,思辨形而上学思维和经验之间的共存基础就被消灭了。在第二自然的魔力的控制之下,人或者被束缚于抽象的自我之中,或者被束缚与肉体的体验之中,而缺乏超出自我的想象力。第二自然使人处于一种魔力的控制之下,阿多诺说:在魔力控制之下,活生生的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不自觉的无动于衷,即一种薄情寡义的审美态度,或者是被卷入者的兽性,这两者都是虚假的生活[2]356。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来说,第二自然导致了人的形而上学经验的消蚀。
那么为什么社会变成第二自然的时候,人就会把感性和理性、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呢?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从文明的一开始,人就开始有一种同一性的思维,有对于肉体的那种矛盾的态度,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却把这种状况发展到极端。按照卢卡奇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的方法已经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功能化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人都成为功能体系中的一个要素,无论人们表面上有多大的差别,他们的内在观念都是一样的。莱布尼兹用先定和谐说明了这个体系的特点,这就是说,在这个功能体系中每个人的角色和功能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按照社会的系统化、功能化的要求来行动。每个孤立的原子虽然表面上不同,而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按照功能系统的要求来行动,他们都有一种功能化的思想方法,在这样一个功能化的体系中,个人的情感是一切错误的来源[3]。因为情感等方面的东西影响了功能体系的运转,该功能系统就变成了第二自然,这个第二自然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素阻止了人的形而上学经验。第一,这个系统中的人都是封闭于自身的个人,而且是越来越被合理化精神所控制的个人,或者说,成为笛卡尔的那种纯粹的理性自我。第二,这些个人虽然也有感性的经验,但是这种感性的经验是按照实证主义原则确立起来的感性经验,或者说,这种感性经验是按照控制自然的需要而确立起来的感性经验。如果这些人对于其他人也有某种感性经验的话,那么这种感性经验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同情和关爱,而是为了市场竞争而确立起来的感性经验,把其他人作为竞争对象而产生的感性经验。第三,生存竞争原则让人失去了同情他人的能力,人越来越纯粹地精神化。阿多诺说:恐惧是与自我持存的个体化原则结合在一起的,然而这个原则由于其自身的顽固性而废除了自身[2]355。这就是说,人生活在一种竞争的恐惧之中,生活在对于自身的自然的恐惧之中,因为这种自然的情感影响了人在竞争中的生存,人越是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就越是要否定自身的自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恐惧之中,人把自身精神化,变成了笛卡尔式的纯粹的精神自我。这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儿童教育一样,许多家长都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样一种竞争压力中,尽管家长也要培养孩子的感性能力,比如,要孩子学习艺术、体育等,但是,这都是被纳入到竞争的需要之中的。竞争需要把一切肉体的东西以及情感的东西都扭曲了,生存竞争最终否定了自身,人越来越使自己成为精神上的存在者。
前面我们论述了肉体和精神的对立,那么为什么这种对立导致形而上学经验的消蚀呢?因为,当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的时候,人就更容易脱离肉体的体验而对现实采取一种冷漠的观察态度。
阿多诺说:自我持存只是必须要怀疑,它在其中强化自身的那种生命变成了让它害怕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幽灵[2]357,这就是说,竞争的需要把人的生命变成了让人害怕的东西,人的生存变成了一种精神化的状况,比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互相竞争,但是这种竞争越来越与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无关了,或者说,这种竞争不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加幸福,而只是要让人有征服他人、超越他人的快感,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这就是要让生存竞争永恒化。本来人在没有足够食物的时候,需要进行生存竞争,但是在基本的物质条件得到保障的时候,人的生存竞争就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更加体面、更加高人一等,这就如同有人为了一部名牌手机可以出售自己的肾一样。人的生存已经精神化了,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脱离“肉体”的存在者,这种脱离肉体的人、精神化的人具有一种“超越”的精神,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直接的肉体需要而生活。
这种脱离了肉体的生活的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人,是孤立的个人,是数据意义上的个人。由于这样的人把肉体的体验和理性的思考割裂开来,他们习惯于用一种经验观察的方法、用纯粹客观的方法来观察这个社会。本来,痛苦是无法用数字来表示的,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贫困就是可以用数据来表示的痛苦。在这种“痛苦指数”中,缺乏的是对于人的肉体上的同情,没有肉体上感同身受的体验,本来脱离肉体的需要可以让人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能力,这就是让人不受自己的感觉要素的影响,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从而更客观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一般规律。阿多诺甚至也承认,这种做法确实能够非常轻易地与资产阶级的冷漠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做法,如果人只是沉溺于自我的感觉和肉体的体验中,那么人就会缺乏形而上学的维度,而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维度也有“人道的方面”,这是因为,在这里,个人也能很快而又毫无畏惧地意识到存在的虚无[2]356。这就是说,人作为旁观者,很容易忽视人的具体的生存,或者说,人会意识到,在对他人的观察中他人的具体生存立刻就会化为虚无,对于这种忽视他人具体生存的自觉意识是具有人道方面的。阿多诺举例说,萧伯纳在去剧院的路上,向乞丐出示了“记者证”,这种玩世不恭的做法,其实就是要揭示旁观者的冷漠,是对这种冷漠的自觉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人道的。但是,抽象地生存的人却由于缺乏肉体上的冲动,缺乏自主性。对于阿多诺来说,这种肉体上的冲动会对观察者的冷漠态度提出质疑和反思,而抽象地生存的人却缺乏这种反思。
超越具体生活,对于生活进行冷静的观察,这是形而上学的需要,没有这种冷静的观察就不可能有形而上学,但是,如果没有反思,那么这种冷静观察就是不人道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冷漠。对于阿多诺来说,我们需要把形而上学的思考与生活中的体验结合在一起,只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冷静的观察才具有人道的方面;只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才可能有形而上学的经验。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之后的形而上学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他指出,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再也不能把形而上学上的那种概念思考和肉体的体验分离开来了。如果我们还是沉溺于过去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冷漠地看待奥斯维辛,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看作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这是极度不公正的,是对逝者的漠视,人们在情感上再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形而上学了。形而上学必须是带有经验的形而上学,是日常生活中人的肉体体验联系在一起的形而上学,而现代社会中,肉体的体验与理性思考的分裂却不断地侵蚀这种形而上学经验赖以产生的基础。康德的形而上学就是在这样的分裂的基础上产生的形而上学,而阿多诺的形而上学经验就是要超越这种形而上学,他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形而上学,这就是和经验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学,而不是纯粹超越的形而上学。
三、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转向
在阿多诺看来,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对立不是现代社会才发生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的。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把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的过程。阿多诺强调,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必须遵循一种新的道德命令:决不能让奥斯维辛再次发生,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扭转传统的形而上学,就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思考与人的肉体的体验结合在一起。阿多诺把这种转换称为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的转换,而在过去的精神统治的时代,人从精神上蔑视这种肉体的体验,把它看作是下等人的事情,看作是过于平庸,陷入日常琐事之中。有些人甚至从道德上认为,这种东西是“绝对的恶”[2]358。在阿多诺看来,奥斯维辛之后的形而上学却必须转向这种绝对的恶的东西,转向人的生活中所遭受到的肉体上的痛苦。阿多诺说:活生生的人的肉体的、远离意义的层面是经受痛苦的舞台,这种痛苦烧毁了精神所提供的一切安抚剂,烧毁了精神的对象化产品即文化,在集中营中,它们提供不了任何安慰[2]358。纯粹精神上反思的那种形而上学无法给人们提供任何安慰。
其实,从阿多诺对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他看来,这些哲学家们虽然热衷于精神上的思辨,但是这种思辨之中都无法排斥“物质生存”,并且他们的形而上学也必然会滑入物质的生存,比如,康德关于“理知的世界”的分析就是如此,尽管这样,这些人的思想还是过于抽象了,对于生活中的肉体体验缺乏关注。按照阿多诺的分析,儿童从生活的一开始就把外部的体验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他们常常会随口说一些脏话,这些脏话是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得来的,并且无意识地纳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为此,阿多诺说:如果有人能够成功地用诸如“粪堆”“猪圈”之类的词语让他们想起曾经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大概比黑格尔在绝对知识那一章所说的绝对知识更接近于绝对知识,因为尽管他承诺给读者提供绝对知识,但为的是要高傲地收回绝对知识[2]359,这就是说,人在成年时代所说的那些脏话包含了生活的体验,如果这些脏话能够让人想起人的那种生活体验,那么这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知识,是人的肉体体验中得到的最真切的知识。阿多诺认为,这种知识比黑格尔的抽象绝对知识还更接近于绝对知识,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的哲学就是要把握这种绝对知识。
然而长期以来人类的文化排斥肉体,阿多诺把这种排斥肉体的做法理解为“把身体的死亡整合到文化之中”,这就是说,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中,人们都强调精神的东西,而排斥人自身的自然、排斥身体。在宗教神学之中,这种排斥身体的做法特别明显,在这样的文化之中,身体“死亡”了,所以,阿多诺强调,在神学之中记载着文化和形而上学的融合。笛卡尔把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的二元论从理论上确立了这种状况的正当性,而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就是在脱离身体的意义上抽象地讨论死亡,相反,在阿多诺看来,在文化之中就应该包含身体,包含肉体的死亡,而只要肉体死亡包含了“恶臭”的,那么文化之中就应该包含恶臭,如果文化之中排除了“恶臭”,那么这个文化就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文化。于是,在这里,阿多诺用饱含激情的话语指出:文化憎恶恶臭,因为它发出恶臭,正如布莱希特用夸张的话语所说的那样,文化的大厦是用“狗屎”建成的,就是在这句话写出的几年之后,奥斯维辛无可反驳地证明了文化的失败[2]359,这种纯粹精神的文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表现得最为明显。排除了“脏话”的文化,是脱离活生生的生活的文化,排除了“不文明”东西的文化恰恰是极端不文明的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思想中所反映出来的尼采思想。
在这里,人们也会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人类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没有关注人的身体吗?阿多诺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人的身体在现代文化中被扭曲了,或者说,虽然身体也受到关注,但是身体是作为受排斥、被异化了的东西而受到关注。阿多诺说:对身体的爱憎影响到一切现代文化,身体在被作为卑贱的东西而遭到叱责和拒斥的同时,又作为禁止的、对象化的和异化的东西而受到追求[1]216。这就是说,现代文化也关爱身体,但是,在这里身体被扭曲了,被作为异化的身体而受到关注,比如,现代社会的女性让自己的身体变成时尚的身体,现代的劳动者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商品来出售,在这里,身体都是以异化形式出现的身体,而身体的异化是与现代社会中劳动的分工有关的。按照阿多诺的看法,身体的异化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产物,从事文化生产的精神劳动人蔑视体力劳动[1]215。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是精神和肉体分离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人也承认肉体的地位,但是肉体是被扭曲了的肉体;虽然精神也表达了肉体的要求,但是却是一种扭曲的形式来表达肉体的要求。阿多诺说:精神的绝对性和文化的光环遵循同样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依不饶地伤害它所假装要表达的东西[2]360。人们用伤害肉体的形式来表达肉体的要求,这就好像现代社会中在儿童的艺术培训中往往容易出现的情况那样,人们用伤害儿童兴趣的方式来培养儿童的兴趣。
按照上述分析,人们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阿多诺是要彻底颠覆人类文化,彻底否定人类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是“狗屎”堆起来的。这当然误解了阿多诺,阿多诺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人类文化,而是要指明,这种文化排斥了肉体或者扭曲了肉体,他所主张的是把肉体纳入到文化之中,把人的身体的感知纳入到形而上学之中,所以,他说:任何人,只要他为保持这种极其罪恶、卑劣的文化辩护,就变成文化的帮凶,而那些否定文化的人就直截了当地推进了野蛮状态,这也是文化会展现出来的野蛮状态[2]360。简单地否定文化是野蛮的,简单地肯定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排除了“恶臭”)也是野蛮的。
同样的道理,简单地否定身体是野蛮的,而简单地肯定身体也是野蛮的,就身体的体验来说,任何人都不直接肯定自己的身体体验,并据此来否定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贝克特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绝望描写(比如《终局》),在他的戏剧中,人好像生活在集中营一样,毫无出路。那些从集中营成功逃生的人也许会指责贝克特说,他对于集中营的描述太悲观了,他应该给人们提供挖壕沟的勇气。确实,从这些成功逃生的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贝克特恰恰拉开了与这种肉体的体验距离,并据此说明集中营中的体验,这是一种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对于集中营的体验的思考,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反思。成功逃生的人恰恰缺乏这种形而上学的维度,缺乏贝克特思想中的反思维度,这就是形而上学要达到的地方[2]360。形而上学需要肉体的东西,但是也不能拘泥于肉体的东西。
四、拯救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形而上学经验,如果没有这种形而上学经验,一个人就无法超越自身而关爱其他人,而现代社会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经验正在被消蚀,甚至越来越严重地被消蚀,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这种形而上学经验被消蚀的势头,那么法西斯主义的东西就会沉渣泛起。
那么如何才能拯救形而上学经验呢?阿多诺指出,拯救的观念就是要把人从这样一种被延长了自我持存的钳制中松弛下来[2]384。人当然需要自我持存,但是我们不是把自我持存的努力无限扩大,不能把自己始终束缚在自我持存的钳制之中。在生活中,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这就是对于自己儿童时代的幸福时光的怀念。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觉得儿童时代特别幸福呢?这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生存斗争的残酷体会。阿多诺也通过《追忆似水年华》中有关说法来说明人的形而上学经验,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儿童时代的那种幸福体验有关,而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看到生存斗争的钳制被延长了的情况。本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基本生活条件是得到保障的,但是生存竞争的观念却不减。人们在生活中相互比较,看看谁的项链更粗,谁的手机更“高档”,虽然这种极端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感到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把自己束缚在这种被延长了自我持存的钳制之中。
阿多诺说:我们诅咒这种生存强制,因为这种生存强制与其说是要驱使人们超越纯粹的此在,不如说要把它伪装起来,把它固化为形而上学的权威[2]390。这就是说,过去的形而上学是以生存竞争原则为核心的,生存竞争原则被固化为形而上学的权威,就是在这种生存竞争中,人的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了。用精神否定肉体或者用肉体否定精神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两种原则,笛卡尔所强调的精神和肉体的二元对立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
要拯救这种形而上学就是要放弃肉体和精神的二元对立,这就是要让脱离肉体的精神和脱离精神的肉体都经过“死亡之门”,只有这种对立起来的东西都经过了“死亡之门”,我们才拯救它们。阿多诺强调,任何一种未被改变的东西,任何一种未经过死亡之门的东西,都无法得到拯救。如果拯救是每一种精神的最内在的冲动,那么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毫无保留地放弃:既希望那应被拯救的东西,又希望那满怀希望的精神[2]384。毫无保留地放弃,不是要放弃人的生命和人的精神需求,而是要放弃传统的形而上学、放弃肉体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只有放弃了这种二元对立,生命和精神才能得到拯救,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精神”,或者说,这是复活了的精神和生命。阿多诺说:希望意味着肉体的复活,并且这种希望通过其自身的精神化而知道它被剥夺了其最好的东西[2]393。人在生活中充满了希望,而希望就是肉体的复活。我们知道,肉体复活的说法是基督教传统中的观念,这是上帝经过了死亡之后的复活。阿多诺借用这个思想来说明,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结合不是说肉体不受精神的制约,但是精神在制约肉体的时候,精神要进行自我否定,它要知道,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在剥夺人的最好的东西。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全新的生命和精神呢?这就是既要承认肉体的需要的合理性,又要限制肉体的需要,这就是要让“精神开始与其自身中的那种控制自然的原则相分离”[2]384,同时也要让精神中那种违逆生命的东西在其内省中达到顶点,使精神认识到,这种违逆生命的东西是极端可恶的。当精神与控制自然的原则相分离的时候,精神就是要承认肉体的欲望的合理性,但是,这不意味着精神不控制欲望。精神应该是这样来行动:如果精神要求别人禁欲,那么这种禁欲就是错误的,如果它要求自己这样做,它就是善的:它在自我否定中超越自身[2]385。人的幸福生活来自于肉体和精神的和解,这不是说精神不能控制自然,而是说,精神不能否定自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欲望是道德的,但是,如果精神要求别人禁欲,把这种禁欲理想当成一种要求别人的道德原则,那么这就是恶的。
当精神和肉体和解的时候,当精神承认肉体是它的内在客观要素的时候,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就可能了。阿多诺说:精神通过其一切中介而参与到定在——这种定在取代精神的所谓的先验纯粹性——之中,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就存在于精神的这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就存在于精神的那种先验客观性要素中,这个要素既不能从精神中剥离开来,也不能被本体论化[2]385。这就是说,精神必须和物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精神不仅要吸收外部的现实,而且要结合内在的自然。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就存在于精神中的这种客观要素即人的内在自然之中。在阿多诺看来,肉体的东西是精神中的客观要素,并且是先验的客观要素。在这里,阿多诺其实就是要表明,在历史上,精神和肉体被对立起来了,而他要致力于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和解,在这种和解中,成年人才有可能保留儿童时代的那种幸福感。阿多诺说:人的形而上学兴趣需要他们有一种未受伤害的感知能力,即感知他们自己的质料性东西的能力[2]391,这种所谓的质料性的东西就是指人的肉体。
五、现代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倾向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在现实社会中,自我持存的钳制被过度延长,人们把自己束缚在生存斗争的模式之中,这种生存斗争的模式甚至改变了人们对于生命和死亡的体验。在法西斯主义那里生命就是一个数字,在这里,生命本身就已经类似于死亡。缺乏形而上学经验的人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人的生命的,于是,虽然人都会说“生命”,但是传统的人们和现代社会的人们所说的“生命”的含义是不同的。传统社会中所说的生命是包含了肉体体验的生命,而现代社会中,人们所说的生命是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是与精神分离开来的生命,缺乏形而上学经验的人越来越无法从生存体验的角度去理解生命的意义,无法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意义。同样的道理,现代人对于死亡的理解也与古代人不同,现代人更容易把死亡理解为一个数字(现代人的同一性思维使他们越来越难于理解生存和死亡概念的这种差别),所以,在这次新冠疫情之中,当某国领导人说按照目前的趋势,该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十万,他甚至会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但是在笔者看来,他所说的“可怕”才特别可怕,因为这个“可怕”是缺乏形而上学经验的可怕,是无情感的情感。
当然,这也不是这个国家的某个领导人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整个的社会氛围的问题。在这些国家,长期的市场竞争,肉体和精神的分离被固化为形而上学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里,自我持存的钳制如此根深蒂固,在关爱“生命”之中漠视生命已经成为常态,因此,当疫情来临时,人们首先考虑到的不是如何保留生命,而是如何更好地开放经济,这个国家努力保证经济的开放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经济随时会崩溃,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们随时面临生存的危机,而是因为这个国家在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的同时还要保持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对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的关注是这个国家的人们共同的思想习惯,这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自身选择上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的许多或者大多数选民的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牺牲一些人的生命就成为这个国家被承认的选项,为了确证这个选项的正当性,一些人甚至不顾最起码的科学常识,把是否戴口罩变成一个政治议题。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新冠疫情来临的时候,人们所关注的不是如何来控制疫情,如何科学地看待疫情,而是操弄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社会背景,当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也利用这个危机制造种族对立。一些人基于经济竞争的需要,制造中国威胁论,把正常经济上的竞争变成了一种民族斗争、政治上的冲突以及国家之间的敌对斗争。在这里,经济上的竞争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变成了国家制度的斗争,甚至潜在地包含了人种上的斗争,一些人在自己的内在意识中无法接受一个东方国家的兴起。这里都隐藏着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只是,这种“法西斯主义”不能再直接以种族灭绝、种族屠杀的形式出现,但是却会以变形了的种族主义的形式出现。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样一个情况,在美国,种族主义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被否定了,但是,种族主义在社会层面上从来都没有停止。白人至上主义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白人至上主义是在阿多诺所分析的那种法西斯主义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种族主义是无法被根除的,国家层面上消灭种族主义恰恰表明这种种族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从“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fe matters)的口号之中,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不是反对种族主义而是在强化种族主义,这种所谓的反种族主义恰恰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基础上的。
阿多诺所提出的非同一性思想是破除这种思想的有力方法之一,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感知,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肉体上的感知出发,而又超越这种肉体上的感知而对待其他人,或者说,人们可以带着一种形而上学经验去对待他人。经济上的竞争不能被延伸到其他领域中去,或者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把生存斗争的钳制无限地延长或者极度地扩展,这种极度扩展了的生存竞争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