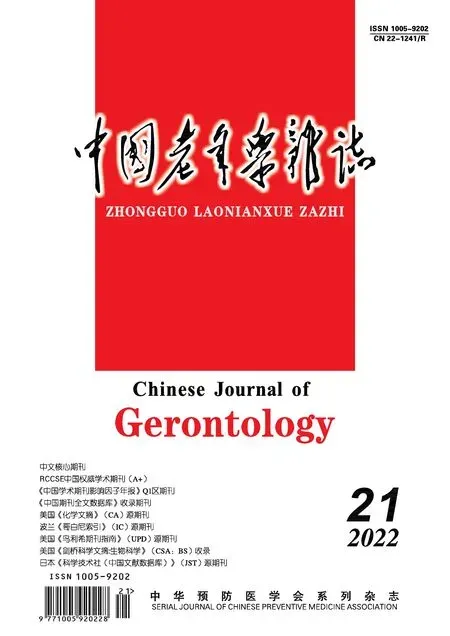应激对机体的影响
彭玲 卢凤美 张辉 黄蓉 薛超 吕婷 刘东璞
(佳木斯大学基础医学院微生态-免疫调节网络与相关疾病重点实验室,黑龙江 154007)
应激作为一种非损伤性刺激,能够较好地模拟人类生活中“无法控制”的生活状态,使人们出现焦虑样行为、记忆障碍和内脏敏感性。Lugovic-Mihic等〔1〕通过调查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大流行和萨格勒布地震对特应性皮炎(AD)患者心理应激水平和疾病状况,发现了灾难和不良事件作为一种应激源会导致AD恶化、也会扩大患者的心理问题。Komorita等〔2〕也证明了在地震后的急性、亚急性期,心力衰竭和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率显著增加。尽管目前已经证明了在持续的应激作用下,确实会对各脏器产生影响,但其具体的影响机制还有待探讨,因此,本文对应激造成各脏器的影响进行总结,并探讨其发生的机制。
1 应激对大脑的影响
Khana等〔3〕通过慢性轻度应激(CMS)大鼠模型发现了应激对大脑的不同区域都会产生影响。①海马。慢性应激诱导的肾上腺类固醇激增改变了海马的细胞功能和可塑性,导致成年齿状回树突萎缩、树突棘缺失和神经发生抑制,由于树突和轴突物质的丢失及胶质细胞的变化,是导致海马体积损失的最可能因素,因此这些细胞变化导致海马体积损失。研究证明了应激诱导海马中间神经元数量的变化,在特定的海马亚区,表达小白蛋白、生长抑素、钙视网膜蛋白和神经肽Y的神经元数量减少。应激还降低了原发性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表达及BDNF树突转运,这可能导致应激诱导的树突萎缩。②前额叶皮质(PFC)。慢性应激可减少人类和啮齿类动物体内PFC体积,这种体积减少的细胞基础很可能是树突物质的丢失,但应激诱导的胶质细胞增殖减少也可能是原因之一。研究还表明,应激诱导的前额叶(PrL)和边缘下(IL)皮质锥体神经元顶端树突萎缩,PrL和IL皮质Ⅱ层神经元密度降低及PrL和IL皮质Ⅰ/Ⅱ层体积减少。③其他新皮质区。应激导致了运动和听觉皮质区域的显著微观结构改变,发现了应激使大鼠的听觉皮层细胞外扩散率显著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神经轴突密度水平的中度增加,还观察到应激暴露大鼠的运动皮质显著变薄。④杏仁核。在应激暴露后,杏仁核有助于长期储存情绪唤醒和恐惧相关记忆,而海马和PFC与应激诱导的记忆恢复和工作记忆损伤有关,海马显著的树突萎缩和伴随的突触萎缩及杏仁核的肥大可能是这种对比记忆模式的重要基础。与海马相反,慢性应激暴露后杏仁核中BDNF表达增加。⑤大脑其他区域。缰核:缰核是一个小型的、进化上保守的大脑结构,位于上丘脑,在厌恶性加工中起着核心作用,应激易感大鼠内侧缰核的生长抑素-2受体显著上调。伏隔核:伏隔核位于腹侧纹状体,是介导奖赏和动机的大脑回路中脑皮质边缘系统的关键元件,应激诱导的快感减退与伏隔核中的树突肥大和中等棘状神经元的棘密度增加有关。视交叉上核:视交叉上核是下丘脑(视交叉正上方)的一小群神经元,通过与许多其他大脑区域的广泛相互作用,控制着昼夜节律的许多方面,在应激状态下,视交叉上核的分子节律振幅降低,这与情绪相关行为直接相关。
此外,研究证明了应激会导致大脑中MicroRNAs(miRNA)变化。应激可以改变大脑不同区域的miRNA表达。慢性束缚应激导致大鼠大脑的两个应激反应区域(海马CA1区和杏仁核中央核)的miRNA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大多数的变化是减少。相反,Rinaldi等〔4〕观察到急性和反复应激后PFC中miRNA表达水平增加。Higuchi等〔5〕首次证明海马miRNA在慢性应激诱导的抑郁样行为和神经可塑性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2 应激对心血管的影响
应激可导致心血管和自主神经发生变化,包括:血压和心率升高、心脏自主神经失衡、压力反射障碍及心脏和血管功能障碍。Kloner等〔6〕通过大量调查发现,应激会引起心源性猝死、应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脑卒中、心律失常、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此外,Lacey等〔7〕通过调查发现,严重应激会导致心碎综合征的发生。这种疾病也称为应激性心肌病(SCM),其特征是出现类似冠心病的症状,通常与经历过严重应激有关。各种应激源,包括重大地震等,都可能会造成这种疾病的发生。其机制主要与儿茶酚胺的释放有关。儿茶酚胺可增加需氧量(增加心率、血压和心室收缩力),同时有可能通过收缩一些血管床来减少氧气输送,导致冠状动脉痉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及增加血栓形成的倾向(增加血小板聚集和减少溶栓),这种供氧/供氧方式的不平衡会导致心肌缺血、心肌梗死,也会导致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Schwartz等〔8〕研究也发现,急性应激,无论是由工作压力还是地震引起的,都会导致斑块破裂、心肌梗死。主要是由于急性应激可增强交感神经输出、高凝状态和内皮功能障碍,可能导致易损斑块破裂,促进血栓形成,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3 应激对肝脏的影响
肝脏是人体应激机制的调节中心,应激增加了许多肝脏疾病的风险,如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等。Guo等〔9〕研究发现,在应激状态下,会造成肝脏中的铁蓄积,影响肝脏的铁代谢,从而使患肝纤维化、肝硬化及肝细胞癌的风险增加。Corona-Pérez等〔10〕研究发现,应激会加剧肝硬化和纤维化,其机制主要与氧化应激和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HSD)-1的高活性有关,应激促进了肝脏中大量糖原、炎症、轻度纤维化、氧化应激和11β-HSD-1的活性增强。此外,Spiers等〔11〕研究发现,应激增强了特定的肝脏抗炎途径,并调节枯否细胞极化,从而诱导整体促炎反应,其机制与M2巨噬细胞极化标记物的表达和趋化因子受体CXCR2信号的影响有关。此外,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应激也会引起肝脏损伤。Li等〔12〕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肝损伤频繁发生,通常表现为血清转氨酶的短暂升高,然而,患者很少出现肝衰竭和明显的肝内胆汁淤积,除非预先存在晚期肝病。其潜在机制可能与应激和全身炎症反应有关,在严重 COVID-19患者的心理压力条件下,缺氧/复氧、枯否细胞过度激活和氧化应激、肠道内毒素血症及交感神经和肾上腺皮质系统的激活等,都会造成应激性肝损伤。
4 应激对肺脏的影响
肺脏内富含巨噬细胞,应激时氧自由基或炎性因子使巨噬细胞发生活化,巨噬细胞活化后又会释放活性氧和其他炎症因子,造成肺脏损伤,因此,肺脏是应激时最易受损的器官之一〔13〕。应激时肺泡壁增厚,肺泡腔及间质内炎性浸润,肺内毛细血管中度淤血,造成肺脏受损。Rosa等〔14〕研究证明了在应激状态下,尤其是在产前和产后早期,会使儿童患哮喘的风险增加,其机制之一可能与胎盘有关,慢性应激可下调胎盘11-β-HSD-2,增加胎儿皮质醇暴露,增加的胎儿皮质醇激活胎儿应激反应〔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儿茶酚胺和神经营养素〕,诱导辅助型T细胞(TH)2细胞占优势(即易患哮喘的免疫表型),并改变自主神经系统功能。此外,Wright等〔15〕研究发现在围生期发育过程中,应激引起的相关系统(神经内分泌、自主神经和免疫系统)的破坏,可能导致儿童后期甚至成年期更容易发生呼吸道炎症和反应,肺功能降低。其机制与早期发育中神经内分泌功能的破坏,特别是HPA轴和自主神经系统(ANS)功能(交感神经-雌二醇失衡)有关。
5 应激对肾脏的影响
中医上说,肾储存精,五脏之精由肾封闭,持续的应激而不缓解会损害肾气和肾精,造成肾虚,肾虚会导致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变化,进而诱发疾病或某些疾病的易感性。Bruce等〔16〕研究发现,非裔美国人在生命早期被诊断为慢性肾病(CKD),并以比白人更快的速度发展为终末期肾病(ESRD)。其原因为种族主义、贫困、焦虑和愤怒等因素作为一种持续的应激源,加强了对人生存的限制,并导致更高水平的应激状态。其机制为持续的应激会增强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增加糖皮质激素的分泌,并可能增加炎症细胞因子的水平。这些因素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和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升高,而这些疾病都是CKD进展为ESRD的主要危险因素。此外,代谢交感神经系统产物的激素——肾酶的水平较低,因此,一旦CKD发展,长期应激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不受抑制地增加,从而引发恶性循环。Hudecova等〔17〕研究发现,应激增加了肾脏疾病发生发展,如急性肾衰竭。其机制主要与激素调节有关,应激导致儿茶酚胺的合成和作用大量增加,儿茶酚胺调节肾小球细胞功能,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升高,并增加细胞内钙活性,导致急性肾衰竭。
6 应激对胃肠的影响
Jiang等〔18〕研究证明应激可诱导结肠超敏大鼠的迷走神经活动,增强内脏的超敏反应。应激会导致胃出血和溃疡,肠黏膜充血,水肿,炎细胞增多等改变,人们会出现腹部不适、疼痛、腹泻或便秘。其机制与机体的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迷走神经兴奋性增高有关。也与5-羟色胺(HT)的分泌有关,5-HT是调节胃肠功能的关键单胺类神经递质之一,含有5-HT的肠内分泌细胞在肠黏膜中大量存在,并对管腔压力和各种化学信号等刺激作出反应。局部产生的5-HT与黏膜传入神经元和肌间神经元上的多种受体结合,启动分泌运动反应,可引起胃窦收缩、恶心和呕吐及肠分泌增加,最终导致腹泻〔19〕。Deng等〔20〕通过建立束缚应激实验表明,在束缚应激状态下,5-HT通过微生物-肠道-大脑轴使大脑和肠道发生交互作用。5-HT位于胃肠道和大脑中,在胃肠道分布较多。应激时,5-HT把信号从肠道发送到外部神经元和特定受体,通过微生物-肠道-大脑轴来调节大脑活动。
7 应激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脾脏是免疫系统内血液过滤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激能使脾、胸腺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增加、腹腔巨噬细胞(MΦ)释放H2O2功能下降、T淋巴细胞数量和增殖能力降低等。Wei等〔21〕研究发现,应激小鼠脾脏重量增加,进一步表现为造血干祖细胞(HSPCs)从骨髓迅速释放到脾脏,其中脾脏HSPC发展为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和红细胞,此外,CD11b+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也可在应激状态下积聚在脾脏中,导致脂多糖(LPS)诱导的全身炎症,更重要的是,从脾脏释放的免疫细胞或细胞因子随后可以渗透到其他器官,如大脑,从而导致大脑功能和行为的改变。Osborne等〔22〕研究发现应激会使脾脏免疫功能失调,影响免疫应答基因的转录,应激还会增加去甲肾上腺素上的β3-肾上腺素受体,增加骨髓白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释放(例如,白细胞介素-6),这些新释放的炎性细胞以前馈模式表现出促炎性免疫应答基因的高表达和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此外,增加的去甲肾上腺素通过β3-肾上腺素能受体与骨髓基质细胞结合,以减少CXC趋化因子配体(CXCL)12的产生,CXCL12的功能通常是将白细胞保留在骨髓中,这种应激增强了固有免疫细胞的输出,细胞因子的产生增强了动脉粥样硬化。同时,应激会降低抗病毒作用,其机制为糖皮质激素抑制抗病毒基因程序(如干扰素调节因子),儿茶酚胺通过刺激白细胞肾上腺素能受体抑制干扰素调节因子,从而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因此,应激诱导的免疫失调会导致更严重的炎症,同时降低免疫监视,从而促进了疾病的发生。Jiang等〔23〕通过模拟束缚应激状态,证明了应激促进了肝细胞癌的进展,并增加了血液和肿瘤组织中骨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的百分比,脾切除术可以阻止肝癌的生长,阻断应激诱导的MDSC增加。
8 应激对卵巢和睾丸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应激状态下,雌性动物表现为卵母细胞发育能力降低,产仔数量减少等。Pletzer等〔24〕研究发现,在男性中,应激后睾酮显著降低,睾酮水平在20 min后处于最低水平,但直到应激后35 min才恢复到基线水平,其机制可能与性激素和应激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Han等〔25〕在实验中证明了应激使大鼠体重减轻,发情周期延长,并改变了卵巢和子宫的器官系数和形态,发现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mRNA的表达降低,而促性腺激素受体mRNA的表达增加,卵巢与子宫中雌激素受体mRNA的表达也降低,其机制可能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内分泌调节有关。Lautarescu等〔26〕通过研究发现,产前应激会影响后代的大脑和行为,还会导致发育方面发生变化。例如,早产的风险增加,女孩月经初潮提前及端粒长度缩短,提示寿命缩短。研究还报告了产前应激会使免疫功能改变,哮喘风险的增加及出生时性别比的改变,出生的女孩比男孩多。这些变化可能与HPA轴在调节母体应激对胎儿大脑的影响中发挥作用有关。此外,活体脑成像研究报告称,还与边缘和额颞叶网络的变化及连接它们的功能和微观结构联系有关,结构变化包括皮质变薄和杏仁核增大。
9 存在问题与展望
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生活的压力不断加大,应激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Netta等〔27〕研究发现,长期的心理压力影响了年轻人的工作和休息,使许多疾病渐渐趋于年轻化。Lebel等〔28〕也证明了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应激源,加重了孕妇产后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应激的机制通常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糖皮质激素,Chen等〔29〕研究发现,在应激中,糖皮质激素通过影响核因子E2相关因子(Nrf)2-kelch样ECH联合蛋白(Keap)1-抗氧化反应元件(ARE)信号通路对应激发生作用;②儿茶酚胺:Pan等〔30〕证明了儿茶酚胺通过β2-肾上腺素能受体(ADR)阻滞剂/结肠癌转移关联基因(MACC)1信号轴加强了应激反应。当然,应激的机制肯定不仅限于这两方面。机体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特定的应激源,无论其来源如何,都会激活一个共同的神经和生理网络,应激对机体造成的影响,都会使机体的各个器官发生反应,例如,研究应激对大脑的影响时,5-HT会通过微生物-肠道-大脑轴使大脑和肠道发生交互作用,同时影响了大脑和肠道。因此,应激对机体的影响是一个整体的联动反应,在研究机制时,不应将其割裂开来,而应从整体方向上进行把握,这也会为后续的治疗提供一个很好的靶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