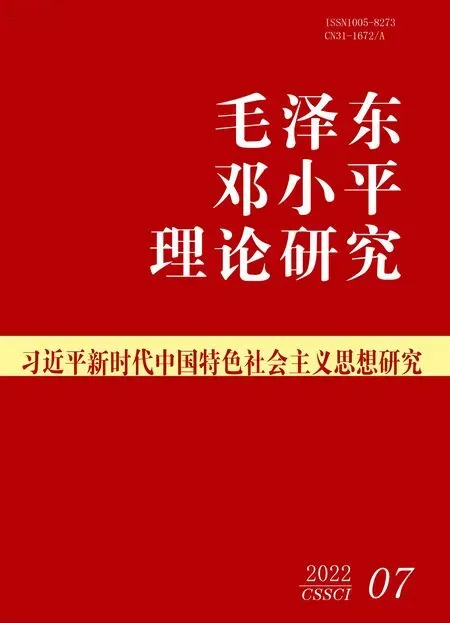社会主义必须有自己的文艺底色*
刘子杰
The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on ideology is usually potential and profound,and often imperceptibly makes people spontaneously identify with or resist certain ideas and values.In many cases,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through literature and art can be more effective than mere theoretical preaching and indoctrination.Socialist ideology determines that the literature and art produced in its dominant ide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distinct socialist undertones,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peoplehood,history and“weapons of criticism”.At present,we should be wary of trends such as the“depoliticisation”of literature and art,clearly understand the means by which Western countries attack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and constantly enhance our cultural confidence to ensure that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do not fade.
一、发挥文艺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
文艺对思想观念的影响通常是潜在而深刻的,往往在潜移默化中使人们对某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产生自发的认同或抵制。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均强调充分发挥文艺对于推动革命、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文艺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强调自身本质是“人民的文艺”,出发点和根本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相一致。与那些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表现主体的文艺截然不同,社会主义文艺始终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描写人民、讴歌人民,充分挖掘人民形象所蕴含的审美特质和思想价值,这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精神的艺术化呈现。第二,强调文艺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文艺以审美方式和形象塑造来表达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有利于让人民群众以审美的方式接受、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艺从不讳言文艺的政治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文艺创作与批评。作家、文艺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待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并从中提炼出创作素材且形成作品,这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文艺创作与批评,另一方面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能够具体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艺术材料,用审美和形象化方式感染、影响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在欣赏文艺作品过程中增进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在很多情况下,文艺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的效果比单纯的理论宣讲和灌输效果更为有效。
不同文艺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作用并不一样,社会主义文艺可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正面的推动作用,非社会主义性质文艺既具有正面作用,也具有消极作用。近年来,在文艺多元化思潮尤其是虚无主义思潮冲击下,非社会主义性质文艺的消解效应日渐显现。这股文艺虚无主义思潮“竭力消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甚至公开主张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可以说,文艺界屡屡出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恶搞历史、颠覆经典、过度娱乐化、盲目西化等不良倾向,从理论上挖根源,都与这股竭力消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甚至公开主张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有关”。[1]其实,文艺“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欺骗大众的话术,甚至会瓦解大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大众文化产业表面上打着文艺“去政治化”的幌子,其实意在消解大众的反抗意志。那些表面去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艺企图通过去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文艺去政治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冲击力不小,比如有些声音在鼓吹文艺不应是“从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产物;有些观点主张割裂文艺的审美性和思想性,鼓吹无思想的纯文艺和一味追求娱乐的俗文艺,试图淡化甚至去除文艺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
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事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区别社会主义文艺和非社会主义文艺,最为显著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文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底色。去除甚至抹杀社会主义文艺底色,正是文艺虚无主义冲击和消解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面对从未停止过的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冲击和消解,我们必须坚定立场,确保社会主义文艺不褪色。
二、社会主义有鲜明的文艺底色
文艺是通过审美形式表现的意识形态,主导文艺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文艺的底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在其主导的思想环境中产生的文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底色。
(一)人民性本质
第一,“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描写人民,尤其是人民中的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世界,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不是仅表现创作者个人情感和生活经验,应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立场。毛泽东曾批评过一些作品“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2](p.856)而文艺作品应“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2](p.857)习近平也对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要热爱人民”“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3]等一系列要求和期待。
第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者的人民性立场。社会主义文艺应歌颂人民,真实反映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真理。社会主义文艺是为人民的文艺,肆意攻击、污蔑、丑化人民是绝不允许的。关于这一问题,近来一种争议值得思考:文学究竟是揭露黑暗,只能批判的,还是可以讴歌呢?我们当然反对刻意夸大中国人贫穷和落后生存状态的作品,中国人民不是丑陋、愚昧的代名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创作不能批评缺点,我们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那些真正揭露问题而引起疗救注意的伟大作品,同样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本质的。比如鲁迅对国民性提出批判,但其本质是批判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封建思想文化,在他的小说里丝毫看不到为拔高具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而贬低贫苦百姓,鲁迅在创作内外也从来没有凸显自己所属知识分子群体之伟大的企图。毛泽东极为推崇鲁迅在作品中常常不用知识分子的眼光高高在上去看待、批评、教育普通人,而是把自己(在作品中表现为小说的叙事者)当成普通人民中的一员,即使在批评人民的缺点时,也将自己作为人民中一份子,一起批评一起反省。[4](p.454)鲁迅因其艺术成就、艺术品格和精神高度而被推崇为“文化旗手”“民族魂”“民族的脊梁”。当很多作家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立场渐行渐远,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必然难以见到真正的人民的身影,难以见到对劳动者的伟大赞颂。
(二)历史性特质
社会主义文艺要重视在历史维度[5](p.443)上反映社会历史的深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艺要反映现实生活世界,社会主义文艺作品要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表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深刻揭示历史真实,而不是仅表达个人际遇。[5](pp.578-579)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应深刻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产生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红色经典,如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创业史》《山海情》等。除美学意义上的成就外,这些作品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用文艺的手法再现了历史真实。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及作品评价和阐释共同再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在不断探索能够真实反映社会历史的创作手法。毛泽东曾强调“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艺术作品不能没有对将来的理想追求,要能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6](pp.121-122)1953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原则和最高批评准则。在随后关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受到推崇。无论哪种创作方法,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列宁的反映论为指导,以现实主义创作为核心,这样的创作自然以文艺对时代的真切反映为旨归。与更多关注个人内心世界、打破现实逻辑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相比,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更注重对外部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真实还原,从创作方法上保证作品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基本特质。由此,我们能够看到文学史记录下一批反映革命斗争历程和新中国巨变的优秀作品。
(三)“批判的武器”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文艺的“批判的武器”实质。理论通过说理的形式让人民群众接受,就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文艺通过形象和情感也可产生这样的效果。
文艺作品如果能揭示出人民群众生活世界的真实,就会对压迫人民的因素产生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济金根》《城市姑娘》等文艺作品时,指出这些作品应该对造成人物悲剧的深层因素进行更全面深刻的剖析,[5](pp.438-444、589-592)这正是对这些作品寄托了这样的期望:通过真实描写和深入剖析成为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的武器。许多中国的优秀文艺作品描写了底层中国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对压迫人民的各种因素进行批判。比如鲁迅的小说通过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尖锐批评了压迫和愚弄人民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茅盾的《子夜》通过描写民族资本家的遭遇,批判了金融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巴金的《家》《春》《秋》通过描写一代青年的情感经历,批判了封建家庭对个体的迫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左翼文艺、无产阶级文艺及其他进步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特质,作为“批判的武器”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和错误观念侵袭的过程中继续显现出批判的力量。
三、抵御错误思潮、确保社会主义文艺不褪色
(一)清醒认知西方国家攻击社会主义文艺的手段
第一,建构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文艺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冷战期间,美国以“新批评派”为基础,结合象征主义、结构主义等文艺理论建构了一套文艺理论和文艺评价体系。之所以把这套新体系的建构主体说成“美国”而非美国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因为那些研究者大都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并按照美国政府意图来进行理论建构。①参见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万芷均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而且,这套理论体系的目的和效果都与美国政府文化冷战的目的一致,从表现形态上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文艺理论针锋相对。比如,美国的这套新文艺理论体系强调文艺理论应回到作品文本内部,文艺研究和评论应抛开外部的社会历史因素,而专注于文艺作品本身。这种主张文学应专注于文学本身的理论的实质是切断文艺作品和外部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因循这种逻辑,那么文艺和人民、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社会主义文艺通过揭露社会现实表现人民生活状态,进而批判剥削阶级这一最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头疼的“批判的武器”功能就丧失了。文艺的人民性、社会历史性、批判性底色也会随之被去除。虽然宣称回归文艺本身的“去政治化”,但其实美国这套新文艺理论体系本身就包藏着宏大的政治目的,他们所有的理论主张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
这套理论体系隐秘地规定了文艺评价的标准:专注于文艺本身的作品是好作品,和外部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联系过多的作品不是好作品。于是,在这一文艺理论体系指引下,有观点打着“去政治化”“回归文学本身”的幌子,对“鲁郭茅,巴老曹”等新中国成立后被确立文学史地位的现代文学大家及其他左翼作家作品进行贬低性评价,尤其是对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为文化旗手的鲁迅极力贬低,认为鲁迅小说结构机械、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作品水平不够高,指出中国现代作家水平不高的原因是“Obsession with China”。“Obsessio”的原意是“精神不正常地迷恋于,执迷于”的意思,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即认为鲁迅及左翼作家不正常地执迷于国家政治,导致小说创作水平不高。这类观点所用手法正是前述美国建构的文艺理论之基本路数:声称回到文艺本身,切断文艺作品的社会历史联系,宣称政治会损伤作品的文学性,进而贬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系紧密的作家作品,抬高自由主义作家的地位,借此重新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述论调是美国文化冷战的产物,[7]目的是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攻击。有国外文学研究者指出这类论调对鲁迅作品评价失之偏颇,虽声称“去意识形态化”,但自己却恰恰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8]然而国内却有部分人误以为这是按照纯文学标准重新评价文学史,有些人认为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文艺作品是因与政治紧密关联才被赋予文学史地位,实质水平并不高,因而对这些作品产生厌恶,转而推崇那些专注于写个人体验、社会主义底色消退的作品。由此我们的少数文艺创作者主动选择切断与现代文学史上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优秀作家之间的联系,那么文艺创作的底色自然会消退。
第二,在大众文化市场利用资本逻辑推行“伪人民逻辑”“伪纯文艺”逻辑。大众文化市场被资本逻辑所主导,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利用这一点企图抹杀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底色。资本逻辑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一方面压缩成本,因而出现了“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另一方面想多卖钱,因而迎合大众趣味,出现了“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利用资本逻辑去迎合大众搜奇猎艳的心理,推动“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9]的作品出现,这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历史性底色造成了极大冲击。
在这一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本来的含义是文艺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资本逻辑却将之歪曲解释为文艺要迎合大众趣味,甚至低级趣味。此外,资本逻辑利用“伪纯文学”的学术逻辑,那些被“去政治化”、回归“纯文学”理念充斥头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的经典作家作品怀有厌恶情绪的研究者有意无意中成为“帮凶”,协助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引导大众喜爱那些抽去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的“纯文学”作品,排斥那些生动反映政治、历史的作品及具有现实批判色彩的作品,由此“三俗”作品和反映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品不断出现。
(二)增强文化自信、坚守文艺底色
虚假观念往往把自己包装得像真理,有些人被西方文艺理论欺骗而不自知,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因为和政治关系紧密所以艺术水平不高。然而,他们相信的那一套主张文艺脱离政治的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比如,一开始美国新批评理论主张“文学科学化”,认为应去除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中的主观感受,按照一套所谓科学的程序流程来进行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他们原意或许是希望能够建构一套看似科学的文学研究流程体系,然后把文艺作品纳入这一体系,得出有利于其政治目的的结论,然而最终未能如愿,以至于后来美国文学研究者放弃了“文学科学”,转而强调文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欣赏,因为只有强调主观性,才能按照他们的政治意图来研究和阐释作品。而“文学科学”却在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流行的理论潮流,[8]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对“文学科学”的接受和认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自信:社会主义文艺是经得起检验的。
文艺“去政治化”思潮流行之初,张爱玲等作家被抬高,“鲁郭茅、巴老曹”遭到贬低,有文学评论家表达了不同意见:要注意张爱玲作品中存在的无精神追求的虚无和浅薄,尤其要警惕很多人竟然把这种浅薄当成深刻;鲁迅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所达到的深度远超一般作品;我们对巴金作品还没有很好地阐释,如果阐释好了会成为我们重要的思想资源;茅盾的作品中有非常优秀的因素存在,但以往的评论者没有充分注意;曹禺的《雷雨》是一部伟大的作品。[10](pp.63、140-141、344、193)这带给我们一定的启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所做的主要判断和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谓“文学性”和“政治思想性”并不像有些别有用心的“纯文学”鼓吹者所言那般截然分离。我们不能也不应被打着各种幌子的文艺虚无主义引上歧途,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文艺道路。
——河北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