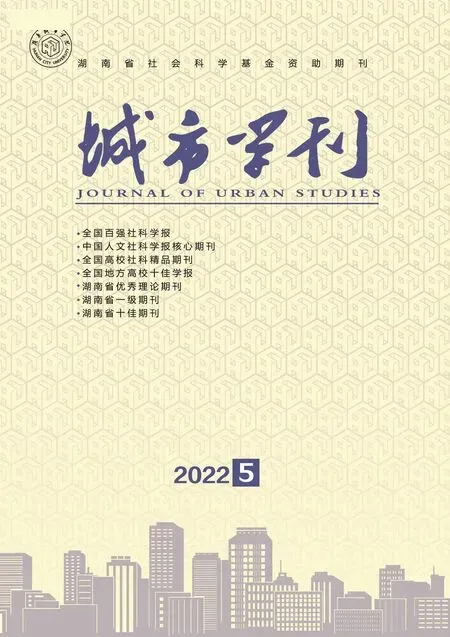周立波小说语言研究
赵炎秋,张 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长沙 401181)
20世纪40、50年代,土改与农业合作化成为中国的时代主题,反映土改与合作化的文学作品很多,但很多作品只是单纯地歌颂这两大主题,将文学作品变成图解党的政策的宣传品。但也有一些作品,成功地将政治与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时代的风云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经典,至今仍有重大的意义。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就是其中代表。周立波小说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语言的运用。分析周立波的小说语言,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他小说语言的风格与特点,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其小说成功的经验与原因。
一、普通话与方言的有机结合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批评部分文艺工作者“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周立波是《讲话》精神的坚定实践者。他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暴风骤雨》描写北方的土改,大量采用了北方农村的日常语言,《山乡巨变》表现南方的合作化,大量采用了南方农民的日常语言,而且用得生动、纯熟。而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又没有受到方言的拖累,作者巧妙地把方言与普通话结合起来,并以普通话为基调,将二者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种有机结合是周立波小说语言的重要特色之一,可从两个方面理解。
其一,普通话的通达与方言的神韵相结合。周立波对方言的重视源于他对民族形式的探讨。他到上海的1928年,正是从“五四”新文学到革命文学运动的转向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论争,促使他思考民族形式的问题。1930年他就在《大众文艺》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征询意见中提出:“每期要发表几篇很精炼很平白的普罗文艺论文,把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树立起来。”[2]不过,在上海时期周立波“以文学评论和翻译为主”,[3]他真正走上“本土化”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在延安时期。延安整风运动和《讲话》对他的小说语言影响深刻。他曾说:“毛泽东同志要大家树立一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使用有力的语言是重要的手段。”[4]对周立波而言,在小说创作中加入方言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他认为,方言是“活的语言”,[5]因此“在创作中应该继续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使用地方性的土话”。[2]544方言是特定区域的人民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语言系统,是当地民众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相较于普通话而言,更具地方色彩,更能反映方言地区人们的生活与精神风貌。周立波选择方言写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应当注意的是,周立波不是孤立地使用方言,而是将其与普通话结合起来使用。周立波认识到方言写作会给方言区外的民众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他的解决办法是将普通话与方言结合起来。他从两个方面实施这种结合。首先是物理层面,周立波在创作中采用三种策略:一是避免使用方言中的冷僻字;二是对可能读不懂的词语加注释;三是反复使用,让读者熟悉。[5]通过这些方法,一定程度上使方言有效融入普通话的基调之中。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功能层面。小说为了获得通行的意义,不能单独使用方言写作,还须依靠通行的普通话。因而,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使用要向普通话靠拢,遵循普通话的规范。用周立波自己的话就是:“在创作上,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语,我们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要经过洗炼。”[2]545这种洗炼既是如前面提到的对方言的物理加工,更是对方言的“普通化”。可以说,周立波小说中的方言是普通化的方言,而非纯正的未经加工的方言。这是艺术创作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方言的使用遵循普通话的规范句法和结构,也就是书面语的表达规范;另一方面小说文本中取消了方言的语音。方言独特的读音是它区别于其他语言的根本特征之一,周立波认为,方言与普通话相比较,普通话是“写在纸上的汉文”,“是全国一致的方块字”,它是统一的,而方言“却非常之多,非常之复杂。特别是南方,不但省和省之间的口音有重大的区别,有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县和县之间的口音,也各不相同。”[2]545方言读音的分散性导致普通话与方言就同一概念通常有不同的读音。周立波巧妙地利用了纸上的方言没有读音这一特点,让方言在文字上尽量向普通话的文字靠拢,向普通话的句法和结构靠拢,从而拉近了方言与普通话的距离,较大程度地增强了方言的可理解性。如“霸蛮”一词就是根据方言的读音,用普通话的文字形构的方言词汇,它也可写成“拌蛮”或“巴蛮”等。周立波小说中的方言统摄于普通话,是对普通话的有益补充和丰富。二者的有机结合使小说语言既获得普通话的规范意义,又不失方言的神韵。
其二,普通话的全局性与方言的地方性相结合。方言虽然生动,但毕竟局限于一隅,而普通话是全国通用。将二者结合起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长处,回避各自的不足。放在当时的语境中,这种结合实质上牵涉到文学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20世纪40、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文学创作除了要有艺术性,还需要平衡好与政治的关系。周立波曾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文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这个方向不容许改变。我们要终生坚持这个方向。但要更好地服务,就必须把文章写得好一些,把小说的艺术性提高一点。”[6]在他看来,文学创作中的政治与艺术并行不悖,要突显创作的政治性,就更应该提高小说的艺术性。使用普通话与方言结合的方式既是提高小说艺术性的一种手法,也是调节政治和艺术关系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周立波个人倾向运用方言进行创作。他在谈写作时说:“我欢喜农民的语言”,并认为相较于长期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农民的方言“生动得多”。[2]566这种语言倾向也成了他的艺术风格和标志。另一方面,周立波是一位《讲话》色彩浓厚的当代作家,对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兵文艺”规范持热烈拥抱的态度。这进一步促使他选择地方性突出的方言进行创作。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的需要,文学的任务从延安时期局限于解放区的“普及与提高”,转变为全国范围的政治宣传与教育,消除语言壁垒使文学在更大范围内配合政治宣教,自然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普通话因而具有政治全局性的价值。周立波支持推行普通话,但不认为在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会阻碍推行普通话,他觉得这是有益无害的。他说:“采用方言,不但不会和‘民族的统一的语言’相冲突,而且可以使它的语汇丰富,语法生动,使它更适宜于表现广大人民的实际的生活。”[2]544他认为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要积极保留方言中有益的词汇和成语,保持普通话的全国性和方言地方性在作品中的有机结合。
在作品中,周立波小说普通话与方言的结合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小说文本中夹杂一些方言词汇。如在《暴风骤雨》开篇的一段描写中,掺杂了植物“西蔓谷”(苋菜)、“苞米”(玉米),景物“草甸子”(低湿地),人物“牛倌”(专门养牛的人),动物“儿马”(没有阉割的公马)、“大牤子”(公牛),事物“轱辘”(车轮)等方言词汇,它们与普通话结合共同描绘出了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晨景。《山乡巨变》中也使用了如“堂客”(妻子)、“老驾”(父辈)、“伢子”(小孩)、“堂屋”(房屋正厅)、“溜沟子”(逢迎拍马)、“背时”(不走运)等方言词汇。周立波小说中普通话与方言的结合,既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又保留了地方性语言的神韵。
另一种是普通话与方言的互释。“互释”指互相解释,通过对话和描写的视角转换来描绘事物,塑造人物。小说文本的语言系统包括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两个子系统,周立波小说中人物语言基本使用方言,而叙述语言则基本用普通话。这样做既满足了塑造人物的需要,也满足了叙述明晰的需要,同时,也能起到转换叙事视角和突出人物性格的作用。如在《暴风骤雨》中萧队长一行人坐着老孙头的马车快到元茂屯的时候:
“快到了,瞅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咱们屯子!”
萧队长连忙抬起头,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7]12
在这段文本中,老孙头用“瞅”“黑糊糊”等方言简单地勾勒出元茂屯的规模,好似户户相连,占满了一大片土地。而萧队长抬头看到的情形则是用普通话描述:“烟云”“长列”“土黄色”“绿得发黑”等词,拓展了老孙头对屯子规模“黑糊糊”的方言描述,让读者对元茂屯的规模大小、排布形态、周边环境有一个直观、准确的了解。而且可以发现,老孙头对屯子的描述与萧队长视角中的描述有所出入。萧队长的描述无疑更接近事实,这从侧面表现了老孙头对家乡的热爱,在外来人面前刻意夸大自己家乡的规模。这样,在方言和普通话叙事视角的转换之间,突出了事物,刻画了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周立波的小说不止运用了一种方言,而是多种方言。如《暴风骤雨》中的东北方言,《山乡巨变》中的湖南益阳方言,都用得十分地道。说明了作家在运用群众语言上的努力,这得益于周立波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写作态度。
二、语言的形象性
高尔基曾说,“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写现实”。[8]文学形象是作家用语言材料形构的,它是作家通过组织语言材料,把头脑中的意象外化并定型为具象的产物。小说语言能否形象地反映现实,是小说艺术性的重要标志。周立波小说中的世界具体可感,各色人物生动形象,这与其小说语言的形象性有关。这种形象性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综合运用各种语言手段,塑造出生动、具体的形象。文学形象由语言创造。语言本质上是抽象的,文学语言要表现感性生活,塑造形象,就需要创作者通过各种手段,突出、放大语词中特殊具体的一面,从而适应表现具体特殊的生活的需要。[9]语言是一整套意义系统,它是公共的,意义是共有的、一般的。文学语言则不同,它是富有作者个性特征和审美倾向的表意系统,是基于公共语言系统之上开发的极其个人化的创造物,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言:“每一个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形态——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10]周立波小说中的形象生动、具体,具有独特的个性,这得益于他在塑造形象时使用了多种语言手段。
一是白描手法。周立波对民族形式的探讨,使其十分注重在小说中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手法,其中白描的使用就是很成功的例子。周立波小说往往用简练朴素的文字将人物“具体、集中、而又扼要地,用白描的手法反映出来”,[2]601以此塑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如在《暴风骤雨》中用白描描写老孙头惹得众人大笑的场景:
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连萧队长也笑弯了腰。小王笑得连忙擦泪水。刘胜笑得连连晃脑瓜,差点把眼镜子晃落。赵玉林笑得嘴里尽骂着:“看你这个老家伙。”郭全海笑得捧着小肚子,连声说道:“这可把人乐坏了。”李大个子一边笑,一边拍拍郭全海的肩膀头说:
“祝君快乐,祝君快乐。”[7]204-205
此段用短短一百余字就刻画出了一幅生动的笑态群像,可谓传神。这些笑的动作既切合人物身份,又突出了性格,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萧队长有责任在身,因而稳重,除了弯腰没有幅度过大的动作;小王年纪小,性格单纯,放肆释放自己的情绪因而笑出了眼泪;刘胜比较斯文,除了脑部动作没有其他肢体动作;赵玉林与老孙头同为农民又相熟,因而边笑边骂,不失豪迈和亲近;郭全海是青年农民,捧腹更显性格开朗;李大个与郭全海年龄相仿,动作更显亲近。
二是偏离手法。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区分为能指与所指,语言是一系列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因而能够准确传达信息。而语言的偏离手法,则打破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将能指引到另一个非常规的所指,形成错位效果,从而大大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也强化了人物的性格。例如,在乡政府开群众会时,亭面糊因躲进后房睡觉而被大家批评,他不紧不慢地回:“‘各位对我的批评,都对。’亭面糊顿了一下,吧一口烟,才又接着补上一句道:‘我打张收条。’”[11]62“收条”原指收到钱或物后作为凭据的条子,它是实在物,这里被偏离为虚化的“批评”,亭面糊幽默的一面就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
三是重复手法。这里的重复不是指语言内容上的重复,而是指语言结构的重复使用,指的是用若干个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态一致的短句成串延伸,以强化语言的表现力。周立波小说多处用到了重复的手法来刻画人物群像。如《暴风骤雨》中众人对工作队心怀疑虑时:
他们从玻璃窗户里,从破纸窗户里,从苞米高粱的密林里,从柳树丛子的背阴处,从瓜架下,从大车上,睁开惊奇的眼睛,瞅着工作队,等待他们到来以后屯子里新的事件的发生和发展……[7]77
在众人群情愤慨围攻韩老六时:
大伙从草屋里,从公路上,从园子里,从柴火堆后面,从麦垛子旁边,从四面八方,朝着韩家大院奔来。[7]176
实际上,这些重复句的结构都指向同一个事件,周立波用重复短句扩展了能指,用多个能指指向同一所指,形成集束效果,所有的能指都集中到一个所指,从而有力地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前一例子六个“从……”指向“瞅着”,生动地表现出群众对工作队只敢在暗处偷偷观望,不敢亮明态度的对待“革命”的情状,但也表明了群众对“革命”潜藏的期待;后一例子中六个“从……”指向“奔来”,表明群众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如雨后春笋一般开始从暗处走向明处参与“革命”,表现出群众觉醒后如暗流化为潮水一样喷涌出来的力量感。
其二,适当运用包括方言在内的生活化语言。浓郁的生活色彩是周立波小说的特色之一。在关于小说创作的论述中,周立波一再强调创作要深入生活,认为:“艺术的美,其源于生活。”[6]在他的创作理念中,艺术只有趋向生活,才能趋向美。因而在小说创作的语言使用上,他注意用包括方言在内的生活化的语言来增加小说的生活感和真实感。
最突出的是方言俗语的熟练使用。方言具有浓厚的生活色彩,是农民生产生活经验具体化的结晶。周立波曾这样表述方言的这一特征:“劳动的人们喜欢把生产过程中习见的具体的事物,用精练的语言构成生动的形象,夹在谈吐中,使得人们对于他们叙述的事情和行动,得到深刻的印象。”[2]546-547方言俗语是农民在生活中所见、所感、所想的集中表达,它把生活中真实或虚构的事物的能指重新组合,指向新的所指,生成新的意义体来强化某种情感,以此来塑造形象。如《暴风骤雨》中韩老六威胁老田头:
咱们哥俩在一起的日子也长了,哪有铁勺子不碰锅沿的呢?……
你要有本事,就甭听我的话,去跟工作队串鼻子,咱们骑在毛驴上看唱本,走着瞧吧![7]22
“铁勺子”“锅沿”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二者联系起来指向生活中炒菜的行为,炒菜中铁勺子和锅沿碰撞现象在这里被转用为邻里间闹矛盾;“毛驴”“唱本”指边走边看,指向等过段时间看事情发展究竟如何。周立波小说中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方言俗语的熟练使用,恰到好处地为小说注入生活化色彩的同时,起到了表现人物情感、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哪有铁勺子不碰锅沿”表示一种希望互相体谅让步的语气,表现了韩老六对老田头的拉拢之意。“骑在毛驴上看唱本,走着瞧”则表示一种胸有成竹毫不让步的态度,表现了韩老六对老田头直白的威胁。态度反差也形象地表现出韩老六奸诈、伪善的性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术语的准确使用。农村生活的本质是生产,艰辛的劳作是农村的主题。周立波提倡深入生活的写作态度,长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他的小说语言带有泥土的气息。如《山乡巨变》中描述禾苗生长的情况:“去看了泡的禾种,来得风快,有些亮胸了。”[11]“亮胸”指发芽谷种的外壳开裂,肉质外露的生长状态,这一词准确、形象地表达出水稻种子刚刚破芽时的状态。又如《暴风骤雨》中对玉米产量的描述:“一垧一万二千棵,好地能打八九石,岗地也打三四石。”[7]32对当地玉米产量的量化描述,既表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也增加了小说的可信度和真实感,使得周立波小说中的农村世界真实、具体,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其三,用语言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塑造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心课题,周立波认为:“典型的创造是一切文学的一个最大任务。”[12]典型人物不仅具有普遍性,更要显出各自的特殊性,也就是鲜明的个性。周立波小说塑造了萧队长、老孙头、亭面糊、陈先晋、刘雨生等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与他主张人物的语言要符合人物性格有密切关系。他认为“描写人物的对话,要根据他们的阶级特征和个人性格,设身处地,摹拟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倾吐的语言”。[2]598-599因而周立波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辨识度很高,似乎闻其言就知其人。《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老孙头是典型的老一代农民,身上交织着多重性格。一方面,他骨子里痛恨地主,由衷地拥护土改,另一方面,他与赵玉林等已经觉醒的先进农民相比,又有性格的局限性,他自私、软弱、胆小怕事、又好吹牛、好表现,这些我们都能在他的言语中体会到。
例如,在选马情节中,选马前,老田头问他的意向,他故意说“还没定弦”,其实是怕说出来自己心仪的马被人选走。选马后,当有人取笑他挑了个瞎马,他卖弄道:“这马眼瞎?我看你才眼瞎呢。这叫玉石眼,是最好的马,屯子里的头号货色,多咱也不能瞎呀。”在老王太太重新挑选马时,他在一旁时不时插话:“就怕儿马性子烈,她管不住。……看上我这破马?我这真是个破马,性子又烈。……这马到哪里都是个扔货,要不是不用掏钱,我才不要呢。”当老王太太没挑他选的马,他没等她选好就翻身上马,一面说道:“你不要吧,我骑走了。”说罢,头也不回地跑了。[7]457-462这些语言形象地表现了老孙头有心机、好吹牛、好表现、自私的性格特征,也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冲突。一方面,他受“革命”的影响,集体意识有所觉醒,私有的观念开始松动,因此在看到大家都愿意让出自己选的马让老王太太挑选时也肯参与。另一方面,小农思想是老孙头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新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限,因此他不如青年农民那样觉悟得彻底,原有的小农思想在他身上还若隐若现,表现出了老一代农民在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内在矛盾。周立波小说用极其个性化的语言挖掘出人物的这一矛盾,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又真实可信。
其四,注意语言的使用语境。周立波小说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真实可信,除了他们说的话符合他们的性格之外,还在于人物的语言符合事情发生的特定语境,也就是说,人物的语言始终与语境保持一致,符合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如《盖满爹》中盖满爹与儿子松森、楠森谈判加入合作社的情节:
两年多以前,这个村子组织了一个互助组,松森和楠森都不肯加入。松森劳力强,怕人占他的便宜。楠森不知听了哪个人的话,说“互助组是乱弹琴,搞不出名堂”。两年以来,互助组搞得还不错,组员都增加了收入,上级批准转社了。松森和楠森还是不干。有人讲怪话,说主任自己的崽也都不加入,农业社一定是软场合。盖满爹连忙亲自回家动员自己的儿子。
“我们何解要入社?要说社好,没看见过,我总不信服。屋门前这几丘田,阳光、土质都蛮好,又挨得近,我一个人作了,松松活活……”
“你一个人作了这几丘豆腐干子田,将来好用机器吗?”盖满爹问他。
“机器还是洞庭湖里吹喇叭,哪里哪里。”松森又说。
父子争论一阵,临了松森说:
“你说社好,我说靠不住,我们比比看,我一根棍子一只碗,高低要藤死几个县官子。”
楠森年纪轻,不谙事,对父亲更为放肆,也更横一些。谈判一阵,他说出了一堆牛都踩不烂的话:
“爷爷,你家里百事不探,净想作官,做了主席还不够,又当主任了。你手指脑往外边屈,一心想怂我们上当。”
“畜生,忤逆子!”盖满爹气得咬着牙齿骂。[13]
这段的叙述部分预设了谈判的语境:父子之间因不同考量,对是否入社存在矛盾。人物的对话则围绕这一语境展开。对松森而言,他“劳力强,怕人占他的便宜”而不愿入社,但不愿忤逆父亲,因而假称是因为自己田好不愿入社。对于楠森来说,因为年纪小轻信他人说“互助组是乱弹琴,搞不出名堂”而不愿入社,又不愿表露自己的真实原由,用更加放肆的话回绝父亲。而对于盖满爹而言,“有人讲怪话,说主任自己的崽也都不加入,农业社一定是软场合”,这是他动员儿子加入合作社的第一动因。他是乡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为了让人信服好开展工作,需要自己的孩子也入社以支持他,因此在儿子以理由拒绝入社时,他一再反驳他们。但实际上,“生气的时候,他恨自己的儿子太忤逆,太丢人。等到气一消,他又看出他们讲究实在的特性了。”[13]这就说明松森、楠森拒绝入社的理由在盖满爹看来实际上也成立,表明当时盖满爹是出于自己的诉求有特意反驳两个儿子的意图。这样,三人的语言符合特定的语境,显得合理自洽,人物形象也更加自然、真实。
三、语言的张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周立波小说语言的再一特色是语言的张力。张力原指物理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所形成的紧张平衡状态,就小说语言而言,张力就是不同语言的内涵与外延在矛盾对立中达到稳定与统一。语言是文学的重要元素,语言的张力必然会给文学作品深厚的内涵和艺术的美感,提高文学作品的成功度。周立波小说用多种方式形成、扩展语言的张力,这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从语言本身来看,周立波小说语言内含通俗与高雅、直白与诗意、方言与普通话的对立统一。周立波小说语言的成功之处在于,既成功地设置了语言的对立关系,又很好地把它们统一在一起。
首先,通俗、高雅的对立统一。中国的文艺发展史上向来存在两种文艺审美倾向,一种倾向高雅的审美,另一种倾向通俗的审美。有学者认为:“‘雅俗’之‘俗’既关乎人,指与文雅之士相对的流俗粗鄙之人,而更多的则关乎文艺和审美。”[14]的确,不同的阶级潜含着不同的文艺审美倾向,形成不同的审美意识。就文艺的语言而言,高雅文艺注重突破语言的工具性,关注语言的内在魅力;通俗文艺的语言更趋口语化或程式化,没有特别的叙事技巧。[15]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信息的交流,高雅语言则力图打破这种工具性,走向“陌生化”,也就是语言的深度意义;而通俗语言则工具性较强,追求语言信息的通俗易懂,以满足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周立波小说语言很好地平衡了高雅语言与通俗语言,他的小说既偏爱用通俗的语言创造通俗易懂的表达效果,也注重用叙事技巧挖掘语言的内在魅力,获得深层次的意义。如《暴风骤雨》中赵玉林评价韩老六:
他吗?人家说:“好事找不到他,坏事少不了他。”赵玉林说。他的脸蛋衬着确青的黄瓜的叶蔓,更显得焦黄,两束皱纹,像两个蜘蛛网似的结在两边眼角上。[7]38
“好事找不到他,坏事少不了他”通俗易懂地勾勒出韩老六无恶不作的形象。用确青的叶蔓和焦黄的脸蛋对比,表明赵玉林健康不佳,用蜘蛛网比喻眼角细密交错的皱纹,其中的“脸蛋”一词一般用于形容年龄较小的人,这进一步与眼角密密麻麻的皱纹形成强烈对比,说明赵玉林尚且年轻就已满眼皱纹,显示其生活的艰苦。无声地控诉了韩老六对农民的剥削,彰显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直白与诗意的对立统一。直白趋向实指,诗意趋于虚指。在周立波小说中,实指是指词语表达的写实义,虚指是指词语诗意化的隐喻义。这种隐喻义是通过一定的语境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离开特定语境,写实词语只有写实义,而在语境中则另具隐喻义。如《山乡巨变》中陈大春和盛淑君第一次夜间幽会:
晚上的月亮非常好,她挂在中天,虽然还只有半边,离团 还远,但她一样地把柔和清澈的光辉洒遍了人间。[11]179
这段描写中的词语单独来看几乎都是写实的,所表达的语义直白明了。不过,从整体来看,这些直白的词语,经作者恰当地组合形成特定的语境——互有好感的青年在月光下的幽会,写实的词语也因此富有了隐喻义。这一语境中的月亮被诗意化,它一方面隐喻时间,更重要的是隐喻人物的情感。“非常好的月亮”寓意盛淑君因要与意中人第一次接触而心情极佳,“挂在中天”点明了时间为半夜,“只有半边”“离团 (月圆)还远”“光辉洒遍人间”则寓意盛淑君的感情状态。从小说有限的视角来看,盛淑君对陈大春的感情目前还处在单相思的状态,离圆满还远但充满希望。语言的写实义与隐喻义构成了语言的内在张力,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意境。
再次,方言与普通话的对立统一。在周立波小说中,方言指向农民的话语,而普通话指向知识分子的话语。周立波小说存在知识分子话语的“农民化”,即用农民的话语来解构普通话的本义而生成置换义,形成语言的张力效果。如亭面糊上初中的儿子勤奋好学,亭面糊时常揶揄他,要他回来“住农业大学”。“农业大学”本义是指培育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在这里被“农民化”,用农民话语中的“农业”这一定语遮蔽“大学”这一中心语,指向辍学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学习就被置换成劳作,极具语言张力。
其二,从语言内涵看,周立波小说语言具有很强的对话性,形成复调的效果。这首先表现在语言中具有多种意识形态的声音。政治是20世纪40、50年代小说写作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周立波同样重视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不过他的小说创作坚持政治意识形态应当遵从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一方面,遵从从文本出发的态度,合理地展现意识形态,而非简单地置入意识形态来规训文本创作。周立波的小说多以重大政策为背景,如《暴风骤雨》的土地改革运动,《山乡巨变》中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但是,他并没有让政策话语掩盖小说内在的叙述话语,政策在小说中作为叙事的起点和主线,但是小说叙事话语则表现出对政策的相对偏离,走向生活化的叙事。另一方面,小说遵从小说人物的身份、性格逻辑上的独立性,表现为小说人物的多种意识话语的共存,呈现出“复调性”的关系。巴赫金这样界定“复调”:“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16]周立波小说的文本呈现众声合唱的局面,每个人物都从自己的个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互相交织又不被遮蔽,都能在文本中得到完全的保留。因而,他的小说人物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由性。
这种复调一方面表现在不同人物之间多种意识的共存对话。如陈先晋、秋瓜丝等传统农民与陈大春、刘雨生等新农民之间,传统的乡土意识塑造了传统农民的个人意识,土地私有是埋在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思想。而陈大春等新农民对新政策抱有强烈的热情,本能地抵触传统的土地私有观念,认为是过时的、落后的。因而当他们面对新的土地公有的政策时,陈先晋本能地依据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进行判断,首先想的是维护个人的土地利益,这就与陈大春等新农民产生意识上的矛盾。小说用十分理性的叙事去理解、包容、尊重不同的个体意识,写出了他们之间本能的抵触,甚至是对抗。但是,小说始终没有将这种对抗视作叙事的主流,而努力展现思想矛盾在对话中走向统一。
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内部多种意识的共存对话。比如邓秀梅在政治上是一个“外来者”,她的第一身份是干部,是政治意识的代表。当在入乡的路上看到土地庙所书的“天子入疆先问我,诸侯所保首推吾”对联,心里本能地用政治意识对它进行了批判:
“天子、诸侯,都早进了历史博物馆了。”
接着,她又想道:“这副对联不也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11]7
土地庙在乡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乡村意识的重要象征。邓秀梅作为一名干部,会自觉地从政治意识的角度批判象征传统乡村意识的土地庙,并从合作化的角度,用土地公有的政治意识解构土地私有的乡村意识。但是在政治身份之外,在情感上她又是一个“同乡者”,小说中有多处说明:“她本来是位山村角落里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11]6“邓秀梅生长在乡下,从小爱乡村。她一看见乡里的草垛、炊烟、池塘,或是茶子花,都会感到亲切和快活。”[11]15作为“同乡者”的邓秀梅又会在工作中不自觉地暂时下放政治意识,回归农民意识,主动去了解农民的心声。小说并未因为邓秀梅的干部身份和政治使命就把她束缚在政治意识一隅,而是给她充分的成长空间,赋予她多种意识形态,在多种意识对话中突显出语言的张力。
其次,表现在人物思想的矛盾与纠缠。多种意识的对话在人物身上表现为多种思想的冲突。周立波的小说选择让政治意识与农民意识进行对话,刻画了小说人物面对历史事件时,游走在多种意识之间的思想的矛盾与纠缠,让周立波的小说充满宏大叙事下的历史真实。比如农民干部刘雨生,他作为干部性格比较软弱,又过于善良,因为怕与漂亮但思想落后的妻子离婚,起初对办社也犹豫不决:
他心里想,组还没搞好,怎么办社呢?不积极吧,怕挨批评,说他不像个党员,而且自己心里也不安;要是积极呢,又怕选为社主任,会更耽误工夫,张桂贞会吵得更加厉害,说不定还会闹翻。想起这些,想起他的相当标致的堂客,会要离开他,他不由得心灰意冷,打算缩脚了。
同时,作为一名农村干部,政治意识在他心里已经萌芽。因此,他会自省,逐渐坚定了干部的政治身份赋予他的责任:
“你是共产党员吗?”他的心里有个严厉的声音,责问自己,“入党时节的宣誓,你忘记了吗?”
开支部会时,听了邓秀梅的报告,刘雨生回到家里,困在床上,睁开眼睛,翻来覆去,想了一通宵。一直到早晨,他的主意才打定。他想清了:“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11]52
小说无疑批评了刘雨生性格中的软弱成分,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种个人意识,而是让角色自己与自己对话,让个人意识与政治意识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刘雨生的个人意识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让渡给政治意识,从而达成了个人意识与政治意识的和解。可以说,正是因为细致地把握了多种意识形态对刘雨生造成的思想矛盾与纠缠,才形塑了一个自然形象、有血有肉的农民干部形象。
周立波小说中多意识的共存、对话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洪子成认为:“在50到70年代,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统一性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但在某个时候、某些作家那里,时或有偏离规范的‘异端’现象出现。”[17]这里的“规范”可以理解为时代的主流政治意识。周立波的小说创作就存在对主流政治话语偏离的“异端”现象。黄秋耘曾这样评价《山乡巨变》:“《山乡巨变》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阶段中的复杂、剧烈而又艰巨的斗争,似乎还反应的不够充分,不够深刻,因而作品中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18]这在当时是对周立波小说评价的一极。不过,这一极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则是一种恰当的艺术表现策略。茅盾就曾这样评价周立波的小说创作:“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地确立起他的个人风格。”[19]周立波的小说创作饱含对民族形式探求努力,他对主流政治意识的偏离并非现实的偏离,而是艺术表现的一种个性化策略。因而这种偏离并非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可消弭的差异,而是一种个人艺术风格带来的表述偏离,其实质是对话的。正如周立波自己说的:“在作品中保持政策的立场,要靠作者平时的思想修养,而党的领导机关的关心和指导,能起决定的作用。作者的任务还得把政策思想和艺术形象统一起来,千万不要使作品的形象和政策分家,使政策好像是从外面加进去似的。”[2]566他承认政治意识对于艺术创作的重大影响,但是政治意识和艺术思维需要调和、对话,这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更是艺术创作的要求。周立波小说中的对话关系,正如有的学者说的那样,“既是为了维护当时主流思想观念,又使之保持适度的平衡,不致在文学政治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20]周立波小说语言的对话关系,成为他调和政治与艺术、个人与国家、民族与形式的策略,也构成了其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客观上,形成了时代与个人、政治与艺术、民族与风格的二元张力。
对语言的成功驾驭是周立波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周立波小说语言的成功反映了作者向群众学习语言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尽量让作品接近日常生活、日常人性,不执着于一种固定的意识,也不执着于当下通行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成功的文学作品。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认真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