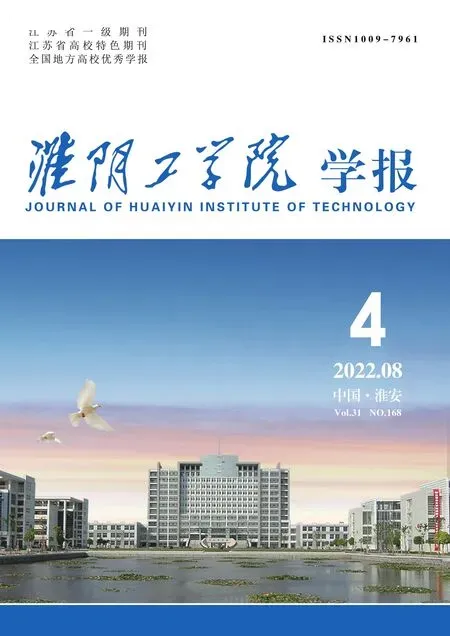越南燕行使者笔下的淮安
——以《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为中心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阮辉莹(1713-1789),越南后黎朝河静罗山人。景兴九年(1748)进士登第,赐探花,官至吏部左侍郎,封都御史。年七十致仕,赠工部尚书。阮氏于景兴二十六年(清乾隆三十年,1765)受命为正使,北行入岁贡。有八种著述传世,其中《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北舆辑览》《燕轺日程》为燕行文献。《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为阮辉莹于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一年(1766)所作的出使记录,该书以日记提纲挈领,缕叙沿途风光、接待规格、公务诸事,而于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记叙最详;每条日记后附诗一首至十数首不等,内容亦多为留连山水、咏怀古迹及与副使唱和之作,是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越关系史的重要史料。该书收录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5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影印出版。
清代越南来华使节朝贡线路主要以广西、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直隶的水路为主,阮辉莹使团亦是如此[1]。《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雍正二年议准,安南国贡使进京,广西巡抚给与勘合,由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山东、直隶水路行,回日由部照原勘合换给,仍由水路归国[2]。”具体路线是先由广西、湖南走水路至湖北武昌,再由湖北武昌沿长江水路东下至南京(当时称江宁),由南京渡江入扬州仪征,在此沿运河北上至山东济宁,在济宁上岸后乘车陆行,经山东、直隶境内至北京;回程则由北京陆行至济宁登舟,再沿运河乘船至南京,然后按原路返回国内。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南北交通咽喉,成为越南来华使团的必经之地。阮辉莹在其《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一书中,留下了众多有关淮安水工设施、水神庙宇和名胜古迹的记载,对于研究淮安水利史、城市史和社会史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为视角,结合地方志、文集等史料,对其所载淮安风物进行分析和考证。
1 阮辉莹所记淮安水工设施
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部,明清时期的淮安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会处,为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永乐年间京杭运河重新贯通后,淮安因其处于南北咽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正是由于淮安段运道黄、运交汇的特点及其在明清漕运体系中的重要性,使得明清时期淮安境内的黄运河工极为频繁,水工设施众多,这在阮辉莹的日记中亦有相关体现。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初六日,阮辉莹一行抵达清江浦。清江浦是淮安市主城区中清河、清浦两区部分地区的古称。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督理漕运,因漕船至淮安城北需盘坝过淮,转输甚劳,遂导水自城西管家湖至鸭陈口二十里,入宋时沙河旧道以达淮,名“清江浦”,并建移风、清江、福兴、板闸、新庄五闸,迭为启闭,节水通流,为漕运津要。明中叶以后,清江浦河运口常为黄河所淤,不通舟楫。成化年间,于清江闸置两坝,运船由此车盘过坝入河,清江闸南岸成为水陆孔道,建有船厂和漕仓,渐成集镇。清康熙时,河道总督驻此;雍正七年(1729),又为南河总督驻所;乾隆时,移清河县治于此。
阮辉莹在其《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对淮安清江浦的闸坝情况做了详细记载:“(十月)初六日,到清江浦,有清河县治,不设城郭。江口有龙凤闸,左碑‘清江正闸’,右碑‘清江越闸’。按:“明初都燕,难于漕运”,仍决黄河与淮河二水,入为头江,名曰里河,以通粮道。但水势冲击,上溯颇艰,于更改凿月河分流,名曰越闸。旁有御诗亭云:‘淮黄疏浚费经营,跋涉三来不惮行,曾几堤防亲指划,伫看耕稼乐功成’。今上亦有御诗刻于碑后,分差江南南河等处河道官统之于总督,辰加修治[3]。”
日记中提到的“清江正闸”,又名清江闸、龙王闸,系平江伯陈瑄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主持建造,为明清南北漕运必由之通道。越闸在淮阴市清河区南,清江大闸西北50米,是里运河分洪道越河水闸,清江大闸的副闸,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4]。《淮安府志》记载清江闸:“去治西北三十里,永乐十三年创建,官厅三间[5]。”《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九《川渎六·漕河海运》记载:“漕河在淮安府城南,永乐十四年,平江伯陈瑄疏浚故沙河置闸通舟,谓之‘清江浦’。今自城而西十五里曰板闸;又十五里曰清江闸,分司主事驻此,俗谓此为‘清江浦’;又十五里曰福兴闸,又十里曰通济闸,闸口即清江浦口,为漕河入淮之处,稍折而北,乃为清口,即黄淮合会处也[6]。”《大清一统志》记载清江闸:“在清河县清江浦,又名龙王关,明永乐中建,旧置分司主事驻此,今有闸官;其北有越河小闸,又南北岸有檀度寺闸,本朝康熙三十五年建;又南北岸有永利闸,皆减水闸也[7]。”《续纂淮关统志》记载:“板闸西十五里,即清江闸,又五里即福兴闸,又二十里曰新庄闸,此平江伯陈瑄所建四闸也[8]。”
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清江闸御诗亭有二:“一在南岸,康熙二十二年建,赐于成龙;一在北岸,三十八年建,赐张鹏翮[9]。”关于碑文的内容,阮辉莹记为“淮黄疏浚费经营,跋涉三来不惮行;曾几堤防亲指划,伫看耕稼乐功成”,而《四库全书》所收《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四十九以及乾隆《江南通志》卷首等均记为“淮黄疏浚费经营,跋涉三来不惮行;几处堤防亲指画,伫期耕稼乐功成[10]”。编校皇帝“宸翰”,《四库全书》当极为严谨,且有多部文献可互证,因此可判断《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记载有误,至于错误原因,可能是后来整理抄录时误写所致。根据阮氏的记载,乾隆皇帝南巡时,亦有御诗刻于碑后。根据学者考证,乾隆在清江闸所作的御诗共有8首,其中七言四句的“阅河”御诗均位于清江闸北岸,五言八句的“阅河堤”御诗均位于南岸[11]。
对运河岸边的镇水铁牛,阮辉莹亦做了记载:“由清江闸历福兴闸、通济闸、惠济闸,闸溯上三草坝山,山里河到外河南头坝,岸上有一大铁牛,铭云‘铁牛作镇奠淮阳,永除昏垫报吾皇’。俗传前代累朝筑堤不就,自铸得铁犀牛镇之,其堤立成[3]。”
日记中提到的“镇水铁犀”位于淮安市淮阴区赵集镇高堰村,东临二河,西为洪泽湖大堤,是现存七具铁犀中唯一没有挪动过位置的一尊,高堰铁犀长 1.73 米,宽 0.83 米,高 0.81 米,昂首屈膝伏卧在宽0.83 米,厚0.07 米的铁板底座上。铁犀与底座连成一体,总重2400 公斤,铁犀肩部有铭文曰:“维金克木蛟龙藏,维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铭文后有说明文字:“康熙辛巳年午日铸,监造官王国用。”高家堰大堤是洪泽湖大堤的北部,在整条大堤中地势最低、建成最早、历时最长,损坏次数最多,花费帝王、河臣的精力和经费也最多,治河大臣们在修建好石工墙之后,采用“五行相克”的原理,将一具镇水铁犀放置此处,期望镇水犀能够镇堤防浪,永保太平[12]。
张鹏翮《治河全书》记载:“康熙四十年,于旧大墩西接筑拦湖堤一道,长一百四十丈,内外排桩镶埽;又接建新大墩一座,周围三十五丈,逼清水七分,敌黄,三分济运;又于大墩下运河口门筑拦河坝,南北共长二十四丈,以御湖水异涨;置造铁犀一座,于新大墩上,以镇水势,刻词于犀曰:‘维金克木蛟龙藏,维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13]。”清人钱载《蘀石斋诗集》卷九所载《铁犀行》一诗云:“风声波声雨乍收,清口未得行吾舟,御诗亭左铁犀一,登岸突见苍蟠虬。维金克水土制水,纪年弗较铭辞优。铭曰:‘维金克木蛟龙藏,维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阳,永除昏垫报吾皇。康熙辛巳午日铸,监造官王国用’[14]。”《金壶七墨》卷五记载:“黄河堤上间数里则有铁犀一具,回首西望,逆流而号,以禳水势。戊申初夏,与邵剑波同谒鲁通甫师于清河之大兴庄,渡河就视,犀腹铸字云:‘维金尅木蛟龙藏,维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末镌‘康熙辛巳五月,监造官王国用’。至今戊申,百四十八年矣[15]。”宣统《续纂山阳县志》记载铁牛:“在武家墩高涧坝高家堰,为康熙年间河臣张文端公所铸,铸以五月五日,命曰‘镇水犀’,凡十六具,分置之地不尽属山阳。背有铭曰:‘惟金尅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16]。”民国《续纂清河县志》记载镇水铁犀:“在马头镇,康熙间,河督张文端公鹏翮铸,铸以五月五日,凡十六具,分置淮黄运各险工上,命曰镇水犀,不尽在清河境内。背有铭曰:惟金克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淮扬,永除昏垫报吾皇[17]。”根据相关史籍判断,阮辉莹此处的“淮阳”亦是较为明显的错误。
在淮安乘船北上宿迁的过程中,阮辉莹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其渡黄的经过:“(十一月)十一日,清河县取小船六只,卫递渡黄河,挽到中流,老班以船尾向前以济。……挽十里入支河到杨家庄,溯流而上,至杨家庄左岸接龙王庙,匾‘灵佑中河’[3]。”
阮辉莹在日记中提到“挽十里入支河到杨家庄”,这里的“杨家庄”指的是现在的淮阴区刘老庄镇杨庄村,为当时的运口所在地。康熙二十五年(1686),靳辅开挖中运河,上接皂河,下至清河县仲庄入黄河,穿黄河与里运河相接。后因仲庄闸出口处黄溜南行,倒灌南运口,且南北运口距离较远,漕船穿行困难。康熙四十二年(1703),将北运口改移杨家庄,是为“杨庄运口[18]”。自此,南来漕船出清口后,顺流行七里,即可入杨庄运口经中运河北上。康熙五十五年(1716),因杨庄运口溜急,又在杨庄闸口南挑越河250 丈,漕船俱走越河,时久以越河为正河,仍名“杨庄运口”。至此,北运口基本固定下来,至清末无显著变化。光绪《清河县志》卷六记载杨庄运口:“康熙四十二年移运口于杨家庄,并建御示石闸;五十五年,闸南开挑越河,长二百五十丈,漕船由越河行走,石闸遂废[9]。”光绪《淮安府志》卷七记载:“(康熙)四十二年上谕,仲庄闸紧对清口,有碍行运,于陶庄闸下挑引河一道,改从杨家庄出口,并建束水草坝三座,其后运道通利[19]。”《钦定南巡盛典》记载:“先是运道由清河县之上仲庄闸,出口形势未顺,有助黄灌清之患;康熙四十二年,皇祖南巡,指示形势,命于杨庄改挑运口,距仲庄闸十余里,在清黄交会下游,地势顺利,舟行称便,盖由圣谟独断,酌中定制,实为万世永赖也[20]。”
2 阮辉莹所记淮安水神祠庙
明清时期的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黄、淮、运在此交会,既是漕运必经之地,也是明清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使得当时淮安境内的水神信仰极为盛行。清河县因水患严重,河工频繁,仅金龙四大王庙就有17座之多。此外,据光绪《清河县志》记载,当时的清河县境内还有天妃庙、龙王庙、淮渎庙、风神庙、风湖大王庙、黄大王庙、栗大王庙、显王庙、张将军庙、卢将军祠等水神庙宇。
阮辉莹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清江浦的金龙四大王庙、风神庙和惠济祠等庙宇:“外河右岸有御诗亭,亭上有庯,庯有金龙四大王庙,匾‘安澜效祉’。按金龙神姓谢,会稽人,宋末勤王,大战于吕梁,见空中有神兵相助,夜梦天帝封为‘四大渎神’。沿右岸半里,有风神庙,碑书敕封‘清和宣惠风伯之神’。又有天后宫,上殿匾‘福佑河漕’,旁有皇帝行宫,匾‘风帆沙屿’。宫后有望黄河亭,抠衣登临,遥见水势湍奔,波涛似卷,中流清浊相间。回头里河中,帆樯戟列,隐然在突柳中,参差如画[3]。”
日记中提到的“金龙四大王”,名谢绪,南宋会稽(今浙江绍兴)诸生,谢太后之侄,愤于朝政混乱,不入仕,隐居于钱塘的金龙山。因其排行第四,隐居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南宋为元所灭,谢绪投水以殉。明太祖起兵,遇水战,谢绪的英灵曾骑白马率潮水助阵。明朝立国后,封其为“金龙四大王”,立庙于黄河沿岸地区。因其具有护漕、捍患的功能,多显灵于漕运和河工危难之时,故不断得到明清两代官方的加封。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载:“淮之清江浦金龙四大王庙,碑称姓谢氏,兄弟四人,纪、纲、统、绪皆宋会稽处士。绪最少。初为诸生,隐钱塘之金龙山。宋亡,日夜痛哭,阴结义士图恢复。知不可为,遂赴水死。题诗于石曰:‘立志平生尚未酬,莫言心事付东流。沦胥天下凭谁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问曰:‘公志决矣,他日以何为验?’绪曰:‘黄河水逆流,是吾报仇日也。’后明太祖与蛮子海牙战于吕梁,不利,忽见云中有天将挥戈,驱河逆流,元兵大败。帝夜祷,问其姓名,梦儒生素服前谒曰:‘臣谢绪也,宋祚移,沉渊死。上帝怜我忠,命为河伯。今助真人破敌,吾愿毕矣!’次日封为‘金龙四大王’,以绪尝居金龙山,殁又葬于其地故也[21]。”万历《淮安府志》记载大王庙:“在郡城外西南隅一里许,相传金龙四大王能捍御,祀之[5]。”光绪《清河县志》记载金龙大王庙:“在清江闸,康熙三十八年建,神姓谢名绪,宋文学,隐于金龙山,元兵入,赴水死;明初,封王建祠,国朝崇奉尤盛[9]。”乾隆《江南通志》记载大王庙:“在清河县东运河口,圣祖仁皇帝南廵时,御题‘安澜效祉’四字匾额[10]。”
乾隆《江南通志》记载风神庙:“在清河县口,康熙五十四年建,雍正十年重建,奉旨钦定封号‘清河宣惠风伯之神’[10]。”光绪《清河县志》记载风神庙:“在清口,康熙五十四年建,西向,雍正十年增修;乾隆十四年,总河高斌重建,南向,增大之,有御赐额[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四十三《礼部群祀·直省风雷诸祀》记载:“雍正六年,覆准洪泽湖口风神庙敕封为‘清和宣惠风伯之神’,遣礼部笔帖式一人,赍祭文香帛,交与河道总督致祭[22]。”《皇朝通典》记载:“又河臣齐苏勒疏言:淮安府清河县清口地方,乃洪泽湖水出口敌黄之所,从前建有风神庙,官民行旅皆致祭祷,至于洪泽一湖,诸水总汇,全赖高堰大堤以为保障。惟此堤工,最忌西风鼓浪,自昔传有‘日费斗金’之说,比年每逢大汛,从无西风,湖工平稳,转险为安,皆由我皇上念切民生,怀柔百神,感召天和之所致也。伏查水道河神,凡有捍灾御患者,俱蒙敇赐爵号,以彰神庥,惟兹风神,福国佑民,潜维默护,神功既懋,褒锡宜隆,伏乞一体敇封,以崇祀典。礼部覆议,从之,乃封为‘清和宣惠风伯之神’[23]。”
日记中提到的“天妃庙”即位于淮安清口的“惠济祠”。《钦定南巡盛典》记载恵济祠:“在淮安府清河县,祠临大堤,中祀天后,明正徳二年建,嘉靖中,赐额曰‘惠济’,其神福河济运,孚应若响。祠前黄淮合流,地当形胜,为全河之枢要,国朝久邀崇祀,我皇上临幸,升香荐帛,礼有加隆焉。乾隆辛未,御书祠额曰‘福佑河漕’,曰‘协顺资灵’,曰‘道光玉宇’,……又御书惠济祠行殿,额曰‘继述平成’,曰‘风帆沙屿’[20]。”
惠济祠位于淮安市淮阴区清口,祠中祭祀天后。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明嘉靖帝赐额曰“惠济”。惠济祠临运河大堤,祠前黄淮合流,地当形胜,为运河重要枢纽。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奉孝圣皇太后南巡,命重修惠济祠,并在惠济祠左侧建一行宫,与惠济祠建筑群联为一体。嘉庆十七年(1812),在圆明三园的绮春园内依淮安原样建惠济祠一座,以便皇帝就近祭祀,保证南北漕运的安全[24]。万历《淮安府志》记载惠济祠:“在新庄闸河口,正德三年始创,武宗南巡,亲至其上;嘉靖初,勑赐额曰惠济,春秋祭[5]。”《续纂淮关统志》记载惠济祠:“即河口娘娘庙,乾隆十六年,奉旨著两淮盐院吉庆动用商捐银两交前监督普福,幷委淮扬道吴嗣爵协同监修;二十一年,圣驾南廵,又谕令前监督高恒重修,叠赐御书诗文、联匾,勒石建亭,金辉碧映,高峙雄观。每逢上阅河工,进香礼拜,灵慈有感,永庆安澜[8]。”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在运口,《乾隆志》云: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章圣皇太后水殿渡河,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雍正五年,勅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南河祀典》则云:‘明嘉靖二十七年建,国朝康熙中,累封天后;乾隆十六年,改称惠济祠’。二说不同。《咸丰志》按:刘良卿有惠济祠碑,嘉靖二十七年立碑云:正德初,道士袁洞明卜地河浒,建泰山行祠;及章圣太后有黄香白金之赐,改名惠济;是明嘉靖中,止祀泰山之神,未尝祀天后也。本朝即其旧宇崇祀天后,遂称天妃庙,乾隆中,复改称惠济祠,具祀典者祗见有嘉靖二十七年碑文,遂以立碑之目为建庙之年,又不知有始祀泰山,今祀天后之异,通合为一,故致牴牾云尔。庙有铁鼓,又名‘铁鼓祠’,邑人汪之藻有《天后庙赋》[9]。”
3 阮辉莹所记淮安名胜古迹
淮安为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名胜古迹众多。阮辉莹在其日记中对淮安府城内的淮阴祠、漂母祠、韩信钓台等名胜古迹亦做了详细记载:“初五日,到淮安,古名淮阴,有山阳县同治。其淮阴祠匾‘国士无双’,又有双槐李家药室,室右槐树,大可二围,匾‘树此甘棠’,明嘉靖建。经西湖临流是漂母祠,匾‘一饭千金’,前有御诗亭。临湖立大碑,刻‘韩信钓台’,其钓处即城下之深潭[3]。”
日记中提到的“淮阴祠”,又名淮阴庙、韩侯祠,位于今淮安市淮安区镇淮楼东约200米处。韩信(?-前196),淮阴(今淮阴市西南)人。初属项羽,继归刘邦,被任为大将:他善于带兵,被封为齐王、楚王,后降封“淮阴侯”,为吕后所杀。他少年丧亲,家贫如洗,至今还留传着他在淮安遭受胯下之辱和向漂母乞食的故事。淮阴祠始建年代不详,明万历年间,推官曹于汴重建;清康熙年间,知县徐恕重修[25]。万历《淮安府志》记载淮阴侯庙:“在郡治东南,祀汉韩信[5]。”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韩侯祠:“漕院东,明代建尝于此立鹰扬会(馆),邑人朱维藩记之,邑令徐恕重修,今岁久失修,旅寓尘杂,非复旧观[26]。”民国《续纂清河县志》记载淮阴侯庙:“在淮阴古城淮水岸,唐时即有之,今山阳东南之庙,乃康熙中知府徐恕所重修,非旧庙也[17]。”至于“双槐李家药室”,则查不到相关记载,有可能指的是淮安当地的名医世家。
漂母祠在淮安市旧城(今属淮安区)西北隅韩侯钓台北边,东临萧家湖,西傍古运河。当年韩信垂钓水滨之时,常得到当地一位漂纱的妇女饭食接济和教育,后人特建祠纪念。祠原在东门内,明成化初,移建于西门外钓鱼台侧,后圮,1982 年重建。万历《淮安府志》记载漂母祠:“旧在郡城西门内,成化初,改迁西门外[5]。”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漂母祠:“旧在东门内,明成化初,迁西门外,后移建钓鱼台侧;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知县王命选捐修;雍正末,知府朱奎扬复葺,增置水榭曲舫;乾隆中,知府李暲属邑人童维祺大修;同治九年复修,增置缭垣[26]。”宣统《续纂山阳县志》记载漂母祠:“本在东门内,改建西门外,后移置北角楼钓台侧[16]。”《续纂淮关统志》记载漂母祠:“旧在淮城西门内,明都御史王炜记;成化初,迁西门外,即今建驿馆地,淮安知府陈文烛记,后移韩侯钓台侧;国朝康熙二十三年,山阳知县王命选捐修;雍正十一年,淮安知府朱奎扬复修;乾隆五年,知府李暲委训导汪克绍、绅士童维祺重修,改造船舫,修葺亭台,并封树陈节妇墓,墓在祠侧,遂为山阳胜境[8]。”
韩侯钓台在淮安市旧城西北运河东畔、萧家湖西侧。相传韩信少时贫寒,流浪于淮水一带,常以钓鱼为生。《史记》正义记载:“淮阴城北临淮水,昔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后人在此筑台,以示纪念。现存的韩侯钓台碑碣,始于明万历年间所刻。同治三年(1864)修葺,1979 年再次重修。《续纂淮关统志》记载韩侯钓台:“旧关志载:在满浦坊,汉时建,今有石碑一座。按《山阳志》辨讹云:《史记·淮阴侯传》载信尝钓于城下,城下乃古淮阴城也,去今淮城五十余里,县废城圯;信所游历处,如淮阴市胯下桥及韩母、漂母诸塚尽湮于水,久无遗迹可考。今淮城北门外漕河堤壖有韩侯钓台,乃明万历中淮守刘大文追建,是以唐宋元人皆无咏钓台诗,至明《潘中丞集》中始见,可知创造未久,焉得漫指为汉时建耶[8]?”《北游录》记载:“己酉午刻,同王编修定尔语近事,寻别,循涯访韩侯钓台,石亭屹然,旁即漂母祠,楹帖曰:‘世闲多少奇男子,终古从无一妇人’。按古淮阴县距今城四十里,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淮阴城北临淮水,昔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则城下寄食当在彼,非今处[27]。”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韩侯钓台:“城西北运河东岸,旧迹在淮阴,此后人移建。按《旧志》,古迹如淮阴市胯下桥、洪泽馆及邱墓内之漂母、韩母墓,其地皆在淮阴,已入《清河县志》篇内,概从删削,庶几征实[26]。”光绪《淮安府志》记载韩侯钓台:“在城西北,原迹在清河,此后人移建[19]。”宣统《续纂山阳县志》刘培元《韩侯钓台记》云:“郡城西北隅有韩侯钓台,俯临运河,望之嶷然。凡雄杰卓荦之士,以及道释、骚人、渔父、贾客过此者,无不婆娑其下,徘徊指顾,想见侯之遗烈。或曰:此特淮人追建以志不忘耳!淮之城建于晋,重筑于赵宋。运河通漕自明永乐始,汉时未有也。由此城而西北数十里,旧有韩信城,与信母墓相近。”太史公《传》云:“侯葬其母,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苏东坡过淮诗云:“朝离新息县,初乱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意侯钓处必在故城,与清淮接近,何可误指此为真迹耶[16]?根据以上史料可知,淮阴祠、漂母祠、韩侯钓台等古迹原先俱在清河县淮阴旧城,后迁于淮安府城山阳县境内。
4 结语
淮安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又控扼泗水入淮之河口,因而自古即在我国水运交通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28]。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淮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素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称。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不仅是南北经济和交通大动脉,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众多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家等经运河北上或南下,在其著作中留下了众多有关运河风情的记载和描述。淮安作为南北交通枢纽、运河文化名城,亦颇受外国人的关注。其中涉及朝鲜、日本、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史料较多,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对清代越南燕行文献进行整理和挖掘的成果相对较少。相较同时期的其他越南燕行文献,阮辉莹《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的记载更为详细,史料价值也更为突出。通过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和解读,对于深化运河城市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