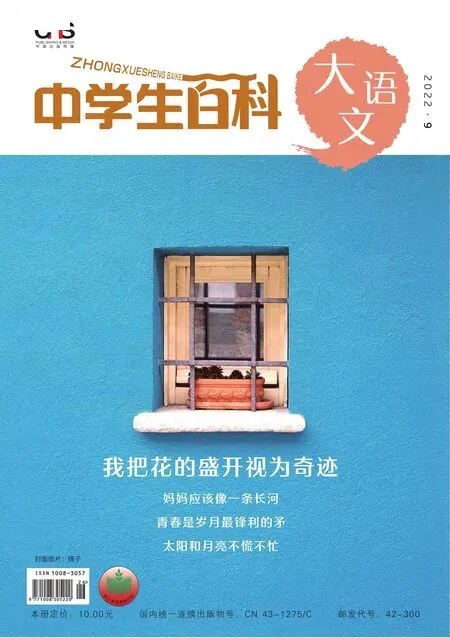那些“失去姓名”的女人
文|玲子

一个周六,儿子约了同学文哲一起去科技馆。一进展馆,两个爱探索的小男孩立刻被各种新科技深深吸引,几乎在每个项目跟前都兴奋地流连良久。
我和文哲妈妈跟在后面,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聊孩子们的学习,也聊养孩子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后来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我们自己。
时至年关,这一聊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远嫁的女儿——她的娘家在四川,我的娘家在山东,而因为远嫁,我们都是一年难得回次娘家。因为疫情,她已经两年没回去了。这种惺惺相惜的情愫,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文哲妈激动地抱了我一下,突然说:“哦,对了,我的名字叫袁俪,以后你就叫我的名字吧。”
我也报上自己的名字,不禁哑然失笑,对她说:“算起来,我们也认识一两年了,差不多每个周末都约着一起带孩子玩,竟然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
文哲妈妈也笑了,说:“可不是嘛,自从有了孩子,我就成了一个没名字的人。走出去就一直被称为文哲妈妈。咱们身边常在一起的宝妈好像都这样,都是‘谁谁妈妈’,从来不知姓甚名谁,成了一帮‘没名没姓’的女人了……”
确实如此啊。自从有了孩子,我的圈子里大多是宝妈们,各自的称呼也顺理成章成了“孩子名字+妈妈”。真名几乎无人问起,自己也忘了告知。
哪怕孩子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我们也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名,见面就喊:“嗳,谁谁妈妈——”大家仿佛已经习惯了这种因孩子而衍生的代称,全然忘记自己也是有姓名的人。
那个周六以后,文哲妈妈便跟我约定,以后我们都以本名相称。在微信上联系时,也称呼对方的名字,不再叫“孩子名字+妈妈”这样的代称。我们必须记得自己是个有名字的人,而不只是谁的妈妈。
不禁想起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名字只存在于她的身份证上,生活中极少听人叫起过。
数十年来,“小红她娘”就是母亲的名字,那是以我的小名而冠名的。我在家中的子女里排行老大,所以即使后来又有了弟弟妹妹,村里人还是习惯那样称呼我的母亲。以我的小名冠以娘亲的称呼,陪伴了母亲大半生。
村里很多母亲都是这样,比如“石头他娘”“桂花她娘”“二美她娘”……至于真实的名字,大概除了自己和自家的人,再无人知晓。
母亲前几年才刚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是因为她在镇上的银行办卡,存取钱需要本人签名。那时已经年近六旬的母亲,才终于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她一笔一画写得很慢,却是极其专注和认真的。确定自己写对了,她笑着拿给我看。那一份兴奋的笑容里,竟含着几分羞涩和小小的得意。
我夸母亲写得好,她笑得更灿烂了。我那因儿女“丢”了自己名字的母亲,终于用笔找回并记下了属于她的真实姓名。
尽管依然没几个人知道母亲的名字,依然叫她 “小红她娘”,但她的名字已深深镌刻在了我的心里。
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妈妈成了“没名没姓”的女人?她们因孩子被重新冠名,变成了“谁谁妈妈”,以母爱的名义。
甚至还有很多妈妈,不仅仅“弄丢”了自己的名字,还“弄丢”了自己,曾经无数个梦想后来只剩下唯一:“当个好妈妈。”
《爱的艺术》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富有成效地去爱别人,他也会爱他自己 ;如果一个人只爱别人,他就根本没有爱的能力。”
作为女人,特别是妈妈,爱孩子是本能,但是,我们在爱孩子的同时,也要记得爱自己。毕竟先爱好自己,我们才能爱好身边的人。
比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会有更饱满的精力去照顾自己想爱的人;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才能用更温和的心境去照抚自己关爱的人。
所以,因孩子而“失去姓名”的女人,都应该记得,自己也是个值得被爱的人;记得自己的名字——或诗意盎然,抑或略带些俗气,但都曾被爱我们的亲人寄予过美好的愿望。
记得我们身为“谁谁妈妈”的同时,我们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