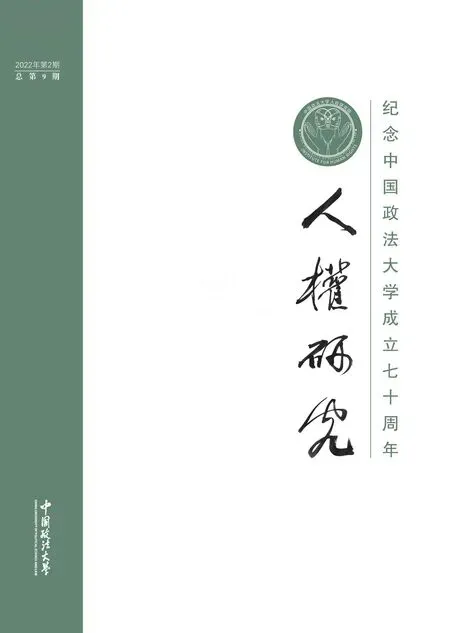欧洲人权法院2021年审判进展
埃马努埃尔·卡斯泰拉林 赫里斯托斯·扬诺普洛斯*
胡弼渊** 译
2021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旨在修订《欧洲人权公约》的第十五议定书在签署近七年后于8月1日生效。该议定书在《欧洲人权公约》序言中加入了辅助性原则和裁量余地两项内容,原文如下:“申明缔约国根据辅助性原则承担着确保本公约及其议定书所界定的权利和自由的主要责任,并且同时享有裁量余地,受到由本公约设立的欧洲人权法院的监督。”该议定书起草于2012年,主要是为了回应欧洲理事会部分成员国表达的担忧。这些成员国认为,欧洲人权法院这一国际性法院正在扮演“第四审法院”的角色1“第四审法院”是部分缔约国对欧洲人权法院的指责。之所以被称为“第四审”,是相对于缔约国国内法院的前三次(或者两次)审理而言的。欧洲人权法院发布的《关于受理标准的实用指南》(Practical Guide on Admissibility Criteria)第289段称,欧洲人权法院应当严守其行事的辅助性原则,尊重《欧洲人权公约》并保障其良好运行的权利首先由缔约国当局享有。只有当缔约国国内当局未能履行其义务时,欧洲人权法院才能进行干预。而部分缔约国质疑的正是欧洲人权法院没有尊重缔约国的国家主权,在申诉人将争议提交欧洲人权法院后,欧洲人权法院事实上成为了凌驾于缔约国主权之上的“第四审法院”,有违欧洲人权法院应遵守的辅助性原则。——译者注,过度干预成员国的国内主权事务以及自决权。
2021年,欧洲人权法院收到了44,250份申诉。针对这些申诉,欧洲人权法院作出了3,131项判决(其中12项由大审判庭作出)和32,961项决定(主要是不予受理决定)。2Se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nual Report 2021, p. 179,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Annual_report_2021_ENG.pdf.本文重在介绍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年度报告或其他摘要中强调的一些案例。3Se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Key Cases 2021, https://echr.coe.int/Documents/Cases_list_2021_ENG.pdf;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dex to the Information Notes on the Court’s Case-Law 2021,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CLIN_INDEX_2021_ENG.pdf.在程序性审理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开拓了与辅助性原则有关的案件处理新方式(第一部分)。此外,欧洲人权法院还着手处理了与国际法有关的问题(第二部分)。而在实质性审理方面,欧洲人权法院照常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裁决多种不同的问题(第三部分)。
一、与辅助性原则有关的案件处理新方式
除了正式引入辅助性原则和裁量余地外,第十五议定书还通过修订《欧洲人权公约》的其他重要规定对欧洲人权法院进行了改革。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第十五议定书将缔约国国内终审判决作出后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的期限从六个月缩短至四个月。这项新规定在第十五议定书生效后有六个月的过渡期,在过渡期结束后于2022年2月1日生效。4详见《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五议定书第8条第3款。
此外,欧洲人权法院决定实施一种新的、更有针对性的案件处理方式,以处理一些不属于“优先案件”类别的重要案件。2009年6月,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了“优先顺序政策”,并在2017年5月进行了修订。该修订的目的是加快最重要、最严重和最紧急案件的处理与审判。新的处理方式并未取代优先顺序政策。相反,新的处理方式旨在解决一些复杂和敏感的案件,这些案件被称为“具有影响力的案件”。欧洲人权法院2021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这类案件的认定“基于三个原则:首先,迅速识别出争议案件;其次,跟踪该案件的进展;最后,简化该案件的处理流程”5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nual Report 2021, p. 8,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Annual_report_2021_ENG.pdf.——译者注。
认定这类案件的标准较为宽泛笼统,足以纳入涉及言论自由、公平审判权、对记者的秘密监控、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案件,以及获得信息的权利、环境保护等主题的案件。新的处理方式将在未来展现其有效性及其对欧洲人权法院案件量的影响。目前已有约530起案件被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为“具有影响力的案件”。
在司法政策领域,值得关注的还有欧洲人权法院在2021年判决的两个案件,分别是姆劳维奇(Mraović)诉克罗地亚案1Mraović v. Croatia [GC], no. 30373/13, ECHR 2021.与图兰(Turan)和其他人诉土耳其案2Turan and Others v. Turkey, nos. 75805/16 and 75794/16, ECHR 2021.。在第一个案件中,案件申诉人被指控犯有强奸罪,该审判是在排除了公众旁听的情形下进行的。排除公众旁听这一决定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作出的,该款规定“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的考虑,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本案中,这一决定的作出是为了保护受害者的私人生活,没有考虑到被告所享有的对其刑事诉讼进行公开监督的权利。然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受害者曾多次在全国性报纸上接受采访。在2020年5月14日作出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个审判庭认为,考虑到“指控所涉案情相当严重,涉及对一个人最具侮辱性的攻击”(第57段,译者注),前述决定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应申诉人的请求,该案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43条和《法院规则》3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ules of Court, https://www.echr.coe.int/documents/rules_court_eng.pdf.——译者注第73条被提交大审判庭审理。但是,由于申诉人在诉讼过程中死亡,且其继承人或近亲属均不愿意继续该申诉,大审判庭决定将申诉从案件列表中删除。4See, among others, Léger v. France (striking out) [GC], no. 19324/02, § 44, ECHR 2009; Borovská v. Slovakia(revision), no. 48554/10, §§ 8-10, ECHR 2016.
但是,欧洲人权法院本可能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37条第1款得出其他结论,即由于本案在人权保障上存在特殊性,需要继续审理该申诉——因为该案提及了涉及公约利益的重要问题5See, among others, Berlusconi v. Italy [GC], no. 58428/13, § 68, ECHR 2018.。欧洲人权法院如果选择这样做,则其可以进一步阐明,在《欧洲人权公约》规定下,申诉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与受害者权利之间最能平衡双方权益的保护标准究竟是什么。但欧洲人权法院对本案作出了相反的决定。大审判庭指出,“本案中,申诉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提出的申诉案件无关立法内容本身,而仅关于该立法在本案中的适用方式”6Mraović v. Croatia [GC], no. 30373/13, § 27, ECHR 2021.,以此证明其司法谦抑。
在图兰和其他人诉土耳其案7Turan and Others v. Turkey, nos. 75805/16 and 75794/16,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了土耳其当局对427名申诉人的逮捕和审前羁押措施——这些申诉人当时都在不同类型和(或)级别的法院担任法官或检察官。在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当局采取前述措施,是因为其怀疑他们参与当局所称的“居伦恐怖组织”(Fetullahist Terrorist Organisation)。在本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一致认定,由于对申诉人的审前羁押不合法,当事国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人身自由与安全权);这些申诉人被审前羁押时,有的是普通的法官或检察官,有的是该国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或检察官。
令人惊讶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决定不详细审查“每个申诉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提出的其余申诉1本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之所以提及“其余”申诉,是因为该案当事人的申诉内容除了本文提到的审前羁押外,还包括“上千个类似申诉”。而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这些类似申诉给法院造成了太多的案件积压,而逐一审理的工作量与处理这些申诉给当事人带来的利益和为判例法发展作出的贡献并不相称(判决书第98段)。因此,其他申诉不为本案所审查。——译者注的可受理性和案情”(第98段)。对欧洲人权法院而言,这是一项基于司法政策的选择。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对每个申诉人提出的其余申诉进行个别审查会严重拖延这些案件的处理,不会给申诉人带来相应的利益,也不会对案件进展作出贡献”(第98段)。欧洲人权法院如此选择,是由于继续处理这些申诉会影响其完成任务的能力。
库里斯(Egidijus Kūris)法官批评了这一实用主义的选择,他认为“司法政策的考量不能取代法律推理,因此仅基于司法政策考量作出的判决本身就不符合对人权的法律解释”2参见该案判决书附件“Partly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Kūris”。——译者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已经在伯米希(Burmych)和其他人诉乌克兰案3See Burmych and Others v. Ukraine (striking out) [GC], nos. 46852/13 et al., ECHR 2017.中得到了适用。在该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决定剔除12,143项待决的相似申诉。这些申诉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乌克兰存在不执行或延迟执行国内法院裁决的系统性问题,且缺乏有效的国内救济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4See Yuriy Nikolayevich Ivanov v. Ukraine, no. 40450/04, ECHR 2009.。
二、与国际法有关的问题
欧洲人权法院在一些案件中谨慎地明晰了其基于《欧洲人权公约》第1条的域外管辖权,这些案件包括两个备受瞩目的国家间案件5作者所说的“两个国家间案件”系乌克兰诉俄罗斯案和格鲁吉亚诉俄罗斯案,下文将详细讨论。——译者注。此外,一些案件与国际法和欧盟法之间存在重要互动。
(一)域外管辖权
《欧洲人权公约》的适用性并不由领土或国籍决定,而是由更广泛的管辖权概念来界定的:“缔约方应当保证在它们管辖之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一章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欧洲人权公约》第1条,着重号由作者标注)。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欧洲人权公约》具有域外适用性,其适用范围在五个案件中得到了明确。这五个案件包括两个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33条提起的国家间案件,这两个案件在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变得更加引人注意。
在乌克兰诉俄罗斯(关于克里米亚)案1Ukraine v. Russia (re Crimea) (dec.) [GC], nos. 20958/14 and 38334/18, ECHR 2020.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俄罗斯不仅在2014年3月18日之后对克里米亚拥有管辖权,而且根据俄罗斯军事存在的有关证据,其在2014年2月27日至3月18日期间对克里米亚也拥有管辖权。欧洲人权法院的立场绝不是承认俄罗斯对该地区的主权或其“吞并”行为的合法性:这些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欧洲人权法院仅仅出于《欧洲人权公约》有关规定的意旨,得出了俄罗斯对该地区存在有效控制的结论。现在,欧洲人权法院必须就该案中俄罗斯当局行政管理时涉嫌多次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行为作出判决。
格鲁吉亚诉俄罗斯(2号)案2Georgia v. Russia (II) [GC], no. 38263/08, ECHR 2021.是欧洲人权法院自2001年著名的班科维奇(Banković)案3Banković and Others v. Belgium and Others (dec.) [GC], no. 52207/99, ECHR 2001-XII.——译者注(1999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电台和电视台总部)以来,首次处理与国际武装冲突中军事行动有关的管辖权问题。班科维奇案后,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域外管辖权的判例法内容逐渐发生了变化: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如需认定一国拥有管辖权,则该国需对某一地区拥有有效控制,并对涉案的有关个人拥有“国家性质的权力和控制”。4Georgia v. Russia (II) [GC], no. 38263/08, § 115, ECHR 2021. ——译者注欧洲人权法院还表明,一国的国家责任不会由于“极短时间内从事的域外行为”而产生。5Ibid., § 124.——译者注据此,欧洲人权法院必须确定,在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两国敌对行动的活跃期(即2008年8月8日至12日),以及在敌对行动停止后的占领阶段,俄罗斯是否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拥有管辖权。欧洲人权法院的结论是,在敌对行动期间俄罗斯没有对这两个地区取得有效控制,因此没有管辖权。但是,格鲁吉亚提供了这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团体在经济、金融、军事和政治等方面从属于俄罗斯的证据。因此,俄罗斯不仅在其军队正式撤离(即2008年10月10日)之前就对这些地区实施了有效控制,在此之后也具有有效控制。由于格鲁吉亚的主张符合受理条件,欧洲人权法院遂对该案进行了实质性审查,并认定俄罗斯应对涉嫌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多项条款的数次行为负责。
在沙夫洛霍瓦(Shavlokhova)和其他人诉格鲁吉亚案6Shavlokhova and Others v. Georgia (dec.), nos. 45431/08 and 4 others, ECHR 2021.的裁决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敌对行动的活跃阶段,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也没有形成有效控制(因此没有管辖权)。欧洲人权法院强调,尽管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领土的一部分,但混乱的环境使格鲁吉亚无法在武装冲突期间行使其国家权力,这使得被告国领土管辖权的正常行使受到限制。尽管这一推理在法律上无可指责,但欧洲人权法院的推理在《欧洲人权公约》如何适用于交战区方面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空白——因为这一推理并未说明,在交战国均没有取得充分有效控制的一些地区,《欧洲人权公约》应当如何适用。
欧洲人权法院还审理了哈南(Hanan)诉德国案1Hanan v. Germany [GC], no. 4871/16, ECHR 2021.中的域外管辖权问题。该案涉及一起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该授权的依据为《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本案中申诉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关于生命权的规定诉称,德国当局没有对杀害他两个儿子的空袭行动进行有效调查,而他也没有有效的救济方式来要求德国当局继续进行对该事件的调查。显然,德国当局在这一案件中没有行使域外管辖权,案情不符合域外管辖权有关规定的适用情形。欧洲人权法院根据其判例法,审查了本案中是否存在《欧洲人权公约》第1条意义上的“管辖权联系”。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不能仅以“进行了调查”为根据来确定存在管辖权联系:如此一来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当事国国内的调查会受到阻碍,而且会导致鼓励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采取不一致的方式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的效果。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存在导致建立管辖权联系的“特殊情况”。本案中,根据习惯国际人道法和德国国内法(与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有关),德国有义务调查空袭期间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而阿富汗当局则因《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地位协定》而无法这样做。因此,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该申诉可以受理,但最终认定德国当局的行为并未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在布兰当·弗雷塔斯·洛巴托(Brandão Freitas Lobato)诉葡萄牙案2Brandão Freitas Lobato v. Portugal (dec.), no. 14296/14, ECHR 2021.的裁决中,欧洲人权法院也审查了该案中是否存在“管辖权联系”,最终认为,虽然葡萄牙法官在东帝汶法院参与了针对布兰当·弗雷塔斯·洛巴托的刑事指控,但其参与不足以建立“管辖权联系”。
(二)与国际法和欧盟法的互动
与其他案件一样,格鲁吉亚诉俄罗斯(2号)案和哈南诉德国案使欧洲人权法院注意到《欧洲人权公约》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互动。欧洲人权法院还以其在其他几个领域对国际法规范的援引来支持其观点,这些领域包括:家庭暴力3See Kurt v. Austria [GC], no. 62903/15, ECHR 2021.、性别平等——包括《欧洲理事会防止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又称《伊斯坦布尔公约》)1See Jurčić v. Croatia, no. 54711/15, ECHR 2021.、记者2See Standard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v. Austria (no. 3), no. 39378/15, ECHR 2021.、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3See Abdi Ibrahim v. Norway [GC], no. 15379/16, ECHR 2021.、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4See K.I. v. France, no. 5560/19, ECHR 2021.、《欧洲理事会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公约》5See X and Others v. Bulgaria [GC], no. 22457/16, ECHR 2021.、防止人口贩卖6See V.C.L. and A.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77587/12 and 74603/12, ECHR 2021.、人权和生物医学7See Decision on the competence of the Court to give an advisory opinion under Article 29 of the Oviedo Convention, request no. A47-2021-001, 15 September 2021.。
这种互动也存在于《欧洲人权公约》与欧盟法之间,后者包括欧盟法院的判例。在2005年博斯普鲁斯航空旅游和贸易股份公司诉爱尔兰案8See Bosphorus Hava Yolları Turizm ve Ticaret Anonim Şirketi v. Ireland [GC], no. 45036/98, ECHR 2005-VI.——译者注中,欧洲人权法院推定欧盟法律秩序形成了“同等保护”(从而推定执行欧盟法的国家行为符合《欧洲人权公约》)。在比沃拉鲁(Bivolaru)和莫尔多万(Moldovan)诉法国案9Bivolaru and Moldovan v. France, nos. 40324/16 and 12623/17,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将其判例法适用于把两名申诉人依据2002年《关于欧洲逮捕令和欧盟成员国之间移交程序的框架决定》(以下简称《框架决定》)移交给罗马尼亚的情况。根据欧盟法院依据《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所作的解释,就本案中其中一位申诉人的情况而言,欧洲人权法院推定《框架决定》提供了同等保护。但是,根据案件的事实状况,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向罗马尼亚当局移交该申诉人构成了对《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的违反,因为存在拘留条件不符合规定的现实风险。另一位申诉人的情况则相反,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就该申诉人而言同等保护的推定不适用于2002年《框架决定》。其原因在于,法国最高法院拒绝了该申诉人希望将涉案事项提交至欧盟法院并由欧盟法院对执行欧洲逮捕令的影响作出预裁决的请求;该欧洲逮捕令关涉一成员国给予随后也成为欧盟成员国的第三国国民难民地位的事由。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认为执行欧洲逮捕令的影响真实存在且较为严重,而欧盟法院未能对其进行审查。因此,欧盟内部基本权利保护体系并未发挥全部潜力。不过,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第二位申诉人的案件中,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罗马尼亚的拘留条件存在构成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风险。
比沃拉鲁和莫尔多万诉法国案所展现出的将欧盟作为法律与事实背景一部分的做法并不罕见。在 M.A.诉丹麦案10M.A. v. Denmark [GC], no. 6697/18, ECHR 2021.中,在没有进行个案评估的情况下,丹麦当局直接对处于辅助性或临时性保护的难民进行立法,规定其需要经过不合理的三年法定等待期才能与家人团聚;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这一立法构成了对“尊重家庭生活的权利”的侵犯(《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在这一框架下,判决拓展了《欧盟关于家庭团聚权的指令》(2003/86/EC)第8条的内容。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没有理由质疑该指令中规定的两年等待期的合理性(三年等待期仅作为例外情形);但如果等待期超过两年,由于难民在原国籍国享受家庭生活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公正平衡评估(fair balance assessment)中将更着重考量难民面临的困难和团聚的需要。欧洲人权法院承认,《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不能被视为对一国施加了同意在其领土上实现家庭团聚的一般义务,但欧洲人权法院坚持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在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是切实可行的、有效的,而不是理论的、虚幻的。
在一些案件中,欧盟法被用于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在 K.I.诉法国案1K.I. v. France, no. 5560/19,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在以犯恐怖主义罪为由撤销涉案难民的难民地位后,法国未对驱逐涉案难民的风险进行评估,便将一名车臣难民驱逐回俄罗斯,这一行为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的违反。其中,欧洲人权法院援引欧盟法院的一项裁决结果来支持自己的事实判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即使当事人的难民地位被撤销,其仍为一名难民。
在尤尔契奇(Jurčić)诉克罗地亚案2Jurčić v. Croatia, no. 54711/15,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拒绝向一位在就业前不久接受体外受精的孕妇提供与就业相关的福利是一种不合理的、直接的性别歧视,这种做法结合《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和平享用财产的权利)构成了对《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禁止歧视)的违反。为支持其说理,欧洲人权法院指出,欧盟法院的判例法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欧洲人权公约》与欧盟法互动的另一个例子是比安卡尔迪(Biancardi)诉意大利案3Biancardi v. Italy, no. 77419/16, ECHR 2021.。在该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考虑了欧盟95/46/EC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欧盟法院的相关判例法,认为因为一名报纸编辑长期拒绝将载有个人资料的出版物删除而对其实施民事责任制裁,是对这名编辑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参见第70段,译者注)。
三、实质审理的有关问题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了为抗击疫情而采取的一些前所未有的措施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目前为止,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发现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的情况。在其他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处理了一些相对传统问题的新面向。就部分国家而言,其国内法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问题引发了大量关注与担忧,欧洲人权法院就此作出了几项判决,认为涉案国家的行为有违《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还对跨境通信监控的国内制度作出了判决,就当代技术产生的挑战制定了公众期待已久的裁判标准。基于辅助性原则以及各国无法达成相关共识的情况,欧洲人权法院在“限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一问题上对各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裁判标准。而与此相反,欧洲人权法院审理的另一些案件则致力于更有效地保护个人(包括跨性别者)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以及更有效地禁止歧视。家庭虐待行为、家庭暴力以及与心理健康有关的问题也是欧洲人权法院关注的重要领域,欧洲人权法院力求在这些领域里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最能平衡各方权益的裁判。
(一)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案件
欧洲人权法院处理的一些申诉涉及为应对不同阶段的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有争议的措施。在泰尔赫什(Terheş)诉罗马尼亚案1Terheş v. Romania (dec.), no. 49933/20,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罗马尼亚当局实施的为期52天的全面封锁不构成《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规定的“剥夺自由”。在这一案件中,申诉人可以基于多种原因离开自己的家,并可以根据情况随时前往不同的地方。他没有受到当局的个人监视,没有主张自己被迫生活在狭窄的空间中,也没有被剥夺所有的社会交际。封锁的强度使得这种封锁并不等同于居家软禁(参见第43段,译者注)。
在赞布拉诺(Zambrano)诉法国案2Zambrano v. France (dec.), no. 41994/21, ECHR 2021.中,申诉人对2021年法国规定的健康通行证制度提出抗议。该制度所设立的健康通行证是进行几项日常活动的必要条件,例如进入酒吧、餐馆、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参加研讨会,以及乘坐火车、长途汽车和飞机等。当时,获得健康通行证的条件是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最近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或接种新冠疫苗。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基于以下原因,申诉人提出的案件不可受理。首先,本案的申诉人尚未穷尽所有国内救济(《欧洲人权公约》第35条)。其次,虽然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判断申诉人是否可以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34条取得该条规定的受害者地位,但其同时指出,本案的申诉人只是抽象地抱怨法国政府的被诉措施不适当、不充分,没有提供有关其自身权益受损等情况的详细信息。欧洲人权法院还处理了基于《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非人道的或者是有损人格的待遇)提出的申诉。申诉人没有证明他作为一个不希望接种疫苗的人受到了任何胁迫。而事实上,法国当局的措施没有规定任何接种疫苗的一般性义务。本案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是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第35条第3款(a)项(禁止滥用申诉)的罕见案件之一。申诉人邀请访问其网站的人与他一起提交集体申诉,并通过自动生成的、标准化的申请表提交多份申诉,导致出现了近18,000份申诉。他的明确目标是在欧洲人权法院造成“拥堵、过大工作量和案件积压”,以“瘫痪欧洲人权法院的运作”,“创造一种权力关系”以便与欧洲人权法院“谈判”,“使整个系统脱轨”,其中欧洲人权法院是“链条上的一环”(参见第36段,译者注)。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这种做法显然与《欧洲人权公约》设立个人申诉权的目的背道而驰。
此外,一起事实部分与新冠肺炎疫情无关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欧洲人权法院在强制儿童接种疫苗这一争议问题上的立场。在瓦夫日奇卡(Vavřička)和其他人诉捷克案1Vavřička and Others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nos. 47621/13 and 5 others, ECHR 2021.中,捷克当局对一些父母处以罚款,并禁止其子女入幼儿园,理由是他们拒绝履行法定的儿童接种疫苗义务。意料之中的是,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强制接种疫苗是一种非自愿的医疗干预,干涉了当事人的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但是,欧洲人权法院接着得出结论,认为涉案措施与被告国追求的合法目的之间存在合理的比例关系,没有超出该国的自由裁量余地,因此可以认定相关措施为“民主社会所必需”。此外,欧洲人权法院还指出,该案涉及医学上较为熟知的疾病。疫苗的接种没有违背申诉人意愿,且根据国内法规定,也无法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进行接种。在国际专业机构相关活动的有力支持下,《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普遍共识,即疫苗接种是最成功、最具成本效益的健康干预措施之一。缔约国的儿童接种疫苗政策各不相同,严格程度从建议接种到义务接种不等。虽然各个缔约国没有就单一的疫苗接种政策模式达成共识,但捷克当局所采取的严格政策也得到了其他几个国家的赞同,其中一些国家因其国内自愿接种疫苗人数有所减少而在近期采取了这种政策。鉴于上述情况,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该案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当然,欧洲人权法院可能很快就需要确定上述评估过程是否也适用于各缔约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疫苗接种政策。
(二)法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欧洲人权法院的另一个重点关注领域是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法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问题也是欧盟法院最近判例法的核心,值得提及。
在 BEG股份公司(Beg S.p.a.)诉意大利案1Beg S.p.a. v. Italy, no. 5312/11,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需要处理仲裁庭的公正性问题。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为解决涉案合同争议而组成的仲裁庭缺乏必要的公正性,因为仲裁庭的一名成员是申诉人竞争对手公司的母公司的高层顾问,而该竞争公司与BEG股份公司之间存在法律纠纷。根据案件适用的程序规则,仲裁员未明确披露待裁决争议中是否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或经济利益。尽管申诉人未对信息披露的缺乏提出异议,但对欧洲人权法院来说,这并不表明申诉人放弃由一个独立和公正的仲裁庭解决争议的权利。进一步说,没有证据表明申诉人知悉仲裁员存在的利益冲突。所以虽然申诉人在仲裁员任命之前自由和自愿地接受了仲裁,但不能被视为明确放弃了对仲裁员公正性的要求,或放弃了对意大利国内法院确保仲裁裁决符合《意大利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正性的期望。因此,仲裁程序必须为申诉人提供《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保障。本案中,在评估涉案仲裁庭公正性的客观方面时,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仲裁员的公正性值得怀疑,或至少表面上值得怀疑。因此,欧洲人权法院认定本案中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情况。这一案例表明,对公正性的要求不仅限于一国法院,对仲裁员法律和道义上的要求也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其他案件表明了欧洲人权法院如何应对国家机关干预法官独立性的情况。霍查伊(Xhoxhaj)诉阿尔巴尼亚案2Xhoxhaj v. Albania, no. 15227/19, ECHR 2021.涉及阿尔巴尼亚当局为打击国内腐败而设立的对法官和检察官进行审查的机构。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上述机构是依法设立的,客观上是独立的、公正的审查机关。欧洲人权法院特别提到了独立性问题,其认为,这些审查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旦被任命为固定任期,并且保证其不可撤换性,该机关就不会受到来自行政部门的任何压力。尽管这些机关的成员并不从在职专业法官中选取,但这符合避免任何个人利益冲突以及确保公众对审查程序信心的需要。总而言之,该案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在一系列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发现了一些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情况。这些案件多由2017年启动的波兰司法制度改革引发。在雷茨克维茨(Reczkowicz)诉波兰案3Reczkowicz v. Poland, no. 43447/19, ECHR 2021.中,波兰当局在任命新设立的波兰最高法院纪律分庭法官方面存在严重违规。欧洲人权法院特别指出,上述任命程序受到立法和行政权力的不当影响,构成根本性的违规,这对整个程序以及纪律分庭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最高法院纪律分庭不属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依法设立的法庭”。
在多林斯卡-菲采克(Dolińska-ficek)和奥齐梅克(Ozimek)诉波兰案1Dolińska-Ficek and Ozimek v. Poland, nos. 49868/19 and 57511/19,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就波兰最高法院另一新设分庭(即特别审查与公共事务分庭)采取了类似的推理。该案中还出现了另一明显违反波兰国内法的情况:波兰总统“公然蔑视法治”(第349段,译者注),尽管波兰总统收到了法院命令,要求暂缓执行全国司法委员会关于任命法官的决议,但其仍进行了任命。
在谢罗-弗洛波兰有限公司(Xero Flor w Polsce sp. z o.o.)诉波兰案2Xero Flor w Polsce sp. z o.o. v. Poland, no. 4907/18, ECHR 2021.中,申诉人诉称,审理其所涉及的一起财产损害赔偿案的宪法法院法官是由下议院(波兰议会的下院)选举产生的,而该职位本已由上届下议院选举的另一名法官填补。这一严重违规行为,以及无视宪法法院在这方面的裁判,意味着审理该案件的法庭不是“依法设立的法庭”。此外,尽管申诉人多次向国内法院提出这一问题,但这些法院并未答复申诉人有关该案法律适用是否合宪的质疑,这构成了未履行提供合理判决的义务,欧洲人权法院据此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也受到了侵犯(参见第291段,译者注)。目前,欧洲人权法院正在审理其他几起案件,这些案件涉及波兰司法制度改革的多个方面。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这些案件应获得最高优先权。因此,预计欧洲人权法院还将作出更多判决,可能还会发出几项谴责。
(三)当今的跨境通信监控手段
2021年5月25日,欧洲人权法院就瑞典和英国的秘密监控制度作出了两项重要判决,这两项判决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应申诉人的请求,这两起案件均提交大审判庭审理。在第一起案件中——也就是“正义中心”(Centrum för Rättvisa)诉瑞典案3Centrum för rättvisa v. Sweden [GC], no. 35252/08, ECHR 2021.——申诉人(一家非政府组织)认为,其通过手机和移动宽带进行的通信有被瑞典国防无线电局以信号情报方式截获的风险。在第二起案件中——也就是“老大哥观察”(Big Brother Watch)和其他人诉英国案4Big Brother Watch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s. 58170/13, 62322/14 and 24960/15, ECHR 2021.——申诉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对英国政府根据《调查权规则法案》(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实施的电子监控计划的范围和强度表示抗议。
通过点明制度的预防目的,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和第10条(表达自由),首次确定了一国在设立国内大规模通信拦截制度时所需要的基本保障。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大规模拦截)与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法中常见的针对性拦截不同1See, among others, Weber and Saravia v. Germany (dec.), no. 54934/00,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6-XI; Roman Zakharov v. Russia [GC], no. 47143/06, ECHR 2015.,针对性拦截主要用于犯罪调查,而大规模拦截除了用于犯罪调查,还可以用于(甚至可能主要用于)收集外国情报、识别已知和未知主体带来的新威胁”2Centrum för rättvisa v. Sweden [GC], no. 35252/08, § 236, ECHR 2021.。因此,欧洲人权法院指出,有必要根据针对性拦截和大规模拦截之间的上述重大区别发展其判例法,并确定为保护个人隐私而必须设置的“端到端”保障。打击现代犯罪行为,如全球恐怖主义、毒品贩卖和人口贩卖以及对儿童的性剥削,属于对《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权利进行限制的正当目的。
所以,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大规模拦截制度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款的规定时,应综合考虑不同的标准,例如,授权进行大规模拦截的理由,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拦截个人通信,授权进行大规模拦截应遵循的程序,选择、审查和使用拦截获得的材料应遵循的程序,向第三方发送拦截获得的材料时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对拦截持续时间的限制,所获材料的储存以及清除、销毁这些材料的情形,独立主管机构监督相关规定遵守情况的程序和方式,对遵守情况进行独立事后审查的程序,以及赋予相关机构处理违规行为的权力。
就现有案件的评估来说,大审判庭不同意此前审判庭认定的未侵犯私人生活这一意见。大审判庭以15票赞成、2票反对指出,瑞典的大规模拦截制度有三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瑞典没有制定明确规则来规定如何销毁截获的、不含个人数据的材料,第二个缺陷是瑞典没有在法律上要求有关机构在向外国合作者传送情报材料时考虑个人隐私利益,第三个缺陷是瑞典的相关规定没有设置有效的事后审查措施。大审判庭对英国《调查权规则法案》的审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调查权规则法案》中的保障比瑞典相关规定中的保障更安全、更有力,但其并未包含足够的“端到端”保障,无法充分、有效地防止当局的任意性和滥用权力的风险。因此,对个人权利的这种干涉是不成比例的,也不是民主社会所必需的。
(四)关于公共事务参与权的新的重要考量
欧洲人权法院至今还远未完全阐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规定的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权。不过,欧洲人权法院对《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条进行了扩展解释,以使其涵盖多种与选举相关的议题,这些议题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其中,公共事务参与权仅由有能力评估其决定的后果并作出有意识的、明智决定的公民享有。
2021年,欧洲人权法院根据辅助性原则,就国内法对《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条的暗含限制作出了两项重要判决。在斯特罗拜(Strøbye)和罗森林德(Rosenlind)诉丹麦案1Strøbye and Rosenlind v. Denmark, nos. 25802/18 and 27338/18, ECHR 2021.中,申诉人被剥夺了法律行为能力,并且根据该国《监护法案》,他们的选举权也被剥夺,无法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投票。通过援引赫斯特(Hirst)诉英国(2号)案2Hirst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2) [GC], no. 74025/01,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2005-IX.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丹麦法官的判决与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相称的,因为“立法者欲使尽可能多的人能够投票,同时希望保护需要监护且被剥夺法律行为能力的一小群人”3Strøbye and Rosenlind v. Denmark, nos. 25802/18 and 27338/18, § 116, ECHR 2021.。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丹麦的立法符合欧洲标准,因为在1996年《监护法案》通过后,丹麦当局逐渐减少了对被剥夺法律行为能力者的选举权的限制。故而,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丹麦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条。
在卡马尼奥·巴列(Caamaño Valle)诉西班牙案4Caamaño Valle v. Spain, no. 43564/17,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采取了类似的解决办法。该案申诉人代表其具有身心障碍的女儿提出要延长对女儿的法定监护权期限。但同时,西班牙法官还裁定取消其女儿的选举权。西班牙的有关制度并未规定被监护人自动丧失选举权,但允许法院通过司法裁定的方式宣告智力障碍者无投票能力。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该国法院作出的裁定(……)属于缔约国规制选举权的自由裁量余地。申诉人女儿的选举权被剥夺,是法院根据她的个人情况,在对她的精神能力进行了彻底分析后给出的结论。与申诉人的主张相反,此案中其女儿的选举权之所以被剥夺,不是仅仅因为她属于某一类特定群体。不能认为取消她的选举权是在阻碍人们在立法机构选举时自由表达意见。”(第77段)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在这两起案件中都提到,《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缔约国之间就“精神障碍者是否享有无条件行使其选举权的权利”这一议题尚不存在一致意见。但欧洲人权法院同时指出,自欧盟基本权利署于2014年5月21日就上述议题发布《残障人士的参政权:人权指标》报告以来,残障人士的政治参与情况略有发展,西班牙、法国和德国于2018年至2019年间赋予精神障碍者选举权。由此,欧洲人权法院注意到了不断变化的情况以及成员国国内法律秩序中正在形成的共识,但欧洲人权法院目前并没有试着在该领域强加一个统一标准5See ibid., § 43; Strøbye and Rosenlind v. Denmark, nos. 25802/18 and 27338/18, § 115, ECHR 2021.。无论人们如何期待这样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都原本可能促使欧洲人权法院对《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条的适用范围作出重大的甚至是有争议的扩展,而这种扩展超越了其权限。
(五)《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
在过去的十年中,《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适用显著增加,因为私人生活是一个“包含了个人生理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多个方面”的概念1S. and Marper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s. 30562/04 and 30566/04, ECHR 2008.。因此,对私人生活这一概念不宜进行穷举性定义。考虑到私人生活涉及一系列广泛问题,与个人身体、心理或道德完整性相关的案件可以通过《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进行审查。在拉卡图斯(Lacatus)诉瑞士案2Lacatus v. Switzerland, no. 14065/15,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对瑞士作出了不利判决,因为瑞士的一些省(州)规定禁止乞讨。该案的申诉人是罗马尼亚人,属于罗姆人群体。她极度贫穷、弱势,却因乞讨而被瑞士法院判处500瑞士法郎的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欧洲人权法院首次将乞讨与人格尊严这一概念联系到一起进行判决,后者(人格尊严)多次在《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意义上被提及。3See, among others, Hudorovič and Others v. Slovenia, nos. 24816/14 and 25140/14, ECHR 2020.在这一背景下,欧洲人权法院没有接受瑞士政府的解释:瑞士政府主张其立法的目的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并保护路人、居民和店主的权利。
2021年,在家庭生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关于跨性别者的有趣进展。A.M.和其他人诉俄罗斯案4A.M. and Others v. Russia, no. 47220/19, ECHR 2021.涉及一名跨性别女性。由于其性别转变,以及有关机关怀疑她与孩子的沟通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她作为父母享有的亲权受到限制,并被禁止与其子女进行联系。欧洲人权法院一致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因为俄罗斯法院没有充分证明申诉人的性别转变对其子女所构成的风险。此外,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将申诉人的性别转变(从男性转变为女性)作为限制其与孩子保持联系的决定性因素,结合《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违反了第14条。欧洲人权法院表示,与其他父母相比,申诉人受到了差别待遇,这些父母也寻求与其疏远的子女取得联系,但他们的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性别相同。与P.V.诉西班牙案5P.V. v. Spain, no. 35159/09, ECHR 2010.相比,本案标志着欧洲人权法院在改善跨性别者的处境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在P.V.诉西班牙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认可了对一名跨性别者与其六岁儿子之间的接触安排所采取的限制措施,理由是有一份心理专家的报告指出,该申诉人的情绪缺乏稳定性。
在X.和Y.诉罗马尼亚案1X. and Y. v. Romania, nos. 2145/16 and 20607/16,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了跨性别者普遍缺乏准确的身份证件这一问题;更确切地说,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了在罗马尼亚获得性别承认的条件。该案中,罗马尼亚当局拒绝承认尚未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的男性身份。这一情况之所以很成问题,是因为这使得不希望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面临两难抉择:要么遵守法律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并获得准确的身份证件;要么拒绝遵守法律,并遵从其个人的自由意志(参见第165段,译者注)。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罗马尼亚关于承认性别认同的法律框架不清晰且不具有可预见性,而且现有的法律制度没有在相关方整体利益和当事人个人利益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因此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款的规定。欧洲人权法院还提到,越来越少的欧洲理事会成员国要求将性别重置手术作为在法律上承认性别认同的先决条件;截至2020年,已有26个成员国不再作此要求。因此,罗马尼亚当局拒绝在申诉人未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情况下于法律上承认其性别,这构成了对申诉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的不正当干涉。
(六)在禁止歧视方面判例的新进展
在贝哈尔(Behar)和古特曼(Gutman)诉保加利亚案2Behar and Gutman v. Bulgaria, no. 29335/13, ECHR 2021.以及布迪诺瓦(Budinova)和恰卜拉松(Chaprazov)诉保加利亚案3Budinova and Chaprazov v. Bulgaria, no. 12567/13, ECHR 2021.中,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和第14条,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了涉案国内法院在针对一个社会群体的负面公开言论问题上未能给申诉人提供救济,也没能防止对该群体形成负面刻板印象的现状。这两起案件的申诉人分别是犹太人(第一起案件申诉人)和罗姆人(第二起案件申诉人),他们主张某一政党的领导人发表了足以构成骚扰和煽动种族歧视的公开言论。同时他们还主张,作为少数群体的成员,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受到了这些言论的影响。4Behar and Gutman v. Bulgaria, no. 29335/13, § 8, ECHR 2021.——译者注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这两起案件的主要问题是分析这类公开的负面言论是否会影响到少数群体成员个人的“私生活”。5See ibid., § 67; Budinova and Chaprazov v. Bulgaria, no. 12567/13, § 63, ECHR 2021.——译者注为了能够适用《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欧洲人权法院指出,案件中申诉人所提出的主张应当超出阿克苏(Aksu)诉土耳其案6Aksu v. Turkey [GC], nos. 4149/04 and 41029/04, ECHR 2012.所确立的“严重程度门槛”。
至于如何确定公众人物的某一特定言行是否超过了上述最低严重程度的要求,应考虑以下因素:涉案群体的特征(例如,该群体的规模、内部同质程度、群体是否存在特定的脆弱因素或污名化历史,以及该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所处的地位);针对该群体负面言论的确切内容(特别是这些负面言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传达对整个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以及此刻板印象的具体内容);发表这些言论的形式和语境,涉案言论对该群体身份和尊严的影响;以及这些发言者的立场与社会地位。1See Behar and Gutman v. Bulgaria, no. 29335/13, § 67, ECHR 2021; Budinova and Chaprazov v. Bulgaria, no.12567/13, § 63, ECHR 2021.——译者注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上述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但各国法院在处理这类情况时应予以考虑。
在贝哈尔和古特曼诉保加利亚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国内法院未能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对涉案方的权益进行必要的平衡,也未能履行其积极义务以充分应对基于申诉人种族的歧视。欧洲人权法院进一步指出,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表达自由),由于攻击种族、宗教或其他群体的言论不应得到保护或仅仅应得到极其有限的保护,因此该政治人物的表达自由只能得到有限的保护(参见第105段,译者注)。
除了这两起关于种族歧视的重要案件外,欧洲人权法院还明确了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和第14条针对恐同暴力行为对国内当局所提出的应对要求。在萨巴利奇(Sabalić)诉克罗地亚案2Sabalić v. Croatia, no. 50231/13, ECHR 2021.中,申诉人诉称,在向一名反同人士透露了她的性取向后,她遭到了该反同人士在身体上的袭击,而克罗地亚当局未能向她提供足够的支持。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应当就申诉人的非金钱损失赔偿10,000欧元,因为克罗地亚当局错误地适用了谢尔盖·佐洛图欣(Sergey Zolotukhin)案3Sergey Zolotukhin v. Russia [GC], no. 14939/03, ECHR 2009.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未充分、有效地履行其根据《欧洲人权公约》而承担的程序性义务,以应对这种基于性而实施的暴力攻击。4Sabalić v. Croatia, no. 50231/13, §§ 114-115, ECHR 2021.——译者注在尤尔契齐诉克罗地亚案5Jurčić v. Croatia, no. 54711/15,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一致认定,由于涉及性别歧视,结合《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该案中存在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的情形,因为雇主拒绝向一位在就业前不久接受体外受精的孕妇提供与就业相关的福利(参见第84—85段,译者注)。
(七)针对家庭成员的虐待行为和家庭暴力
在库尔特(Kurt)案6Kurt v. Austria [GC], no. 62903/15,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审查了奥地利当局采取预防措施的积极义务,以保护那些因他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生命威胁的个人。该案中,申诉人称,奥地利当局未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保护她本人和她的孩子免遭其丈夫的暴力,也未采取措施防止孩子被其父亲谋杀这一明显真实的、紧迫的危险(参见第3段,译者注)。在与之前的案件——例如奥斯曼(Osman)诉英国案1Osman v. the United Kingdom, 28 Octo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I.和布兰科·托马希齐(Branko Tomašić)和其他人诉克罗地亚案2Branko Tomašić and Others v. Croatia, no. 46598/06, ECHR 2009.——进行对比后,欧洲人权法院认定,本案中奥地利当局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因为“当局在回应申诉人关于家庭暴力的指控时非常迅速,履行了必要的特别勤勉义务,并妥善考虑了案件具体的家庭暴力背景”3Kurt v. Austria [GC], no. 62903/15, § 211, ECHR 2021.。据此,欧洲人权法院重申了其确立的判例法: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采取预防性行动措施的义务是一种手段意义上的义务,而非结果意义上的义务,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审查一国是否遵守第2条规定的义务,需要分析该国当局进行的风险评估是否充分,以及在触发作为义务的相关风险已被察觉或应被察觉的情况下当局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是否充分”4Ibid., § 159.。
与此相反,在图尼科瓦(Tunikova)和其他人诉俄罗斯案5Tunikova and Others v. Russia, nos. 55974/16 and 3 others, ECHR 2021.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俄罗斯当局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和第14条,因为俄方未采取妥善措施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也未对四名申诉人受到伴侣或(前)丈夫伤害的情况进行有效调查。欧洲人权法院指出,俄罗斯尚未制定专门法律以解决在家庭中发生的暴力,且俄罗斯已有的立法中也未以任何形式界定或提及“家庭暴力”这一概念(参见第87段,译者注)。在沃洛丁纳(Volodina)案6Volodina v. Russia, no. 41261/17, ECHR 2019.判决两年后,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中再次发现,俄罗斯当局仍未通过打击家庭暴力的立法,也没有为实质上的性别平等创造条件,以使得女性能够免于被虐待的恐惧。欧洲人权法院为此适用了试点判决程序,并正式提出“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不仅仅是由孤立的个案或特定事件的转变造成的,也源于有缺陷的立法”7Tunikova and Others v. Russia, nos. 55974/16 and 3 others, § 149, ECHR 2021.,要求在国家层面实施一般性措施。同时,欧洲人权法院决定将继续以简化流程、加快处理速度的方式处理类似案件。
(八)与精神健康有关的问题
萨夫兰(Savran)诉丹麦案8Savran v. Denmark [GC], no. 57467/15, ECHR 2021.涉及驱逐一名长期定居于丹麦的外国公民的问题。申诉人实施了暴力犯罪,被诊断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针对申诉人的驱逐令于2009年下达,但直至2015年申诉人的精神状况才允许对其执行驱逐。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确立的判例法,驱逐一名将死之人自动触发《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1See D. v. the United Kingdom, 2 Ma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I.对欧洲人权法院而言,可能还有其他例外情况,即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遣返重病的外国人。上述例外可能出现在以下情形中:当一名重病患者被遣返时,考虑到在接收国缺乏适当的治疗或没有得到治疗的途径,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或她将面临现实风险,其健康状况将会严重、迅速、不可逆转地恶化,导致身体极度痛苦或预期寿命大幅缩短。2See Paposhvili v. Belgium [GC], no. 41738/10, ECHR 2016.
然而,萨夫兰案中的情况“未达到《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规定的门槛,无法将申诉人的申诉纳入该条范围”3Savran v. Denmark [GC], no. 57467/15, § 146, ECHR 2021.,但是依据第8条,该案中的情况构成了对申诉人私生活的侵犯。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规定,欧洲人权法院同意,严重刑事犯罪可以构成驱逐的“非常严重的理由”。4Ibid., § 194.——译者注这也与本案相关,因为本案申诉人实施了具有暴力性质的多种犯罪,即使专家认为其攻击行为是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也不能被单纯视为青少年轻微犯罪。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丹麦法院没有考虑申诉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这一状况,这导致申诉人与一般的“定居移民”相比在面对驱逐时更容易受到伤害。5See ibid., § 198.此外,丹麦法院没有考虑到申诉人个人状况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到申诉人与居住国有着牢固的社会、文化和家庭联系的事实。6See ibid., §§ 198 & 201.——译者注由此,丹麦法院的判决以防止混乱与犯罪为目的,在决定驱逐申诉人时将重心置于公共利益,没能适当考虑和平衡所涉及的利益。本案可以与马斯洛夫(Maslov)诉奥地利案7Maslov v. Austria [GC], no. 1638/03, ECHR 2008.作对比,在后一案件中,奥地利当局下达了驱逐一名保加利亚国民的命令,该保加利亚人在未成年时所犯下的罪行主要是非暴力性质的罪行(在14岁和15岁时入室盗窃、敲诈和殴打他人)。
四、结论
2021年5月21日,(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第131届会议在德国汉堡举行,由德国外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担任会议主席,成员国重申了对“作为各国人民共同遗产以及个人自由、政治自由和法治真正源泉的价值观”的承诺。1Council of Europe,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Forthcoming Activities, 131st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Hamburg (videoconference), 21 May 2021], CM/Del/Dec(2021)131/2a, point 4,https://rm.coe.int/0900001680a28ddc.然而,对2021年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的分析表明,传统制度已经步入了新阶段。案件判决的具体结果取决于各国自身情况,且最终取决于每一案件的具体案情。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在各个领域的实质性趋势差异很大,从对被告国进行较为宽松的审查,到采取更大胆、更有利于申诉人的解决方案。然而,欧洲的人权状况面临着若干挑战,欧洲人权法院是确保人权保护有效性的重要主体。欧洲人权法院若要保持其判例法的长期可持续性就意味着要进行谨慎的(尽管有时会引起争议的)平衡,同时也要考虑《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的共同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