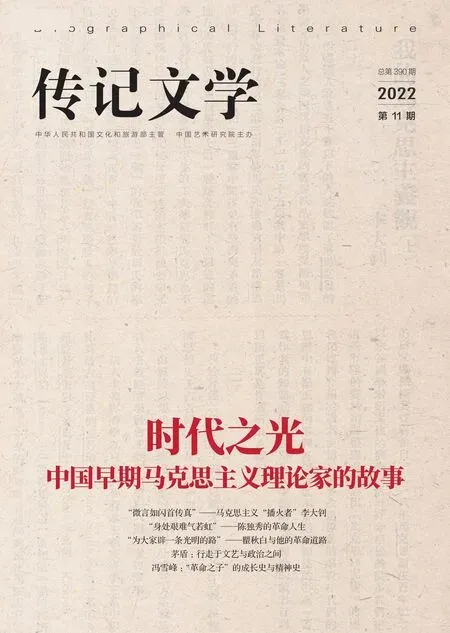遇见美好
——我的问学之路
熊 明

《传记文学》邀我写一个学术自传,本觉得过往平生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可以称道的,每每回首,总不免有“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之叹,尚一事无成,居然就老了。因此总不愿回顾,害怕徒增感伤。但转念,半生已过,无论如何是该认真回顾一下了,不能一日三省身,50 年一省身还是应该且必须的。于是,答应了。因忆数年前,曾作《自叙传》,数载之后,好像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也没有多大差别,或许“我”一直就是这样——除了与岁月俱增的年龄,还有稀少了的头发、佝偻了的腰身和蹒跚了的步伐。所以,仅加上一两句近况的概括,就是过去的、现在的“我”:
熊明,字伯亮,庚戌岁冬月生于四川南充。自始学之年,即负笈他乡,辗转北南。幸得游南开园,师从李剑国先生,学治中国小说史。后乃居盛京,筑室蒲河之阳。更徙青岛,卜居崂山西麓。教授生徒,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文献、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与文献之研究整理。尤耽唐人小说,赏其意趣,故累年沉醉。然天资驽钝,虽不舍昼夜,竟所获无几,案前萧瑟。课徒为学之余,亦不废文章之事,每感风物,必有所作,如或一二语可称,则往往半日欣喜。性沉静少言,好音乐书,亲山爱水,疏宕简易,来去随趣,偃仰任心,故生涯寥落。惟得半窗烟霞,晨昏蒸蔚。意其或可呼龙而耕,播植瑶草,犹堪略慰蹉跎。遂自号呼龙耕烟客,题其见方之室曰耕烟堂。
此《自叙传》的初版曾作为我的简介,贴在我工作过的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官网的“师资力量”栏下的“熊明”词条中。这确实是“我”,就像一张素描自画像,或者白描剪影。
自觉于学问之事,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绩可以称述,也总结不出什么可资借鉴的心得与人分享,倒是一路问学,得到许多师友的扶持帮助,许多美好可以一记,一方面以备不忘,另一方面也正好向他们表达一次我的感激与感恩——我性讷,不善于表达。
少年何处立斜阳
我农历冬月出生。1985 年7 月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报考的是南充县师范学校。后来南北栖止,偶有查问早期学历的时候,我总会耐心地向疑问者解释我的中师学历。这也让我偶尔假设,如果当年报考的是高中而不是师范,我会不会还是现在的我?那一年9 月,我入学南充县师范学校,成为一名师范生,按照当时的政策,三年后我将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师范生活没有学习压力,校长、老师挂在嘴边时时强调的,是要培养做老师的能力,学会备课、讲课和掌握作为一名教师的基本功,比如讲课技巧、粉笔板书、设计黑板报、油印试卷,等等。刚入校时,特别高兴的是,小学初中时常常盼望却常常被主科占去不上的音乐、美术、体育课,却成为师范的重要课程。但后来发现,我在音乐、美术、体育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潜质。那时个子还小,基本条件不够,篮球队、排球队根本就进不去,学校开运动会时,一个项目也没法参与。音乐也一样,五音不全,三年中也就勉强认识了简谱而已。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港台音乐开始在大陆流传,觉得歌星弹着吉他唱歌的样子特别帅气和艺术,于是自己也买了一把吉他,但终究也没学好,倒是扛着吉他的几张师范岁月的照片留下来了,自我觉得特别帅,有港台明星的范儿。现在每每翻看旧时照片,还有些小激动。后来重点学美术了,美术课老师是一位师范刚毕业留校的学长,中国画特别好,又年轻有亲和力,我一点一点跟着学,还勉强掌握了一点国画基础,毕业后也偶尔画,但始终保持在自娱自乐的水平而小有退步。
师范虽然没有学习压力,但学校管理还是很严格的,上午、下午共八节课,从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到历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等,排得满满的,还有晚自习。晚自习基本没有课业,却又必须坐在教室里,也就只好看书了。现在想来,一些基本的文学名著,应该是在那时第一次阅读的。读书除了从学校图书馆借书,那时还有一个来源,就是舅舅的藏书。
舅娘就在我的家乡喻家小学教书,我小学三年级后从本村小学转到乡小学上学,最初就是在舅娘当班主任的班。舅舅此前是一所小学的校长,因为一次公务触电受伤,然后就“退休”了。“退休”后,舅舅住在老家走马乡的乡间祖屋——那也是我母亲曾经生活的地方。舅舅常常来看舅娘,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很严肃,读小学的我不太愿意跟他说话,每次见他来,我总是向他问好后,马上借故远远地躲开。我上师范后,舅娘也退休回到走马乡的乡间祖屋去了。每年寒暑假,特别是寒假,我都要去老家看望他们。这时见到舅舅,也终于没有了畏惧感,可以和他坐下来慢慢聊天。我们常常坐在堂屋的方桌前,舅舅说话慢悠悠的,说话时有时看着我,有时望向门外的院子。
舅舅很用心经营这个院子,栽植了各种花木,其中就有腊梅,我家的农村是没有的,因为腊梅不是经济作物。以前我也就在书上读到过腊梅的描述而已,在舅舅这里见到了实物。他总是要先问我学习怎么样?在一问一答中,也会聊到比如怎么当老师,师范都训练了什么。记得有一年寒假,我说到正在学油印技术,他还拿出家里的一套油印刻字的钢板和专用笔、油印纸,要我练习刻写。我说在学校练过,他说:“要多练,刻字要写得像书上的宋体字,才好看。”于是我只好接过来,练习了一个假期。这个油印技术,在我毕业当老师后,基本没有用上,因为很快电脑普及了,试卷等全部电脑打印制作。不过,师范三年里还是用到过的,我曾和几个同学用这个技术出过几期油印的文学刊物。
当我们沉默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就会隐隐闻到门外腊梅传来的幽香。这时,舅舅站起来,去他的书房抱出一堆书来,说:“这些书你要读一读。”有普希金的抒情诗选、拜伦诗选、华兹华斯诗集、耶鲁达诗集等,还有《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小说。这些书我或者读一个假期,或者接下来的整个学期,然后下次去舅舅家时,再换一批。我想,也许从那时起,心中就有了一个文学梦、诗人梦。虽然最终也没有成为诗人,但诗心永在,给了我看世界的另一种眼光。
记得舅舅给我的书中还有不少种类的杂志,其中的《名作欣赏》让我印象深刻。那时的《名作欣赏》还是月刊,有许多关于中外文学名篇的鉴赏,只是已记不起一个作者的姓名了。读这些文章,让我意识到,原来文学可以欣赏得如此个性。
大约应该是师范二年级时,有一天学校举办了一场讲座,主讲者是来自当时四川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彭华生教授,他胖胖的身材、洪亮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彭教授讲座的主题是诗文中的通感运用,他举出古代诗歌中的许多例子,并提到钱锺书先生的《通感》一文,让我知道一句诗的背后,还有那么奇妙的阐释。
从舅舅那里读到的《名作欣赏》和听彭教授的讲座,是我最早接触到“文学研究”和“学术”,像一道光照进迷雾笼罩的森林,让我混沌的心灵开始一点一点清晰起来。舅舅“退休”后生活清雅,乡间祖屋外种植花竹,室内堆叠盆景。曾见他有座微山水盆景,十分别致,如同一幅立体的国画山水画。他和同好品茶书画,定期雅集,还曾送我当地书法名家的条幅。舅舅几年前去世,那时我在沈阳,表哥没有告诉我,我没能赶回去。
舅娘生活清简,九十多岁了,还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她善于把一个懵懂儿童变成一个小学生,所以只教一至三年级。记得我刚从村小学转到乡小学读书的那一年,有一次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邻村的一名学生挑衅我,故意要激怒我,我针锋相对,差点跟他打起来。当时,很多同学围观。第二天上学刚进教室,舅娘就很严肃地把我叫到教室门外,让我反思犯了什么错误。这是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学校被罚站。我很紧张,但思前想后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舅娘走过来,板起面孔厉声问我:“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吗?”我倔强地说不知道。她说:“你还想跟人打架?本事大了?”听舅娘这么说,我才意识到原因,本来委屈的我更加委屈,哭着说:“不是我惹他,是他惹我,故意找我生事的。”“他找你生事,你就要跟他打架吗?你可以不理他,或者跟他讲道理,选择要跟他打架解决问题,你就有不对。”舅娘一定要我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才让我回教室上课。这件事让我委屈了很久,想不通舅娘为什么一定要我承认错误,而明明并不是我生事在先的。很久以后才明白,凡事都需要从自身先寻找原因,有时退一步的逊让,可以改变一件事的进程,才给许多可能留下了时间和空间。舅娘让我保证不再犯,不只是少年时让我避免了与他人后来可能的一次冲突,还教给我一种处世的方法。
1988 年7 月,我从南充县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了当年我上学的本乡中心小学喻家小学当了一名教师。那时,喻家小学是小学和初中合校的,当时的校长陈世雄老师曾经是我小学5 年级时的数学老师。世雄老师胖胖的身材,方脸、短发,自带一种威严,他经常在学校到处走动,在教室门口一站,吵闹的教室立即就安静下来。那时正是商品经济兴起之时,在我的家乡川北山区,年轻人已开始大批南下打工,大多数学生其实就是想等初中一毕业,然后就外出打工,认真学习的孩子比较少。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一心想把学生教好,有些急躁,还曾体罚过学生。后来想起,常有些后悔,孩子们都在懵懂的年龄,如果我能耐心一点,或许有不一样的效果。
师范期间养成的读书习惯,工作后没有丢掉。那时各种夜大、函大的学历教育、自学考试十分兴盛,我知道自己的中师学历和知识储备远远不够,继续学习提升自己是必要和必需的。毕业后第二年,我决定参加大专自学考试,选读的专业当然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在四川省的主考院校是四川师范大学,川师大的一家辅导机构打出广告,二年之内考完全部课程、获得毕业证,退全部教材费。记得全套教材费应该是300 元左右。那时在小学任教,一个月工资到手不到50 元,一年下来,我手里的钱也不够买一套教材。只好向父亲借钱,并说一定两年考完,退回的钱再还给他。因为自己已工作挣工资,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再向当农民的父母要钱。我用从父亲那里借来的钱从那家辅导机构买了教材,开始了大学专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并在一年半时间全部通过考试,拿到了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证书,也取回了交纳的全套教材费,还给了父亲。
自学考试一年两次统一考试,考点设在县城。同年或前后毕业的许多中师同学都参加了自学考试,因而这两次考试就不仅仅是考试,还能见到同学和朋友,也是两次定期的聚会。我的表哥中师毕业后,在他的家乡走马小学教书,后来也参加了自学考试。有一次考试时我们住在一个宾馆,他考前一直在复习,而我却去见同学和朋友。他问我:“这么有信心?明天考试,今天不用再看看书了?”我说不用。我所有课程都是一次性通过,他有课程还曾重考。后来他说:“还是你学得好。”我说:“这要感谢你啊。”
是的,教会我学习的,有两个人需要感谢,一个是我的外公,一个就是表哥。外公也是老师,据说1949 年前就是,1949 年后在南部县教书,六七十年代一段时间学校停课,他也曾回农村种地,改革开放后重新回到学校。退休后小姨接他的班,在南部县升钟中学的后勤上班。初一时我在本乡喻家小学初中部上学,初二便转学到升钟中学,寄住在小姨家。那时,外公周末会抽出时间检查我的课业。外公特别强调理解能力,要我每天自己总结每门课学过的内容,以提纲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个训练让我终身受益,在后来的学习中,这成为我的习惯,我总能精确地总结出新知识的要点,并迅速掌握它们。外公瘦瘦高高,精神矍铄,年轻时一定十分帅气,说话声音低沉,有些沙哑。有时他也会急,当我第二次犯同一个错误的时候,他的声音就会提高,皱着眉头,特别严肃。那时的我总有一个感觉,好像我不是他的外孙。不过,这也让我养成一个习惯,牢记曾经的错误,避免重犯。
初二结束,我又从升钟中学转学,到表哥所在的走马乡中心小学初中部读初三。表哥正教初三语文,我便插班在他任课和担任班主任的班级。中小学老师都有教学用书,出入表哥家,我有机会翻看表哥的语文教学参考书。教参对每一课的提示,常常从具体的内容入手,指导教师如何一步一步分析得出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如何分析关键或重点文句。在不经意的翻看中,我收获很大,学会了如何去分析一篇文章,找出其中的关键和重点。表哥那时也订阅各种杂志,比如应试的《作文》,非应试的《萌芽》《十月》《人民文学》。《作文》是重点要看的,初三时间紧,但有时也偷偷翻一翻《萌芽》等杂志,新意而新奇。现在想来,从那些不经意的阅读中收获了许多启发。表哥名秦生,瘦高,音声如钟,我常想,如果他去学音乐,说不定会成为歌唱家。我们相差十余岁,后来人生的许多关键时刻,我总会去找他,跟他商量。表嫂特别乐观开朗,让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她家来去。几年前,她因急性哮喘发作,不幸去世,我很怀念她。
毕竟长风起大荒
修读完自学考试专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我意识到自学的不足,眼界局限在仅有的几本书上,获得的知识有限。那时,各级教育学院面向在职教师招生,开设脱产专科、本科学历教育。我希望能脱产学习,继续提升自己。按照当时规定,脱产进修需要县教育局同意并分配名额,获得报考资格。于是1991 年3月初的一个周六(那时一周还是单休周日,周六上班),上午一二节上完课,我决定到县教育局咨询一下有关政策。先搭乘客运汽车到龙门镇,然后换乘从龙门镇到县城的客运汽车。那时交通还很不方便,我只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匆匆赶到县教育局时,应该已是下午4 点多,快到下班时间了。教育局的院子里静悄悄的,三层的办公楼,大多数办公室关着门,一楼左侧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还开着门,而我知道,正是这个当时教育局这个部门主管全县教师的考核、进修和培训等事项。我怯怯地走到门口,办公室最里面靠窗处放一张办公桌,左侧坐着一位男士,四十多岁的样子,他转头问我:“有事吗?”我快步走过去,首先介绍自己,并告诉他我如何在一年半之内考完专科,但觉得知识储备还很不够,希望能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想咨询报考脱产进修本科的规定和程序,并小心翼翼地问:“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名额,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报考名额?”他静静地听完我说话,一直上下打量着我。听我说完,他沉默了片刻,说:“今年的成人高考,现在正在报名。”于是打开另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册子,翻看起来。说:“普通高校的成人脱产进修名额已经没有了,四川教育学院还有空额。”“也行啊,行啊。”我急忙说:“我想报考中文专业。” 他来回翻看了册子上的几页,说:“中文专业没有名额了,历史专业还有,历史专业你学不学?”我不假思索地说:“学!只要是有学习的机会。”他说:“好,一会儿正好要开会,我们会讨论一下你的情况。你把联系方式留下,等消息。”我说:“既然马上就开会,我就在这里等吧。”他说也行。于是,他站起身离开办公室,上三楼开会去了。而我也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在教育局院子一角等待。一个小时后,他开完会下楼,我急忙从角落里跑过去,他看见我说:“定了,给你报名。”
这样,在意料之外,我获得了当年报考四川教育学院历史教育专业本科的名额和资格。后来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新任的县教育局政治处主任,姓卢。接下来忙着备考,录取后也没有去找他表示感谢,实在是有些失礼的。但第一眼见他的样子和在我介绍自己时他那温厚的眼神,一直留在记忆深处,每每想起,便有温暖从心底泛起,潮湿我的眼睛。我并默默地祝福他,正是他无私的决定,让我获得了进一步学习和提升的机会,也因此使我能站到一个新的起点。
1991 年3 月初的那个下午,当我走出县教育局的时候,夕阳西下,正在沉入西山白塔下远处的嘉陵江中。新绿泛泛,春花簇簇,傍晚幽凉的气息胀满我的胸膛,我的脚步有些飘忽,似乎要在空气中浮漾起来。
已是下午5 点多,没有客运汽车班车回去了,我便在县城住下来。有了资格,我该怎么考?这个难题让我很快冷静下来。1991 年成人高考的考试时间是5 月11 日至12 日,从获得报名资格到考试一共只有三个月时间,考中文专业还有些基础,考历史专业就不一样了,以前没有系统学习过历史专业的课程,如何备考才能顺利通过考试,不至于白白浪费这个难得的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三个月内补足历史专业知识,达到大纲要求的水平。这需要阅读历史专业教材和相关书籍,然而书去哪里找?一番搜寻,最终我想到了在南充市的四川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当时,南充县和南充市还没有合并,南充县城高坪镇和南充市隔嘉陵江相望,四川师范学院在南充市内。
我有一位堂伯父在四川师范学院后勤处工作。第二天,我从南充县城的高坪镇过嘉陵江到南充市,找到伯父,向他说明我想从学校借书的想法。伯父听说我是为了学习,十分高兴,说这一定要支持。他马上联系他熟识的教务处处长,通过他又联系到图书馆领导,图书馆领导同意为我办一张临时借书证,这样我就能顺利地走进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借书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大学图书馆,宏大的图书馆让我震惊和欣喜,能随便进出这样的图书馆多好!看着学生们进进出出,我羡慕不已。一个上午,我在图书馆的历史书类书架前,挑选了包括全套历史专业教材在内的五十多本书,打包成一捆,下午出发,辗转从南充市返回我所在的喻家小学,开始三个月的高强度补习。因为借书给我,我一直对四川师范学院心存感激,在那个找书困难的小县城,她没有拒绝一个乡村教师的借书请求,而正是这些书,让我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在1991 年9 月,脱产入学四川教育学院历史系学习,成就了我的大学梦。
四川教育学院两年本科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专业课程开设特别全面,而我在这里,也如愿以偿地领略了个性鲜明、各有专长的老师们的风采。
随着眼界的开阔,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心中长久以来朦朦胧胧、未曾唤醒的追求,过往我学到的、获得的“文学”“历史”,只是“知识”,只是“事实”,我希望探寻这些“知识”“事实”背后的生成逻辑,真正走入对“文学”“历史”的研究。由此我树立了下一个目标:考研读研。
但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面前,研究生入学考试都要考外语,而我从未系统学习过任何一门外语。怎么办?立即学!我很快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了学得扎实,一步一个脚印,我买来全套初中英语教材、高中英语教材、大学本科的《大学英语》教材,从零开始学习英语。如果要在四川教育学院本科毕业时就参加研究生考试,按照考研时间,实际上只有一年半的准备时间。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时间表,每天从早上6 点开始,到晚上11 点半教学楼封闭,一周六天,除了上课,其余时间精确安排。空出周日一天,用来到其他学校听讲座、买书、整理内务。平时如有好的学术活动,临时调整。
1992 年10 月,研究生报考开始,由于脱产学习并没有调转户口和人事档案,按照当时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规定,我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南充地区招办报名点报考。那时,成都和南充之间既没有通火车,也没有高速公路,两地之间来回要坐6 至8 小时的长途汽车。为了不至于来回奔波,我准备好报考材料,包括四川教育学院历史系为我出具的一封报考介绍信,在报名开始的前一天回到南充。报名开始的第一天,我早早来到南充地区招办的报名点,向工作人员提交材料。工作人员看完材料,告诉我说,你虽然是应届本科毕业生,但属于脱产学习,有工作单位,这得咨询省招办,看是否需要人事档案所在单位的介绍信。他记下我的信息,让我等待消息。我于是便从南充市横过嘉陵江,来到南充县教育局。卢主任已不在政治处工作了,工作人员跟我说,你这个情况特殊,还在脱产学习,能不能给你出具介绍信,我们得报给局领导批示。他也记下我的信息,让我等待消息。这样,今年还能不能报上名,也就成为一个未知数。
连续三天,我每天一趟南充地区招生办和南充县教育局,报名点报考人多,工作人员十分繁忙,县教育局政治处工作人员说,已上报,还没有结果。我意识到今年报考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不能因此耽误了正常的学习,便委托在南充教育学院读书的中师同学苏海明君,接下来几天一直到报名结束,替我到两处探问结果,我则坐长途汽车返回成都。那时,海明君、龙万平君和其他几位同学一直在帮我想办法,宽慰我,让我不至过于焦虑。
回到成都,我迅速安定下来,和从前一样继续按部就班地学习,准备明年报考。那应该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晚饭后,我收拾好书包,站在寝室窗前,正准备去找教室学习。窗外,夕阳照在楼下人民南路人车如流的街上,马路中间的汽车道在密集错落的灌木与杉树掩映下,并不嘈杂。倒是两侧宽阔的自行车道上密集的自行车车流,引人注意。那时出行,自行车还是主要工具,下班高峰,安静地流淌,偶尔一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那一定是青年学生骑车在车流中快速穿梭,炫耀车技和速度。两旁竹影婆娑,世界繁忙而沉静。这时,一位身材高大、红红面庞的大爷来到寝室门口,问:“谁是熊明,熊明在不在?你南充的同学苏海明让我转告你尽快给他回电话。”我连忙道谢,谢谢他费力爬上六楼来通知我,立即到楼下电话亭给海明君回电话。电话那端,海明君说,今天招办说你可以报名,不需要人事档案所在单位的介绍信,你今年想考就再回来一趟吧。放下电话,我有些激动,立即再次请假,坐长途夜班车赶回南充。第二天早上6 点多,汽车停靠南充长途汽车站。离上班时间还早,我便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早餐店吃完早饭,一路步行前往南充地区招办。在南充早晨匆匆的人流中,独我脚步不紧不慢,左顾右盼,欣赏着从高楼间斜漏下来的阳光和阴影,潮湿的江风吹拂,心中也像有个太阳正在蓬勃跳跃。
报名点准时在8 点开始工作,我第一个领取表格。当年还没有网络系统,所有信息几乎全部凭借翻阅招办准备的一本本厚厚的资料、在表格上手写填入。在填写报考学校时又遇到一件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我原本查好并打算报考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史学史方向,但恰恰这一年杭州大学的招生简章上,没有列出史学史方向,史学史方向不招生。没有办法,我只好临时在一堆招生目录中查找设有史学史方向并且当年招生的学校,最终填报了辽宁大学历史系史学史方向。当时也没有思考很多,只看专业。然而,正是这次选择,让我与东北结缘、与沈阳结缘,开启了我在沈阳一去25年的人生旅程。
终于完成报考,剩下的就是努力准备,争取考好、考上。如今回顾,一切都那么完美和美好,我顺利达到初试线,进入复试,并顺利通过复试。在复试时见到我的导师顾奎相先生和田廷柱先生。
记得我是提前一天从成都坐火车到沈阳,绿皮火车,路上两天时间,还在北京站换乘,因为是在复试的路上,一路春风,倒也没觉得有多漫长。面试前一天晚上到达沈阳,当时辽宁大学还只有崇山校区,我找到学校并在校内的招待所住下来。第一次到东北,发现沈阳的夜来得比成都早,而晨光也来得早。当我一觉醒来,发现天大亮,一惊,以为自己睡过头,慌忙起身,一看时间,才凌晨5 点多。面对窗外的晨光,一惊之后睡意全无,也就索性起床,走出招待所游览校园。4 月中旬,沈阳的春天才刚刚开始,落叶的梧桐、杨树、柳树们光秃秃的枝丫才冒出些苞芽来。路边的草坪还没有转青,只是在向阳的墙角有些许的蓬松的生机,但一丛丛金黄的迎春花开得正盛,在初春的沈阳特别耀眼。是的,迎春花是沈阳春天的信使,迎春花开,就像一声呐喊,其他花们才应声次第开放。后来居沈阳近25年,就是这样看着迎春花开,迎接一个一个春天。
我提前半小时来到哲经楼三层历史系面试点。辽宁大学那时还有许多50 年代建校时的建筑,大多是三层高的板楼,灰墙红瓦的中式风格中夹杂着一些显著的苏联元素。哲经楼就是这样一座有着典型苏联特征的楼。多年后,哲经楼中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先后搬走,这座楼也被改称他名,但我一直仍称之哲经楼。田廷柱先生已经在面试室里了,他靠在一张桌上,双手抱在胸前,正和一位工作人员说着什么。那天田先生着深蓝色西服套装,系领带,高而挺拔,短而直竖的黑发中已点缀些白发,黑框眼镜,见我在室外探望,脸上带着和蔼的笑意,示意我进来,问我姓名。我赶紧走过去,鞠躬问好。知道我姓名后,他说,“我是田廷柱,带史学史方向学生,你有可能成为我的学生。”在后来的面试过程中,一位微胖、笑容可掬的先生问我看了哪些史学史的著述,我向他介绍了仓修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陈光崇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论丛》等著述,先生含笑未作评点。后来我知道,提此问的是顾奎相先生。
就这样与我的两位硕士生导师第一次见面。复试后,顾先生和田先生都说,回去好好多看原始史料,也要看当代中国和西方史学理论专著。从两位先生的叮嘱中,我提前感受到肯定的信息。不过,从那时到我再次来到辽宁大学报到入学之前,还有一个让人有些心惊的插曲。
从面试现场出来,我到研究生部去确认信息,并向学籍办的老师询问,我的家乡比较偏远,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发?能不能让我现在带走呢?“不能的,还有很多程序”,老师明确告诉我,不过又说:“倒是现在就能基本确定能不能录取,我可以帮你问一下。”于是,他拿起电话,我知道,应该是打给历史系办的研究生秘书,去向我的两位导师确认。他放下电话,说,没问题,你就准备9 月来读研吧。我于是很放心地离开,径直回到成都,继续完成在四川教育学院的学业。但一直到开学前,我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也曾询问研究生部,说早已寄出。所以,后来我是在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情况下,到辽宁大学报到并开始研究生学习的。报到两周后,研究生部学籍科的老师才找到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书退回来了,并把通知书给我。一看,才知道,收信的地址写错了,把“喻家乡”写成了“翼家乡”。
蜀石未许还堪琢
我是幸运的,硕士期间有两位导师。顾、田两位先生都治史学史,又都长于唐宋史。
顾先生著有《中国史学史讲稿》《司马光》《〈资治通鉴〉选读》等著作,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研究,进而开拓出中国古代改革史的新领域,先后完成《改革理论探索》《中国古代改革家》《中国古代改革史论》《亚洲史上十大改革》等著述。记得研一时,顾先生的《中国古代改革史论》刚出版不久,与我们谈起过他如何从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研究,拓展到古代改革史的研究。先生的研究进路,对我启发很大。顾先生时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公务繁忙,但他给我们开的课却从未耽误,在给我们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上,他要求阅读《史通》《文史通义》两部原著,掌握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理论,并要通读《资治通鉴》,认为阅读《资治通鉴》是初学历史、了解宋前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典籍。我能在硕士研究生期间通读一遍《史通》《文史通义》,正得益于顾先生的要求和督促,那时虽然还是囫囵吞枣,却也了解了两书的大意,为后来进一步精读积累了初步的阅读经验。而对《资治通鉴》的阅读,正是我后来硕士论文选择《通鉴纪事本末》为研究对象的知识背景。
田先生治学、授课十分精细,一丝不苟。田先生上课,穿着十分严谨,常常西服领带,讲课抑扬顿挫,特别清晰,而且时间安排特别准确,一节课的内容讲完,正好距下课2-3 分钟,与我们聊聊闲话。每次课都觉得像是一次完美的讲座。田先生主要治隋唐史,所撰《武则天》《唐明皇》等隋唐帝王传,流行一时,而《隋唐士族》一书,至今仍是研究隋唐士族的重要专著。研二时,田先生完成《东观奏记》和《明皇杂录》的点校,中华书局将其收入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成为此二书最为通行的点校本。《东观奏记》和《明皇杂录》刚刚出版,田先生签名赠我,那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与古籍整理相遇。翻看时,发现《明皇杂录》目录有卷上、卷下,还有“补遗”“逸文”“辑佚”,曾有疑惑:名目这么多?“补遗”“逸文”“辑佚”都是辑佚,为何不并入两卷之中?当时没有问先生。先生于课上,涉及史料,如有多说或歧异,也往往进行辨析,让我初步了解了史料辨析的基本方法。多年后,当我整理汉魏六朝杂传文献时,重翻田先生整理的《东观奏记》和《明皇杂录》,看到《明皇杂录》的分卷,才明白一本薄薄的《明皇杂录》,卷上、卷下之外,“补遗”“逸文”“辑佚”之设的真正学术意涵,对先生古籍整理的谨严也便有了更深的认识。
三年研究生时光可谓惊心动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幸运的,能那么顺利地考入辽宁大学读研,又那么幸运地遇到美好的老师、美好的同学,还那么幸运地与我的妻子在这里相识,并陪我一路走来。有时想,我那么偶然地选择报考辽宁大学,而后来的经历,又仿佛是造物主的安排,让我选择了这里,来到了这里。我一直对辽宁大学怀抱感恩之情,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留校任教,并在博士毕业后重新回到这里,一直到2019 年离开沈阳,移居青岛。
毕业留校任教后,顾先生和田先生依然对我关心有加。那时我和妻已结婚,学校住房很紧张,在顾先生的协调下,我们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窝”——一幢三层的筒子楼一层最西边北面的屋子,20 平米左右。我和妻子置办了几样简单的家具,就这样开始了高校“青椒”的生活。田先生听说我们终于有了固定住处,特意在一次课后,打电话给我,说要来看看。我在楼门口等他,正下课,学生漫道,田先生从两行榆树的浓荫中过来,依旧西装领带,风度优雅。我带着他穿过幽暗的走廊,来到最西头我的家中。先生坐下来,说很好,我当年初来,还没有这个条件,然后叮嘱了很多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刚走上讲台,十分忙乱。毕业后第二年,我才将硕士论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抽出,整理成文,题《论〈通鉴纪事本末〉的史学成就》,发表在《辽宁大学学报》1997 年第4期上。这也是我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改定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辽宁大学学报》编辑、也是历史系老师的申笑梅先生指点了很多。笑梅先生小小的个子,乍看外表十分柔弱,但却特别坚韧刚强,历经人间少见的屈辱苦痛而脾性不改,为人亲和友善。
毕业时,同届很多同学直接读博了。留校工作后,我和妻都意识到,继续提高自己是必须的。妻主动提出让我先考博读书,她来承担家务和照顾双方父母。于是我又开始了考博准备,经过再三思虑,决定报考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文学专业,并选定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小说方向。这次和考研不同的是,我多了一位时刻在身边可以请教的专业英语老师,妻是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方向硕士,与我一同留校,在外国语学院担任教师。我知道自己当时掌握的外语是不扎实的,而研究生阶段的外语课,只在研一时开设。所以,要报考文学博士,不但要系统地补习文学专业领域的欠缺,还要系统补习外语,实质性提高外语水平。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专著,也浏览了大量中外学者有关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学术著作,也购买了真正意义上我的第一批“专业”藏书。英语在“家庭教师”妻子的指导下,也有了很大进步。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在1997 年底博士生招生考试报名开始后,从容地选择了报考南开大学。
初试顺利通过,记得面试时陈洪先生和李剑国先生都在,两位先生都招收中国古代小说方向的博士生。两位先生特别亲和,本来特别紧张的我,也逐渐放松下来。临离开时,陈先生还笑着纠正了我一个字的读音。我报考的是陈洪先生的博士生,面试后不久,陈先生亲自给我打电话,当时陈先生是文学院院长,问我愿不愿意转到李剑国先生名下,因为当年孙昌武先生正在日本访学,无法招生,他需要协调整个文学院的招生。我表示只要李先生不嫌弃,我十分愿意。陈先生说,他已与李先生商议,李先生对我印象很好。就这样,我有幸能立雪李门,成为李先生的弟子。
记得第一次正式拜见李先生,我向先生承认自己跨专业的先天基础知识不足,表示一定努力弥补,先生安慰我:“这虽然是不足,但也是优势,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也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考察。你可以在这方面多思考。”第一学期,在先生指导下,我全面补习了小说史及小说理论、小说批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和文章。那时,先生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一版刚刚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细读书前的《唐稗思考录》时,注意到先生对唐人小说源头的判断,提到 “六朝志怪并不是唐传奇的唯一源头,虽然它非常重要,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先唐的历史传记小说,先唐历史传记小说是史传的直接支派”。而在更早的1993 年发表在《古典文学知识》的《怎样读唐传奇》的文章中,先生对此就已有了思考。在先生思考和判断的启发下,我决定将唐人小说作为我的重点研究对象,并拟从考察唐人传奇的渊源入手。
那应该是一个春天下午,我从图书馆出来,径直来到二楼李先生的工作室。先生每天到工作室工作,我们已养成习惯,去找他时都不用事先预约。敲开门,先生正端坐在靠窗的电脑前工作。工作室很简陋,三面书架上插满了书籍,桌上空余的地方也都堆满了一摞一摞的书。除了电脑桌,另外还有一张小桌,几把木凳。电脑桌是竖放的,先生坐在右侧,见我推开门,转头示意我进来。来到先生工作室,我们已习惯先拿水壶烧上一壶开水,先生拿出好茶泡上,然后,我们搬一把木凳坐下来,便开始了与先生特殊的“聊天”。当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与先生时,先生表示同意,建议我结合自己原来学历史专业的优势,在跨学科视阈下思考唐人传奇渊源,可以把梳理杂传与唐人传奇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这成为我博士学位论文展开的基本立足点,也成为我后来专注于杂传研究的最初动因和起点。当我的博士论文《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第一次在辽海出版社出版,以及后来经修订完善后以《汉魏六朝杂传研究》重新在中华书局出版时,先生两次作序。第一篇序作于2002 年9 月,那时先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访问;第二篇序作于2012 年7 月,两篇序文相隔10 年,而在两篇序文中,先生都谈到这一经过。每每读来,当年那个下午温馨的场面,就一次一次浮现在眼前。
做任何研究,一定要从阅读和掌握研究对象的原典及其相关文献开始,先生告诫我们,首先掌握有关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原典文献,要尽量做到涸泽而渔。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指导,是先生自己学术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唐前志怪小说史》的写作,就是以对唐前志怪小说的汇集、整理为基础。如今,不仅《唐前志怪小说史》成为研究志怪小说的必读经典,作为其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成果《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也成为志怪小说文本整理的经典。按照这一路径,我以《太平广记》为唐人小说的基本原典文献,开始了对唐人小说的细读。同时,也开始着手对作为其渊源之一的唐前杂传进行细读。然而,和唐人小说有《太平广记》这样的现成总集可以利用不同,唐前杂传虽在史志书目中著录宏富,却大多散佚,除了清人在辑佚其他文献时顺便的少量辑录外,没有现成的总集,甚至也没有小部分的汇编。要了解唐前杂传,就必须自己动手首先对其进行辑佚。
根据我国小语种导游缺失的现状,本文提出互助外语导游这一概念,以期充分地将现有资源进行整合,探讨如何以创新的方式有效缓解外语导游缺失严重的问题,利用互助导游的创新模式改善市场上外语导游供需不平衡的困境。
就这样,我开始一卷一卷、一篇一篇阅读《太平广记》,同时也开始对唐前杂传的搜集和整理。那时,电脑还主要是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刚开始出现,还是“奢侈品”。台式电脑无法移动,我每天带着纸质的笔记本和笔,一大早图书馆一开门就进馆,中间出来午餐、晚餐,其余时间都在图书馆一本书一本书地查阅,一条一条地抄录,一直到晚上图书馆闭馆,回到寝室。从书目开始,我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等历代史志,以及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历代私家目录,《玉海》《郑堂读书记》等笔记,一一翻过,不放过一条有关杂传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翻览《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水经注》等历代古籍旧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事类赋注》《天中记》《渊鉴类函》等隋唐至清代的类书,从这些旧注和类书中一条一条地辑录唐前杂传。回到寝室,再把它们录入电脑,并进行初步整理,如有疑问,就做好标记,第二天先查证前一天的疑问,再继续新一天的工作。
南开数载,那是忙碌而充实的岁月,除了先生开课之外,我和师兄弟们定期去见先生,请教疑问。先生有时很严厉,特别是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目的是让我们记住,成为以后治学的习惯。先生曾在辽海版《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的“序”(2002)中说过一段话:
在我10 多个博士生、硕士生里,我的感觉,熊明是那种读书非常刻苦,悟性也很高的学生。记得给熊明他们讲课,其实常常是聊天,我经常讲这些看法,有时针对学生的问题讲得很狠,我说,“响鼓须得重锤敲”,叫你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熊明每每笑嘻嘻地说,先生,我们记住了。我自信不偏爱哪个学生,一碗水端平,但也没少对其他学生说过熊明的好话,称赞他上路子很快,做学问用功、踏实。
这样的“聊天”时间很多,先生给我们上课时或其他我们拜见先生的时候,每次“笑嘻嘻”回答先生的教诫,我总在心里默念多遍,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牢记。而在自己做研究的过程中,也总常常回忆:这样的情况,先生是否有过教诫?从而也养成了疑问处反复琢磨、思考的习惯。
天津的旧书市场很好,周日有时也和师兄弟们相约去淘书。骑一个从二手市场买来的自行车,自行车可以很旧,但一定要有车筐,就是为了装书。那几年,各种方式买来的书很可观,古代小说研究的许多基本书籍,都是在那时买的。记得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电子光盘版刚出来,在南开工作的余才林师兄得到消息,通知我,我们一起骑车去买回来。我的电脑也因此有了第一套古籍检索系统,对我当时的杂传资料搜集和整理帮助很大。
终于,按照既定计划和目标,我完成了对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初步搜集和整理,有了这近400 种第一手的杂传文本及其相关文献资料,我如期完成了近50 万字的毕业论文《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论文从对每一种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微观细致考订与分析入手,进而宏观总结与厘定杂传的概念、分类等基本问题,梳理汉魏六朝杂传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文体特征,提出并总结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倾向及其具体体现,建构起了汉魏六朝杂传的理论体系。并以中国正统史传和古典小说建立一个立体的坐标,通过跨文史或者说兼文兼史的视角,对大量杂传从文体学和叙事学角度进行了个案分析,从而最终指向杂传和传奇文体的传承关系,明晰了传奇文体的渊源问题。
论文顺利通过外审,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肯定,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分别是石昌渝先生和谢思炜先生。石先生的《中国小说源流论》是我写作博士毕业论文时的手边书,先生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许多论断给了我很多启发。而在接送陪侍石先生、谢先生的过程中,也让我近距离切身体会到老一辈学者间温良的学术友谊,一直感动至今,并在后来的经历中,时时提醒自己以他们为榜样。
从来处处有芬芳
2002 年6 月获得博士学位后,我离开南开园回到沈阳,继续在辽宁大学任教。本来也是可以继续读一站博士后的,但最终放弃了。我想,在南开园李先生门下,我已获得了充分的学术训练并找到了学术方向。而且,家庭和孩子也需要我。
1998 年入学南开时,儿子刚出生一个多月,四年来陪他很少。记得有一次回家,妻开门,儿子在她身后怯怯地看着我,妻说:“儿子都不认识你了”,并把儿子抱过来,说:“爸爸呀,这是爸爸,叫爸爸。”我接过孩子,他没有叫爸爸,但轻轻趴在我肩头。我知道,应该多陪伴他了。自此一直到2016 年他离家上大学,儿子几乎每一天上学、放学,都是我接送,从最初上幼儿园他每天要求“第一个来接我”,到后来上高中时偶尔说“你今天不用来接我”,以一种日常而普通的方式,陪伴他读书成长。虽然他后来开玩笑说,我小时候你也不陪我打篮球、踢足球,要是那时候就陪我玩球,说不定我现在进国家队了。儿子好运动,我不善运动,没有陪他打球、踢球,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重回辽宁大学后,每天除了接送儿子和上课之外,我都埋头在故纸堆中,安安静静地继续在南开园开始小说和杂传研究。先是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整理,仍名《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交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其间请李先生作序。李先生那时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时正值中秋,我向先生和师母问候后,便有先生序中所记“中国的月亮小而圆,美国的呢”之问。这当然是源于20 世纪末十分流行的崇外风气,先生回答:“月是故乡明。虽来这里才一个多月,却油然生归焉之志,我很怀念我那些学生,怀念和学生们相处的快乐日子。”可见先生对这一风气也是不以为然的。书在2004 年1 月出版,学术书籍受众少,销售困难,书的印数不多,除了给我一部分之外,进入书店销售的应该很少,不久就很难见到了,记得2005 年左右,应该是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员,还曾问我要去30 册书,说是为了参加国际书展,但市面上买不到。
《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出版后,我开始整理写作此书时搜集的近四百种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文本,确立了采用辑校的整理方式,题《汉魏六朝杂传辑校》,并设计了基本的整理体例,将汉魏六朝杂传总分为两大类,一散传,一类传;并以时代为序,分为两汉杂传、三国杂传、两晋杂传、南北朝杂传四编;每一篇首标传名,次作者,继之题注和正文。题注对该传及其作者进行简单而精省的考证,正文分条辑录,以注释校对文字异同,以按语考证相关问题。在原来整理的基础上,再一次查对原文,补充新得资料。从2003 年到2007 年基本完成整理。于是在2008 年以“汉魏六朝杂传辑校与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并获得立项。
“汉魏六朝杂传辑校与研究”立项后,我意识到有必要略微转换对杂传的考察视角,从之前的小说主体视角,转变为杂传主体视角。于是,一边继续完善《汉魏六朝杂传辑校》,一边依据杂传主体新视角,并根据最新整理成果,修订《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书稿,易名为《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在此期间,为了调查国外杂传研究现状及拓展视野,我申请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于2009 年9 月至2010 年9 月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W)亚洲语言文学系做访问学者,合作导师是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先生。康达维先生治汉魏六朝文学,《文选》研究成就卓著,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对西方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学人及相关研究十分熟悉。在他的指导下,我利用访问学者身份,通过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系统,查阅了大量西方相关研究资料。在康达维先生身边的一年,也近距离感受了西方学者的学术研究方式,获得许多有益的经验。
完善《汉魏六朝杂传辑校》和修订《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两项工作在2010 年年初基本完成。从美国回国后,我即向全国社科办提交了项目结项请求。2011 年年初,以“优秀”等级获准结项。又经一年沉淀,2012 年年初,我将两部书稿《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与《汉魏六朝杂传辑校》打印并装订成册,投寄中华书局。半年后,俞国林先生告知,中华书局同意出版二书。我说与李先生,并请求他为二书作序,李先生同意了我的请求。本来先生已曾为《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为序,此次又另作一序,让我感动不已。书稿最初由李天飞君担任责编,中华书局编书特别细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于2014 年5 月方编定出版。《汉魏六朝杂传辑校》则根据书局的建议,改题《汉魏六朝杂传集》,经反复校对,于2017 年6月方得编定出版,前后6 年,其间天飞君从中华书局离职,改由俞国林先生亲自责编。《汉魏六朝杂传集》出版后,获得了学术界的许多肯定,被评为2017 年度中华书局古籍类图书年度“十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古籍整理是枯燥而沉闷的,为了纾解辑录、校对的疲劳,我把《太平广记》放在手边,做不下去的时候,便读几页《太平广记》。这样,在整理汉魏六朝杂传的几年中,我又把《太平广记》翻了一遍,也有了一些想法,于是设计为题,在国家社科基金结题后,即以“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为题,申报了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并获批立项。2014年年底完成了项目同名书稿《唐人小说与民俗意向研究》,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5 年5 月出版发行,2015 年8 月以本书作为成果向教育部提交了结题申请并被批准结项。
在翻看《太平广记》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太平广记》作为一部类书性质的小说总集,在小说史的宏观视阈下,《太平广记》在唐宋之交的历史时空背景下成书,不仅仅是总结了宋前小说成就、汇编了宋前小说而已,对宋以降中国小说的发展嬗变也有着重要影响,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考察。在思考并获得一些初步的结论后,2013 年,我便以“《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为题,申报了当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并获批立项。在接下来数年中,我一边按照书局要求校订《汉魏六朝杂传集》,一边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析。
为了考察和确认《太平广记》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作用、地位,我决定以小说文体特别是与中国古代小说特殊品格相关的基本要素,如叙事性、传闻性或虚构性、形象性以及文体体制等为核心,梳理一遍中国古代小说演进的历史过程,厘清中国古代小说作为小说的特殊品格的发生与演变,以确定《太平广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一次以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核心要素为中心对中国古代小说史进行梳理,最终以《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书稿的形式呈现出来。此书稿后来受到北京人文在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全额资助,2018 年1 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有了切实的把握后,我便将《太平广记》置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宏观视阈进行考察,2017 年年底完成了项目同名书稿《〈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并向全国社科规划办提交了结项申请,2018 年8 月被批准结项,书稿2021 年7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同时,我并没有停止对汉魏六朝杂传的关注。《汉魏六朝杂传集》为有佚文存世的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辑本的汇集,汉魏六朝时期还有大量散佚的杂传,散佚杂传相关文献的整理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因而,有必要对汉魏六朝杂传篇目及其相关文献做一次全面的调查和清理。2019 年,我便以“汉魏六朝杂传叙录”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并获批立项,随后便着手收集、整理汉魏六朝每一种杂传的全部相关资料,包括作者、文本、影响、传播等所有方面,一种一种撰写叙录。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到省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基金的支持,这些基金支持使我的思考从粗糙走向成熟、从大略走向具体,从设想走向计划,从计划走向行动,而在获得支持、研究开始后,它们也变成一种动力,促使我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好它、完成它。我是感激这些基金的,如果没有这些基金支持,我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想法和思考是无法付诸实施和完成的。
自2002 年告别南开园,小说与杂传研究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时光流逝,儿子长大成人,总觉自己只是徒增了年岁,翻看自己每一本小书的“后记”,发现自己一直都在感叹时光流逝,不待斯人。2004年辽海出版社版《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后记”说“岁月如流,不经意之间,已步入而立之年……面对镜中的自己,有时,我茫然不知所措:年少与青春的岁月,我在哪里?”2014 年中华书局版《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后记”说:“初游津门,余尚未及而立,于今不惑矣。每灯下困怠,举目暂望,寂然长夜,月隐矮墙,常生落落之思。昔青春年少……” 201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后记”说:“冬去春来,季节变换,总让人心常恨恨。时光流逝,年华老去,却发现镜中的自己,智慧不增,学问未成,而鬓发已疏,怎不让人唏嘘。”2017 年中华书局版《汉魏六朝杂传集》 “又记”云:“余去蜀北来,僻居关外,二十又三年矣,而乡音犹存……余多感,常恨花飞叶落,日迁月替,而岁月之不待斯人。”202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修订本)“又记”云:“时光荏苒,每回望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总让人惊悚诧异:这么漫长的一段岁月,竟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毕竟人生即使百年,和无尽时间的逝川相比,也是短暂而微茫的,面对一天一天时光的流逝而读书有限、所成无几,焦虑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2018 年,在基本完成《〈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的初稿之后,对一些问题的思考长久没有进展而让我茫然无措,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正好有驻访学者计划,于是我提出了申请并被接受。3 月初往杭州,驻访浙大高研院。驻访浙大高研院的三个月,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高研院设在之江校区,而驻访学者住在玉泉校区,每天从玉泉到之江,在之江古朴典雅的校园与布置温馨的工作室或独自看书,或与同访学者交流,让我凝固的思维重又慢慢打开。而穿行在西湖和周边的溪山林木间,重又让我“文艺”起来,每践一处一景,为文赋诗,颇得古人行游之趣。这期间,妻和儿子曾往杭州“探望”我,见我大不同从前,妻说:“看来你也是贪玩的,好多年不写诗了,居然又能写出诗来了,得让你多出来走走。”
这也是后来移居琴岛的最初动因。青岛临海,多山而秀,见而爱之。那年春节,向当时已从青岛大学移席中国海洋大学、主持古代文学学科的刘怀荣先生致问候,本是一句玩笑话,但怀荣先生认真的态度,让我也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最终同意了怀荣先生的建议。感谢怀荣先生,我是适合青岛的,山海间逶迤的晨岚与晚霞,崂山的春茶、八大关的秋叶,让我沉醉迷恋,也让我可以于其间沉思凝想。2020 年,经过深思熟虑,我以一直以来的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与小说研究为基础,申报了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中标,从而有机会对早已熟悉的中国古代杂传在更加宏观的层面展开研究。
从川北农村一路走来,我的问学之路虽几多曲折,但我终是幸运的,在每一次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有朋友温暖的援手;在我失路迷茫的时候,总有贤哲睿智的指引;在我困窘沉沦的时候,总有师长无私的提携。我曾在中华书局2017 年版《汉魏六朝杂传集》的“又记”中表达我的心声:“余不敏,而颇得长者垂怜,时贤顾惜,幸亦大焉。此《杂传集》及《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之终能成书梓行,当揖而谢者,复有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评审及结项鉴定诸先生,中华书局审阅研评及锤定刊印诸先生,其间乃有至今不得而知其人者,感佩切切焉。其奖掖原创,甘为津梁,诚道统之所在。”这不仅仅是一时一地之想,而是我心中一生一世的念。曾夜雨无眠,为诗寄兴云:
无端夜雨断肠声,
始忆青春客盛京。
寂寞书前怀贾谊,
温柔灯下愧菰羹。
新词且傍松风赏,
老酒宜添月桂烹。
即使从来萧瑟处,
落花满地也多情。
——《夜雨有怀》(2016.6.26)
是的,回首来路,虽然萧瑟,但处处都有关怀与关爱,一如落花,多情了我来路的每一天。曾坐在海大浮山校区草地的白石上看刺猬慢慢在灌木丛中爬行,看灰喜鹊从一棵树滑到另一棵树,又从另一棵树滑到草地,歪头翻开一片枯叶,细细打量。“常常想,人生原本应如此从容,春来看花,夏来听雨,秋来观风,冬来踏雪。作与息、停与兴、来与往,正与天地四时的消息相应。一切因缘自在,顺应而已。”(《〈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后记”)也曾在新近完成将要出版的一书的“后记”中说:“年年春来,草木枯而复荣,一季红紫芬芳,岁岁可期。如我不敏如斯,于学问一途,穷人生百年,能得一而有所成,已是奢望。惟孜孜矻矻,日将月就,以终岁月而已。”问学之路迢遥,我将以此为态度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