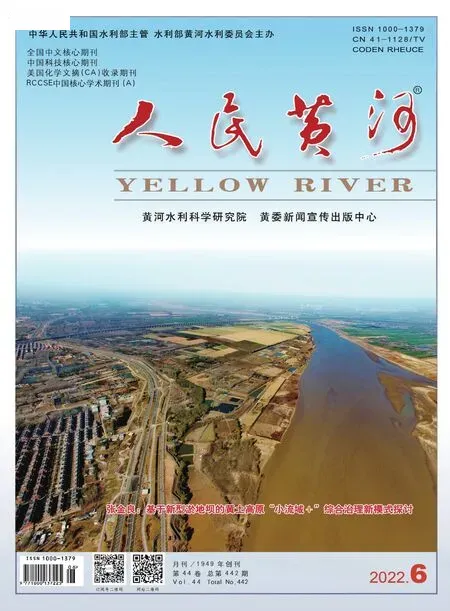基于《中国古代山水文学散论》分析苏轼山水文学的情怀与意境
李 娜
我国古代山水文学底蕴丰厚、特色鲜明,表现出古代文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思想理念。 其中,苏轼作为山水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宦游期间游历天下,留下诸多经典的山水诗词作品,极大地推动了山水文学的发展。 因此,研究苏轼山水诗作的情怀与意境对于了解山水文学的思想内涵、创作特点等具有重要价值。 由李亮伟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6 年5 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山水文学散论》一书,以作品文本为依据,系统阐释唐代至元代山水文学的演变历程,并深度解析苏轼、柳永等山水文学作家的作品风格与思想意境,弥补当前学界对古代山水文学研究的不足,具有良好的理论参考意义。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散论》选取了十几位古代著名词人,按照朝代更迭顺序,先后叙述各词人山水文学作品的创作思路、风格特色及蕴含的山水情怀。 其中,作者从唐五代山水词入手,简要分析这一时期山水词的写作手法、代表人物以及情怀意境。 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宋代山水词人的作品风格以及山水情结,尤其以苏轼为代表的“岷峨”情结,充分体现宋代山水词的独特意境,为人们了解苏轼山水文学创作特点提供了依据。 除此之外,柳永、叶梦得、张孝详等词人的山水词也是作者研究的重要对象,采用细腻的笔触深入分析各类作品的修辞手法、物象特点、情感内涵等,高度赞扬他们对宋代山水词做出的贡献。 该书以元代山水词收尾,深入分析元朝散曲前后的山水词作,并探讨元代山水楹联与隐逸派山水文学的情怀理念。
参阅全书可知,苏轼游历天下,留下40 余篇山水文,包括赋、跋、小品、诗序等多种题材,其中质量最好的当属苏轼贬谪时期的作品。 这一时期,苏轼正处中年,遭到曲折艰难的仕途打击,逐渐改变了锋芒毕露的外向型性格,变得更加沉稳老练、恬淡不惊,将创作重点从社会国家转变为人生问题,推动其文学成就更上一层楼。 系统梳理苏轼山水文发现,苏轼与山水之间的关系呈现动态变化特征,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具体变化过程如下。
第一,逃避山水。 苏轼初次创作山水诗,主要出于第一次离开蜀地的兴奋与激动心情,借“锦水”“蛮江”等山水意象抒发远离故乡、前往未知地方的不舍、留恋但又好奇的情感。 此时苏轼尚未与山水建立起紧密联系,只是作为路过的旅人记录途中所见的山水风光。 之后,苏轼在《过宜宾见夷中乱山》中写道“蛮荒谁复爱,穠秀安可适。 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描述了景物的基本特征与整体风貌,与山水景物建立起初步联系,表达出对于隐居山林的恐惧感。 总之,苏轼在早期创作山水诗时,未与山水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仅是从审美与观赏角度描绘周围景象,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疏离。
第二,迎合山水。 在前往杭州的过程中,苏轼与山水的关系由之前的外来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开始尝试与山水互动交流。 这一时期,苏轼的山水诗表达出强烈的思乡情感,用“我家江水”“我本山中人”等生动展示自身与山水之间的亲密关系,将思乡、思家之情寄托于山水中,使二者之间的情感更为亲切。 同时,苏轼继续深化这一亲密关系,与山水景物之间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交流。 比如,借助“令山俯仰”“与月徘徊”表达行舟感受,向山水诉说自身情感。 之后,苏轼与山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为知己,“东风知我欲行山”将东风比喻为有思想情感的人,体现出东风知我、懂我的亲密关系。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苏轼主动融入自然山水,将自然景物拟人化,与其开展深入的情感交流,甚至视山水为家乡,拉近了与山水之间的距离,达到人与山水相互融合的境界。
第三,关注自己。 离开杭州后,苏轼继续前往其他地方游览,但是与山水的亲密关系已经无法带给他新鲜感,开始试图在山水中找寻自我、了解自我,相比于山水景物,这一时期的苏轼更加关注自身的内心感受。 比如,“独专山水乐”表达出在游览山水过程中获得的愉快心情;“人生如朝露”形容人生短暂、时光易逝,要及时行乐,享受与山水愉快相处的过程。 由此可见,作者在这一阶段将自身内心感受放在首位,山水不再是知己或者家乡的象征,仅仅是愉悦身心的一种方式,
山水文学与政治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古代文人往往胸怀治国兴邦的远大志向,拥有自身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希望将一生所学用于治理社会、扶济百姓中。 但是在封建皇权统治之下,文人经常受到排挤,仕途波折不断、屡屡受挫,形成困顿失意的思想状态。 为此,以山水构建的自然艺术世界,使文人主动亲近自然,从残酷的现实世界中摆脱出来,在自然山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与安定,苏轼也是如此。 具体来说,苏轼的山水文学中蕴藏着如下情怀。
第一,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对封建文人而言,山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够带给人们饱满的活力与生命乐趣,进而产生通达乐观的态度与认识,沉浸在自然山水的美丽景色中,感受生命的欢乐。 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苏轼眼中的山是奇骏且宁静的,具有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美。 苏轼初到庐山,便沉浸于高低不平、此起彼伏的山林景色中,发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叹,读来使人顿生磅礴大气之感。 同时,在《石钟山记》中,苏轼描写了石钟山山林静谧的场景,无论是潺潺溪水还是鸟儿鸣叫,都无法打破山的宁静,同时也保留了自己心中的宁静。 除了山林景色之外,苏轼也充分表达出对于水的喜爱之情。 一方面,水是流动的,在不同的形态下具有不同的美感。 水面静止时,呈现出平静温和的美;缓缓流动时,呈现出清凉柔和的美感;激流涌动时,则显现出汹涌澎湃之美。 另一方面,水具有吉祥的寓意。 在《喜雨亭记》中,苏轼描写了农民由于下雨而欣喜若狂,许下来年丰收的美好愿景,表现出雨水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感。
第二,家国情怀。 山水文学固然描写了大量美丽的山川景物,但本质用意仍在于抒发情感、寄托志向。 苏轼以民生疾苦和家国大事为对象创作山水文。 其中,苏轼通过描写民间百姓的困苦生活,强烈批判现实社会和奢靡腐败的官场。 比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中,苏轼借助“海上港”“水底村”等景物描写,表达出对于当地山水的喜爱之情,但全篇的主旨思想则是批判官员贪污腐败。 同时,苏轼体察民情,常常深入民间走访,以“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的细腻笔触,书写农村雨后的美丽景象,表达出强烈的喜悦之情,体现出苏轼对于民间百姓生活的关照。 此外,在家国大事方面,苏轼寄情山水、以情明理,表达出对于国家治理的关切之情。 比如脍炙人口的词作《水调歌头》,借助凄清孤冷的月光表达人间悲欢离合之情,侧面反映出作者的仕途苦闷之情无处排解,只能自我慰藉、旷达一笑。
第三,放达之怀。 苏轼山水文前期采用长篇幅的赋、记形式,通过说理与议论表达自身观赏感受;后期则完全相反,不仅篇幅短小,而且改变了以往较强的说理风格,仅注重欣赏山水景色,从中获得愉悦闲适的心情,这反映出苏轼在经历长期的波折与坎坷后,在中老年时期转为清静无为、淡泊闲适的心境,对于仕途、名利、功绩等保持顺其自然的心态,只求内心的平和与清净。 比如,在《临皋闲题》中,用“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道出自身超然豁达的心态,认识到人生的无常与多变,开始关注自然山水的美丽风光,享受生活的美好与山川景物的滋养,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 苏轼之所以会经历这样的转变,是由于受到释道思想的深刻影响,经历过诸多仕途坎坷、人生磨难之后,苏轼秉持的儒家治世思想频频受挫,这使他感到愤懑与痛苦。 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开始将视角转向释家与道家的思想,尽可能远离世俗人情,回归到大自然中享受清静自在的生活。 因此,苏轼醉心于山水中,治愈自己苦闷焦躁的心理状态,让身心得到完全放松。
苏轼山水诗作运用多种艺术手法,采用精练的语言,生动描写出秀丽美好的山川景色,使山水景观更加传神动人,并且倾注了深厚情感,结合大胆奇特的想象力,营造出独特的山川意境之美。 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色彩美。 色彩是绘画的重要艺术语言,能表达出丰富的情感和艺术张力,增强艺术作品的生机活力。在我国古代绘画中,文人往往用水墨画来描绘山川景象,呈现黑白墨色变化。 因此,山水景象在诗文画作中总是单一的色调。 苏轼在创作山水诗时,大胆突破创新,运用多种色彩描绘景物特征,打造出色彩鲜明、生动艳丽的自然风光,为人们带来独特的艺术享受。 比如,“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运用深红、浅紫、雪白、鹅黄四种颜色,生动刻画出花朵竞相开放的艳丽景象;“黑黍黄粱初熟后,朱柑绿橘半甜时”,用黑色和黄色形容黍、高粱两种粮食作物,用朱红色、绿色形容水果柑橘,描写出春天物种生长的繁茂景象。 但是苏轼在取色、用色方面并非随意发挥,而是根据事物的外形特征选取相符合的颜色。 比如,“日上红波浮碧巘,潮来白浪卷青沙”分别用红白和翠青颜色进行对比映衬,描绘潮来之时江面上的美丽景象,既增强了视觉享受和艺术美感,也可以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第二,形象美。 苏轼山水诗作用词精炼准确,写作手法形象多元,使得山川风景跃然纸上,极具形象美。 比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借助鸭子、飞雁两种物象,描绘出春日时节万物复苏的美好景象。 虽然两首诗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都使用了“知”字,将春日时节南方春暖花开与北方风雪侵袭的物候景象联系起来,构成一幅生动逼真的春日图景,充分体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艺术想象。 再如,诗作《泛颍》中,作者运用变化多端的水景比喻世间之事的无常多变,具有一定理趣性。
第三,构图美。 苏轼擅于取景构图,将身边的一切美好物象融入诗句中,运用巧妙的手法将其串联起来,构成诗情画意的山水景色,呈现诗画交融的意境美。 在《夜泛西湖五绝》中,苏轼先从西湖的整体风貌入手,刻画出曼妙的湖水、夜晚开放的荷花以及扑面而来的荷花清香,寥寥数笔,勾勒出空旷寂静的西湖夜景,体现出景物的整体美感,表达出作者对于自然景物的热爱之情。 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中,侧重局部描写,从远处的黑云起笔,再串联雨点、船只、湖水等物象,勾勒出风雨交加下湖水浩瀚无际的壮丽景象,使得景物分布错落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