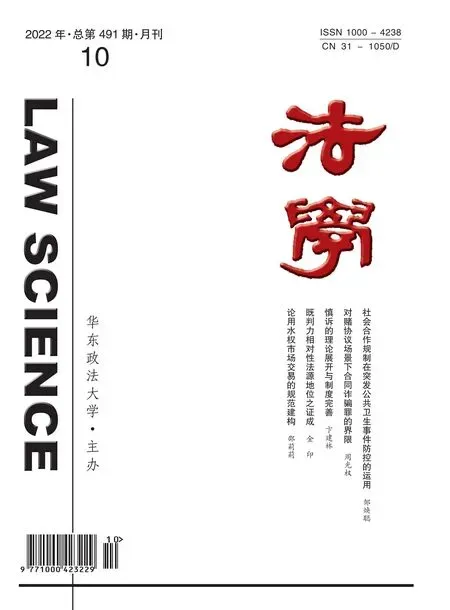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民刑防卫限度之协调
●康子豪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刑法和民法规定有关防卫限度的规范表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规范表述上的差异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我国刑法与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究竟应当将何者作为认定基准?对此,实务中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案。
案例一:为制止黎某2的攻击,黎某1用拳头将黎某2击倒在地,致其遭受轻伤。在本案中,法院主张,民法和刑法对于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并不完全相同,尽管黎某1在刑法上构成正当防卫,但仍然可能在民法上成立防卫过当。〔1〕参见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20)川0704刑初7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7民终3368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二:王某持菜刀追砍鲁某,鲁某受伤后即进行还击,致王某轻伤。在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认为,鲁某系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需赔偿王某的经济损失。〔2〕参见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楚中刑终字第1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案例三:陈某与杜某扭打在一起,其间杜某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刺伤陈某。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杜某的行为不构成刑法上的防卫过当,并据此认定其在民法上也成立正当防卫。〔3〕参见云南省施甸县人民法院(2018)云0521刑初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案例四:李某追打李德强,李德强在反击的过程中将李某打死。本案刑事判决认定李德强构成防卫过当,民事法官依据前述该判决认定李德强在民法上也构成防卫过当。〔4〕参见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2刑初23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2019)粤0282民初2312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判决表明,我国部分法院主张,在民法和刑法中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是一致的,而另一部分法院则认为,民法和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不同。事实上,如何协调民刑防卫限度不仅是实务中极具争议的问题,同样也是困扰理论界的重大难题。刑法理论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也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立足于违法相对论,少数见解采取了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认为我国民法和刑法就防卫限度采取了不同的判断标准。〔5〕参见高铭暄、王红:《刑民交叉视角中的防卫过当》,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65-74页。而当前学界主流意见则是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从违法一元论出发主张民法和刑法中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应当具有一致性。〔6〕参见于改之:《刑民法域协调视野下防卫限度之确定》,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第42-53页。
因此,研究如何协调民刑防卫限度的问题不仅有利于保证司法适用的统一;而且有助于推动学界对于防卫限度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实现问题性思考与体系性思考的统一;还可以加深学界对于法秩序统一性问题的认识,推动民刑法域冲突排除机制的构建。然而,尽管学界已经在协调民刑防卫限度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专门研究相关问题的文章不过寥寥数篇。细究起来,对于民刑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是否应当保持一致,如何保持一致,以及如何处理民刑相关规定间的关系等问题,学界都缺少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此外,在研究思路方面,当前的研究也大多仅围绕着防卫限度的判断与法秩序统一性间的关系展开讨论,鲜有学者从正当防卫的哲学基础等正当防卫自身的特殊属性出发进行研究。但是,如何协调民刑防卫限度毕竟是有关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问题,脱离正当防卫制度自身的特点研究这一问题并不妥当。
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正当防卫的特性,首先分析保持民刑防卫限度一致性的理论依据,然后探讨认定防卫限度的基本准则,最后明确刑法和民法相关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立场选择: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之坚守
在民刑防卫限度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上,主要存在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与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的对立。本文认为,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存在缺陷,相较而言,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更加合理。
(一)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的问题
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主张,民法和刑法对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存在重大区别,在个案中需要分别判断防卫行为在民法和刑法上是否构成防卫过当。〔7〕参见杨玉英:《正当防卫在民法和刑法中的区别运用》,载《前沿》2006年第9期,第138页。支持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的理由主要是违法相对论和我国当前有关防卫限度认定的立法和司法情况。但是,这些论证可能都缺乏说服力。
1.从违法相对论角度进行论证的不足
立足于违法相对论,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认为,民法和刑法的规范目的不同,导致民刑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不同。刑法放宽防卫限度是为了震慑不法侵害人,达到保护法益的目的,民法的规范目的在于平衡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需要放宽防卫限度以震慑不法侵害人。〔8〕参见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199页。上述论证看似合理,实则不然。
一方面,违法相对论本身就存在缺陷。该见解过于强调刑法自身的特殊性,使刑法在整体法秩序内陷入孤立,无法实现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有机联动,并且根据该观点,其他部门法上合法的行为仍然可能具有刑事违法性,也有违反刑法谦抑性之虞。〔9〕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王昭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另一方面,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即便肯定违法相对论,也不一定要采取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首先,违法相对论也要求法秩序具有合目的性的统一,在规范目的相同的场合,不同部门法对于同一行为的法律评价可以相同。〔10〕参见简爱:《从“分野”到“融合”刑事违法判断的相对独立性》,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2期,第443页。根据通说的见解,刑法〔11〕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10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26页。和民法〔12〕Vgl. Repgen, in: Staudingers Kommentar, BGB, 18. Aufl., 2019, § 227 Rn. 5 ff.规定正当防卫均旨在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并确证行为规范的有效性。既然如此,纵然采取违法相对论,也无法得出需要对防卫限度采取不同标准的见解。
其次,根据违法相对论,法秩序的合目的性统一还要求低位阶的规范目的不能与高位阶的规范目的存在矛盾。〔13〕参见[日]京藤哲久:《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王释锋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年第1期,第151页。在一国的实定法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在规范目的的阶梯中,某一制度的宪法目的无疑也具有最高的位阶,其他法律设置相关制度的目的都不得与之冲突。根据我国《宪法》第33条的规定,我国宪法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是维护个人权利,民法和刑法在设置相关制度时都不得违反这一目的。〔14〕参见魏超:《防卫权向生命权让步》,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124-125页。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在民法上为防卫限度设置了比刑法更严格的标准,致使实践中防卫人若要避免自己的行为被认定为民事违法行为,就只能按照民法确立的严格标准进行防卫。这种做法不利于保护个人权利,与我国宪法设置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相冲突。因此,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不符合法秩序合目的性统一的要求,即使从违法相对论出发也不应当采取这种见解。
最后,在违法相对论看来,为实现法秩序的合目的性统一,还必须要求目的的实现与采取的手段之间不得明显违反比例原则。〔15〕参见陈少青:《法秩序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载《法学家》2016年第3期,第18页。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通过限制民法中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来实现民法平衡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目的,这一做法便有违比例原则中的均衡性原则。因为,均衡性原则要求达成目的所实现的利益大于为实现该目的所造成的侵害。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的立场实际上是以增加正当防卫失败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不法侵害人,其所侵害的是防卫人的合法权益,却维护了不法侵害人的利益。由于在正当防卫的场合,相比于不法侵害人的利益,防卫人的合法权益处于质的优越地位,故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难免导致其所侵害的利益明显大于其所实现的利益,从而悖离比例原则的要求。有鉴于此,即便从违法相对论出发,也不应当采取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的观点。
2. 从我国法律实践角度进行论证的缺陷
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还认为,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后,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规定也经历了多次修订,但立法者始终没有跟随刑法的修改调整民法中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这说明立法者是有意为民法和刑法设置不同的防卫限度标准。〔16〕参见王洪芳:《正当防卫在民、刑法上的构成条件比较》,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00页。而且,在防卫行为仅造成轻伤及以下结果的场合,如果该案也被作为刑事案件处理,那么民事法官会采取刑法确定的宽松标准,从而认定防卫人构成正当防卫。与之相对,如果该案仅被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民事法官就可能根据民法规定确立的严格标准,认定防卫人构成防卫过当。这便导致我国民事审判关于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出现不协调之处。只有采取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使民事判决不受刑事判决的影响,才能维持民事审判标准的一致性。〔17〕参见高铭暄、王红:《刑民交叉视角中的防卫过当》,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71页。上述理由也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仅从条文规范表述的不同无法推出民刑防卫限度标准存在差异的结论。在我国法律中,不同用语表达相同含义的情况并不少见。譬如,根据相关立法解释,《刑法》第196条中的“信用卡” 就包含了银行法中的借记卡。而且,文义解释优先仅意味着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能超过文字可能含义的边界。在根据文义解释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性的场合,需要对法律条文进行目的解释。在防卫限度的场合,基于违法评价的冲突化解功能,可以认为民法和刑法规定表达了相同的实质内涵。〔18〕参见于改之:《刑民法域协调视野下防卫限度之确定》,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第46-47页。
其次,当前民事审判的现实情况只能说明我国民事审判实务并未严格遵守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不能据此认为应当采取民刑防卫限度二元论。如果严格遵守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那么在前述仅作为民事案件处理的场合,法官也应当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作为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认定仅造成轻伤及以下结果的防卫人不构成防卫过当,同样可以维持民事审判标准的一致性。
(二)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的合理性
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主张,任何防卫行为只要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就具有违法性,应受到禁止,民法与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相同,〔19〕参见陈璇:《防卫过当中的罪量要素》,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5期,第16-17页。本文赞同这种见解,理由如下。
1.合乎宪法基本原则的要求
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符合我国宪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其一,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与平等原则相契合。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了平等原则。通常认为,平等原则意味着法律在设置权利义务时不应因公民的种族等情况给予差别化待遇,对于相同的情况应当给予相同的对待。在此基础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进一步主张,根据平等原则,在法域交叉的情形,不同部门法针对同一行为的评价应当一致。〔20〕Vgl. BVerfG NJW 1996, S. 2086.否则,就未能给予同一行为相同的评价,没能做到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上述理解也获得了德国刑法学者的广泛支持,〔21〕Vgl. Wagner, Die Akzessorietät des Wirtschaftsstrafrechts, 2016, S. 32.本文亦赞同这一观点。根据这种见解,宪法中的平等原则除了要求法律不得对公民做出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还要求法秩序针对同一行为的价值判断不应存在矛盾。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便满足了平等原则的上述要求。该说为防卫限度设置了统一的标准,只要防卫行为满足这一标准,其在整体法秩序内就是合法的,不同部门法对该行为的评价是一致的,能够给予其相同的对待,符合平等原则的要求。
其二,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符合法治原则的要求。我国《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了法治原则。根据该原则,国家应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尽可能避免法律漏洞的存在,通过法律规范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22〕参见焦洪昌:《宪法学》(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7页。如果立法者使某一行为在法律上既被禁止又被允许,公民在行为时就无法知晓自己的行为究竟是合法还是违法,此时法律就没能为公民提供确定的行为指引,便形成了所谓“因规范冲突而出现的法律漏洞”,〔23〕Engisch, Die 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1935, S. 42.不符合法治原则的要求。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能够避免出现因规范冲突产生的法律漏洞。根据这种见解,民刑防卫限度标准具有一致性,只要防卫行为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其在整体法秩序内就是违法的。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法秩序对同一行为作出既合法又违法的矛盾评价,能够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
2.符合正当防卫的哲学基础
在哲学史上,诸多法哲学思想对正当防卫制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些哲学思想出发,应当认为民法和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具有一致性。
首先,根据社会契约论,正当防卫是公民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譬如,普芬道夫曾指出,“由于按照自然法则,和平义务应当是相互的,一个首先对我违反了这些义务的人,也就免除了我对这些义务的履行,并且通过宣布自己是我的敌人,允许我对他使用无限的或者在我看来适当的武力。”〔24〕Samuel Pufendorf,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Samuel Pufendorf, edited by Craig L. Carr, translated by Michael J. Seid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9.由此可知,根据社会契约论,正当防卫权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其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理念,即便是公民通过缔结契约建立的国家也不能剥夺和限制公民的防卫权,〔25〕参见王钢:《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与防卫限度》,元照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9页。作为国家制定的行为准则,法律亦不能自行确定正当防卫的界限。相应地,各部门法的特殊性便无法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
其次,从康德的法权思想出发,民法和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也应当是相同的。根据康德的法权思想,“凡是妨碍自由的事情都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事实上,“在普遍自由的原则支配下,根据每一个人的自由,必然表示为一种相互的强制。于是,权利的法则……也就是根据作用与反作用的平衡的物理法则”被展示出来。〔26〕[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1-43页。由此可知,正当防卫作为捍卫普遍法则之自由权利的强制措施,其与自由权利如影随形,且正是在其与行使自由的相互作用之下,才形成了公民自由权利领域。相应地,正当防卫的限度就是公民间自由权利的界限。又由于在康德看来,法律是那些使任何人的自由意志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可以和其他人的自由意志相协调的条件的总和,〔27〕同上注,第40页。因此,作为公民自由权利的界限,正当防卫的限度在不同部门法中就应当具有一致性。
最后,根据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民法和刑法对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也应当具有一致性。在卢曼看来,像正当防卫这样的“私力救济首先直接表达的是法律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法律在遭到侵犯的地方现身;为了平息由此可能引发的怀疑,……法律自身需要通过暴力获得具体展示”。而且,“法律机制的一致性在于这样一种期望:其他人期望着通过运用物理暴力而使法律得到保证”。所以,“物理暴力具有结构上的高度独立性特点。……物理暴力自身无须像法律规范和情景那样被分化,而是仍然保持在可统一组织的状态,无论法律变得多么复杂”。〔28〕[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148页。相应地,作为物理暴力的表现形式,正当防卫在结构上也应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并保持在可统一组织的状态。这就需要在不同部门法上对防卫限度采取相同的判断标准,使正当防卫在不同部门法中的成立范围相同。
3.契合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
就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当前学界存在个人权利保护说、法秩序维护说以及二元论三大阵营。无论采取何种观点,都会要求民法与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具有一致性。
在个人权利保护说看来,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来源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防卫权在本质上属于救济权,基于权利无须向不法让步的理念,在紧急情况无法及时获取公权力救助之时,国家准许公民在一定限度内通过自力救济排除危害行为。〔29〕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8-199页。个人权利保护说中的“权利”是先于民法和刑法等实定法存在的自然权利。相应地,正当防卫权也是先于实定法存在的权利。因此,正当防卫的限度也必然先于民法和刑法等法律规范而存在,不同部门法的特殊性不会影响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
法秩序维护说认为,正当防卫的正当性来源于其维护了法秩序的经验有效性。法秩序唯有获得大部分国民的认同和遵从,才具有经验有效性。在正当防卫的场合,不法侵害人以其行为表达出了其拒绝认同法秩序的态度,动摇了国民对行为规范有效性的信赖。而正当防卫则通过制止不法侵害,迫使不法侵害人认同法秩序,确证了行为规范的有效性。〔30〕参见王钢:《法秩序维护说之思辨》,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6期,第102页。根据法秩序维护说的见解,防卫限度就取决于维护法秩序经验有效性的客观需求。由于其中的“法秩序”是指整体法秩序,而不是具体的民法秩序或者刑法秩序,故依据这种见解,对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在民法和刑法中也不应有所不同。
二元论主张,防卫行为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通过制止不法侵害,正当防卫行为不仅维护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同时还在国家无法及时有效地采取保护措施的场合,肩负起了对抗不法侵害的任务,确证了法秩序的经验有效性。〔31〕参见劳东燕:《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第1331-1339页。与前述两种见解一样,二元论所要保护的公民个人利益也是先于民法和刑法规范存在的,由该利益派生出的防卫权自然不受民法和刑法等实定法的影响;其所维护的法秩序也是整体法秩序,而非具体的刑法秩序或民法秩序。因此,采取二元论的观点,民法和刑法应当对防卫限度采取相同的认定标准。
三、判断基准:刑法基准说之提倡
在民刑防卫限度一元论的内部,就具体的判断基准,又存在着民法基准说和刑法基准说两大阵营。在本文看来,相比于民法基准说,刑法基准说更加合适。
(一)对民法基准说之批判
民法基准说主张,在防卫限度的认定上,刑法的判断应从属于民法。民法规定中的“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判断防卫限度的基本准则,刑法规定中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只是区分可罚与不可罚的防卫过当的标准。在理论上,就如何论证民法基准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诠释路径。但是,这三种诠释路径均存在不足之处。
1. 可罚的违法性诠释路径的问题
可罚的违法性诠释路径主张,只要防卫行为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该行为就具有一般违法性。但如果该行为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其就因缺少可罚的违法性而不具有刑事违法性。〔32〕参见于改之:《法域冲突的排除:立场、规则与适用》,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98-99页。于改之教授在其最新的论文中,改变了之前的立场,转而支持刑法基准说,参见于改之:《刑民法域协调视野下防卫限度之确定》,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第42-53页。
可罚的违法性诠释路径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该说混淆了(形式)违法性与不法(实质违法性)。违法性是指行为对规范的命令和禁止的违反,只有违法与否的区分,而无量的差异;反之,不法则标示了该行为给法益造成的实质侵害,具有量的区别。〔33〕Vgl. Eisele, in: Schönke/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30. Aufl., 2019, Vorbem. §§ 13 Rn. 47 ff.在违法判断的过程中,必然要关注行为在不法程度方面的差异;但就最终结论而言,行为却只能要么违法,要么合法。〔34〕参见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具体到防卫过当的场合,尽管在违法判断的过程中,当防卫行为尚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时,可以认为其并未达到刑事不法的程度;但就最终结论而言,由于该行为已经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根据民法基准说,必须认定其在整体法秩序内均违法,而不能主张其在刑法上是合法的。
其次,该说无法避免刑法与民法规范间的逻辑矛盾。尽管可罚的违法性理论通过承认一般违法性维护了法律评价的统一,但该观点同时承认了不同部门法自身特殊的违法性,难以避免不同部门法规范间出现逻辑矛盾。〔35〕参见王钢:《警察防卫行为性质研究》,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第55页。具体到正当防卫的情形,在防卫行为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尚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的场合,根据可罚的违法性诠释路径,该行为在民法上是违法的,相对方并无容忍义务,可以对之实施逆防卫;但该行为在刑法上却仍然是合法的,相对方负有容忍义务,不得实施逆防卫。这就导致刑法和民法规范间出现矛盾冲突。
再次,该说容易造成司法适用上的混乱。将这种可罚与不可罚的区分推广至其他正当化事由,就会得出需要将正当化事由区分为一般正当化事由与刑事不法排除事由的结论。前者使行为在整体法秩序内都被认定为是合法的;而后者则仅使该行为不受刑事处罚。〔36〕参见[日]日高义博:《违法性的基础理论》,张光云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7页。但是,这种区分缺少明确性。譬如,在同样肯定这种区分的学者中,德国的京特教授〔37〕Vgl. Günther, Klassifikation der Rechtfertigungsgründe im Strafrecht, in: FS-Spendel, 1992, S. 195 f.和施来霍夫教授〔38〕Vgl. Schlehof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StGB, 4. Aufl., 2020, Vorbem. § 32 Rn. 65.均认为,被害人承诺和推定承诺属于刑事不法排除事由,而日本的曾根威彦教授则认为它们属于一般正当化事由。〔39〕参见[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3页。这种不明确性会不当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统一地适用法律。
最后,该说给理论研究带来诸多的困扰。譬如,根据限制从属性说,只有存在故意的违法主行为时,才可能成立共犯。如果承认一般违法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的区分,那么其中的“违法”具体是指什么就并非不言自明的。再如,当行为人对可罚的违法性产生认识错误时,究竟应当将之作为何种类型的认识错误,也会出现争议。又如,究竟是只要行为具有一般违法性,就可以对之进行正当防卫,还是只有当其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时,才允许对之实行防卫,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2.罪责诠释路径的缺陷
罪责诠释路径主张,虽然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防卫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如果该行为是因慌乱等原因形成的,便阻却了行为人的罪责,在刑法上仍可将之认定为正当防卫。与之相对,民事责任较少考虑责任阻却,故在前述场合行为人仍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40〕参见孙国祥:《民法免责事由与刑法出罪事由的互动关系研究》,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第160页。
罪责诠释路径可能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该说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不协调。一方面,该说不符合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与德国刑法不同,该条款仅规定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样的不法要件,而未规定慌乱等影响行为人罪责的要素,就规范表述而言,无法得出该条款是关于责任阻却事由成立条件的规定。〔41〕参见于改之:《刑民法域协调视野下防卫限度之确定》,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第49页。另一方面,该说与我国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相矛盾。在避险过当的场合,避险人也经常是因为慌乱等原因导致避险过当,倘若认为第20条第2款是有关责任阻却事由的规定,那么立法者在紧急避险的规定中也应当平行地规定相应的条款。但是,我国刑法中却不存在这样的规定。
其次,民法只是不明确区分不法与罪责,但不意味着民法不考虑罪责的问题。事实上,在民法中同样需要考虑责任能力等问题。〔42〕Vgl. Geilen, Strafrechtliches Verschulden im Zivilrecht?, JZ 1964, S.7.譬如,在各国民事法律中,均存在有关责任年龄的规定。〔43〕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6页以下。《德国民法典》 第828条明确规定了民事责任年龄,我国《民法典》也在第1169条间接确定了责任年龄。〔44〕参见杨立新、郭明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因此,倘若认为刑法是因为存在责任阻却事由而不处罚普通的防卫过当,那么在民法上该行为同样不会引起民事责任。
最后,该说还与刑法现有的理论框架和基本理念存在矛盾。该说将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具有责性的行为也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做法,会造成犯罪论体系的混乱。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只有当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时,才会去检验是否存在责任阻却事由。因此,即使防卫人因具有责任阻却事由而不构成犯罪,其也不可能再成立正当防卫。不仅如此,该说也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存在实质抵牾。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并不处罚任何侵害法益的行为,其规制范围具有不完整性。尽管该说通过肯定存在责任阻却事由的方式为行为人出罪,但其在防卫限度的判断中采取了基本相适应说,仍然不当地扩大了刑事不法的范围,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
3. 罪量诠释路径的不足
罪量诠释路径认为,相比于一般犯罪行为,防卫过当的不法程度和一般预防必要性均明显下降,普通的防卫过当并未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的程度。所以,立法者对防卫过当的入罪标准做了“超严格化处理”。〔45〕参见陈璇:《防卫过当中的罪量要素》,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5期,第16-19页。罪量诠释路径存在如下缺陷。
(1)缺少理论根据
罪量诠释路径的论证缺乏说服力。根据该观点,刑法之所以不处罚普通的防卫过当,是因为相比于普通犯罪行为而言,普通防卫过当的不法程度和一般预防必要性都有所下降,并未达到值得刑罚处罚的程度。按照这一逻辑,刑法处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就应当是因为这种防卫过当的不法程度和一般预防必要性相比于普通的防卫过当均有明显提升,从而达到了值得刑罚处罚的程度。但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一方面,与普通的防卫过当相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的一般预防必要性不一定更高。某一犯罪行为的一般预防必要性取决于该行为被效仿的可能性。譬如,根据通说,之所以相较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盗窃罪的一般预防必要性更大,就是因为盗窃罪往往使行为人获得收益,相比于“损人不利己”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其被效仿的可能性更高。〔46〕参见阮齐林:《中国刑法各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页。具体到正当防卫的场合,无论是普通的防卫过当行为,还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均旨在制止不法侵害,并且行为人也都是因恐惧等原因僭越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能够获得普通公民的理解。所以,不论防卫行为超过防卫限度的程度如何,其对于行为规范有效性的影响相对较弱,致使公民效仿行为人实施防卫过当行为的可能性较低,缺少进行一般预防的必要性。
或许有论者会认为,相较于普通的防卫过当而言,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的不法程度通常更高,社会危害性更大,法秩序更有必要防止其他公民实施这种类型的防卫过当,故其一般预防必要性更高。但是,在刑法中考虑一般预防因素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行为不法程度对于定罪和量刑的影响。〔47〕参见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与积极一般预防》,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39、47、48页。若行为的一般预防必要性取决于该行为的不法程度,则一般预防因素就无法再发挥前述调节作用。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也表明,犯罪行为的一般预防必要性与其不法程度并无直接关联。譬如,作为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不法程度显然高于盗窃罪。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两罪的法定最高刑却基本一致。刑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相比于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言,更有必要对日常生活中常见多发、易于被效仿的盗窃行为进行一般预防。同理,尽管相比于普通的防卫过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的不法程度可能更高,但却不能据此认为其当然地具有更大的一般预防必要性。
另一方面,在个案中,相比于普通的防卫过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也不一定具有更高的不法程度。就行为无价值而言,在部分案件中,行为人可能是故意地实施了普通的防卫过当行为,在其他案件中,行为人则可能只是过失地实施了明显超过防卫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若二者造成的损害相同,相比于前者的场合,后者行为无价值的程度就不一定更高。就结果无价值而言,个案中防卫行为所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也可以同时是重大损害。譬如,在超过防卫限度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场合,死亡不仅是不应有的损害,而且是重大损害。因此,相比于普通的防卫过当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不一定造成了更高的结果无价值。
(2)不符合相关刑法规定和理论
罪量诠释路径还与我国当前的刑法规定和理论不协调。首先,该说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间存在矛盾。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尽管不成立正当防卫,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倘若认为刑法将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作为区分可罚与不可罚的防卫过当的标准,那么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便构成可罚的防卫过当,行为人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应当再对其免除处罚。不仅如此,该说也与我国刑法有关紧急避险的规定相冲突。相比于普通犯罪行为,避险过当的不法程度和一般预防必要性也明显下降:此时避险人客观上保护了合法利益且主观上具有避险意识,其行为的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都被大幅抵消,不法程度明显下降。同时,避险过当也多是由慌乱等情绪引起的,能够获得普通公民的理解,对行为规范有效性的影响较弱,一般预防必要性较小。因此,若刑法是因为相比于普通犯罪,防卫过当的不法程度和一般预防必要性都有所下降才提高了其入罪标准,那么,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立法者理应对避险过当也作相同的处理。但是,我国刑法却并未这样规定。
其次,该说与刑法理论对假想防卫和偶然防卫的处理不协调。在假想防卫和偶然防卫的场合,相应罪行的不法程度和一般预防必要性与防卫过当的情形基本相当。分言之,在偶然防卫的场合,尽管由于缺少防卫意识无法抵消行为无价值,但结果无价值已经完全被抵消,故偶然防卫与防卫过当的不法程度大体相当。同时,偶然防卫的情形极为罕见且客观上也确实保护了法秩序肯定的利益,其对于行为规范有效性的影响较弱,几乎没有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在假想防卫的场合,尽管因不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结果无价值无法被抵消。但是,此时行为人的认识错误仅涉及与防卫势态相关的事实,其对于法律规定的防卫限度具有正确的认识,主观上没有僭越防卫限度的故意或过失,故与防卫过当的情况相比,假想防卫的行为无价值可能更低,两者的不法程度基本相同。此外,在假想防卫时,行为人往往是因惊慌等原因误认事实才实施了“防卫行为”,其并未表现出拒绝认同法秩序的态度,基本不会动摇公民对行为规范有效性的信赖,从而也缺少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因此,如果刑法是因为行为的不法程度和一般预防必要性下降才不处罚普通的防卫过当,那么刑法也就不应当处罚假想防卫和偶然防卫,或者至少应当区分可罚与不可罚的假想防卫和偶然防卫,仅处罚不法程度较高和一般预防必要性较大的假想防卫和偶然防卫。然而,这并不符合当前刑法学界的主流意见。
(二)刑法基准说的合理性
刑法基准说主张,刑法规定确立了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民法有关防卫限度的判断应从属于刑法。本文赞同这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考虑正当防卫制度发展的历史,应当采取刑法基准说。原因在于,不是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是刑法理论和实践始终推动着放宽防卫限度的进程。以德国为例,在最初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中,德国法律对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也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直到1813年的《巴伐利亚州刑法典》,立法者才取消了这种限制,放宽了对防卫限度的要求。〔48〕Vgl. Krey, Zur Einschränkung des Notwehrrechts bei der Verteidigung von Sachgütern, JZ 1979, S. 702 ff.不仅如此,正当防卫是少有的产生于刑法,并逐步被其他法领域接受的正当化事由。〔49〕Vgl. Roxin/Greco,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5. Aufl., 2020, § 14 Rn. 37.据统计,直到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未在民法中规定正当防卫制度,或者仅在民法中作宣示性规定,在具体判断时则援用刑法的相关规定。〔50〕参见杨秀朝:《民法上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立法与适用》,载《求索》2010年第9期,第167-168页。即便在民法中较为详细地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的国家,立法者也往往是依据刑法规定设置民法的正当防卫制度。比如,《德国民法典》在确定正当防卫的要件时便参照了《德国刑法典》第32条的规定。〔51〕Vgl. Grothe,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8. Aufl., 2018, BGB § 227 Rn. 1.
其次,从刑法和民法的价值功能出发,应当采取刑法基准说。在整体法秩序内,刑法的价值功能是通过打击犯罪以实现法益保护的目的,而民法的价值功能则是平衡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犯罪是最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作为法秩序用以规制犯罪行为的最终手段,刑法规定才体现了有效遏制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必要限度。反之,民法旨在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关系,并不关注是否能够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这就导致民法允许当事人采取的防卫手段往往缺少威慑性,甚至不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不利于维护合法权利。既然正当防卫是国家赋予公民在无法及时获取公权力保护时通过自力救济制止不法侵害、维护合法权益的手段,其规范目的无疑与刑法法益保护的目的更为契合。因此,以刑法规定为基准认定正当防卫的合法限度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正当防卫制度的价值诉求。
最后,考虑1997年《刑法》修改正当防卫条款的立法目的,也应当采取刑法基准说。众所周知,1997年《刑法》之所以对防卫限度条件做出重大修改,就是为了通过放宽防卫限度强化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52〕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7年第2期,第222页。相应地,立法者在修改过程中也突破了基本相适应说的局限,倾向于采取必需说的立场。〔53〕参见梁华仁、刘为波:《评新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的修改》,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第29页。为了实现放宽防卫限度的目的,应采取刑法基准说。只有这样,必需说才是防卫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标准。只要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该行为就属于合法行为,相对方对此负有容忍义务,不得对之实施逆防卫。相应地,防卫人可以自主选择对于制止不法侵害而言必需的手段,而不需要时刻顾及自己的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之间是否大体相当,能够有效地减少防卫人实行防卫的顾虑,有利于实现放宽防卫限度的立法目的。
四、调和冲突:刑法基准说之具体展开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应当将刑法规定作为判断防卫限度的基准。但是,刑法和民法相关规定的规范表述明显存在差异,故还需讨论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调和规范表述方面的矛盾冲突。传统刑法基准说主张,两者之间是注意规定和基本规定的关系,即注意规定说。不过,这种见解也存在不足之处。下文就具体分析注意规定说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观点。
(一)对注意规定说的检视
注意规定说认为,刑法与民法相关规定之间是注意规定与基本规定的关系,其中,刑法规定是注意规定,而民法规定是基本规定。与民法规定相比,刑法规定进一步说明了何谓防卫限度,故在个案中应以刑法规定为指导进行判断。〔54〕参见于改之:《刑民法域协调视野下防卫限度之确定》,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第51-52页。其理由是,民法和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规定均来源于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修改旨在使1979年《刑法》所确定的标准更加明确和具体,便于司法机关理解和把握,属于“技术性”修改,并未改变原有的判断标准。〔55〕参见陈航:《“民刑法防卫过当二元论”质疑》,载《法学家》2016年第3期,第145页。该见解也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该说无法与刑法有关紧急避险的规定保持协调。1979年《刑法》关于防卫限度与避险限度的规定完全相同。在1997年《刑法》修改的过程中,立法者在修改防卫限度规定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其与紧急避险条款的协调。譬如,1979年《刑法》第18条第2款原来的规定是,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负刑事责任。在刑法修改时,配合对防卫限度规定的修改,立法者将其中的“危害”修改为“损害”。倘若立法者对正当防卫规定的修改不会影响防卫限度的判断,为了避免误解,立法者就应当对避险限度的规定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但是,立法者并没有这样做。〔56〕参见陈璇:《防卫过当中的罪量要素》,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5期,第15页。
其次,现行《刑法》中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与1979年《刑法》中的“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之间存在实质差异。一方面,“明显”作为一个程度副词,强调了防卫行为超过必要限度的显著性和严重性。〔57〕参见黎宏:《刑法学总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141页。因此,在“超过必要限度”前增加“明显”二字,会对防卫限度的判断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不应有”与“重大”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根据2020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13条的规定,“重大损害”是指重伤和死亡结果,其判断标准具有客观性。这一见解也获得了刑法学界的普遍赞同。〔58〕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79-281页。而“不应有的危害”,是指因实行防卫所造成的过剩损害,其判断标准更具主观性。〔59〕参见陈兴良:《正当防卫的制度变迁: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载《刑事法评论》2006年第2期,第474页。
最后,注意规定说在体系融贯性方面存在问题。其一,注意规定是在法律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员注意的规定。因此,注意规定只是对基本规定内容的再次重申,即使法律不设置该规定,也能够将基本规定作为司法适用的依据。〔60〕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63-864页。倘若认为《刑法》第20条是注意规定,而《民法典》第181条是基本规定,那么刑法规定就只是对民法规定的再次重申,即使没有刑法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民法规定处理防卫限度的问题。这使得刑法的判断在实质上从属于民法,显然与刑法基准说的理论基点存在实质冲突。其二,如前所述,立法者通过1997年《刑法》修改摒弃了基本相适应说的见解,转而支持必需说的立场。如果认为1997年《刑法》对防卫限度规定的修改不涉及实体内容,那么就应当认为现行《刑法》仍然采取了基本相适应说,在个案中仍应将基本相适应说作为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这无疑不符合刑法基准说自身在防卫限度判断中所坚持的必需说的立场。
(二)本文的观点
在本文看来,我国刑法确立了防卫限度的认定标准,只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行为才具有违法性。与之相对,我国民法只规定了当事人双方如何分担损失的标准。如果防卫行为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其仍然合法,只是基于民法利益平衡的规范目的,可以要求正当防卫人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所谓“适当”的民事责任,不仅意味着防卫人不是就防卫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责任,而且意味着仅在适当的场合其才需要分担损失。至于防卫人应分担损失的场合和比例,则须由司法工作人员在个案中具体加以确定。一般而言,在防卫行为超过必要的限度并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基础上,若防卫行为所侵害的利益相对较大,则防卫人需要适当分担损失。本文的立场不仅符合民事责任的规范目的,契合正当防卫的正当性根据,而且是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的必然选择。
1. 民事责任的规范目的
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填补损害,与行为是否违法并无直接关联。各国民事法律规定均体现出了这一点。一方面,并非只要行为违法,行为人就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例如,尽管犯罪未遂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民法却并未对之施加民事损害赔偿责任。〔61〕Vgl. Grothe,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BGB, 8. Aufl., 2018, BGB § 227 Rn. 2.另一方面,并非只要行为合法,行为人就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譬如,根据《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在被害人是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遭受损害的场合,受益人也可能是责任承担主体。〔62〕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及适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84-286页。因此,尽管《民法典》第181条第2款规定,防卫行为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防卫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但却不能据此认定“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判断防卫行为违法与否的标准。
事实上,我国《民法典》第181条第2款规定本身也表明其并非有关防卫行为是否违法的规定:其一,该款的规定为,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正当防卫人”这一用语表明,在适用该规定的场合,防卫行为仍然构成正当防卫。因为,在确定行为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时,若根据防卫过当的判断标准已经可以肯定其防卫行为成立防卫过当,系违法行为,那么其行为便不再是正当防卫,自然也不能再称其为正当防卫人。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刑法》 第20条第2款也使用了“正当防卫”这一术语,但却不能否定《民法典》第181条第2款仅适用于合法的防卫行为。这是因为,《刑法》第20条第2款是在行为模式部分论及“正当防卫”,而《民法典》第181条第2款则是在法律效果部分使用了“正当防卫人”的称谓。在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中,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具有不同的价值功能。前者是法律规则中描述人们如何行为或活动的部分,后者体现出了法律规则对于人们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的态度。〔63〕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04页。与之相应,行为模式部分的用语更加注重对于事实的描述,而法律后果部分的用语则带有更加明显的价值评价的成分。在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是在实施正当防卫的过程中,因其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被法律评价为违法行为,所以在描述防卫过当的行为模式时或许仍然可以使用“正当防卫”的术语。与之相对,在规定防卫过当的法律后果时,法律规则要给予防卫过当的行为否定性的评价,此时便不能再使用“正当防卫”“正当防卫人”这样带有积极意义内涵的表述。
其二,如果《民法典》第181条第2款是对防卫限度的规定,那么“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便是多余的。因为,若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防卫行为构成防卫过当,其便属于侵权行为,可以根据民法中有关侵权责任和共同过错的规定确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而没有必要单独规定其法律后果。事实上,在域外立法例中,各国民法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均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譬如,《德国民法典》第227条和《日本民法典》第720条均未单独规定防卫过当的法律后果。若防卫行为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则依据民法有关侵权行为和共同过错的规定确定防卫人的责任。〔64〕Vgl. Repgen, in: Staudingers Kommentar, BGB, 18. Aufl., 2019, § 227 Rn. 79ff.
其三,就体系地位而言,《民法典》第181条被置于有关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中。该章中还规定了按份责任等责任分配方式,停止侵害等责任承担方式,以及公平责任等损失分担方式。所以,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完全可以认为《民法典》第181条第2款是关于当事人损失分担方式的规定。如此理解,该款规定也可以与《民法典》第182条第3款的规定保持协调。我国民法理论认为,《民法典》第182条第3款规定了在避险行为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场合当事人应当如何分担损失。其理由是,真正影响避险行为合法性的是该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的性质、类别和数量,而危险发生的原因以及其对损害发生的作用大小则只是确定损失分担的重要依据。《民法典》第182条规定正是将引起危险的原因作为确定紧急避险法律效果的依据,〔65〕参见陈甦:《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5-1307页。故该条是有关损失分担的规定。鉴于《民法典》第181条第2款与第182条第3款法律效果部分的规定基本相同且两款规定相邻,根据体系解释的基本原理,将两者均理解为关于损失分担方式的规定方为妥当。
2. 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
前已述及,学界对于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大致存在个人权利保护说、法秩序维护说和二元论三种见解。然而,在本文看来,上述见解均有不足之处。首先,个人权利保护说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根据个人权利保护说的见解,只能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实施防卫行为,但是,我国刑法明确允许为了公共利益进行正当防卫,个人权利保护说无法为此提供说明。而且,如果片面地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则为维护其利益,防卫人可以采取任何方式进行防卫,不应对防卫限度作出限制,将导致防卫权过于宽泛。〔66〕参见张明楷:《正当防卫的原理及其运用》,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2期,第52-53页。其次,法秩序维护说无法说明为什么正当防卫不要求法益权衡。如果法秩序想要通过不计损失的方式确证自身的有效性,那么这种宽松的限度要求应当首先体现于通过刑罚惩罚犯罪等直接确证其有效性的场合。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情形都存在比例原则的限制。既然如此,在正当防卫的场合,法秩序也应当使防卫行为受到比例原则的限制。〔67〕Vgl. Erb,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StGB, 4. Aufl., 2020,§32 Rn. 16.最后,在传统二元论下,个人权利保护与法秩序维护之间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其相互结合只会削弱对方的说服力。因此,二元论无法真正将两者同时应用于对个案的说明,在具体适用时只能选择放弃其中部分内容。〔68〕参见王钢:《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及其限度》,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第1601-1603页。
本文认为,唯有从整体性二元论角度,才能论证正当防卫的正当性。根据这种见解,正当防卫的正当性来源于自利理性人的普遍同意。正当防卫是原初状态下获得理性人普遍认同的正当行为规则。在理性人于无知之幕下商定了自由权利分配的规则后,其便会要求对此予以维持。国家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就是为了维持权利分配规则而设置的保障措施,其为个人自由权利提供了前置性保护。同时,当国家不能及时保护其自由权利时,理性人便会要求针对不法侵害进行反击,通过正当防卫维护自身权益。当然,受到最大最小值原则的限制,理性人也不会允许防卫限度过于宽泛。〔69〕同上注,第1603-1606页。这种整体性二元论不仅可以合理解释正当防卫保护超个人法益的功能,论证正当防卫无须受法益均衡限制的理由,而且也使个人权利保护与法秩序维护之间不再是紧张的对立关系,具有合理性。
从整体性二元论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律要求正当防卫人适当地分担损失。在无知之幕下,由于理性人无法知晓自己在未来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为了避免未来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他会力求在最坏的情况中得到最佳的结果。〔70〕参见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50页。具体到正当防卫的场合,自利理性人会想到自己也可能处于侵害人的位置,尤其是在自身法益遭受严重损害的场合,考虑到因防卫行为产生的损害会给其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自利理性人就会要求采取凌厉防卫措施的防卫人适当给予补偿。一方面,通过这种适当的补偿帮助侵害人的重大法益恢复到相对圆满状态,避免其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适当的补偿也可以起到吓阻防卫人滥用防卫权的效果,避免防卫人采取过于凌厉的防卫措施。当然,自利理性人也会考虑自己处于被侵害人位置的情形。但是,即便如此,其也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给予适当的赔偿,只是损失部分微小的利益。一边是遭遇凌厉的正当防卫使个人未来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另一边是损失部分微小的利益。两相比较,前者显然是理性人更加无法容忍的风险。所以,理性人会同意要求正当防卫人适当分担损失的方案。
3. 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要求
本文的观点还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要求,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根据帕累托最优原理,如果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的改变使得至少有一个人的状态变好,而没有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则认为这种资源配置状态的变化就是“好”的,即帕累托改进。当某种配置状态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时,其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71〕参见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
从帕累托最优原理的角度也可以说明放宽防卫限度并要求防卫人适当分担损失方案的正当性。在开始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不同的策略选择进行赋值。〔72〕在是否具备帕累托改进的分析中,都是分别比较各方案中相同主体的获益情况,而不会比较不同主体的获益情况,所以具体赋值对于结论基本没有影响,进行赋值只是为了能够更为形象地展现不同策略选择对于各主体收益的影响。当法律对防卫限度作宽缓的要求时更有利于维护防卫人的利益,故假定对防卫限度作严格要求时其收益为900,作宽缓要求时其收益为1000。而且,宽松的防卫限度会给侵害人带来更大的损害,故对防卫限度作严格要求时其收益为-1900,作宽缓要求时其收益为-2000。防卫人适当分担损失一定会使其利益受损,但仅是微小的利益,故分担损失时其所获收益减少50。同时,在这一场合,防卫人的利益损失能够有效避免侵害人在未来发展中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故此时侵害人的利益增加100。根据前述赋值,在对防卫限度做严格要求的场合,若防卫人适当分担损失,则防卫人和侵害人获得利益分别为850和-1800;若防卫人不分担损失,则两者的获益情况分别为900和-1900。在对防卫限度做宽缓要求的情形下,若防卫人适当分担损失,则防卫人和侵害人的获益情况分别为950和-1900,若防卫人不分担损失,则两者的获益情况分别为1000和-2000。此时,博弈结果如表一所示(每组数值均以防卫人在前,侵害人在后)。
在上述四种策略条件组合之中,相比于组合2,组合3在没有改变侵害人利益状况的情形下,明显提高了防卫人的收益,是对前者的帕累托改进。同时,尽管从表面上看,相比于组合1和组合4,组合3并不存在帕累托改进。但是,若考虑严格限制防卫限度和要求防卫人适当分担损失的规范目的,组合3与这两种组合之间其实也存在帕累托改进关系。一方面,要求防卫人适当分担损失旨在避免侵害人在未来发展中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不能过度加重防卫人实行防卫的负担,故相比于所防卫的利益,分担的损失只是微小的利益。当防卫行为保护了重大的利益时,因分担损失而出现的利益减损就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正当防卫的场合,防卫人通过实行防卫往往保护了其人身权利等重大利益,而其分担的损失则表现为微小的财产减损,故现实中防卫人是否适当分担损失对其收益基本没有影响。在此意义上,与组合4相比,组合3在没有明显改变防卫人收益的情况下,改善了侵害人的利益状态,是对前者的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严格限制防卫限度和要求防卫人适当分担损失在实质上都是为了避免侵害人在未来发展中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故现实中当防卫人分担损失可以有效改善侵害人利益状态时,严格限制防卫限度对侵害人利益状况的影响就变得十分有限。此时,是否对防卫限度作严格的限定基本不会影响侵害人的利益状态。就此意义上而言,与组合1相比,组合3可以在不明显改变侵害人利益状态的情况下,增加防卫人的收益,是对前者的帕累托改进。
五、结语
综上所述,民法和刑法关于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具有一致性。这不仅符合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契合正当防卫的哲学基础及其正当性依据。在具体认定时,应当将刑法规定作为防卫限度的认定基准,民法规定只是判断正当防卫人是否需要分担损失的标准。这种做法不仅符合正当防卫的正当性依据及其发展历史,合乎放宽防卫限度的立法目的,而且体现了民法和刑法不同的功能定位,有利于实现民事责任填补损害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
在本文开篇提及的四个案例中,都应当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作为判断防卫行为过当与否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在案例一至案例三中,黎某1等人的防卫行为均不构成防卫过当。只不过,如果法院认为其行为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并有必要要求其适当地分担损失,可以判决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在案例四中,李德强的行为成立防卫过当,其同时需要根据民法中有关侵权责任和共同过错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