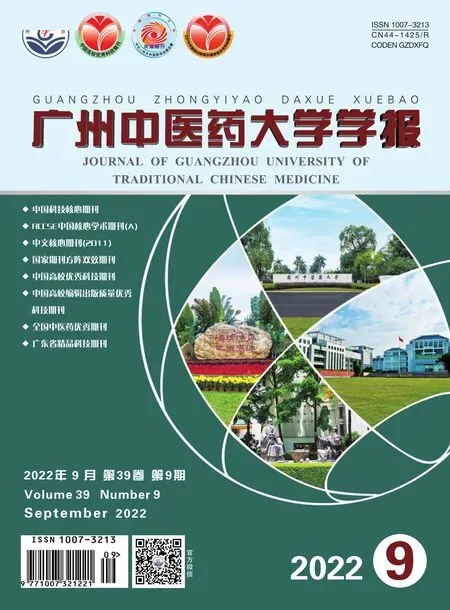基于伏气温病理论辨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神经系统后遗症
丘金钰,周润津,皮立宏,林兴栋,吴智兵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广州 510405;2.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3.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广州 510378)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以来,全球经济和医疗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世界各国共同面临严峻的挑战[1]。COVID-19是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介导的传染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人群普遍易感,其症状多以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呼吸系统表现为主。且越来越多的报道[2-3]提示,COVID-19可引起其他系统并发症或后遗症,神经系统(包括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系统)和骨骼肌均可受累。
目前,现代医学对于COVID-19相关神经系统后遗症仍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中医学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应对传染病的丰富经验,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医学的伏气温病具有待时而发、初起即见里热证、病势较重、病程较长、迁延难愈等特点[4-5],与COVID-19具有潜伏期或无症状感染者、危重症多、后遗症多和存在“复阳”病例[2,6-10]等特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伏气温病常波及营血分,心神、营阴易受邪气侵扰,遗邪留伏而成神经系统后遗症。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从伏气温病理论出发,配合卫气营血辨证思路,以“清透”为基本原则,以青蒿鳖甲汤主方加减,对于新冠肺炎相关神经系统后遗症有一定效果[6-7]。以下探讨基于“伏气温病”理论辨治COVID-19相关神经系统后遗症的思路。
1 伏气温病理论概述
伏气温病理论可溯源至春秋战国时期。《素问·生气通天论》[11]11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金匮真言论》[11]13又云:“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以上论述提示伏气温病“感邪之后,逾时而发”的特点,及其内虚、外邪共同作用的发病机理,论述较为朴素,未能成系统[12]。西晋王叔和基于此提出“伏寒化温”说,用来阐述温病的病因病机,以感邪后是否伏而后发作为区别“伏气”和“新感”的要点,这是相对于狭义伤寒而言[13],这一概念的“是否伏而后发”内涵一直沿用至今。
有关伏气温病的病因[12],隋代的巢元方认为冬感温邪也可过时而发;宋代的韩祗和提倡“伏阳致温”说,认为伏气温病并非寒邪引起,而是伏阳被寒邪郁折,外发而成。在发病时间上,金元时期医家刘完素提出,伏气温病四时皆有,突破了伏气温病在季节上的局限。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宋明医家逐渐认识到温病不仅有伏寒外发,也有新感异气、温热之气而发者[13]。如宋朝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天行温病论》[14]云:“即时发病温者,乃天行之病耳。其冬月人感乖戾之气……至天气暄热,温毒乃发。……又四时……感异气而变成温病也”。同时代的郭雍在《伤寒补亡论·伤寒瘟疫论》[15]中亦论及:“冬病伤寒,春病温气,与夫时行温疫之类,皆无根本蕴积之类,才感即发,中人浅薄,不得与寒毒蕴蓄有时而发者同论也”。清代何廉臣所撰的《重订广温热论》[16]中引汪石山语:“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名曰温病;若更遇温气,变为温毒,亦可名曰温病,此伏气之温病也。又有……新感之温病也”,正式提出了“新感温病”和“伏气温病”之名[17]。清代的伏气温病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俞根初承继吴又可对温疫“邪伏膜原”的病机认识,将伏气温病分为虚实两端:“实邪多发于少阳膜原”,病浅而轻,治疗上以祛邪为法;“虚邪多发于少阴血分阴分”,病深而重,需滋阴宣气与凉血清营并用[18]。何廉臣、俞根初的以上论述,即后人所谓的“伏暑晚发”说。至晚清,伏气温病理论渐趋成熟。对于伏气温病在时间上过时而发、病程上迁延难愈、假愈后易复发的特点,刘吉人在《伏邪新书》[19]中做了经典的概括性总结:“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邪,已发者而治不得法,病情隐伏,亦谓之曰伏邪。有初感治不得法,正气内伤,邪气内陷,暂时假愈,后仍作者,亦谓之曰伏邪。有已治愈,而未能除尽病根,遗邪内伏,后又复发,亦谓之曰伏邪”。王孟英则提炼了伏气温病的卫气营血传变规律,“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20],在治疗上主张直清里热,对伏气温病的证治具有指导意义。柳宝诒的《温热逢源》[21]则对“邪伏少阴”之说作了深入探讨,强调顾护阴液的重要性。清末的何廉臣则以“伏火”统领伏气温病的病因,以“灵其气机,清其血热”作为治伏邪第一要义[22],较为完整地总结了伏气温病辨证论治体系。
综观伏气温病理论的发展,不难看出,伏气学说对温病发病过程强调邪伏、化热、外发三个环节[23]。关于邪伏部位虽有不同见解,但诸家均遵《黄帝内经》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观点,不外乎伏于正虚之处[24-25]。关于伏气性质亦有“伏寒化温”“伏火”“伏暑晚发”“四时伏气”“异气”等论述[26]。但无论何种邪气,伏藏日久,则气机升降出入障碍,怫热郁结化火,而最初伏藏之邪或无从辨识,或于治疗意义不大。因此,治疗最终需落实到伏气外发时的证候表现上来,据此进行辨证论治,而非对最初所伏之邪进行追溯或揣测[27]。
伏气外发的内涵涉及时间和病位两方面[4]:时间上指邪气伏而后发;病位上则指由里出表、由深及浅,初起即里热炽盛。其时间特性可解释一些传染性疾病的潜伏期、隐性感染,或发作-缓解性疾病的缓解期,为临床提供思路;其病位特性则可从临床表现反推伏气的病位、病机,并通过实践得到验证[26,28]。
伏气发病,里热外达,故临床上初起即见气分热盛、气营(血)两燔之证。若由外感引动者,则兼有表证,表现为卫气同病,卫营(血)同病。伏气之病,病势较重,变证较多,病程较长,难以速愈。伏气传变,顺则由里达表,症状渐轻,逆则邪气内陷,病情加重。在治疗上,针对热郁伤阴的病机,采取清解里热、养阴透邪外出的治疗原则[5]。
2 COVID-19与伏气温病的关系
此次COVID-19疫情,中医学者多认为其可归属中医的“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6],不少专家认为其临床特点与伏气温病相符[29-31]。
从“有时而发”的时间特点来看,COVID-19的潜伏期为1~14 d,亦有学者报道个别病例潜伏期可长达24 d[32],这符合伏气温病伏而后发的时间特点。此外还存在无相关临床表现但呼吸道等标本病原学检测呈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7,33]。“无症状感染”的含义有二:一是经14 d的隔离医学观察,均无任何症状与体征;二是处于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状态[7]。二者都可视作伏气在体内伏藏未发的阶段。
从临床表现分析,COVID-19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可伴有咽痛、头痛、肌痛,或见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34],与伏气温病初起即见里热证的特点相符。COVID-19重症和危重症病死率高[8],预后差。重症患者多在发病1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及多器官功能衰竭(MOF)等[6],这类似于伏气温病热入营血、耗血动血、内闭外脱等表现。
从病程及预后来看,部分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但核酸结果仍然阳性,亦有患者达到出院标准后,仍再次检出核酸阳性(即所谓“复阳”)[35]。一项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研究[10]显示,COVID-19患者的“复阳”率为12.2%,并提出复阳可能因出院时核酸检测假阴性或病毒未完全消除。有研究[36]指出,未完全清除的病毒来自胃肠道,因感染后抗体产生缓慢或抗体水平低下所致,这些未完全清除的病毒可导致病毒持续排出,并造成传播。此外,部分患者出院后仍有再次感染的可能。以上表现均与伏气温病反复发作、留恋难清的特点类似。又有研究[9]显示,32.6%的COVID-19患者在慢性恢复期仍存在持续的呼吸、消化、循环、神经等不同系统后遗症,亦是伏气温病遗邪留伏之反映。
在发病人群的特点上,危重症患者多见于老年人、有慢性基础疾病者、晚期妊娠和围产期女性、肥胖人群[6],这与伏气温病的病本在正虚的特点相合。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虚乃邪伏之原因,而人群体质各不相同,体质薄弱之处也不同,故COVID-19的临床表现多样,不同器官或系统均可受累[6,34],即使到了慢性恢复期,也常遗留不同系统的后遗症[9]。
3 伏气温病与COVID-19相关神经系统症状表现
目前,关于COVID-19相关神经系统症状或并发症的报道逐渐增多。研究[3,9]显示,COVID-19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可出现在中枢神经系统(头晕、头痛、意识障碍、急性脑血管病、癫痫、共济失调等)、周围神经系统(神经痛、视力障碍、味觉障碍、嗅觉障碍等),或表现为骨骼肌损伤,而且重症患者更有可能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在恢复期持续存在。
伏气为病,郁久而发,故其病性往往从热从火而化,病位常波及营血分。心在五行属火,主神明,营气通于心。因此,营血分的邪热易侵扰心神。“神”不仅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还包括言语、应答、肢体活动姿态等外在表现。因此,心神受邪,则可出现反应迟钝、精神萎靡、神昏谵语、痉厥等神志及肢体活动的改变。由此观之,COVID-19的神经系统症状可认为是伏气郁久而发,化热化火而扰神窜络的表现。
“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神接受外界事物刺激并对其做出恰当反应。疾病后期,心神尚未恢复,加之久病耗伤阴精,患者在其他症状缓解后,仍可遗留味觉障碍、嗅觉障碍等后遗症,此乃因伏气致病,心神受损,余邪留恋,阴精耗伤所致。
在COVID-19相关神经系统疾病及其后遗症中,常见局灶性的神经症状或体征,如肢体乏力、共济失调等。这些局灶性的神经症状或体征表现除与心神受损有关外,尚可从络脉学说得到解释。络脉“易虚易滞、易入难出”[37]。故机体存在邪气可累及络脉,且留恋难解[38]。因此常遗留肢体活动不利等神经缺损症状。
综合以上分析,COVID-19的神经系统后遗症可基于伏气温病理论、结合卫气营血体系论治,属伏气温病后期,因余邪留滞,阴精损伤所致,治疗当以透热外达、滋养阴精为法,方药可采用青蒿鳖甲汤为主方加减。吴瑭在《温病条辨》提出:“青蒿不能独入阴分,有鳖甲领之入也;鳖甲不能独出阳分,有青蒿领之出也”。青蒿鳖甲汤以鳖甲入络搜逐邪热,青蒿清热透邪达表,生地黄、知母养阴清热,牡丹皮清热凉血,诸药合用,共奏透热外达之效。
4 病案举隅
患者辛某,男,48岁,以“行走不稳伴言语不利3个月余”为主诉,于2021年3月23日入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科。患者于2020年12月16日夜间出现呼吸困难、发热,之后意识丧失,由友人送往加拿大北约克医院就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脓毒性休克”,入住该院重症监护室(ICU),予机械通气、血管活性药物治疗。3 d后意识恢复,呼吸困难好转,但出现爆破样语言、眼球震颤、头晕疲乏、行走不稳、精细动作欠稳准等症状;无感觉异常、肢体乏力。结合辅助检查(具体不详)诊断为:(1)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性小脑炎;(2)克雷伯杆菌相关性肝脓肿;(3)脓毒性休克;(4)艰难梭菌结肠炎;(5)急性肾衰竭;(6)慢性乙型肝炎;(7)高血压。予肝脓肿引流术、抗感染(万古霉素、头孢曲松钠)、激素抗炎、预防性抗凝、控制血压、补液、退热等处理后,病情好转,仍遗留言语不利、行走不稳等神经系统症状,于2021年1月26日出院,并前往多伦多某医院进行言语及肢体康复训练,在该院继续予抗感染(头孢曲松钠)、控制血压等治疗,症状稍有改善。2021年2月22日于加拿大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及抗体阴性,2021年2月26日自广东省广州市白云机场入境,为求进一步诊治由我院门诊收治入院。
入院症见:仍遗留言语不利,语音呈爆破样,无其他异常声音或气味;头晕但非天旋地转感;形体肥胖,宽基步态,行走不稳、精细动作欠稳准,需借助辅行器方可行走;无偏瘫、乏力、饮水呛咳等不适,纳可,眠一般,二便调;舌淡,苔白腻;脉弦滑。既往有高血压病史15年余,最高收缩压达180 mmHg,一直口服苯磺酸氨氯地平(5 mg,qd)、富马酸比索洛尔片(2.5 mg,qd)以控制血压;既往有慢性乙型肝炎病史,但未行治疗。
入院查体:言语欠流利,呈爆破样语音。颅神经未见明显异常,未见眼震。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双侧指鼻试验欠稳准,双手轮替动作笨拙,跟-膝-胫试验稍欠稳准,宽基步态,Romberg试验阴性。全身深、浅感觉及复合感觉未见明显异常。右侧肱二头肌肌腱反射、右侧膝反射减弱,病理反射未引出。脑膜刺激征阴性。入院后实验室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示:尿酸468μ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3.45 mmol/L;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乙肝病毒e抗体、乙肝病毒核心抗体阳性,新冠病毒IgM抗体(-)。肝胆、脾、胰彩超结果示:肝右叶小囊肿,胆囊内胆泥淤积。颅脑核磁共振成像(MRI)及核磁共振血管成像(MRA)结果示:环池右侧结节样异常信号灶,疑海绵状血管瘤可能,轻度脑白质变性;左侧大脑前动脉A1、A2段未见显示,考虑先天变异,轻度脑动脉硬化。血液分析、凝血四项、甲状腺功能三项、糖化血红蛋白、心电事件记录、心脏彩超结果未见明显异常,双侧颈动静脉、锁骨下动脉及椎动脉彩超结果亦未见明显异常。
中医诊断:喑痱(邪留阴分兼风痰阻络证)。西医诊断:(1)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性小脑炎;(2)高血压3级(很高危组);(3)慢性乙型肝炎。西医治疗采用抗血小板聚集、调脂稳斑、控制血压、改善循环、营养神经等处理。中药治疗则从伏气温病论治。
2021年3月24 日初诊。结合伏气温病理论,患者辨证为“邪留阴分兼风痰阻络”,以透热外达、滋养阴精为法,佐以燥湿化痰通络,方拟青蒿鳖甲汤合二陈汤加减。处方用药如下:青蒿(后下)15 g,醋鳖甲(先煎)15 g,牡丹皮15 g,黄连片5 g,陈皮15 g,桔梗10 g,麸炒枳实10 g,法半夏10 g,茯苓15 g,姜厚朴15 g,淡竹叶10 g,忍冬藤15 g。共3剂,每日1剂,水煎至150 mL,饭后温服。
2021年3月27 日二诊。患者言语不利有所好转,较前易被理解,精细动作仍笨拙,行走不稳同前,无头晕,纳眠可,二便调,舌淡,苔白稍腻,脉弦滑。考虑患者为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在原方基础上酌加石菖蒲3 g以化痰开窍。共2剂,每日1剂,煎服法同前。
2021年3月29 日三诊。患者言语较前清晰,可不借助辅行器缓慢行走,精细动作改善不明显,纳眠可,二便调,舌淡,苔较前转薄,脉弦滑。患者症状得到明显改善,舌苔转净,提示伏气得到透发,但因患者痰湿之体,病久痰瘀互结,故症状难以速愈。拟方采用二陈汤加减,以燥湿化痰行气,使气机流通,改善后遗症状。处方用药如下:法半夏10 g,陈皮10 g,姜厚朴10 g,麸炒枳实10 g,牡丹皮15 g,干益母草20 g,泽泻12 g,桔梗10 g,紫菀12 g,紫苏梗15 g,生姜15 g,党参12 g。共3剂,每日1剂,煎服法同前。
经治疗,患者行走不稳较前明显改善,可不借助辅行器行走,言语较前清晰,语速较前增快,精细动作亦有所改善,无明显头晕,舌淡,苔薄白,脉象较前和缓。遂予办理出院,嘱门诊随诊。
按:该病案患者诊断为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相关性小脑炎,起病急,初起即见里热证及神志症状,快速进展,现遗留神经系统症状,主要表现为行走不稳、言语不利、精细动作欠稳准,可从伏气温病论治。结合其症状、舌脉,辨病为“喑痱”,辨证为“邪留阴分兼风痰阻络”。
患者体型肥胖,为痰湿素盛之体,伏气藏于体内,怫郁热结,故初起即邪热燔灼而见发热;热极生风,挟痰上扰清窍,故见神志不清;邪热壅肺,故呼吸困难;火热之邪扰心神、窜血络,心主血脉,在窍为舌,心主神志的功能受损,络脉受邪,故而行走不稳、言语不利、精细动作笨拙;久病则耗伤阴精、筋脉失养,同时又容易阻滞气机、聚湿生痰,使病情胶结难解,因而行走不稳、言语不利、精细动作笨拙等症状遗留至今。舌淡提示患者久病亦有气虚,苔白腻、脉弦滑佐证了患者痰湿偏盛。综合以上分析,在治疗上不宜苦寒直折,而应以清透为法,佐以燥湿化痰,从而畅通气机,使伏气从表里、三焦而解,以青蒿鳖甲汤为主方加减。先以鳖甲滋养阴精而不留邪,又取其入络搜邪之用,配合青蒿之透邪出表,清透邪热;牡丹皮化瘀且泻营血分之热,黄连燥湿又清心经之热,以除郁热;忍冬藤清热解毒、解表通络、清透络脉所伏邪气,与淡竹叶共取“透热转气”之意;又以桔梗开宣肺气以宣上,以二陈汤中之茯苓健脾渗湿以渗下,法半夏、陈皮则燥湿化痰以畅中,加用厚朴、枳实行气化痰,淡竹叶清心利尿,从而分利湿热从三焦而解,畅达气机,助邪气透达。
三诊时患者言语表达较前流利,行走不稳较前改善,舌脉好转,提示伏气得到透发。但因患者痰湿之体,且邪气深重,遗留日久,故气机受阻,痰瘀内生,病情胶结,不能速愈。阴精受损,不能滋养四肢,又兼痰瘀留滞络脉,精细动作的恢复更为缓慢。遂用二陈汤加减以燥湿化痰行气,使气机流通,改善后遗症状。仍以法半夏、陈皮、厚朴、枳实燥湿化痰行气,以泽泻代替茯苓加强利水渗湿之力,采用牡丹皮继续清营血分邪热,益母草利水兼能活血,以桔梗、紫菀宣肺祛痰,紫苏梗、生姜宽中行气,配合党参健脾益气养阴,扶助正气。全方共奏燥湿化痰,分消湿热之效。
患者出院时神经系统后遗症状明显改善,表明在辨病辨证的基础上,基于伏气温病理论治疗COVID-19相关神经系统后遗症是切实有效的。
5 小结
COVID-19患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后,其中大部分症状在慢性缓解期仍然持续存在,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以“伏气温病”为切入点对COVID-19相关神经系统后遗症进行辨证论治,契合COVID-19的临床特点,并反映了疾病发生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使治疗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温病学说的治疗原则强调祛邪务尽,扶助正气,扶正中又以护阴为首,契合COVID-19伏气致病之邪热内伏、耗伤阴精、缠绵难解的临床特点,故运用伏气温病理论诊治神经系统后遗症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