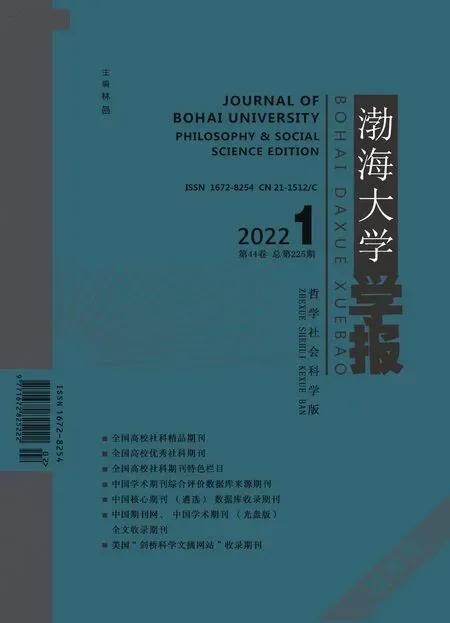苦难中孕育的生命之花
——评杨大群长篇小说《人·狗·狼》
吴 南(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5)
杨大群是一位将自己深深扎根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历史演义的跌宕起伏,抑或是战争时代的波澜壮阔,都没有离开东北这片热土,没有离开东北的人们。从早期作品《小矿工》,到后来历史演义小说《关东演义》《伪满洲国演义》,及文学传记《毛岸英》,这些创作,都如同北方的土地一般在沉稳中透着坚定,在粗糙中含着韧性。北地所特有的空旷凛冽铸造了他更为坚韧的军人气质,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养料。在他的文字中,东北宽广质朴的土地、川流不息汩汩奔腾的江河、皑皑的延绵白雪,以及苍茫起伏的林海,都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在那里,你能够看到一个作家对一片土地深厚的情感,并且通过阅读那些平实而自然的文字,于历史的岁月和时光的缝隙中感受与触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人与物的痕迹,回顾他们经历过的颠沛与磨难,体味他们在特殊的年月中于挣扎和苦难里造就的生的传奇与壮阔。
相较于杨大群的其他小说作品来说,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人·狗·狼》给人印象深刻。小说主要以日本侵华时期东北赫哲族一家在沦陷中的逃亡与反抗作为主要故事情节,相较于杨大群的其他小说作品来说整个故事情节的架构并不复杂,但是读罢整部小说,读者却能够透过这些颇具东北民俗特点的文字感受到一种悲怆与凝重,感受到一份深邃和感动。杨大群曾把这部小说比作自己整个文学创作的“老来得子”,在他的眼中这部作品的分量并不比其他的作品轻,甚至更重。在整部小说中作家所要展现的不只是历史记述的继承,而是更深层次的超越,这种超越既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超越,更是一种心灵的超越。就如杨大群在谈到其创作意图时所表述的那样,“我没有想把《人·狗·狼》简单写成侵略者如何残暴,被侵略者如何宰割,或者单纯把思想基调放在讴歌爱国主义精神上,而是想更进一步地去展示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如何转嫁到大自然,转嫁到整个自然生态的破坏上,从而在本质上更深邃地展示人性的深层结构,认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中所占的位置。”[1]应该说《人·狗·狼》这部小说不仅是一段民族历史的记录,它更是扎根于苦难中作家对生命的一种探究和思考,作家想透过历史的真相为我们揭露人性的复杂和矛盾,揭露人与自然的冲突和联系。透过这部小说读者能够于酣畅的文字中体味到一种人性、兽性的纠葛,体味到生命在特殊环境中的坚韧顽强,在杨大群的文字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他们都在命运的推动中表现了一种非比寻常的色彩和光亮,而这种光亮色彩于苦难的土壤中迸发,在磨难的火焰中发芽,更显得精彩和绮丽。
一、多重困境下的苦难书写
小说的故事情节被放置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日本侵占东北地区作为大的时间背景。故事讲述了东北赫哲族姜祥发、霞云一家在日军侵略下颠沛流离的逃亡与反抗经历。在日军侵略以前赫哲族人生活在黑龙江江边的九岔子屯,他们世代倚靠江河而居,靠捕鱼打猎为生,生活环境的严寒和荒芜造就了他们应对自然的体魄和勇气,他们从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也珍惜并敬畏着自然的力量与馈赠。在小说的最开始作者运用了很多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赫哲族人特有的风俗和习惯。他们世代养狗,把狗作为自己的家产,以狗拉的爬犁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甚至为了决出好的头狗,定期举行爬犁赛。他们用美酒拜客,通过比试来求亲,铜锣皮鼓的篝火中,一群精壮的小伙子会在挂满了彩色鱼皮条子的树枝间争取婚恋的资格,即使是女人也能和男人过招比试。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描绘的是一群颇具原始粗犷气息赫哲族的风土人情,他们有着自己生存规则和习惯,有着自己的民族信仰,他们与自然抗争的同时也遵循着自然的法则,而这种原始到近乎闭塞的生存状态被日军的侵华战争所打破时,对赫哲族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危机,更是民族的灾难。
整部小说虽然以日本的侵略及在此之下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作为主要的故事背景,但是通读小说,我们几乎没有找到作家对这种侵略的正面表现。无论是对日军的刻画,抑或是战争场面的记述,作者似乎都没有进行过多笔力的投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苦难的残酷是通过很多侧面展现的,是通过姜祥发和霞云夫妇的人生经历来进行透视的。作家似乎在有意地回避这种正面的铺陈,而将读者的视野拉到人物的流亡上,将这种国家和民族的苦难投射到个体的生存苦难之上,以更加直观的视角为我们展现这种人类自身的异族残杀,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和迫害,以及这种迫害对自然的冲击毁灭。在小说中杨大群运用了很多笔墨来书写姜祥发和霞云夫妇的逃亡和磨难。他们坐着七条狗拉着的爬犁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在原始森林中、在冬日雪原里、在沼泽洪水间艰难地生存着,他们在严寒的气候中挣扎,与狡猾的狼群搏斗,在沼泽的泥泞和洪水的波澜中试探,只为寻求一线生机。日军带着狼狗清扫残存的赫哲族人,炸弹的炮火焚烧着森林,毒气使得成群的动物倒下,即使强壮如黑熊也只能在这种屠杀中失去生命,每当他们找到了一处定居点时都会在日军的追逐中被迫放弃。食物和工具在追逐下丢失了,七条狗最后只剩下一条,饥饿、恐惧、绝望轮番袭击着它们,即使生下了血脉和后代,也在生存的危机中惶惶不可终日。杨大群在整部小说中似乎为主人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困境,无论是哪一种困境都能够将其逼到绝地。但是姜祥发和霞云在这种生存的苦难中却未曾倒下,他们应对着外界所赋予的一切磨难,没有食物就去打猎采蘑菇,失去住所就去寻找下一个,丢失了工具他们就将自己完全融入自然之间,砍倒马架子,如动物一样于江边的洞穴中躲避藏匿,用最原始的力量求存。支撑着姜祥发夫妇心中之火不灭的是种族的责任,是繁衍的使命,是印刻流淌在血脉中的对生的渴望和坚韧,也是对故乡故土的怀念。黑龙江川流不息的江水呼唤着他们坚韧的生命力,所以在生的绝境下姜祥发会挖洞探听黑龙江水的声音,渴望聆听故土的消息,会在失去妻女的情况下,怀抱着挖出的祖先铁杵而重燃信心与希望。这种对故土的依恋和民族的坚守,让他们即使饱受磨难和苦涩,也能擦干眼泪继续前行。就像小说中姜祥发无数次表述的:他们不能死,也不会死。“他们用这个身心的力量来吸吮生命之泉,呼唤爱欲之火,他们在挣扎、咆哮、呐喊……”[1](113)人在自然的残酷中颠沛流离,又在与自然的搏斗中焕发了更加高昂的生命活力,生命的韧性和生命的强悍在杨大群的文字中被渲染得更为生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在主人公的人生体验中被凸显得淋漓尽致,与其说小说为我们讲述的是一场由侵略所带来的民族悲剧,不如说作者是意图通过无数绝境的逃亡,向我们呈现一场在苦难中迸发出的生命奇迹。杨大群在整部小说中通过赫哲族人的人生历程为我们展现了生命的尊严和意义,体现了其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他将苦难化为生命本身的构成要素,在对姜祥发和霞云个人经历的展现中体现人物于苦难中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和英雄气概。在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个体的生命是渺小甚至是卑微的,更何况是在闭塞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赫哲族人。但是个体的生命又是极为坚韧、具有力量的,无论是小说的最后姜祥发在十数年的逃亡中,仍旧选择在日军洋马和狼狗的围捕中护送掩护抗联战士,还是行差踏错的刘淑亚为了种族的繁衍使命向姜祥发借种,在投靠日军的情况下仍旧放过姜祥发的儿子小龙,种种行为都体现出一种生命的抗争和决绝,这种抗争使得他们无论出于何种境况,仍旧能够抱有希望,并残留善念。而这种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再发现,或者说是肯定与歌颂,在“文革”过去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不得不说亦展现了杨大群这位东北作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倾向和思想深度。
二、人性与动物性的杂糅置换
在《人·狗·狼》中除了描写主人公姜祥发和霞云夫妇的人生历程,作家还运用了很多的笔墨来表现动物的形象,这些动物形象在整部小说的篇幅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并且与主人公一起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的生命图景。这些动物在小说中有的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如在日军的毒气中与姜祥发和霞云夫妇一起挣扎逃生的野鸡、松鼠、熊瞎子等,也有和姜祥发缠斗十几年的黑尾巴梢子狼、白爪牙狗、白鼻梁母狗等个体动物形象,在这些生动的动物形象身上杨大群可以说投入了大量的笔墨,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这些动物仿佛是站立在天平的中央,既承接着人与自然的联系,也串联着人类的过往和现在。人们从这些动物的身上体会到自然所蕴含的原始的生命活力,也通过这个与人类颇具亲缘的他人映衬出自己的良善与卑劣,甚至在特定的环境下,作家将人与动物的特性进行了某种杂糅错位,使得人性与动物性在两者身上发生了不同的呈现,让读者在这种交错中品读到人性深处的美好和黑暗。
小说中描绘最为生动的动物形象是与姜祥发夫妇相依相伴的白鼻梁母狗。白鼻梁母狗是姜祥发从黑尾巴梢子狼口中救下的狗崽,它温驯聪明,对姜祥发夫妇忠心耿耿。它带着其他狗拉着主人穿过雪地去迎接冲喜新娘,在日军的包围下,奋力狂奔带着姜祥发和霞云冲出围堵找到生路。它陪伴主人打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在食物不足其他狗都争抢肉干的情况下能够忍下饥饿吃蘑菇汤果腹,当狗群在白爪牙狗的带领下背叛主人互相撕咬奔逃时,它能够以自己个体的力量为主人追逐阻拦狗群。它为主人看家护院,时刻警惕,在日军的炮火中为主人示警,帮助主人逃离火场。甚至当姜祥发、霞云又一次在日军的追赶下陷入生存危机时,它自觉承担起了寻找食物的重任,一次次为饥寒交迫的主人带来食物补给。
杨大群赋予了白鼻梁母狗以一切人类所钟爱的动物特性,它是姜祥发怀念亲人故土的精神寄托,更是其在极端生存困境下无法割舍的世代相伴的助手和伙伴。就像小说中所讲述的那样,“在赫哲人居住的地方,养狗和有狗爬犁是各户人的家产。一幅狗爬犁至少要套五条狗、七条狗,甚至十几条狗,这样看起来才够威势。看爬犁,要看犁橇;看拖爬犁的狗,要看头狗”[1](14)。“没了狗,就意味着今后打猎短了胳膊,没了腿,白天没有报信的,夜里没有打更的。”[1](94)白鼻梁母狗和姜祥发夫妇的分歧开始在母狗生崽上,白鼻梁母狗在春天发情时躲过抓捕和日军的狼狗交配生下了几只狗崽,这些有着尖耳朵的狗崽使得它与主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狼狗崽让姜祥发想起了日本人对自己民族的迫害,想起惨死在狼狗口下的父亲,他厌恶这些狗崽,同时也憎恶着抛弃骨气为狼狗产下后代的白鼻梁母狗。母狗的母性本能使它不得不违背主人的意愿,抚育狗崽,它自己寻找食物甚至不惜截获主人的猎物以保证喂养狗崽的乳汁。可是最后这些被白鼻梁母狗精心呵护的狗崽还是难逃一死。当自己的狗崽最终还是被主人无情地杀害时,白鼻梁母狗在愤怒和痛苦之下叼走,并杀死了霞云的儿子,逃离了家。
小说中白鼻梁母狗对狼狗崽的母性和霞云对于儿子的母性在这种杀害中达到了某种融合。当霞云得知丈夫每次为自己带来的兔子其实都是母狗的狗崽时,“她忽地感觉到肚子里肠子翻个儿了,大口地呕吐起来,好像那些小狼狗尖尖的爪子在她胸腔里挠着……她变成了白鼻梁母狗,那些小狗崽都在她身上爬,伸着嘴巴四处拱,争着叼她的奶头……她像是失去了理智,两只手变成了爪子,在马架子里爬,对哭叫着的孩子伸脖用舌头舔着”[1](150)。而白鼻梁母狗失去幼崽后它找到霞云的儿子复仇,“它叼着包着孩子的熊皮,皮包里的孩子带有着它崽子的气息,仿佛化成了六个毛茸茸的小宝宝,它杀死了孩子,但是却“放声哀嗥起来,眼泪顺着眼角扑簌簌往下淌”[1](152),甚至当主人找到儿子将其埋葬时,它彻夜守在林中悲惨地呼叫声音,撕心裂肺,在母性面前,人变成了狗,而狗变成了人,面对孩子,人性和动物性获得了共鸣,融合为一体,使得人与狗虽然作为自然界不同的生命主体却能够于特定的时间和情形中完成一次交流与共通。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可以说将白鼻梁母狗的这种人性特点推到了至高之处。当霞云和女儿小凤被迫和丈夫儿子分开在沼泽独自求生时,没有食物让她和女儿几乎陷入了绝境,这个时候霞云意外拾到了几只死去的狗崽,而这些狗崽竟然是白鼻梁母狗咬死了自己的孩子送到主人身边的。“白鼻梁母狗叼着死狼狗崽,缓缓地走过来时,女人看得很清楚,在母狗的眼眶里还滴答着泪水呢。”[1](192)这种颇具戏剧性和传奇性的杀儿救主的行为可以说在虚构中将白鼻梁母狗的灵性渲染到了极致,将其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的良善和忠诚表达到了一种近乎崇高的地步。白鼻梁母狗身上的动物性被摒除在外,而成为一种人性美好的标志,作家意图通过这种动物近乎神化的虚构来表现一种人性没有杂质的美好与纯真。小说的最后,当姜祥发和霞云都死在了日军的残害之下,白鼻梁母狗从冰窟窿里拖出来口袋中的小龙“它蹲着身子,仰着白色鼻梁的头四处看,好像在看天,看地,看大森林,看白皑皑的大雪……它用暖烘烘的身子贴着孩子,不时用舌头舔着孩子的脑门,好像妈妈给孩子摸体温那么轻巧”[1](227)。人性的美好带来了生的希望,也带来了未来的光亮,白鼻梁母狗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参与着战争给予人类的苦难,同时它又是旁观者,旁观着人类的挣扎,旁观着人类在卑劣与残酷的掠夺下所造成的恶果。
对比小说中的白鼻梁母狗,小说中所表现的人在某些时候显得又那么富有动物性。例如在小说的最开始姜老头在江水中看到了刘淑亚,“一个披着黑黑长发的姑娘,冷眼看去,像是大马哈鱼变的”[1](16)。还有在姜祥发刚刚离开族群时那个被迫和他绑在一起的姑娘,在他看来就像是一只垂死挣扎的狐狸,不安焦躁。又如在小说的末尾,刘淑亚出现在主人公姜祥发的身边,带着满身的伤痕,在儿子和主人公的眼中她又仿佛是一只长毛的狼狗,“会吃人,会嚼人,也会吞人”的女妖。在小说中曾用过很详细的笔墨来表现主人公姜祥发身上所具有的动物性。当白鼻梁母狗产下尖耳朵的狗崽时,面对着食物的紧缺现状以及没有乳汁哺育儿子的妻子,姜祥发不顾白鼻梁母狗曾经给予的忠诚和帮助,杀死全部狗崽来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像探囊取物一样,把一个小狗崽抓住,使劲地往木杆子上一撞,小狗崽子就蹬腿了。他把小狗崽装在鱼皮口袋里转身就走了”[1](149)。“男人看着女人嘻嘻一阵冷笑:‘我恨日本鬼子,我恨掏了我爹爹的狼狗,我恨这些尖尖耳朵的小狼狗,我把狼狗耳朵咬下来了。’他歇斯底里地在雪地上大步走着……他那满脸胡子、破烂的鱼皮袍子、掉落底的鱼皮靰鞡——除了它和女人看着不感到意外,要是被林子外边人看见,准会吓得掉了魂儿”[1](150)。人抛弃了良善如同野兽一般撕咬吼叫,粗狂而野蛮地活着。可以说,杨大群在整部小说中,于字里行间里将人类身上的这种动物性特征嵌套了进去,与作者在书写日本侵略者对人类与自然的冷酷迫害和残忍暴行不同,杨大群在表现这些赫哲族人时,仿佛尝试用一种怜悯的姿态赋予他们动物性的特征,在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境遇里给予人类这种动物性的出现以合理的原因,当生命的较量及生存的无奈成了人与动物所无法逃避的事实时,动物性的存在方式也许不过是人类繁衍和延续的一条不得不选择的道路。
三、生命平等与和谐的探寻
在《人·狗·狼》这篇小说中作者似乎有意去营造一种特殊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生存环境中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主体都被放置到了同样的位置上,不管是人、动物还是山林树木,它们仿佛都处于同样的生存境遇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生命的继承和延续。
姜祥发和霞云夫妇乃至于后来投入日军的刘淑亚,他们肩负的是繁衍后代的使命,小说中出现的抗联战士,承担着的是整个国家的存亡和未来,是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期盼和渴望。而在文中的动物形象白鼻梁母狗、白爪牙狗及黑尾巴梢子狼它们的挣扎和抗争也只是为了生存,或者说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种族的延续。这种共同点使得小说中所表现的生命主体在生的面前处于同样的地位,人类作为自然的灵长在这种环境中也许并不比其他生命主体具有更多的优势,有时甚至处于劣势,就像在小说中当姜祥发和霞云在丢失了生活工具不得不在树林中定居时白鼻梁母狗用嘴叼回了野鸡、松鼠、兔子,甚至是耗子给主人,在霞云和女儿被困沼泽时也是白鼻梁母狗更快地适应环境找来了食物,杨大群的文字把人类自身的生命与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主体融为一体,它们在同样的环境中,处于平等的处境里。
小说中曾写过这样一个情景,日本的飞机向姜祥发和霞云定居的森林投下了毒气,“绿烟呛得他们喘不上气来……像下饺子一样,蹲在树上的野鸡、飞进林子里的黑老鸹和爬上树的松鼠,都着了魔一样纷纷掉落在雪地上,砸得雪地直冒烟儿”[1](157)。“熊瞎子眼睁睁地一屁股坐在雪地里直打磨磨圈,好像站不起身子来,它们挤在一起,连看他们都不看一眼……整个大森林在旋转、翻腾,脚下的雪地在下陷、崩裂。雪变成了绿色,从森林的缝隙透在雪地上的白色斑点也泛起狼眼一样的绿光……”[1](158)森林中的人、动物,甚至森林本身在这个时候都处于同一生存危机之中,生存成为所有生命主体共同的期望。在文中姜祥发、霞云夫妇与白鼻梁母狗之间这种生命的和谐融合似乎表现得也很多。经历了火海之灾后的主人公们与白鼻梁母狗劫后余生地倒在一处,在沉静中,白鼻梁母狗向着天空嗥叫,远处飞来的大雁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也带来了生的希望。马架子后面的山坡上,霞云发现了一条子绿菜芽“她跪下身子,两手像捧金子似的连土捧起来,轻轻地按在胸脯上‘啥宝贝,这样撩你的心?’‘是—菜—菜芽!’‘啊!拱出头了?’‘你闻闻看多香。’‘啊!香。’祥发的手捧住女人的手,使劲地抽鼻子。白鼻梁母狗也跑过来,将两只前爪搭在女人的胳膊上,不住地用红润润的舌头舔她的手背”[1](114)。新萌发的菜芽想来不会如鲜花一般具有不可思议的香气,但是它却激起了姜祥发和霞云,甚至白鼻梁母狗无比激动的心,撩起了他们的热情,想来吸引他们的并不是菜芽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生的希望,绿色的希望,在这种生命的萌发面前,人与动物处于同样的平等之处,人与自然在生的面前达到了一种和谐和共生。
除了白鼻梁母狗,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情节,姜祥发和霞云一家人几经波折回到了黑龙江边,他们在老林子里有了自己的儿子小龙,在一个不大的江湾里藏身。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到处都郁郁葱葱,充满了生机。各种鸟都来垒窝,就连他们住的地窖子周围都出现不少小动物。草稞里有蹦跳的兔子,树丛中有飞飞落落的野鸡,江边不时出现来喝水的鹿、狍子哦、熊。祥发从打有了江里的鱼,从不惊动这里的野兽,几年前从林子里出来时所看到的那些被毒死的野兽总在他眼前浮现,他觉得能活下来的动物都不易呀!”[1](165)当他不得不为自己刚刚降生的儿子找一块裹身的布头时,他反复思索了很久,才不得不捉了几只兔子,闻着满地兔血的腥气,“他忽然想到以后在草稞里会不会还有兔子。他摇着脑袋想:是我不对吗?人吃尽了一切以后,是不是也吃掉了自己……”[1](166)姜祥发的疑问可以说正是作家借助这个以自然为生的赫哲族男人的口询问人类自身的,人类以自己的所需向自然不断地索取,以万物灵长自居试图驾驭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灵,但是这条道路的尽头又是什么呢,当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灵都遭遇了人类的侵害,人类自己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呢?应该说在小说中杨大群试图用巧妙的情节设置以展现一种生命的平等与和谐,展现一种生的美好和尊严,生命在生存面前如同花蕊一般绽放出了特有的美丽和绚烂。
王烨曾在其文章《关东的呼唤与寻找中的自我——略论杨大群和他的小说创作》一文中这样评价过《人·狗·狼》这部小说,说它是“既没有像《关东演义》那样揭示先进思想对人民的影响,也不同于《黑泪》所标新出来的‘寻找’意识,而是集中在对人类本身生存意志的挖掘,是对生存意志的礼赞”[2]。可以说,在小说中杨大群以平实自然的语言和文字,向我们展现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赫哲族人所经历的家国苦难,以及在这种苦难中他们遭遇的种种生存的危机和挑战。在杨大群的笔下他描绘了以姜祥发为代表的赫哲族人在日军的侵略和迫害中经历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这种极致的苦痛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不断拉近,人性本身的良善和卑劣得以凸显,生命自身的力量和璀璨在这种血与泪中迸发了出来,如同悬崖上的松柏在坚韧和顽强中呈现出不一样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