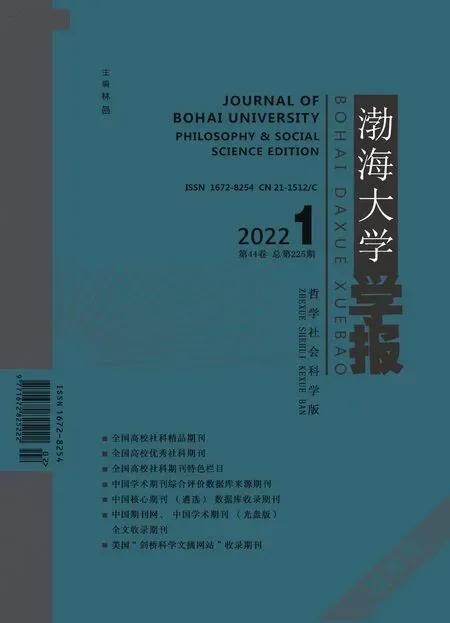两汉魏晋诫子书的文体形态与文化意蕴管窥
杨 允 赵女女(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家训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塑造理想人格、培育优良家风、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16年,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谈及家风家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
作为家训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诫子书”蕴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对当前推进家庭美德建设、培育社会文明新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诫子书,从广义上说是指以教诫子侄后辈为内容旨趣的各种家教类文献。”[2]两汉魏晋时期是中华传统诫子书发展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的诫子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诫”“书”二体是主要文体形式。基于前人的相关研究,立足于诫子书文本,本文拟对两汉魏晋时期诫子书的主要文体“诫”“书”二体及其文化意蕴做些许探究,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家训文化与汉前诫子书的发展
中华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其重要表征之一便是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诫子活动。据《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早在五帝时期就出现了家庭内部的诫子活动,如《左传》载:“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3]逮及西周,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王室尤为重视子孙教育,留有较为丰富的诫子文献。春秋战国之际,文献典籍中同样记载了古人的家庭教诫,如《仪礼·士昏礼》记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4]《论语》记载孔子教诫儿子孔鲤学诗学礼之事,后人称为“过庭之训”,等等。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暨诫子传统由来已久,这一时期出现的诫子活动,奠定了中华传统家训的文化基因。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注重家庭教育、家风建设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诫子书是家训文化的重要载体。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的诫子文献大多是由史官或后人追记,教诫主体与诫子文献的写作者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诫子事例零散地保存在不同的典籍文献中。到了汉代,训诫主体与诫子文献的写作者才“合二为一”,成为同一人。
从先秦至两汉魏晋,诫子书经历了由诫子行为至诫子文献,再到诫子书写作的发展历程。两汉魏晋时期正值由诫子文献向诫子书写作发展的关捩期,也是中华家训文化主体思想的定型期,文体形态多样,文化意蕴丰厚,无论对先秦家训文化及诫子传统的传承,还是对后世“诫子书”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两汉魏晋诫子书的主要文体形态
两汉魏晋时期的诫子书无论是数量、内容还是文体样式都实现了较大发展,“诫”“书”二体为主要应用文体。
(一)“诫”体
两汉魏晋诫子书的主要文体之一为“诫”体。“诫”体即表示教诫、警敕的一种文体。具备文体意义之“诫”与“戒”之本义密切相关。南朝任昉《文章缘起》云:“后汉杜笃作女诫。”陈懋仁注曰:“《淮南子》有‘尧戒’。诫,警也,慎也。”[5]刘勰《文心雕龙》释“戒”云:“戒者,慎也。”[6]可见,“诫”体早期的文体意义是从“戒”警慎、戒敕的本义发展而来,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韵书:‘诫者,警勅之辞’”[7]。
从文体特征上看,两汉魏晋“诫”体诫子书的标题通常都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凸显了这一类文本的实用功能。“诫”体诫子书的标题大多为《诫/戒××》,如东方朔《诫子》、刘廙《戒弟伟》等。此外,《家诫》是这一时期“诫”体诫子书又一常用的标题样式。而由于教诫对象的不同,针对家中女性成员而作的诫子书,通常又以《女诫》为题,如班昭《女诫》、荀爽《女诫》等。
两汉魏晋“诫”体诫子书行文较少铺垫,文章开篇即直奔主题。“诫”体诫子书通常由两部分组成:“道理阐述”+“教诫内容”。这两部分无固定的体制,往往依教诫主体而定。班昭《女诫》是较为特殊的一篇诫文,文章开篇是一段带有序文性质的文字,内容是交代她作《女诫》的缘由与意图。三国时期李秉的《家诫》也是体制较为独特的一篇。文章记叙了李秉答司马文王之事,通篇为两人之间的对话。结尾部分,李秉由事而诫,教诲家中后辈立身行事需谨慎。
两汉魏晋的“诫”体诫子书常引他人他事以教诫子侄如何为人处事。诸如东方朔引伯夷、叔齐、柳下惠之事迹,并评价他们的行为,“首阳为拙,柳惠为工”[8]。荀爽《女诫》引宋伯姬遭火不下堂之事。王昶《家诫》引成汤刻铭自我警戒、三郄为戮于晋等事。通过援引事例的方式,使教诫更具说服力。
两汉魏晋“诫”体诫子书引他人他事的特点受“诫”体诫子书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两方面影响:内容方面,“诫”体诫子书本就是为教诫家庭成员而作,教诫内容自然是每篇诫子书的重中之重。诫诲子侄如何为人行事,引他人他事的方式不仅能够具体贴切地传达训诫主体的意思,同时也给训诫对象以直观的鉴戒。形式方面,“诫”体诫子书是通过教诫、使训诫对象知所戒慎之辞。作为讲论道理的一部分,引他人他事的方式不仅强化了“诫”体诫子书的文体功能,凸出了戒慎主题,而且还彰显了“诫”体诫子书质素实用的文体风格。引用他人他事的写作技巧在魏晋诫体“诫子书”中较为常用,文章篇幅较长也在情理之中。
“诫”体诫子书以达意为主,形式灵活,诸体兼备。句子以散句为主,偶有整齐的韵语。句式整体上以短句为主,少长句。其中,两汉时期“诫”体诫子书,语言简略而理皆要害。魏晋时期,“诫”体诫子书的篇幅明显增长,王昶、嵇康的诫子书长达千字之多。教诫者在文中明是非、处利害、陈醇理、定从违、传经验、教方法,方方面面的教诫内容体现了为人父母挚切深沉的爱子之情。
概而言之,从整体上看,两汉魏晋“诫”体诫子书篇目较短,结构清晰,句法灵活,训诫主体能够根据需要巧用一定的训诫方法,重实用的特点使得这一时期的“诫”体诫子书总体上形成了较为质朴的风格。但其中也不乏一些“诫”体诫子书,注重了辞藻的敷设,使作品增添了一定的文学色彩。魏晋时期的“诫”体诫子书,已开始注重句式及辞藻的使用,一些作品中排比句屡见,流动中见整齐丽密之美。如东吴陆景《诫盈》教诲子弟诫盈守谦说:“富贵,天下之至荣;位势,人情之所趋。……盖居高畏其危,处满惧其盈。富贵荣势,本非祸始,而多以凶终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丧而身随之矣。是以留侯、范蠡,弃贵如遗;叔敖、萧何,不宅美地。”[9]长短句式自由变换,前人典故穿插其中,充分阐述了富贵无常、福祸相依的道理。
(二)“书”体
“书”体是两汉魏晋诫子书的又一主要形式。古代“书”体文是涉及范围相对较广的一种文体,先秦时期君臣往来的文书称之为“书”,汉代朋友之间的往来答复亦可称之为“书”。不同时期,“书”体文的具体指称有所不同。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所云:“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6](278)吴讷在其著作《文章辨体序说》中提及“书”体说:“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7](41)从上述阐释可见:广义的“书”体文包括私人书信和公牍书文。
从“书”体文的公私分类上看,“书”体诫子书属于私人书信类。但从文章体式上看,“书”体诫子书的文章体制与一般的私人书信之“书”体还有所不同。私人书信之体,以上下款称呼、开头结尾谦辞敬语为常态,但“书”体诫子书大多无这些格式。除西汉孔臧《与子琳书》、刘向《诫子歆书》以及东晋陶渊明《与子俨等书》有开头称呼语外,这一时期的“书”体诫子书开篇即进入正文。如郑玄《戒子益恩书》开篇即云:“吾家旧贫,为父母群弟所容。”[10]羊祜《诫子书》首句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11]以子孙为致“书”对象,不同于官场同僚、朋友之间的带有社交性质的书信文,需要一定的格式。私家领域的书文没有那么正式,自然不用严格遵循一般书信体完整规范的格式。
当“书”体诫子书没有了一般书信的固定体制,相对灵活的形式就为写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书写空间。
首先,两汉魏晋的“书”体诫子书,或从教诫缘由写起,或从写作者本身写起,行文灵活自由。但行文的自由灵活并不意味着结构的松散,相反,“书”体诫子书结构圆融,过渡自然。这一时期的“书”体诫子书通常从教子具体事宜写起,中间以阐明道理过渡,结尾再次回归诫子,文章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如刘向《诫子歆书》,从儿子刘歆得官拜职写起,其后格言事例并举,说明福祸相依之理。文章结尾再次回到儿子刘歆得拜黄门侍郎之事,教诫儿子谨慎为官。而一些侧重道理阐发的“书”体诫子书,文章结构则更为严谨,诸葛亮的《诫子书》即是其中的典型。围绕如何修身这一主题,诸葛亮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才、志、学之间的关系,修身需立志,明志需勤学,而学习则需“静”,文章层层推进,阐述道理精辟透彻。
其次,灵活宽松的文章体制为“书”体诫子书内容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书”体诫子书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对家庭成员的训诫及希冀、个人遭遇的倾诉、复杂情感的抒发,甚至对时人世事的评价等,都能够容纳到文章中。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借评述龙伯高、杜季良教诲侄子马严、马敦要谨慎言语、慎重交友。郑玄《戒子益恩书》,既有郑玄人生经历的叙说,又饱含对儿子的希冀。
再次,“书”体诫子书中,写作者常引用经典的语言来说明所要表达的道理。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将引用大致归为两大类:“略举人事”和“全引成辞”[6](411)。举人事以徵义,引成辞以明理。“书”体诫子书以引言的方式代替繁复的论证,既有说服力又显得内容充实。
与灵活的形式为写作提供广阔的书写空间相对,内容的丰富多样也决定了形式的灵活。如上所论,就内容方面而言,“书”体诫子书是包蕴性极强的一种文体。将如此丰富的内容纳入诫子书中,篇幅有长有短,写法灵活多变,作者往往因需而定。如郑玄的《戒子益恩书》,叙事是主要的表达方式。作者以简重精当的话语叙述了自己大半生的经历,而后以自己年迈七十,“案之礼典,便合传家”[10](846),自然过渡到对儿子的教诫,精简恰当的叙事为诫子主题的阐发做了必要铺垫。王修《诫子书》、陶渊明《与子俨等书》叙事抒情相结合,孔臧《与子琳书》、诸葛亮《诫子书》则是以说理为主。这些“书”体诫子书写法的不同,受诸多因素影响。究其根本,诫子内容决定了写法的多样。陶渊明的《与子俨等书》主要是教诫诸子和睦相处,抒情的表达方式更能拉近父子之间的感情。诸葛亮诫子勤学修身,说理的表达方式则更容易让儿子领悟学习的重要性。两汉魏晋面向子孙的“书”体诫子书,形式灵活,内容多样,情文相生,形成了亲切自然的文体风格。
综上,“诫”“书”二体是两汉魏晋诫子书的主要文体形式。对诫子主题的阐发,“诫”体倾向于戒敕,即警戒子孙不去做某事;“书”体则更多是明理以教诫子孙应该怎样做。同样是讲论道理,“诫”体更为直接,“书”体则相对舒缓,“书”体明显的抒情也是“诫”体所不具备的。
三、两汉魏晋诫子书的文化意蕴
数量众多的两汉魏晋诫子书,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写作者知识涵养、社会背景的不同影响着诫子书的具体内容,也折射出时代的文化格调。
(一)重儒兴教背景下的汉代诫子书
汉代重儒教的时代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诫子书在创作主体、诫子内容及作品风格三方面,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文化对诫子书创作的影响。
1.诫子书的创作主体以经学儒士为主
比较而言,两汉时期诫子书的数量较后世为少,梳理可见,明显的儒学背景是这一时期诫子书创作主体鲜明的群体知识特征。刘向,萧望之、周堪荐其“宗室忠直,明经有行”[12]。崔瑗,“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13]。张奂、蔡邕、郑玄,无一不是经学素养深厚之士。经学儒士为诫子书创作主体与武帝之后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汉初统治者的“无为而治”政策造就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武帝时,汉王朝国力强盛,“无为而治”已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此后,经学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尊经、读经、治经成为时代的风尚。汉代系统化的经学以明教化为根本,深受经学浸染的儒士不仅自身明经守礼,而且十分注重家庭教育。这是诫子书生成的主体文化特征。
2.诫子书的主题内容与儒学相契合
“诫子”自黄帝时即已萌芽,至周代真正意义上的诫子书产生,此间的诫子内容多王室内部的政教关怀。春秋以降,受时代环境影响,诫子内容多样,依教诫主体而定,极具个性。汉代以来,尤其是自武帝开始,儒学成为社会的主流学术。重儒兴教的社会环境加上创作主体的知识涵养使得诫子书的思想主题与经学相契合。马援诫子侄周慎敦厚,郑玄诫子勤学修德,郦炎教诲幼子“事君莫如忠,事亲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礼,汝哉其勉之!”[10](820)这些作品中教诲子孙应当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汉代人伦纲常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常行之德相契合。汉代女诫的思想内容与经学更为契合,以班昭《女诫》为例,文章对女子如何处理好与公婆、丈夫及叔妹的关系,都做了详细论述。论及夫妇之道,班昭《女诫》中多次以天之阴阳相比,如“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10](966)班昭《女诫》中流露的阳尊阴卑等内容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对此,我们应秉承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辩证看待,“去其糟粕”。但从中不难看出汉代女诫作品鲜明的教化宗旨,旨在维护等级秩序。
3.文章的风格凸显了质实重教的特点
诫子书是为教子诫家而作,文章的实用功能影响着文类的风格。尤其是在发展期的汉代,诫子书整体呈现出质实重教的文章风貌。
两汉时期的诫子书普遍以教为先,教化为本,诫子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两汉诫子书大多因事而诫,文章重点围绕诫子展开,内容较为单一。刘歆年少即居显处,处高临深,因此刘向写《诫子歆书》教诫儿子谨慎以避祸。东汉文人郦炎临终之际写有《遗令书》。郦炎自知将去,遂作书交代后事。他首先以老母托付兄嫂,其后对幼子止戈进行教诫。郦炎教诫幼子履行自己的训教,博学著书,忠孝信礼。文章结尾处写道:“咨尔止戈,吾蔑复有言焉,其永览于此。”[10](820)郦炎嘱咐幼子要永远阅看这篇家书,永以为戒。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年,郦炎《遗令书》、郑玄《戒子益恩书》等诫子文章,作者在文中开始以抒情教诫,个体的情感意志也借此得以展现。这一做法,魏晋诫子书有所继承。
两汉诫子书的创作主体以经学儒士为主,援引经书字句以教诫子孙是普遍现象,《诗》是最常引之书。如荀爽《女诫》引《卫风·竹竿》中的诗句:“泉源在左,淇水在右。”[14]郑玄《戒子益恩书》引《大雅·民劳》诗句:“敬慎威仪,以近有德。”[14](1142)班昭的《女诫》更是多次引用《诗》《易》《礼》,文中“经语”俯拾皆是,散发出浓厚的经学气息。两汉诫子书的创作主体多受儒学熏陶,诫子文章多中规中矩,引经据典,言之有本,往往以平实的语言把对子孙的教诲直接表述出来。但作者的个性并未因此被遮盖,典型如蔡邕。蔡邕,好辞章,妙操音律。蔡邕的两篇诫子书巧设譬喻,文辞精当,很有艺术性,风格独特。《女诫》一文由女子的梳妆打扮切入,借女子日常的面容修饰道出应注重心灵的修饰,构思巧妙,比喻形象。《女训》则将弹琴技巧与家庭礼仪的教诫相结合,教诫女儿鼓琴守礼,尊敬公婆长者。
(二)清谈玄学背景下的魏晋诫子书
与秦汉“大一统”相比,混战与分裂是魏晋时代的主旋律。这一时期,儒家独尊局面被打破,清谈、玄学因时而起。“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479)。魏晋诫子书在承续两汉诫子书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呈现出不一样的时代风貌。
1.诫子书创作主体多名士
“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本文借“名士”一词主要是就魏晋诫子书创作主体与两汉诫子书创作主体多经学之士相辨别。对“名士”的群体身份特征,本文认同牟宗三先生所论,“清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清谈、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征”[15]。概而言之,“名士”即魏晋时期带有清逸之气的士人。魏晋时期,诫子书的创作主体多为“名士”。如羊祜,德行清俭,其《诫子书》教诲儿子忠信笃敬。诸葛亮本避世清远,后入世辅佐刘备,其《诫子书》训诲儿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受社会环境影响,魏晋诫子书创作主体的知识结构较为复杂,不拘于儒学一家,如陶渊明。陶渊明早年尊儒,说自己“游好在六经”[16],曾经立志“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16](147)。而中晚年时期的作品则体现出鲜明的玄学及道家思想,崇尚自然,超脱豁达,向往隐居生活。陶渊明的《诫子书》中就流露出这种复杂的思想,他既教诫诸子和睦相处,追求齐家,希望他们“兄弟同居,至于没齿”[11](1179),又告诉儿子们:“夫天地赋命,有生必有终。”[11](1178)
2.背离时代主流的诫子内容
称为“清谈”或“玄学”的思想代表了魏晋时期的时代思潮,魏晋风流之士清谈老庄、善言名理。阮籍“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17]。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17](605)。在这种名辩清谈之风盛行之时生成的诫子书,主题内容却与主流思想相疏离。王昶《家诫》教子处世戒骄淫、言行多深思,保身全己以显父母。魏晋风流名士的代表嵇康,被捕入狱后留给儿子嵇绍的《家诫》全然与其本身的行为相左。嵇康在《家诫》中教诲儿子要立志守行、立身清远、言行谨慎。魏晋时期,任达放诞蔚然成风,而诫子书的作者仍诫勉子孙重视自我修养、谨慎言行、守礼立身,立身行事仍尚儒家之风,明显呈现出与时代主流相背离的特点。
3.情理相生的文章风格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作家任气使才,这一时期的诫子书整体呈现出情理相生的文章风格,极具情致又兼备理趣。
自汉末郦炎、郑玄叙己事、抒己情以教诲儿辈,魏晋诫子书创作主体在诫子的同时流露出更为明显的主体意识,抒发了更为浓烈的自我情感。王修《诫子书》开篇抒发对儿子的思念之情:“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10](952)结尾道:“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惜也。”[10](952)寥寥数语尽显天下父母的爱子之情。陶渊明《与子俨等书》中,对因自己绳倡固穷守节而累及儿子,深感愧疚,陶渊明写道:“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耳。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11](1178)深切的话语足见其对儿子们的挚爱之情。不仅如此,阅此一文,作者人格高洁、情怀高雅、向往自由安逸生活的自我形象跃然纸上。同时,“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11](1178)等清新活泼的描写为文章增添了美感。
魏晋诫子书作者在诫子的同时,也更注重诫子的语言技巧,援引他人他事自不待说,这一时期的诫子书开始敷设辞藻、讲求句式声律。兹以嵇康《家诫》为例(节选):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燿,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9](532-533)。
从选文可见,嵇康之诫句式整齐,语义层级递进。嵇康提出君子应当立志进而守志,反面论述无志及“心疲体懈”的几种原因和表现时,三组复句构成的层递,增强了表达的层次性和条理性,极富逻辑美。不仅如此,申包胥、伯夷、叔齐、柳下惠以及苏武等人的典故,巧妙地融入文章的论述之中。句法的整齐、词义的层层递进,典故的巧用以及间用韵语使得文章音韵和谐,进而形成了整饬的语言风格。排比复句的使用在这一时期的诫子书中不胜枚举,如姚信《诫子》云:“舍伪从实,遗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适泰,可以弘矣”[9](715)。
魏晋诫子书围绕诫子主题,把深刻的哲理引入文章,同时将其巧妙地与诸多艺术形象结合起来,使文章深刻的内涵得以形象地表达。殷褒《诫子书》开篇论述“道”为“易寻而难穷,易知而难行”[9](455)之理。何为“道”,“道”之难易又如何理解,对于这一抽象深奥的道理,作者巧借汉人京房、姚平之口加以解释,又指出当以颜回、曾参为榜样,教诫儿子朝益暮习、恭敬谨慎。
结 语
两汉魏晋时期诫子书的文体以“诫”“书”二体为主,每一阶段皆有佳作。“诫”体体制简洁,文章整饬精要;“书”体内容多样,形式灵活,文章亲切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诫子书均有所发展。重儒兴教背景下的汉代诫子书,以教化为本,引经据典是其最为常用之法;而清谈玄学背景下的魏晋诫子书,文章更讲行文技巧,文情并茂、情致理趣兼备,诫子书逐渐朝着“文质彬彬”的方向发展。作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产物,诫子书的实用性较强,有着特殊的用途与内容,但这一文类也鲜明地体现出少有的抒情色彩与强烈的文学性。
重视对子女的养成教育,对其立德修身进行规诫,为其成才成长打好必要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华道德文化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诫子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一抹亮色,“诫子书”中蕴含的思想十分丰富,是家风及家训传承的重要载体,对中华家训文化的承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两汉魏晋时期是中华诫子书发展的关键期,这一时期诫子书蕴含的立志修身、恭谦谨慎等思想为优良家风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当下,在我们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进行优秀家风承传及“立德树人”教育的今天,合理汲取中华“诫子书”中的精华,对弘扬良好家风、传承中华文化与中华美德,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