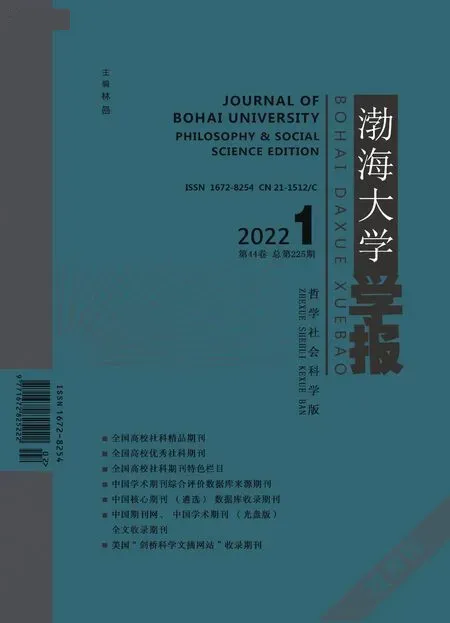评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
武新军(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较劲”与“死亡”
过去读邵丽的小说,感触最深的是她对弱小者内心创伤的细腻呈现,对卑微者深厚的人性关怀。长篇小说《金枝》在爱恨生死的纠缠中,对女性问题进行了历史化的书写,并通过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之间的“较劲”及由此形成的“心结”,从而抵达人性最敏感、最脆弱之处,并揭示由“较劲”而产生的“心结”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小说具有明显的女性视角,显示出对女性问题的强烈关注。穗子、朱珠两位女性与丈夫周启明相互“较劲”了一辈子:周启明与穗子结婚,是祖母包办的结果。周启明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后,与穗子离婚而后娶了朱珠。穗子恨朱珠夺走了自己的丈夫周启明,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她虽然蜗居老家,但“一直控制着我父亲,并企图通过父亲操控我母亲和我们的家庭”[1]。为了发泄内心的仇恨,她甚至还采用巫术整治朱珠,并把内心的仇恨向女儿周拴妮发泄,常常把女儿身上掐得紫一块青一块。革命者朱珠宠辱不惊的,但她也不能置身事外,在获悉周启明在农村曾经结过婚并有个女儿后,她开始悄悄打扮自己,家里家外都精精神神,仿佛和谁较着一股子暗劲儿似的。而周启明一辈子精神上最大的重担,就是他乡下的妻子和女儿,他一辈子都不曾爱过她们,但他一辈子都欠着和怕着她们。这让他苦不堪言。他一辈子小心翼翼地逃避亲情,也与这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作者用了较多的笔墨揭示祖母和穗子两代女性的悲剧,并写出她们在“死亡”面前的觉醒:她们都生活在执念中,更相信“身份”和“仪式”的力量,而不清楚自己究竟需要什么。被周同尧抛弃后,祖母一辈子等待他归来,“我死了要埋在周家的坟院里,按着辈分,埋在你太爷爷太奶奶下首。周同尧死了,要拉回来和我合葬!”[1](37)这是她一生坚持的底线,也是她活下去的理由。即将到来的死亡使她觉醒了,她用尽力气将庆凡与穗子的手拉到一起,希望穗子不再重复自己一生守寡的悲剧。而穗子则异常看重周家少奶奶的身份,虽然离了婚,但她一辈子坚持自己是周家明媒正娶、用八抬大轿抬来的,生是周家人,死了也要埋在周家坟地里,与周启明合葬。因为生活在名分的执念中,她看不起没有身份的下人,拒绝了关心、帮助了自己一辈子的周庆凡,拒绝了小店主的求婚。她也是临死前才觉醒过来,叮嘱女儿把她葬在自家的田头,与周庆凡的坟隔田相望。她终于明白了真正的关爱才是最重要的。
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周语同,也是在不断地与人“较劲”中成长起来的:她与自己的父亲格格不入,与父亲“较劲”了一辈子,“我这半辈子为什么如此努力。我就是想让你爷爷他们重视我,我必须证明他们对我的轻视是多么不公允,我就是要混出个样子来。……我是要用我的好,证明他们有多不好!”[1](213)周语同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拴妮,也差不多“较劲”了一辈子:她们都认为对方夺去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幸福。在穗子的折磨与哭骂声中,周拴妮仇恨抛弃了他们母子的周启明,并因此而仇恨周家所有的人;而周语同则仇恨周拴妮闯入了自己的家庭,让一家人受尽屈辱,憎恨周拴妮的母亲穗子。
上述由“较劲”而产生的“心结”,只有在死亡面前才得以化解。当父亲进入晚年后,周语同一直以爱的名义控制父亲,在父亲去世前,两人的关系突然逆转了,父亲不再听命于女儿的安排,他的死亡结束了父女之间相互漠视的斗争。周语同和拴妮子之间关系的缓解,也是因为她们共同父亲的死亡。周启明去世后,周语同开始反思自己与周拴妮的关系:“我们斗了一辈子,分出什么输赢了吗?或者说,即使分出了输赢,胜利者真的胜利了吗?而且那大约是父亲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1](117)在不断反思和调整中,周语同“对周拴妮和她的孩子们,都有了另一种理解,至少不再那么抵触了”[1](171)。
二“代际冲突”与“隔代亲”
《金枝》给人印象很深的,还有作者对“代际冲突”与“隔代亲”现象的细致书写,并由此呈现出周家家族史的一些基本面貌。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周家不同代际的人之间,是存在明显差异的:革命者周启明是有信仰的,他内心简单,一辈子都像心智简单的儿童,但他又不是现在的巨婴,他除了能够承受生活的苦难,还有着担当和底线。他不允许后辈冒犯自己的信仰,当有人试图触碰他的底线时,才知道它有多么坚固。周启明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是靠信念和信仰支撑起来的,他亲眼看到父亲和革命同志惨烈的死亡,自己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批斗折磨,但他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热爱党和领袖。有谁在他面前说领袖的不是,他立刻会拍案而起,甚至会反目成仇。他和自己的女婿——周语同的丈夫之间,曾因为如何评价革命历史而经常出现矛盾。他告诫做官的儿子要清正廉洁,否则他自己会站出来检举。而母亲朱珠的精气神,也是靠信念支撑起来的。她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存活于世的人,她和丈夫周启明之间没有温柔的情感,也不懂得如何悉心呵护自己的儿女,一辈子都不会说一句柔软得像母亲该说的话。她宽厚忍耐、从容镇定,有咀嚼和消化屈辱并使自己更坚强的能力。她更注重真实而远离时尚,她衣着朴素,习惯穿自己缝制的棉布衣裤,活了一辈子,骨子里还是个乡下人。
周启明的女儿周语同这代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走向社会的。在重视个人主体性的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他们并不完全认同父辈们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个人的奋斗与个人的成功,也就是作品中多次出现的“要混出个样子”。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女们能够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成功。在如何评价革命历史的问题上,他们与父辈有着明显不同,他们更为看重个人的主体性,不能完全认同父辈们的历史观。与周家的革命父辈相比,周语同的子辈们,则更为缺乏积极向上的力量:周小语婚姻失败后精神崩溃,失去了搏击生活的力量,“金枝玉叶一旦遭摧折,比普通的一枝一叶更不堪”[1](208)。作者认为他们缺乏的正是祖辈们的精神和劲头。
在小说中,“代际冲突”多发生于父辈与子辈之间。周启明和周语同父女之间,始终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缺少相互的理解与沟通:女儿小时候,父亲一直在控制女儿,阻碍女儿去当兵,反对女儿穿裙子、反对女儿自主选择婚姻;而女儿也不理解父亲,她一直渴望能早日离开父母,离开这个冷漠的家,在父亲衰老后,她一直在控制着父亲,干涉父亲的衣食住行,一次次粗暴制止父亲想回老家看看的愿望。“我”与女儿林树苗之间,也隔着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沟壑:“我”希望女儿成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成功者”,逼迫她学钢琴,歇斯底里地控制她,以爱的名义对她施暴,千方百计地想要把女儿纳入自己设计的道路;而女儿则一直在反抗、拒绝“我”对她的人生安排,想要走自己的道路。穗子与女儿周拴妮的关系也是如此。穗子认为周家三代女人守寡,是因为男人读书变心,因此不让拴妮子上学认字,将她一辈子拴在身边;拴妮子也为此恨了她一辈子。
作者还以不少篇幅展示代际关系中“隔代亲”现象,这种现象具有永久性特征,更多地与人的年龄、生理情况等有关。周启明夫妇无暇体会孩子内心的创伤与疼痛,周语同的幼年充满孤独、痛苦与绝望,只有奶奶周庞氏给予她更多的理解。而耐人寻味的是,周启明对子女漠不关心,进入老年后在孙子孙女们面前却像变了个人,“被孩子们所要挟,温情得一塌糊涂”[1](182)。他过分呵护外孙女林树苗,帮她对抗妈妈,帮她扯谎和拖延时间,“我”和父亲因此出现严重冲突。接下来,“隔代亲”的现象又循环出现了:周语同对女儿冷酷无情,等她年龄大了,竟然也像自己当年反对的父亲那样,对外孙格外地柔情似水,帮他扯谎和掩盖错误,因此与女儿林树苗之间出现尖锐矛盾。在女儿林树苗打骂外孙时,周语同突然脱口而出:“他还这么小,有你这么狠的妈妈吗?说完之后,我自己先呆住了,这不是我父亲的话吗?怎么从我嘴里说出来了?”[1](183)周语同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当年呵斥父亲太过分了。
作者从代际关系角度展示周氏家族的历史,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尤其是对“隔代亲”现象的书写,我们在过去的作品中很少见到。但小说从不同代际的差异揭示社会历史内涵方面,还略显不足,对历史环境、社会变革与周家不同代际的性格特征、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空间。小说更多地呈现出革命前辈、自己一辈、孩子一辈在精神气质上的某些重要差异,而对于三代人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对话则用力不够。受此影响,作者对革命历史与当下生活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就很难深入下去了。
三、“阶级”与“血缘”
听说《金枝》在正式出版前,曾经被命名为《阶级》,从书名的修改更容易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及面临的困境。在叙述周家城市与乡村两个家庭的关系时,作者确实有进行阶级分析的考虑,也势必会面临如何处理“阶级”与“血缘”关系的难题。
在叙述周家的历史时,小说关注“阶级身份”对人的影响。周同尧、周启明都是地主家庭出身,都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走上革命道路,也都因此在后来受尽折磨。父亲的祖父周同尧参加过长征、打过鬼子、驱赶过老蒋,有过光荣的革命经历。只因为说不清长征途中脱离部队三个月的历史问题,在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最后含冤而逝。周启明因为叛徒爷爷和失踪的父亲,无论工作多么积极、多么有能力,也不能得到重用。周语同也受到父辈们的影响,因为父亲的革命经历,她在各种表格中可以填写“革干”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出身不好的代称,对她的成长也造成不良影响。周庆凡是周家收养的孩子,是周家忠实的长工,后来被错划为地主。因为这个身份,他爱了穗子一辈子却未能结婚。地主子女刘复来有智慧,却生活得像贱民一样:不能与相爱的人结合,不能当兵,不能上大学,甚至不能参加高考,只能以“倒插门”的方式,“嫁”给了穗子的女儿周拴妮。
《金枝》有意把“血缘”与“阶级”的关系并置在一起,在有着血缘关系的两个家庭的成员发生交集时,作者刻意呈现其生活水平、家庭教养和精神状态的差别:周雁来生活困窘,她第一次到周语同(母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家时,对其富足的生活充满好奇和羡慕,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周启明的葬礼上,作者也对两个周家的子弟们的言谈举止进行了对比。而当作者摆脱了“血缘”的纠缠,笔触就更为自由了些:周鹏程第一次上胡楠家吓了一跳,胡楠家的大房子、高级家具、生活方式等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周拴妮给新过门的城里儿媳“红包”时的权衡,儿媳妇慷慨地向农民婆婆表达心意,显示出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
作者还把“阶级”分析的意图贯穿两个家庭后代的对比中。身在农村的周拴妮的儿女们(周开河、周鹏程、周雁来、周千里)都具有独立自强的精神:他们考上大学,周拴妮只给一年的生活费,周开河靠家教、承接设计活儿完成学业,一口气读完本硕博,此后,又出国深造;周雁来靠端盘子、洗碗、替环卫工人扫大街完成学业,后来成为会计师;周鹏程依靠个人奋斗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娶了总工程师的女儿,屈辱是他前行的动力,他所有的努力与付出,都是为了让妈妈能够在周家活成个人,活得有点尊严。这种为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而奋斗的精神,完全符合周语同坚持的人生哲学,难怪她会为周拴妮几个子女而激动:“我感到周家的历史画卷呼啦一下被展开了。谁说我们周家一代不如一代呢?我激动得有点眩晕,也有点轻微的战栗”[1](178),也难怪她会欣赏周开河“脸上的那种自在从容,在我们家其他孩子脸上还真没看到过,即使在周围的人中也很难见到。那自信是透明的,清晰可见”[1](176)。
作者也以较多的篇幅揭示了贫穷对周拴妮儿女们的影响:他们孤陋寡闻,没有见过世面,缺乏教养和体面,周雁来到林树苗家做保姆,很快就开始对保姆颐指气使,显露出野蛮生长的孩子的粗鲁。他们不敢任性和叛逆,因为任性是需要资本的。周鹏程内心一直充满压抑、屈辱和卑怯,他嫉妒“周天牧可以不读硕不读博,他敢于任性,那是因为他有任性的本钱。他们这些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金钱和名利都无所谓,即使输了,也是惬意的,是他们自己愿意输”[1](224),即使周鹏程博士毕业,即使他娶了胡楠好多年后,仍是觉得内心难以平衡。
周语同在叙述自己城里兄妹几个的孩子时,一方面展示他们的体面和教养:周家的每个男人都高高大大,都有娘胎里带出来的贵气,大哥的儿子周天牧举止斯文,待人接物沉稳有度,礼貌周全,一看就是大家调教出来的孩子。另一方面她又不满意他们一个比一个不争气:周天牧中看不当用,念初中、高中妈妈都租房子请长假陪读,一个孩子花了人家几个孩子的力气,才勉强上完本科。周小语则养得太精细,失去搏击生活的力量,丢弃专业,失去婚姻,屈服于命运,她有浪漫的心却没有浪漫的能力,既不知如何去爱,也不懂得如何拒绝,在她精致的躯壳里面,揣着一颗漠然的心,她从不索要温暖,也不会温暖别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差别问题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但都很难称得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分析:作者把家族血缘与阶级分析纠缠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学分析的视野,尤其是作者笔下两个家庭子女之间的鲜明差异,让人感觉多少有点牵强。作者希望以血缘亲情来缓解两个家庭(或者说作者所谓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周拴妮从京城儿子儿媳家荣归故里,与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其乐融融地吃饭,“久违的亲情在刹那间被激活了”[1](223)。周语同对周拴妮几个子女的支持,如慷慨地帮助周雁来静心学习考研,拿出大量的钱资助周千里买房子,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也是周家的后代,与自己有血缘关系。这样的叙述是存在风险的:假如没有这个血缘关系,周语同与周拴妮的子女们萍水相逢,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当如何呢?这样也许会有更多的阐释空间。以家族史来呈现社会历史的变革,在过去并不缺乏成功的作品,其前提是家族的命运具有广泛代表性,深度关联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能写出社会历史的变革对家族关系的深刻影响。而《金枝》则局限于家庭的层面,好像在有意规避周家的子女们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样的写作路径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温情来解决“阶级”矛盾问题,人为地、轻易地使矛盾得以和解,这不但会掩盖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也会成为进行深层次社会历史分析的障碍。
四“自我经验”与“历史书写”
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周语同,是一位“拿奖拿到手软的著名艺术家”,她对事件的叙述与评价,更多的是从自己的“成功哲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果一直让周语同在小说中喋喋不休,那就可能把这本小说写成一篇通俗小说。好在周语同在叙述时,是时时有自我反思、自我批评乃至自我反讽的。她既是家族史的叙述者,也是自我叙事的反思者。作者也尝试着引入其他的叙述角度,周语同的女儿林树苗觉得:这个家庭的复杂程度是无法想象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全方位地描述,“我妈妈,鹏程的妈妈,包括我的舅舅们,甚至周家的这些亲戚们,他们每个人叙述的我姥爷都不一样。我想了解姥爷的过去和现在,然后将这些故事写出来。”[1](228)假如作者选择林树苗作为主要的叙述者,小说可能会更深入地揭示这个“复杂程度无法想象”的家庭。
周语同曾给侄女画了一幅名为“金枝玉叶”的肖像画,她渴望周家女孩儿真的活成金枝玉叶,实现自己不曾实现的,完成自己不曾完成的,拥有自己不曾拥有的。林树苗并不认同这种女性观,她曾尖锐地批评母亲的成功学:“我妈一辈子都在纠结周家的后代争不争气,那是因为她不屑于了解我们。她端着架子生活在云端里,不肯纡尊降贵,多看咱们一眼。”[1](228)母亲则以忍耐和宽容,彻底颠覆了周语同的人生哲学,“她用她的智慧固守一个男人,通过一个男人固守一个家,通过一个家固守整个世界”[1](270)。母亲最终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浅薄,开始反思自己:“我自以为是的成功,父母他们认可吗?”[1](269)在小说中,周雁来也是周语同叙述的质疑者,小说插入了周雁来的文章《穗子》,周雁来害怕写这个家族的历史,会曲解了她的姥姥穗子,忽略了他们的父亲刘复来,而这也正是周语同的叙述所存在的偏差。由于多了一个观察和叙述《穗子》的角度,穗子和周栓妮的性格与行为,她们生存的艰辛与无奈,刘复来为周家所做的牺牲,才能够被读者更好的理解,小说也因此具有更多的人性内涵。
周语同的自我反思,林树苗、周雁来等叙事者的引入,实际上是从平常人看事物的眼光中超脱开来,向精神的高处攀升,这虽然使小说在精神层面抵达了一定的高度,但还有着诸多提升的可能性。就整体感觉而言,小说中周语同的话还是太多了些,形成了垄断性的叙述,其“贵族式”的、“成功者”的叙述,多少影响了作品的多元性与对话性,周拴妮、林树苗、母亲、周雁来、周鹏程等人的叙事,在作品中都没有得到充分展开。邵丽在谈及《金枝》时,曾表示自己可以进一步从周拴妮的角度展开历史叙述,写作一个长篇小说。我们对此充满期待,希望能够读到一部整合不同叙事视角、整合历史与当下的更为精彩的长篇小说。
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邵丽的《金枝》更多的是个人经验的书写,作家的自我意识是强烈的,这种写作姿态是宝贵的,但也容易产生问题:要想在个人、家族的小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大历史之间建立有效联系,形成同频共振的历史叙述,过多地依靠个人生活经验是很难完成这个使命的。如果不在自我与时代之间进行深入探索,过于强烈的自我反而会成为进入历史的障碍。更多地凭借个人经验,而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未能跟上,也会影响历史小说的完成度。在整合个人经验与历史变革的关系时,也不应过多地依赖各种偶然性,而是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支撑,需要不断地把个人生活经验提炼为历史的话题,需要在感觉与观念之间自由穿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触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才能够呈现出历史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够创造性地呈现历史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家庭、伦理、性别等问题。《金枝》触及了如何评价革命年代的重大问题,这是很好的,这个问题需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空间进行客观考量,而不能从个人的、情感的角度做出人言人殊的历史评价。视野拘囿于家庭内部,回避广阔的社会生活,是很难深度呈现波澜起伏的历史变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