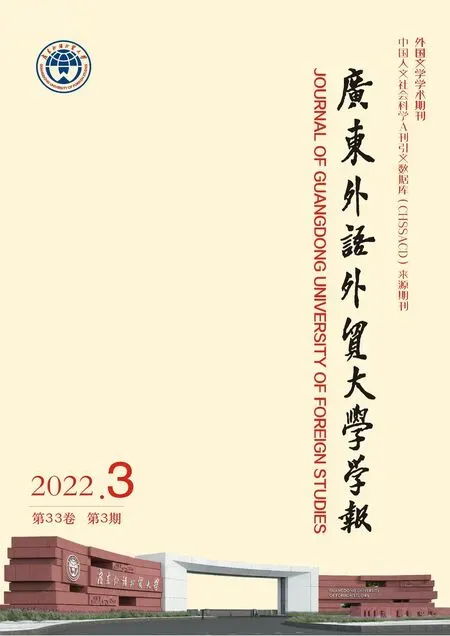明代小说《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海外传播与启示
谭渊 刘琼
引 言
作为比较文学和传播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中国故事”的海外传播近年来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早在18世纪,伴随中国典籍的外译,中国文学作品就开始传入西方。1735年,耶稣会教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在巴黎编辑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ph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chinoise),将元杂剧《赵氏孤儿》《诗经》中的《天作》等八首诗歌、《今古奇观》中的三篇小说以及一批小故事介绍到欧洲,正式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西方传播的历程。在这批作品中,元杂剧《赵氏孤儿》引起的反响最大,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据此改编创作了戏剧《中国孤儿》,在欧洲引起轰动。而《中华帝国全志》中刊出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三部短篇小说虽然也在欧洲文学中留下足迹,但受到学界关注较少。本文以《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为重点,对这一故事近三百年来在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历程进行梳理,并对推动这一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传播的动力源泉进行分析。
《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行善故事与道德训诫
1735年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选入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三个故事均出自明代冯梦龙、凌濛初编写的小说集“三言二拍”,后被收入抱翁老人选编的《今古奇观》。就《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译文与《今古奇观》在细节上的吻合程度来看,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所选译的三篇小说均是以抱翁老人加工过的版本为底本。近年,法国汉学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殷弘绪的译作手稿,手稿(Ms. Fr. 19536)上有其签名,署有“1723年11月28日于北京”字样(蓝莉,2015:239,342)。
纵观《中华帝国全志》选入的三篇中国小说,它们都通过精心编排故事情节,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带有道德训诫的色彩,同儒家的伦理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中华帝国全志》第3卷中,杜赫德还在中国文学译著前附有一篇名为《中国人在诗歌、史传和戏剧方面的品味》(DuGotdesChinoispourlaPoésie,pourl’Histoire,pourlesPiècesdeThéatre)的导言,文中写道:“中国小说与我们近几个世纪以来流行的小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我们的小说大多都是些爱情故事以及虚构的故事,它们虽然能供读者娱乐消遣,但同时它们对激情的过度渲染却使其变得十分危险,尤其会腐蚀青年读者。而中国小说则充满训诫,包含非常适合用于教化品行的格言,并几乎总是教导人践行美德”(du Halde, 1735:291-292)。杜赫德虽然对中国文学了解甚少,只能通过殷弘绪等人寄来的有限几篇译作管中窥豹,但这番评价却与“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观》编者的动机不谋而合。
《今古奇观》全书共有40篇,均选自明代著名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在《警世通言·序》中,编者冯梦龙(2012:1-2)明言自己编撰此书的目的是“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即为宣扬儒家忠孝节义思想服务。同时,冯梦龙将作品集分别命名为《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仅从这种命名就不难看出编者强烈的道德劝诫和伦理教化意味。“二拍”紧随“三言”之后问世,编者凌濛初(1992:2)在《初刻拍案惊奇》卷首《凡例》中宣称作品“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通过在故事中插入大量劝诫性的诗文来达到“劝善惩恶,有益风化”的宗旨。而《今古奇观》则是优中选优,从“三言二拍”中精选出40篇,在编辑加工时进一步强化了宣扬儒家伦理的意味,编者抱瓮老人秉承冯梦龙、凌濛初的宗旨,他在序言中坦言自己编选此书就是为了使“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抱瓮老人,2013:2)。因此在《今古奇观》所选的40个短篇中,在题旨(开场诗)中指明以“扬孝悌”为宗旨的作品就有20多篇(代智敏,2014:79)。
殷弘绪翻译完成的小说《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出自《今古奇观》第31回,故事中的主人公吕大郎原名吕玉,他心地善良,由于孩子喜儿早年被人拐走,他离开家乡无锡,到外地一边经商一边寻访孩子下落。有一次,他无意中捡到一个装着二百两银子的钱袋,于是在路边等了一天,待失主前来认领,后来终于在下一个客店中找到失主陈朝奉,送还了钱袋,并拒绝失主与之平分银两的建议。意想不到的是,吕大郎在说出自己的儿子7年前被人拐走后,陈朝奉想起7年前人贩子丢在他家里的孩子也来自无锡,名叫喜儿,于是叫孩子来相认。通过核验喜儿腿上的胎记,吕大郎得以与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相认,父子终于团聚。此后,吕大郎在返回无锡的路上又看到有人落水却无人搭救,于是出赏金请人救起落水之人,等到被救者来道谢时,他才发现此人竟然是来寻找自己的三弟吕珍。原来,他的二弟吕宝生性贪婪,趁哥哥不在家之际,谎称哥哥病故他乡,想将嫂子王氏卖给外地商人做妾,发笔歪财。但阴差阳错地是,因为王氏在黑暗中掉落的白色孝髻正好被吕宝的妻子杨氏捡去戴上,商人又与吕宝约好以白髻为识别王氏的标记,结果上门抢人时反而错将二弟吕宝的妻子杨氏抢走。最终,行善的吕大郎终于阖家团圆,子孙昌盛,而作恶的二弟吕宝却赔上自己的妻子,最后羞愧无比不知所踪。整个故事彰显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从标题发生的变化来看,殷弘绪直接舍弃了原标题《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将其改为《一个关于行善之举使家庭得以兴旺的故事》(Histoireoùl’onvoitqu’enpratiquantlaVertuonillustresafamille),更加强烈地突出了教人向善的道德伦理主题。同时,殷弘绪不辞辛劳地译出小说中的多首诗歌,尤其是故事开头的题旨诗“善恶相形,祸福自见;戒人作恶,劝人为善”(抱瓮老人,2013:375)起到了总领全篇、画龙点睛的作用;而故事结尾处的一句“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抱瓮老人,2013:380)则被殷弘绪变为一句呼吁:“让我们从这个故事学到践行美德是多么有益:这就是家族日益兴旺的原因”(du Halde,1735:303),更加凸显了故事的道德训诫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1735年版《中华帝国全志》第3卷中,《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等三篇具有道德说教意味的翻译小说还与位于它们之前的章节《中国的道德哲学》(DelaphilosophiemoraledesChinois)、《关于品行的格言、睿思和范例集》(Recueildemaximes,deréflexions,&d’exemplesenmatièredemœurs)等构成了一个单元。《关于品行的格言、睿思和范例集》其实选自明末清初福建人李九功所编的五卷本《文行粹抄》中的《崇德集》《修慝集》《辨惑集》,其中许多小故事都有树立道德典范的意味,如“罗惟德任职宁国时乐善好施”“一位徽州商人途经九江,施惠获报”“有钱有势者不应不认穷亲戚”等(蓝莉,2015:238)。而“崇德”“修慝”“辨惑”均出自《论语·颜渊》,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格局体现了《中华帝国全志》编者杜赫德的良苦用心:他将反映中国人伦理观念的故事、小说编排在对中国道德观念的介绍之后,强调了中国人对道德伦理的重视,凸显了道德伦理教育在中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也建构和传播了启蒙时代作为“道德伦理之乡”的中国形象,并有将中国作为欧洲人道德榜样的意味。由此也不难看出,耶稣会的译者和编者之所以优先选择《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之类并非一流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传播,正是因为看中了作品强烈的道德教诫意义,其选择标准是故事所包含的伦理观念和教化功能,而非作品所达到的文学水准。
耶稣会传教士对道德教化作用的重视一方面决定了他们在译介中国古典小说时须对翻译对象进行精心选择,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他们要对译文进行小心翼翼地处理。《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吕玉少年久旷,也不免行户中走了一两遍,走出一身风流疮。服药调治,无面回家。捱到三年,疮才痊好”(抱瓮老人,2013:376)。“行户”是古代人对妓院的称呼,所谓“风流疮”则是对性病的委婉说法。在耶稣会神父笔下,这段文字变为:“买家拖欠货款,加上又有一场严重的疾病侵袭了吕玉,使他在这个省逗留了三年”(du Halde,1735:363)。该小说的译者殷弘绪曾在中国传教30多年,算得上一个中国通,很难想象他是由于对中国社会百态的隔膜而没有读懂小说中的这一细节。他在翻译时隐去主人公吕玉逛妓院并染上性病的情节,显然是因为这一情节客观上损害了主人公吕大郎的道德楷模形象,同时也与杜赫德在序言中所宣扬的中国小说没有“激情”相矛盾,只有不动声色地将这一细节略去才符合耶稣会士通过中国故事宣扬道德教化的目的。
可见,耶稣会选择《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作为中国文学的代表作进行翻译是基于其道德立场,他们与“三言二拍”的中国作者们一样将文学作品视为宣传道德教化的有力工具,积极肯定了中国小说弘扬道德的立场,并在文学传播过程中向西方读者呈现了一个作为道德伦理之乡的正面中国形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的“还金”故事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Dieudonné,1638-1715在位)在资助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6位耶稣会士到东方传教时,特别希望他们“在传播圣教之余”也对中国文化加以报道(王宁、钱林森、马树德,1999:41)。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从1687年法国耶稣会士抵达中国到1773年耶稣会被罗马教廷下令解散,来华耶稣会士出版的汉学著作多达353种,其中除杜赫德出版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外,从1702年起,在巴黎的郭弼恩(Le Gobien)、杜赫德神父等人还将传教士发自中国及东南亚的书信报告系统汇编为《耶稣会通信集》(Lettresédifiantesetcurieuses),又称《耶稣会士书简集》,前后出版34卷。几乎就在《中华帝国全志》发表的同时,1736年《耶稣会通信集》第22卷刊发了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龚当信神父(Cyrile Constantin, 1670-1732)在1730年10月19日写给杜赫德的信。在这封信中,龚当信赞扬中国皇帝(雍正)治国有方,他不仅摘译了多份中国官方《邸报》中公布的诏令,还抄录有一份出自雍正皇帝的训令,其中提到了一位中国农民拾金不昧的真实故事,它与同一时期《中华帝国全志》中发表的文学故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相映成趣,对塑造启蒙时代欧洲人心目中作为“道德伦理之乡”的中国形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龚当信的信里,这个拾金不昧的故事首先由河南总督田文镜通过奏章详细报告给雍正皇帝,雍正收到奏章后非常高兴,下令表彰拾金不昧的农民翟世有,并发布训令,要各级官员廉洁奉公,以求转变社会风气,使民风淳朴。龚当信将训令的内容完整翻译下来并冠以标题:“河南省总督上奏皇帝表彰一对诚实无私的平民夫妇”(龚当信,2005:334)。龚当信提到的这个故事发生在1728年田文镜治下的孟津地区:
阴历初三,陕西省的商人秦泰到孟津去收购棉花来贩卖,他身上带了一个装有一百七十两银子的钱袋,他在宋家山附近的途中不小心掉了钱袋,但他没有发现仍继续赶路。
第二天早上,一个叫世有的当地穷耕夫到宋家山附近去耕地,捡到了这个钱袋,他并没有想到要据为己有,而是想归还给失主。他在原地干了一整天活,等待失主来寻回钱袋,可没有人来。晚上,他回到家里,给他妻子徐氏看那装满了银子的钱袋,给她讲了是怎么一回事。她马上说:“这钱不能拿,我情愿受穷也不愿意拿别人的钱,你明天想办法去找到那个失主,把钱还给他。”
……客商寻回来了。世有问了他钱袋外表、银子的包装、数目、形状、成色,客商一一作了回答,他认定了钱袋就是这位客商的,就亲手交还给了客商。(龚当信,2005:335)
随后,这个叫翟世有的贫苦农民还拒绝了失主与之平分这笔钱的建议,也没有要任何其他报酬。虽然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还金完骨肉”这样巧合的事情,但官员们对此的反应却远远超出了文学家的想象,他们不仅对拾金不昧者给予嘉奖,而且将这件好人好事作为民风改善的证明加以大肆宣扬:
县官很高兴在他治下有这么一件好事,他召来了几个见证人,问明了真实情况,向我(巡抚)做了报告。我马上派人送了五十两银子给农夫世有,奖赏他和妻子的品德,我同时还给了他们一块匾。然后,嘱咐省里的财务总管写下这件事,让老百姓学习他们的好榜样。然后,我令孟津县官在该农夫家门前竖一块碑,刻上他的事迹,留作永久的纪念,鼓励当地居民更好地坚持好品德。(龚当信,2005:336)
引起欧洲传教士注意的还有中国皇帝得知此事后的反应:“皇帝得知了此事后,显得很高兴,趁此机会劝告全国改良民风。他亲笔写了下述训示,附了总督的奏报,下令发到全国各省”,并且下令赐给这个拾金不昧的农民七品顶戴和一百两银子(龚当信,2005:336)。雍正毫不掩饰自己这样做的目的:“表彰一下那些特别忠实、虔诚、节欲、正直的人们,他们对这些人的表扬就会激励其他人加强道德,不久,即使在百姓中也会讲究道德成风。讲道德是会有报偿的,每个家庭都会争先恐后地做名副其实的好榜样” (龚当信,2005:338)。同时,雍正皇帝还借题发挥,在激励其他人仿效榜样的同时,希望官员们都能奉公守法,树立正直、简朴的民风,“用好的世风来改良所有朕的臣民们的心灵”(龚当信,2005:339)。
这个故事当然并非道听途说,雍正长达1200多字的谕旨也很容易在《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中查到原文。在田文镜巡抚和雍正皇帝的眼中,这个故事使人们“在最贫穷粗俗的百姓家庭里看到了最英勇无畏的道德情操,最完美的正直”(龚当信,2005:339),这种拾金不昧行为背后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道德情操,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无疑是一股清流,褒扬这种行为,激励更多的人向正面典型学习,对于扭转社会风气、移风易俗都能起到一定效果,同时也证明了在一个风气良好的社会里,即便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贫苦农民也同样可以在道德上受到教化,成为道德模范。因此,雍正皇帝对此激动不已也就不足为奇了。
将“还金”故事传播到欧洲的龚当信在1730年11月这封信中还提到,他此前寄回欧洲的关于中国治国之道的信件已经公开发表在1729年出版的《耶稣会通信集》第19卷中,受到读者欢迎。受此激励,他如今将包括“道德榜样”(exemples de vertu)在内的中国“命令、训令、条例”继续翻译出来,寄给杜赫德神父(Gobien,1736:190)。不言而喻,这封信能很快就在《耶稣会通信集》中出版,其原因也与《中华帝国全志》中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一样,是因为它“包含非常适合用于教化品行”的内容,并“教导人践行美德”。对欧洲读者而言,这个故事不仅证明了《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拾金不昧行为并非虚构,而且同样为欧洲人树立了“践行美德”的榜样,并迎合了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的文学化特征(韩水仙,2008:14)。因此,中国农民拾金不昧的故事同样具有超越文化界限的意义,即便在启蒙时代欧洲一样具有道德感召的力量,对引导欧洲社会风气也有积极意义。这正是龚当信、杜赫德神父青睐拾金不昧的故事的真正原因。
《一千零一日》中的“马尔迈尔还金”故事
1979年,贝鲁特知识出版社首次在阿拉伯语世界出版发行了波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日》。根据编者在前言中所述,这一版本以摩洛哥开旺大学收藏的阿拉伯文民间故事手抄本为基础,并参考了此前出版的法语版《一千零一日》(LesMilleetunJour),手稿上标明原作者为波斯僧正莫切里士(Moclés或Moklés,又译谟克莱)。该抄本最初为埃及学者所收藏,后来被赠予法国东方学家圣·卡罗(M. Sainte-Croix Ajpot),后者将手抄本整理并翻译成法文(克罗依克斯,1991:5)。这一说法在1844年法文版《一千零一日》序言中也得到证实,但1844年版序言中也指出,手抄本上标注的名字并非《一千零一日》,而是《一百零一夜》(Croix,1844:5)。
在阿拉伯语版《一千零一日》中,主人公在102至108日讲述了一个带有中国色彩的故事,即《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马尔迈尔与吕大郎一样来自中国无锡,妻子名叫雅斯敏。马尔迈尔家也同样有兄弟三人,老二名为雅古特,妻子名为奈尔吉斯,老三名为鲁禄,生性狡诈,并娶了一个同样品行不端的妻子黛拉尔。马尔迈尔由于独子萨法被人拐走,于是外出寻找多年。有一天,他在赶路时捡到了一条装着二百两银子的蓝色腰带,上面还绣有失主的名字。马尔迈尔进城后在一家客栈中找到了失主白德尔,就送还了钱袋,并拒绝了失主的酬谢。于是,白德尔请马尔迈尔到自己在扬州的家中做客,并与他结为兄弟。在得知马尔迈尔的儿子萨法在7年前被人拐走后,白德尔说自己几年前也收养了一个被拐骗的孩子,名字也叫萨法,于是叫孩子出来与马尔迈尔相认。虽然孩子容貌大变,也不记得自己从何而来,但他们还是通过孩子背上的一块胎记确认了他就是马尔迈尔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此后,白德尔还将自己12岁的女儿莎利娅许配给了萨法。在按当地习俗为两个孩子举行完婚礼后,马尔迈尔带着儿子儿媳乘船返回无锡,在路上碰到另一条船沉没,于是上前救人,结果发现被救者正是他的二弟雅古特。马尔迈尔询问家中情况,才得知他的三弟鲁禄因为赌输了钱,于是谎称哥哥病故他乡,想将大嫂雅斯敏卖给他的一个商人朋友抵债。得知消息后,马尔迈尔连忙往回赶。另一面,雅斯特偷听到鲁禄和妻子黛拉尔的阴谋,决定在商人上门来抢人之前自尽,但当她上吊时,绳子却断了。戴拉尔听到动静去查看,正好前来抢人的商人也在此时上门,由于按照当时的风俗女性见外人时必须遮掩面容,匆忙中黛拉尔将嫂子常戴的黑色面纱戴上,结果抢人者将她误认为黛拉尔抢走。第二天早上,鲁禄发现嫂子还在家中,才知道自己掉进了自己设计的圈套,居然把自己的妻子卖出去抵了赌债。羞愧之下,颜面扫地的鲁禄离家出走。而他刚一出门,马尔迈尔、雅古特、萨法、莎利娅一行人就回到了家中,全家人终于得以团圆。从此,“他们一家人过得和睦幸福”(《一千零一日》,1991:74)。
从情节上看,《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与《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几乎一模一样,连无锡、扬州等地名都没有变化,只是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被冠以阿拉伯世界中常见的名字。在角色设置方面,《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中老二老三扮演的角色虽然与《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正好相反,并增加了一位妻子的角色,但对故事发展没有任何影响。情节方面,马尔迈尔拾金不昧、在失主家中偶遇儿子、在路上救下弟弟,鲁禄设计盗卖嫂嫂却阴差阳错落入自己的圈套等环节都与《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如出一辙,只是失主的名字被改为白德尔,增加了几段对话,关于儿子萨法外貌和胎记的描写略微有所不同。而两个故事的结局也同样相去无几,都是好人一家团圆,坏人家毁人散。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阿拉伯版本中并没有《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开头结尾处劝人行善的诗歌,主人公丢失孩子和去外地经商的情节也都十分简略,去行户的情节更是没有出现。此外,在中国故事中,两位妯娌被抢亲者误认的原因在于主人公吕大郎的妻子王氏所戴的黑色发髻被弟媳在黑暗中误戴,而在《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中,这个拯救了大嫂的关键性饰品被置换成了阿拉伯妇女中常见的遮面黑纱。可见,阿拉伯文版《一千零一日》对吕大郎故事的核心情节完全没有改动,只是为了便于当地人民接受而在少数细节上进行了替换和增减。由此可以断定,《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应该是《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阿拉伯语改编本。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是如何进入阿拉伯语世界并成为波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日》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并未加以关注。但阿拉伯语《一千零一日》中的前言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我们知道,现存的波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日》与法国东方学密切相关。17世纪下半叶,当法国东方学家克罗依克斯(Francois Petis de la Croix, 1653-1713)在亚洲游历时,他在名城伊斯法罕偶遇了一位国王尊敬有加的高僧。通过结识这位知识渊博的波斯大僧正莫切里士,克罗依克斯得到了一部波斯民间故事集并将其翻译成法语(Croix, 1710: 3-4)。1710年,由克罗依克斯翻译、小说家勒萨日(Alain René Lesage,1668-1747)改写的波斯民间故事集正式出版。由于此前法国学者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1646-1715,又译迦兰)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刚刚引发了一股“东方热”(孟昭毅,2007:277-280),克罗依克斯将他带到法国的这部故事集定名为《一千零一日》。此书出版后很快风靡欧洲,被翻译成英语、德语等多种语言。但在18、19世纪,欧洲学者在翻译出版东方文学作品时有任意改编加工的风气,即便是赫赫有名的《一千零一夜》也难逃一劫。如《阿拉丁和神灯》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就被说成是《一千零一夜》的续篇,硬塞了进去,有的编者甚至干脆把《神灯》变成了第731至764夜的故事(郅溥浩,1997:299;葛铁鹰,2007:195)。同样,法文版《一千零一日》故事的来源也远比克罗依克斯所说的要复杂,可能来源于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多个地区(罗湉,2006:159),此外与中国也有一定渊源。
《一千零一日》中名气最大的故事当属后来被德国作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意大利剧作家戈齐(Carlo Gozzi, 1720-1806)、音乐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搬上舞台的《图兰朵》。在1710年的法文版中,该故事被命名为《卡拉夫王子和中国公主的故事》(第45-48日、60-82日),那位居住在北京的公主有一个波斯化的名字:图兰朵赫特,“图兰”来自古代波斯人对中国的地理认知,而故事中的卡拉夫王子则来自蒙古金帐汗国分裂后产生的一个小汗国——诺盖汗国,位于东欧。在早期的法语版《一千零一日》中,编者对卡拉夫王子为何要去中国几乎没有任何铺垫,只是有一天王子获得一套好装备后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看看伟大的中华帝国”,并预感自己会在那里“获得辉煌,赢得君王的友谊”。但在1844年问世的新版《一千零一日》中,卡拉夫王子则是在听朋友讲述了一个中国故事后,对中国“心驰神往”,这个故事就叫《吕玉的故事》(HistoiredeLiu-iu)。不过,笔者查阅1710年至1840年间的各个《一千零一日》版本都找不到这个中国故事,显然,它并非出自克罗依克斯之手,而是一百多年后的编者为加强故事集的东方情调并使故事与故事间的衔接更为合理才将其编入了1844年版的《一千零一日》。对比1735年版《中华帝国全志》中的《一个关于行善之举使家庭得以兴旺的故事》和1844年版《一千零一日》中的《吕玉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二者都同样译自《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甚至后者多半是抄自前者。二者在文字上仅有很小的区别,如吕氏三兄弟的名字拼写发生了细微变化,在1735年版中,吕玉的“玉”被直接音译,在1844年版中才被正确地翻译为玉石(jaspe)。此外,1844年版还为《吕玉的故事》配发了7幅富有中国情调的精美插图,这在整部书中都实属罕见。因此,《吕玉的故事》很可能只是1735年法译本基础上的一个修订本。这些新增的元素不仅符合那一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而且使图兰朵的故事更多地渲染上一层中国风韵。由于1979年阿拉伯语版《一千零一日》并非直接译自波斯语,而是参考了法语版《一千零一日》,因此《吕玉的故事》可能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阿拉伯语世界。
“还金”故事的中国文化基因和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从概览中不难发现,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作家对于中国知识的接受情况可能截然不同,其大致可以视为两类: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但文本本身书写的并非中国故事;而另一类文本的作者则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兴趣,创作了赋有典型中国哲学色彩的小说(张秋,2020:131)。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中国故事”是对中华民族这个多族群共同体的生活记录,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经验与情感,反映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除了文学意涵,还包含丰富的历史和政治意涵,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在世界文学中,由于中国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生动性、曲折性和生活性,各种中国故事被他国文学所征引、改编的案例并不少见,而侧重点各不相同。从类型学角度看,世界文学对中国故事的征引包括了从故事母题、内容题材、人物形象到表现手法、艺术技巧的多种类型。运用比较故事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对中国故事原型和被他国文学征引改塑的故事母题、情节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并就故事中的“中国基因”——中国文化因子进行考察解析,并将这种文化基因的海外传播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背景下进行阐释,以促进学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会通的研究。
从根本上讲,1735年通过《中华帝国全志》传入西方世界的《赵氏孤儿》《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等中国故事既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也体现着同时代欧洲人在“他者”视角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方面,其传播受到他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无论这些故事经历了怎样的改写,都在世界上传播着“中国声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这一思路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能在法语和阿拉伯语世界获得如此持久地传播值得深思,它的成功与故事中的中国优秀传统美德以及思想感染力密不可分,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是非爱憎与伦理道德,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故事中过多基于巧合的情节设置虽然远离了现实,但却不乏生活基础,因此,《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依然是一个以历史性、传奇性为特征的优秀传统故事。
在《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故事中,最核心的中国文化基因是“还金”,即“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曾流传下来众多歌颂拾金不昧的故事。早在1500年前,南北朝时期的范晔就曾在《后汉书·列女传》中留下一篇脍炙人口的《乐羊子妻》,其中写道:“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在《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吕玉在拾到装有二百两银子的钱袋后也是在第一时间想到中国古人的榜样:“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我……要这横财何用?”(抱瓮老人,2013:376)而《耶稣会通信集》中提到的贫苦农民翟世有在捡到钱袋后也没有据为己有,他的妻子也表示“情愿受穷也不愿意拿别人的钱”(龚当信,2005:335)。这几段故事一脉相承,体现出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其所达到的道德制高点使“还金”故事具有一种超越文化差异的感召力,这正是它打动欧洲和阿拉伯世界读者的力量之源。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另一重要文化基因是“善恶有报”的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在东西方都有广泛的民间基础,从印度佛经到西方《圣经》,从中国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到德国《格林童话》都不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前文已经提到,殷弘绪神父在翻译《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时相当完整地翻译了体现这一思想的题旨诗,可见其对此的看重。而在1736年的《耶稣会通信集》中,龚当信神父所翻译的褒奖拾金不昧行为的训令中同样写道:“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谋分文不义之财,理智就是他的尺度,他不做任何违心的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幸运到处跟随着他,他的子孙们也因此得福”(龚当信,2005:336)。而阿拉伯语的《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虽然在《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但是对于行善者得到好报、作恶者自作自受的情节也丝毫没有改动。
不过,《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善恶有报”故事还具有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基因——“天”的惩恶扬善角色,即吕大郎宣扬的“皇天报应,的然不爽”以及故事结尾处所写的“世间唯有天工巧,善恶分明不可欺”(抱瓮老人,2013:380)。早在西周初年,“天命观”就已在中国宗教生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后来成为儒家“敬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褚斌杰、章必功,1983:54-55)。由于耶稣会士在来华传教过程中采取“融儒”的传教路线,在“礼仪之争”中尽力调和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与儒家的“敬天”思想,受此影响,1735年的法语版《中华帝国全志》也尽力凸显中国对人格化的至高神明——“天”的崇拜,如《中华帝国全志》第2卷中选译的《诗经》中的《天作》《皇矣》等8篇都无不强调“天”在中国神明崇拜中的重要角色。同样,杜赫德将《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选入《中国帝国全志》,也有借此展现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敬天”思想的意味。例如上文中提到的两句在法译本中就分别被译为:“这一切都是天的特殊作用,导致了这些不同的事件”以及“天的行为是令人敬佩;它完全区分了好的与坏的:没有任何人能逃过它”(du Halde,1735:303)。值得注意的是,法语译者并没有用基督教中的“上帝”(Deus/God)一词来翻译此处的“天”,而是将其译成了大写的“Ciel”,即神灵化的“天”,展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天”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在1736年《耶稣会通信集》第22卷中,龚当信翻译的雍正皇帝训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你践踏了天律以后,难道你还相信能够逃脱它的怒火吗?天将不动声色地看着你,惩罚你”(龚当信,1736:337)。而阿拉伯语版的《商人马尔迈尔的故事》中虽然没有赞美“天”的诗句,但在文中同样也出现了“上天给你的赏赐”“天意难违”(《一千零一日》,1991:68,74),使阿拉伯世界的读者了解到“天”在中国宗教信仰的角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作为一个跨文化传播的“中国故事”,不仅以现实中国社会中形形色色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和传统价值观念为叙说中心,一方面其“中国基因”源自生活,具有较强现实性、通俗性与贴近生活的特点,更容易以特定的形式进入世界文学;另一方面其伦理性与说教性叙事特色虽然形成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特殊语境,但与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追求的社会公正、惩恶扬善的理想完全相通,并带有一定理想色彩,兼具娱乐性和教育性特色,因而更容易通过跨文化交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精神财富。
结 语
从《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海外传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拾金不昧、善恶有报和敬天思想是对故事的成功传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核心要素,而隐藏在这些成功要素背后的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因此,走进世界文学之林的“还金”故事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综合体现,它的成功离不开情节安排上的高超叙事技巧、人物设定上的鲜明品质,但归根结底还是得益于独具特色的道德教化诉求和传统文化色彩,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基因使“中国故事”更加具有世界意义,成功地走入了世界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