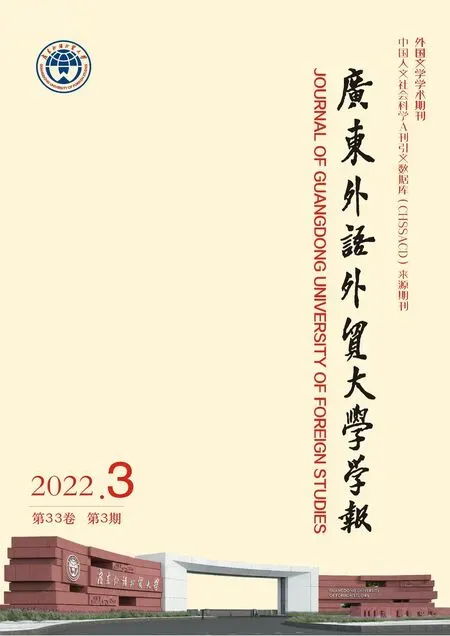“普通读者”与外国文学研究:殷企平教授访谈录
张琰 殷企平
“普通读者”话题的前情
张琰:殷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是国内最早对“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这一概念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2018年11月17日至18日,《外国文学》编辑部牵头的《西方文论关键词》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您做了题为“普通读者”的主旨发言,从文学批评中的“普通读者”传统出发,探讨当下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呼吁学界搭建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桥梁。您的发言引发了全场最为激烈的争论。当时有学者就您对文学批评去审美化、泛政治化现象的严厉指责表示不满。随后,您的论文《西方文论关键词:普通读者》刊载于《外国文学》2019年第6期,这成了学术圈内一次“黑天鹅”事件,引发不少国内学界同仁的反思。例如,但汉松教授就在最近出版的《文学之用》封面引用的推荐语以及《文学为什么重要》的中译版序中,将“普通读者”作为关键词,来介绍国外学者的基本观点①。周星月与王敖在近期引进出版的《看不见的倾听者》的译序中称,诗歌批评家文德勒(2019:3)想象的“看不见的倾听者”有两类,即诗人与“普通读者”。叶丽贤(2020:34)在《萨缪尔·约翰逊〈诗人传〉对英诗经典的建构》的绪论中,探讨了约翰逊笔下“普通读者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文学批评理论中,还是文学作品的经验性研究中,如今都出现了您所说的“普通读者的身影”。尽管存在偶然与巧合,但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普通读者”可被称为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词。
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您总能从社会问题出发,关照现实生活。如今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理论先行、批判先行的思维方式,然而,理论与读者本身的阅读体验没有多大联系,理论的专业术语往往在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之间设下障碍。以上问题,是否就是您文章中提到的“文学批评的异化”?(殷企平,2019:46)②您还提出,文学批评变异的根源在于“去经典化浪潮”(48)。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高歌猛进,文学系似乎也逐渐变为文化研究系。而您对审美的辩护,对经典的守护,让我想起了大洋彼岸捍卫正典的大批评家布鲁姆。您的《普通读者》一文,能否看作您对布鲁姆-詹姆逊之争的遥远回响?
殷企平:与其说我呼应了布鲁姆-詹姆逊之争,不如说我呼应了克莫德-卡勒之争,那场争论事关文学批评的宗旨。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文学批评的宗旨之一是为普通读者服务,这意味着批评家有义务就文学经典价值与普通读者达成共识;背离了这一宗旨,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异化,而异化的根源在于去经典化思潮(48)。这一思潮在过去几十年已经泛滥成灾,其背后有许多推手,但是最大的推手要数卡勒(Jonathan Culler)(45)。在他的诸多奇葩理论中,最有害的是主张文学批评应有“新型的研究对象”,即以晦涩为共同特点的文学文本,为此他推崇所谓“晦涩的长处”(the virtues of obscurity),同时又猛烈抨击所谓“奉清晰为圭臬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lucidity)(48-49)。换句话说,晦涩成了正道,而清晰则成了邪道。既然晦涩是正道,那么普通读者自然就被拒之门外了(49)。克莫德奋起反击卡勒,不仅仅是维护普通读者的正当权益,而且是捍卫文学批评的根本宗旨,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我。当然,卷入“普通读者之争”的远不止克莫德和卡勒,还有很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其中包括了您提到的布鲁姆和詹姆逊。关于布鲁姆-詹姆逊之争,我还未做深入研究,但是希望有人来研究,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青年学者。
“普通读者”的内涵与外延
张琰:首先我注意到,“普通读者”作为一种术语,出现在您与其他评论家的批评话语中,而未得到严格的界定。例如,布鲁姆(Harold Bloom)称自己对约翰逊的爱促使他离开学术论争,“转向颂扬我不断遇到的众多孤独的读者”(Bloom, 2000: 23);同时,他还在《西方正典》(TheWesternCanon, 1994)中指出,“约翰逊和他之后的伍尔夫称为‘普通读者’的人仍然存在着”(Bloom, 1994: 518)。这里的“普通读者”被视为一位“孤独的读者”,通过阅读来扩大自身的存在,从而获得一种崇高,一种世俗超越,以消减孤独。然而,这样浪漫的“普通读者”,显然与您文章引用的《正典与普通读者》(TheCanonandtheCommonReader, 1990)中那种具有民粹力量的“普通读者”全然不同。此外,布鲁姆本人大概会把该书的两位作者打入“憎恶学派”,理由是这两位把“普通读者”归入(在文学经典建构中)与文化精英对立的阶层,或是权力斗争中的“他者”——这类“他者”在不同时期表现为“约翰逊的普通读者、阿诺德的非利士人、美国贫民窟的黑人小孩,以及大批被剥夺权利的妇女”(Kaplan,etal., 1990: 11)。当然,《正典与普通读者》的那两位作者恐怕也会生气地大喊:“普通读者”应该是真实的生命,而不是神秘主义者的空想,更不该沦为一种修辞术,成为布鲁姆自白的传声筒。
殷企平:布鲁姆所说“孤独的读者”有多种含义。除了您刚才指出的“浪漫”色彩以外,他所说的“普通读者”之所以孤独,主要是因为讨论、评价文学经典/正典的正当途径越来越少,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理论已经不对非专业人士言说。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不以“晦涩”为耻,反以为荣。用克莫德(Frank Kermode)的话说,过去四五十年可以视作“文学理论全盛期”,而这恰恰意味着对文学本身的冷漠乃至敌视,或者说“理论正在淹没文学”(Kermode,1989:7)。面对这一潮流,重提“普通读者”,其意义在于恢复文学应有的地位,同时保持专业/职业批评家与普通读者的良性互动,促进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共同繁荣。正是在这一点上,布鲁姆与克莫德是并行不悖的。尽管他们所说的“普通读者”成分不尽相同,但是也不乏重合之处,至少他俩借“普通读者”话题发出了共同的心声,即反对任何“淹没文学”的理论。
张琰:关于“普通读者”的说法,您援引了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与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观点,但我发现,他们的观点也彼此冲突。伍尔夫称,普通读者不为传授知识,不为纠正他人观点,仅为愉悦自我而读书;但在约翰逊笔下,普通读者能够凭借出色的常识来决定诗人地位,光荣地参与公共领域的文学经典建构。关于“普通读者是谁”,这一问题在您那里仍然悬而未决。在您眼里,“普通读者”会是真实存在者吗?或许只是“理想读者”的语义反复?
殷企平:伍尔夫并非只把普通读者看作“为愉悦自我而读书”的群体,而是跟约翰逊一样,认为普通读者“在最终裁定诗坛荣耀方面有某种发言权”,而且“值得写下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理由是尽管这些思想和见解“本身微不足道,却能促成一种巨大的效果”(Woolf,2010:4)。关于“普通读者是谁”这一问题,您问得很好。在我看来,普通读者既可以是现实存在者,又可以是理想读者,但首先是现实存在者,他们是广大的受众。古今中外,都有志存高远却被挡在学府以外的“寒门学子”,就像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裘德那样——裘德尽管是艺术虚构的人物,却是千千万万受众的缩影。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不再“寒门”,但是能进入文学专业的读者总是少数。也就是说,不是文学专业却又热爱文学的读者总占多数,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普通读者。至于您所说的“理想读者”,无论是当年的约翰逊和伍尔夫,还是后来的克莫德,他们心目中的普通读者可能跟现实中的不完全相符,很可能会在品味、志向和毅力方面高出现实中的普通读者,但是理想总是基于现实的,而且对现实起着形塑或引领作用。换句话说,即便理想读者暂时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也会对现实中的普通读者起到感召作用,从而催生出新的、接近理想水平的读者。
张琰:在“普通读者”文化史的细察者中,有人称18世纪之前没有“普通读者”,只有“文雅的读者”,前者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建构,由作家、出版商、评论者、读者的交流配合构成(Engell, 1989: 160);但也有人说,“普通读者”指的不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而是新古典主义下具有普遍人性的人,或者说是批评者用来掩饰自己身份的一种方法(Wellek, 1955: 95)。当然,除了被虚构的那一类,还有被视为真实的“普通读者”。例如,有人相信“普通读者”有客观实指,但指的不是当时全体的书籍消费者,而是(伴随印刷品大量涌现而产生的新兴读者中)被约翰逊塑造的那种读者共同体,不过约翰逊本人并没有明确赋予该群体阶层、职业、教育等内涵(Kernan, 1989: 232)。此外,还有人认为,“普通读者”其实指代约翰逊本人的血肉之躯,以及他的“经验自我”(Damrosch, 1977: 41)。
然而,上述引发“多与一”“在场与缺席”之争的“普通读者”,被克莫德、伊格尔顿和哈特曼等理论家简约为“公众”这一建制性观念,并与“公共领域”等具有启蒙内涵的话语挂钩③,最终成为语用工具。可见,“普通读者”在给学者带来灵感的同时,也被时代赋能。例如,上述三位理论家就将“普通读者”这一概念移植到理论的时代,他们借助“普通读者”的前理论视角,审视批评制度的变化,反思“理论热”。然而,在对“普通读者”的呼唤中,这三位都偏好公众而非大众。换句话说,当专业读者占据了底层读者的发声立场时,前者却回避了后者的心声。例如,最讽刺是,当学院派利维斯哀叹“普通读者已死”④时,自称“平民”⑤的伍尔夫刚好完成了《普通读者》第二集。当您把“普通读者”阐发为文论关键词时,您会有什么顾虑吗?我的意思是,我们该如何关照那些沉默的底层读者呢?
殷企平:当今世界,“建构”理论盛行。在不少学者眼中,几乎天下万物都是由人脑建构出来的。阶级、性别、种族、主体/自我和客体/他者,统统都可以冠以“建构”之名。在某些学者的论述中,就连男女性别之分也因“建构”一说而被彻底“消解”了。当然,上述概念确实是建构出来的,但是它们能够完全脱离现实的物质基础而得以建构吗?显然不能。任何概念多多少少带有建构/虚构的成分,这一点不假,但是把“建构”论推向极致,否定任何概念的现实/物质基础,那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普通读者”这一概念也可以有不同的建构,可以有不同阶层、职业、教育背景等内涵,可以有约翰逊那样的血肉之躯,也可以是在利维斯所在时期“已经死去”的——因而也只是他理想中的——普通读者,还可以是“公众”/“公共领域”中的一员,当然更可以是您所说的“平民”“大众”或“底层读者”。所有这些内涵都可以因“建构者”而异,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以及因不同目的而被植入“普通读者”这一大概念,但是它们应该有一个最大公分母,即文学专业/职业之外的所有读者,而后者是客观存在的。我前面提到了裘德,他是哈代建构出来的,可是假如哈代身边没有成千上万普通读者,他就不可能建构出裘德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可以从狄更斯那里找到: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他所创作的《老古玩店》引起了无数普通劳动者浓厚的兴趣,他们纷纷给狄更斯写信:
写信者都居住在沼泽地带和密林深处的那些小木屋里。许多被斧头和铁锹磨炼得非常坚定的手,许多被夏日骄阳晒黑了的手,拿起了笔杆子,向我叙述一个个有关普通人家悲欢离合的小故事。(狄更斯,2015: 18)
狄更斯这里讲述的显然是您所说的“底层读者”,不过这些普通读者并没有沉默。倒是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不得不沉默了,这是因为在他们和文学作家之间隔着“理论家”。某些“理论家”把文学作品阐释得越来越晦涩,这自然会吓跑一大批受众,至少会让他们沉默。让我们再回到您提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关照那些沉默的底层读者呢?最好的关照就是还他们应有的地位。重塑普通读者(包括底层读者),重申他们在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维护他们对于经典化的参与权,承认他们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这既是对他们的关照,也是对我们自己(专业读者)的关照,是对文学/文学批评性质的关照。
“普通读者”与共同体
张琰:您将普通读者纳入共同体研究,这让我想到您文中提到的、意图将公共生活与私人创造结合起来的罗蒂(Richard Rorty)。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Irony,andSolidarity, 1990)中提出,小说能促使读者想象他人的痛苦,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加强各个时代读者的“协同性”。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功能不在于解释意图或评估价值,而在于梳理脉络、建立人物关系,他所垂青的批评家有阿诺德、佩特、利维斯、艾略特、克莫德以及美国的威尔逊、特里林和布鲁姆(Rorty, 1989: 80)。其中,利维斯以《细察》(Security)为阵地,塑造了一批有“共同追求”的学生读者团体(Leavis, 1956: 105);特里林通过散文、书评培养了一群美国中产阶级读者,“这些散文构成了一种理想的亲密的共同体”(West, 1989: 170)。在我看来,您与罗蒂也十分相似:你们都捍卫文学经典,回避意识形态行话,欣赏具有对话意识的批评家,重视文化实践。简而言之,你们的核心诉求都是发展文学文化,防止让科学文化、哲学文化占绝对优势。
殷企平:我很高兴您捕捉到了我那篇文章的潜台词之一,即普通读者应该纳入共同体研究,或者说共同体研究离不开对普通读者的关注。我欣赏罗蒂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的创造性活动结合起来的主张,但是我不同意文学批评的功能“不在于评估价值”这样的说法。文学之所以重要,文学批评之所以重要,多半是因为文学阅读能帮助人类甄别价值,从事价值判断。共同体需要共同的价值观来维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普通读者大有可为。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没有他们的文化实践(文学作品的阅读、鉴别和讨论就是一种文化实践),共同体的价值纽带就难以形成,形成了也会消失。我赞同您把罗蒂放在由阿诺德、利维斯、艾略特、克莫德和特里林等人形成的传统中加以审视。作为中国学人,我们有必要借鉴他们在建设阅读共同体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个使命,即超越他们。我们要构建的阅读共同体,不能局限于利维斯所塑造的学生读者团体,也不能局限于特里林所培养的中产阶级读者,而是服务于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阅读共同体。另外,我还要就您所说的“文学文化”“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多说几句。把“文化”这样细分的做法多见于西方,我更喜欢中国文化中“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当然,这一传统多多少少受到了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我们在这里谈论普通读者,应该考虑到随着教育的普及及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如今现实生活中有文化诉求的人不仅会阅读文学作品,而且会尽可能地阅读其他学科/专业的书籍。也就是说,如今普通读者在挑选读物时,变得越来越具有跨学科视野,他们的文学知识往往跟其他学科的知识相互交融。这又把我们带回到您刚才所说的“科学文化”:真的有纯粹的“科学文化”吗?我不禁想起了19世纪英国科学家兼教育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诗人兼教育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之间关于“文化”的争论,后者可以看作20世纪利维斯(F. R. Leavis)和斯诺(C. P. Snow)关于“两种文化”之争的先声。赫胥黎通常被视为科技教育的倡导者,但是他在批判所谓“人文主义者”拘泥于古典教育的同时,还提出了如下著名观点:科学技术是整个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时,并不贬低文科教育的作用。他说:
我比任何人都深信真正的文科教育的重要性……单一的科技培训只会扭曲人的心智,就像单一的文科训练一样。如果一艘货船的形状十分难看,它装的货物即使再有价值也弥补不了它的丑陋。如果我们的理工学院造就出来的尽是一些畸形的人才,那会使我十分遗憾……(Huxley, 1898: 153-154)
赫胥黎还呼应过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提出了“哲学即科学”的主张:“哲学和科学……是全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⑥。 我引用赫胥黎的话,是想说明科学是不能单独成为文化的,因而也是无法跟文学截然分开的,而普通读者往往会穿梭于两者之间,这是我们建构阅读共同体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琰:您没有遵循“普通读者是谁”这一本质主义的思考方式,而是提供叙事和形象,从而不断塑造多文化的、跨国的读者社群;您还试图重新描述一种以约翰逊、伍尔夫、克莫德为代表的、具有读者共同体意识的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由此重申人文主义的立场。例如,您提到,伍尔夫建议读者不要听从什么指点,要独立判断(46)。这听上去有些独断,但她绝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意思;相反,伍尔夫比学院派批评家更擅长倾听,她经常通过做比较,接受不同观点,考虑它们的复杂性,然后做出经验判断,而非纯理性批判;在此过程中,她还习惯称呼她的读者为“我们”。这种“倾听的共同体”与费什的“阐释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照,即以普通读者群为一方,以专业读者群为另一方。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只能在学科之外的文化荒野中相遇。以上观点,您同意吗?另外,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普通读者与共同体的关系,这与您研究过的文化观念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殷企平: 恕我不敢苟同“文化荒野”这样的说法。学科之内就一定没有荒芜之地吗?学科之外就一定是文化荒野吗?不过,您确实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要看我们如何界定“文化”一词。根据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考证,“文化”一词如今有三种常见的用法:1)用来形容思想、精神和审美演变的总体过程;2)表示一个群体、一个时期、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3)指涉思想艺术领域的实践和成果(Williams, 1893: 87-90)。这三种定义无一把“文化”局限于学科之内,第二种定义尤其如此——如果“文化”指人类社会的总体生活方式,那么它远远超出了学科的范围。也就是说,在学科之外,文化可谓“芳草碧连天”。说得更明白一点,对普通读者来说,天涯何处不(文化)芳草?专业读者若把这碧连天的芳草关在学科高墙之外,那就只能陷入孤芳自赏的局面。在此,我还想进一步引用威廉斯的观点,他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Society, 1958)一书中说道:
文化一词的演变记录了人们对历史性变化的反应,即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做出的重要而持续的反应。该词的演变本身好比一种特殊的地图,从中我们可以探索那些变化的性质。(Williams, 1958: xvi-xvii)
威廉斯这里所说的重大历史性变化,指的是社会转型,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正是这一转型,造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乃至总体生活方式的空前变化,而这一转型带来的焦虑,是我们所说“文化”观念的最主要内涵。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普通读者/共同体与我研究过的文化观念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联系可大了!2012年以来,我有幸跟国内40来位学者一起,从事一项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研究,题目是“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最终成果已经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6卷本丛书的形式出版)。在这套丛书中,我们用了10个关键词来勾勒文化观念的主要内涵,分别是“转型焦虑”“愿景描述”“共同体形塑”“秩序诉求”“审美趣味”“心智培育”“文学语言的创造”“民族良心”“道德伦理传统”和“工作/生活方式”。这些关键词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对于社会转型的焦虑意味着人类的工作/生活方式(因转型)出了问题,或者说“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伦理道德败坏)。既然“文化”由“转型焦虑”而生,那它就必须提供走出焦虑的途径,如描述各种愿景,包括共同体愿景、乌托邦愿景,或者关于美好社会秩序的愿景,而后者的实现离不开心智的培育、民族良心的锻造和民族特性的构建,以及提倡理想的工作/生活方式,等等。不妨对“共同体”做这样的归纳:它是一种人类生存和相处的结合机制,主要由血缘、地缘、精神或利益关系构成。“共同体”本身极具复杂性、矛盾性,它和历史上各种思潮进行着复杂互动,这是它的迷人之处,考验着人们的经验、智慧、思辨能力和批评意识,这也是它成为历代英国作家文学想象的重要客体的原因之一(姜仁凤、李维屏,2021:6)。我们在那套丛书里所要证明的观点之一就是:英国文学家们在拓展上述文化观念内涵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承认,我们在丛书中没有直接用“普通读者”一词,但是每一卷都有不少篇幅讨论“共同体形塑”话题,其中多多少少隐含了普通读者的作用。例如,由杭州师范大学欧荣教授牵头的第6卷中提到,利维斯对“共同体”的想象体现为“少数人”与“心智成熟的民众”之间的创造性合作(欧荣,等,2021:8)。这里,“心智成熟的民众”就是普通读者。利维斯的“少数人文化”常常遭到误解,其实他只是想解决“大众文明”时代的“文化困境”,并且十分清楚光靠“少数人”的突围是不够的,只有得到“心智成熟的民众”的回应和支持,文化传承才有希望,为此他提出了“共同语言”(Leavis, 1956: 109)一说。普通读者当然也是这“共同语言”的使用者。
张琰:我还注意到,您和您的同事们不仅在理论层面讨论“普通读者”的重要性,不仅视其为一种文化实践,而且身体力行。在您的带领下,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创办了外国文学经典读书会——敦雅书社。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敦雅书社的经典阅读、“普通读者”等系列活动?
殷企平:“敦雅书社”是浙江省社科联下属“阅读联盟”的集体会员之一,旨在推进全民阅读,以期在作品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天然而健康的关系。书社开展的活动大致有三类:1)经典作品分享会,每月一次,每次安排一位专业读者做读书报告,而对象既包括专业读者,又包括普通读者;2)经典作品进校园,可以进高校,也可以进中学和小学,以期待培养不同层次的普通读者;3)经典作品进公共图书馆,如浙江省图书馆等。2020年6月10日,我们书社“普通读者”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并邀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陈众议研究员以腾讯会议形式作了题为“时代的需要与文学的问题”的开幕讲座。2020年11月1日晚,我们还把读书活动移到杭州宝石山上的纯真年代书吧,与诗刊《诗建设》、浙江图书馆文澜朗诵团共同举办了2020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诗歌双语品读会。这类线上线下的读书活动已经得到不少普通读者的热烈响应。如您所说,我们从事的是一种文化实践,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话语实践。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中国北宋文学家苏洵在《管仲论》中的一句话:“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我们不妨试问:“建造共同体之功”成于何时呢?我想这样作答:成于文学/话语介入之日,成于普通读者热烈参与之时。
张琰:殷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期待您更多学术成果问世!
注释:
① 关于外国学者对“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良性互动”的主张,参见:菲尔斯基.2019.文学之用 [M].刘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9;伊戈尔斯通.2020.文学为什么重要 [M].修佳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6。
② 下文凡引自殷企平.2019.西方文论关键词:普通读者 [J].外国文学(6),只标注页码。
③ 关于将“普通读者”化约为“公众”的观点, 参见:Kermode F.1989.An Appetite for Poetry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9;Eagleton T.2005.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M].London:Verso:9;Hartman G H.1991.Minor Prophecies: The Literary Essay in the Culture Wars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5-16。
④ 关于“普通读者的传统已死”的观点, 详见:Leavis F R.1932.How to Teach Reading: A Primer for Ezra Pound [M].Cambridge:G. Fraser, The Minority Press:4。
⑤ 关于伍尔夫自称“平民”的观点, 详见:Woolf V.1947.“The Leaning Tower” [C]∥The Moment and Other Essays. Woolf L (ed.). London:Hogarth Press:125;关于《普通读者》第二集的出版时间,参见:Woolf V.1932.The Common Reader-Second Series [M].London:Hogarth Press。
⑥详见:殷企平.1995.英国高等科技教育 [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