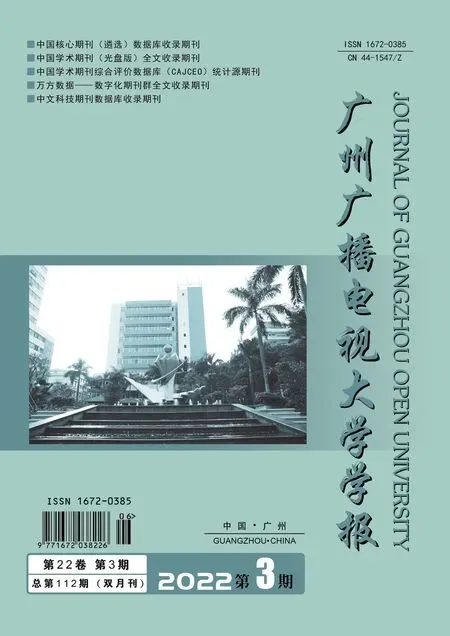“灯下漫笔”:《呐喊》《彷徨》中的“灯”意象研究
张佳滢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曾指出鲁迅在文艺上是个“诗人”,“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更是的”[1],而作为“诗人”的鲁迅用以“把握具体事物”的途径之一便是对意象的出色使用。正是因此,对于鲁迅作品的意象研究始终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学术话题,如专著《鲁迅小说意象主题论》(隋清娥,2007)就对鲁迅小说中的“吃人”、“路”、“铁屋子”、“人血馒头(药)”、“辫子”和“剑-头”等六大意象进行了主题式考察[2],而鲁迅笔下的“鬼”(或“女吊”)、“疯癫”、“村庄”、“黑暗”、“鲁镇”、“动物”和“伤痕”等多种意象亦已为学界所关注,整体来看,对鲁迅作品的意象研究呈现出较为成熟、完善的态势。但仍有一个异质性现象为学界所忽视:在《呐喊》《彷徨》收录的25 篇小说中,有13 篇①反复出现了“灯”这一意象,而这些灯的意象,或是温馨,或是暗淡,或是诡谲,但大体而言可以分为:“苦难之灯”、“守旧之灯”与“家庭之灯”三类。在鲁迅的文本中,对于“灯”意象的书写不仅展现出了他对于象征主义艺术手法的出色应用,更反映出鲁迅进行创作时的“沉思者”姿态与文本中潜藏着的现代性隐喻。因此,研究与探讨《呐喊》《彷徨》中的“灯”意象具备了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苦难之灯”:与“病”相联,照亮现实
鲁迅曾言:“……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而在《呐喊》《彷徨》之中,“灯”意象的无遮挡的光明便成为“揭出病苦”的手段,照亮现实的“苦难之灯”展露了鲁迅对底层人民深切的同情与幽隐的人道主义关切。在《药》、《明天》、《白光》和《弟兄》四篇小说中,“灯”意象的出现,往往与“病”相联系,暗中昭示着新旧交替时代底层庶民的苦难命运,在这些文本中,主人公面临的,或是极其困顿的生活之苦,或是足以摧毁精神世界的精神之苦,而这种“苦”原本是微隐的,是幽暗地蛰伏在生活之中的,却被无情的“灯”照亮了,变得一时间无比清晰地横亘在人生道路之中了,由此引发了无限的恐惧、无穷的悲伤,“苦难之灯”由此成为了迈向现实的通路,成为鲁迅“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方法。而同时,“苦难之灯”的意象从《呐喊》到《彷徨》发生了明显的滑变,而这实际上揭示了鲁迅从《呐喊》到《彷徨》的写作对象、写作内容的变化与内在精神的嬗变,是“灯”意象之现代性隐喻的展露。
在《药》中,“灯”与小栓的肺病共同出现,照亮的是华家因孩子的疾痛而陷入的贫困苦难。《药》甫一开篇,便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的情境,而在这情境之中,“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4]这盏点上了的昏暗灯盏,却照亮了“茶馆的两间屋子”,使其“弥满了青白的光”。一个昏暗而油腻的灯盏能够“弥满”的两间屋子,无疑是极小的,但这却是华老栓一家三口夜间的栖身之所、白天的营业场所,足以见其生活之困苦;而这“油腻的灯盏”与“青白的光”又使得《药》一开篇,便带着一丝不祥的色彩,在破旧的茶馆陈设中,读者洞见了属于华老栓一家的庶民之苦。然而,当华大妈艰难地摸出家中的最后一点积蓄后,就连这油腻、昏暗、不祥的灯盏也很快熄灭了,老栓点上了灯笼,而在这更加幽晦的灯光中,只余下小栓的咳嗽声。在《药》开篇的这个场景中,寥寥数行,“灯”便照亮了老栓一家捉襟见肘的现实环境,隐喻着小栓的肺病给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庶民之家带来的深重的生活之苦,熄灭了灯的老栓看似是提着灯笼走出了这个苦难的家,去求一条小栓的生路,他的心中也感到了些许的轻松,但家中的苦难就如那熄灭的灯盏一样,隐没在黑暗中,却未尝真正消失。唐弢认为,“在鲁迅的小说里,他所捕捉和描写的生活细节总是真实的,常见的”,在他看来,这正是鲁迅小说创作现实主义风格的典型表现[5]。正是因此,在《药》中,“灯”意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鲁迅的独具匠心之处,通过一盏灯的狭窄视阈,勾勒出了一个充满贫苦、疾痛的现实空间,这指向了华家在文本中的二重身份——他们因愚昧、迷信乃至于“吃人”而成为鲁迅批判与“怒其不争”的对象,但同样也是鲁迅报以深刻关怀的苦难庶民,正如李欧梵所认为的那样,鲁迅有着两种“斗争着的冲动”:一种是“公众的训诫主义”,一种是“个人的抒情”[6]。当鲁迅以带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的冷峻之笔书写小栓不可避免的死亡时,“公众的训诫主义”强烈地讥讽着蒙昧迷惘的华家,但当他细细描摹这个“破败之家”的“苦难之灯”这一现实主义的文本细节时,展露出的是“怒其不争”的讽刺背后“哀其不幸”的人道主义“个人抒情”。
而在《明天》中,“灯”同样与“病”同在着,照亮了单四嫂子痛失爱子之苦难。《明天》的开篇,“黑沉沉的灯光下”,单四嫂子为自己患病的宝儿踱步、心碎,焦虑而又自欺欺人,而这灯光照亮了宝儿的脸——“绯红里带一点青”,显然已经有了将死的预兆,“苦难之灯”又一次照亮了乡镇贫民的悲剧性时刻。而在痛失爱子后,“灯”这一意象再度出现——当单四嫂子“点上灯火”,灯火下的屋子清晰无比,充斥着空旷与死寂,正如宝儿逝去的现实般真实而贫瘠,痛苦继而化为某种具象的感受——“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他现在知道他的宝儿确乎死了;不愿意见这屋子,吹熄了灯,躺着。”[7]在“灯”的一点与一熄之间,单四嫂子无力面对“灯”照亮的苦难现实,最终选择了和《药》中的老栓一样熄灭了灯,等待虚幻的“梦”、虚幻的“明天”。但熄灭的灯下暗藏的悲惨现实仍旧没有改变,“熄灭的灯”就像刻意被回避的苦难一样。“灯”总会再度亮起,就仿佛象征着这种庶民之苦难是无法回避的、永恒真实存在于底层人民生活之中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及鲁镇“有古风”而早早熄灯,故而在深夜中最晚熄灯的只有丧子的单四嫂子家和热闹的咸亨酒店,而这一悲一喜、一静一闹、一空一挤的两个并置的“亮灯”的空间展现出庶民苦难的深刻悲剧质地,在李欧梵看来,“单四嫂子的不幸实际上已把她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了,并没有人真正关心她”[8],确乎如此,在《明天》这个文本中,“灯”是那样清晰地照亮苦难,又在“明亮”空间的对比中确证、深化了这种苦难。如果正如李氏所说,单四嫂子是一个“由于某种情况被置于舞台中心”的“庸众之一员”,那么“苦难之灯”在这个“舞台”中的作用便是“聚光”,它使得悲剧越发鲜明,而痛苦更加锋利。
在《白光》中,“灯”则与屡试不第的陈士成的癔症联系在了一起,照亮了无法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给读书人带来的精神苦难。当陈士成又一次没在县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幻梦再次破灭,他感觉自己的身躯已经“涣散”,只是“懵懵的走向归家的路”,凋零的家境、不被承认的个人价值将屡试不第带来的精神困境无限扩大化,最终使得陈士成陷入了疯狂,满心只想找到传说中深埋的巨额祖产。当他陷入幻想的狂乱中时,“张惶的点了灯”,然而这盏被寄予了厚望的“灯”最终却只照亮了地下死尸的烂骨头与烂牙齿,这灯光下的贫瘠的现实使得陈士成更加疯癫,几近“癔症”,又觉得辉煌的灯火照亮的下巴骨“异乎寻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边看”。在疯狂出奔的陈士成背后,留下的依然是灯照亮的现实——
“灯火结了大灯花照着空屋和坑洞,毕毕剥剥的炸了几声之后,便渐渐的缩小以至于无有,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9]
“灯”再一次熄灭,而这一次,陈士成的个人生命也毁灭了。《白光》中的“灯”照亮的正是旧式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难,与“灯”一道出现的癔症具有福柯所谓“超越于想像,而又根植于想像”的特性[10],它呈现出的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知识被无限功利化的图景:陈士成之流的知识分子把个人的“成功”归咎于两条道路——要么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要么通过祖产成为一方豪富,只有这样,其个人的尊严才会得到尊重。苏珊·桑塔格认为,在“现代的文本”中,疾病往往被用作一种“隐喻”,反映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失调”,并以之指责“社会的压抑”[11],而陈士成的癔症所欲传递的正是一种“疾病的隐喻”,当“苦难之灯”照亮了贫瘠如死人下巴骨般的现实时,陷入疯癫几乎成了这些落魄知识分子的必然命运,他们的悲剧性命运背后隐含着封建社会的结构性压抑。
在《弟兄》中,“灯”则与弟弟靖甫的疹子联系了起来,灯映照着城市普通市民阶层亲情与物质的双重苦难。哥哥沛君与弟弟靖甫本是关系极融洽的亲兄弟,也共同维持着家中生计,但靖甫疑似“猩红热”的病症则打破了这种兄友弟恭的幻象:
“他走进房去点起灯来看,靖甫的脸更觉得通红了,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眼睑也浮肿起来。”[12]
灯光下弟弟的病症使得沛君思量起了弟弟死后自己的花销将加倍增长,想到不可能让自己和兄弟的孩子都上学,想到弟弟棺木的花销……这种暴露在灯光照耀的现实中的,是兄弟之间虚伪的和谐情谊和城市之中庶民的生存压力。当面临危机,亲情瞬间被生活中现实性的利益取代,当弟弟的病痛在“灯”下展现,沛君的虚伪也在“灯”下无所遁形,“灯”隐喻着亲情与生计的双重苦难。
二、守旧之灯:封建的势力与教条的象征
鲁迅的作品对于“象征”手法的广泛而纯熟运用俨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如孙玉石就较早地注意到了“鲁迅如何接受外来象征艺术思潮的影响,以《野草》写梦及其他情境为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中开辟了象征主义文学传统的先河”[13],唐弢亦曾提及鲁迅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中运用了一些“浪漫主义的甚至是象征的手法”[14],李欧梵更是指出,在鲁迅的现实主义技巧中,存在着一种纯粹的“象征叙述”,“在这种叙述结构中,‘现实’故事的因素只有和较高层次的象征寓意结合起来读才有意义。”[15]然而前辈学者未曾关注到的是《呐喊》《彷徨》中象征着封建教条的“灯”意象,这一意象将鲁迅小说的象征手法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长明灯》、《祝福》、《阿Q 正传》和《风波》里,“灯”都作为旧规矩、旧教条的直接象征物存在着,成为了鲁迅政治寓言的一个奇特中心。
《长明灯》是“守旧之灯”意象最具象征意义的寓言。该小说被李欧梵认为可以归入纯粹的“象征叙述”,全文围绕着一盏“长明灯”展开,这盏号称是从“梁武帝时就点着了的”长明灯是小说中“吉光屯”的象征,但其“绿莹莹”的颜色与其说是“吉光”,倒更容易令人想到恐怖的鬼火。当青年想要熄灭这灯时,四面八方的封建守旧势力闻风而动,斥他“胡闹”“不肖子孙”“疯”,这灯照着“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照着一切顽固、丑恶、封建、迷信的力量。而文中想要熄灭灯的父与子仿佛正是被启蒙的、革命的“超人”的象征,是“狂人”的进化,“狂人”窥见了封建势力的本质,只感到畏惧与惊惶,惊惶过后,又再次融入了“吃人”的封建秩序之中;而这对执着于熄灯的父与子则是真正想要摧毁封建力量的人,当父亲被哄骗着失去了熄灯的机会与勇气,儿子却接着踏上了熄灯的道路。吉光屯的群氓们想要保卫这盏灯,因为这盏灯象征着对于传统宗法制(祖宗捐钱建立的长明灯庙)、帝制(梁武帝点的)、封建迷信(熄灭了吉光屯会变成海、人们会得瘟疫)的因循守旧力量的病态崇拜,也是因此,他们极力哄骗、绞杀、毁灭、禁锢着革新的力量,被哄骗的父亲、被关起来的儿子都是最先觉醒的时代“超人”,他们个体的力量太过薄弱,因而轻而易举地被守旧的力量给毁灭了。但这盏“守旧之灯”还能点多久呢?鲁迅终究是在“还没吃过人的孩子”的歌谣里留下了一丝微渺的希望——“此刻熄,自己熄。/戏文唱一出。/我放火,哈哈哈!”[16]青年逝去了,孩子就是熄灭守旧之灯的时代重任的继承人,《长明灯》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充斥着象征色彩的寓言,而寄寓着封建信仰与道德的“长明灯”意象则成为了全文本象征体系的中心,指涉出鲁迅小说文本里“灯”意象的丰富意涵。
而在《祝福》当中,鲁镇的灯光同样是旧教条的象征,当鲁镇的人们在灯下“祝福”时,被侮辱、被损害的祥林嫂只能在黑暗和凄冷中死去。《祝福》中的灯光是暖色调的,看似渲染了一派温馨的环境景象:时逢年节,夜色深沉,“人们都在灯下匆忙”,窗外寂然无声,连雪花落地之声都清晰可闻,爆竹声中鲁镇又迎来了喜庆的时节——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17]
在这静谧、温和、宁静而又欢喜的灯光里,被人们遗弃的“消遣之物”——“百无聊赖的祥林嫂”终于彻底如草芥般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人世。暖色的“守旧之灯”笼罩着落雪的鲁镇,但灯光不属于“纯乎一个乞丐似的”祥林嫂,而为那些“吃了人”的人“淡然”地独享着。这灯象征着那股毁灭祥林嫂,使得她惨死的巨大的“恶”的封建守旧力量,象征着压迫人的旧教条与旧规矩,代表着李长之所说的那种“咀嚼着弱者的骨髓”的“哄笑与奚落”[18]的总的集合,辉煌的“祝福”时节的灯火照亮一切愚妄者的面目,在祥林嫂死去的这段情节中,“灯”的象征意义跃然于纸面,它不是《长明灯》中那般显见的“鬼火”,相反的,它用它有限的、狭窄的温馨光芒勾勒出了两个世界的图景,以它的温暖反衬祥林嫂冰冷绝望的死,它是“守旧之灯”最模糊也最具讽刺意味的展现,在文本的间隙中沉默闪耀着,见证着一个底层妇人被封建教条迫害以至于最终走向死亡的一生。
在《阿Q 正传》里,“灯”背后的规则意味着一种无声的权威,“点灯权”成为了一种封建统治的外化象征:
“但赵府上晚饭早,虽说定例不准掌灯,一吃完便睡觉,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 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因为这一条例外,所以阿Q 在动手舂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19]
在赵府的规定下,“灯”是被赵太爷掌控的、具有威权意味的对象,正如巨大的封建势力所规定的旧教条一样,每个人都是这种教条制约下的无能力者,但蒙昧的庸众们也并不希望反抗赵太爷的权威,反而为他的“破例开恩”感恩戴德、倍感荣耀。而能让他“破例开恩”者,唯有如赵大爷一样恭顺的读书人,或如阿Q 这样一时能为自己服务的庶民。而除了上述两条“点灯”的特例规矩,赵府的第三条“破例点灯”规矩同样与阿Q 有关:在赵府的饭桌上,赵家商讨之下认定了阿Q 的“古怪”,认为自己应当小心门窗,对阿Q 的行事充满着不屑,但又对阿Q“价廉物美”的“好东西”产生贪念,“于是家族决议,便托邹七嫂即刻去寻阿Q,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从这第三种破例点灯的情境里,又可以看出:封建旧教条就像赵太爷点灯与否的旧规矩,全然掌控在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手里,是对庶民的单向度束缚,这种旧道德、旧思想是那样独断和专横,乃至成为了统治者一己私欲的遮羞布,当他有私心、有诉求时,一切教条都可以被任意打破和解读。
在《风波》里,这“灯”的意象则与七斤家的旧规矩联系在了一起。作为村中“出场人物”的七斤,仍旧必须严守“夏天吃饭不点灯”的教条,尽早回家,否则就会挨骂。夏天吃饭不点灯是七斤所在村庄“农家的规矩”,纵使每天“太阳收尽了他最末的光线”时,“土场上一片碗筷声”,人们都得摸着黑吃饭,也未尝有人提出质疑,毕竟正如九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20],在村里人看来,昔必胜今,合理不合理倒是其次,重要的是这毕竟是祖上的规矩。“农民在经济上的被剥削,在精神上、意志上、人格上,也同样被剥削,农民已经失掉了自己”[21],对“点灯”的合理化举措的漠然、对黑暗的麻木与服从使得“灯”在《风波》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地位与意义,“守旧之灯”未曾在现实中点亮,但却早已在农民木然的心灵中高悬着,它的光芒渗透到了方方面面,仿佛是那位在文本中隐而不出的“皇帝”的代言物。“奴性和愚蠢,造成了农民特有的精神上的伤疤”[22],“守旧之灯”正是《呐喊》《彷徨》中农民“精神奴役创伤”最鲜明的象征物。
三、家庭之灯:影射家庭关系,映照俗世纷扰
在《呐喊》《彷徨》中,“灯”意象也常常作为家庭关系的影射而存在,温馨明亮的灯盏往往代表着稳固的家庭结构,凄枯倒斜的灯则影射家庭的崩裂、夫妇的纠葛与矛盾,这在《肥皂》、《孤独者》和《伤逝》等篇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在《肥皂》当中,“灯”是家庭布景中的“重头戏”,实际上隐晦地昭示了四铭一家的家庭结构。首先,“灯光”是四铭一家晚餐时节的象征,作为一种“号召晚餐的烽火”,带有不言自明的指令性,而“中央的桌子”在空间位置上的中心地位昭示了其在家庭关系中作为一个重要场域的存在,而四铭一家就餐时的相对位置则是一种对于家庭关系的隐喻:
“灯在下横;上首是四铭一人居中,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圆脸,但多两撇细胡子,在菜汤的热气里,独据一面,很像庙里的财神。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右横是学程和秀儿一列。”[23]
一家人加上一横灯,构成了一个稳定完满的四边形,就如四铭一家的稳定形态一样,指涉着俗世家庭的平稳与安宁,身处这个稳定结构之中。而当四铭与太太为了肥皂与孝女的问题爆发了争端时:
“最后在离灯最远的阴影里的高背椅子上发见了四太太,灯光照处,见她死板板的脸上并不显出什么喜怒,眼睛也并不看着什么东西。”[24]
当四太太远离了稳固温馨的“家庭之灯”,而坐在阴影中时,家庭争端便开始了,此时的灯光微微照亮着的,是四太太近乎阴森的面容,表征着四铭一家家庭矛盾的酝酿。当家庭争端在无声中爆发,四铭看到“堂屋里的灯移到卧室里去了”[25],而他一个人怀着忧伤独步在院子中,再也看不到灯光,只看得到月光。夏志清认为,“就写作技巧而言”,《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展露出了敏锐的讽刺感[26],而在笔者看来,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灯”意象所展露出的家庭关系的微妙变化,无疑在细节上加强了小说的讽刺意味,通过细化描写一场家庭矛盾的始末,鲁迅揭露出了四铭这类满口仁义道德的道学先生的虚伪面孔。
在《孤独者》中,“灯”则指涉了魏连殳在祖母去世、亲族争产中彻底失去家庭、陷入孤独的苦难境遇。起初,魏连殳“一面点灯”,一面讲起他祖母的事;父亲去世,家庭败落,祖母靠针线活艰难养活一家人,此时“灯火销沉”;而讲到祖母艰难维持家计,好不容易等到魏连殳可以赚钱,却又一命呜呼时,魏连殳沉默了,而刚刚添过煤油的灯竟然再一次“微微颤抖”。这盏灯伴着孤独者魏连殳讲述他的家庭是如何由凋敝到四分五裂,乃至于彻底地毁灭的,是魏连殳家庭关系破裂的倾覆破裂的标志;而在魏连殳孤独生活乃至死亡以后,“我四顾,客厅里暗沉沉的,大约只有一盏灯”[27],这盏灯是孤独无家的魏连殳最后的陪伴,而暗沉沉的、只有一盏灯的“家”无疑意蕴着魏连殳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孤独乃至于消亡的结局。竹内好十分重视《孤独者》这篇小说,他认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乃至收录于《朝花夕拾》的《范爱农》中的“范爱农”)都几乎是“同一个人物”,并且在他看来,这几篇文章所描写的人物是“和作者极为接近的一个人”[28],而这个极度孤独的“人格的创造”,或者说是作者的自我抒写,在很大程度上由“灯”意象映衬而来,“家庭之灯”的凋敝与倾覆暗示着魏连殳作为一个绝对的“独异个人”的形成,也影射着鲁迅写作《彷徨》时所面对的《新青年》团体分化,自身“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而“新的战友在那里”尚未可知的孤独无依的心理境况。
在《伤逝》里,“灯”则伴随着涓生和子君的小家庭由建立到衰败的全过程。在涓生回忆起请求子君与其同居时,他感到这回忆“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这是两人建立关系的伊始,此时的回忆是那样明亮幸福,宛若暗室孤灯一样照亮涓生的心灵;而当两人真正住到了一起时,“冲突和意思的误会”消失了,只余下了看似和谐实则平淡枯乏的“灯下对坐的怀旧谭”,此处暗示出两人激情渐渐褪去,生活的骨感暗露端倪的状态,失去观点的针锋相对,新式的自由恋爱也被家庭生活的琐屑所征服,两人归于某种死水一样的平淡之中;而到了涓生被解聘的那天,“灯”的意象再次出现了,在两人的对话里,子君的声音浮动,而涓生眼中,那一刻“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此时,深刻的生存危机在灯火中成为昭然若揭的存在,当“我”写作时,子君把“黯淡的灯”拿了过来,而她在灯光照耀下的脸却是“凄然的”;最后,当两人的小家彻底破灭时,涓生返回家中,看到的是“没有灯火”,而只余下无尽的“昏暗”,而与之相对的是,正屋生活优渥、稳定的官太太一家“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而灯光中是夫妇“逗着孩子玩笑”的声音,展露了一个“灯光”映照下的温馨之家的幻影[29]。“灯”贯穿了涓生和子君的小家庭从幸福的开端走到了破灭的边缘的全过程,当灯是“暗室孤灯”那样的显眼明亮时,两人的关系由恋爱转为同居、建立家庭;而当生活陷入无力的寡淡之中时,“灯下”的回忆则成为两人心灵的唯一支撑;当灯黯淡昏沉时,二人情感陷入困境;当灯彻底地消失了,二人的情感也走到了尽头。“灯”是家庭关系的表征,也是预言,当“灯”逐渐黯淡乃至于终而熄灭时,这对自由恋爱的情人也终究要被这个守旧社会所戕害,他们的家庭终究走向流离与毁灭。
四、结语:为何是“灯”——沉思者姿态与现代性隐喻
从“苦难之灯”、“守旧之灯”和“家庭之灯”的反复出现之中,不难感受到鲁迅对“灯”意象的偏爱,这种偏爱首先来源于“灯”之于鲁迅,代表了一种颇具复杂性的身陷沉思之中的写者姿态。在鲁迅的散文、杂文乃至于小说之中,“灯下的沉思”始终是个形成知识分子身份自我确证的典型场景,在《祝福》里,作为叙事主人公的“我”在雪夜中“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30],思考祥林嫂苦难的生命与教条带给她的沉重压迫,对她的人生油然而生一种静穆中的悲悯,但最终,“我”又为一生被侮辱被损害的祥林嫂得以解脱渐而“舒畅”,而在《兔和猫》中,“我”为兔的死,总不免“夜半在灯下坐着想”[31],静坐沉思中又为造物的无情而倍感凄凉;而在诸多杂文末尾,鲁迅总不免署下“x 月x 日灯下”的写作时间,更有杂文名篇《灯下漫笔》,在该文中,鲁迅于灯下思忖,由自身在袁世凯称帝前后的经历,得出了国民始终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32]中徘徊的结论,并由此期盼着青年能创造第三样的时代;而在《写在<坟>后面》中,身处厦门的鲁迅感受到了黑夜中无限的寂静、野烧的微光,由此在“辉煌的电灯”中,记录下此刻淡淡的哀愁与无尽的忧思;而在《野草》中,徘徊于现实与幻梦之间的鲁迅常写“灯”下的故事,不论是《秋夜》中在灯下看着小虫扑灯火而亡,还是《好的故事》中在灯下读《初学记》而产生的朦胧幽雅的幻象,抑或是《腊叶》中灯下看《雁门集》[33],“灯”都是思想的发端,也是鲁迅游走于现实与幻梦哲思之间的边界性的存在。由此,“灯”作为一种光明性的存在,映衬出的是鲁迅复杂的写者姿态,在灯下长时间的写作与思考铸就了鲁迅文本中无处不在的“灯”,这一方面无疑隐喻着鲁迅在浓黑幽暗的处境中对于光明的执着追求,正如他在杂文中号召着青年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34],殷切企盼着青年们成为“唯一的光”,而与之相对的,阿Q 那样的代表着国民劣根性的人物,则是讳“光”“亮”“灯”“烛”等一切发出光亮之物的;而另一方面,在鲁迅看来,文艺本身就是指引方向的“灯火”,在《论睁了眼看》中,他写道:“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而这“火光”与“灯火”恰恰是互为因果的,惟有真诚的、“看取人生”的作家,才能引燃真正的“火”,创造出点燃国民精神的新文艺[35]。
此外,“灯”意象之中还蕴含着现代性的神话的隐喻。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以“防火灯作矣,汽机出矣,矿术兴矣”[36]作为西方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典型表征,使得“灯”背后的现代性意义在文本中昭然若揭;而在《论照相之类》中,鲁迅讲述了自己曾听说的乡野传闻:西方人喜好挖人心肝,熬成油,点了人心之油的灯,便可以向地下寻宝,“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37],在这个故事中,迷信与现实荒诞地融合了起来,乡野妇人并不了解殖民与资本积累,故而在其眼中,“灯”就成为一种现代性的“道具”表征,一种通向富有现代物质生活的媒介与法门,而其神秘、诡谲的色彩展露出一种“异类”想象的荒谬。从这些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灯”与现代性神话在鲁迅文本中的复义纠缠,“灯”是现代的火、启蒙的光,怀着这个符号体认而深窥《呐喊》《彷徨》中的“灯”意象,我们可以看出“灯”下景致所折射出的现代性与隐喻性,就仿佛同样是“与病相联”的“苦难之灯”映照下的不幸之家,在《呐喊》里,《药》中花钱买了人血馒头的华家仍旧失去了儿子小栓,《明天》中求了“神签”、发了愿、吃了单方、诊了何小仙的宝儿仍旧失去了生命,《白光》中犯了癔症的陈士成即使在水里拼命挣扎、指甲中嵌满泥沙也仍旧难以摆脱变为“浮尸”的命运;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彷徨》中,小说《弟兄》里的弟弟靖甫原本被中医认定感染了致命的猩红热,但灯光的映照下,如神明一般降临的西医普大夫确认靖甫所得的不过是普通的疹子,靖甫的生命得到了挽救。在这些文本中,灯意象意蕴着一种“现代性”的割裂与落差,它照亮病苦的特性使得一种“启蒙”与“现代性知识”在鲜明对照中得以阐发,有学者指出,从《呐喊》到《彷徨》,鲁迅的书写对象产生了迁移,在《呐喊》中,鲁迅所构设的往往是“时代落伍者”“未启蒙者”的群像,在14篇小说中有8 篇聚焦于旧式文人和带着愚昧色彩的急需被启蒙者;而在《彷徨》中,11 篇小说中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要写作对象的有8 篇,其更多聚焦于以启蒙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焦虑,带着对于《新青年》团体破裂的懊丧、对于启蒙大众的彷徨和绝望心境,其中的知识分子困顿往往带着鲁迅本人的影子[38]。无知无识的农民、旧式文人与接受了“现代知识”的知识分子看似生活在同一时代之中,但农民、旧式文人精神上的贫困、荒芜、封建时代的精神奴役创伤将他们与“现代”彻底割裂,“灯”映照下的“现代”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地域性与区隔性,它反映出的是某种五四乡土小说的“乡土想象”的共性,即“现代”只是极少数都市人的现代,而在都市以外的广袤乡野中,“现代”仍旧是一种值得远眺的奢侈品、虚无缥缈的愿景罢了。
综上所述,鲁迅之选用“灯”意象绝非漫笔,它所映照出的病苦、守旧陋习与家庭的衰亡、兴建,恰恰是鲁迅自身沉思者姿态的彰显与现代性思考的延续,小说文本中,这一个个由“灯”照亮的世界之角落,正是鲁迅的关怀之所在、痛切之所在。
注释:
① 这十三篇分别为《药》、《明天》、《阿Q 正传》、《兔和猫》、《风波》、《白光》、《祝福》、《孤独者》、《幸福的家庭》、《伤逝》、《长明灯》、《肥皂》和《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