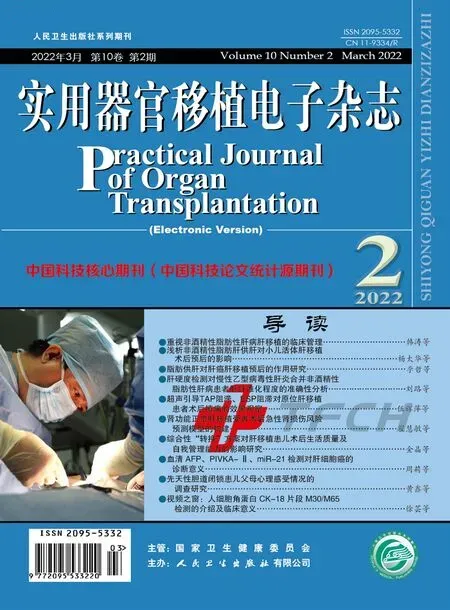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肝癌的研究进展
徐亮,陶雪梅,宓余强(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人民医院临床学院,天津 300192)
1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肝癌流行病学及自然史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肝脂肪变(non-alcoholic hepatic steatosis)、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目前NAFLD 的全球流行率约为25%[1],其中我国NAFLD 患病率为29.81%[2],且仍呈迅速上升趋势,预计在2016 年至2030 年期间,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NASH 患病率将增加56%[3-4],NAFLD 的高发势必会助推NAFLD-HCC 发病率的不断攀升。因NAFLD而导致HCC 的比例在过去20 年一直在稳步上升,到2017 年在美国已占比18%[5]。研究显示,每年新登记接受肝移植的NAFLD-HCC 患者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持续增长,从2003 年的0.05/10 万增加到2015 年0.81/10 万[6]。Estes 等[7]使用Markov 模型根据肥胖和糖尿病的动态趋势来预测美国2030 年NAFLD-HCC 的年发病率将增加137%;同样在另外7 个国家(中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NAFLD-HCC 发病率预计均将增加,增幅最小的日本也达47%(2016 年2 200 例到2030 年3 240 例)[4]。所以,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到2030 年NAFLD-HCC将成为世界许多国家HCC的主要病因。
NAFLD、NASH 及NAFLD 相关肝硬化的HCC发生率各有不同。Kanwal 等[8]对美国退伍军人中296 707 例NAFLD 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NAFLD患者的HCC 发生率约为0.02/1 000 人年,在NAFLD相关肝硬化患者HCC 的年发病率最高10.6/1 000 人年。另一项在25 万名美国退伍军人的研究中[9],排除肝硬化患者单纯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NAFL)或NASH 队列的HCC 发生率低得多,为0.08/1 000 人年。Gawrieh 等[10]的研究显示,在没有肝硬化的HCC 患者中NASH 的比例较大,为20%~50%,而其他肝病如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则小于10%。Orci 等[11]纳入了18 项研究进行Meta 分析,在无肝硬化NAFLD 患者中,HCC 的发病率为0.03 / 100 人年,在NAFLD 肝硬化患者中发病率为3.78 / 100 人年,接受定期HCC 筛查的NAFLD 肝硬化患者HCC 发病率为4.62 / 100 人年,并且NAFLD 相关肝硬化患者的HCC 发生风险与其他原因肝硬化患者相似。
2 NAFLD-HCC 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
NAFLD-HCC 患者的年龄至少比其他肝病相关性HCC 患者大5 ~10 岁,男性比例更高,肝硬化患者的比例更低,合并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情况更普遍,代谢危险因素更为常见。NAFLD-HCC 往往更晚期被诊断,这可能部分归因于未能及时诊断出潜在的肝硬化(导致缺乏筛查)或没有肝硬化(因此没有筛查的指征),但也可能与NAFLDHCC 缺乏特征性生物学表型有关。NAFLD 一些最具特征的危险因素,被认为是NAFLD“表型”的组成部分,也与HCC 独立且密切相关,包括肥胖、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与其他肝硬化病因相比,2 型糖尿病与NASH 肝硬化患者HCC风险增加的相关性更强[12-13]。2 型糖尿病使发生HCC 的风险增加2 倍,使因HCC 死亡的风险增加1.5 倍;代谢综合征和2 型糖尿病的存在使HCC 的风险增加5 倍;(body mass index,BMI)>35 kg/m2使HCC 发生风险增加4 倍[14]。与没有代谢特征的患者相比,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患者进展为肝硬化/HCC 的风险高1.8 倍[15]。Tobari 等[16]的研究发现非肝硬化NAFLD 发生HCC 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比值比(odds ratio,OR)=7.774,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2.176 ~27.775〕、轻度饮酒(OR =4.893,95% CI =1.923 ~12.449)、FIB-4 指数(fibrosis index based on the 4 factor,FIB-4)高(OR =2.634,95% CI =1.787 ~3.884)。
除此之外,NAFLD-HCC 发生的危险因素与种族也相关[9,17]。基因遗传多态性与HCC 相关,有的增加HCC 发生风险[18],如含PATATIN 样磷脂酶域蛋白3(patatin-like phospholipase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3,PNPLA3)、跨膜6 超家族成员2(transmembrane 6 superfamily member 2,TM6SF2)、葡萄糖激酶调节因子(glucokinase regulator,GCKR)、膜结合O-酰基转移酶结构域7(membrane bound Oacyltransferase domain containing 7,MBOAT7),有的降低HCC 风险[19],如17-β 羟类固醇脱氢酶13(hydroxysteroid 17-beta dehydrogenase 13,HSD17B13)。
3 NAFLD-HCC 发病机制
NAFLD 在危险因素包括糖尿病、胰岛素抵抗、肥胖、老年、男性、遗传基因多态性(PNPLA3、TM6SF2、GCKR 和MBOAT)的基础上,加之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经历“多次打击”后发生NASH、肝纤维化、肝硬化,其中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活性氮(reactive oxygen species,RNS)介导的氧化应激在NAFLD/NASH 的发病机制和并发症中起重要作用。ROS 的大量产生导致线粒体损伤、脂质过氧化和低密度脂蛋白氧化,促进炎症因子释放、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s)的活化,诱导天然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促进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T cell,NKT)、CD8+T 细胞、Th17(T helper type 17)CD4+T 细胞、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A+B 细胞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分子产生增多,导致免疫对HCC 监测的缺失,与肝细胞DNA 损伤、遗传易感基因突变共同作用诱发HCC 发生[14,20]。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SIBO)、肠黏膜屏障功能的破坏和高脂肪饮食似乎都加剧了肝纤维化和NASH 的发展,导致NAFLD/NASH 患者发生HCC。沉默lncARSR(long non-coding RNA activated in RCC with sunitinib resistance)可抑制IRS2/AKT 通路,从而通过下调YAP1(yes-associated protein 1)降低HCC 细胞增殖和侵袭,证实了长链非编码RNA lncARSR 通过促进YAP1 和激活IRS2/AKT 通路,促进NAFLD 相关肝细胞癌的发生[21-22]。
近期Ocker 等[23]研究显示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s,FGFs)介导了与NAFLD、NASH 和HCC 发展相关的关键病理过程。FGF21 主要参与介导NAFLD 和NASH 进展过程中的代谢作用,而旁分泌FGFs (FGF7、9、10)激活肝细胞增殖和再生过程,FGF1、FGF2 和FGF8 家族(FGF8、FGF17、FGF18)通过支持血管生成、通过HSC 激活调节基质和增加肿瘤细胞存活来介导HCC 的形成。
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是一种在真核细胞中广泛表达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MPK 信号调节通路抑制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c 及其靶基因的表达,促进NASH、HCC 发生发展[24]。信号转导器与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3,STAT-3)抑制剂的失活被认为是肥胖环境中致癌的可能机制之一。STAT-3是细胞质转录因子家族的成员,它调节参与细胞生存、增殖和免疫应答的基因表达,被JAK(janusactivated kinases)的磷酸化激活,直接与DNA 结合,将信号转导到细胞核。JAK/STAT 缺陷可能导致免疫缺陷疾病,而其异常激活(尤其是STAT-3和STAT-5)参与实体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研究发现,肥胖人群中NASH 与HCC 的发生可能是由STAT-1 和STAT-3 信号通路各自参与驱动的两个独立事件,O'Shea 等[25]和Grohmann 等[26]在C57BL/6 小鼠模型上进行的一项研究证明,肥胖和氧化应激导致了磷酸酶T 细胞蛋白酪氨酸磷酸酶(T cell 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TCPTP)的失活,而TCPTP 具有抑制STAT-1 和STAT-3 的作用。
Cai 等[27]采用基因表达微阵列(GSE74656,GSE62232) 鉴定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检测到7 个中心基因,包括CDK1(cyclin-dependent kinase 1)、HSP90AA1(heat shock 212 protein 90 alpha family class A member 1 213)、MAD2L1(mitotic arrest deficient 2 215 like 1)、PRKCD(protein kinase C delta)、ITGB3BP(integrin subunit beta 3 binding protein)、CEP192(centrosomal protein 192)和RHOB(ras homolog family member B),通过功能富集和通路富集分析,这些DEGs 与细胞周期和细胞外分泌体相关,与NAFLD 和HCC 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新基因CEP192,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 检测到ITGB3BP 和CEP192 的体外表达,提示在NAFLD 发展为HCC 的进程中可能存在DEGs。
4 NAFLD-HCC 的筛查管理
NAFLD 的发病率较高,所以关于NAFLD-HCC的筛查策略既要结合HCC 发生风险,又要考虑成本效益,针对高危人群,即使昂贵但筛查诊断效能高的方法也具成本效益。目前,腹部超声(ultrasound,US)和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作为进展期肝纤维化、肝硬化患者常规HCC 的标准筛查被国内外指南所推荐,在US 不能提供足够信息时,增强CT(computer tomography)和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扫描被推荐用于HCC 的强化筛查[28-30]。
有研究显示[31]在没有肝硬化且不伴有FIB-4 指数升高的患者中,肝癌风险估计仅为0.39 / 1000 人年,所以经非侵入性检查(non-invasive tests,NITs)评估不太可能有进展期肝纤维化的NAFLD 患者不应进行常规监测。所以,美国肝病研究学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指南[30]则建议筛查HCC 仅适用于肝硬化,但目前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指南[28]建议对NAFLD 肝硬化患者进行HCC 监测,并建议考虑对F3 纤维化患者(包括弹性成像诊断的F3 纤维化)进行HCC 监测。NITs〔FIB-4 指数、增强肝纤维化(enhanced liver fibrosis,ELF)检测、超声瞬时弹性成像(vibrationcontrolled transient elastography,VCTE)和磁共振弹性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MRE)〕显示NAFLD 患者可能有进展期肝纤维化,应考虑HCC 监测。肿瘤标志物如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e k antagonist-Ⅱ,PIVKA-Ⅱ)、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和AFP-L3(lens culinaris agglutinin-reactive fraction of AFP)可能有助于鉴别NAFLD 中HCC 的高危人群。最近发表的一项美国胃肠病协会(American Gastroscopic Society,AGA)更新版临床实践也采用了类似的建议[29],支持肝硬化患者和有证据显示进展期肝纤维化的NASH 患者进行HCC 筛查,比如VCTE >16.1 kPa、MRE >5 kPa、FIB-4 >2.67,同时也不建议无进展期肝纤维化的NAFLD 患者常规筛查HCC。
有学者将HCC 危险因素和预测因子纳入“HCC风险计算器”中,进而准确地估计每例患者发生HCC 的风险,Bianco 等[18]将PNPLA3-TM6SF2-GCKR-MBOAT7 的变异组合成肝脏脂肪变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s-hepatic fat content,PRS-HFC),然后进行HSD17B13 校正形成PRS-5,结果显示PRS 和HCC 之间的关联主要是通过严重纤维化介导的,但在临床相关亚组中与肝纤维化无关。同样在UKBB 队列中,PRS 可以独立于经典危险因素和肝硬化预测HCC,结果还发现PRS 截断值(PRS-HFC/PRS-5 为0.532/0.495)在UKBB 队列中检测HCC 具有90%的特异性,PRS 对HCC 的预测价值不受有无肝硬化的影响,但灵敏度有限。
多种生物标志物模型〔包括基于多蛋白和循环肿瘤衍生DNA(液体活检)的模型〕以及简化的MRI 规则和其他基于成像技术的规则作为筛查试验正在积极探索中,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为真正基于精确的HCC 筛查提供理论依据[32]。另外,将遗传基因多态性与上述预测因子合并到HCC 风险计算器中可能会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随着NAFLD 成为最常见的HCC 病因,优化NAFLD 的HCC 筛查策略至关重要。使用NAFLD特异性HCC 危险因素和预测因子来评估肝硬化或非肝硬化NAFLD 患者的HCC 危险将使我们能够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并针对不同的HCC 危险类别制定合理、经济的策略。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应用大量预测因子建模[33],而不是传统的回归技术,可能会在预测精度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数百万NAFLD 患者中确定筛查重点。
5 NAFLD-HCC 的治疗
防治NAFLD-HCC 最重要的是预防,首先预防NAFLD 和NASH(一级预防),预防HCC在NAFLD/NASH 中的发生(二级预防)[34]。预防NAFLD-HCC 发生分为可改变因素与不可改变因素,不可改变因素包括年龄、性别以及遗传基因易感性,改变生活方式为可改变因素[35],维持正常的BMI、不饮酒、不吸烟、坚持地中海饮食和充足的睡眠时间可显著降低NAFLD-HCC 发生风险〔风险比(hazard ratio,HR)=0.13,95% CI =0.06 ~0.30〕[36]。
最近的证据表明,肝脏中血小板募集和激活有助于小鼠HCC 的发展,特别是通过血小板糖蛋白Ⅰb α 信号[37]。在美国的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n =133 371)中,Simon 等[38]发现每周定期使用至少650 mg 阿司匹林可降低50%的HCC 死亡风险(HR = 0.51;95% CI =0.34 ~0.77)。 瑞典一项研究[39]证实定期摄入少于160 mg/d 的阿司匹林5 年以上,可以降低肝癌的风险(HR =0.69;95% CI =0.62 ~0.76),且不会增加胃肠道出血的风险。
二甲双胍抗HCC 的报道越来越多,其机制如通过降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 1,IGF-1)水平,下调c-Jun 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 p38 促 分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和NF-κB(nuclear factor-κ-gene binding) 通路, 激活AMPK、 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减少内源性活性氧的产生[40]。在37 个试验的亚组分析中[41],作者发现应用二甲双胍者HCC 发病率下降78%、病死率下降77%。另一项纳入10 项研究的Meta 分析显示[42],在334 307 例糖尿病患者中有22 650 例HCC,应用二甲双胍可使HCC 发病率下降41%。但也有研究不支持上述观点[43]。
体外研究表明[44],吡格列酮的抗癌作用可能是由于其抑制肝星状细胞的活化,低剂量吡格列酮的抗纤维化和抗癌作用在2 个小鼠模型中得到证实,另外,吡格列酮作为一种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 体-c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c,PPAR-c)的激活剂,也可以降低HCC 发病率。
German 等[45]以34 例HCC 患者为观察组,68 例为对照组(91%为肝硬化),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他汀类药物对肝癌具有保护作用(OR =0.20, 95% CI =0.07 ~0.60, P =0.004),而高血压是肝癌的一个危险因素(OR =5.80, 95% CI =2.01 ~16.75, P =0.001)。
辛伐他汀被证明能降低肿瘤细胞生长,削弱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单层膜的黏附,从而减少肿瘤细胞侵袭[46]。最新对24 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47],使用他汀类药物者HCC 发生风险降低了46%。另一项荟萃分析的亚组分析显示[48],使用亲脂性他汀类药物与使用亲水性他汀类药物相比,HCC 风险显著降低(51%比27%),潜在的机制包括抑制MYC、蛋白激酶B 和NF-κB 通路,以及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 和转化生长因子-β1 的产生减少。
Ⅲ期STORM 研究未能显示索拉非尼在NAFLDHCC 的无复发生存期方面优于安慰剂对照组(33.3 个月比33.7 个月,P =0.26),这表明索拉非尼在NAFLD-HCC辅助治疗中不是一种有效的选择[49]。在之前报道的所有试验中,不良事件并没有根据HCC 的病因进行区分,目前也没有NAFLD-HCC 亚组中治疗引起的不良事件的临床数据[50]。
Inada 等[51]的研究显示与NASH 相关HCC 患者对16 种肿瘤相关抗原的免疫反应较差,32 例HBV-HCC 患者的免疫应答率为68.8%,42 例HCVHCC 患者的免疫应答率为76.2%,18 例NASH-HCC患者的免疫应答率为33.3%。关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52-54],3 个大型随机对照Ⅲ期治疗晚期HCC 的临床试验 (CheckMate-459、IMbrave150 和KEYNOTE-240)表明,非病毒性HCC 对这些治疗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与 HR 可能不如病毒性HCC〔如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或HCV;非病毒OS HR=0.92,HCV-HCC OS HR =0.68, HBV OS HR =0.64〕 。Pfister 等[55]研究进一步证实NASH 存在慢性淋巴细胞衰竭,使肝脏中异常激活的CD8+PD-1+(procedural death-1)T 细胞增多。在NASH 诱导的HCC 临床前模型中,针对PD-1 的免疫治疗激活并扩大了肿瘤内CD8+PD-1+T 细胞,但未导致肿瘤消退,表明肿瘤免疫监视受损。在NAFLD 或NASH 患者的肝脏CD8+PD-1+T 细胞中发现了相似的表型和功能特征。总的来说,这些数据表明,非病毒性HCC,特别是NASH-HCC,病因可能与NASH 相关的异常T 细胞激活导致肝组织损伤、免疫监测受损有关。
Chin 等[56]对9 项研究中5 579 例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接受肝切除术的NAFLD-HCC 患者中与非NAFLD-HCC 患者相比,无病生存率(disease-free survival,DFS)(HR =0.85, 95% CI =0.74 ~0.98,P =0.03)和总生存率(OS =0.87,95% CI =0.81 ~0.93,P <0.0 001)均有更好获益,只有2 项研究报道了NAFLD-HCC 患者的围术期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虽然NAFLD-HCC 患者的复发率(44.6%)低于HCV-HCC 患者(65.2%)[57],但另一项研究发现,NASH 肝硬化患者的HCC 复发率与其他原因导致的肝硬化患者的HCC 复发率相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NAFLD-HCC 患者比非NAFLDHCC 患者面临更高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58-59]。
欧洲肝脏移植登记处(European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ELTR)在2002 年至2016 年期间对近69 000 例肝移植患者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60],NAFLD-HCC 的OS 略低于酒精导致的HCC,与HCV 或隐源性肝硬化相比没有差异(10 年生存率分别为46.9%、51.8%、48.2%和52.9%),尽管短期术后风险增加,但接受肝移植的NAFLD-HCC 患者与其他肝癌患者相比,在总体上有相似的移植后预后。
一项美国回顾性研究发现[61],与其他潜在的肝癌病因相比,接受射频消融术(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治疗的NAFLD-HCC 患者的OS 没有差异。目前关于NAFLD-HCC 患者行经肝动脉栓塞化疗(transhepatic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及体外放射治疗/立体定向全身放射治疗、选择性内放疗(selective internal radiation tharapy,SIRT)等新辅助和辅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生存率无显著差异[62],但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6 NAFLD-HCC 预后
目前研究多认为NAFLD-HCC 的预后不差于其他病因所致HCC,Safcak 等[61]的研究发现,在巴塞罗那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B 和C 期HCC 患者中,未发现NAFLD-HCC 与非NAFLD-HCC 的OS 或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存在差异,而基线患者的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5 mg/L、血小板/ 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PLR)≥150 与OS 降低相关 (P =0.012,P =0.0 028);与白蛋白-胆红素(albumin-bilirubin grade,ALBI)分级1 或2 相比,ALBI 分级3 级预测的OS 更差(P =0.00 021),并且即使在校正了BCLC 分期,PLR 和ALBI 仍然是总生存率的重要预测因子。Chen 等[63]纳入肝癌治疗方法,建立NASH 肝硬化HCC 生存风险评分,研究显示此评分与生存期呈正相关。甚至Chin 等[56]的研究认为行根治性治疗后的NAFLD-HCC 患者生存期更长。
总之,NAFLD-HCC 已逐渐成为危及人民健康的重要问题,但目前我们对其认识较少,很多数据及研究来自于国外,所以我们需要开展更多关于NAFLD-HCC 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来增加我国在此方面的数据,建立适合我国人民的筛查模型、预测模型及诊疗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