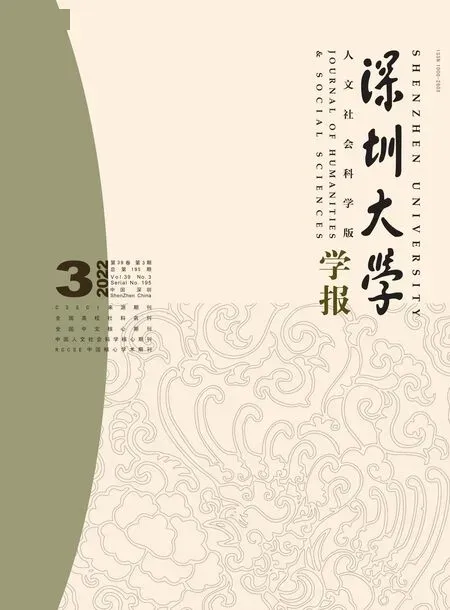从灾虫到神虫: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
靳 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32)
“蝗不入境”,又称“飞蝗出境”或“飞蝗避境”,是中古史籍中常见的用以构建、形塑地方良吏的一种书写模式。关于这一书写模式下历史叙事的虚与实,已有学者做了较为深入讨论①。但对于这一书写何以出现在东汉②,以往研究者只是从天人感应灾异思想、汉代对循吏的褒崇这些大的时代背景做了探讨,即使谈到谶纬学说影响,也仅泛泛而论。实际上,东汉时期“蝗不入境”书写的出现与东汉时期蝗灾频繁而又严重、谶纬学说盛行而又意识形态化、“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及其积极宣扬更有直接关联性。
一、《东观汉记》蝗灾书写的特质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历史的官修史书,也是当时人编纂的当朝史。从历代辑佚片段来看,其中有关蝗灾的记录与书写如下:
1.(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群起,四方溃畔[1](P2)(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2.(永初)四年,司隶、豫、兖、徐、青、冀六州蝗[1](P101)(卷三《恭宗孝安皇帝纪》)。
3.(永初)七年,郡国蝗飞过[1](P101)(卷三《恭宗孝安皇帝纪》)。
4.(永兴二年)诏司隶:“蝗水为灾,五谷不登,令所伤郡国皆种芜菁,以助民食”[1](P125)(卷三《威宗孝桓皇帝纪》)。
5.马棱,字伯威,为广陵太守,郡界常有蝗虫伤谷,谷价贵。棱有威德,奏罢盐官,振贫羸,薄赋税,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蝦。兴复陂湖,增岁租十余万斛[1](P455)(卷一二《马棱传》)。
6.卓茂,字子康,南阳人。迁密令,视民如子,口无恶言,吏民亲爱而不忍欺之。……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见乃服焉[1](P471-472)(卷一三《卓茂传》)。
7.赵憙,字伯阳,为平原太守。后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1](P501)(卷一三《赵熹传》)。
8.宋均为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阳、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辄东西别去,由是名称[1](P693)(卷一六《宋均传》)。
9.司部灾蝗,台召三府驱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审使臣驱蝗何之?灾蝗当以德消,不闻驱逐。”时号福为直掾[1](P876-877)(卷一九《梁福传》)。
10.喜夷为寿阳令,蝗入辄死[1](P878)(卷一九《喜夷传》)。
东汉时,通常将“蝗”与“螟”混称。《东观汉记》中还有一条有关“螟”的材料,也可视为蝗灾的记录与书写:
11.鲁恭为中牟令,时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察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鶵”。亲嘿然有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三异也。府掾久留,担扰贤者。”具以状白安[1](P476)(卷一三《鲁恭传》)。
《东观汉记》有关蝗灾的11条记录中,“1”至“4”是对蝗灾的客观记录。当然“1”又是灾异谴告思想在历史书写中的反映,是史籍为了突出王莽失天下的比较常见的书写模式。而“5”至“11”这7条则明显不同,具体来讲有3种形式:其一,“蝗不入境”。“6”卓茂(“独不入密界”)、“8”宋均(“南到九江,辄东西别去”)和“11”鲁恭(“不入中牟”)的事迹均属这种形式。其二,“蝗入辄死”。“7”赵熹(“入平原界辄死”)以及“10”喜夷(“蝗入辄死”)的事迹都是这种形式。其三,“蝗入海”。对于“5”马棱(“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蝦”),如果“飞入海”的“海”不在广陵郡境内,那么其三与其一均可归为“蝗不入境”现象。具体形式而言,二者略有不同,一个是“飞入海,化为鱼蝦”,一个是“别去”(飞出界,未记述最终具体飞往何处)。如果“飞入海”的“海”在广陵郡境内,那么其三与其二并非“蝗不入境”,而是自灭于境内。有学者将这些不同形式的记载称为“蝗不入境”模式的变体[2](P14)。但也有学者提出东汉时期“蝗不入境”书写还处于初始阶段,并没有形成为一种固定书写模式[3](P24),如果这样的话,所谓“蝗不入境”模式之变体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严格来讲,只有卓茂、鲁恭、马棱事例中的蝗灾书写表现出“德化”的灾异思想,把以往所谓的“害虫”升格为“神虫”。梁福所言的“灾蝗当以德消”是这一书写在思想方面的直接呈现。由此可见,在东汉史学中,这种“德化”灾异思想仍然不够成熟,所谓的“蝗不入境”书写在东汉时期历史书写中的确难以形成为一种固定用以描述良吏的“模式”。
“蝗不入境”书写始现于东汉时期,这是为什么?学者们对此也有过分析,或认为西汉中期以后灾异祥瑞论的盛行、汉王朝对循吏的褒崇、以往史籍中形塑地方良吏时对盗贼止息的描述等是造成这一历史书写出现的因素[2](P17-18),或把灾异天谴论与治蝗实践之间的博弈看作这一历史记载出现的因素[4],或重点分析了天人感应与谶纬学说对支撑这一历史记载的史学观念的影响[3](P21-23)。然而,无论是汉王朝对循吏的褒崇,还是天人感应下的灾异天谴说,这些只是东汉“蝗不入境”历史书写的大背景,缺乏直接关联性。即使有的学者分析到了谶纬说,但在具体论证中也往往泛泛而谈。实际上,“蝗不入境”书写始现于《东观汉记》,与东汉时期蝗灾频繁而又严重、谶纬学说盛行而又意识形态化、“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及其积极宣扬更有直接关联性。
二、东汉蝗灾与《东观汉记》的两次大规模修撰
关于东汉时期蝗灾的相关记载,与西汉相比在数量上有较大增长。不少学者对此做过统计。如杨振红提出,两汉时期蝗螟灾共出现了57次,其中西汉为18次,而东汉则为39次[5]。温乐平的统计数据与此略有不同:西汉时发生蝗灾16次,东汉时发生26次[6]。张文华对两汉蝗灾发生的次数也做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60次(西汉18、东汉42)[7]。由于不同学者统计时所依据的史料范围不同,或对蝗灾的判断标准不同,因此所得出来的蝗灾发生的具体次数都有些许出入。不过,这些统计数据有一个共同点,即西汉蝗灾数量明显低于东汉,甚至不到东汉蝗灾数量的一半。
东汉蝗灾不仅在数量上远多于西汉蝗灾,在爆发频率、规模、对社会影响程度上,同样体现出其严重性。陈业新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结果,把两汉时期蝗灾的时间分布序列特点做了概括,分为4个历史阶段来探讨,其中第四阶段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至东汉末年(220),为整个两汉时期的蝗灾高发阶段。他指出:“跨时219年,有蝗虫之灾48次,蝗灾发生的概率为4.6年一次,大大高于两汉虫灾发生的平均概率,是两汉时期蝗灾发生集中阶段。”而且,通过对本阶段内蝗灾发生时间分布的考察,他发现一个现象,即“在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二年(46)至顺帝永和元年(136)间存在一个频发时段,在91年的时间里有28次蝗灾,平均约3年一次,是‘宋前蝗虫发生频率大约是9年一遇’的三倍,与中国历史‘后期的五年二遇’的发生率极为接近。特别是在光武建武二十二年(46)至明帝永平四年(61)、安帝永初四年(110)至元初二年(115)各有16年和6年的两个时段里,前者发生蝗灾9次,后者发生蝗灾7次”[8](P47)。
如果再细细梳理这些史料记载,就会发现:光武帝时期,在建武二十二年之前,仅有建武五年与建武六年各1次蝗灾记载。据《续汉书·五行志三》刘昭注引,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师、郡国十九蝗”;建武二十三年,“京师、郡国十八大蝗,旱,草木尽”;建武二十八年,“三月,郡国八十蝗”;建武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农蝗”;建武三十年,“六月,郡国十二大蝗”;建武三十一年,“郡国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国十六大蝗”[9](P3318)。明帝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从塞外入”[9](P3318);永平十年,“郡国十八或雨雹、蝗”[9](P3313)、“未数年,豫章遭蝗,谷不收。民饥死,县数千百人”[9](P3318);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弥行兖、豫”[9](P3318)。 除此之外,还有范晔《后汉书》中的一些记载。如建武二十二年,“是岁……青州蝗”[9](P74)(卷一下 《光武帝纪下》)、“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9](P2942)(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建武三十一年,“是夏,蝗”[9](P81)(卷一下《光武帝纪下》);中元元年,“秋,郡国三蝗”[9](P83)(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相比以往的“蝗”,这里出现了“大蝗”的记录。“蝗”与“大蝗”在史家笔下是有程度区分的,即史家有意识地用“大蝗”一词描述范围较广泛和程度较严重的蝗灾[10]。80个郡国爆发蝗灾,这也可见蝗灾规模和影响之大。
据相关研究,《东观汉记》的前后大规模修撰主要有四次[11](P136),第一次在汉明帝永平年间,除了《世祖本纪》外,还有对东汉初功臣等列传的编撰。《后汉书》卷四〇《班彪列传》载曰:“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从上述所列蝗灾记录及其严重性来看,很有可能“蝗不入境”书写的代表者卓茂的传记就是在这一阶段初步编撰完成的。卓茂是西汉末年通儒。光武帝即位,寻访拜见,高度赞赏他为密令时“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封其为褒德侯,待以很高礼遇。建武四年(28)卓茂去世,光武帝“车驾素服亲临送葬”[9](P871)(卷二五《卓茂传》)。此外,赵熹在更始时就被封为勇功侯。建武之初,光武帝赞其“长者”而待诏公车。光武帝叔父刘良去世之年(建武十七年),赵熹为平原太守,直至建武二十六年迁为太仆[9](P912-914)(卷二六《赵熹传》),做了近10年太守,也出现了所谓的“蝗入界辄死”的德化记录。建初五年(80)去世。宋均被光武帝“嘉其功”,建武间,他曾为九江太守,出现了“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的现象。中元元年(56),他仍任九江太守,更是出现了“蝗不入界”的德化之应。建初元年(76)卒于家[9](P1412-1414)(卷四一《宋均传》)。汉明帝时下诏令班固等撰功臣列传,虽然赵熹、宋均不会名列其中,但他们的德化事迹应被世人传颂或有史官记录在案,这为汉安帝时期第二次大规模撰写提供了素材。可以说,因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以来蝗灾频繁而又严重,故在褒奖名臣的编撰旨意下史书遂出现了“蝗不入境”的书写。
汉章帝时,在目前所见的有关文献中没有蝗灾记录。汉和帝时,有3年5次蝗灾记录。汉安帝时,共有8年9次蝗灾记录,其中永初四年(110)至永宁元年(120)之间,就有8次蝗灾记录。同样,蝗灾损害也很严重。如安帝永初五年,“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9](P2888)(卷八七《西羌传》)。面对严重蝗灾,统治者愈加重视,一方面实施救灾措施,另一方面下诏罪己以安民心。安帝于永初五年就曾下诏曰:“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9](P217)(卷五《孝安帝纪》)。元初二年(115)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甲戌,诏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异不息,忧心悼惧。被蝗以来,七年于兹,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今群飞蔽天,为害广远,所言所见,宁相副邪?’”[9](P222-223)(卷五《孝安帝纪》)帝王因蝗灾下罪己诏,不仅体现了国家对蝗灾的重视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蝗”与“蝗灾”拉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自然修史人员也不例外。诸如前面所列《东观汉记》所记述的马棱,从汉章帝章和元年(87)任广陵太守,和帝永元二年(90)转任汉阳太守,安帝永初(107-113)中卒于家[9](P862)(卷二四《马援列传》附《马棱传》)。鲁恭专以德化为理,汉章帝集诸儒于白虎观,“恭特以经明得召,与其议”,后拜中牟令。安帝永初六年(112)卒于家[9](P873-882)(卷二五《鲁恭传》)。 从大的时间段来看,马棱任广陵太守期间所出现的“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蝦”、鲁恭任中牟令时所出现的“蝗不入境”,与《东观汉记》第二次大规模编撰于安帝永宁年间(120-121)在时间上是相合的。
蝗灾愈加严峻、民众深受蝗灾之苦与统治者的重视使得蝗与蝗灾在时人的生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时人将蝗灾与灾异书写相联系。当然,东汉时期“蝗不入境”书写的始现,也不仅仅有蝗灾盛行这一自然灾害之社会现实的基础因素,还应有思想观念方面的促成因素,即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盛行起来的谶纬学说、“变复学说”,这些学说与东汉“蝗不入境”书写同样有密切关联。
三、谶纬学说意识形态化与官修史书
关于谶纬起源的说法有多种,但盛于西汉末特别是东汉时期,这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顾炎武《日知录·图谶》云:“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刘师培言:“董、刘大儒,竞言灾异,实为谶纬之滥觞。哀、平之间,谶学日炽……是则东汉之学术,乃纬学昌盛之时代也”[12]。
谶纬在东汉盛极一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被帝王提倡。建武三十一年(55)改元中元,“宣布图谶于天下”[9](P84)(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光武帝信谶,使得谶纬由一股民间思潮转变为国家宪章的政治力量[13]。不但光武帝信谶,整个东汉一代盛行谶纬学说,诸位皇帝都将谶纬学说应用到了政务处理中。《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载曰:“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9](P1911)。谶纬还被视为“内学”。《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载曰:“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自是习为内学”[9](P2705)。
谶纬学说不但对经学影响甚大,如樊鯈“以谶记正《五经》异说”[9](P1122)(卷三二《樊宏传》),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经学,即位,删定拟议,稽合图谶”[1](P58)(卷二《显宗孝明皇帝纪》)。而且,谶纬学说也影响到官修史书。这是因为,“一方面,统治者要宣扬谶纬迷信,君权神授,迫切需要历史知识为之论证;另一方面,统治者要加强思想箝制,又要直接控制和垄断史学,以便可随心所欲地借用史学这个工具来体现统治集团的意志。”在“这种情势下,绝大多数史家只好迎合统治者的口味,历史遭到了任意的解释附会,甚至宰割和篡改,史学著作充斥着虚妄不实的内容”[14]。如永平五年左右,参加修撰《世祖本纪》的有陈宗、尹敏、孟异、班固等。其中史书明确记载尹敏善言阴阳灾异。建武二年,他上疏光武帝,“陈《洪范》消灾之术”[9](P2558)(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后来,“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9](P2558)(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尽管尹敏谏光武帝“谶书非圣人所作”[9](P2558)(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往往菲薄谶纬,以其为世俗之辞,非圣人所言,但他修史的职掌却是主光武谶记。
永平十五年左右,参加修撰《建武注记》等史篇的有马严、杜抚、班固等。马严,“从司徒祭酒陈元受之”[9](P859)(卷二四 《马援列传》李贤注引 《东观记》)。而陈元在阐释《左氏春秋》经义时“多引图谶”[9](P2582)(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故说马严受图谶影响是可以的。杜抚“受业于薛汉”[9](P2573)(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而薛汉“尤善说灾异谶纬”。建武初,薛汉“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高最知名”[9](P2573)(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薛汉不仅善说图谶灾异,且受诏校订图谶学说。既然杜抚为薛汉最知名弟子之一,他也应善说图谶灾异。有学者由此而指出,“从此次修史人员的知识背景,我们发现修撰《注记》之时,熟知掌故的旧吏不再需要,但精通谶纬灾异的儒生则必不可少”[11](P126)。
据《典引》序文,参加永平十七年诏问的有班固、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这些人应是参与了官方修史。《后汉书》卷一四《北海靖王兴传》载曰:“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刘)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9](P558)。贾逵虽然反对谶纬[9](P1912)(卷五九《张衡传》),但他还是受到谶纬思想的影响。他在上汉章帝的奏书中言:“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9](P1237)(卷三六《贾逵传》)。贾逵与诸生考论图纬,又上书言《左传》中有汉家尧后之明证。郗萌,正史无传。然《隋书·经籍志》载有“《春秋灾异》十五卷,郗萌撰”,又云:“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这是说,郗萌为汉郎中时亦善言图谶。
通过上述可见,永平年代修史者,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史臣外,汉明帝还加入了两类修史人员,一类是宗亲近臣,一类是谶记儒生。这是永平修史的一大特色。可见,“宣扬汉命天授的谶纬之说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知识背景,进而化为史臣的一种自觉”[11](P128)。
谶纬内容很繁杂,但有其中心思想。顾颉刚曾言:“谶纬的中心思想是阴阳五行,是灾异祯祥”[15]。具体而言,东汉谶纬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大讲气类相感、天人相应。两汉灾害谴告说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盛行的纬书中也有较多反映。如《孝经援神契》云:“木气生风,火气生蝗,土气生虫,金气生霜,水气生雹。失政于木,则风来应;失政于火,则蝗来应;失政于土,则虫来应;失政于金,则霜来应;失政于水,则雹来应。毁伤致风,侵蚀致蝗,贪残致虫,刻毒致霜,暴虐致雹,此皆随其事而致也”[16](P699)。《易稽览图》云:“凡异所生,灾所起,各以其政,变之则除,其不可变,则施之亦除”[16](P112)。纬书中对灾害谴告说的诠解和发挥内容常为两汉(主要是东汉)说灾论害者所引用[8](P172)。清代史学评论家、方志理论家章学诚,一方面批判地指出“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17](P1)(《内篇一·易教上》),另一方面就方志中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撰写而论道:“然而石鹢必书,螟蝗谨志者,将以修人事,答天变也。自《援神》《鉤命》,符谶荒唐,遂失谨严”[17](P856)(《外篇三·天门县志五行考序》)。这就明确指出了蝗灾与谶纬学说的密切关联。
四、“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宣扬与“蝗不入境”书写
王充较早提及到“蝗不入境”这一书写实例。《论衡·感虚篇》云:
世称:南阳卓公为缑氏令,蝗不入界。盖以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县也。此又虚也。夫贤明至诚之化,通于同类,能相知心,然后慕服。蝗虫,闽虻之类也,何知何见,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贤者处深野之中,闽虻能不入其舍乎?闽虻不能避贤者之舍,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县?[18](P257-258)
王充以批判虚妄为出发点,引用了南阳卓茂“蝗不入界”这一叙事及观念,认为所谓“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县”是没有说服力的,“蝗不入境”叙事是虚妄的。这也说明“蝗不入境”叙事在王充撰写《论衡》时应该就有了,且代表了一种社会观念。
而“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县”的社会观念离不开“变复家”的思想宣扬。《论衡·商虫篇》云:“变复之家,谓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也”[18](P713)。《论衡·遭虎篇》又云:“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18](P707)。所谓“猛虎渡河”的良吏书写同样与变复家有关。细检《论衡》全书,提及“变复”多达28次。可见,“变复之家”与“变复学说”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很盛行。
何谓“变复之家”,其学说内涵又是什么?《汉书·五行志》载晋侯与大夫士文伯的对话,谈及日食与善政的关系问题。班固写道:“此推日食之占,循变复之要也”[19](P1494)(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下》)。这是较早地明确提及到“变复”的灾异观念。由士文伯所言“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适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19](P1494)(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下》),显然,“变复”就是通过占卜、采取善政而消除灾变。不过,整部《汉书》仅有这一处灾异观念意义的“变复”,而且是班固运用“变复”之说来解释日食灾异。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西汉时“变复之家”还没有形成。而东汉时人在论述灾异时常提及“变复”。如永初三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汉安帝下诏曰:“朕以幼冲,奉承鸿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噉食。永怀悼叹,若坠渊水。咎在朕躬,非群司之责,而过自贬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务思变复,以助不逮。”接着,下令“以鸿池假与贫民”[9](P212)(卷五《孝安帝纪》)。郎顗向帝王陈述消灾之术时云:“臣伏见光禄大夫江夏黄琼,耽道乐术,清亮自然,被褐怀宝,含味经籍,又果于从政,明达变复。”对于“明达变复”,李贤注曰:“言明于变异消复之术也”[9](P1070)(卷三〇下《郎顗传》)。光和元年,有虹蜺昼降于皇宫嘉德殿前,汉灵帝派人向蔡邕、杨赐等人询问。杨赐对曰:“幸赖皇天垂象谴告。《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惟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内亲张仲,外任山甫,断绝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无敢怠遑。冀上天还威,众变可弭”[9](P1780)(卷五四《杨赐传》)。对于“变复”,李贤又注曰:“谓变改而销复之。”又《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载曰:“(樊)英既善术,朝廷每有灾异,诏辄下问变复之效,所言多验”[9](P2724)。此处“变复”,李贤则注曰:“变灾异复于常也。”这与前两处“变复”注解略有不同,但指意是一致的。《资治通鉴》卷四九《汉纪四十一》“孝安皇帝永初三年”条下载曰:“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务思变复,以助不逮。’”胡三省注曰:“变,改也;改过以复于善也”[20]。
无论李贤注还是胡三省注,他们对于“变复”的理解还停留在语言识读层面上,并没有对这一学说的内涵、特点做深层分析。实际上,王充在《论衡》中对“变复之家”与“变复之说”有明确论述。
《论衡·变虚篇》云:“若夫寒温失和,风雨不时,政事之家,谓之失误所致,可以善政贤行变而复也”[18](P208)。这里的“政事之家”指的就是“变复之家”,他们认为寒温风雨这一自然现象之所以出现异常,是缘于为政上的失误,可通过善政贤行“变而复”。《论衡·明雩篇》亦云:“旱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此变复也”[18](P665)。《论衡·感虚篇》明确云:“变复之家曰:‘人君秋赏则温,夏罚则寒。’”王充对此批判道:“寒温自有时,不合变复之家。且从变复之说,或时燕王好用刑,寒气应至;而衍囚拘而叹,叹时霜适自下。世见适叹而霜下,则谓邹衍叹之致也”[18](P241)。在王充看来,寒温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君秋赏夏罚的为政之道无关;“变复之家”所言的燕王、邹衍事例只不过是一种巧合而已。《论衡·寒温篇》亦言:“然则寒温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温之至,遭与赏罚同时,变复之家,因缘名之矣”[18](P628)。《论衡·明雩篇》更云:“夫如是,水旱饥穰,有岁运也。岁直其运,气当其世,变复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过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变复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术”[18](P665)。
由上述可知,“变复之家”言寒温灾异,有人把它视为“五行占验家之流”,未必不是事实③,但“变复之家”认为灾异缘于失政所为,与一般的灾异占验家有所不同。对此,王充明确言:“京氏占寒温以阴阳升降,变复之家以刑赏喜怒,两家乖迹”[18](P632)(《寒温篇》)。这是说,“变复之家”的思想与京房灾异思想在灾异产生的途径上是不同的,前者以政言灾异,认为灾异是失政造成的,故只有善政才能消复灾异;后者以阴阳言灾异,认为灾异是阴阳升降造成的,故只有顺应阴阳时序才能免除灾异。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而京房师从焦延寿,且“用之尤精”[19](P3160)(卷七五《京房传》)。故京房以《易》为本,纯粹根据风雨占候,采取象类相比附的方式来说灾异[21]。实际上,王充是以京房的阴阳灾异思想来批驳“变复之家”的灾异学说。《论衡·寒温篇》云:“《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阴阳,气有升降。阳升则温,阴升则寒。由此言之,寒温随卦而至,不应政治也”[18](P631-632)。马宗霍《论衡校读笺识》卷一六《商虫篇》云:“虫应贪吏,其说见于《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仲任所称‘变复之家’,京氏其一也”[22](P223)(卷一六《商虫篇》)。这一认识是没有注意到王充所明确提及的京氏以阴阳占验灾异说与“变复之家”以政关联灾异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家。正如日本学者柳濑喜代志所指出的,王充本要批判寒温风雨出现异常及政之失这一不合理性而引用两种学说,反而将当时关于虫灾的一种解释公之于世[23]。也就是说,“变复学说”表明了对灾异发生原因的新见解。
“变复学说”与灾异天谴说很相似,但也有差异。首先,“变复学说”是由灾异天谴说发展而来的。《论衡·谴告篇》云:“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马宗霍释曰:“此文之意,盖谓变复之家,其言天也多妄,以妄言加之于天,是天受其诬也,故曰‘见诬’”[22](P204)(卷一四《谴告篇》)。王充又言“论灾异者,谓古之人君为政失道,天用灾异谴告之也”“犹夫变复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18](P634-636)(《谴告篇》)。这显示出二者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二者在灾异与政治的关联上是趋同的。其次,天谴说更多强调的是君主或帝王这一政治最高统治者层面,而“变复学说”则侧重部吏这一政治基层治理者层面。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言:“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9](P2498)(卷五六《董仲舒传》)。《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亦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24]。董仲舒阐发的灾异天谴说突出“国家之失”。这并非单是董仲舒一人的观点,而是汉代谈灾论异者的普遍认识[11](P147-148)。如《汉书》卷四《文帝纪》云:“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19](P116)。成帝时,谷永上书说:“臣闻灾异,皇天所以谴告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畏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19](P3450)(卷八五《谷永传》)。无论“人主不德,布政不均”,还是“人君过失”而引发了灾变,都是在强调君主或帝王的无道与灾异之间的关联。而谶纬学说逐渐把君无道与吏贪暴相糅合,使得灾异观范围更广。蔡邕在回答光和元年诏策时就引《河图秘徵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并言“蝗虫,贪苛之所致也”[9](P3320)(《续汉书·五行志三》)。“变复之家”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部吏为政与蝗灾的内在关联性,这一点从上引“变复学说”就可得到很好地说明。再者,二者的区别还在于,灾异天谴说强调的是一种警示、引诫或反思,而“变复学说”突出的是德化、仁政的效应。实际上,一个是侧重反面警醒,一个是侧重正面范式。
王充还提出“政治之灾”与“无妄之变”两种灾异类型,这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变复学说”。《论衡·明雩篇》云:“夫灾变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灾,有无妄之变”[18](P671)。何谓政治之灾?何谓无妄之变?《论衡·明雩篇》又曰:“德酆政得,灾犹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变应来者,政治也”[18](P671)。无妄之变与政治无关,是自然而应,无需变革。而政治之灾乃由德衰政失造成,必须改变为政之道。《论衡·明雩篇》云:“夫政治,则外雩而内改,以复其亏;无妄,则内守旧政,外脩雩礼,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气,历世时至,当固自一,不宜改政”[18](P671-672)。而“变复之家”并不区分政治之灾与无妄之变,一味地强调灾异因失政所为,提出善政才能“消复”。《论衡·明雩篇》云:“变复之家,见变辄归于政,不揆政之无非;见异惧惑,变易操行。以不宜改而变,秖取灾焉”。
在“变复之家”看来,既然蝗灾是由于官吏的贪暴所造成的,那么蝗灾无需防治,只要部吏勤政廉洁,感化于天,蝗虫自然会消匿,社会秩序也就会继续步入正常轨道。所以,在东汉蝗灾的历史书写中,所谓德化事迹多了起来,蝗虫也就从灾虫变成了神虫。有学者推测,“对蝗虫予以神化,并立庙予以专祀可能就发生在两汉时期”[25](P182)。严格来说,对蝗虫神化的立庙专祀现象更有可能发生在东汉时期。
天人感应之下,“变复论”甚嚣尘上[25](P128)。“变复之家”积极宣扬“虫食谷者,部吏所致”的变复思想,对东汉时期“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思想家、批判者的王充,很敏锐地注意到“变复学说”对于东汉官修史书的深刻影响,并作了批判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时期“蝗不入境”书写模式的产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故清人王夫之言:“变复之术,王充哂之,亦知言者夫”[26](卷五《系辞上》)。
综上所述,东汉有关“蝗不入境”的记载中有“蝗不入境”“蝗入则死”“蝗入海化为鱼蝦”等多种书写方式,而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用“德化”灾异观念解释,故“蝗不入境”的记载尚难构成一种固定用以描述良吏的“模式”。然而,这种“德化”灾异书写确实始现于《东观汉记》。根据相关史籍的统计,东汉蝗灾不仅在数量及频率上多于西汉蝗灾,在程度上也更为严重。而且从《东观汉记》前两次大规模修撰来看,蝗灾与历史书写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东汉蝗灾频繁而又严重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时人将蝗灾与灾异书写相联系,是“蝗不入境”书写在社会现实方面的基础因素。谶纬学说在东汉十分盛行,且由民间思潮转变为国家宪章的政治力量。东汉官方修史的诸多参与者具有谶纬思想的相关学术背景,而纬书中又有对蝗灾的直接记载与阐释。“变复学说”是由灾异天谴说发展而来的。天谴说强调君主过失导致灾害发生,而谶纬学说逐渐把君无道与吏贪暴相糅合,使得灾异观范围更广。“变复学说”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官吏修德可以消除蝗灾,恢复原有秩序。这样,东汉蝗灾的历史书写中所谓德化事迹多了起来,蝗虫也就从灾虫变成了神虫,《东观汉记》始现“蝗不入境”的书写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撰写得益于师妹田艺景《中国古代“飞蝗避境”现象记载与史家观念演变》一文的启发,在蝗灾资料方面,也承蒙她的无私帮助,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注:
①可参见:夏炎.环境史视野下“飞蝗避境”的史实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15,(3):132-134.田艺景.中国古代“飞蝗避境”现象记载与史家观念演变[J].史学史研究,2021,(1):18-21.
②关于卓茂的“蝗不入境”现象,在《后汉书》与《八家后汉书》中皆有记录,但因其编撰时间晚于《东观汉记》,故《东观汉记》为最早出现“蝗不入境”现象记载的史籍。
③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九《五代中》中言“变复不惟其德而唯其占”(中华书局,2002年,第905页)。黄晖《论衡校释·感虚篇》引清人沈涛《铜熨斗斋随笔》云“变复家盖亦五行占验之流”,并言“《史记·日者传》,数诸占家之名,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一家,而无变复家。”
——以王嘉《拾遗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