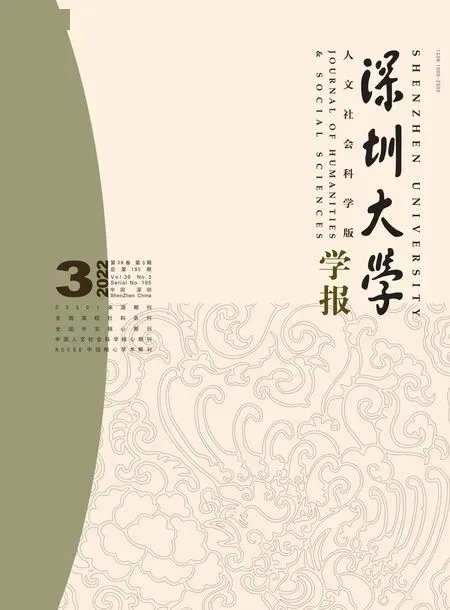数字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及其空间话语
吴红涛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互联网、数字媒介、电子商务、虚拟现实与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要的表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并不简单等同于“拥有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1],它为资本主义带来的革命几乎是全方位的,乔纳森·佩斯(Jonathan Pace)将其概括为“生产技术的变革”、“生产对象的变革”、“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变革”和“劳动者工作方式的变革”等[2]。由于数字资本主义形塑的多元效应,国内外学界近年来围绕数字资本主义所展开的讨论呈逐年增多之势。然而,一个尚未引起学者们重视但又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论数字资本主义如何演变、延伸与发展,都离不开“机器”(machine)的生产及应用。数字资本主义对机器的依赖是根本性的,诸如计算机、手机、摄像头、平板电脑、导航仪、无人机、电子穿戴设备、智能机器人等,离开了这些可批量生产的机器,数字资本主义不仅缺失了最为基础的物质载体,还无法建构起真正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正如伯纳德·马尔(Bernard Marr)谈到的,数字资本主义倚重的数据(Data)“不仅由手机、平板和电脑产生,而且还由智能恒温器、火灾报警器、安全摄像头、婴儿监视器及其它诸多家电等机器产生”[3]。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各种机器尤其是易于流动的微机器,数字资本主义一方面得以摆脱了传统资本主义所遭受的空间限制,成为现实地理空间中无处不在且随处可在的强势威权;一方面还引领人们进入直至沉迷数字机器所着力营造的虚拟空间,借此非但侵吞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部生活时间”[4](P482),还力图占领包括精神空间在内的全部生活空间,从而为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数字剥削”与“信息奴役”等开辟新的地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机器生产无疑内含了鲜明的空间政治,它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空间话语的当代延续,机器、空间与数字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三维辩证体。
一、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空间诊读
早在19世纪初叶,李嘉图(David Ricardo)便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著中强调:“机器的发明是逐渐出现的”[5](P338)。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李嘉图难能可贵地意识到机器随现代文明演进而不断得以改良的事实,同时还预判到机器在人类社会中将扮演的关键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之前卢梭、拉·梅特里与笛卡尔等人的机器观,李嘉图率先确认了机器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之间的亲缘关系,“任何生产部门内应用机器,只要能节省劳动,便是一种普遍的利益”[5](P331)。然而李嘉图围绕机器生产而展开的论述,过多停留在它对劳动量及工资收入的影响,未能全方位触及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核心问题。这种缺憾直到马克思的出现才得以填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马克思将“机器”和“大工业”放置在一起考察,揭示“机器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而获利的一种手段”[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系统剖析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历史背景、逻辑动因、内在原理及生发效应,这些分析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学者甚至提出“马克思—机器”(Marx-machine)[7]这样的专属概念,以此来突显马克思机器学说的重要价值。
马克思论及的“机器生产”首先指代的即是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所具备的生产功能。“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4](P427)是马克思机器学说的起点。“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8](P32),机器是工业革命的特殊产物,体现了技术文明的进步,它能够替代过往相对粗糙的工具,“机器的出现不是取代了人,而是赋予工具以人才有的技能,工具变成机器的一部分”[9]。然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机器作为技术进步的结果不是解放人类,而是进入到资本及其价值创造的某个过程”[10]。换言之,机器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物,被资本家们纷纷纳入到其资本生产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工厂制造业、采矿业、造船业等领域里,“机器总是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11](P263),成为增加剩余价值与资本财富的新型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生产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
列斐伏尔曾揭示,资本主义向往的剥削与统治型关系“是通过整个的空间并在整个的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12](P136),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借助和利用空间蕴藏的无尽潜能,还要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破除各种空间壁垒。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热衷于“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经典论点,此处的“时间”,确切地说是把“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3],即节约时间成本。机器生产的出现完美契合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这种企图,主要显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机器具备自动化、批量化和程式化的特征,因而大幅度减少了物件生产的单位时间,资本家们得以在单位空间里迅速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机器生产形塑的“时空压缩”来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而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时期最具时代意义的机器发明,更是“催生了工厂和大规模的生产,铁路和大规模运输时代到来了”[14],资本主义生产所遭遇的空间障碍就此被大大消解。其二,机器具备多样化和精细化的功能,能够有效化解过往资本主义过度依赖劳力数量的短板。由于诸多劳力需要在空间中进行生产上的分区协作,这就使得资本家们需要付出相应的空间成本,劳力越多,空间成本就越高。机器集结了不同劳力在生产中所对应的不同角色,它能有效节省资本家的空间成本,如斯密所说的:“由于发明了大量的机器,方便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15]。其三,机器不同于普通劳力,后者是现实中的个体人,除了在生产空间中劳动,还需要去往其他空间展开休闲、娱乐、休息和交往等活动,这就为资本家们建构“剥削与统治型关系”带来了空间上的不确定性。而机器只需要固定于特定的生产空间中,它可以在这个空间持续无休止地运转,既能够减少空间流动的不确定性,又能够提升空间利用的效益。
由此可见,机器生产悄然融入了资本主义的空间话语,是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尽管机器生产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过度倚靠劳力所形射的空间困境,但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机器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满足资本主义的内在诉求,机器本身也面临着空间上的弊端。众所周知,无论机器的功能指向如何,它首先都是一个有形的物质实体,特别是在马克思生活的工业革命时代,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塞缪尔·克隆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的自动骡机等为代表的实体机器,更是以体积庞大而著称。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提出过著名的“巨机器”(Megamachine)的概念,单从字面上看,“巨机器”首先即是那种外形巨大的机器,为此芒福德又称其为“大机器”(Big Machine)[16],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论及到的诸多机器,基本上也都是这种“大机器”。由于体积庞大且组装复杂,其必须放置于某个固定空间(如厂房),要使用它,人们就必须去到这个固定空间。诚然,大机器的这种属性虽满足了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所说的“空间固定性”(spatial fixity),便于特定空间中“资本的聚集与集中”[17](P8-90),但它易于耗损且难以促成跨空间的自由流动亦是不争事实。资本家们当然不仅需要在固定空间里从事“死劳动”的“大机器”,还期待那种可渗透到任意空间开展“活劳动”的“好机器”(Good Machine)①,从而将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真正落实到地球的每一处。
因此,“改良机器”便成为了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的议题。恩格斯指出:“所有的机器都经过无数次微小的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18](P9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机器自身的价值并不等于机器生产的价值,机器自身的价值受机器质量、磨损、功能等要素的影响,所以资本家们需要想方设法地减少机器价值的转移,“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4](P445-448)。为此马克思提到,当资本家们获取由固定资本所转化而来的货币后,就会拿出一部分来“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11](P192)。不难察觉,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已然开启了一次关键的内部转型——从“通过机器来改良生产”到“通过生产来改良机器”,前者聚焦于“生产”,后者聚焦于“机器”,机器不再只是生产的工具,其自身即是生产目的,机器生产也由此从“使用机器进行生产”换成了“对机器本身的生产”。在资本家那里,无论是“使用机器进行生产”,还是“对机器本身的生产”,共同目标其实都指向了剩余价值和资本利润的生产。
二、机器生产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策略
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积累阶段所倾力追求的主要是作为不动产的空间(土地、领土、矿场等),那么随着资本主义衍变的不断拓深,这种粗放式的不动产空间已完全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更为灵活且更具张力的“空间动产化”成为他们的新宠。1972年,列斐伏尔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次学术讲演中强调,由于不动产存在着“极为慢性的消耗”,同时也不利于资本的快速循环,因此对空间不动产的“动产化”成为资本主义空间策略的最新呈现[12](P100-102)。诚如前文所分析的,早期资本主义投入生产的“巨机器”,鉴于其先天特性,大多只作为固定空间中经专业人力操作的不动产而存在,难以在不同空间区块之间进行跨空间的自由流动,因而也无法进入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这无疑就限制了资本势力的进一步空间扩张与资本力量的进一步空间辐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醒:“机器永远都必须在一种关系中被看待,所以资本家才会使用它”[19],正是出于机器遭受的空间限制会对资本主义利益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改良机器”才会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规划议程之中。
如何让机器突破诸多空间性限制,促成机器在空间上的“动产化”?首要方法即是先大幅度缩小机器的空间体量,减少机器的空间占位,使得机器能够更便捷地实现空间位移。我们可以看到,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经由信息时代再到如今的智能时代,除了部分特定行业里的大机器(如飞机、火车等),机器改良一直在朝着两个方向持续深化:一是外在形态的轻便化与微缩化,二是内在功能的精细化与多元化,两者合力促成机器变为“微形态”与“大功能”的结合[20]。显然,这种改良超出了马克思在考量工业生产时曾经论及的“现有机器的局部改良”[11](P192),它是一种由内至外的全局性改良。以计算机为例,毫无疑问,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机器发明。自1930年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创造世界首台模拟电子计算机以来,计算机陆续经历了电子管数字机、晶体管数字机、集成电路数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几个阶段,其功能归属从军事国防领域过渡到普通的商业领域,与之相伴的还有外观呈现形态的不断缩小。早期的计算机体积庞大,1946年诞生的世界首台电子数字积分式计算机(ENIAC)的重量高达30吨,这对空间面积无疑有着极高要求,更不可能在不同空间中实现流通。美国《纽约客》杂志曾如此描述早期计算机:“机器的核心部件是玻璃面板后面的电子管及线缆,它们就占据了房间的三面墙壁,而两个类似于超大号邮筒的‘料斗’高高矗立在房间中央”[21](P106)。1965年至1975年间,随着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的出现与应用,大型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可以由数百或数千个集成电路来合成,计算机的制造成本为此降低了近100倍,由之开启的“微电子革命”(The Microelectronics Revolution)更是将计算机的微型化直接变成了现实,“微型计算机”(Microcomputer)即是“电子工业追求小型化(miniaturize)的必然结果”[22]。有学者认为,计算领域的这场变革取决于两个关键步骤——“小型计算机”(minicomputer)和“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21](P216),无论是前面的“小”还是后面的“微”,首先都指向了空间维度上的压缩。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它在所有方面为消除空间障碍而做出的创新,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都是极具意义的”[23]。算法领域的微型革命使得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机器成功摆脱了空间限制,它不只是固定在厂房或车间里的生产型机器,也不再是放置在机要部门或特定领域的巨型机器。机器自此逐步实践了自身的日常生活革命,由体积变小和重量变轻所带来的空间穿透性,使得机器能够便捷地进入到包括日常生活空间在内的所有现实空间,由此催生了个人计算机、游戏主机、数码相机、移动电话等各种可为普罗大众使用的小型机器,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部分机器甚至能够按照指定程序在不同空间中进行自动切换。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日趋成熟,“微形态”与“大功能”在机器上的结合显得愈来愈突出。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数字技术实际上也体现了某种“空间压缩”,即借助特定的设备将图像、文本、声音、视频等各种信息,统统压缩为机器能够识别的二进制数字,而后经由机器的二进制编码实现信息的解码、拷贝、传送与还原等[24]。很难想象,以前需要整个房间才能摆下的上千本纸质图书,如今通过数字技术,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储存在一个巴掌大小的机器里,机器进步带来的空间压缩不言而喻。
数字、机器与互联网的结合推动了机器进化,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深刻转型,数字资本主义就此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学界习惯将“数字资本主义”的提出追溯至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那里②。20世纪末,席勒出版了《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认为因特网“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范围”,同时还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深化”(deepening of the market),它们共同造就了数字资本主义的诞生[25](Pxiv)。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关涉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著述中,学者们习惯聚焦于席勒对因特网或信息技术的分析,而忽略了席勒对于机器的强调。事实上,席勒通篇都在突显电脑这种机器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的关键作用,由不同电脑借助因特网所组成的电子空间(electronic space)也即“网络空间”(cyberspace)[25](P9)才是数字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活动场域。网络空间是一种由因特网和机器共同建构的虚拟空间,它虽不同于现实空间,但又是现实空间的数字化扬弃,而电脑计算机恰好为数字资本主义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搭建了一个互通桥梁。有异于以往的资本主义,建基于机器生产之上的数字资本主义是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一种崭新的空间话语。
其一,通过机器生产,数字资本主义借助其所串联的虚拟空间来增加和助长资本利润的数字化积累。从最早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到如今的平板电脑,从过去的有线电话、移动电话到现在的触屏手机,机器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数字资本主义对它们一以贯之的情有独钟。马克思提到:“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4](P431),数字机器在信息时代里具备超强的“信息生产力”(Informational Productive Forces),它们的能量远远超出了劳动力的简单堆积,离开了这些机器,资本主义根本无从布局自己的数字劳动、数字剥削和数字控制。机器将资本带到由网络串联的虚拟空间,机器由此成为资本主义向虚拟空间输送资本与输出利益的中转媒介。不同于实体空间,“机器通过传感器产生各种数据,从而模拟和自动化人类体验”[26],因此它不受地理时空的制约,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跨地域、跨空间的互联,如豪斯谈到的:“网络化经济还使原来在空间上相对狭小的市场变成了大市场。距离曾经阻碍了市场空间的扩大,但网络化经济可以轻易逾越地域的界限”[27]。任何空间里的人只要使用机器,就能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版图里盘剥的潜在对象,机器为人们打开了无限可能的虚拟空间,也为资本主义开辟了无限可能的数字阵地。
其二,通过机器生产,数字资本主义得以继续维持和扩张自己在全球地表空间的势力范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以觊觎和侵占他族或别国领土空间作为其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帝国主义时期更是赤裸裸地在全球地表进行野蛮粗暴的空间征服与空间殖民,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批评的:“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不属于你的、遥远的、被别人居住了和占有的土地的谋划、占领和控制”[28]。随着世界各地反殖民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在他国的空间殖民统治逐渐落下帷幕,其空间势力也由此遭到了极大程度的削弱。如何继续维系资本主义在全球实体空间里的强势威权,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机器的批量生产,以“商品”形式将之流通到世界各个地方,从而在机器、使用者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了空间上的有效串联。与此同时,通过高端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将倾注其意识形态的软件、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经由机器分别输送到使用者那里,以虚拟社区和数字平台的形式来对其他领土空间的人们施行抽象的数字化征服,“数字空间的变革使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方式接触全球的顾客”[29],这样也就助长了资本主义话语在全球地表空间的另类殖民。
哈维曾经分析到,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缺乏机器生产的主动性,他们更沉迷于机器具备的生产功能,因此“工业资本家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借钱购买机器,并在机器的整个寿命期内分期偿还债务,要么直接购买机器,并将每年的折旧放在货币市场上赚取利息,直到需要更换机器”[30]。数字资本主义则与之明显不同,它是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互相作用的辩证结合体,而机器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先决条件。出于这个逻辑,数字资本主义必然要极力推崇机器的生产,这种生产显然不只是对机器数量进行简单的扩容,而是从功能、外形、包装与美学风格等多个维度对机器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生产。
三、机器生产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异化
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学者一致认同,“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31](P189)。任何时候,资本主义的残存都离不开“空间的生产”,空间生产促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空间发展被当作整个社会发展的必要环节,而不仅是一个独立要素”[17](P94)。当然,在列斐伏尔建构的空间生产理论中,资本主义主导的空间生产并不仅局限于实践的物质性空间,还包括象征的抽象性空间。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机器生产除了为资本家打通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界限,同时也不断“生产”出各种围绕机器而在的新空间。不同于其它普通空间,这种由机器所生产出的特定空间先天内含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符码,能够更精准、便捷地实现资本主义的各种意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因机器流通而生产的新空间。“从一开始,机器就拥有了制造全新东西的潜力”[31](P508),一旦机器流通到某个空间,这个空间便不再是其所是,它的属性、功能和结构将被重建,因而它被“生产”为一个新的空间。以普通家宅里的房间为例,在机器未流入以前,这个房间只是居住者用来休息或娱乐的日常空间场所。数字机器的入驻将各类数字元素网格化地覆盖到这个空间,像无数条血管蔓延到身体那样蔓延到房间里的每一处。这样该房间作为机器的“因果力”(causal power)③就被赋予了数字化特质,它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只要条件具备,即能迅速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活动场域。此外,经由数字资本主义精心布局的数字技术,也能够在各种机器的协助下潜入到各个空间,将该空间生产为受资本主义掌控与监视的另类空间。
其二,因机器使用而生产的新空间。不同于只为劳力所使用的机器,如今的机器早已面向普通大众,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机器。人一旦开始使用数字机器,机器便会改变使用者所处的特定时空,从而围绕机器使用生产出新的空间。同样以前面的房间为例,当居住者在这个房间使用机器来进行数字劳动、网络消费、移动支付和电子娱乐时,这个空间就已经开始抽离其本原,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数字资本主义促使这个房间成为三重空间的叠合:一是原本用来居住的空间;二是能利用机器来进行数字活动的空间;三是资本主义用来实现其数字生产的空间;此外,机器使用还可生产出各种数字平台空间,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等虚拟社区的流行无不建立在全球人机交互的基础之上。由于机器的微缩化,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机器,即便是在卫生间、火车站、饭店、厨房等功能限定极强的空间里,数字资本主义也能即时生产为其所用的空间。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早有预判,在资本主义那里,“空间形式总会依据既定的生产方式和具体的发展模式来传达和维护其统治利益”[32]。
其三,因机器销售而生产的新空间。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4](P512)。数字资本主义对机器的依赖与推崇注定导致机器的大批量生产,机器从工具到商品的转变反过来对机器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商品的机器,必须要完成审美化包装,加快它们“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4](P512)。因为商品售卖是“在一个给定的速度下商品和金钱在空间和时间里进行的运动”[33],所以机器销售也必然会生产出新的空间,它不仅包括摆放机器商品的商业实体店铺④,还包括经由机器来售卖各类数字产品的虚拟商业平台。为了刺激人们的机器消费,这种空间内构了资本主义的“奇观”(Spectacle)话语,它充斥着“商品化、制造虚假欲望和无处不在的广告”[34]。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机器不断生产和培育这些为其所用的空间,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人类美好生活提供新的可能,而是为自己获取数字化的剩余价值创造新的可能,因而这类空间被数字资本主义化约为“被支配的空间”(dominated space)和“被取用的空间”(appropriated space)[31](P239)。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空间异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人类生活世界触发严峻的空间困境,亟需我们展开批判性的辨识。
首先,数字机器在各类空间进行利益生产的空间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数字机器的根本使命即是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及资本利润,作为商品的机器同时也就不啻为资本主义的利益工具。由于“空间”在人类社会中时常显现为一种“语境假定物”(contextual given)[35],不同语境对空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因而肩负资本主义使命的数字机器一旦进入到某个空间,必定会想方设法地将该空间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专属领地。无论是数字劳动和数字消费,还是数字娱乐和数据收集,其最终目的无不指向了资本主义的利益生产。如此一来,该空间便逐步遭到资本势力的异化,其不仅异化着空间本身,还异化着该空间中的主体对象、社会关系以及生产实践。空间就此披上了资本外壳,成为表征资本主义伦理的抽象符号。
其次,数字机器在全球范围不断寻求空间霸权的空间异化。机器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使得资本主义一方面加速生产与更新各类机器产品,另一方面还要努力确保其机器产品在全球市场空间的强势地位。列宁强调,资本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源自垄断,“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36]。机器垄断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经之路,机器垄断可以确保机器消费和机器使用的垄断,从而也就有利于机器在全球市场谋求的空间垄断。为了维护和延续数字机器的空间霸权,资本主义必定会极力打压其它国家的机器产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批判地指出,即便是数字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所需的基本原材料,都需要依靠对非洲等诸多贫穷地域的掠夺式盘剥,“笔记本电脑、手机、游戏、MP3播放器和网络摄像头等产品含有大量金属。就体积而言,最重要的是铝、铁、铜、镍和锌”,而“非洲国家(刚果、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南非、赞比亚、津巴布韦)是通信技术所需矿物的最大生产国”[37]。
第三,数字机器对人类生活空间施行反向控制的空间异化。马克思提醒,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4](P490)。显然,马克思早已预判到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将带来的不良后果,它并不在意将人从奴化劳动中真正解放出来,相反,它加剧了对劳动者的各种反向奴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肆意侵入到人类生活的每一处空间,这就使得数字劳动和数字剥削彻底摆脱了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将人类变成吸附于机器之上的数字奴隶。更令人不安的是,数字资本主义极力诱导人们沉迷于机器使用,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数字孪生等各类高端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机器被赋魅成无所不能的超级工具,人对机器的过度依赖势必会削弱人的主体性地位,人机关系从“人主动使用机器”让渡为“人被机器所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生活空间也将由此遭受机器的侵扰、监视与控制,成为被机器异化的空间。
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导致的空间异化,依然没有脱离马克思劳动异化的范畴,其归结为一点,即是走向人的全面异化。众所周知,“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被置于‘空间’中的存在,人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展开,空间是人的先天活动场域”[38],因此空间异化最终也会造成“空间人”的异化。透过前文分析可知,数字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的目的是利用机器将资本主义话语输送到任一空间中,从而维系与巩固它的空间利益与空间霸权。这样,空间就不再围绕主体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存需求而呈现自我,它不仅成为了被资本主义势力异化的场域,同时还化身资本主义异化主体人的工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该清晰认识到,伴随着各种高新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数字化时代,数字机器由此也变成人类必须面对和接纳的对象。事实上,数字机器如今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合理地利用数字机器,对于人类世界有着非常积极的正面意义。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数字机器本身,而在于如何使用和为何使用数字机器。数字资本主义为机器注入了独特的意识形态编码,使得机器悖离了其自身,沦为服务于资本主义利益扩张与数字殖民的奴仆。因此,为避免数字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跨空间的势力渗透,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快机器领域的自主创新,减少在关键技术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全球加速的数字时代里强化机器生产与机器应用的安全屏障;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全社会积极宣传和倡导健康的机器意识,防止人们过度沉溺于数字机器及其营构的虚拟空间,积极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侵蚀与数字同化。
注:
①这里的“好机器”(good machine)一词,借用自尤尔(Andrew Ure)的《工厂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一著,用来形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中那种能够产生巨量效益且符合资本家理想诉求的机器。马克思非常重视尤尔的理论文本,在《资本论》中探讨机器问题时,马克思反复引用尤尔的著作。参见:Ure A.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M].London:Charles Knight,1835.32.
②在席勒之后,道森(Michael Dawson)和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出了“虚拟资本主义”(Virtual Capitalism),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提出了“高科技资本主义”(High-Tech Capitalism),乔蒂·狄恩(Jodi Dean)提出了“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还提出了“MP3资本主义”(MP3 Capitalism),但这些概念都不如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更具影响力和传播度。
③“因果力”(causal power)由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厄里认为,空间具有作用是因为它朝向的对象具有某些特征,这些对象构成了空间的因果力。参见:John Urry,“Localities,Regions and Social Class”,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1,(5):455-474.
④譬如美国苹果公司分布于全球各大城市的“Apple Store”实体直营店。苹果实体店的一大特色,即是将iPhone、MacBook、iPad、iPod等各种机器商品精心摆放在宽敞的空间中,顾客一进入这个空间,即可看到这些机器并随时试用这些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