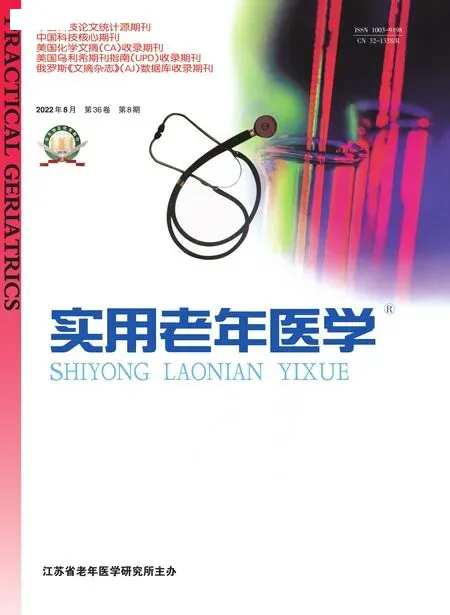衰弱综合征与老年肺部感染
许伟 吴剑卿
肺部感染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是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最常见的始动因素;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肺炎起病隐匿、临床表现不典型、合并症多、病原体复杂,易延误诊治,增加短期和长期病死率[1]。衰弱综合征是老年综合征的核心,衰弱指数(frail index,FI)作为生物学年龄的替代指标,已在欧美用于预测老年人的全因死亡率[2]。受衰弱和失能影响,老年人肺部感染是住院最常见的诊断之一;感染与衰弱在病理生理路径上反复交互,可能引发恶性循环;肺炎会增加衰弱的严重程度,反之,衰弱与老年人肺炎的易感性和严重程度密切相关[3]。当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的背景之下,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发布了COVID-19管理快速指南,建议使用临床衰弱评估指导≥65岁老年病人的危险分层和监护升级的临床决策[4]。基于现有的文献,本文就衰弱综合征与老年肺部感染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衰弱的概述
衰弱综合征是指一组由机体退行性改变和多种慢性疾病引起的机体易损性增加的综合征;其核心是老年人生理储备减少或多系统异常,外界较小的刺激即可引起负性临床事件的发生。衰弱涉及多个系统失调,具有多因素病因,因此存在广泛的临床表型。尽管衰弱有多种定义和概念框架,但学者对衰弱的三个特征基本达成共识:(1)衰弱发生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衰弱水平随机体老化而提高,但并非呈线性关系;(2)衰弱是多维度的,涉及不同的功能领域,如生理衰弱、认知衰弱、社会心理衰弱和营养衰弱;(3)衰弱是动态的,纵向研究提示,基于衰弱表型的衰弱状态之间常相互转换[5]。
衰弱是老年综合征的核心,是尿失禁、跌倒、谵妄和抑郁等其他老年综合征共同的危险因素,彼此相互促进,最终促成了失能、住院、死亡的发生;高龄、跌倒、疼痛、营养不良、肌少症、多病共存、多药共用、活动功能下降、睡眠障碍及焦虑、抑郁等均与衰弱相关。研究发现,相较于多病共存、失能等老年综合征,老年人衰弱状态常和其他老年综合征重叠;但相对其他老年综合征,衰弱可防、可逆。
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共纳入51万余名研究对象分析FI 与全因死亡和死因别死亡风险的关联,揭示了在中老年人群中利用FI 开展风险评估、指导预防的价值[6]。
2 衰弱与感染双向关联
衰弱和感染是双向联系的,既是相互的危险因素,又是彼此的后果。研究表明,衰弱的潜在机制可能归因于年龄相关的或疾病相关的变化,或者两者的结合。衰老的细胞特征包括干细胞衰竭、细胞间通讯改变、基因组不稳定、端粒磨损、表观遗传改变、蛋白平衡丧失、营养感知失调、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细胞衰老。这些细胞机制加上低体力活动水平和营养不良是导致诸如慢性炎症、免疫衰老等衰弱病理生理学变化的重要原因[7]。
流感、其他病毒性肺炎(如冠状病毒)和细菌性肺炎等急性感染的炎症反应几乎影响所有的器官和系统。首先,在感染期间,机体下调生长因子,抑制受损大分子和细胞器更新的合成代谢信号,从而导致组织中未修复的损伤逐渐积累。其次,伴随急性感染的炎症反应和体力活动缺乏,可能加重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和肌肉萎缩,同时,热量和营养摄入不足进一步对机体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第三,感染可能通过触发特定病理状况,间接地促进衰弱状态[3];荟萃分析表明:近期呼吸道感染与心肌梗死风险增加相关;接种流感疫苗可将近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病人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55%;有趣的是,接种流感疫苗被证明可以有效预防心肌梗死[8]。此外,肺炎相关的缺氧、感染诱导的持续促炎状态和氧化应激可能通过增加β-淀粉样蛋白沉积和小胶质细胞激活来触发或加速神经退行性过程,增加认知衰弱的风险[9]。与此同时,衰弱的个体更容易发生感染,更有可能经历漫长且复杂的临床过程和慢性并发症。
3 免疫衰老参与衰弱和感染
尽管多种机制导致衰弱,但与年龄相关的免疫变化,即免疫衰老,似乎起着核心作用[10]。免疫衰老的特点是免疫系统功能受损和失调,包括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并且伴随着慢性低度的全身炎症状态,导致机体促炎和抗炎平衡的失调,即炎症老化。免疫衰老和炎症老化相互促进,参与老年人群中发生的大多数病理状况,如增加感染风险、降低疫苗接种的有效性[11]。
在先天性免疫方面,老年人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吞噬作用和杀菌活性降低;在适应性免疫方面,幼稚T细胞数量逐渐减少,功能失调的记忆T细胞增加,T细胞受体多样性下降和原发性淋巴器官退化;适应性免疫反应受损可以加强对先天免疫反应的刺激,导致促炎细胞因子释放;促炎分子的释放增加又会对适应性免疫反应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可以解释老年人对感染性疾病的易感性,尤其是由肺炎链球菌和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3]。而重要的感染屏障,如咳嗽反射和发热,也受到免疫衰老的影响。
研究表明,表征老化免疫细胞的分子生物学改变与其他系统和器官(如肌肉)在一定程度上重叠,被确定为衰老的标志;其中,自噬缺陷和线粒体功能障碍被认为与免疫衰老高度相关;这些分子生物学变化很大程度上与衰弱的发生发展有关[12]。此外,潜在的炎症机制还包括基因组不稳定性、微生物群组成变化和NLRP3炎症小体激活等[13]。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炎症在衰弱中的作用,其特征是促炎细胞因子如IL-1β、IL-6和TNF-α以及CRP水平升高;而抗炎细胞因子水平降低,如IL-10和IL-1受体拮抗剂。中性粒细胞是组织修复的核心,新近研究表明,衰弱老年人群的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细胞数量有所增加,但趋化能力大大降低,因此,中性粒细胞在迁移时会产生更多的组织损伤和继发性全身炎症[14]。炎症导致老年人基础疾病的临床特征复杂化,增加分解代谢的能量失衡并干扰稳态信号,促进具有加速衰老特征的综合征(如衰弱、肌少症)的发生发展。
4 衰弱的评估及优化
目前,衰弱评估的方法较多,尚无公认的衰弱风险评估金标准,也尚未发现识别衰弱的最佳生物学标记物和干预靶点[15]。Fried衰弱表型评分操作简单,包含5种生物表型,但该评估方法未纳入心理、社会因素等重要变量。临床衰弱量表(CFS)通过简单的问题来度量9个衰弱等级,即使在急性疾病期间也能够基于家庭成员提供的病史进行评估而被广泛使用。
以个体健康缺陷累积数量与疾病严重程度为基础的FI模型要求评价指标涵盖症状、体征、辅助检查、躯体功能和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其能更好地区分中度和重度衰弱并预测临床预后;但FI评估过程稍繁琐,限制了其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Rockwood 等提出了基于老年综合评估(CGA)项目计算FI 的模型(FI-CGA)。FI-CGA 包含10个方面的功能损伤指数和共病指数,受试者健康缺陷越严重,其数值越大[16]。FI-CGA 和FI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Blodgett 等[17]建立了基于常规实验室检验结果的衰弱指数(FI-Lab)模型, FI-Lab 相较于基于自我报告的临床衰弱指数(FI-Clin)提高了预测住院、用药、骨折、跌倒、死亡等不良事件风险的效能,有助于亚临床衰弱的检出;联合FI-Lab 和FI-Clin 评估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不良事件的预测效度。
大多数学者在临床研究和临床评估中采用Fried衰弱表型和FI 模型以及由此衍生来的70多种评估工具,以量化老年人的健康状态。目前,衰弱评估已在欧美等国家的社区医疗、急诊医疗、围手术期医疗、重症医疗及部分疾病诊疗中选择性的应用[15],但其在我国老年人群中的适用性研究仍相对较少。
5 衰弱与老年肺部感染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衰弱和老年肺部感染的临床研究结果尚存在争议。Kundi 等[18]对270 308例 ≥ 65岁老年肺炎病人进行医院衰弱风险评分(HFRS),发现与HFRS<5分者相比,HFRS≥15分的病人30 d内再住院率、死亡率明显增加;将HFRS加入传统的基于共病的风险预测模型(CCI)中,有助于提高对老年肺炎预后的预测。日本一项多中心的横断面研究发现,衰弱增加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易感性和严重度[19]。来自韩国老年CAP病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提示, FI评分为目前广泛使用的肺炎严重程度评估(CURB-65评分和PSI评分)提供了附加的预测价值[20]。土耳其一项全国性队列研究发现,2个基于国际疾病分类编码的FI与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和肺炎住院病人的一年再入院率和死亡率以及长期死亡率密切相关[21]。另一项来自我国的纳入256例 ≥ 65岁老年肺炎病人的前瞻性研究也揭示了衰弱对老年肺炎病人长期预后的预测价值[22]。
然而威尔士的一项纵向队列研究结果显示,衰弱和共病是老年肺炎病人入院的重要危险因素;在预测住院死亡方面,基于CCI的共病模型和基于HFRS的衰弱模型的预测价值相似;对于长期疾病转归的预测,共病模型更优[23]。
6 衰弱与重症监护资源分配
目前,老年病人肺部感染预后评估的准确性显著低于年轻病人。大多数预后评估工具将年龄作为危险因素,当病人病情严重程度相近时,老年病人得分更高,预计死亡率更高,对ICU等高级医护资源的需求更高[1]。与年轻病人相比,ICU在多大程度上使高龄病人获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根据病人的意愿、短期和长期预后、ICU治疗获益可能性等多维度评估老年肺部感染病人的病情,制定治疗决策,显得尤为重要。大约1/3的ICU病人在住院前已经衰弱,这增加了病人短期和长期的残疾与死亡风险,入院时衰弱筛查已被建议作为危重病人护理的常规部分。
当前,COVID-19的流行再次迫使各国考虑升级重症监护治疗的临床决策。众多衰弱的研究旨在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储备和不良预后风险,而不是实际年龄,进行危险分层和重症监护资源分配。研究发现,在非COVID-19相关的ICU治疗环境中,CFS≥5分与40%~60%病人的30 d死亡率相关,而较低水平的衰弱老年病人具有较好的临床结局。一项来自欧洲11个国家63家医院开展的多中心队列研究,旨在调查COVID-19 病人中CFS评分与住院死亡率和进入ICU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所有年龄的衰弱病人住院死亡率和进入ICU的风险均显著高于非衰弱病人;而对于≥65岁的病人,衰弱病人和非衰弱病人的重症监护比例无显著差异;作者推测CFS评分是COVID-19病人住院死亡率的风险标志物[24]。另一项来自英国最大急诊科的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使用电子健康记录调查不同程度衰弱对老年住院肺部感染病人预后的影响,发现衰弱仍然是预后的重要标志[25]。还有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170个ICU的对非COVID-19肺炎病人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提示:非衰弱(CFS=4分)和轻度衰弱(CFS=5分)病人的死亡风险相似,仅重度/极重度衰弱(CFS≥7分)与死亡风险相关;该研究不支持单独以CFS≥5分指导重症监护资源的分配[26]。研究对象的异质性、评估工具的差异、研究终点的不同设置,可能是当前研究结果有分歧的主要原因,亟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证据。
近年来对衰弱的定义、评估、识别和干预的生物学基础和临床转化等方面的认识和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当前衰弱领域仍然存在巨大知识缺口。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需要专注以下几点:阐明肺部感染与衰弱的直接因果关系,以及其潜在病理生理和分子生物学机制;利用组学技术、成像技术等提高衰弱机体成分测量的准确性,探索血液和(或)器官特异的衰弱生物学标志物;提供个体化的衰弱管理策略:如制定肺康复处方、连续化一体化多模式护理、个性化疫苗接种等。总之,高度重视衰弱的识别和防治既是中国健康老龄化面临的挑战,也是未来的机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