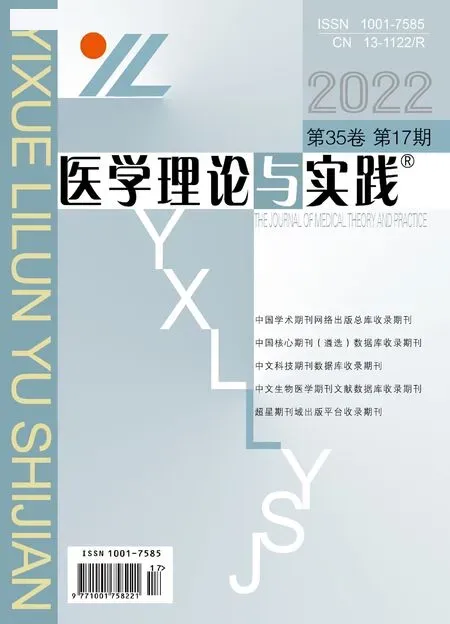胶质瘤术中肿瘤边界确认技术的研究进展*
王 维 陈 聪 王 亮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300450
胶质瘤是颅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目前胶质瘤的治疗方案为最大安全限度地切除肿瘤后再接受同步放化疗,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可以减少肿瘤残留,降低复发率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1]。由于胶质瘤侵袭性强,其生长过程中经常向周围脑组织侵袭,常规手段难以检测肿瘤的边界。随着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胶质瘤的术中检测技术也不断更新,以帮助术者在胶质瘤手术时更好地做出决策。近年来,由于生物信息学的发展,胶质瘤的特异分子标志物不断被挖掘出来,与此同时,传统影像学结合这些特异分子标志物来更为精准地检测肿瘤边界,一些新的技术也在不断涌现。本文将对传统影像学及一些新兴辅助检测技术的应用及其优缺点进行综述。
1 术中导航
现阶段的手术辅助技术多依赖影像导航,多模态影像融合可以将脑组织、血管、功能、代谢影像进行融合及三维重建,引导术中肿瘤切除,为术中及术后肿瘤切除程度做对比。一般来说,低级别弥漫性胶质瘤的影像范围由T2/FLAIR界定,高级别胶质瘤由T1对比增强界定,而代谢影像MRS 及PET将肿瘤边界从“影像学边界”扩大到“代谢边界”,进一步提高了肿瘤切除率[1]。收集患者的影像数据,整合注册到导航设备,术前在手术室再将整合的影像数据与患者进行匹配,术中向术者提供跟踪和定位功能[2]。尽管这一系列的影像融合能在术前帮助术者完成定位,确定手术切除范围,制定手术计划,但其在术中却因不可避免的脑移位而受到限制。Ian J Gerard等对术中脑移位做了综述[3],他将引起的原因分为物理、手术及生理因素,随着手术的进行,可能发生导航设备的偏移,脑脊液、脑组织的丢失等都可能引起术中的定位与术前的影像数据发生偏移,不同脑部位出现的平均偏移量为1.2~20mm,显然导航技术在术中无法为术者提供准确的信息。
2 术中核磁
术中导航对肿瘤手术边界的确定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不可避免的脑偏移使其在术中的应用受到限制。术中核磁能为术者提供实时的影像与三维重建,指导调整手术方案,而恶性肿瘤需要术后72h内复查MRI评价手术切除程度。术中核磁为术者提供肿瘤切除程度的客观影像证据,早期发现术中并发症,如脑出血、脑梗死等。Christian Senft等[4]以常规显微手术为对照,进行iMRI的RCT研究,结果iMRI组 VS Control组GTR:96%VS 68%,P=0.023,相对于单用导航技术,联合术中核磁的总体切除率和无进展生存期都有所提升。
术中核磁发展至今,其临床价值已从简单的解剖结构影像,向整合脑功能、肿瘤组织形态、生物学特征和血流动力学信息方向转变。Stephan Ulmer等[5]证实术中高磁敏感增强MRI(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SC-MRI)的可行性,DSC-MRI是通过输注MRI对比剂,以T2WI梯度回波序列为基础,利用磁共振快速扫描技术,反映组织毛细血管水平的血流动力学情况,可快速无创地评价局部微环境内的血流动力学变化。DSC-MRI常用于胶质瘤的诊断、鉴别诊断、肿瘤分级及术后疗效评价,其具有快速、简便、可靠的临床应用价值。
术中核磁最显著的优点是术中可以得到高分辨率及高辨识度的影像资料,一般来说,术中核磁通过术前及术中的影像对比判断肿瘤的切除程度,有些方法可以辅助肿瘤切除程度的判断,包括不同的造影剂、术腔滞留造影剂的灌洗和吸引设备等。瘤腔中的血液成分,如各种手术止血材料吸附的血液,会使T1信号变短,如果不与术前T1成像进行比较,也会被误认为是局部增强,在术中核磁的应用中存在干扰因素较多。另外,术中核磁需要对手术室进行改造,且需要配套的器械,低场强核磁耗时短,费用稍低,但其只能提供简单的解剖学影像,高场强核磁可以提供整合脑功能、肿瘤组织形态、生物学特征和血流动力学信息,但更多的数据采集意味着术中耗时更多。另外,术中核磁费用高昂,根据场强的不同,术中核磁的搭建费用从300~800万美元不等[6]。
3 术中超声
术中核磁能在术中提供高分辨率的影像,但其对手术室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用。术中超声显示颅内病变的位置、大小与术前CT或MRI吻合度极高,很少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且其具有无创性[7]。术中超声为胶质瘤手术提供了一种便携经济的技术,3D超声能为术者带来更直观的影像,简单识别脑组织,促进肿瘤切除,评估肿瘤残余,改善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生活质量[8]。术中超声的特点为便携、实时且经济,与其他术中影像技术相比,其可实时成像,手术流程无影响,术中可反复进行。其局限性主要为图像质量参差不齐,术中出血、水肿对其干扰较多,使其无法再准确向术者提供残余肿瘤信息。术中超声的敏感性及特异性会随着手术进行而下降,手术切除开始之前最高,在其他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变化的客观存在[9]。另外,术中超声易造成伪影,其主要原因是术腔血液、冲洗液与脑组织的衰减差异较大,对术区超声成像影响较大,通过适当的技术和方法,我们有可能将这些伪影最小化[8]。
4 荧光成像
近年来,术中荧光成像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荧光素钠、吲哚菁绿、5-ALA已用于胶质瘤领域并展现出临床效果。注入荧光显色剂后,试剂可在肿瘤区域富集,术者可通过转换显微镜激发荧光从而获得肿瘤区域边界。其中,荧光素钠和吲哚菁绿的机制为可以透过肿瘤区域受损的血脑屏障进入脑实质,在正常区域则无法透过血脑屏障,因此在显微镜下肿瘤出会被激发荧光,可引导术者进行切除。但是这种机制并不能达到“肿瘤细胞特异性”,其缺点很明显:首先在血管增生不活跃、血脑屏障破坏较少的低级别胶质瘤中应用受限;其次手术过程中人为造成的微血管破坏会引起荧光显色剂的渗漏,造成术者对肿瘤区域的误判,且随着手术的进行愈发严重。5-ALA为血红蛋白代谢的中间产物,肿瘤细胞会增加对其的摄取,5-ALA在肿瘤细胞中转换为原卟啉Ⅳ,亚铁螯合酶的相对不足造成原卟啉Ⅳ向血红素的转换延后,通过荧光照射可激发出荧光[10]。由于荧光物质在肿瘤细胞内合成,所以并不存在荧光素钠这种依赖血脑屏障破坏的荧光试剂在手术中出现污染手术视野的情况。但是,在肿瘤的边界区域,由于肿瘤细胞密度低,混合了部分正常细胞,在荧光激发后,呈现出微弱的粉红荧光,针对粉红荧光区域的去留已有不少研究,但结果具有争议,且5-ALA在低级别胶质瘤中也存在这一问题。荧光成像技术在术中为术者提供更直观的肿瘤区域,通过荧光成像术中快速切除肿瘤,相对于传统成像模式,其操作性十分占优,但由于荧光试剂存在一定的漏洞,荧光素钠并没有直接靶向于肿瘤细胞,其特异性低导致在术中出现干扰而迅速被淘汰。5-ALA相对于之前的荧光成像,能直接靶向于高代谢的细胞,但其在转换为荧光信号的分辨率不足以让术者确定肿瘤的切除边界,而且其目前在国内的试剂来源亟待解决。
5 光学成像
拉曼散射是一种新型的光学成像技术,在成像过程中,光子与介质分子之间发生非弹性碰撞,能量交换产生的效应称为拉曼散射。在拉曼散射效应中,散射光子的能量和介质分子相关,以此为基础,通过采集特定区域的拉曼光谱进行分析获取该区域的各类分子成分信息。
以拉曼散射为基础拓展出的受激拉曼散射(Simulated Raman scattering, SRS)近年来在生物医学领域开始广泛的研究。相比于脑细胞,胶质瘤细胞在分子水平上拥有更多的蛋白质和核酸,脂质成分相对较少,针对胶质瘤的SRS基本成像思路是通过检测蛋白质、核酸及脂质的比例来鉴别肿瘤细胞。2017年,李聪教授团队发表关于SERS的两篇研究成果,SERS是通过吸附在某些金属分子表面从而达到增强拉曼散射的表面敏感技术,可以实现对单分子的检测。通过SERS 设计出针对EGFR Ⅷ和H+的金纳米探针,通过对EGFRⅧ的检测实现对EGFR Ⅷ突变阳性的胶质瘤鉴别[11]。而对于H+的检测则可以获取肿瘤组织中的酸度信息,因为胶质瘤特别是高级别胶质瘤的微环境往往都是酸性的,所以通过酸度信息便能获取到胶质瘤的微环境边界,实验证明通过术中应用手持拉曼扫描仪的荷瘤小鼠肿瘤达到完全切除。李聪团队于2020年设计了基于酸性金纳米探针的手术过程,与目前通过MRI勾勒胶质瘤边界的手术策略相比,显著延长了胶质瘤模型的生存时间并降低了手术导致的神经功能损伤[12],至此,拉曼散射应用于胶质瘤的临床研究成果展现了良好的前景。
6 其他技术
6.1 术中采样 术中瘤腔多点采样快速病理可获得最高的诊断准确性,但其取样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不连续的,即使快速冰冻病理检测,其时间成本也颇高,因此该方法更多地用于术后瘤腔边缘是否残留,评价手术及预测患者预后。随着各种检测设备的研发,术中获取样本病理信息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在诊断准确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时间成本可能会让术中采样在以后的手术中得到广泛应用。
6.2 术中MRS、PET-CT 术前的MRS和PET-CT可以很好地定位到胶质瘤的“代谢边界”,MRI联合PET-CT能提供胶质瘤边界更准确的信息[13]。但是目前尚无此类技术应用于术中的文章发表,在术中通过MRS和PET-CT确定胶质瘤的“代谢边界”以指导手术切除尚处于理论阶段。
7 总结
对于胶质瘤患者,手术全切获益已经得到证实,如何在术中获得精确的肿瘤病理学边界,实现肿瘤细胞的清除,杜绝肿瘤进展及复发,是神经外科医生的美好愿望,也是一大挑战。我们必须在扩大肿瘤切除的潜在获益与引起神经功能缺损及生活质量下降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这要求对每种技术的获益与风险进行客观评估。在临床上,各种应用技术的风险与获益评估是很困难的,我们总是需要多种技术来为每一个病人争取最良好的预后,因此,本文针对每种技术综合阐述其优缺点及曾经各自单独应用于临床时产生的临床效益进行综述,以期指导临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