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与君共考古 夏鼐与吴金鼎的交往
文图/袁博 徐小亚
夏鼐(1910—1985)与吴金鼎(1901—1948)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说来也巧,夏鼐与吴金鼎充满了相似性。比如在名字上,夏鼐(鼐即大鼎之意),字作铭;吴金鼎,字禹铭。二人都曾就读于清华大学,都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前辈的热切期盼下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导师都是叶兹教授,归国后都曾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考古事业上,二人也都以顶尖田野考古成就而著称:吴金鼎被誉为“田野考古第一”;而夏鼐的考古技术也被认为在老一辈考古学家中无人可出其右。考古是连接二人的纽带,两人因考古而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长达13 年的时光里互相勉励、共同奋斗,将诞生之初的中国考古学推向了高峰。

1925 年冬摄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前排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
殊途同归
虽然两人最终都走上了考古之路,但过程却极不一样。吴金鼎是接触到考古之后,便将考古视为了自己的第二生命,从此便致力于考古事业;而夏鼐则不一样,他走上考古之路更多是命运无奈下的选择,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了考古学的魅力和意义,最终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的泰斗。
1921 年安特生发掘并命名了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在当时疑古思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上古史系统受到极大冲击。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1925 年,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想要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大师。当时的李济从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归来,主要教授人类学和考古学。1926 年,吴金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届36 名学生,只有他一人选择了考古学。在李济的指导下,吴金鼎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缺乏考古材料,他并没有写出考古学论文。1928 年,吴金鼎从清华大学肄业,受聘于齐鲁大学,但他始终钟情于田野考古,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考古调查。1928 年3 月—1929 年10月,吴金鼎6 次到济南平陵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龙山遗址。他将这一发现报告给李济,当时在殷墟发掘遇到困难的史语所立即将力量投入其中。1930年11 月,吴金鼎参与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并正式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此后的日子里,吴金鼎先后参与了殷墟、四盘磨、后岗等遗址的发掘,还在鲁南和鲁东等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撰写了多篇考古文章,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的主要撰写者。李济在序言中写道:“初稿大部分是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页费时很久。”

夏鼐

吴金鼎
吴金鼎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和赞许。在傅斯年的大力举荐下,吴金鼎获得山东公费留学的名额。1933年7 月,吴金鼎和妻子王介忱前往伦敦大学,在叶兹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考古学。吴金鼎不负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期望,留学期间十分刻苦努力,极看不起那些荒废学业、纸醉金迷的留学生。在长期的考古学习实践中,吴金鼎决定以陶器为切入点,讨论“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问题,将毕业论文确定为《中国史前陶器》。1935年5 月17 日,他回国搜集论文材料之时,在殷墟遇到了初次进行考古实习,等待下半年出国留学的夏鼐。
在见到吴金鼎的前几天,夏鼐还在日记中抱怨:“我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作考古学家,但是命运却偏与作对……我恨不得赌气放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着命运的摆布了。”要理解夏鼐为何抱怨,就要从他走上考古道路的经历说起了。
1930 年,22 岁的夏鼐考入燕京大学,不久后便转学清华大学,在短暂纠结后,最终选择走上史学道路。他当时的兴趣和主攻方向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经济史和外交史,其毕业论文便是在蒋廷黻指导下写成的《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1934 年元旦,夏鼐在日记中写道:“今年也许是我的生活史上划时期的一年,至少可以说,我一生的事业是决定于今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是他的毕业之年,如果按照当时的方向走下去,也许夏鼐会在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近代史学者,可命运却偏偏引导他走上了考古之路。当时的夏鼐同如今的大学毕业生一般,也担心着“毕业即失业”,摆在他面前的只有出国留学、进研究院、找工作三条路,志在升学的他更倾向于出国。1934 年清华历史专业有两个留学生名额,分别是美国史和考古学,夏鼐最终选择了考古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取留学资格。获知这一消息后的夏鼐是彷徨无主的,他内心还没有完全接受学习考古学的事实。
1935 年夏天留学之前,在多方询问和思考之后,夏鼐决定前往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也正是在这次实习中,夏鼐确定了前往伦敦大学留学的选择,这为其与吴金鼎相识提供了契机。此时的吴金鼎一心想要在考古上做出一番事业,而夏鼐仍然对于是否要从事考古心存疑虑。但无论如何,正是考古让二人得以相识。
留学生涯
刚刚大学毕业的夏鼐比较腼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也多是倾听他人的见解。此时的吴金鼎有着丰富的考古经历和留学经历,这些对于初入考古之门且即将出国留学的夏鼐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殷墟的两次交流,主要是“出国以前之预备及出国后之一切情形,承其详细指导……”,“听吴金鼎讲述陶器制作法,并述及近来考古学趋势……”。
在留学英国后,夏鼐常与吴金鼎一起学习、做实验、聚餐、游玩、聊天。吴金鼎的经历与学识,深深地吸引着夏鼐,并对夏鼐的学业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夏鼐在日记中多次写道:
“与吴金鼎同赴不列颠博物馆……随便谈论中国考古的情形。”
“下午赴吴君处闲谈,又说起中国考古界的情形。”
“下午至吴禹铭君处谈话,畅谈国内考古学界情形。”
“邀吴君夫妇及曾君聚餐顺东楼,闲谈国内考古界情形。”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两人的聊天多以“谈锋甚健”的吴金鼎为主。他们围绕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共同关心着国内考古事业的发展,并对国内尚不规范的田野发掘工作极为忧虑。一次,二人的老师李济来英,夏鼐便表达了对于殷墟发掘的不满。李济无奈地回答:“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正是这些交流,让二人坚定了学术报国的决心。
夏鼐留学英国后,和吴金鼎一样,也追随叶兹教授学习中国考古学。但夏鼐对“有名无实”的叶兹教授十分不满,认为他并不能帮助自己增进学术能力,白白浪费时间。所以,到英国后不久,夏鼐便下定决心离开叶兹教授,延长留学年限,改学埃及考古学。在写给梅贻琦的信中,夏鼐三次提到吴金鼎,认为吴氏跟随叶兹教授三年,都未有头绪,未能完成研究目标,可见导师和研究方向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从而请求梅贻琦同意他的申请。由此可见,与吴金鼎的交流和对其经历的借鉴,是促使夏鼐下定决心改换导师与所学方向的因素之一。最终梅贻琦、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都同意了夏鼐的请求。正是这一决定,使夏鼐成长为我国的“埃及学之父”,对夏鼐的学术道路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夏鼐对于吴金鼎选择叶兹教授也分外惋惜,他坦言道:“(吴金鼎)跟了叶兹教授习中国考古学,不过为得博士头衔而已,论叶兹教授的学问,哪里配做他的导师。”但他也十分能够体谅吴金鼎的难处,只是为中国考古学的长远发展而感到可惜:“一个人到了中年,饱受由于没有外国洋博士学位受歧视的刺激,自然要顾功名,不能像傻子一般专为学问干,这又何能怪他!不过,为中国考古学的前途着想,未免为之惋惜而已!”
1937 年,吴金鼎将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的稿子交给夏鼐求取意见。夏鼐和李济的意见相仿,认为此篇论文“用力颇勤,而所得并不多,结论之年代比较,更多悬空忖想,不着实际”。这并不是夏鼐对于吴金鼎有偏见,事实上,夏鼐十分赞赏吴氏,他说:“吴君人很忠厚,读书很用心,田野工作也很能吃苦,是不可多得的考古学人才。”夏鼐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正是说明他为人坦荡,实事求是,在学术面前不愿丝毫虚伪作假。吴金鼎是否采纳了夏鼐的意见不得而知,但从夏鼐后来对于吴氏论文的评价—“他的这一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的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在还没有人出来再做这样的综合的工作以前,吴先生这部书,仍不失为最详尽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参考书”来看,他还是很认可吴氏的成果的。
与君共考古
1937 年吴金鼎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而夏鼐则仍在国外留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吴金鼎在西南地区大展拳脚,1938—1940 年间发掘了洱海等遗址,将所学尽情挥洒在祖国的大地上,实现自己学术报国的理想。此时的夏鼐也在埃及、巴勒斯坦等地进行考古实习,并在开罗博物馆从事了一年的考古研究工作。二人虽远隔万里,但常有书信往来。吴金鼎盼望夏鼐早日归来,加入国内考古工作,他在给夏鼐的信中写道:“苍岩云欲往,洱海月长流,佳景如斯,才堪考古;中土燎方扬,西溟波复起,大功成矣,何不荣归。”
夏鼐回信:“吴老板开张之喜,掌柜有贤妻,伙计是良朋,如此搭配,若君真堪考古;桐棺作徐塌,广厦多臭虫,尚待须臾,则我亦将归来。”两人的惺惺相惜之情跃然纸上。

彭山崖墓考古队人员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冀、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发掘彭山崖墓时夏鼐抄录的有关文献资料手迹
1941 年初,夏鼐终于回国,他的归国首秀,便是与吴金鼎、曾昭燏、高去寻等人在彭山县豆芽房、寨子山发掘汉代墓葬。两位田野考古大师终于迎来了“合体”。此次发掘工作,吴金鼎为团长,夏鼐则是他的得力助手,两人搭配十分默契,稍摘录一段《夏鼐日记》1942 年的记录便可见一斑:
“9 月23 日,吴禹铭君脚气病稍痊,试步下山,偕赴江口镇。”
“9 月25 日,与吴禹铭君同赴李家沟,其间崖墓颇不少,规模与在寨子山者相似,多数未经近人扰过。”
“9 月26 日,与吴禹铭赴寨子山,拟再挖一二墓,与工头包工议价不合,决定暂时放弃此间。”
“9 月27 日,与吴禹铭赴江口镇,与镇长商谈,拟开掘豆芽房沟及止观亭附近之崖墓。”
“9 月28 日,与吴禹铭同往豆芽房视察崖墓,以便选定其一,明日开工。”
“9 月30 日,下午与吴禹铭赴双江镇小学,晤及刘绍光先生”。
“10 月1 日,上午与吴禹铭君同赴插旗山及纱帽山,视察崖墓。”
“10 月5 日,上午与吴禹铭君至江口镇,接洽禁止王家沱石厂之擅毁古崖墓,及保存已取下之双羊刻石。”
“10 月9 日,下午在家中刷洗陶片,并与吴禹铭、冯汉冀二君商酌发掘成都琴台事。”
“10 月27 日,吴禹铭君身体不适,上午代替之至豆芽房监视No.167、168之发掘。”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1944 年3 月,夏鼐参加西北考察团,将前往甘青地区进行考古工作。在临出发之际从傅斯年处得知吴金鼎因一些原因辞去史语所职务,投笔从戎,进入军委会战地服务团的消息。震惊之余,他向李济询问细节,并致信吴金鼎以挽留,只可惜并未劝回吴金鼎。自此以后,吴金鼎彻底离开了考古界,而夏鼐则在甘青地区取得了重大考古成就。在齐家文化的墓葬中,夏鼐发现了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地层学证据,“从而否定了安特生关于甘青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这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这是夏鼐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1944 年4 月夏鼐刚到兰州不久,便去寻访吴金鼎的堂弟吴良才。吴良才对考古十分感兴趣,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初,尚在金陵大学农学院读书的他便在南京北阴阳营的大土丘上捡到了史前遗物。此时的吴良才正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他不仅将早年在南京北阴阳营的发现告知夏鼐,还将自己在兰州附近和渭水流域的调查发现分享给夏鼐,并陪同夏鼐考察兰州附近的遗址。夏鼐在兰州的生活与出行也多受他的照顾。西北考察结束后,夏鼐便是在吴良才草稿的基础上完成了《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一文。1947 年3 月29 日,夏鼐想起吴良才的提示,还亲自前往南京北阴阳营考察史前文化堆积。另据苏秉琦所说,1945 年底,在北京公办的吴良才还在琉璃河附近发现西周陶片并告知他,成为日后探索琉璃河遗址的重要线索。或许是受堂兄吴金鼎的影响,对考古工作十分关注的吴良才不仅通过实地调查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了贡献,并与两位考古泰斗结缘,实是一段佳话。
最后的时光
1946 年2 月,阔别已久的二人在重庆相逢,一同去看望卧病在床的梁思永,梁思永知道二人要来探视,“甚为兴奋”。当夏鼐讲述西北考察经历,并出示照片、拓片等传看时,不知吴金鼎内心又是何想。
离开史语所的吴金鼎,曾多次想要回归田野考古,却始终未能如愿。1946 年3 月,将考古视为第二生命的吴金鼎回到齐鲁大学。1948年9 月18 日,吴金鼎因胃癌病逝于齐鲁大学,终年48 岁。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吴金鼎是不如愿的,他在寄给夏鼐的信中写道:“到济后即如加轭之牛,除饮食外,几无余暇。”而他所心心念念的便是和夏鼐等人一起进行考古工作,如他在给夏鼐的信中还写道:“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如今读来,实在令人唏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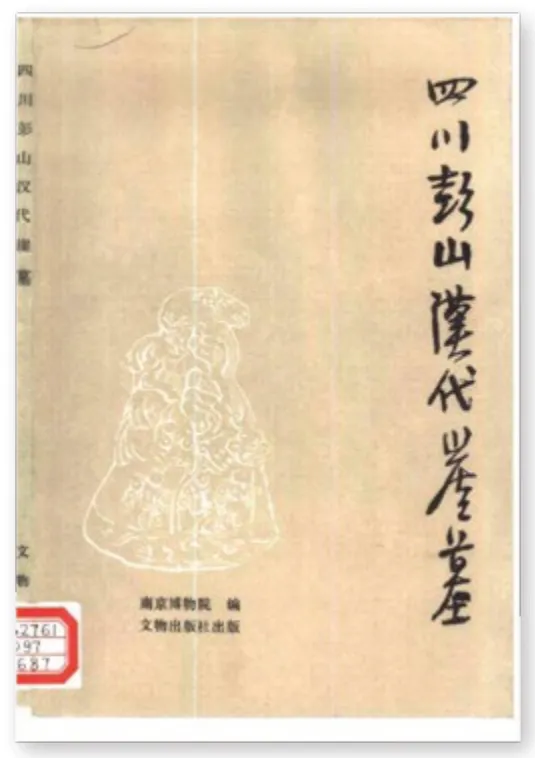
《四川彭山汉代崖墓》书影
1948 年10 月28 日,夏鼐收到吴良才的来信,得知了吴金鼎的死讯。悲痛万分的他连夜写下悼念文章,发表在《中央日报》上,并译成英文寄给叶兹教授。夏鼐在悼念文章中写道:“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夏鼐明白,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是无法安心于考古事业的。他将对亡友的悼念和对中国考古学的殷切期盼书写于此文中,相信在“时局如此紧张”的时候,“有此或足以对死友矣”。
时代的浪潮滚滚而来,在古老的中国即将迎来新生之际,吴金鼎满怀遗憾地去世了,史语所考古组的故人多数迁往台湾,夏鼐在此时坚定地留在了大陆,迎接解放的曙光。多年后,作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掌门人,夏鼐已是著作等身的考古学家,举世闻名的“七国院士”,对于二人曾经共同奋斗的成果—《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先生本欲留下一篇序言,只可惜这本报告迟至1991 年才问世,夏鼐的序言未及写出,便在1985 年逝世了。
历史总是会留下诸多遗憾,不知夏鼐会在序言中如何悼念这位已故的知己。或许正如夏鼐回赠吴金鼎的那副对联中所说:“尚待须臾,则我亦将归来。”如果有另一个世界,希望两位先生能够晒太阳于考古的田野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