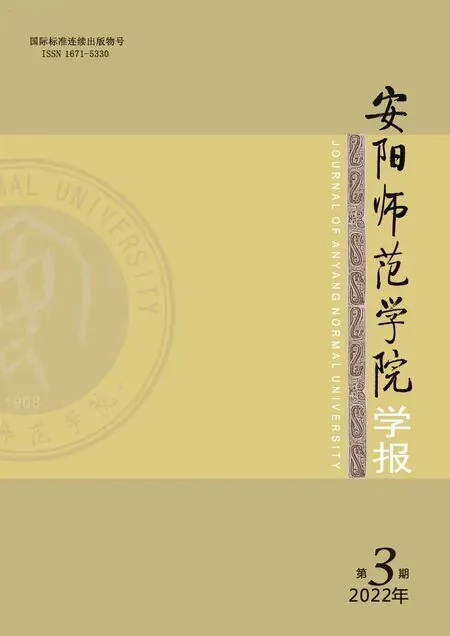《周易》真精神的探求
廖名春
(1.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2.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从古至今,尽管人们大多承认《周易》为文王、周公父子所作,但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却始终存在分歧。
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重视《周易》的德义。《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解随卦卦辞“元亨利贞”的“四德”说,《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的“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说,都可视为义理易学的滥觞[1](P4406)。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晋人以《周易》占筮论事,史不绝书。如果鲁太史出示给韩宣子的《易象》只是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一部筮书,韩宣子决不会如此大发感慨。从《易象》中可“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可见其内容决非讲卜筮,应是一部阐发《周易》中文王、周公父子政治思想的著作。
也许是受鲁国太史所藏《易象》一书的影响,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槖”(帛书《要》),以致成为文王、周公易学思想的代言人。孔子说:“《易》,……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1)本文从宽式释文,释文据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第99、1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帛书《要》认为《易》有“德义”,具体而言,既有“以阴阳”表现的“天道”,又有“以柔刚”表现的“地道”,还有“以上下”表现的“人道”,更有“以八卦”表现的“四时之变”。
传世文献也有相同的记载。《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并借“子曰”赞为:“《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这就是说,孔子不但视《周易》为自然哲学之书,更视它为社会政治哲学之书。孔子的这一易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郭店楚简《语丛一》篇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与帛书《要》孔子所谓“《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说同。郭店楚简《六德》更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狱犴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戴矣,观诸《礼》《乐》则亦戴矣,观诸《易》《春秋》则亦戴矣。”(2)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按:诸“戴”字原作“才”,“戴”从才声,故可通假。是说包括《周易》在内的“六经”都是肯定和推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道的,与帛书《要》孔子所谓《易》“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说完全一致。
荀子说《易》忠实地秉承了孔子之教,认为“《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荀子·非相》)。“《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都是以《易》为政治伦理之书,旗帜鲜明地反对卜筮,这种风气甚至波及到其他的学派。如《庄子·天运》就模仿孔子的口气,以《易》为“六经”之一。《庄子·天下》认为“《易》以道阴阳”“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吕氏春秋·务本》《慎大》《召类》三篇引《易》以及《尸子·发蒙》篇引《易》,都是取其义理。可见先秦时期的思想精英,不少都接受了孔子的《易》教,认定了《周易》为德义之书。
汉兴,《周易》“列于学官”,班固《汉书·艺文志》更将《周易》列为“五经”之首,此后,历代公私书目都以《周易》为群经之首。而以王弼注、孔颖达疏、程颐易传为代表的义理易便成为传统易学的主流。尽管其解释各有千秋,但基本秉承了孔子之教,视《周易》为讲天道人道之书。
但另一方面,将《周易》视为卜筮之书的风俗也很普遍。
《周礼·春官·宗伯下》云“大卜”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云“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周易》为“大卜”“簭人”所掌,显然是用于卜筮。
《左传》《国语》有关《周易》的记载共二十多条。其中《庄公二十二年》的“陈侯使筮之”、《闵公元年》的毕万“筮仕于晋”、《僖公二十五年》的卜偃“筮之”、《襄公九年》的穆姜“始往而筮之”、《襄公二十五年》的崔武子“筮之”、《国语·周语》的“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国语·晋语》的“公子亲筮之”、董因“筮之”等诸条,都是以《周易》占筮,显然是以《周易》为卜筮之书。
晚年以前的孔子也是如此。《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帛书《要》篇说孔子“老而好《易》”,可见孔子晚年以前并不喜好《周易》。为什么?因为他也跟当时的一般人一样,认为《周易》没有“德行”,是讲“卜筮”的。
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是这样认为的,以致于老师孔子“老而好《易》”以后,他仍持《周易》为卜筮之书的旧说,不肯接受《周易》进入孔门的事实,对孔子易学观的改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3)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段的记载,廖名春《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一文有讨论,《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汉简本《周易》,每卦的卦爻辞后都附有卜辞,就是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普遍以《周易》占筮的证明。
秦始皇焚书时,在《诗》《书》诸子百家之书禁绝的情况下,“《周易》独以卜筮得存”(《汉书·艺文志》),“传者不绝”(《隋书·经籍志》)。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书目中子部术数类的易学著作,基本上都以《周易》为卜筮之书。
至南宋,朱熹著《周易本义》,力主“《易》本是卜筮之书”,影响颇大。
近代以来,政治形势和学术观念大变。学人们在不信王注、孔疏、程传圣人作《易》专为说理以教人说的同时,却极为肯定朱熹的“《易》本是卜筮之书”说。从顾颉刚到李镜池,最后由高亨集其大成,形成了近代以来的以“疑古”为特征的新易学体系。
比如陆侃如说:“我们知道《易经》并不是古圣王说教的著作,而是民间迷信的结晶,从起源到写定,当然需要几个世纪。这些迷信的作品,与近代之‘观音籖’‘牙牌诀’极相近,既谈不到哲理,更谈不到文艺。”(4)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转引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岭南学报》8卷1期,1947年12月。按:《中国文学史简编》为陆侃如、冯沅君合著,有开明书店1939年10月版本。
高亨说:“我认为研究《周易》古经,首先应该认识到《周易》古经本是上古的筮书,与近代的牙牌神数性质相类,并不含有什么深奥的哲理。”[2](P5)
朱伯崑也说:“就《周易》全书的情况看,大部分内容仍属于筮辞的堆砌,多数卦的卦爻辞之间缺乏甚至没有逻辑的联系。所以《周易》还不是《诗经》一类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哲学著作,而是一部占筮用的迷信典籍。”[3](P10-11)
总而言之,他们都认定《周易》的“哲理”是后人“加上”去的,是《易传》强加给《易经》的,故而“孔子之《易》”而非“文王之《易》”。
为什么同样一本书,人们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解释的方法不同所致。
《周易》源于卜筮,文王作《易》是在原来筮书的基础上精心改编、创作而成的,其工作可谓“旧瓶装新酒”。也就是说,其表现形式是筮书,其内容和实质则是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是借用筮书的外壳来表达的,后人解《易》、用《易》,只见其筮书的外壳,便以其为卜筮之书;能发现其蕴含的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便以其为义理之书。认识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容易,故社会上以《周易》为卜筮之书的观念非常流行;能认识到其内在的思想价值不容易,故视《周易》为义理之书的往往只是少数。即便孔子也只是晚年归鲁后,才透过其筮书的外壳认识到《周易》内涵的文王、周公父子的“德义”。没有孔子易传的阐发,后人更难以认识到《周易》内在思想的价值。
读《周易》容易歧途亡羊,主要就是迷于其卜筮语言,《周易》中文王、周公父子的思想,许多都是借用卜筮语言来表达的。这些《周易》特有的语言,与一般的哲学语言不同,它往往“旧瓶装新酒”,在古老的卜筮语言里,注入了文王、周公父子的“德义”。不懂得《周易》语言的这种特殊性、复杂性,往往难得正解。
比如《周易》卦爻辞中常见的“贞”字,传统的王弼注、孔颖达疏、程颐传释其为“正”,守持正固,以其为哲学语言。而今人一般则据甲骨文文例和《说文》训“贞”为卜问,以其为“筮辞”,认为是《周易》属卜筮书之铁证。其实,《周易》卦爻辞之“贞”虽源于筮书,但经过文王、周公父子的改造后,《周易》里的“贞”,已没有一例作贞问解了。“元亨”一词在筮书里是大亨、大吉的意思,但在《周易》里,则已变成一个条件句。比如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是说强健者,做到“元”,则“亨”;做到“贞”,则“利”。这里的“元”绝非大或始的意思,而是《左传·襄公九年》穆姜所谓“体仁足以长人”之“体仁”,也就是体谅、关心下人的意思,所以下文说“而有不仁,不可谓元”。“利贞”即“利于贞”,这里的“贞”不是贞问的意思,而是守静不争的意思。“贞”与“鼎”同字,故有“定”义,引申则有静义,则有不争义。卦辞“乾元亨利贞”是说,作为强者,能体谅关心人,就能亨通;能守静不争,就能吉利。这里的“亨”是由“元”决定的,这里的“利”是由“贞”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为而不是天意,因此不需要贞问。坤卦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也是如此。“利牝马之贞”不是贞问母马是否有利,而是说像母马一样柔顺不争则利。“牝马”是否“利”,不是贞问的结果,而是由是否“贞”决定的。“元亨利贞”这些“筮辞”,经过文王、周公父子的改造,在《周易》里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从卜筮语言转换成哲学语言了。这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孔子晚年已经体会到了,故说《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有四时之变焉”(帛书《要》)。一般人则习焉不察,还是以卜筮语言读之,将文王、周公之《周易》混同于时下流行的筮书,辜负了文王作《易》的深意。
孔子对《周易》的解释,今本《易传》八种十篇中有所体现(5)一般以为七种十篇,但《大象传》《小象传》非一人所作,是两篇不同的东西,与《系辞传》上下、《彖传》上下不同。,但对卦爻辞的直接解说,即以“子曰”为说者非常有限。《周易》的卦爻辞,创作年代早,其语言脱胎于卜筮,不易理解。他们虽然继承了先秦象数易学的卦气、互体、五行、爻辰、互体、阴阳灾变种种异说并有所发展,但逻辑有欠严密,说服力不强。王弼以来的义理易学号称尽扫象数,实质是继承了《彖传》《小象传》爻位说,以秉承比应、当位得中一套解《易》,表面上《周易》的卦爻辞无所不通,没有解不了的,其实是撇开了难解的《周易》卦爻辞而另起炉灶,离文王作《易》之精神远矣。近代以来的疑古易学追本溯源、无征不信,但以《周易》为卜筮之书,从根本上否定文王作《易》之精神,亦难被认可。
孔子易教的重光,实得力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的出土。帛书《易传》共6篇,约16 000余字。第一篇帛书《二三子》记载了孔子对乾、坤、蹇、解、鼎、晋、屯、同人、大有、谦、豫、中孚、小过、恒、艮、丰、未济等卦卦爻辞的解释,其一半的篇幅着重论乾坤两卦,这种重视乾坤两卦的思想同今本《系辞传》《文言传》一致。其解《易》只谈德义,罕言卦象、爻象和筮数,这种风格与《左传》《国语》所载易说迥异,尤近于《文言传》与今本《系辞传》中的“子曰”。第二篇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传》基本相同,不同处除通假字很多外,缺少今本《系辞传》上篇的第九章,下篇缺少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的一部分,以及第十、第十一章(6)依朱熹《周易本义》所分,下同。。第三篇帛书《衷》,其内容开始说阴阳和谐相济,为《易》之精义。接着历陈各卦之义,其说解多从卦名入手,然后为今本《说卦传》的前三章,再分别阐述乾坤之“详说”。最后为今本《系辞传》下篇的第六、七、八、九章。这些说解大部都称之为“子曰”。第四篇是帛书《要》,其开始部分残缺,内容应是今本《系辞传》下篇的第十章,接着是今本《系辞传》下篇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后面有两段文字特别重要,分别记载孔子晚年与子贡论《易》之事和孔子给其弟子讲述《周易》损益二卦之理。第五篇是帛书《缪和》,记载缪和、吕昌、吴孟、张射、庄但等向“先生”问《易》之事,讨论了涣、困、谦、丰、屯、蒙、中孚、归妹、复、讼、恒、坤、益、睽、明夷、观等卦卦爻辞之义。第六篇是帛书《昭力》,以昭力问《易》、“先生”作答的形式出现,阐发师、大畜、比、泰等卦卦爻辞之义[4](P15-21)。
这六篇帛书易传,明确记载了孔子《易》有《二三子》和《要》两篇。其中孔子许多的说解不见记载,属于首次面世,让我们对孔子的易学思想和解《易》方法有了新的了解,这足以纠正古今一些学者对《周易》的种种误解。可以说,在帛书易传出土前,仅凭传统文献读懂《周易》的卦爻辞是不可能的。有了帛书《易传》,有了帛书《易传》记载的孔子对《周易》的解说,我们读懂《周易》的卦爻辞才有可能。
比如《周易》之乾卦,“乾”之本字是什么?谁都没有说清楚。帛书《周易》经、传都写作“键”,联系到《大象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我们才知道“乾”之本字当作“健”。
又如乾卦有“用九”,坤卦有“用六”。朱熹以为“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而圣人因系之辞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占之,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盖即纯坤卦辞‘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之意”“用六言凡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遇此卦而六爻俱变者,其占如此辞。盖阴柔不能固守,变而为阳,则能‘永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贞’,即乾之‘利贞’也,自坤而变,故不足于‘元亨’云”[5](P32、P46-47)。而帛书《易经》中,“用九”写作“迵九”,在帛书《系辞》中“通”都写作“迵”。可见“用”当读为“通”,因此“用九”即“通九”,而“通九”即全九、皆九。乾卦六爻都是九,所以称为“用(通)九”;坤卦六爻都是六,故称为“通六”。朱熹以假借字“用”为释,不得要领。
再如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陆德明释文:“惕,怵惕也。郑玄云:惧也。”孔颖达疏:“‘夕惕’者,谓终竟此日后,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朱熹本义:“言能忧惧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5](P31)高亨今注:“君子日则黾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6](P191)都是以“惕”为“惧”。而帛书《二三子》引“孔子”说:“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君子之务时,犹驰驱也。故曰:‘君子终日键键’。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故曰:‘夕沂,若厉,无咎’”(7)参见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按:释文有改动。。帛书《衷》也载:“《易》曰:‘君子冬日键键,夕沂。若厉,无咎。’子曰:‘知息也,何咎之有?’”[7](P384)又引“子曰”说:“‘君子冬日键键’,用也;‘夕沂。若厉,无咎’,息也。”[7](P383)这使我们想起了《淮南子·人间》所言:“‘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8](P756)他们都是以“息”释“沂(惕)”。其“‘终日乾乾’,以阳动也”,与帛书《衷》“‘君子冬日键键’,用也”说同。“‘夕惕,若厉’,以阴息也”,与帛书《衷》“‘夕沂。若厉,无咎’,息也”说同。“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说明这条爻辞就是讲的因时而动、因时而止的道理[9](P39-40)。
这些例子说明,《周易》卦爻辞的“德义”,若无孔子的说解,后人不易得到正解。而孔子对《周易》卦爻辞“德义”的说解,传世文献不是缺乏,就是少而未能引起重视。有了帛书《易传》,我们才得以窥见孔子易学的真容,才有机会超越王弼、孔颖达、程颐等前贤。所以,研究《周易》的卦爻辞,利用帛书《易传》等新材料激活传统文献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从《周易》卦爻辞语言的特点入手来把握其内在的哲理,寻求蕴含其中的文王、周公之道,这就是《周易》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