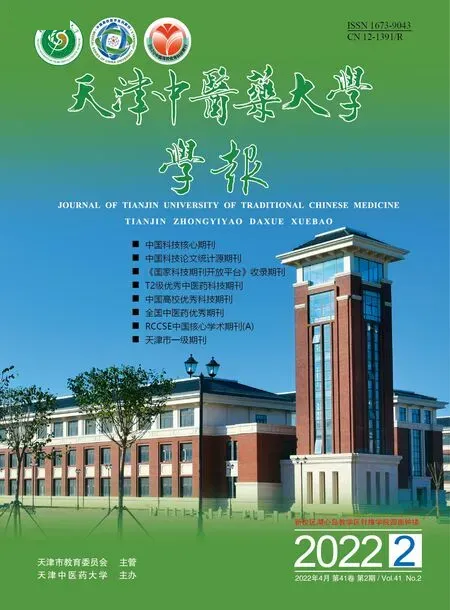醒脑开窍针刺法结合夹脊穴治疗肯尼迪病医案1则*
秦子玲 ,胡赫其 ,鲁海 ,张春红 ,3,4,赵晓峰 ,3
(1.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临床部,天津 300193;2.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天津 301617;3.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4.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深圳 518000)
肯尼迪病(KD)又称脊髓延髓肌萎缩症(SBMA),是一种X-连锁隐性遗传性运动神经元变性疾病,临床表现以下运动神经元损害为主,而无上运动神经元损害,常合并感觉障碍、雄激素不敏感表现和内分泌疾患[1]。该病起病隐匿,病程长,临床症状不典型,实属临床罕见病,极易误诊为运动神经元疾病,基因检测(CAG≥35[2])为其诊断的金标准。且目前尚无确切治疗方法,姜黄素化物和醋酸亮丙瑞林正处于试验阶段[3]。
赵晓峰教授为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嫡传弟子,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医临床、科研工作30余年,擅长针灸治疗脑血管疾病及神经内科疑难杂病。笔者跟师临床学习,观察赵晓峰教授针灸治疗肯尼迪病1例,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1 典型病案
患者男性,50岁。初诊日期:2020年8月31日。主诉:进行性四肢无力10年,加重2年余。现病史:患者10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无力,行走迟缓、不稳,步行较长时间后腰腿部重坠无力,休息后略可缓解,并逐渐出现上肢无力症状,伴全身肉跳,先后多次就诊于天津、北京三甲医院。查颅脑MRI示:未见明显异常;腰椎MRI示:L3~L5椎间盘轻度膨出,血清肌酸激酶(CK)明显升高;肌电图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神经传导速度(NVC)示:双上肢周围神经源性损害(感觉纤维);基因检测结果示雄激素受体(AR)基因第1外显子中CAG重复次数为48,结合其家族中母亲为病变基因携带者,弟弟为肯尼迪病患者,确诊为“肯尼迪病”。因患者拒绝西药治疗,间断于当地社区医院行针灸治疗,症状未见明显缓解。近2年肢体症状较前加重,运动耐力显著下降,为求进一步治疗遂就诊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刻下症:四肢无力,双下肢近端尤甚,蹲起不能,搀扶行走200 m后需休息,双上肢抬举不利及握力减退,伴姿势样震颤,时呛咳,无吞咽困难,无声音嘶哑,性功能正常,纳少,寐安,二便调,舌红,苔白微腻、脉弦细。查体:神志清晰,语言流利,双侧鼻唇沟对称,伸舌稍偏右,舌肌萎缩(右侧显著)及纤颤,悬雍垂稍偏右,咽反射减退。无男性乳房发育。双手大小鱼际肌、骨间肌、双侧上臂及肩胛带肌群、骨盆带肌群、臀大肌、股四头肌等远近端肌肉萎缩,双侧上臂及大腿可见明显肌束纤颤,双上肢姿势样震颤。双上肢肌力:近端4级,远端5级;双下肢肌力:近端4级,远端4级。四肢肌张力正常。双上肢腱反射对称减弱,双下肢腱反射消失,四肢病理征阴性。深浅感觉正常。辅助检查:CK:1655.4 U/L(正常值为 30.0~200.0)。
西医诊断:肯尼迪病;中医诊断:痿证—窍闭神匿、阴阳俱虚。治以调神醒脑、补益脾肾、通督振阳。采用“醒脑开窍”针刺法及蟠龙刺法治疗。取穴:1)仰卧位:内关、人中、印堂、上星、百会、三阴交、极泉、尺泽、委中、肩髃、曲池、合谷、足三里、中脘、气海、阳陵泉、太溪、照海、太冲。2)俯卧位:天柱、风池、完骨、涌泉、华佗夹脊穴。操作:局部皮肤常规消毒后选用0.25 mm×40 mm毫针。1)仰卧位先按照“醒脑开窍”针刺法标准手法量学,先取内关,直刺13~25 mm,施捻转提插复式泻法1 min;再刺人中、印堂,人中向鼻中隔方向斜刺,印堂向鼻根方向斜刺,均进针8~13 mm,施轻雀啄泻法,以流泪或眼球湿润为度;继刺上星,沿皮平刺透向百会,施小幅度、高频率捻转补法1 min;三阴交沿胫骨内侧缘与皮肤成45°斜刺,进针25~40 mm,施提插补法;极泉在原穴循经下移25 mm,避开腋毛,直刺25~40 mm,施提插泻法;尺泽屈肘成120°,直刺25~40 mm,施提插泻法;委中仰卧直腿抬高取穴,直刺25~40 mm,施提插泻法,尺泽以前臂手指抽动3次为度,三阴交、极泉、委中皆以受术肢体抽动3次为度。余穴常规针刺,针刺深度13~40 mm,合谷、太冲采用泻法,其他穴采用补法。2)俯卧位先刺天柱、风池、完骨,针向喉结,进针25~40 mm,施小幅度、高频率捻转补法1 min;再刺华佗夹脊穴,施以蟠龙刺针法,在两个相邻棘突间隙旁开13 mm处取穴,从下向上在相邻棘突间隙左右交替针刺,诸穴均向脊柱45°斜刺8~13 mm,施平补平泻法,因该针法刺激量较大,若患者出现针刺放电感,可将针身稍稍退出或调整针刺方向,以患者舒适为宜;继刺涌泉,直刺13~25mm,施提插捻转补法1 min。诸穴以患者局部酸麻重胀或术者针下沉紧为得气标准。其中气海、足三里采用温针灸,将2 cm左右艾条插在针柄上,艾条底端离皮肤2~3 cm,点燃施灸,每穴灸两壮;选取两组华佗夹脊穴接电针,用断续波刺激15 min,电流强度以患者耐受为度。除内关、极泉、委中穴行快针外,诸穴留针30 min。采用俯、仰卧位交替治疗,间隔1 d,每日1次,每周3次,12次为1个疗程。
预后:1个疗程后,患者自觉全身肉跳减轻,腰腿部重坠乏力症状缓解。继治疗2个疗程后,舌肌、双侧上臂及大腿处肌束纤颤明显减少,四肢尤其是下肢无力症状较前明显缓解,可搀扶行走500 m。本病缠绵难愈,需长期针灸治疗,定期跟踪远期疗效。
2 讨论
KD是一种罕见的迟发型X-连锁隐性遗传性运动神经元疾病,在1968年由Kennedy等[4]首次报道。该病以缓慢进行性下运动神经元损害为主,表现为肢体近端肌无力、萎缩、震颤及真性延髓麻痹,查体可见反射减退或消失、感觉障碍,常合并男性乳房女性化、生殖功能低下等雄激素不敏感表现及血糖、血脂代谢异常等内分泌疾患。发病机制是位于Xq11~12的AR基因1号外显子N’端的一段CAG出现重复序列异常扩增[5],导致其编码的AR多聚谷氨酰胺链延长,致使突变AR与配体睾酮结合后异位至核内,造成突变AR蛋白在细胞核内积聚,其毒性作用和降解异常等机制最终导致细胞变性坏死[6]。CAG重复序列数目与发病年龄呈负相关,而与临床症状、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争议。目前KD尚无特效疗法,主要在于抑制雄性激素水平,而临床效果尚不明确。针刺被认为是对萎缩的失神经支配肌肉组织的一种良性刺激,通过改善其代谢状态、增加肌肉组织血氧供应、改善肌纤维缺氧状态,发挥微循环的调节作用。故适当针刺治疗可能缓解KD患者肌肉萎缩与无力症状,改善其生活质量。
本病属中医学“痿证”范畴,《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记载:“痿,谓手足痿弱,无力运行也。”赵晓峰教授根据患者症状体征,认为本病病位在筋脉、肌肉,与肝肾、脾胃、脑关系密切。本案患者先天肾精不足,肝肾亏虚,加之后天脾胃虚弱,气血津液生化乏源,以致神气亏损而使神伤,脑神失职,统领肢体运动功能失常,又因神伤导致五脏失调,加重气血津液生化乏源,以致筋骨肌肉失养,肌肉软弱无力,消瘦枯萎,如《灵枢·本神》论:“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脱肉……”且患者患病近10年,脏腑俱虚,气血精液不足,阴不制阳,水不涵木,虚风内动,以致患者筋惕肉瞤,肌束纤颤。结合舌脉,提出调神醒脑、补益脾肾、通督振阳治法。《灵枢·本神》曰:“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治疗时当先从治神入手,故采用“醒脑开窍”针刺法,通过调神醒脑来调节全身机能,使神旺而速效。内关为八脉交会穴之一,且属手厥阴心包经络穴,又通阴维脉,《灵枢·平人绝谷》云:“血脉合利,精神乃居。”故针之可理血养心、醒脑宁神;人中为督脉与手足阳明经之会穴,可调泻督脉、健脑调神,配印堂、上星、百会可共奏调脑神、益精髓之功,又能通调十二经脉之气,平衡阴阳、畅达气机;三阴交为足三阴经气血交会之处,为调补气血、滋补肝肾之要穴;极泉、尺泽、委中疏通经络,激发四肢经气,加强脑神对肢体调控。“治痿独取阳明”,选取多气多血手足阳明经的肩髃、曲池、合谷、足三里,配以任脉上的气海、中脘以健脾益气,充养气血生化之源;合谷、太冲合用,一阴一阳,一气一血,一升一降,可通调脏腑气血、畅达三焦气机;阳陵泉、太溪、照海补肾益精、强筋健骨;风池、完骨、天柱三穴联用可改善椎-基底动脉供血,以健脑养神、祛风通窍,缓解肌肉掣动;涌泉激发肾气、调神醒脑;夹脊穴内夹督脉,外贯足太阳膀胱经,与两条经脉经气相通,采用华佗夹脊穴蟠龙刺,配合电针可通督调神、运行气血、调和阴阳。局部辅以温针灸可达温通经脉、培元固本之效。且现代解剖学证实,夹脊穴下有脊神经的前支、后支和交感神经干,针刺夹脊穴可直接刺激脊神经根,改善神经根局部微循环、减少炎性因子刺激、促进受损神经细胞功能的修复和神经纤维再生,进而调节内脏、躯体感觉和运动功能,恢复机体神经、免疫等系统功能稳态,促进疾病康复。
综上,本病案主要采用“醒脑开窍”针刺法及华佗夹脊穴蟠龙刺治疗,以治神为核心,整体局部兼顾,气血阴阳共调,结合患者病情虚实辨证论治,疗效显著,值得临床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