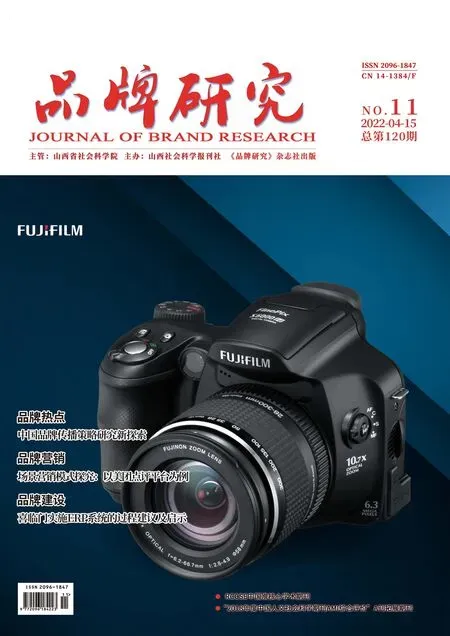碳边境调节机制下碳税实施路径与协调
文/涂智越(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一、引言
2021年7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的草案细节,草案提出将对水泥、电力、钢铁、化肥和铝业五个行业征收碳关税,但同时也允许抵扣国外生产商已经购买过的额度或缴纳过的碳税。尽管草案规定在2023-2025的过渡期之内,进口商只负有报告碳排放信息的义务,但2021年11月的CBAM立法议案修正意见稿中提出将CBAM的过渡期缩短一年,这就意味着2024年之后进口商就必须就相应产品的超额碳排放购买相应的碳排放许可,各国建立相应碳减排机制的时间也更为紧迫。
从短期来看,CBAM涉及的产品范围仅占我国对欧出口的1.19%,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大。但从长期来看,CBAM的实质是对碳定价权的争夺[1],国外出口商曾购买的配额与缴纳的碳税可以抵扣的前提是其获得了欧盟的认可,而这就意味着欧盟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能否定欧盟又将更多领域的产品纳入碳关税的征收范围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尽快完善我国的显性碳定价机制,建立与全球接轨的统一碳定价市场以应对欧盟碳关税并争取碳定价权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碳税及碳排放权交易比较
碳税及碳排放权交易是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两种主流碳定价机制,分别从价格角度及总量控制的角度来达到碳减排的目的。我国目前主要采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尽管目前存在消费税及环境保护税等具有碳排放调节作用的税种,但并没有直接针对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开征碳税。
(一)作用机制
碳税起源于庇古税,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税收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以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资源配置失效的问题。碳税实施过程中主要由政府部门直接对碳排放的价格进行市场干预,通过相对的市场价格变动来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权交易起源于科斯定理,主要是通过明确产权来体现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并创造一个市场来体现碳排放权的经济价值[2],即政府赋予企业一定的碳排放权,从而通过总量控制的方法来起到减排作用。
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区别在于碳税控制了减排的边际成本,但由于减排成本的不确定性,其减排效果也不能确定,而碳排放权交易在数量导向之下产生的减排效果是一定的。但由于企业的减排成果是与企业利益直接相关,由此产生的减排成果与减排成本的差异也导致了不同政策之间预期福利的差别[3]。
(二)覆盖范围
由于碳排放交易权需要确定每个排放主体的碳排放限额,因此碳排放交易权适用于较大的排放主体,否则其政策的实施成本就会很高。而碳税是针对于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直接征收,理论上来说只要能够确定相应的碳转化系数就能够通过企业的燃料消耗等易得的数据直接计算出相应的计税基础及税额,故碳税的适用范围更广,能够覆盖小规模的碳排放主体。
我国现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较窄。从行业来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只包括了电力行业,没有包括其他碳排放量较大的工业企业。就企业规模而言,现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仅包括了电力行业中,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的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并没有被纳入交易范围。尽管目前没有开征碳税,但从具有碳排放作用的环境保护税及消费税等税种来看,其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碳排放企业。
(三)政策灵活性
碳排放权交易中碳交易的价格是由市场机制确定的,其受到了经济因素、市场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能够及时反应市场的波动情况,为企业及时提供减排信号。但碳税受到法律的限制,其税率、计税基础等税收要素不能及时随着市场情况变动,相比起碳排放权交易灵活性较低,但这也意味着碳税是一种更加稳定的碳定价机制。
三、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协调
CBAM提案中对于碳价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在避免重复计税规则下可以抵扣的均为显性碳定价机制下国外生产商所付出的减排成本,而鉴于我国现在显性的碳定价机制只有碳配额及CCER等,这就意味着我国国内生产商在环境保护税等隐性碳减排机制下付出的减排成本有可能并不会被欧盟承认,国内生产商可能面临着国际双重征税的困境。
因此,无论是从实现碳中和的角度,还是从应对欧盟CBAM,避免重复征税的角度,建立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同时存在的复合碳减排机制都十分必要。鉴于碳税与碳排放权在调节范围及政策灵活性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建立复合碳减排机制,首先要在政策制订上对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进行协调,避免给企业带来过重的减排负担。
(一)覆盖范围的互补
在碳税与碳排放权覆盖范围重合的情况下,碳税会逐渐蚕食配额的价格,当碳税税率高于碳配额价格时碳配额将完全失效[4]。因此,碳税及碳排放权的覆盖范围应该有所互补,而不能完全重合。一方面,就企业规模而言,碳排放权交易更适合覆盖大型碳排放企业,而碳税则可以覆盖更多的小规模及分散的碳排放企业。另一方面,从行业角度而言,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需要有较为精准与翔实的行业数据作为支撑,而碳税则可以覆盖更多的行业。但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行业,都需要注意覆盖范围的互补,在征收碳税时对于已经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业予以适当的税收优惠及减免,避免给企业带来过重的减排负担,从而增加政策推行的阻力。
(二)碳价协调机制
由于碳排放权交易中碳价实质上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其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会产生碳价波动较大的情况,而碳税与碳交易的组合模式则可以维持碳价的相对稳定。一般而言,碳税税率既可以充当最高限价也可以充当最低限价。当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持续低迷时,其减排效果也将无法实现,此时碳税可以将碳价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从而避免碳排放交易体系失效。而当碳配额价格过高时,企业可以选择缴纳碳税而不是购买碳配额,此时碳税税率就是碳配额交易价格的最高限价。
四、国际经验借鉴
欧洲各国早在20世纪末期就开始了征收碳税,在2005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开始运行之后,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同时采用碳税与碳排放权权交易体系以完成《京都议定书》要求的减排目标,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芬兰、英国、挪威等国家,其对于碳税与碳排放权不同的协调机制及其产生的减排结果也为我国进行碳减排复合机制构建提供了国际经验。
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征收碳税的国家。2005年,芬兰加入欧盟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该体系主要覆盖以电力及供热为主的能源生产行业及能源密集型行业。芬兰对涉及这些行业的企业进行了碳税的减免。
英国于2001年10月开征气候变化税,其主要针对工业部门的能源产品征收,尽管英国并没有将其命名为碳税,但其发挥的作用相当于碳税。2002年,英国开始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制度,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国家。英国的在碳减排复合制度之中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其在2013年引入的最低碳价机制。其规定,如果碳排放权交易的碳成交价格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碳价,政府通过加征排放价格支持机制税来弥补差额,从而稳定碳价,弥补了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可能市场失灵的缺陷。
法国在 2014 年开征碳税,在碳税征收范围上,主要是针对化石燃料征收,与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覆盖范围没有交叉,即碳排放权交易覆盖的排放主体如发电行业并不需要缴纳碳税。
挪威在1991年开征碳税,2005年加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油气、造纸、航空等部门同时受到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双重管制,加重了企业负担。并且减排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2008-2018 年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 -0.4%。
从上述国家的经验中可以看出,避免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调控范围的重合是十分必要的,挪威缺乏协调的双重管制就使得政策的碳减排效果丧失。因此,一方面实行碳减排复合机制要注意避免碳税的征税范围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覆盖范围的重合,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中包含的企业应当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或减免,避免给企业造成过重的减排负担。另一方面,由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依靠市场及价格机制进行调控的,难免会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同英国一样在碳税中引入最低碳价机制以维护碳价的稳定十分有必要。
五、碳税制度设计及建议
在考虑碳减排及碳排放权交易协调的基础上,碳税的具体实施路径的确定需要结合税率、征税范围和征税环节等征税过程中的具体要素进行考虑,以确定最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
(一)碳税实施路径
碳税的实施路径有两种方式,第一条路径是单独设立针对化石燃料碳排放征收的税种或税目,第二条路径是在现有税种的基础上征收附加税。考虑到新设税种的阻力较大,政策完善所需时间较长,加之CBAM立法时间以及过渡期的提前,在现有税种基础上设立附加税可能是更为可行的方案。
许文[5]指出,可以采用在现行煤资源税和成品油消费税的基础上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依据加征碳税。但其缺点是在现行税种下设置附加征收可能不利于税收优惠的设置,且受到电力价格管制的限制,煤炭资源税可能难以向下传导。
(二)征收范围与税率
我国目前如果开征碳税,是在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在逐步完善的背景之下嵌入碳税制度,因此在征收范围以及税率的设置上需要考虑与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协调。
在征收范围的设置上,需要避免与碳排放交易权的重合,对纳入碳排放交易权的行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或税收减免。另一方面,由于现行碳排放配额分配实行无偿分配制度,与传统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不符,因此可以对小规模纳税人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以弥补因大企业无偿获得碳排放配额而只需就超额的碳排放付费的不公平效应。
在税率的设置上,考虑到政策实施可能会面临的阻力,碳税税率的初始设置不宜过高,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提高。同时,考虑到不同部门的碳排放量及能源需求存在差异,因此碳税的设置不宜采用单一税率,根据能源的污染程度及需求程度实行差别税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三)碳税收入归属及使用
碳税收入的归属目前有两条可能路径,一条是将碳税划分为中央税,其收入直接归属于中央,另外一条路径则是将碳税划分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按照一定的比例与地方分享。而之所以不考虑将碳税作为地方税,主要原因是碳税与地方碳排放量直接相关,如果碳税收入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可能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纵容地方企业的碳排放行为,从而削弱碳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在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一直存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因此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分成以弥补抵偿政府的税收执法成本以及地方减排成本可能是更为恰当的选择,苏明(2009)指出7:3可能是较为合理的分成比例。在改造现行税种的路径之下,尽管碳税是作为附加税征收,但在印花税的实践中不同税目分别归属于地方与中央也早已为碳税的分成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
就碳税收入的使用而言,出于资金的合理利用以及财政统一预算管理,将碳税收入纳入财政统一预算管理可能是更为合适的选项。而专项财政资金可能导致资金的沉积,资金难以得到合理的配置[6]。
六、结语
目前我国已经开始逐步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建立碳税制度则是应对CBAM,实现碳中目标的必要举措。建立碳税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其应该与现存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覆盖范围以及价格机制上进行协调,以保证我国碳减排复合制度能够顺利地实现减排目标,碳税政策的设计也应该在合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我国国情的考量,避免产生水土不服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