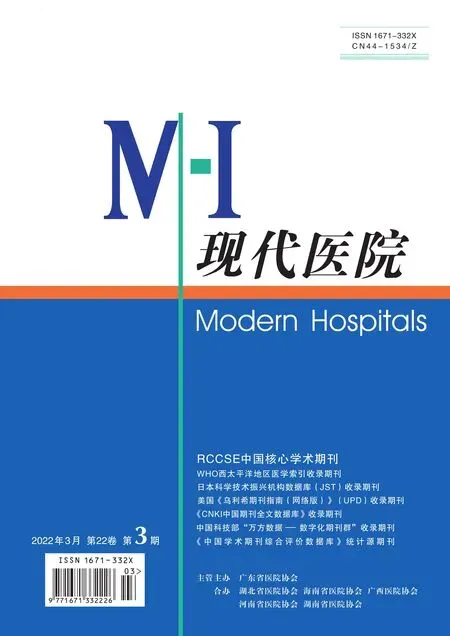后疫情时代中医药防疫在综合医院中的发展路径与对策思考
胡 赟 王钰婷 朱 亚
1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江苏南京 211100;2 苏州京东方医院 江苏苏州 215000;3 南京医科大学健康江苏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1100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已给全球造成巨大灾难。疾病爆发后,国家紧急调用4万2千多名军地医务人员第一时间驰援武汉市和湖北省其他地市。而中医的参与力度和广度也是前所未有,先后近800名中医专家,近5 000名中医医务人员参与一线救治。江苏省中医系统共派出了438名中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战斗在湖北救治一线[1]。
回顾两年来抗疫的经历,中医药在治疗方面深度介入,针对患者病情轻重,采用“一人一策”“中药和非药物疗法综合干预”等规范化措施。并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作用,将中药纳入“四早”干预。有效降低了发病率、转重率、病亡率,促进了核酸转阴,提高了治愈率,加快了恢复期康复。尽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仍未结束,但随着全球疫苗接种增加,病毒变异,人群免疫屏障的建立,乐观估计,疫情发展趋势将逐步回落。2022新年伊始,已有诸多国家打开国门,而中国也在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提出常态化防疫和全链条精准防控“动态清零”要求:需要在应急救治、防控体系方面对既往存在的规范原则进行调整;需要在中医与西医、公卫与疾控等领域有机融合协作[2]。
1 后疫情时代综合医院中医药防疫现状与困境
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救治策略,是中医与西医有机融合,协同抗疫的必然要求。在国家层面,有“中医国家队”驰援武汉;各地出现的本土病例及输入病例的救治中,也都可见中医医疗机构、研究机构有效救治与预防的例子。但在综合医院中,不论是选拔驰援疫区的医务人员,还是日常防控工作,均缺少中医药专业人员的参与以及中医药防治方法和举措。
1.1 综合医院中医药防疫现状
防疫两年多来,尽管国家层面与社会层面对中医药防控认知空前高涨,对中医药防控认可高度提升,基于民众的赞同所带来的氛围更新,让中医药迎来利好的发展环境。即便如此,在某些综合医院,由于内环境的相对封闭,以及人才、物力的短板效应,使得在防疫一线,依然存在重西而轻中,甚至全西而无中的困境;有些综合医院甚至因本院中医自身发展的滞后,没有完备的中医能力、物力、人力参与疫病防控,从而出现欲重中医而无人的尴尬局面。
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为例,从疫情爆发开始调集院内骨干力量开赴湖北,到4月份结束,抗疫所在地患病人员清零,总共派出三批59名队员参与当地医疗工作。后又陆续派出数名医务员工奔赴北京、新疆、河北等地驰援抗疫。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无中医药专业医生征调进入抗疫一线。在整个疫情期间,医院成立肺炎防疫小组,增加发热门诊工作人员,设立核酸检测点,组建检测应急队伍,院内不间断开展感控大督查,各项防疫工作有条不紊,但是中医药专业人员加入和中医药防疫方法使用却寥寥无几。
1.2 综合医院中医药防疫困境
1.2.1 综合医院中医药建设及影响滞后 综合医院中医科,普遍存在重视不足,地位偏低,中医特色缺乏,业务运行封闭,医与药管理分离的局面。有的历史较久的中医科,由于几代中医人的努力,也形成了一个或几个特别病种或中医药诊疗中心,但大多数综合医院中医科,存在亚专科各自独立,小门诊小病房的尴尬局面[3]。
仅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的中医科为例,先天条件来看,该科室具备医学人才、先进技术、优质设备的支持,但同时又存在中医科室专业方向、发展定位不明确的特点。院内外人士,始终受制于中医内外妇儿不同科的模糊概念,形成模糊印象,使得原本可以在慢性病、传染病、免疫性疾病等领域发挥中医诊治特色的功能受到限制[4]。临床工作方面,中医不能全面参与,在很多急慢性疾病诊疗方面,丧失了中医药干预的先机。另外,由于中医科医师专业领域的差异,临床工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精通。
1.2.2 综合医院中西医协作不足 在国内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医医院或接受中医治疗医疗机构的报道,比如中医药100%全程参与,轻症康复比例增加,转危重率下降,而且住院天数,出院后复阳,治疗花费方面均满意结果。但若从综合医院收治的报道来看,虽然也不乏治愈率、转重率、复阳率方面的积极信号,但中医药参与救治的具体数据不详,主要是综合医院的中医药使用率并不高。在很多综合医院,新冠肺炎患者的整个治疗康复过程中,甚至没有中医专业医生协同参与,中医药治疗基本无从谈起。有些综合医院仅仅是使用了部分协定方或中成药,缺乏辨证论治、不可能“一人一方”,更没有机会把中医的防疫药方[5]、保健养生之法用于防疫临床中。
1.2.3 综合医院中医学科设定与发展不足 在我国,依照“中西医并重”方针建立了综合医院和中医医院两种不同类型的医院。综合医院一般均设置中医科,中医医院也提供中西两种医疗服务。但归根结底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科室,因为综合医院中医药的发展,与中医医院的发展不尽相同。
“十三五”以来,由于国家重视中医药发展,各地中医药不断迎来高速发展时期。由于中医科在综合医院普遍体量小、地位低,发展慢,故而振兴中医药事业的重任落在了各级中医医院的身上,而身处“西医”环境之中的综合医院中医科往往被忽略。如河北省对40家省级注册的三级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现场调查显示,设置中医床位数占床位总数仅2.2%,30%的综合医院仅开设中医门诊,而未设立病房。仅有14家综合医院达到了《综合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基本标准》中医师和护士的配备。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上级中医管理部门的政策、信息可以直达中医医院,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人员却不能及时了解掌握中医政策和中医发展战略,尤其在新冠疫病爆发以来,综合医院中医药防疫工作所面临的现实,与中医医院相差悬殊。但是中医中药骨肉相连,从中医学科发展角度来看,不论是在中医医院还是综合医院,都已经开始经历一段特别时期[6]。多学科、多领域的创新、整合,为防疫体系提供了机遇[7],也为中医防疫及其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舞台。
2 后疫情时代提升综合医院中医药防疫路径
2.1 充分利用后疫情时代这一延续中医发展的特别时期
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期,我国各级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均迎来了医疗快速增长的时期,对中医医疗的需求增长非常明显。以百度健康2020年3月官网发布的数据为例,疫情期间单日咨询量为30万,而中医的网上接诊量占到40%,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8]。山东省的一项调查表明,84.53% 的被调查者在疫情后认为中医是科学的,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及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疫情后对中医药的认知程度均有提高,比疫情前增长了 23.12%,尤其是年轻人群体正向态度提升明显[9]。
2.2 以政策倾斜引导中医建设
2020年9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文中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要深入研究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问题,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副总理在指导疫情防控中也多次指出,要中西医结合打好救治组合拳[10]。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健康意识增强,以及医学目的调整和医学模式改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值,越来越为民众所喜爱,并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坚持中西医并重,全面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健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推动中医药开放发展,是党中央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重大部署[11]。
中医药事业越是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12],迈向高质量发展,就越要推动中医药特色发展、内涵发展、融合发展。防疫两年多来,凸显中医药优势的鲜活经验不断涌现,“三方三法”的广泛使用,中医防疫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教育,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带来不竭动力[13]。成就固然令人欣喜,但当前中医药发展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中医药发展自信,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202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科室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综合医院中医科同中医医疗机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均是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骨干力量[14]。
2.3 以法律支持构筑中医成长
整个“十三五”期间,党中央把中医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医药改革发展。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的印发,为心潮澎湃的中医药人划定了奋斗的坐标,字里行间饱含着催人奋进的力量。
2020年开始,全国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相继出台一系列实施意见和办法,尤其是北京市相关部门起草了《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进一步落实中医药法律保护具体举措,这无疑是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为保障中医药健康创新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20年8月《江苏省中医药条例》中要求:“扶持和促进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医疗机构发展,提供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同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再次明确中医药发展的重大意义。
总体而言,中医药立法对中医药发展起到纲领性作用,有利于制定中医药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医药健康创新发展的标准、规范,对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执业规范,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并走向国际、惠及世界的重要保证。中医药立法无疑对中医药健康创新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2.4 以专业自信融入医院发展
中医药系统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现了五个“首次”,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两年多来中医药抗疫所取得的成绩成为增强中医药自信强有力的砝码,但中医药的自信不仅仅来源于疗效自信,其在几千年发展中所不断累积、不断生发出来的历史自信、理论自信、方法自信共同铸造了强有力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种最硬的“软实力”,中医药的文化自信,渗透并塑造着中医人的思维和观念[15]。具备了强大的自信,才能让中医学子更加重视中医药课程、知识的学习,才能让中医药临床工作者更好地运用、推广中医药传统疗法,才能让中医药科研工作者更进一步挖掘经典、经验,才能让中医药管理者更好地参与国家、地方中医药行政规划与决策。可以说,这些专业自信、临床自信、研究自信、管理自信是中医药成长的有力支撑,为中医药的发展进一步凝神、聚力、添彩。
综合医院中医科在日后的工作中,应谨守传统、发扬创新,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医院的整体的发展。可以尝试与多科室,多部门协同、合作。不仅把中医药用于防疫,更要推广至慢性病、老年病、急症、肿瘤、术前术后以及康复、营养中去。综合医院中医科室的发展需依托和服务于医院的整体,做好中医科室的角色定位,制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并保持与总目标相吻合。结合综合医院的“大综合、强专科”发展模式,形成“有机配套” “有的放矢”“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局面。
2.5 以应急救治需求共谋中医防疫新体系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疫疠时常肆虐,为灾于我国人民,我们智慧勇敢的祖先,与疫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与疫疠的长期斗争中创造了许多防止疫疠传染的有效方法。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从公元前243年《史记》“天下疫”记载开始,到公元 1840 年,中国至少发生了 321 次疫病;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我国共发生较大的疫情500余次,中医学一直是我们对抗疫情灾难的主力军[16]。比如在《黄帝内经》中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记载,提出“疫”具有传染性。东汉医家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因受“伤寒疫病”流行之苦,他有感而发,潜心研究,奋笔疾书,最终著成《伤寒杂病论》。三国时期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描述了当时疫病的发生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中医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手段,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在现代医学有效药物和疫苗未研发成功之前,中医药可提供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治疗策略、方药、技术,具有快速反应、快速救治、疗效显著的优势。可以看出,中医药不是“慢郎中”,是中医药护佑了华夏儿女的繁衍生息。同时,从SARS、禽流感到新冠疫情整个防治过程看到,中医药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防疫救治不仅仅在疫病爆发阶段,在疫病未发,病后恢复阶段皆应参与其中,从而形成预防保障、救治康复、中西医协同的新体系[17]。
综合医院对于应急、感控、防疫的部门建制管理,属于院内一级科室,有专门人员,专业人士负责[18-19]。因上述工作内容,需要在单位全面铺开,多部门齐抓共进,中医科只是属于其中的一个需要配合部门而已。中医药对于应急、感控、防疫并不是无计可施,无以应对。相反,中医药治未病强调未病先防,防病于先;欲病救萌,防微杜渐;已病早治,防其传遍,瘥后调摄,防其复发[20]。可以融入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建议能够招聘中医疫病学专业医生,充实到医院防疫的一线工作中。配合防疫小组,制定防疫防护计划,疫病救治计划,疾病康复计划,健康养生计划。
总而言之,只有克服综合医院中医药在应急、日常防疫方案、防疫管理制度、防疫人才归口的缺失才能更好地满足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21]。不仅需要综合医院工作的中医医生的参与,更需要上级中医药管理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