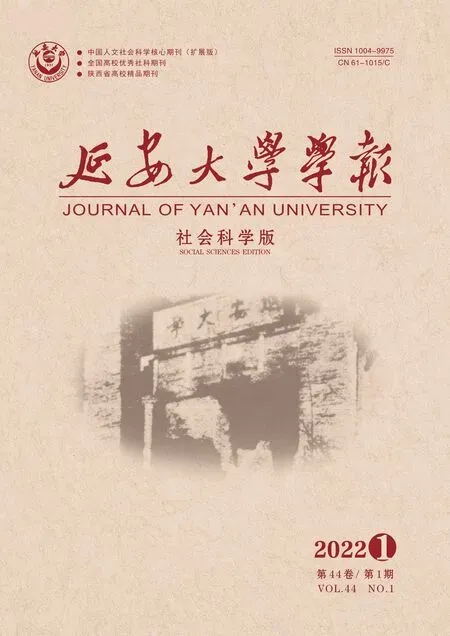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孙犁抗战小说研究
李振刚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孙犁的抗战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前对孙犁抗战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文化心理学出发的人性人情主题意蕴研究,从艺术风格出发的文本剖析以及文本比较研究,而对小说地理空间的建构尤其是作家创作与小说地理空间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偶尔涉及也是分散的个别研究,没有系统地从冀中尤其是白洋淀的地理学角度进行根性地挖掘,没有寻找出小说地域文化现象的地理渊源和文化背景。无论是作家在小说中所描绘的自然风光,还是人文风俗景观,都无法脱离地理空间而存在。本文将孙犁抗战小说置于文学地理学的视阈下,深入探究白洋淀的自然地理面貌和人文地理环境对孙犁创作的影响,以及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在作品中的呈现方式和价值意义,以其更深入全面理解孙犁的抗战小说。
一、孙犁抗战小说中地域文化书写之自然地理景观
(一)芦苇
有着“华北明珠”之誉的白洋淀,由143个相互联系的大小淀泊组成,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该地区较大的一块湿地。人类最早的农耕文化,就是在湿地上诞生的。“没有湿地就没有农业,也就不会有民族文明的形成”,[1]4它是“孕育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1]187白洋淀地区西望太行山脉,东临古黄河,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淡水湿地,它不仅是宝贵的植物物种资源库,为人们提供大量的生产生活原料,更是孕育多样文学与优质文化的重要地方。
白洋淀是芦苇重要产地,“白洋淀盛产水生草本植物芦苇,是织席、打箔、造纸的理想原料”。[2]小说《芦花荡》中“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散”。[3]119芦苇也是白洋淀地区重要的自然景观之一,百里苇海碧波荡漾,水苇相映,风景如画。无论是春秋还是夏冬,一望无际的芦苇点缀着水淀,使其散发着迷人的美景。白洋淀芦苇历史悠久,在白洋淀形成不久之后便出现了广袤的芦苇海洋。芦苇不仅是白洋淀一道美丽的风景,还与人们的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芦苇在白洋淀水生植物中经济价值最高、产量最大,它是白洋淀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作物。孙犁在小说《采蒲台》中这样描述:“抢光白洋淀的粮食和人民赖以生存的苇,白洋淀的人民就无以为生,鱼米之乡,变成了饿殍之世界。”[3]231淀边村民既种粮、种菜,又从事渔苇生产。淀边村庄不仅有“麦秋”“大秋”,还有“苇秋”。苇子可造纸、织席、打箔、编篓、打帘和制作苇制工艺品。在白洋淀地区,村民们的院子门前要留一块空地用来碾苇和编席。
但是孙犁并非单纯地描写芦苇的美,而是赋予它们一定的象征意义,“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4]水生嫂们逃离敌人的追击,划船躲进淀里,茂盛的芦苇像一面面铜墙铁壁,忠诚地守护着自己的家乡,它们像坚强的战士,寄予了作者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芦苇“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3]114当芦苇丰收时,就如一条苇子的长城,而这条“芦苇的长城”忠诚地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看似柔弱优美的事物被注入革命的情感,它们是保卫家乡人民高昂精神的象征,是前进的革命口号,更是革命胜利的信心所在,表达着作者对白洋淀这片水土以及人民的高度赞扬和热爱。
孙犁不仅描述了白洋淀的芦苇,白清的水淀,还有朦胧的星星,皎洁的月色,白绸子的水鸟,碧绿的荷花,初夏的小麦黄梢等。在这抗战之中的“世外桃源”中,孙犁“感知大自然的声音、色彩和节律,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5]108在《采蒲台》等抗战小说中,我们听到的不是传统战争小说中的隆隆炮声,而是傍晚时“苇塘里的歌声”,半夜后苇塘里“飒飒的风响”,深夜时苇塘里“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我们闻到的不是传统的战争小说中弥漫的硝烟,而是白洋淀芦花荡里自然风光的优美和静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勇敢、机智,用莲蓬的清香将鬼子引进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后,又仅用一根竹竿就把十几个鬼子打得头破血流,这是白洋淀抗日军民高昂的抗日斗志和对胜利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二)村庄、田园与山脉
孙犁笔下的村庄与田园往往联系在一起,村落外面即是田园,《走出以后》中“围村一条堤,堤外接连不断已经收割起庄稼的田亩,杨柳树也很多。村西有一条大河绕过,隔河望去,又是一围村庄,一片田亩苇坑麻地”。[3]36围堤、田园、杨柳、大河等,这是典型的冀中平原村落外围景象,抗战中孙犁几乎踏遍了冀中的大部分地区,所以孙犁对此是十分熟悉的。
《纪念》中也有对白洋淀地区村庄的典型描绘:“一清早,我又到小鸭家去放哨。她家紧靠村南大堤,堤外面就是通火车站的大路。她家只有两间土坯北房,出房门就是一块小菜园,园子中间有一眼小甜水井,井的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3]178这是村庄的内在景象,也即一种近景。我们在孙犁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土坯房、菜园、水井等作为冀中平原村落常见的景象。而对于村落中农家的描写更是细致入微,《风云初记》中,“房椽下面吊挂着很多东西,大葫芦里装满了扁豆种子,长在青稞上的红辣椒,一捆削好的山荆木棍子,一串剥开皮的玉米棒子。两个红皮的大南瓜,分悬在门口左右,就像新年挂的宫灯一样”。[6]孙犁在此并非像其他作家粗线条勾勒,而是细致地描摹,逼真地再现了战时农村的景象。即使现在走近冀中平原,在一些农户的家中依然可以见到如此场景。在抗战艰苦的生存环境下,冀中人民充分利用自身的地形优势,在贫瘠的山村中乐观地生活。各种颜色的农作物衬托了村庄的欣欣向荣,这些景色同样是作者浓烈情感的呈现,既有对家乡的眷恋,又彰显着对革命事业的积极乐观精神。冀中平原尤其是白洋淀地区是他成长的地方,冀中平原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都是浓厚“家园”意识的体现。
抗战中孙犁走过很多地方,虽不是名山大川,甚至大多是带有原始意味的山野与乡村,但是在孙犁笔下却焕发着生机与活力。这些山川与河流世代守护着这里的人们,不仅是他们生存的根基,更是其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于冀中平原,孙犁也给予了真实再现,“大平原的田野,叫庄稼涨满,只有在大平原上才能见到的圆大鲜红的太阳,照着红的高粱、黄的谷、正在开放的棉花一切都要成熟。红光从大地平铺过来,一直到远远的东方去”。[3]493这段描写有色泽、形象更有状态。其中,涨满的庄稼、鲜红的太阳等既从现实角度描绘了丰收的景象,又从象征的层面展示了时代领袖的光辉思想以及迎接光明前途的信心与力量。同时孙犁在小说中对冀中山脉进行了细致描绘,《老胡的事》中关于大黑山的描写具有鲜明的冀中特色,“山谷是南北的山谷,在晋察冀倒是一条宽的……谷的南口紧连着一条东西谷,那是大道,大道那边是一条不高的平的出奇竟像一带城墙一样的山,而这条山谷的北面,便是有名的大黑山,晋察冀一切山峦的祖宗,黑色,锋利得像平放而刃面向上的大铡刀”。[3]60这是晋察冀地区的风景描写,更是这一地区的风俗画面。大黑山比作锋利的大铡刀,其险峻可见一斑。在这样的画面中,粗壮、勤劳的姐姐热爱劳动,而同龄的妹妹则对战斗充满了激情。这姐妹俩对新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渴望,身体里“好像被过多的青春鼓动”,这种火一样的热情与坚毅的性格与其成长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风俗成为人物性格塑造中深层次的时代与历史因素。在困苦的生活环境中,孙犁感受到祖国壮丽山河的庄严,增强了作为冀中儿女的志气与自信。
二、孙犁抗战小说中地域文化书写之人文地理景观
白洋淀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了雄安儿女,也孕育了别具风情的北国水乡民俗文化。淀区渔民在服饰、饮食、婚丧礼仪等方面均与非淀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片水域中,男人们下河捕鱼养家糊口,女人们织网编席养儿育女,世世代代靠着这片水域繁衍生息。独特的生存环境,养育了一方纯真朴实的民风乡情。不同于沈从文在小说中描摹世外桃源般的风俗画,也没有汪曾祺追求小桥流水般的古朴美,孙犁笔下的风俗不仅带有浓厚的冀中色彩,而且带有深深的历史与时代色彩。不仅如此,作者还将人物形象塑造融入地方风俗的展示中,在环境与人物的描摹中展示时代色彩与冀中地方风俗相统一的画面。
《荷花淀》《红棉袄》《麦收》《黄敏儿》等作品中,人物的刻画与地方风俗的展示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非单纯地方风俗画的简单拼凑或叠加展示,而是绘制了特定时代冀中地区抗战军民迎风斗雪的独特性格。《红棉袄》中山区姑娘虽然少见世面,感情含蓄,但是却深明大义,懂得革命道理,为了救助受伤战士抵御严寒,在“脸飞红了一下”后,仍然断然脱下崭新的红棉袄盖在战士身上。孙犁笔下的风俗描写,看似与人物的性格没有关系,但在仔细品味中却能够给人物塑造营造一种兴味盎然的时代氛围。
《荷花淀》中关于芦苇的描写细致而富有诗意。这里的芦苇有大头栽,大白皮,一捆捆的苇席,在满足人民生产需要的同时,更是人民换粮食等重要的生活来源。“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3]91这些场景描写虽然没有人物的行动,但是却构成凸显人物性格的必要风俗。试想,假如没有那一幕幕的冀中风俗描写,没有抗日战争中民族与阶级冲突的特殊环境,那么冀中人民对敌人的恨之入骨以及对敌的英勇作战的行为是不能深入表现的。因为他们的性格与抗战意志,恰恰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爱国热情与保卫家乡信念孕育而生的。
风景画、风俗画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方色彩,不同地域之间的风俗具有鲜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域人民性格与心理的显著特征。诸如婚丧嫁娶、饮食服饰、交往方式,甚至节日礼俗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嘱咐》中,水生在抗战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路上的风景,“高大的杨树与柏树……他看看麦地,又看看天,看看周围那像深蓝淡墨涂成的村庄图画……他走上了通到他家去的那条大堤,这里离他的村庄十五里路”。[3]165此外还有大雾笼罩的水淀以及水生嫂的黑布头巾等,这些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单纯风景画,鲜明地体现了冀中平原冬季的风俗色彩。
风俗不仅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而且是推动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吴召儿》《红棉袄》中红棉袄的描写具有浓厚的象征韵味。红色象征着希望,代表着冀中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一颗颗火热的心。这一鲜明的意象连接着部队战士与后方群众至深的军民情谊。尤其是《吴召儿》中的山区女孩穿着红棉袄黑夜带领战士爬山的描写,更是凸显了战争中的革命激情与必胜的革命信念。“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乱石山中,突然开了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3]251黑夜里爬山的战士筋疲力尽,但是这个山区女孩儿却像一道光,在人们艰难的时刻给人们鼓舞与信心。“望见这个光,我们都有了勇气,有了力量;它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前进,到它那里去。”[3]251这件红棉袄映现了吴召儿的性格,也即冀中人民在抗战中表现出崇高的责任感和勇敢、坚毅的品格。作品中地理景观并非简单的地理特色描述,而是融入了创作者自身深刻生命体验的丰富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内心精神还乡的家园与寄托。
孙犁抗战小说多是表现冀中尤其是白洋淀地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无畏和乐观的精神。这些人物并非具有特殊本领的英雄豪杰,而是生活在山区或平原中的普通人。他们有一种爱国、勇敢、健康的性格,一种新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特殊历史与时代的产物,更是冀中平原自古以来勇敢与忠义精神的传承。《荷花淀》中几位家庭妇女借口给男人送衣服的行为虽然在战争中显得世俗气,但却是真实夫妻感情的再现。《嘱咐》中水生嫂对丈夫离家的不舍与坚决的支持,更是将夫妻二人之间依依不舍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水生嫂踏着冰面护送水生的描写,在景物与人物心理的细腻描摹中充分展示了抗战年代冀中平原妇女的光荣与伟大品质。作者在风俗展示中生动、真实地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吴召儿、水生嫂、如意、香菊等人物都是真善美的化身,这些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了特定时代中冀中人民高尚的精神风貌和绚丽多彩的生活情态。这些风俗人情与严肃的主题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其独特的小说风格。
燕赵大地以其天然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并培育了燕赵儿女独特的生活观与价值观。冀中尤其是白洋淀地区的战斗与生活经历是孙犁一生最宝贵的文学资产,白洋淀优美的自然风景与民俗传统为孙犁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并使其为我们绘制了美丽多姿的地域文化景观图。
三、地域文化与孙犁抗战小说艺术个性的生成
孙犁的抗日小说以其淡雅清新的风格独树一帜,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人性美、人情美。表现了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思考与关切。同时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孙犁,在真善美的歌颂与追求中,以其细腻的笔触以及简练、明朗的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
文学作品的风格,体现着作家的创作个性,而作家的创作个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知识素养与艺术趣味。孙犁曾说:“风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丰盛的生活和对人生崇高的愿望。”[7]孙犁出生在滹沱河两岸的安平县东辽城村,那里是个风景秀美的村庄。青年时孙犁又应同学之邀,来到了保定白洋淀地区教课。美丽多姿的白洋淀给孙犁美的熏陶与追求,对其气质与创作个性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气候、物候等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到文学家气质的养成与作品风格的形成”。[5]117在这里他不仅领略到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是被当地淳朴、真挚的民俗深深感染。抗日战争中,他的主要足迹就是冀中地区。在这片土地上,他和冀中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一切都给孙犁心灵的浸润和艺术的濡染。
孙犁自走上文坛伊始,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要求描写的精确,精确的描写给人以真实、新鲜的感觉,冀中地区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其笔下的诸多描写都具有厚重的生活实感。《采蒲台》中妇女们在编苇席时哼唱的歌:“快快编,快快编/我小红编个歌儿你看看/编个什么歌儿呀/眉子细,席子白/八路同志走了你还要来。”[3]233在白洋淀,几乎家家户户都编制苇席,而这样的歌曲在抗战年代也是耳熟能详的。正是孙犁真实的生活经历以及深刻的生活体验,才有笔下人物的细致与真切,也正是这份真实,才使得孙犁的创作经受住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考验。
孙犁笔下很少描写叱咤风云的战斗场面,而是主要描写人民的现实生活。作品中各种生活场景与事件的展示,既是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是其最为熟悉和最关心的。孙犁笔下很少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而是普通的农民与战士。他没有刻意地拔高他们,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既写他们的优点,也不回避他们的弱点,因此其笔下的人物真实可信。《丈夫》中的妻子有很多孙犁妻子的影子,而小说中丈夫的经历与生活轨迹如“在保定府上中学”、春节期间“整日在家里翻书本”,由此显得“孤僻”等正是作者本人的自画像。《嘱咐》中,水生对家乡的想念,参军后从白洋淀到延安,再回到家乡中与妻、儿团聚的情景正是作者本人生活经历的回放与再现。可见孙犁创作时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依托,将自己的感情投掷到小说的人物以及事件中。而《荷花淀》的写作,更是孙犁在白洋淀同口镇教书以及生活经历的缩影。“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8]由此可见,冀中地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孙犁的创作。
不仅人物描写,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芦花荡》中关于苇塘的叙述,“每到傍晚,苇塘里的歌声还是那么响,不像是饿肚子的人们唱的;稻米和肥鱼的香味,还是从苇塘里飘出来”。[3]115物产丰富的白洋淀水丰草茂,盛产鱼虾,同时它的生态系统丰富,为鱼类鸟类提供了食物资源和栖息地,如此秀美的人间天堂怎能不激起作者及人们的热爱。同样《光荣》中“滹沱河在山里受着约束,昼夜不停地号叫,到了平原,就今年向南一滚,明年向北一冲,自由自在的奔流”。[3]189虽然孙犁没有对滹沱河做具体的外观与流势的介绍与描摹,但却真实地写出了滹沱河的样子以及它与冀中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
孙犁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融入了主观抒情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孙犁更加注重意境的渲染与纷然多姿的人物形象的逼真描摹。孙犁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妇女形象的塑造是形成其独特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笔下的青年妇女大都温柔善良、刚毅干练,这些人物出生不同,阶级不同、性格与年龄也有所差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即她们都带有冀中平原的泥土气息。既有白洋淀水乡的阴柔与温婉气质,更有北方燕赵儿女的勇敢与刚强。她们千姿百态、活泼水灵,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像月下织席的水生嫂,既有普通农村妇女的勤劳、质朴,又有飘渺若仙的轻灵美感。不仅如此,像水生嫂、刘兰、小菊、慧秀等乡野妇女都有一个特点:像男子一样生产劳作,不仅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在面对敌人进攻时能够义无反顾地支持前线战斗。她们抬担架,做军鞋,看护伤兵,既有荷花般妩媚,又有山石般坚韧,广大女性在“阴柔”的外表下蕴含着燕赵儿女的坚强与硬朗。《山地回忆》中,那个曾经锋芒毕露的妞儿,当她看到战士在冷天中还光着脚时,热情、爽朗地邀请其到家中给战士做袜子,展示了冀中姑娘纯真、诚恳而又热烈的精神世界。吴召儿在战争时成了女自卫队员,反“扫荡”时成了军队的向导,在敌人出动的时候,带领干部截击敌人。转移中人民爬得筋疲力尽,但她却像“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3]251浪漫描写中展现了吴召儿的坚定信心、勇敢的行为以及崇高的责任感。此外,还有勇敢肩负生活重担,但又乐观的姑娘小红(《采蒲台》);细心呵护伤员的香菊(《浇园》),这些多姿多彩的形象栩栩如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简洁凝练、如诗如画的语言运用更是其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孙犁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善于发现诗意,以情感人,以景动人。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诗情画意,不做作,不娇柔,不雕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同时他的语言具有浓郁的口语风味,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与乡土气息。孙犁从中学开始便生活在冀中,其抗战生涯也始于白洋淀,因此,他非常了解冀中人民的生活与语言。孙犁创作中,无论是叙述还是对话,都如口语般清新自然。《浇园》中“天旱的厉害,庄稼正需要雨的时候,老天偏不下雨。这叫卡脖子旱,高粱秀不出穗来”。[3]217“卡脖子旱”是冀中地区的农村的口语,这个词语生动形象,给人以具体的感受,不仅体现了孙犁对事物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生活的切身感受,更呈现出其身上浓郁的冀中气息。
孙犁自抗战以来便活跃于文坛,凭借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吸引了大量创作者与读者,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燕赵大地尤其是白洋淀是孙犁创作的起点,也是其一生挚爱的故乡,创作中他总是将鲜明而浓厚的地域文化融入作品中。在这些蕴含了鲜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我们都能强烈体悟到孙犁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感知到其对自己家乡的浓烈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