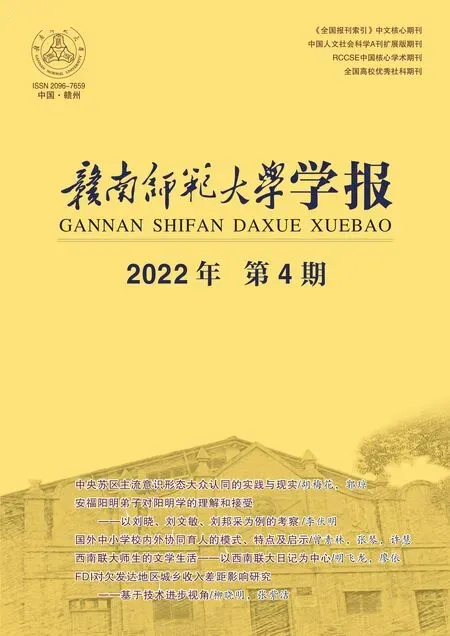安福阳明弟子对阳明学的理解和接受
——以刘晓、刘文敏、刘邦采为例的考察*
李伏明
(井冈山大学 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 343009)
一
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其实主要是在吉安,尤其是在安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传江右王门学派学者33人中,吉安府占了22人,其中安福县又有12人,尤其是安福的刘晓是吉安地区第一个拜王阳明为师的学者,安福的惜阴会是江西的第一个阳明学讲会,安福的邹守益是公认的江右王门学派头号领袖人物。王畿称:“阳明夫子平生德业著于江右最盛,讲学之风亦莫盛于江右,而尤盛于吉之安成。盖因东廓诸君子以身为教,人之信从者众。”[1]这就是说,研究阳明学在安福的传播及其影响,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人们对阳明学传播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著名学者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二是阳明学在某一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显然,所谓阳明学在某一地区的传播,说到底就是该地区的学者传播自己所认识和理解的阳明学,这就意味着必须深入研究他们对阳明学的认识和理解,实际上就是他们在阳明学方面的学术思想成就。
学者的学术思想成就显然并非单纯研读和体悟相关文献的结果,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生平和际遇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研读和体悟相关文献的方式、角度和视野,也决定了其深度和广度。就阳明学者而言,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生平和际遇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拜师学习阳明学的动机和过程,决定了他们对阳明学的理解和接受。无论是阳明弟子、阳明学者,还是一般士民,都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识基础和现实需要来认识、解读和接受王阳明和阳明学的。至于他们的认识和解读是否“正确”,是否合乎王阳明的本旨,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要探究阳明学的实际社会影响,应当更加关注他们对王阳明和阳明学的认识、解读和接受,而不是王阳明的本旨。
王阳明本人及其学术思想当然至关重要,这是人们认识、解读和接受的对象。而且,众所周知,王阳明经历曲折,“百死千难”,学术思想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不同时期拜师王阳明的人动机不同,对王阳明及其学术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虽然此后可能会与时俱进,但必然深刻影响其本人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会极大地影响其传播阳明学的内容、方式和效果,影响着阳明学在地方上的传播及其实际社会影响。
正是由于王阳明本人的曲折复杂经历和阳明弟子不同的际遇,不同的拜师动机和过程,使得阳明学的传播呈现出复杂而多彩的景象,本文以刘晓、刘文敏、刘邦采为例展开探讨,分析阳明学的社会影响。他们对阳明学在安福的传播贡献卓著,名气比不上邹守益,但实际贡献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
尽管邹守益是公认的头号领袖人物,但吉安地区最早拜师王阳明的学者是刘晓,刘晓(1481—1562年),字伯光,号梅源,正德八年(1513年)举人,安福三舍人。正德九年(1514年),刘晓拜师王阳明于南京,回到家乡安福后,将其所学所悟与本地学者分享。他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安福乃至吉安地区阳明学的“嘉谷之种”。[2]
不过,刘晓赴南京,并不是基于对王阳明的政绩或学术的敬仰而前往问学拜师的。实际上,当时王阳明职任南京鸿胪寺卿,正四品,这在明代虽然属于高级官员系列,但其实没多大实权,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政绩。虽然热衷于讲学,但在学术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突破,讲学的内容也大抵上是他在龙场所悟之道。
据束景南先生考证,刘晓是奉命携带新修成的《竹江刘氏族谱》赴南京请王阳明作序跋的。[3]770-772安福竹江刘氏与刘晓所属的三舍刘氏都属安福南乡望族,虽然不是同一支宗族,但相互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府城吉安有共同的刘氏宗祠。竹江刘氏家族当时甚为显赫,王阳明在《竹江刘氏族谱跋》中指出:“且竹溪翁之后,其闻于世者历历尔。至其十一祖敬斋公而遂以清节大显于当代,录名臣者以首廉吏。敬斋之孙南峰公又以清节文学显,德业声光,方为天下所属望。”[4]敬斋即刘实(1396—1461年),字嘉秀,号敬斋,宣德五年(1430年)进士。南峰即刘丙(?—1518年),字文焕,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当时任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据地方史志记载,刘丙曾对王阳明有“知遇之恩”。正德四年(1509年),刘丙任贵州按察使,延请其时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的王阳明为诸生讲学,王阳明大为感激。(1)刘学愉修: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竹江刘氏族谱》修成后,(正德八年,1513年)考取举人的刘晓即奉命携带族谱,前往南京请王阳明为族谱作序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刘晓的器重和提携。刘丙作为王阳明的“故交”,且政治地位实际上比王阳明稍高,刘丙请王阳明为自己的族谱作序跋,王阳明自然会欣然应允,他热情地接待了刘晓。王阳明当时正热衷于讲学,身边有一批追随者,于是刘晓和他们一起研习王阳明所悟之道,一起切磋交流,并正式拜师王阳明。《王阳明年谱》记载说:
自徐爱来南都,同志日亲,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季本、许相卿、王激、诸偁、林达、张寰、唐愈贤、饶文璧、刘观时、郑骝、周积、郭庆、栾惠、刘晓、何鳌、陈杰、杨杓、白说、彭一之、朱箎辈,同聚师门,日夕渍砺不懈。[5]
束景南指出:
大致其时来受学者包括五类人:一类为是年科举中进士而来南都任职者,如黄宗明、林达等;一类为是年科举落第而来南都受学者,如薛侃、陆澄、季本等;一类为昔日弟子而再来南都问学者,如唐愈贤、杨礿、刘晓等;一类为由原弟子或友人介绍新来受学者,如马明衡、郭庆、何鳌等;一类为原即在南都任职者,如穆孔晖、王道等。[3]751
刘晓此次拜师问学的王阳明,(2)没有证据证明刘晓此前曾拜见过更不用说师从过王阳明。或者说,在刘晓的心目中,大抵上只是一位对程朱理学持批评态度,对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有新颖感悟和见解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学者。刘晓虽然经认真学习体悟,感到大有收益,但未必将阳明学认定为绝对真理——只是接触学习到了一种新颖的学术理论而已。正因为如此,刘晓回到安福后,并没有大肆宣扬,只是将自己所学与族人刘文敏、刘邦采等人分享,并吸引了相距不远的南乡福车村刘阳等人,刘阳正式拜刘晓为师。同治《安福县志》记载说:
初,王阳明为南鸿胪,吉郡士未有及门者。惟晓最先受学,与徐曰仁、薛侃辈切磋。久之,充然有得。守仁别以诗,期许甚。至归,以语刘文敏、刘邦采、刘阳,同往师焉。晓结屋梅花之源,合同志岁时讲业,题曰“惜阴”。守仁为著《惜阴说》。[6]
王阳明巡抚南赣时,刘阳奔赴赣州拜师问学王阳明。阳明学因此在安福得到传播。《三舍刘氏六续族谱》记载说:
时吾宗北面姚江者,始于梅源,而狮泉、印山继之,两峰又同偕九人者往,一门九刘,雅为文成推许。(3)《三舍刘氏六续族谱》卷三十,《家传八》。
刘晓似乎在学术上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他没有提出什么独树一帜的学术主张,但他对阳明学在安福的传播贡献极大。三舍刘氏本来就是安福南乡的望族,科举成就卓著,强大的宗法宗族势力为刘晓等人传播阳明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最初正是借助这一平台传播阳明学的。刘晓和刘邦采、刘文敏等人于嘉靖五年(1526年)在刘晓的梅源书屋中组织起了江西的第一个阳明学讲会——惜阴会。在参考借鉴了中天阁讲会的模式的同时,又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开创了阳明学在吉安地区传播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模式,很快得到王阳明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以三舍惜阴会为模式的阳明学讲会不仅很快在安福各地推广开来,而且传播到吉安府其他各县。此后各地的阳明学讲会往往统称为惜阴会——虽然通常有自己的名称。刘晓及三舍惜阴会在阳明学研究和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4)关于安福惜阴会,见拙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第三章第一节。鉴于该书中已经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吉安地区的阳明学讲会,本节只做简要的介绍说明。
三
在安福的阳明学者中,刘文敏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一介布衣,但在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阳明学界地位崇高。他去世后,江西督学邵梦麟下令助祭。万历十二年(1584年),吉安知府余之祯和安福知县闵世翔下令将刘文敏祀于安福复古书院。黄宗羲认为,刘文敏是江右王门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刘文敏(1490—1572年),字宜充,号两峰,安福南乡三舍人。“三舍之刘,在邑为巨姓,所居东南,有两山屹立并峙,学者既瞻望先生素养之高不可及,以两山之秀而特起也,足以配先生之德,遂称之曰两峰先生云。”尽管刘文敏学术地位崇高,备受尊重,但相关文献资料甚少,据说是因为他不喜著述,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介布衣。据记载,刘文敏“自幼朴实,不知世有机械事”,但矢志圣贤,“思所以立于天地间者”。基于思想文化界的共识,要成为圣贤,首先必须研习程朱理学,体悟和践行天理,格物致知则是全部问题的基础,刘文敏因此致力于探究和体悟格物致知之学。
但刘文敏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找到成为圣贤的门径,以至于经常彻夜难眠。族人刘晓从南京回来后,将其所得的王阳明的语录与他分享,刘文敏由此接触到了阳明学,但他显然并没有立即接受阳明学。与刘晓一样,刘文敏最初大约也认为王阳明只是一位对程朱理学持批评态度,对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有新颖感悟和见解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学者。
可能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刘文敏并没有前往赣州向王阳明拜师问学,不过设法得到了《传习录》。据王时槐所述,刘文敏是在研读《传习录》之后,发现其“所论格物致知之旨与宋儒异,展(辗)转研思,恍然有悟,遂决信不疑,躬践默证,久之,惟觉动静未能融贯,乃叹曰:‘非亲承师授不可。’”[7]476也就是说,在刘文敏看来,所谓圣人之道无非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的精神境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诠释是正确的,但自己难以理解和消化,于是率刘邦采等弟侄一共9人前往绍兴拜师问学王阳明。
显然,刘文敏前往绍兴拜师问学王阳明,与其说是基于对王阳明的敬仰,或者说是为了研习阳明学,还不如说是为了得到王阳明的亲自点拨,帮助自己真切地体悟与天地万物为一的精神境界。
刘文敏的绍兴之行大有收获,觉得王阳明给他指出了一条成为圣贤的正确道路,自己只需要切实地践行即可。从此,刘文敏心无旁骛,矢志追求“心外无物”的境界,“一闻正学,即弃去不复应试,布袍蔬食,韬光晦景,没齿不求人知。”“身任斯道,安于躬耕”。[7]477
刘文敏并没有在学术理论上做太多探究,也没有提出具有显著特色的观点主张。他坚信,所谓“格物致知”,所谓致良知,无非是在生活实践中体悟“心外无物”之境,进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的精神境界。在刘文敏看来,他当初之所以“动静未能融贯”,就是因为被外物干扰,只要回归虚寂之心,也就是回归人的天性,不被外物干扰,自然动静融贯,与天地万物合一,“吾心之体,本止本寂,参之以意念,饰之以道理,侑之以闻见,遂以感通为心之体,而不知吾心虽千酬万应、纷纭变化之无已,而其体本自常止常寂。”[8]基于这一判断,刘文敏“每与学者言知体虚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习气,涤凡情,纤瑕勿留,意念感应,生生化化,务协天则,云销日朗,垢尽鉴明,天全而性复矣。”[7]476-477他给弟子王时槐等人的遗训是:“知体本虚,虚乃生生。虚者天地万物之原也,吾道以虚为宗,汝曹念哉,与后学言,即涂辙不一,慎勿违吾宗可耳。”[7]478
刘文敏强调,回归虚寂之心并不是走向禅定。在他看来,只有回归虚寂之心才能体悟到心体或者说良知本体,真正地让至善之“心”做主宰,从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沉溺于计较一事一物,不意气用事,进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换言之,回归虚寂之心是为了超越或超脱纷繁复杂的现实,确保消除物欲的可能性。
但是,个人的精神境界与其实际的社会生活并不是一回事。尽管现实生活中的刘文敏致力于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也备受人们敬重。但他只有初级功名,为了维持生计,他长期设馆执教,教学内容自然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是说,他必须教授程朱理学。毕竟,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的科目,指导帮助弟子通过科举考试是设馆执教的首要任务。
这就意味着刘文敏必须把他的个人精神追求与社会生活实践作必要的区分。一方面,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坚持追求让心做主宰,追求生活超脱。另一方面,虽然乐意参加阳明学讲会活动,积极参与切磋交流,但其不大愿意组织领导相关活动,在社会教化上也不是很热心,其“安于躬耕,无慕世用”,[7]477尽管如此,刘文敏还是培养出了王时槐、陈嘉谟等具有崇高政治社会地位的阳明学者。
四
刘邦采(1492—1577年),字君亮,号狮泉,是刘文敏的从弟。他早年与刘文敏一起学习,与刘文敏一样,刘邦采也从小便立志成为圣贤,对科举不感兴趣,声称“学在求诸心,科举非吾事也”。[9]437他与刘文敏同时从刘晓那里分享到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后又与刘文敏弟侄九人前往浙江拜师王阳明。据记载,刘邦采与王阳明相见甚欢,王阳明称“君亮会得容易”。[9]437刘邦采后来成为公认的江右王门学派的重要领袖人物。
刘邦采与刘文敏不同。首先,刘文敏是一介布衣,而刘邦采虽然对科举不感兴趣,但还是在各方面的劝说下,参加了乡试,并考中了举人。后出任寿宁县教谕、嘉兴府同知,职务虽然不高,但也意味着他拥有更高的政治社会地位,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无论对于他的日常生活还是学术活动都大有帮助;其次,刘邦采虽然坚信“学在求诸心”,追求个人崇高的精神境界,但他显然更重视阳明学的社会实践价值。也就是说,对刘邦采而言,阳明学首先是一种具有重大的真理性价值和现实性意义的新颖的儒家学说,因此必须付诸实践,指导人生和社会实践,进而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为此,刘邦采大力传播阳明学,致力于探究如何以阳明学指导人生和社会实践。《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儒林二》称:
守仁之门,从游者恒数百,浙东、江西尤众。善推演师说者,称弘纲、廷仁及钱德洪、王畿,时人语曰: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然守仁之学,传山阴、泰州者,流弊靡有底极,惟江西多实践,安福则刘邦采,新建则魏良政兄弟。[10]
这就意味着,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求诸心”。为此,刘邦采一方面致力于在家乡传播阳明学。他先是与刘晓、刘文敏等人组织起了江西的第一个阳明学讲会——惜阴会。后来又在惜阴会的基础上,与邹守益等人一起创办了复真书院,复真书院是阳明学研究和传播的重镇。据记载:
吾南里之有复真也,自明嘉靖戊午始。东廓先生倡之,刘狮泉、尹湖山、刘三五、周东川诸先生成之,远迩各著姓共襄之。肄业有所,博闻有书,供会有田。登其堂者,上则规斯道之精微,次亦变化气质,娴习威仪。谨出入,慎取舍,以弗即于慆淫,所造乎人心风俗者大矣。(5)王吉:《安成复真书院志》卷首《序》。
由于邹守益不可撼动的头号领袖地位,后人把复真书院的创建归功于邹守益的倡议,但南乡惜阴会学者是复真书院的主体。“吾里之有复真,则始于惜阴诸贤倡,以祀新建者也”。(6)王谦言:《王谦言序》,北京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二年原刊本。刘邦采的贡献尤为卓著。复真书院的阳明学讲会的参与者以学者和士绅为主,除了学者和士绅之间的切磋交流外,更担负起了维风导俗、教化地方的责任和使命。
另一方面,与刘文敏不同,刘邦采对学术理论探讨有相当的兴趣,他不仅与他人分享自己致良知的体悟和感受,并根据自己的体悟和感受提出相关的要求和建议,更愿意阐述致良知的理论方法。质言之,刘文敏指向的是个人的精神境界,而刘邦采则指向社会,指向社会实践。
刘邦采发现,当时学界和社会上广泛流行“良知现成”说或者说“见在良知”说,他认为,这实际上忽视甚至否定了致良知工夫的重要性,背离了王阳明良知学的宗旨。刘邦采因此奋起批判。黄宗羲说:“阳明亡后,学者承袭口吻,浸失其真,以揣摩为妙悟,纵恣为乐地,情爱为仁体,因循为自然,混同为归一,先生惄然忧之。”[9]437
在刘邦采看来,即便现成良知确实存在,也是不可直接依赖的,因为良知本体不可能自动发用流行,必须有坚实的致良知工夫。为此,刘邦采提出了他的“悟性修命”说。他认为,唯有“悟性修命”,才能真正地致良知。要成为儒家圣贤,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必须进行严格的修养,决不能空谈玄虚,更不能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必然导致无视纲常名教,危害世道人心。
在刘邦采那里,所谓“悟性修命”,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求诸心”,体悟到良知本体的存在。为此必须“虚其心”,具体地说,就是必须“澹心”“洗心”和“忘心”,这样才能使人的内在的良知本体不受蒙蔽,这是良知本体发用流行的基础。而良知本体发用流行,或者致良知的目的是完全自觉地遵守名教纲常、礼法制度,也就是必须“修九容”“慎九思”“叙九畴”。
刘邦采的“虚其心”“澹心”“洗心”和“忘心”等主张没有引起争议和质疑,人们关注的是他的“修九容”“慎九思”“叙九畴”说,认为这与阳明学的基本逻辑严重不符。
所谓“九容”,是《礼记》所要求的人的九种行为举止,即“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礼记·玉藻》)所谓“九思”,据说是孔子提出的九种言行要求,所谓“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所谓“九畴”是指《尚书·洪范》所提出的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九条基本原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刘邦采强调,“修九容”“慎九思”“叙九畴”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否则根本谈不上致良知,谈不上成为圣贤,“九容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不慎,是无心也;九畴不叙,是无天下国家也。修容以立人道,慎思以达天德,叙畴以顺帝则,君子理此三者,故全也。”[9]441
显然,所谓“九容”“九思”“九畴”,说到底是外在的客观的社会道德和制度规范,尽管他认为这些本来就是天理的体现,本来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但这些看起来与程朱理学家所倡导的道德修养方式并无二致。正因为如此,刘邦采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王畿认为:“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如此分疏,即是二用,二即是支离,只成意象纷纷,到底不能归一,到底未有脱手之期。”[11]罗洪先也认为,刘邦采的“悟性修命”说在学理上与阳明学不一致,“分主宰、流行两行,工夫却难归一。”[12]
从逻辑上说,刘邦采的“悟性修命”说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确实不一致,但对刘邦采而言,阳明学首先是个人社会实践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致良知不是空谈,人必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所遵循。进一步说,教育和引导人们严格遵守名教纲常,“修九容”“慎九思”“叙九畴”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圣贤,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的崇高精神境界,并实现天下太平。也就是说,是不是在学理上合乎阳明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阳明学被社会接受,发挥其就有的社会价值。实际上,这才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宗旨所在。
五
现代学者,尤其是从事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习惯回到王阳明及其著作本身,或回到著名阳明学者的著作本身,对其理论条分缕析,探讨其理论构成及其特征,但以此为出发点讨论社会价值和影响,这其实无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和事实的真相。所谓阳明学的传播,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在学者之中的传播,二是向社会大众的传播,也就是阳明学者如何将其所认识和理解的阳明学向社会传播,他们对王阳明和阳明学的接受、认识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理解和认识也许并不“正确”,但发生的社会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刘晓、刘文敏和刘邦采三人虽然都是杰出的阳明学者,都是江右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重要领袖,但他们对王阳明和阳明学的认识和理解有很大差异。自然地,他们传播阳明学的方式方法,尤其是社会影响不同。他们体现出阳明学在安福传播的不同侧面和特征。实际上,所谓“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正是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解,运用不同的方法手段向社会传播阳明学的成就,并因此塑造了地方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