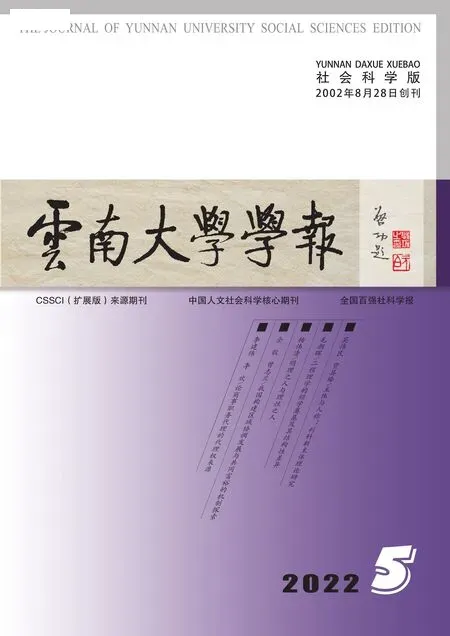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及其结构性差异
毛朝晖
[华侨大学, 厦门 361021]
自从冯友兰先生将二程截然区分开来,二程理学的异同便成为宋明理学研究的一大公案。(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69页。归纳起来,约有三种看法。主异的一方认为二程理学根本不同,分属两个思想系统,冯友兰、牟宗三、庞万里、钟彩钧等先生拥护这种看法;主同的一方认为二程思想完全相同,可以不作区分,吕思勉、侯外庐、张立文、潘富恩、徐余庆等先生支持这种看法。此外,还有一种折中看法,认为二程思想根本一致,但倾向有所不同,管道中、唐君毅、劳思光、韦政通、陈来、李景林、日本学者宇野哲人、英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等支持这种观点。(2)彭耀光:《二程道学异同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13页。
与多数理学家一样,二程理学也具有经学的奠基。(3)蔡方鹿:《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之《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据程颐透露:“(明道)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4)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8页。程颐自己治学也是“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5)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944页。这说明,二程都是自觉地回归儒家经典并以儒家经典作为各自理学的基石。事实上,在《二程集》中,除了“语录”,最主要的部分便是“经说”,包括《系辞》《书》《诗》《春秋》《论语》《改正大学》《孟子解》《中庸解》各一卷。另外,还收录程颐的经学专著《易传》四卷。关于二程理学的经学奠基,学界目前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二程经学是以《易》学为主干。例如,张岂之先生便认为“二程经学的主干是《周易》之学”。(6)张岂之:《关于二程的〈易〉学思想及其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另一种看法强调二程对“四书学”的表彰。例如,顾宏义先生认为“大力表彰《学》《庸》并将其与《论》《孟》并行者实当归功于二程”。(7)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页。此外,李明友先生折中二说,认为二程“借《周易》以抗佛学,突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是二程经学的基本内容”。(8)李明友:《理学的主题与二程的经学》,《浙江学刊》1991年第6期。本文从经学视角切入二程理学异同的争议,旨在揭示二程经学奠基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理学异同。
一、二程的“道统”论与 《四书》《易传》
二程理学的宗旨是什么?我们不妨先考察二程亲炙弟子的看法。吕希哲说:“二程之学,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而己必欲学而至于圣人。”(9)程颢、程颐:《二程集》,第 420页。范祖禹说:“先生为人,清明端洁,内直外方。其学,本于诚意正心,以圣贤之道可以必至,勇于力行,不为空文。”(1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33页。刘立之也说:“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载之后,芟辟榛秽,开示本原,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学士大夫始知所向。”(1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29页。吕、刘、范都是二程的及门弟子,三人异口同声,都认为二程理学的宗旨是“必欲学而至于圣人”“以圣贤之道可以必至”“圣人之庭户晓然可入”。此外,作为二程亲密的讲友张载也提出:“二程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今尽及四十未能及颜闵之徒。”(12)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80页。可见,无论是二程的及门弟子还是讲友,都认为二程的学术是以“学圣人”为宗旨。(13)美国汉学家葛艾儒(Ira E.Kasoff)指出:宋代以前,儒家学者虽然也学习圣人之道,但并没有明确提出通过心性修养可以使自己也成为圣人。到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哲学的“圣人”话语有一个思想转变:人们所追求的不仅是圣人之道,而且是自己成为圣人。这种“学圣人”的新观念以二程、张载为代表。参见Ira E.Kasoff, The thought of Chang Tsai (1020—10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4.
那么,“学圣人”要如何入手呢?
程颢主张向圣贤学习。圣贤之所在,便是道之所在,因此,最关键的便是厘清“道统”。确定“道统”的意义在于,只有先确定“道统”的传承,才能确定谁是“学圣”的对象。他在《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提出:“昔七十子学于仲尼,其传可见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余门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为学,虽同尊圣人,所因而入者,门户则众矣。”(1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503页。在这一“道统”中,自孔子以下,程颢最推崇的人物是颜回,其次则是曾子和孟子。他一再强调:“人当学颜子之学。”“孟子才高,学之无可根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15)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36、19页。程颢认为,孟子去圣较远,而且,孟子才高,难以着力;相比而言,颜回去圣较近,入圣工夫最可“根据”,学者“有用力处”。在个别地方,程颢也曾将曾子与颜回并列。他说:“颜子默识,曾子笃信,得圣人之道者,二人也。”(16)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19页。总之,颜、曾、思、孟都继承了“道统”,但他们的“学”却有所不同,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入圣工夫有所不同。显然,正是从工夫论的角度,程颢最推崇颜、曾之“学”。
程颐的“道统”论与程颢的几乎完全一致。他说:“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17)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27页。所不同的是,程颢在《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认为邵雍继承了“道统”;而程颐则认为是程颢“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18)程颢、程颐:《二程集》,第640页。换言之,程颐认为是程颢而不是邵雍继承了孟子以后失传的道统。
与其兄一样,程颐也对颜回和曾子推崇备至。他提出:“曾子传圣人之道,只是一个诚笃。”又认为:“颜、孟之于圣人,其知之深浅同,只是颜子尤温淳渊懿,于道得之更渊粹,近圣人气象。”(19)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58、151页。根据程颐的判断,如果单从对“道”的领悟来看,孟子与颜回的理解“深浅同”,但如果从修养工夫来看,颜回“于道得之更渊粹”,而孟子则仍略有不足。显然,程颐对颜、曾的推崇也是从工夫论的角度得出的。
二程认为,学习圣人之“道”的不二法门是求之于“经”。就像程颐所透露的,程颢便是“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类似地,程颐也认为:“为学,治经最好。”(2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页。二程共同主张:“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2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95页。蔡方鹿先生指出:“二程‘经所以载道’的思想不仅提出治经学的目的在于明道、明义理,而且强调圣人之道存于经书之中,与经书不相脱离,从经学入手,才能掌握圣人之道。”(22)蔡方鹿:《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2页。
那么,“学圣”应该治哪些经典呢?
二程认为最根本的经典是《论语》《孟子》。二程认为:“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2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05页。二程认定《论语》《孟子》是圣人之“道”的标准。如果读《论语》《孟子》而不见道,那么,就算读再多书也是枉然。如果能明白《论语》《孟子》中的道,再去面对其他事物时就像是有了“丈尺权衡”。基于这一认识,程颐进一步提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2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22页。这是明确主张以《论语》《孟子》作为《六经》的根本。
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两本经典尤其是《论语》保存了孔门言语,蕴含了圣人气象。程颐说:“《乡党》分明画出一个圣人出。”(25)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94页。伯温问:“学者如何可以有所得?”程颐答道:“但将圣人言语玩味久,则自有所得。当深求于《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耳。若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26)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79页。可知,只要能于二书熟读玩味,则不仅能学习圣人之道,而且能观摩圣人气象,涵养久了会“甚生气质”。这一重要性,是其他经典无法比拟的。
除了《论语》《孟子》,二程认为最根本的经典还有《大学》《中庸》和《易传》。唐棣初见程颐,问:“初学如何?”程颐告诉他:“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又说:“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又说:“《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中庸》乃孔门心法。”(27)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77、311、325、411页。众所周知,程颐毕生深研《易传》。程颢也十分推崇《易传》,他说:“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28)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3页。不过,二程对《大学》《中庸》《易传》的推崇与对《论语》《孟子》的推崇不同。《论语》《孟子》记载圣人气象最为亲切,而《大学》《中庸》《易传》则更多的是对圣人之道的理论说明。二程说《大学》是“入德之门”“修身之序”,《中庸》是“学者之至”“孔门心法”,《易传》是“圣人用意深处”,都旨在强调《大学》《中庸》《易传》是传圣人之道的“心法”“用意深处”和修养工夫的“序”。
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共同构筑了二程的“道统”,而“道统”的叩问正是“学圣”宗旨的内在要求。二程表彰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程颢说:“《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又说:“《中庸》一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卷书。”(29)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8、160、153页。这是说《大学》《中庸》继承了孔门的道统。二程又认为:“《易》之书惟孔子能正之,使无过差。”(3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94页。孔子所“正”的不是卦爻辞而是《易传》,则《易传》出自孔子,也直接承载了孔子的“道”。比较而言,《论语》《孟子》更多地代表了具体的圣人言行和圣人气象,而《易传》《大学》《中庸》《孟子》则更多地阐发了圣人之道。总之,二程的“道统”建构是基于以上五部经典。
二、二程的本体论与《易传》
如前所述,二程理学的宗旨是探究圣人之道并使自己成为圣人。所谓圣人之“道”,也就是二程所说的“理”或“天理”。“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整个宋明理学继承了二程对“理”的重视,这也是人们把这一时期新儒家称为理学的基本原因。(31)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因此,我们要了解二程所说的圣人之道,就必须先了解他们所说的“理”。
对于程颢而言,“理”即是“天理”。他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32)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24页。其实,“天理”这个概念并非程颢首创,而是在先秦便已出现。例如,庄子“依乎天理”(《庄子·养生主》),韩非子“不逆天理”(《韩非子·大体》),《礼记·乐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但总的来说,“天理”这个概念在先秦思想中并没有被特别强调,使用的例子也非常有限。那么,程颢“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程颢所说的“天理”,首先是指自然世界的存在原理,有时也被称为“天道”。例如,他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3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21页。程颢认为此“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辩证法具有存在的普遍性,因而是“天地万物之理”,这是没有例外的。同时,这些原理也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原理。
其次,“天理”也是指人文世界的价值本体。例如,程颢说:“理、义,体用也。”“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3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33、124页。这即是说,“理”是“义”的价值本体。以“忠”“恕”关系为例,“忠”是天理,是“恕”的本体;“恕”是人道,是“忠”的作用。
由此可知,程颢的“理”概念具有两重性。“理”既是自然世界赖以存在的原理,也是人文世界赖以建立的价值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理”既是存在的本质,也是价值的本源;既是存在本体,也是价值本体。陈来先生对这一点有很好的阐述:“二程哲学中的‘天理’既指自然的普遍法则,又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天理的这种意义本身就表现了天人合一。”(35)陈来:《宋明理学》(第二版),第63页。传统的西方本体论是关于“存在”(being)的理论,杨国荣先生指出:“存在的现实形态既关联‘是什么’,又涉及‘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36)杨国荣:《存在与价值》,《文史哲》2003年第3期。程颢的“理”概念典型地体现了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的两重性。用休谟的概念说,程颢的“理”既是“实然”之理,也是“应然”之理。休谟对“实然”能否推出“应然”,或能否从“是”(to be)命题推出“应该”(ought to be)命题,持保留态度。(37)David Hume,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Vol.2, Edinburgh: Adam Black and William Tait and Charles Tait, 1948, p.236.但是,这一困惑对于程颢而言并不存在,因为他的“理”概念具有上述的两重性。正是这种两重性消泯了实然与应然的鸿沟。
程颐所说的“理”同样具有这种两重性。一方面,他也用“理”指代自然世界的存在原理。例如:“物理须是要穷。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辞,更有甚?”(38)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57页。在这里,他将“物”当作自然,而将“理”当作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的自然原理。另一方面,他也用“理”指代人文世界的价值本体。例如:“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39)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14页。这里的“理”显然是价值之理,指的是人心之中固有的价值本体,只要不受物欲习气牵制,此“理”便长存人心。因此,程颐反复强调:“灭私欲则天理明矣。”(4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12页。
关于二程的本体论,冯友兰先生曾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二程对于“理”的见解不同,程颢所说的“理”指一种自然的趋势,程颐所说的“理”则略如希腊哲学中的“概念(理念)或形式”。(4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875页然而,如上所述,无论是程颢所指的自然的趋势,还是程颐所指的“概念(理念)”或“形式”,都并不仅是自然世界的存在本体,而且也是人文世界的价值本体。在这一根本立场上,二程的本体论并无本质差异。因此,葛瑞汉先生将西方哲学“一元”与“二元”的对立用在二程身上也并不适切。(42)A.C.Graham, Two Chinese Philosophers: Ch‘êng Ming-tao and Ch‘êng Yi-ch‘uan,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58, pp.119-126.
尽管二程的本体论消弭了“实然”与“应然”的鸿沟,但他们必须论证二者的统一性。
二程论证说,“实然”的自然本体与“应然”的价值本体密不可分。二程认为:“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谓之教,孟子在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4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页。与张载一样,二程所说的宇宙也是一个气化的宇宙。程颢指出:“《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4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18页。阴阳是器或气,是“形而下”者;道,则是“形而上”者。这说明,在二程的形而上学中,道与器、理与气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然而,“道”与阴阳原不相离,因此说“元来只此是道”。
由此,二程认知的自然宇宙与道德宇宙也是一个整体。因为二程认知的自然宇宙是一个万物一体、相互交感的宇宙。一方面,二程强调人与宇宙的一体性。二程认为:“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45)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5页。这样,自然宇宙就成为一个充满道德感受的“仁”的宇宙。另一方面,二程强调人与宇宙的交感。程颐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46)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52页。这意味着,宇宙中的人与万物都是主体性的存在,既是“应者”,也是“感者”。周广友先生即根据程颐对《周易·咸卦》的诠释,指出程颐的“感”概念是对宇宙万物的“一种本体论的说明”。(47)周广友:《程颐咸卦阐释中的感应论简析》,《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春之卷。事实上,这两条语录都被选入《近思录·道体》篇,也足见其在本体论上的重要性。(48)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33页。对于二程而言,“感”不但是自然宇宙的存在本体,而且是“仁”的本体论根据,是孕育道德的价值本体。如此,“感”的概念实现了“实然”与“应然”的统一。
我们在上文中看到,二程是通过《系辞》来说明道器、理气的统一性。事实上,程颢便是通过《系辞》明确论证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实然与应然的统一性:
“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继之者善也”,有道则有用,“元者善之长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49)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35页。
程颢的论证是一种“体用”论证。基于“体用”视角,他论证有“体”则必有“用”,而“道”便是所谓“体”,或“道体”。程颢援引《系辞》的话,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以阴阳气化为存在本体,这便是“道”;“继之者善也”是阴阳气化的作用,“有道必有用”,顺应着“道”便自然产生“善”,这即是价值本体。这表明,“道”与“善”在“体用”的意义上具有统一性。
基于上述本体论,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著名命题: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5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92页。
其实,“性即理”的论断可以从上述《易传》的诠释中直接推出。既然顺着“道”便是“善”,体现在人身上便是“性”。那么,“性”实际上就是“道”在人身上的具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说“性即道”,或者说,“性即理”。这里说“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就是《易传》所谓“继之者善也”;这里说“所谓理,性是也”,就是《易传》所谓“成之者性也”。由于“理”具有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的两重性,因此,“性”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理”是指阴阳气化的存在本体,由此产生人的自然人性;另一方面,由于“理”是指人文世界的价值本体,由此产生人的道德人性。程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5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81页。便是强调自然人性与道德人性的两重性。
三、二程的工夫论回环与《中庸》
由于二程的本体论具有两重性,强调“天道”与“性”的统一与贯通,这决定了他们的工夫论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天道”是价值本体,因此,只需诚意即可由“天道”直接显发道德人性,这便是“诚”的工夫;另一方面,“天道”是存在本体,由此产生自然人性或所谓“气质之性”,这就需要后天的努力,才能克治自然人性,从而朗现“天道”,这便是“敬”与“致知”的工夫。
二程通过《中庸》(52)今本《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中有《中庸解》一卷,据庞万里先生考证,认为“《中庸解》既非程颢亦非程颐所作,而是吕大临之作品”。但姜海军先生指出“其中的观点主要还是二程思想体系的展现”。本文以语录与《中庸解》互参,以确定二程的工夫论。参见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7页;姜海军:《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阐发了这两种工夫论。二程指出:
“诚”者,理之实然,致一而不可易也。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无二,虽前圣后圣,若合符节,是乃所谓“诚”,“诚”即天道也。天道无勉无思,然其中有得,自然而已。……“诚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诚而复之,故明有未穷,于善必择,诚有未至,所执必固。善不择,道不精,执不固,德将去。学问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5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158页。
又,
理之实然者,至简至易。既已至之,则天下之理,如开目睹万象,不假思虑而后知,此之谓“诚则明”。致知以穷天下之理,则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于简易实然之地,而行其所无事,此之谓“明则诚”。(5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158-1159页。
在这里,二程对《中庸》的“诚”与“诚之”或“自诚明”与“自明诚”,做了工夫论的区分。根据二程的界定,“诚”的工夫本身就是“天道”“理之实然”,所谓即本体即工夫。也就是说,这种工夫是本体自然的发用,因此“不假思虑而后知”“自然而已”。反之,“诚之”的工夫则是“以人求天者也,思诚而复之”,需要通过后天的“学问思辨”或“致知”工夫。二者的结果殊途同归。
在《中庸》中,跟 “诚”与“诚之”和“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区分相应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区分。《中庸》提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二程发挥说:
德性,广大高明皆至德;问学,精微中庸皆至道;惟至德所以凝至道也。虽有问学,不尊吾自德之性,则问学失其道矣。虽有精微之理,不致广大以自求,则精微不足以自信矣。(55)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162页。
这说明,“尊德性”与“道问学”工夫是相须为用的。即便我们具备德性的精微之理,但如果不做“道问学”工夫,则“精微不足以自信矣”;反之,即便我们致力于学问思辨,但如果脱离“尊德性”工夫,则“问学失其道矣”。
二程的工夫论沿袭了《中庸》的上述二分法,但各有侧重。程颢更重视的是“诚”的本体工夫,也就是说,只要认识本体,就自然具足工夫。这种工夫被程颢称为“识仁”: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56)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6-17页。
在这里,程颢提出“识仁”工夫。从本体论讲,“仁”便是“浑然与物同体”。从工夫论讲,关键是以“诚”“敬”存之。在这段文字中,程颢并没有对“诚”“敬”进行明确界定。但在其他语录中,程颢提出“敬胜百邪”。(57)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19页。可见,“敬”是对邪恶的防闲。那么,上文所谓“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未尝致纤毫之力”,说的显然不是“敬”的工夫,而是“诚”的工夫。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需要“敬”的防闲工夫呢?这是因为,如果“昔日习心未除”,仁心便会懈怠,“若心懈,则有防”,这才需要做“敬”的防闲工夫。
程颐则更重视“敬”与“致知”的工夫。他说:“真近诚,诚者无妄之谓。”(58)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74页。可见,“诚”就是符合天理,否则即是伪、妄。他也肯定:“学者不可以不诚。虽然,诚者在知道本而诚之耳。”(59)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26页。不过,这也表明程颐认为最首要的工夫是“知道本”,只有“知道本”才能“诚之”。怎样才能“知道本”呢?程颐提出两项工夫。一是“敬”。他说:“闲邪则诚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诚将来存着。”(6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49页。这就是说,如果能做到“敬”的工夫,亦即防闲工夫,便能够“诚自存”。二是“致知”。他说:“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又说:“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6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88、187页。为此,程颐将“敬”与“致知”双提并举,如“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62)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88页。
这种倾向在程颐十八岁所作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中便已初露端倪:
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故《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6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577页。
在这里,程颐强调“先明诸心”。也就是说,修养工夫的关键在于人为努力,这包括“尽其心”“信道笃”。所谓“信道笃”,是指必须以圣人之道作为效法的榜样,“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并且,要对这些圣人之道“尽其心”或致“思”,这样才能“邪僻之心无自生矣”。显然,程颐关注的焦点也是“习心”陷溺的问题。如何摆脱外在习气对仁心的习染呢?程颐的办法是诉诸《中庸》的“自明诚”或“诚之”的工夫。
从整体上看,二程的工夫论是继承《中庸》的二分法,而且都由两个环节构成。一是顺向地由“天道”自然发用为“人事”的本体工夫,这即是“诚”的工夫;二是逆向地通过“人事”的后天努力而逆证“天道”,这即是“诚之”的工夫,其中又可细分为“敬”与“致知”两项工夫,亦即程颐所谓“敬义夹持”工夫。这两个环节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一顺一逆的“回环”。前者是顺向地由“天道”下贯“人事”,由本体顺显工夫;后者是逆向地由“人事”上达“天道”,由工夫逆证本体。两种工夫是互为其根、交互促进的关系,共同构成一种工夫论的“回环”,并以《中庸》作为经典的依据。
关于二程的工夫论,许多学者认为二人截然不同。冯友兰先生认为二程的修养方法一个是“先立乎其大者”,一个是敬义双修,开启了后来心学、理学二派。(6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894页。此后,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都沿着这条思路。唐先生说:“大率明道偏在积极言存诚敬,以内直外说工夫;伊川则偏在由消极之闲邪使心不之东,不之西,不之此,不之彼,自整肃警醒其自己,说工夫。”(6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牟先生说:“(伊川)涵养是涵养那‘经验的直内”之经验的敬心也,不是孟子之言存养,是存养那先天的道德本心也。”(6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403页。彭耀光先生指出唐、牟的判定是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划分,(67)彭耀光:《二程道学异同研究》,第113页。这是切中肯綮的批评。又如,葛瑞汉先生判定伊川是“客观的方法”(objective approach)而明道是“主观的方法”(subjective approach),(68)A.C.Graham, Two Chinese Philosophers: Ch‘êng Ming-tao and Ch‘êng Yi-ch‘uan, p.75.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上文的分析表明二程的工夫论共享了同样的“回环”结构,都具有顺向与逆向、积极与消极、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的两环,只是侧重有所不同罢了。
四、从《大学》改本看二程工夫论的差异
尽管二程的工夫论都具有一个“工夫论回环”的义理结构,但在一顺一逆的两个环节中,二程各有侧重,强调了不同的入手方向。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们的《大学》改本中。二程重视《大学》,据刘斯原先生考证,“《大学》之有改本,始于程颢。”(69)刘斯原:《大学古今本通考》,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1978年,第205页。通过《大学》改本的比较,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二人工夫论的差异。
在本体论方面,二程都认为“明德”即是“理”。程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于至善’,反己守约是也。”(70)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37页。这就是说,明“明德”就是明“理”。程颐也说:“‘亲民’,以明德亲民。”(7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47页。这也是以“明德”为本体,以“亲民”为作用,而上文已经阐明,程颐所说的本体就是“理”。
基于这一认识,二程都首先凸显“明明德”的诠释。“《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这一段,连同对“亲民”“止于至善”的诠释,在《大学》古本中原来都位于“诚意”的诠释之后。二程将这三段诠释统统提到“诚意”的诠释之前,用以阐发“明德”概念。其中, “皆自明也”,凸显了“明德”作为价值本体的内在性与主体性;“天之明命”,则凸显了“明德”具有客观的存在本体的根据。二程的《大学》改本没有注解,朱熹继承二程改本,注解说:“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7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更明白地强调了“明德”本体的两重性。
然而,在工夫论方面,程颐强调“致知”的优先性。为了凸出“知”的优先地位,程颐特地将“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一段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诠释之后提前到“此谓知本”之前。这样,“致知”就被提到首要的位置,不但被置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节的诠释之前,而且被置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诠释之前。程颐的用意,大概是想用“致知”来诠释“明”,用《康诰》《大甲》《帝典》三语来诠释“明德”,这样,“致知”就成为“明明德”的首要工夫。
在程颐看来,“致知”工夫比“诚意”工夫更具优先性。程颐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于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诚。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尝复行。他人复行,知之不至也。”(73)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65页。程颐认为,“大学之道”最首要的工夫是“明明德”;同时,他又用“知”来诠释“明”,用“诚”来解释“至善”。依据这一逻辑,他得出:“知既至,自然意诚。”
程颐将“致知”置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诠释之前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二程语录中有一条说:“明德、亲民,岂分人我?是成德者事。”(7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84页。这条语录将“明德”“亲民”视为“成德者事”。在程颐的《大学》改本中,“致知”被置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诠释之前,显然也是以“致知”作为“明明德”的工夫,而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成德者事”。于是,“致知”便被诠释为成就“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首要工夫。根据上文的分析,这条语录反映的应该是程颐的思想。
与程颐不同,程颢强调“诚意”的优先性。与《大学》古本一样,程颢维持“诚意”的优先次序,将其置于所有修养工夫的首要地位。如前所述,程颢最重视的是“诚”的工夫,这就是《大学》的“诚意”工夫或他在《识仁篇》中提到的“良知”工夫。他认为,只要不自欺,每个人都自然能够“存久自明,安待穷索”。由于“诚”能够“存久自明”,“防检”“穷索”便是次要的甚至不必要的工夫,这是程颢强调“诚”的工夫的优先性并维持《大学》古本“诚意”地位的理由。
此外,程颢没有凸显“致知”。在《大学》古本中,“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一段原本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诠释之后,“修身”的诠释之前。如前所述,程颐特地将这一段提前到“此谓知本”之前,而且居于所有修养工夫的首位,组合成“致知”的诠释;而程颢则将其后移到“治国”的诠释末尾,未予重视。
这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与他们对“致知”工夫的态度有关。程颢在《识仁篇》中强调的“知”是偏于道德意义的“良知”,由于“良知”是先验的,因此,只要“诚”就足够了。程颢虽然也提到“穷索”或“致知”工夫,但这仅仅是对“诚”的工夫的一种补充。而程颐所说的“致知”则并不只是道德意义的“良知”,而是兼指经验的感官认知。例如,他说:“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或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75)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88页。在这里,“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固然也涉及道德意义的“良知”;但所谓“读书”“讲明义理”“论古今人物”,则主要是指经验知识。由于程颐所说的“知”并不只是道德意义的“良知”,因此,他理解的“致知”工夫就不能被完全还原为“诚”的工夫。明乎此义,我们就能理解程颐为什么一定要在“诚意”一节之前特立“致知”一节,而程颢却不需要这样处理。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二程理学的宗旨是“学圣人”,出于这一宗旨,二程首先致力于确立“道统”,他们建立“道统”的根据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部经典。二程认为,《论语》《孟子》保存了圣人言行和圣人气象,而《易传》《中庸》《大学》则阐明了圣人之道的本体与工夫。二程的本体论是奠基在《易传》的基础上。二程本体论的核心概念是“理”,而他们所说的“理”概念具有两重性,既指存在本体,也指价值本体。二程对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统一性的论证都是以《易传》作为经典依据,其工夫论也都具有一个“工夫论回环”的义理结构,包括一个顺向的“诚”的环节与一个逆向的“敬”与“致知”(“敬义夹持”)环节,共同构成一个工夫论的回环。这一回环结构可以追溯到《中庸》中“诚”与“诚之”和“自诚明”与“自明诚”以及“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双向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二程的工夫论回环是以《中庸》作为经学奠基。不过,在这一工夫论的回环结构中,程颢更重视的是顺向的“诚”的一环,而程颐更重视的则是逆向的“敬”与“致知”的一环。这一差异在他们各自的《大学改本》中被充分地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