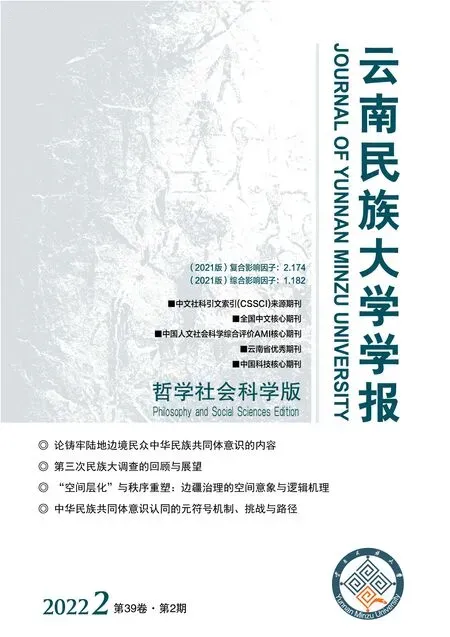被面与哈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帛礼”认同与民俗实践
孙海芳
(西安外国语大学 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其内涵特质是“共同性”(1)丹珠昂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构成、内涵特质及铸牢举措》,载《民族学刊》2021年第1期。,即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疆域,共同书写的历史,共同创造的文化,共同培育的精神。(2)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微观意识层面的自觉性行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有力见证,“如何形成”的过程性最能体现其演进历程,“如何动态”地理解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凝合与认同作用的核心物质及其主导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不可忽视的视角。
在西北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常见“搭被面”(俗称“披红”)的现象,即在重要的民间仪式中,为特定的人群披上被面,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寓意。一方面,为重要宾客“披红”表示尊敬,是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如在丧仪中,逝者的母舅方(大外家(3)逝者母亲的娘家人,如舅舅或者舅舅的子代。)、娘家(小外家(4)逝者兄弟及其子代。)来吊唁,主家就会以献礼形式为他们披上鲜艳的被面,表示尊敬。另一方面,“披红”有辟邪之意,例如新婚夫妇参加别人的婚礼时,或者探视产妇时,或者即将婚嫁的新人参加葬礼时,在新人身上“披红”,有辟邪之意;还有一种现象更为常见,如祝福他人新婚、新房奠基、购买新车等吉事时,赠送被面可表达祝福之意,这与藏区常见“献哈达”习俗的愿景有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在民间,“被面”除了承担日用品的实用功能外,还具备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那么,为何在诸多实用之物中,“被面”会被赋予丰富的精神含义而广为流传呢?可否从“微观”意识入手,在相似的同质性现象中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为此,本研究着眼于民俗所见西北地区汉族“搭被面”与藏族“献哈达”的常见仪式,结合田野调查所见活态延承的民俗案例,分析相似现象背后相同的文化基因、原型编码及精神内核,阐释蚕桑信仰、丝帛礼制及其文化形态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动力。笔者认为,西北地区汉族“搭被面”的习俗,与古时桑蚕起源的信仰原型及丝织锦绣的礼制文化有着密切关联;藏族“献哈达”的文化现象及仪式行为,是藏族同胞对农耕文明丝绸(桑蚕)价值观的接纳与认同,“搭被面”与“献哈达”同为中国式文化图景下“帛礼”文化的活态延承与记忆呈现,是微观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藏汉等广大民众共同培育、共同建构了“化干戈为玉帛”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完整体系的建构历程。
一、桑蚕崇拜:文明发生期的信仰与圣物
桑蚕文化与我国的农耕文明同根同源。如李济先生所言,中国早期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出现了桑蚕业。(5)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考古资料所见,最早可确定年代的丝织物,是河南省荥阳青台村瓮棺葬内出土的炭化纺织物,碳14测定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公元前5370±130年—公元前5535±170年)。(6)郑州市考古文物研究所:《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载《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结合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所见“半割”的蚕茧,(7)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北平: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版,第22~23页。浙江钱山漾遗址中的丝织品,(8)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黑陶上的“蚕纹”,以及妇好墓所见青铜礼器上附着的丝织物(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8页。等大量考古材料,可见我国育蚕织绸年代悠久,殷商时期就具备了较为先进的丝织技术。(10)李发,向仲怀:《先秦蚕丝文化论》,载《蚕业科学》2014年第1期。
此后的各个时期,考古发掘丝织物屡见不鲜。如西周时期的代表有:陕西宝鸡茹家庄墓葬出土的周代“绮”类丝织品;(11)李也贞,张宏源等:《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载《文物》1976年第4期。辽宁朝阳县魏营子墓出土的“绢”类丝织品;(1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载《考古》1977年第5期。山西绛县横水墓地出土的刺绣凤鸟棺罩等。(13)宋建忠,吉琨璋,田建文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6年第8期。春秋时期的墓葬中,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中发现了绛紫色绣绢、细绢等丝织品;(14)欧漳生:《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84年第4期。江西李洲坳墓葬出土大量纱、绢、绮、织锦、刺绣及经编织物等;(15)徐长青,余江安,杨庆松等:《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9年第2期。山东淄博郎家庄一号殉人墓出土了平纹组织绢、锦及丝编织物(16)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等。战国时期,丝织物种类愈加丰富,出土所见纱、绢、纨、绦、锦、刺绣、丝绳、帛书等,尤其是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35件衣衾,织绣种类达数十种,形成了完备的种类体系,为后期桑蚕丝织业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神话思维”(17)[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的支配下,日趋丰富、成熟的养蚕制丝行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神话叙事的方式被表达,例如,我国常见的神话文本中,有伏羲画蚕为丝、黄帝元妃嫘祖(西陵氏之女)始养蚕治丝、蜀王之先祖教人桑蚕的传说,将“显圣物”桑蚕及丝织物包裹在神话的象征叙事之中。笔者认为,丝织物之所以能够进入我国精神文化的象征层面,与早期“桑蚕”的神圣认知有关。
就蚕而言,它之所以成为神圣象征物,形成 “蚕神”信仰体系,与“蚕”适应自然的生理属性密不可分。一方面,蚕的一生经历了蚕卵、蚁蚕、蚕蛹、蚕蛾这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蚕成熟后吐丝结茧,蜕皮时一动不动,可谓“休眠”,犹如“死亡”,化蛹成蝶宛若再生,先民们对这一神秘的变化过程百思不得其解,《荀子·赋篇》中,将蚕的这些自然特性升华为“蚕理”,即冬伏夏游、三伏三起等,认为是蚕具有“重生”的神秘力量,这一点,与我国原始时期对“蛇”“蛙”“熊”等冬眠后“再生”的“羽化”崇拜原理相似,在此不作赘述。另一方面,蚕超强的生殖力也是被先民们广泛神化的因素之一,通过对蚕的神圣表达以祈盼氏族获得如蚕一般强大的繁衍力,为此,蚕神常常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如教民养蚕缎丝的嫘祖神、蚕丛氏、蚕姑、马头娘等。(18)屈小强:《古羌蜀人的虎、鱼、蚕崇拜》,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就桑树而言,作为蚕最为理想的食物,桑树在中国“大传统”文化视域下,是神树之一。《山海经·北山经》(19)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01页。中谓洹山:“三桑生之,其树皆无枝,其高百仞”;《山海经·中山经》谓视水:“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柎,名曰帝女之桑”(20)袁珂:《山海经校注》,第208页。;又《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21)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05页。,颇具神性,是为神树。
神化桑树的原因具体有三。其一,桑树上鲜红的桑葚,在原始思维“相似率”的支配下,常常与太阳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桑树与太阳神信仰有关,这一点,在汉代画像砖、帛画中极为常见,如马王堆汉墓的帛画上,“扶桑”常常成为太阳的栖身之所,为此,殷周时期有在“桑林”中祈雨的习俗。其二,桑树与生殖意义相关,如汉代画像砖中,常见桑林下男女交合的场景,桑树或为生殖崇拜之树,《艺文》卷八十八讲,伊尹诞生时,其母化成了桑树,具有浓郁的生殖意味;再如,《艺文类聚》引《春秋元命苞》中,讲到圣人稷的母亲姜嫄,因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下了稷,桑林常常等同于圣人生殖繁衍的神圣之所,可见“桑”与生殖意义的紧密关联,在中国汉语语境中,桑林甚至成为表示淫秽场所的隐语。(22)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其三,分枝能力强的桑树,被视为死而复生的超强生命力,所以桑树也是丧葬之树,具有辟邪的神性,如山东武氏祠汉画上,坟堆上绘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表达出墓上桑树的形态,桑树成为死后升天的媒介,为此,它与其他具有神秘性的树木一样,更是世俗通往神界的“天梯”,是通天建木的原型。
由此可见,从蚕到桑,再到吐丝制帛,这是中国神话语境内一套完整的神圣叙事,在中国文明起源之初就具备了“形而上”的象征意义。作为由神物蚕变化而出的“精华”,丝帛自然成为“圣物”,并携带有蚕、桑共同的象征意义,其精神层面的隐喻主要落脚在生殖与重生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原型编码。虽然较之于玉礼器、青铜礼器的研究,作为礼仪用品的丝帛研究较少,但是其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自在”的核心元素,见证了华夏文明发生及延续的演进历程,在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统合作用。因此,从“帛礼”视角下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是思考在“桑蚕”崇拜的基础上衍生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礼制文化及民俗延承,对于理解华夏文明的精神特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丝帛礼制:桑蚕信仰衍生的价值谱系
《后汉书·卷九十四·志·礼仪上》载:“汉旧仪曰,春桑生而皇后亲秉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23)范晔:《后汉书·卷九十四·志·礼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10页。,敬蚕神女圣以求早日抽丝,体现出崇蚕之礼。中国丝帛礼制的精神旨归,潜藏着上述“桑蚕”崇拜的原始思维方式与认知编码,反之,正是桑蚕崇拜的原始信仰催生了相应的“丝帛”之制。器以藏礼,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24)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可见帛与礼之间的等同意义。《礼记·礼运》言:“其治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养桑蚕就是为了织布帛,织布帛的终极意义是为了祭祀敬神,此处的丝麻布帛,是“事神致福”的媒介,也是求得神灵护佑的礼品。
随后,桑蚕生殖、重生的原始信仰进入“小传统”而逐渐延伸到政治、宗法等级、礼仪制度等方面,遍布在中原王权国家的社会现实之中,成为整个中华文化认同的基本因素,并逐渐过度为中原、边疆及诸多文化族群文化认同的核心标的物之一。(25)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
在政治文化层面,农耕定居的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决定了汉族民众规律化、秩序化的生活方式,倡导天人合一的礼制文化。农耕文明“顺应天时”的智慧追求体现在桑蚕养殖与丝织生产的活动中,要求生产环节与季节节点形成约定俗成的对应性,如石声汉在《四民月令校注》(26)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中讲,不同季节从事不同的养蚕织丝工作,正月“命女工趣织布”,清明“命蚕妾治蚕室”……六月“命女工织缣练”…… 八月“趣织缣帛,染彩色”,十月“卖缣帛敝絮”,丝帛生产“与四时合其序”(27)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页。,与《礼记·礼运》所言:“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的记载完全吻合,农耕文化天人合一的有序生活是“桑蚕”“丝帛”礼制产生的客观基础。
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礼制”又代表了国家之纲纪,即“礼,国之干也”,礼制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政职责紧密结合,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路径;而另一方面,在“万物有灵”的思维支配下,蚕的神秘属性也必然与德行等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它沟通天地、造福众生,它吐出的丝帛之物是沟通天人的神圣媒介,所以,先民将丝帛与玉器一同比喻德行,如《礼记·礼器》所言:“束帛加璧,尊德也”,而德行是我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根基所在,丝帛制品则成为统治阶层身份与地位的表征与符号,与道德、社会规则结合在一起“帛礼”,更是引导与约束民众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
在宗法等级方面,阶级产生后,族群内不可逾越的等级秩序需要物化的表现形态,而“桑蚕”“丝帛”这类围绕原始信仰被逐渐规范为礼制的物品,则成为等级符号象征体系中的重要原型编码,如《晋书·礼志》:“蚕礼,皇后至四郊,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彩九条”,以区别身份不同。
在礼乐场所中,服饰最能表达“分尊卑、别贵贱”的等级差异,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与权力,是中华礼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通过服饰体现阶层身份的高贵与威严,从而与君子德行的人格相匹配,丝帛服饰成为彰显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赏赐册命时,不同的阶层、身份,所获丝帛物品也不尽相同,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尤其是不同的丝帛服饰与旌旗,用以对应不同的官职,且丝帛的色彩、数量、纹饰、搭配、形制等都是用以区别不同级别与身份的标准,是权力分配与等级区分的路径。此外,桑蚕丝帛常常与礼乐等结合在一起。如《淮南子·览冥训》言:“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28)刘安,等编:《淮南子·卷6·览冥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高诱注:“新丝出,故丝脆。商于五音最细而急,故绝也。咡或作珥……商,西方金音也。蚕,午火也”,将蚕与音律结合在一起,而音律也是表达礼制等级的方式之一。
三、献帛之礼:丝帛礼制的具体实践
基于上述系统的丝帛礼制,贵重的丝帛制品必然成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馈赠的必需品,从原始社会的“全面馈赠制”到封建社会初期的“礼仪”,整个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规范性与系统性,而神圣物——丝帛则无疑成为重要的贽见信物,如据《尚书》记载,九州中的兖州、青州、徐州、荆州、豫州、扬州皆以丝帛作为朝聘之礼。
(一)作为“礼物”的丝帛
马赛尔·莫斯关于礼物的论述中,指出礼物会使馈赠双方形成互惠与认同,而中国古代“物”的流动中,“物”与原有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纽带。(29)[法]马塞尔·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卢汇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孔子云:“礼之先币帛也”,“献帛之礼”最常见于各类仪式之上,丝帛常常在各类融通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媒介身份,《新唐书》中就有记载,唐代举行祭天之礼时,以燔燎的方式奉献丝帛,而祭祀地祇时,则用瘗埋的方式奉献丝帛,可见丝帛在中华文明意识形态体系中的神秘与可贵。在外交礼仪中,人与人往来以“币帛”为先,由于桑蚕与丝织品的神圣性,而外交馈赠之仪式常常在神圣之所进行,使得丝织物成为联系不同社会关系的载体,如韩江苏在释读甲骨文“紤”时,指出“紤”其实是诸侯送给商王的一种丝织品。(30)韩江苏:《释甲骨文中的“紤”字》,见郭旭东主编:《殷商文明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8~143页。钱玄先生在《三礼通论》中也提到,朝聘礼中除了繁文缛节的礼仪,作为经济实物的礼币中,就有丝织品。(31)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7页。郭店楚简载:“币帛,所以为信与征也”(32)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6页。,在礼节往来中,币帛是不可或缺是物品,某种程度而言,它是诚信交往的表征符号。
王铭铭先生指出,中国的“礼”是具有等级性的,除了人与神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外,在人与人之间,也常常以性别、阶级、辈分等标准进行地位的区分,“其政治运用通常跟授与受、事与致、贡与赐、献与颁等观念对子结合……形成某种上下关系,意味着自身妥协的关系形态”,它既有“自上而下的‘礼贤下士’,又有自下而上的‘敬’”(33)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页。。无论是国家层面之间的政治往来,还是个人身份之间的交流,“束帛”“束锦”皆是礼物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除了玉,丝帛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更是诸侯见禹的献祭之礼与信物。
(二)基于生殖崇拜的“婚礼之帛”
因桑蚕崇拜中丰富的生殖意义,在婚礼仪式上的纳吉、纳征环节,就少不了以丝帛作为礼物相赠。例如,周代婚礼纳征时“玄縷束帛”,答谢送亲的人“酬以束锦”,如《周礼媒氏》讲:“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士婚礼》言:“舅飨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姑飨妇人送者,酬以束锦。若异邦,则赠丈夫送者以束锦”(34)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可见,纳征物品中,丝帛是必备之物,且根据等级、阶层不同,丝帛级别也不尽相同。
官方的制度礼仪与民间的乡村习俗,不断相互矛盾、相互吸收,在“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流动中,(35)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0页。而其中的原型意义始终未发生质的变化,在后期的民俗延承中依旧大量存在。
本研究田野所见“搭被面”现象,最常出现在新婚之时。例如,在西北地区,女孩出嫁时,其父母要为女儿准备丝绸面料的被面,质地讲究,数量也以双数为主,一般为六床、八床、十二床,寓意夫妻二人百年好合,图案与纹饰上,也经常选用中国传统花纹,如牡丹花开、龙凤呈祥、凤凰高飞、鱼儿戏水、鸳鸯同心等,以及饱含多子多福期待的“百子图”等,均透视出民众浓郁的生殖向往。此外,被子与“辈子”谐音,其字音本身就携带了人们对婚姻长久的心理期待,缝制被子的人也有要求,必须是儿女双全、配偶、公婆、父母均健在的人,才有资格缝制新人的被子,且必须在吉时才能缝制。在山西平遥一带,还有“引被子”(36)张晓洁:《浅论山西平遥婚礼的“被子”习俗》,载《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的习俗,即在婚礼当日,由儿女双全、父母健在的人头顶红绸,将五枚铜钱币等缝制在被子上,期盼夫妻二人永结连理,此后,新郎按照特定的仪式在被子上“踩八卦”,讨得吉利,新郎的母亲则抱着踩过的被子吃油糕,即“坐被子”,也称“坐富贵”,婚礼上的被子文化虽复杂,却无不蕴含着百姓有关婚姻生育的美好期待。
婚配后繁衍子孙是最基本的行孝行为,婚礼上的被面(被子)与生育文化有关,也有趋吉避凶的心理有关,反映出中华文化中最原初的生殖信仰。当然,伴随着时光的推移与文化的变迁,中国民间的“被俗”文化,在最初生殖崇拜的原型驱动下,衍生出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也有驱邪规诫的教育意义,更具有调适男女双方角色转换后的心理变化,这种民间的“小传统”衍生,来自于丝帛礼制所蕴含的“大传统”文化基因,这些最原始的文化编码在历史的长河中潜移默化,无形中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保留着原初的本体意义。
(三)基于重生信仰的“葬礼之帛”
同理,桑蚕的“再生”信仰,也折射在葬礼文化中,丝帛依旧是事鬼神上帝的重要物品,除了随葬,荒帷(覆盖在棺椁上的纺织物)和铭旌(灵柩前的旗幡)也是用丝织品“愉神”的物品之一。丧礼中的致禭礼仪,就是由逝者的亲友向死者衣、物等随葬品,如《仪礼·士丧礼》中讲,此类葬礼上的丝帛赠送,有“君人禭”“亲者禭”“庶兄弟禭”“朋友禭”(37)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礼仪·既夕礼》,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4~665页。等。
田野调查所见,西北地区,寿终正寝的“喜丧”仪式上也见“搭被面”的现象,逝者的亲人及后代将鲜红的被面铺盖在棺材上,或者围系在孝子贤孙的腰间,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在兰州地区,人们将“被面”简化为一根根红色的布条,并将这种布条平铺在逝者的身下,主要集中在腰部,当乡邻们来吊唁时,会从逝者的身下抽出一根红色的布条用作腰带,或者将其缠绕在自己的皮带上,以期分享逝者的“长寿秘诀”并辟邪驱病。
更为常见的现象是,逝者身上所穿“寿衣”为质地精良的丝帛制品,这种寿衣,需要在有闰月的年份,由女儿在老人离世前提前准备好。其中,女儿是生殖力的代表,有闰月的年份要比平常的年份多出一个月,有岁月绵长、生命长久的美好祈盼。在老人寿诞之日,要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寿衣穿在身上,以期获得健康与长寿。
如上所言,在我国农耕文明中,原始的桑蚕信仰与完备的丝帛礼制体系是最为核心的初始编码之一,它既源自于生产生活的现实所需,也是群体制度与规则的内在逻辑,更是人际交往中关系调适的物化途径,在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置时,正因为丝帛背后蕴藏的文化寓意与精神信仰,才使其成为最佳礼物符号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地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桑蚕崇拜”与“丝帛礼制”是中华文明中“自在”的原型编码,在漫长且客观的文化变迁历程中,关于桑蚕与丝帛文化的认同,在主流话语领域内不断强化与巩固,铸塑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与认同模式,从而成为俗文化的母胎,构成华夏文明特有的文化景观,相关思想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纵深开掘,遍布方方面面。
四、基因同质:文化的认同与“共同体”的凝合
藏族文化极其重视礼仪,而哈达则是最为常见的礼仪用品之一。无论是宗教活动,还是节日庆祝,以及日常交往都能见到敬献哈达的环节,藏胞见面时互相呈递哈达表示尊敬、友好、祝福及信守承诺,在婚礼、葬礼、节日庆典、拜会尊长、联络感情、书信往返、欢送迎接等时,均有献哈达的习俗,例如请婚时,先由介绍人献上一方哈达,如女方接受请婚,就会收下哈达,如果拒绝请婚,就会退回哈达;藏胞书信往来时,也会随附一哈达,表示写信者的意愿郑重和感情真挚;新房落成、新船下水、新器皿使用时,都有奉献哈达的习惯,意为祝贺。
貌似普通平常的丝帛制品背后,蕴含着该民族深厚的礼仪文化,可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中,藏族同胞对农耕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同,“献帛之礼”是藏汉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培育、共同塑造的精神文化。在此,本文不讨论哈达的起源,只关注其与中原“献帛之礼”的内在关联,从而审视“帛礼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问题。
丝绸未传入藏地之前,藏族先民就有将兽皮、羊毛作为礼物的习俗,也有羊毛缠头、缠脖的仪规。自丝绸传入藏区,在汉藏文化交融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代重“汉缯”之俗成为吐蕃的社会风气(38)石硕,罗宏:《高原丝路:吐蕃“重汉缯”之俗与丝绸的使用》,载《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39)杜佑:《通典·西戎二》吐蕃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71页。,与松赞干布对丝绸的认可密不可分,《旧唐书·吐蕃传》载:“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渐慕华风”(40)《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221页。。吐蕃丝绸的获取除了战争、互市外,还依靠朝廷赐品的渠道,唐德宗在《赐吐蕃将书》中讲:“假使踰于万匹……安人保境”,这种赐大量丝绸的举措,与“和亲”一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吐蕃对唐的侵扰与威胁,唐玄宗也曾言:“缯绣以益其饶,衣冠以增其宠,鸿恩大造”,丝绸更是维系唐蕃交好的纽带,在民族团结与文化互惠之间起到了一定的凝合作用。与此同时,这些传入吐蕃的丝绸并非普通民众可以享用,倾向于礼仪性的装饰,且仅局限于上层王室与贵族大臣,与其所处的身份、地位、阶层对等。
那么,传入藏地的丝绸有何用途?石硕先生认为,最初是作头巾使用,或装饰和点缀衣饰。佛教传入后,丝绸的使用就发生了转向,用以装饰佛像、佛堂及寺院,并向僧人表达敬意,自此作为宗教的礼仪用品,升华为表达尊贵和敬礼的象征物。此外丝绸在吐蕃社会还被用以流通交换,充当一般等价物,这一点在敦煌藏文写卷、吐谷浑文书、藏文简牍中均有记载。与汉文化不同的是,吐蕃地处高原苦寒之地,顺滑轻薄的丝绸并不如汉地使用广泛,缺乏实用性,就某种程度而言,藏地的丝绸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内容,这就使得丝绸更趋向符号意义与精神含义,尤其是在佛教的推动下,精神属性远远大于物质属性,更具礼仪文化的核心价值,成为携带神圣信仰与情感的象征符号。
在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中,吐蕃接纳了汉地的帛礼文化,在松赞干布“重汉缯”的认同与推进中,将丝绸所携带的精神意义与藏地原有的习俗进行重构与融合,进一步延伸与发展了丝绸作为礼佛物品的象征寓意,形成了“献哈达”的民俗文化。
由此可见,当下民俗生活所见的“搭被面”与“献哈达”现象,就其内在原型意义而言,具有祈福的礼仪功能,无论是婚礼中趋吉避凶的心理期待,还是表达敬意的文化符号,其内核均源自于丝帛文化铸就的意识形态与精神价值,与丝帛礼制的认同与延承密不可分,这种悠久的文化向心力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里潜含的价值观要素与深层理念,它将大江南北和黄河两岸的各地先民联系在一起,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基石,“帛礼”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凝合价值。
五、“自在”的共同体:帛礼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自在”的,这种自在,源自于中华文明独特的绵延性,(41)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84~400页。而礼仪在此历史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礼仪的特点是礼与俗之间形成了自在的互动与交融,(42)彭牧:《拜:礼俗与中国民间信仰实践》,载《民俗研究》2021年第5期。并以整套的实践系统渗透在社会生活中,使得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参与到礼俗实践中,从而形成、建构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明自生的桑蚕信仰与丝帛礼制,就是以具体的民俗形态和集体无意识的隐性传承方式,活跃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那么,除了“搭被面”与“献哈达”的民俗现象,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活态的“帛礼”习俗呢?“自在”的“帛礼”认同如何广泛存在并实践于全国范围内呢?
桑蚕最本初的生殖象征意义决定,帛礼文化最常见于婚礼之中。例如,在新疆地区,伊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的塔塔尔族,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新娘的头上要披一条白色的长纱巾,象征纯洁的爱情;伊宁、乌鲁木齐等地的乌兹别克婚俗中,女方允婚后要将一块洁白的毛巾交给男方,男方将一块红色毛巾交给女方,婚事即定,白毛巾象征晶莹纯洁,红毛巾象征生活红火,百年恩爱;柯尔克孜族迎亲时,当新娘来到新郎家的毡房前,男方家用大花毛毡从房里一直铺到房外,铺花毡也是一种“献帛之礼”的变形,表示夫家对新娘的欢迎、尊敬和爱护;巴里坤等地的哈萨克族,婚礼时,当新娘的面纱被揭开后,新郎的母亲则拿出带颜色的布块,撕成宽窄不等的布条,分送给前来贺喜的宾客,表示感谢,并象征大家共享喜庆之乐。
其他地区的婚礼上,亦有相似的“帛礼”风俗。甘肃肃南的裕固族婚俗,丝帛象征至诚至敬,说亲时,男方家长请两个媒人带一瓶系有红头绳的酒和若干哈达(按照女方长辈的人数决定),还要给女方的父母送上连在一起的“二连”哈达;结婚时,新娘被迎入帐房(举行婚礼仪式的堂屋)后,婚礼总管请客人们也进入帐房,进门时分男左女右两队,男客队,长辈为队首,新郎为队尾,同牵一条很长的蓝布带子;女客队也如此,只是手牵白色布带,进入大帐房后,新郎新娘向宾客行礼,敬酒致意,在这里,蓝、白二色的布带,也是“敬帛之礼”的表现。(43)刘锡诚,王文宝:《中国象征辞典》,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广西金秀的瑶族,婚礼之日,新婚夫妇行“交行礼”,新娘将棉条交个新娘,新娘接过棉条再交回新郎,象征夫妇情意绵绵,和谐到老。云南陇川等地的阿昌族,男女青年结婚时,由双方长辈依次给新郎新娘将一条一米长短的红绸或红布披挂在身上,象征幸福、美满,披红时要致祝词,如“一道彩虹三尺长,而今披在新郎裳,敬老爱妻礼为上,婚姻美满百年长。”蒙古族的习俗中,定亲时,小伙子带着适当的礼品与媒人到女方家,在定亲酒席上,女方的亲友会将女孩亲手做的丝绸烟袋送给男方,象征女方对男方的爱慕之心。在陕西合阳、澄城一带,在男女订婚时,会给女方送一匹长四丈八或者四丈九的花布,中间不得剪断,表示婚姻长长久久,女方要将它保存到结婚时,如果女方退婚,要将完整无损的引亲布退还,如有缺损,则会受到男方的谴责。
此外,桑蚕原始意义中关于生命力的象征,在民间也能找到相似的风俗。如满族神树火祭的仪式中,东海女神德立克降临时,女萨满手持彩布(绸)翩然起舞,并用彩带抚擦人的头、胸、背等部位,彩布(绸)象征源自太阳的宇宙光,会给人们带来吉祥和生命力。在祭祀女神佛托妈妈的礼仪中,萨满要给孩子胸前挂上从子孙绳上取下来的彩布条,这是喜利妈妈的赐物,能保佑孩子健康成长。在野祭时,崇祀天花女神他拉哈妈妈时,在神鼓上放彩布块。海南的黎族,婴儿出生时,由父母请来的“道公”“娘母”(男、女巫师)在举行祈福祛灾仪式上,将青、蓝、红三色线做成的平安线系在婴儿的手脚上,也有“娘母”在为病人驱病时,也将此绳系在病人的手腕、脖颈上,以驱病祈安。而汉族的“百家衣”,婴儿出生后,祖母要到左邻右舍讨要布头做成衣裤,穿在孩子身上祈盼祛灾纳福,也是“帛礼文化”的变迁,但是其内核并未发生改变。
诸多民俗现象的“再情境化”,可见“帛礼”文化依旧鲜活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丝帛”的文化认同既是物质文化的接纳与认可,更是物质文化背后精神观念的接纳与认同。在历时性的长时段视野下审视“丝帛礼制”的延承,缀连其从未断裂的发展脉络,为本研究的结论提供了分析和推理的参照性文化背景。
六、结语
综上所述,桑蚕崇拜是华夏文明本土信仰支配下生成的原始价值观,以此衍生的丝帛礼制与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丰富多元的民俗文化证实,丝帛作为礼器的认同叙事在华夏文明中从未断裂,透视不同民族之间相似的同质性民俗现象,如“搭被面”与“献哈达”的仪式行为,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动态演进,尤其是在“献哈达”这一微观、具体的形态中,体现出藏族同胞对农耕文明丝绸(桑蚕)价值观的接纳与认同,丝帛制品及其制度文化在民族团结、文化互惠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凝合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作为初期“事神致福”的显圣物,“帛”及“丝帛信仰”是调适人神之间神圣关系的媒介;在“小传统”视域内,对于桑蚕信仰及其衍生的“帛礼”文化及精神价值的认同,是调适不同国家、民族、族群及个人之间多重关系的纽带,是贽见双方互惠的信物,彰显出中华文明和平友好的交往原则与“以和为贵”的精神要素。丝绸之路的开辟与通畅,就是基于丝绸这一华夏认同的文化基因,将这一精神理念弘扬至全世界的历史实践,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声音。“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和为贵”,建构多方开放、合作、共享、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从未断裂且活态延续的“帛礼”精神的当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