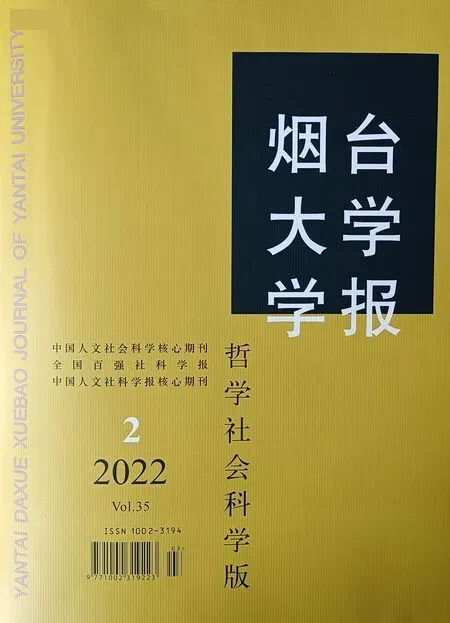早期莎评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继承与超越
辛雅敏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一
众所周知,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古代戏剧尤其是希腊戏剧开始被西欧的人文主义者所认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也被奉为圭臬。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出现了在创作中摹仿希腊戏剧,并将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关于戏剧的诗学理论教条化的风气。古典主义诗学原则最早在意大利逐渐形成,最终却在法国成为教条化的规则,这些规则在17世纪之后又通过法国影响了整个欧洲。要讨论17-18世纪的早期莎评,首先要了解深刻影响当时英国批评家们的古典主义诗学原则是从何而来的。古典主义诗学的一系列原则是17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经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意大利文人,直接或间接从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那里总结出的一系列关于诗歌(尤其是戏剧诗)创作的僵化教条性原则,其源头还要从意大利讲起。
15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出现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拉丁文译本,而1536年帕齐(Alessandro Pazzi)翻译的拉丁文版《诗学》译本影响最大,此后许多人开始对《诗学》进行评论、阐释以及重新翻译,如吉安·特里西诺(Gian Giorgio Trissino,1478-1550)、吉拉尔迪·钦西奥(Giraldi Cinthio,1504-1573)、弗兰切斯科·罗伯特里(Francesco Robortelli,1516-1567)、斯卡里格(Julius Caesar Scaliger,1484-1558)、明屠尔诺(Antonio Sebastiano Minturno,1500-1574)、卡斯特尔维特罗(Lodovico Castelvetro,1505-1571)等等,正是这些人确立了亚里士多德在古典主义诗学中的权威地位,并总结出一套适用于戏剧和史诗创作的普遍法则,而著名的三一律——“情节、时间、地点整一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总结出来的。
在《诗学》第八章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到了情节要整一:“在诗里,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事件的结合要紧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或脱节。”(1)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9页。这便是古典主义诗学情节整一律的基础。关于时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五章提了一句:“在长度方面,悲剧尽量把它的跨度限制在‘太阳的一周’或稍长于此的时间内。”(2)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58页。根据这个说法,1543年钦西奥在《论喜剧和悲剧》(Discorsodellecomedieedelletragedie)中首次提出了悲剧和喜剧的行动都应该在一天之内完成的观点,将亚里士多德的事实性描述变成了一条戏剧规则。另一位意大利古典学者和人文主义者罗伯特里在1548年首次提出,由于晚上人要睡觉,因此戏剧内的一天应该是十二小时。此后,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太阳的一周”到底指什么开始有争议,有人认为是二十四小时,也有人认为是十二小时。但实际上,在《诗学》第七章,亚里士多德又一次提到悲剧的长度问题,他认为情节的长度“以能不被费事地记住为宜”,“作品的长度要以能容纳可表现人物从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或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的一系列按可然或必然的原则依次组织起来的事件为宜”。(3)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75页。也就是说,悲剧的长度还是以情节的设置为基础的,只要情节整一律得以遵守,那么长度满足情节的要求即可。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根本没有提到过地点整一律,但按照意大利学者的理解,如果戏剧内行动的时间被限定在一天之内,那么这些行动必然会被缩减到一定程度,为了保证戏剧所摹仿的行动的真实性,地点自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在一天时间内人能够移动的距离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时间整一律是地点整一律的逻辑基础。经过斯卡里格和明屠尔诺等人的暗示,卡斯特尔维特罗最终明确地提出了地点整一律,由此也完成了三一律的雏形。
卡斯特尔维特罗以翻译并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著称,尤其以三一律的最早提出者闻名于世。但实际上卡斯特尔维特罗的某些观点并不正统,比如他并不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当作权威来对待,而是认为这本小书只是一个大纲或草稿,并不完整,因此其中的许多观点需要重新阐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卡斯特尔维特罗对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进行了修正,其中最离经叛道的是他对诗歌目的的认识。与后来的古典主义者从贺拉斯那里继承来的寓教于乐的观点不同,卡斯特尔维特罗不强调诗歌的教育意义,却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娱乐。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卡斯特尔维特罗认为戏剧诗是写给普通人看的,因此观众是一群缺乏想象力、耐心有限、无知却只会寻求快乐的人,这也许与当时的教育水平有关,但这种虚构的观众却导致卡斯特尔维特罗以观众的认知能力出发,制定严苛的规则以适应这种无知的观众,从而提出了三一律原则。而且基于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时间和地点整一律比情节整一律更重要。
16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法国出版。此后,法国批评家们不仅接受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总结的古典主义诗学原则,而且开始不断完善这些原则,最终这些诗学原则伴随着高乃依、拉辛等人的戏剧创作开始影响整个西欧。到了17世纪上半叶,一大批古典主义批评家已经活跃于法国戏剧界,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有法兰西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让·夏伯朗(Jean Chapelain,1595-1674)、梅萨迪艾尔(La Mesnardière,1610-1663)、海德林(François Hédelin d'Aubignac,1604-1676)、玛勃兰(Pierre Mambrun,1601-1661)以及剧作家让·梅瑞特(Jean Mairet,1604-1686)等,这其中有些人也是1637年著名的“《熙德》之争”(La Querelle duCid)的参与者。正是这几位法国批评家将古典主义诗学原则不断系统化,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到了17世纪下半叶,法国古典主义诗学进一步发展,又出现了几位代表性人物,其中包括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勒内·拉宾(René Rapin,1621-1687)、勒内·拉博苏(René Le Bossu,1631-1680)和安德烈·达希尔(André Dacier,1651-1722)等人,其中以布瓦洛名望最高。布瓦洛著有《诗的艺术》(L'Artpoétique),此书模仿贺拉斯的《诗艺》,集中阐述了古典主义诗学思想,成为法国古典主义诗学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在此,古典主义诗学虽然得以进一步完善,但也更加僵化和教条化。
于是,法国古典主义诗学在至少两代人的努力下,最终形成的理论体系包括以下几个重要原则,即或然律(logical verisimilitude或rational probability,又译可然律)原则、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原则、一致性(unities)原则(主要指三一律)以及合适(decorum)原则。前三个原则主要应用于情节方面,最后一个合适原则主要是对人物塑造的规定。除了这几个重要原则,法国古典主义诗学也有一些次要原则,比如悲喜剧文体应该分用等。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提出情节是悲剧的第一要素,因此古典主义诗学首先便强调情节的重要性,或然律原则便与情节有关。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比历史更富哲学性,也更严肃,因为诗歌“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4)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第81页。根据这一原则,诗歌反映的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而是可能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诗歌中符合逻辑要比符合真实更重要。因此,或然率便是要求情节需要符合逻辑并符合理性,也就是要可信。
诗性正义原则来自法国古典主义对诗歌目的的认识,其源头同样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达到的效果是“净化”或“卡塔西斯”(Katharsis),关于卡塔西斯是什么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是从道德层面进行解读,认为它所达到的是一种教化作用。贺拉斯更是明确提出,诗歌的目的在于寓教于乐。因此在古典主义者看来,诗歌的最终目的在于教化,娱乐只是其达到诗歌最终目的的手段而已。如果诗歌要有教化作用,那么其情节的结局一定要让正义得以彰显、邪恶得到惩罚,这就是诗性正义原则的理论来源和逻辑基础。
三一律是古典主义诗学最著名的规则,也是最具争议乃至最饱受诟病的规则,代表着法国古典主义对古代戏剧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僵化认知,但正如上文所述,这一原则其实来自意大利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法国古典主义批评家们从卡斯特尔维特罗那里学到了三一律,而在“《熙德》之争”之后,三一律成为戏剧创作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且日趋严苛,许多法国批评家往往将剧内时间限定在十二小时以内,有人甚至要求剧内时间等同于戏剧表演时间,这就极大限制了戏剧创作的自由。
“合适”原则更多是对人物塑造的规定。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为人物性格的刻画制定了四条原则: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性格应该好;第二,性格应该适宜;第三,性格应该相似;第四,性格应该一致。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性格刻画与情节一样,也应符合必然和或然律原则。亚里士多德的性格刻画原则在罗马作家贺拉斯那里得到了进一步阐释,在《诗艺》中,贺拉斯便提到不同年龄的人物性格的合适与得体问题:“如果你希望观众欣赏,……那你必须(在创作的时候)注意不同年龄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以恰如其分的修饰。”紧接着,在描述了从儿童到老年的不同性格表现之后,贺拉斯总结道:“所以,我们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5)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此外,在《修辞学》第二卷第十二到十七章,亚里士多德也论述过人的性格问题,尤其详细讨论了年轻人、老年人、壮年人的不同性格,以及财富和权力对性格的影响等问题。虽然这里不是指悲剧性格,但对后世批评家关于人物性格的理解有一定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与贺拉斯的这些论述是合适原则的理论基础,不过在法国古典主义诗学中,合适原则对人物的规定更繁复,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而且与法国的宫廷与贵族品味有关。在“《熙德》之争”时,法国批评家们还只是要求人物塑造要符合时间、地点、年龄、习俗等因素,后来的规定则越来越复杂和明确。梅萨迪艾尔便已经开始明确列出许多具体的规定,将人物进一步类型化,甚至规定了每一种人物的行为规范,而这些规范则多与当时的宫廷礼仪相关。此后玛勃兰、海德林、拉宾、拉博苏等法国批评家更是将这些规定进一步细致化,同时也趋向僵化,最终形成了古典主义合适原则。
17世纪中叶到下半叶,法国正值“太阳王”路易十四当政,政治、文化均进入全盛时代,其宫廷风尚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欧。此外,英国复辟国王查理二世曾流亡法国多年,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因此法国的古典主义戏剧品味和戏剧文化开始在英国大行其道。
二
托马斯·莱默(Thomas Rymer,1643-1713)应该算是复辟时期英国最博学的批评家之一,但同时也是最固守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一位。早在1673年,莱默便翻译了法国作家勒内·拉宾的《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反思》(ReflectionsonAristotle'sTreatiseofPoesie)一书,显示出他对法国古典主义的了解和认同。莱默在1677年出版了专著《从古典作品和常识看上一时代之悲剧》(TheTragediesoftheLastAgeConsider’dandExaminedbythePracticeoftheAncients,andbytheCommonSenseofAllAges),除了提到不少古典主义诗学的老生常谈外还攻击了弗莱彻的三部剧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情节是悲剧六要素中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深刻影响了文艺复兴之后戏剧理论和创作,莱默在此书中一开始便提到,自己最关注的是“虚构”(fable)或“情节”,因为这是悲剧的灵魂。莱默认为评论戏剧作品的情节不需要太多的学识,仅靠常识(common sense)便可以做出判断,因此莱默自称自己的戏剧评论是建立在常识和普遍理性(ordinary reason)的基础上的。随后莱默反驳了英国与希腊历史地理不同而有不同的标准的观点,他认为自然(人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因为“人是一样的,两个地方的人都会爱、会伤心、会恨、会嫉妒,有同样的情感和情欲,同样的原因促使他们行动。在一个地方能激起怜悯,在另一个地方也会有一样的效果”。(6)Brian Vickers ed.,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1, 1623-1692, London: Routledge, 1974, p.187.这是典型的古典主义诗学理论,即承认普遍人性、否认文学创作的具体历史语境。如果在承认这种普遍人性论的前提下强调古代戏剧的典范作用,那么为不遵守古典主义原则的莎士比亚等英国剧作家辩护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从古希腊到近代英国,如果所谓的自然或人性是不变的,那么模仿自然便可以通过摹仿古人来完成,古代的典范便应该遵循。莱默最后总结道:“我认为我们上一个时代的诗歌和我们的建筑一样粗俗,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当时不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我们还不知道这本书之前,意大利人就已经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评论此书了。”(7)J. E. Spingarn ed.,Critical Essay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ol. 2, Oxford: Clarendon, 1908, p.207.
也许是由于攻击矛头并没有明确指向莎士比亚,与后来的《悲剧简论》相比,莱默的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并不算大。当时著名的书商汤森(Tonson)曾提到,莱默出版了《从古典作品和常识看上一时代之悲剧》之后,曾专门赠送给著名的剧作家约翰·德莱顿一本。大约在1677年,在为汤森版的《鲍芒与弗莱彻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德莱顿系统地评价了莱默的这本书,并在这篇文章中为英国戏剧进行了辩护。德莱顿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恐惧和怜悯并不是悲剧的主要目的,悲剧的目的是道德层面的趋善避恶,恐惧和怜悯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英国戏剧在激起怜悯和恐惧方面做的并不比古代戏剧差。英国戏剧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德莱顿看来原因在于:“我认为莎士比亚和弗莱彻是代表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民族的天才。因为正如莱默所反驳的,自然(人性)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样,理性也一样,但气候、时代以及作家所面对的人民的性格却是不同的,所以让希腊人感到愉悦的东西未必能打动一位英国观众。”(8)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1, 1623-1692, London: Routledge, 1974, p.199.这段话是针对莱默的普遍人性论的反驳,德莱顿肯定了莱默的普遍人性论,但却用性格(dispositions)的差异来为英国戏剧辩解,进而强调古代戏剧与近代戏剧的不同,这就避免了与古典主义诗学的冲突。另外,根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划分的悲剧六要素,德莱顿认为在人物、思想、言辞等方面,英国戏剧都比古代戏剧好,只是在情节上不如古人,但这并不是问题,因为“如果古人的戏剧在情节上更正确,那我们的戏剧就在文笔上更精彩;如果我们在更差的基础上反而能达到同样的情感效果,那就说明在悲剧方面我们更有天赋,因为在悲剧的其他所有方面英国人都超越了他们”。(9)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1, 1623-1692, London: Routledge, 1974, p.200.
德莱顿认为,在悲剧的几大要素中,语言和言辞是英国戏剧的强项,尤其以莎士比亚为代表。而关于悲剧的效果,德莱顿提到,怜悯和恐惧只是悲剧所激起的情感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怜悯和恐惧是悲剧所激起的主要情感,是因为他看到的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而没有看到英国的悲剧,如果他看了,“说不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10)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1, 1623-1692, London: Routledge, 1974, p.201.
最后,德莱顿对莱默的这部著作进行了总体评价:
它非常博学,但它的作者对希腊戏剧的了解比对英国戏剧要多;所有作家都应该学习一下这位批评家的观点,因为他是我见过论述古代作家最好的;他在这里给出的那些悲剧的典范无疑是优秀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悲剧并不是只有一种典范。古代的悲剧在情节和人物上有种种规矩,此书的作者让我们尊崇和学习古人,却对我们本国带有偏见。(11)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1, 1623-1692, London: Routledge, 1974, p.202.
而在1679年的《悲剧批评的基础》一文中,德莱顿再次提到了莱默,不过口气更缓和了一些,承认了莱默所提到的那些缺点,言外之意是认为莎士比亚的文采抵销了他的过失:
莎士比亚和弗莱彻全部的戏剧情节包含了什么样的缺点,莱默先生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已经指出了:我辈追随他们也无法避免同样或更大的错误;这在我们更是不可原谅,因为我们缺少他们那种文采来抵销我们的过失。(12)杨周翰选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这样看来德莱顿与莱默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严重,大家都在古典主义诗学的框架内心平气和地讨论英国戏剧的优缺点,但情况随着莱默的新著出版很快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莱默在《上一时代之悲剧》中对英国戏剧的指责以及德莱顿为英国戏剧的辩解还算温和理智的话,那么莱默另一部著作的出版就彻底激起了德莱顿等英国批评家们的民族情绪。莱默在1693年出版了《悲剧简论》(AShortViewofTragedy)一书,其中将攻击的矛头直指莎士比亚,尤其是《奥赛罗》。在此书第七章,莱默详细评价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他首先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出发,指出悲剧有四大要素,即情节、人物、思想以及言辞,然后进行了一些解释。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莱默认为情节是悲剧的灵魂,但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人物与道德哲学有关,思想与修辞学有关,言辞则与文法有关,只有情节完全是诗人的工作。随后莱默便分别从这四要素出发对《奥赛罗》中的缺点进行了评论。
莱默首先指出《奥赛罗》的情节来自意大利作家吉拉尔迪·钦西奥的小说,如果说原小说在情节上还讲得通的话,那么经过莎士比亚的修改却变得更不符合或然律原则了。为了说明这一点,莱默引用了贺拉斯的《诗艺》,因为贺拉斯在《诗艺》开篇就提到:“‘画家和诗人一向都有大胆创造的权利。’……但是不能因此就允许把野性的和驯服的结合起来,把蟒蛇和飞鸟、羔羊和猛虎,交配在一起。”(13)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第127页。因此,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组合本身就有问题。威尼斯贵族小姐苔丝狄蒙娜不应该也不可能爱上摩尔人奥赛罗,威尼斯元老院更不可能用一个摩尔黑人当将军去攻打土耳其的穆斯林。总之,《奥赛罗》在情节上完全不遵守或然律,莱默总结道:“在自然中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可能发生的谎言更令人厌恶的,也没有哪部戏剧像《奥赛罗》一样充满各种不可能性。”(14)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29.
从人物的角度出发,根据古典主义诗学原则,人物的性格特征要符合人物的身份,莱默认为在这方面《奥赛罗》同样充满不可思议和荒唐的描绘。奥赛罗不仅不像个将军,而且出于嫉妒杀妻根本不是军人应有的品性;伊阿古更是如此,军人应该有勇敢、忠诚、正直、诚实等品性,绝不应该是个恶棍;苔丝狄蒙娜作为威尼斯贵族小姐也不应该如此愚蠢。在讨论完人物的问题后莱默指出,由于在人物性格上完全不可理喻,《奥赛罗》在悲剧的第三要素“思想”上必然是既无理智也无意义的,这也导致此剧的第四个要素“言辞”根本不值得单独拿来讨论。此时莱默说出了也许是整个莎评史上关于莎剧最严苛的批评之一:“马的嘶鸣或者犬的吠吼都各有其意义,其中都有生动的表达,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许多时候都比莎士比亚的悲剧更有人性。”(15)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30.马鸣犬吠都比莎剧更有“人性”,这话也许比后来的伏尔泰、托尔斯泰、萧伯纳等著名的莎士比亚诋毁者们的言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正是这彻底激怒了德莱顿、约翰·丹尼斯、戈尔登等同样信奉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英国诗人和批评家们,导致他们都对莱默的这部著作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击。
在从悲剧四大要素的角度上对《奥赛罗》进行评价之后,莱默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开始花费大量篇幅细致分析此剧文本中的不合理细节,尤其对第二幕和第四幕中的一些场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从古典主义原则出发指出其诸多荒唐和不合理之处。最后,莱默这样总结《奥赛罗》:“此剧中有些滑稽、幽默场景,也时不时有些喜剧的机智,有些摹仿能吸引观众的注意,但从悲剧的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场血腥的闹剧,毫无味道可言。”(16)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54.
三
德莱顿对莱默这些观点的不满很快就表现出来,但是严格按照古典主义诗学原则来说,莱默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他的分析不仅条理清晰,而且引经据典,还辅以大量莎士比亚的文本进行说明。这样严密的论证让德莱顿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境地。在写给另一位剧作家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1658-1734)的信中,也许是明知道莱默的论证很难从细节上进行反驳,德莱顿干脆写道:
我们的喜剧不讲规则,和古代的戏剧完全不同,我们的悲剧也一样。莎士比亚在这方面是个天才。我们知道,不管莱默先生说了什么,这种天才本身就是优点,而且这种优点比所有的其他条件加起来还要大。你能看到这位博学的批评家在污蔑莎士比亚方面获得的成功。他找到的几乎所有错误都确实存在,但谁会放着莎士比亚不读而去读莱默的作品?对我来说,我尊重莱默先生的学识,但我看不惯他的恶意(ill nature)和傲慢。确实,从这方面来说,我有理由惧怕他,但是莎士比亚却不会。(17)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86.
不难看出,德莱顿的这番言语在不满的同时也透露出些许无奈,因为在古典主义原则的框架下,除了强调英国戏剧的独特性,他很难再对莱默进行有效反驳,最后只能说出“我有理由惧怕他,但是莎士比亚却不会”。不过德莱顿在无可奈何之中却提到了一个后世莎评家为莎士比亚辩护的关键词,那就是“天才”。“天才本身就是优点”恰恰是后来的18世纪莎评将莎士比亚视为民族诗人的主要逻辑,而天才理论也是一百多年后浪漫主义对抗古典主义的主要武器。由此可见,早在17世纪末,“天才”已经开始变为莎士比亚与众不同的重要特质。
约翰·丹尼斯的情况和德莱顿差不多,他也对莱默的评论不满,但同样难以从学理上进行反驳。1693年在一篇针对莱默的《公正的批评家》(TheImpartialCritick)的文章中,丹尼斯先提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天才”,随后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弗里曼(Freeman)之口说道:“他(莱默)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大部分情况下是理智和公正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因为莎士比亚有错误,所以他就没有优点”。(18)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62.但有趣的是弗里曼并没有说出到底是什么优点,只是向对话者说下次见面再说。正是这句“下次再说”的承诺让另一位剧作家和批评家查理·戈尔登(Charles Gildon,1665-1724)等了一年,因为他觉得作为戏剧界的前辈,丹尼斯的反驳一定比自己更有力,可是等来等去却没等到丹尼斯进一步的阐述。于是,在1694年献给德莱顿的《对莱默先生〈悲剧简论〉的一些思考和对莎士比亚的辩护》(SomeReflectiononMr.Rymer’sShortViewofTragedyandanAttemptataVindicationofShakespeare)一文中,戈尔登向德莱顿说道:“既然我发现莎士比亚的支持者们集体沉默,认为莱默对莎士比亚的异议无可反驳,那么我决定花两三天的时间写一篇文章来证明莱默是可反驳的。”(19)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64.的确,莱默让喜爱莎士比亚却囿于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大部分英国批评家们陷入了难以为莎士比亚辩护的尴尬境地,此时是戈尔登在德莱顿面前主动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与德莱顿和丹尼斯等同时代人一样,戈尔登也信奉古典主义诗学原则,但与德莱顿和丹尼斯等人用莎士比亚的天才含糊其辞地去搪塞莱默严密细致的文本分析不同,戈尔登终于在古典主义诗学的框架下完成了对莱默学理上的反驳,因此他的辩驳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戈尔登先是将莎士比亚的缺点归因于他的时代,将时代通行的错误与莎士比亚的本人所犯的错误进行区分。戈尔登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是为了取悦和迎合观众,这就是他的悲剧中会混有喜剧成分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人物的反常、语言上的繁复与粗俗都可以用那个时代在审美品位上的缺陷去解释。至于莎士比亚违反三一律的事实,戈尔登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去解释,那就是莎士比亚确实不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却可能了解另一部古典主义诗学的权威著作——贺拉斯用拉丁文写成的《诗艺》。但贺拉斯在《诗艺》中并没有对戏剧的时间、地点、情节等问题进行规定,因此,“由于在这方面他无法从贺拉斯那里得到指示,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他对三一律的违反”。(20)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69.
随后戈尔登提到了那个在贺拉斯那里就已经存在的老问题,即自然(Nature)和技巧(Art)哪个对诗人来说更重要。莱默显然认为是技巧,但戈尔登则认为技艺和规则是对天才的束缚,因此天才可以冒犯规则:
对于伟大的天才来说,完全遵守规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束缚,必然想挣脱它。……人性中的伟大事物更能让我们接近伟大的永恒之完美,也更能让我们尽可能地接近无限。这不是靠普通的规则或方法所决定,而是靠超越常规带来的荣耀(Glories in a Noble irregularity)。这不仅表现在文学中,也体现在一些人的行为中。亚历山大、凯撒、亚西比德(Alcibiades)等人似乎都不是以常人的准则行事,在他们身上都有伟大的德行与深深的恶行并存,莎士比亚的创作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被认为是英雄,那么莎士比亚也必将被当作诗人。英雄便当如阿喀琉斯:让他宣称规则不是为他所制订的。(21)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70.
强调天才可以无视规则,单独看这段话,我们甚至会以为这是一百年后某位德国或英国浪漫主义莎评家的言论。也许是意识到这段话说得有点过了,戈尔登马上又补充道:“我并不是认为伟大的人一定要抛弃规则,因此我必须承认维吉尔、索福克勒斯和您本人(即德莱顿)都是伟大的人,却都非常符合规则。”(22)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70.戈尔登继而指出,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虽不完美,但我们不应该因为有缺点就忽视其价值,因为诗歌的目的便是寓教于乐(Pleasure and Profit),莎士比亚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
在此文后半部分,戈尔登针对莱默在《奥赛罗》中挑出的缺点对莎士比亚进行了具体的辩护。莱默指出《奥赛罗》最大的问题在于情节,他便从情节入手进行反驳。戈尔登认为完美的戏剧情节既要有不寻常的一面,也要遵循常理,这样才能同时做到既吸引人又符合或然律。《奥赛罗》的情节无疑是吸引人的,莱默质疑的主要是或然律,即威尼斯元老院不可能用一个摩尔人当将军来攻打土耳其,苔丝狄蒙娜也不可能爱上摩尔人奥赛罗等等。戈尔登指出,奥赛罗的基督徒身份可以证明他的高贵,而苔丝狄蒙娜对奥赛罗的爱也有维吉尔笔下的狄多对埃涅阿斯的爱情作为先例。因此,戈尔登反驳莱默的主要策略是用古代作家作为反例与莎士比亚形成类比,来证明莱默所遵循的古代典范本身便是有问题的。
进入18世纪以后,莱默莎评的影响还在持续,不断有人站出来为莎士比亚辩护。1710年,戈尔登在为莎士比亚诗集写的序言中又提到了莱默,并以自己的阅读体验为论据,回到了从效果的角度出发为莎士比亚辩护的老路:
必须承认莱默先生过于吹毛求疵了,一个人只要稍能欣赏诗歌便会承认莎士比亚的天才。抛开那些明显的错误,当我在阅读莎士比亚的时候,即便是他最不符合诗学规则的剧本也能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以至于我的判断力受到影响,会忽视那些错误,纵使它们从未这样粗俗和明显。那些艺术原则虽然以坚实可靠的理性为基础,但他有一种魔力能用他所惯用的方式让它们完全消失,以至于让我觉得我从未了解过这些原则。(23)Brian Vickers ed.,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ge, 1974, p.218.
四
由于始终没有放弃古典主义思想,晚年的戈尔登比早年更为保守,对莱默的同情和尊重更多一些。但在1709年,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1674-1718)在自己编辑的莎士比亚文集《序言》中对莱默进行了挖苦,坚定地与德莱顿等人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我必须承认,在整个世界都倾向于尊重莎士比亚的情况下,我不太清楚他(莱默)对一个在许多方面很优秀的人提出如此责难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莱默是为了展示自己在诗艺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便是这种做法背后的虚荣,问题是他对他人指点江山、大谈原则和规范的时候,是否自己就没有缺点,而且他自己写的悲剧是否展示了他的优秀的天赋。如果他对莎士比亚心怀不满,存心想诋毁莎士比亚早已确立的名望的话,他的企图早已失败,他会发现比起他的评论大家至少同样喜欢莎士比亚。但我不相信任何一位绅士或一位心胸宽厚的人会喜欢他的评论。不管他用意如何,挑毛病总是知识工作中最轻松的一种。有良好判断力的人一般也都有温良的气质,一般都会抛弃这种“学究式暴政”(Tyranny of Pedants)的忘恩负义的做法。一个人如果接触到莎士比亚的美好,他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也更可爱的世界。(24)D. Nichol Smith ed.,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on Shakespeare,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3, pp.9-10.
罗在这里并没有对莱默进行有效的反驳,却在质疑莱默自己的诗歌创作才华。其实德莱顿当年也有类似的说法。德莱顿在1693年为自己的诗歌作品所写的题献中说道:“二流作家(ill writers)常常是最刻薄的批评家,因为他们在完全完成这种蜕变之后便会醋意大发,重返文坛。于是,一个作家的退化便是一个批评家的诞生。”(25)W. P. Ker ed.,Essays of John Dryden Vol. 2,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0, pp.2-3.德莱顿写这话的时候大概正是莱默在《悲剧简论》中攻击莎士比亚之时,这里的二流作家很可能指的就是莱默。正如罗所谓的“学究式暴政”,德莱顿作为文学成就斐然的大作家,显然是在抱怨二流作家化身批评家之后对一流作家的“挑毛病”现象。但是作家同时身兼批评家是很常见的现象,文学批评的本质便是辨析作品的好坏,对其作出价值判断,而且一个人的鉴赏能力与创作能力也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活动,因此用一个人在文学创作领域的成就来判定其在文学批评领域成功与否显然不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观点。
不过罗对莱默的反驳并未结束,他在后文中又进一步批评道:
由于我不准备介入任何批评争论,我不打算考察莱默先生评论《奥赛罗》的正当性。他确实明智地指出了一些错误,也有许多人都同意这些确实是错误,但是我希望他同样能看到一些优点,因为我认为一个公正的评论应该做到这一点,奇怪的地方就在于莱默一句优点也没提。如果故事情节不合他的品味,至少思想是高贵的,言辞是雄壮和适宜的。在这些方面莎士比亚的赞誉是难以质疑的。他的情感与意象是伟大而自然的,他的言辞(虽然偶尔有些杂乱)是恰当的,适合于他的主题与场景。这样的优点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而他的书被大家广泛阅读,只要沉浸其中,总会发现我说到的这些让他成名的特点。(26)D. Nichol Smith ed.,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on Shakespeare,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3, pp.20-21.
罗在这里用了另一种方法为莎士比亚辩护,那就是指责莱默只说缺点不谈优点,继而指出莎士比亚的优点大于缺点,这个辩护在逻辑上是有效的,类似于戈尔登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为莎士比亚所做的辩护。由于罗的这篇《序言》在18世纪广为流传,几乎每一版莎士比亚文集都会将其收录其中,他的观点虽然既不深刻也不全面,却影响巨大。更重要的是,在提到上述这段话之前,罗还说了这样的话:“莎士比亚仅仅依靠自然的微光,也从不知道那些前人的规则,因此很难用一种他不知道的规则去评判他。”(27)D. Nichol Smith ed.,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on Shakespeare,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3, p.15.这个为莎士比亚辩护的观点后来被很多人重复,其背后的逻辑可以追溯到德莱顿的那句“让希腊人感到愉悦的东西未必能打动一位英国观众”。18世纪的大诗人蒲柏便说过类似的话为莎士比亚辩护:“用亚里士多德所制订的规则去评判莎士比亚就像用一个国家的法律去判决一个在另一个国家行动的人。”(28)D. Nichol Smith ed.,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on Shakespeare,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3, p.50.从德莱顿到罗再到蒲柏,这些古典主义诗学的拥护者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莎士比亚和希腊悲剧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但已经暗示了这种区别,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相对论和历史批评的开端,而后来英国的莫根和德国的赫尔德等人所开启的浪漫主义莎评更是将这种从历史相对论的角度为莎士比亚辩护的方法视为反抗古典主义诗学的主要武器。
通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英国批评家们在被莱默激怒的时候,往往会更加强调莎士比亚的“天才”。也就是说,莱默的批评愈发激起了关于莎士比亚的天才论。由此可见,天才能够无视艺术技巧,进而对抗规则,这种典型的浪漫主义观点在17世纪下半叶已经若隐若现。不过,17-18世纪的英国批评家们并不像浪漫主义者一样想用天才理论来对抗古典主义,恰恰相反,当时的批评家发现这种对天才的强调其实也有其古代源头。17-18世纪的英国批评家之所以能认识到天才的重要,很可能得益于朗吉努斯的崇高理论的传播。早在1652年,古希腊批评家朗吉努斯(Longinus)的《论崇高》一文的英文版便已问世,当时影响并不算大,不过德莱顿在1679年的《悲剧批评的基础》一文中便已经提到了朗吉努斯。到了1680年,英国出现了从布瓦洛的法文版翻译而来的英文版《论崇高》,在布瓦洛的影响力作用下,此文渐渐进入英国批评家的视野并成为古典主义诗学的又一经典文献。在1712年的时候开始有批评家试图用莎士比亚来反证朗吉努斯,随后更多的批评家们开始用“崇高”概念来论证莎士比亚剧作,以使其更符合古典主义的品味,或者说使其能与古典主义相协调。这其中尤其是朗吉努斯关于天才的论述使英国批评家们如获至宝。“我知道,最伟大的才华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十全十美的精细容易陷于琐屑;伟大的文章,正如巨大的财富,不免偶有疏忽。低能或平庸的才情,因为从来不敢冒险,永不好高骛远,多半也不犯过失,最为稳健,而伟大的才情却因其伟大所以危险——这也是理所当然的。”(29)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这段话不正是英国批评家们长久以来所苦苦寻找的天才理论么?简直像是完全为莎士比亚量身定做一样,最重要的是,这种天才理论出自古代权威,可以成为古典主义诗学的一部分。
总之,莱默成功地让复辟时代以及18世纪初的英国批评家们暴露了对待莎士比亚与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两难困境,当然也更加激发了以德莱顿为首的批评家们的民族情感。在古典主义诗学原则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莱默对莎士比亚的批评之所以被一再反驳,正是因为他挑战了英国批评家们的民族情绪。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莎士比亚从德莱顿时代之后便已经走在了通往民族诗人的道路上。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会发现,英国批评家们对莎士比亚的辩护遵循这样几种基本逻辑:第一,将莎士比亚的优点与缺点分开对待,将其缺点和错误归因于他所处的时代,因此这些缺点是可以原谅的;第二,承认莎士比亚的缺点,但认为他的优点远大于其缺点;第三,莎士比亚是天才,天才不应该被规则所束缚,甚至可以无视规则;第四,莎士比亚的创作有其时代特征,不能用古代戏剧的标准来衡量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可由第一点推导而来);第五,针对莱默本人的质疑,以莱默文学创作的成就质疑他是否有资格对大作家莎士比亚进行评论。这其中第五点近乎人身攻击,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前四点是对莱默有效的反驳。从前四点来看,第一点和第二点并没有走出古典主义诗学的语境,但第一点在逻辑上已经有了历史相对论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和第四点,戈尔登明确提到了第三点,德莱顿和蒲柏等人则暗示出了第四点。用天才对抗古典主义的规则和将莎士比亚置于具体历史语境来强调古代主义原则的无效恰恰是后来浪漫主义莎评惯用的逻辑,但我们看到,这种逻辑实际上已经隐含在英国的古典主义批评家那里。也就是说,得益于朗吉努斯《论崇高》的传播,后来浪漫主义者们所钟爱的天才理论在德莱顿等古典主义者为莎士比亚辩护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应该说,这是古典主义诗学内部的一次自我更新。
莱默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反而激发了英国批评家们的民族情绪,正是在对莱默的反驳中,英国批评家们逐渐从古典主义诗学内部完成了对它的突破,同时也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将莎士比亚当作对抗法国文化入侵的工具,这个过程无疑有助于莎士比亚在英国本土经典地位的确立,而这也许才是莱默所始料未及的。18世纪30年代之后,英国批评家们用古典主义诗学原则指责莎士比亚的声音越来越少,而对类似莱默观点的反驳却日渐增多,为莎士比亚辩护的声音开始在批评界流行。当然,辩护的主要原则还是老生常谈,即莎士比亚虽然有缺陷,学识也有限,但他靠天赋写作,是自然诗人的代表,他模仿的是自然,替自然发声等等。虽然为莎士比亚辩护的逻辑没有变,但这种辩护的声音却越来越大,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最终将莎士比亚推到了民族诗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