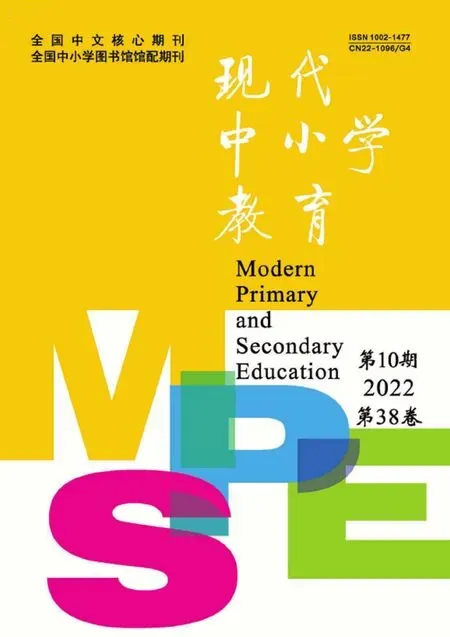主体间性视域下教育惩戒的困境与突围
胡 倩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教育惩戒是我国教育实践中备受争议却饱含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一种必要性的教育举措,教育惩戒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面临着艰难的现实处境。从根本上讲,对主体间性师生关系的把握不当,是导致教育惩戒涵义失真、以至饱受诟病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想挽救教育惩戒于泥淖之中,就必须从主体间性师生关系出发,立足于教育惩戒的现实困境,开拓教育惩戒的突围进路。
一、主体间性视域下教育惩戒的现实遭遇
教育惩戒是教师对学生实施的引导性教育举措,是师生主体间的教育活动。然而,由于对师生主体间性关系的不明确,给教育惩戒的定位与实施带来了错误理解,因此产生了偏差性的目标,自此教育惩戒深陷泥潭。
1.儿童客体化:无教育的惩戒
无教育的惩戒将作为手段的惩戒当作目的,丧失了教育惩戒的本真意蕴,是当前教育惩戒的普遍存在状态。无教育的惩戒侵犯了学生的独立性,其实质是对儿童主体地位的忽视。这种将儿童客体化,仅以成人的姿态与标准来管束儿童,以此达到惩戒效果的行为,丧失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这种无教育的惩戒已经演变为一种控制和规训,是在“主客体完全疏离的情况下,将我(主体)的意志强加于他人。”[1]无教育的惩戒混淆了教育的目的与手段,反映了主体—客体的教育结构,是“我—它”的关系体现,是教师主体异化的结果。教师对儿童主体地位的僭越,将儿童看作客体化的教育对象,无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这种居高临下的行为忽视了教育指向儿童发展的根本目标,丧失了最本质的教育意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非教育现象。由此,教育惩戒导向了惩罚的轨道,失去了教育意涵,形成了教育之“恶”。
个体主体性已经走向“黄昏”,主体间性才是师生关系的最终归宿。师生同为教育活动的主体,理应同时具备主体性。因此,必须从主体间性理论来构造师生观,承认师生双方共在的主体性。教育惩戒作为一种纠偏学生不良行为的教育举措,也应将师生平等作为教育惩戒的实施基础。在充分尊重儿童主体性的基础之上,将儿童发展作为教育惩戒的最终目的,才是教育惩戒的合理性所在。
2.师生对抗:教育惩戒的根本阻碍
中国传统“师道尊严”思想以及西方教师中心理论的流传,使教师地位被置于学生高处。这种片面强调教师主导性的观点,将学生物化为客体,造成了教育中“主体”对“客体”的支配与压制。然而,近现代以来,关怀理论、学生中心理论等快速发展,给教师主体化带来了巨大冲击,迎来了学生主体性的新高潮。至此,师生关系步入教师主体化和学生主体化两个极端。这两种单主体性的师生模式,将师生置于“二元对立”的局面,成为相互对立的主体。教育惩戒也由此呈现两个发展阶段,即“惩罚”的盛行与回避。其一,“惩罚”的盛行。教师将学生物化,利用惩罚的手段让其感知错误的后果,其中驯服的意味更高,其惩罚性远大于教育性。其二,“惩罚”的回避。由于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关注异化,教师不被允许对学生采取惩罚措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用“惩罚”代替“惩戒”的原因在于,惩戒本身蕴含着惩罚和戒除的意味,是用惩罚的手段戒除不当的行为,是在教师引领下学生改正错误行为的教育措施。而在此师生对抗的前提之下,教育惩戒就失去了教育性,演变为教师单纯发泄不满情绪的惩罚行为,因此只能用“惩罚”一词概括。
师生对抗将教师和学生置于对立面,使得教育惩戒沦为教师驯服学生的工具,逐渐褪去其本来面貌。这种对抗导致师生关系呈现暂隔、孤立、冲突的形态。然而,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是人与人心灵之间的交流。师生同为教育场域中共生的主体,其关系理应是和谐、融洽、交往的。教育惩戒作为一种引导性、纠正性的教育措施,也应当立足于和谐、交往的师生关系,扎根学生发展的根本目标。
3.教师霸权:教育惩戒的目标偏离
教育惩戒是一种引导性的教育措施,其目的在于“借助适度惩罚达到戒除、矫正学生不合范的行为,助其完成社会化的进程。”[2]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之中,由于对师生地位的理解偏差,教师地位往往被置于学生之上,教育惩戒则被误用为教师以惩罚来发泄对学生不良行为的怨愤。这种以单向度的惩罚遮蔽教育惩戒的教育目标,导致了教育初心的偏离,由此出现了教师“霸权”现象。教师霸权指的是传统师生关系中,教师作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主体,不顾学生主观感受和身心发展,而对学生行为采取单方面的支配或命令。教师霸权体现在多个方面,典型表现为教师话语霸权,即教师单向度的灌输使得学生丧失言语自主权,抹杀了师生言语交往的可能性。此外还有包括教师评价霸权、管理霸权等等。教师霸权是错误实施教育惩戒时所产生的偏差后果,同时也是加深教育惩戒异化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教育场域逐渐演变为教师的领土,掩盖了培养人的根本目标。
教育惩戒应以助长学生健全发展为目标,学生理应是与教师相互承认、平等存在的主体。然而,在教育惩戒走向异化的道路上,平等和尊重销声匿迹,随之而来的是霸凌和欺压的横行。自此,教师地位僭越于学生之上,教育惩戒的目标随之偏离,走向教师霸权的归途。主体间性关系是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是对主体霸权的消解。教育惩戒必须以主体间性为实施基础,明晰教师与学生共在的主体性,以共生为归途,构建教学相长的理想形态。
二、主体间性视域下教育惩戒的本质凸显
“主体间性之于教育是对本真的一种追溯,是教育本性的要求,具有本体意义。”[3]教育惩戒的开展必须明确师生的主体间性关系,摒弃师生关系的二元对立,为解决目前教育惩戒所面临的困境提供理论性支撑。
1.平等:教育惩戒的前提性话语
主体间性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体现,表达的是人与人同等存在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师生关系突出师生主体的平等性,将作为认识和实践的人与认识和实践对象的人同等看待。主体间性理论摆脱了学生客体化的观念,认为“学生既是占有教育内容的主体……又是师生交往的主体”[4]。此外,主体间性理论还认为学生必须发展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体,强调学生的主动性,摒弃了双主体教育观念中受教育者的被动性。主体间性理论超越了主体性个体化和自我异化,将师生平等提到核心地位,认为教师和学生都不是唯一的主体中心,而是在人格和权利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主体。需要明确的是,教育惩戒之所以饱受诟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不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教育惩戒中的师生,使得促进学生发展的目标退隐到惩罚的背面,从而导致教育惩戒的异化。此外,对学生人格的欺压引发了师生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教育惩戒的异化。由此,教育惩戒一步步走向惩罚甚至体罚,逐渐偏离教育轨道。
教育惩戒以惩罚为基本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难免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倘若将学生看作物化的客体,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学生的反抗,以此无法真正为学生发展的教育目的而服务。学生主体发展是教育目标所指,教育惩戒的实施必须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看作与教师平等的个体。并以主体间性师生关系为基础,以此构建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从而为教育惩戒的开展构建和谐的教育氛围。
2.交互:教育惩戒的路径性话语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区别于对象化的主客体关系,人与人实际上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因此,个体生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交往的、互动的。主体间性又可译为交互主体性,体现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主体间性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5]“自我”与“他者”是客观存在的主体,也是处于交互状态的主体。交往对于教育具有本体意涵。教育是在师生交往中生成的,属于“交往行为范式。”[6]主体间性理论要求,一切教育活动的开展都必须基于师生双方的教育交往,从言语交流和情感交互两方面相互感知、相互观照。教育惩戒作为一种“灵肉一体”的教育活动,也应当立足于交互的师生关系,摆脱支配与占有、奴役与控制的异化状态,换之以理解与关爱、交往与互助的和谐形态。
教育惩戒是师生主体间的教育活动。然而,主体性不是自然存在的,是立足于“主体间的交往关系”[7]之中,需要师生双方相互承认、彼此成全的。同时,师生作为“彼此相互关系的创造者”[8],其主体间性关系也必须由师生双方在交往中共同创造。主体间性师生关系强调师生主体的双向和统一,认为师生不仅仅同为主体,更互为他者,且是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的他者。有别于对象化活动,交往所生成的不是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而是交互式的群体主体性,这在原则上把握了师生主体的共在性与平等性。因此,教育惩戒要想把握师生双方共在的主体性,就必须立足于交往活动。
3.共生:教育惩戒的诉求性话语
生命的共在性是生命的本然,自我封闭的生命是违背人类群体特性的。主体间性理论认为,个体的“此在”与他人的“共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共在”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9]此外,“此在”不能孤立地存在,“独在”也是一种“共在”。主体之间的共在,表明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你”将一切存在者都看作为和自身一样的主体存在,承认“主体间的‘相遇’关系”。[10]不同于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圭臬的个人主体性,主体间性强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在性,认为我与他人分别以主体形态存在于彼此的世界之中。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生命的共在性往往被遗忘,从而异化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导致教育演变为“一种心灵隔离的训练”[3]。作为“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1],教育的发生不能局限于封闭的自我世界,师生应敞开自己的心灵世界,感知彼此的共在。
教育惩戒是一种教育干预手段,教育惩戒的实施也应当关注师生的共在状态。教育惩戒中的“共生”指的是作为惩戒者的教师和被惩戒者的学生之间的共同存在与共同成长。其一,共在是师生存在的基础。教师和学生(惩戒者与被惩戒者)的身份是相互依赖、彼此成全的,双方的共在见证了双方的“此在”。其二,师生是共同发展的主体。教育惩戒不仅有助于纠偏学生行为、促进学生发展,同时包含着教师自我能力的提升。
三、主体间性视域下教育惩戒的突围进路
主体间性理论对于教育惩戒本体含义的把握具有指导作用,是教育惩戒突围进路中的指导思想。主体间性理论所倡导的视域融合、教育交往以及和谐共生,有助于缓解教育惩戒的艰难现状、挽回教育惩戒的成人本心。
1.视域融合:教育惩戒的主体观照
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他看来,教师和学生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是处于平等地位的教育主体。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交流,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必须同时观照师生主体。教育惩戒是一种教育管理措施,师生必须克服“为我性”,在感知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同时,教师作为惩戒的实施者,更需要站在学生立场上体谅学生,以视域融合的方式实施教育惩戒。视域融合原指理解活动中,理解者带着“先见”从当下场景出发,与被理解对象的视域相接触,最终整合形成一个新视域的过程。师生同时互为教育场域中的理解者与被理解对象,是教育理解活动的主体,也是教育发生的核心要素。在教育惩戒中,视域融合要求师生从原有视域出发,通过对话与交流进行“视域互换”,形成“交叠共识”,最终产生视域融合,达到自我与他者的统一。
需要说明的是,视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而非静止、封闭的。因此,视域融合必须要建立在交流与拓展的动态过程中,通过对话交流不断消除成见。视域融合还需要师生双方彼此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相互感知、相互理解,并在视域融合之中超越自身,以此升华自我。
2.教育交往:教育惩戒的本质思维
“教育过程就是一种交往过程”[6],教育过程所体现的是一种“主体—中介—主体”的交往实践关系。教育的旨趣在于“成人”,师生共生共在的交往性才是教育生成的本质。教育不是一种占有式活动,教育交往要立足于主体间性理论,关注师生主体间的双向建构。主体间性视域下的交往,摒弃了工具合理性对交往合理性的压制,使得生活世界免于“系统”的入侵,摆脱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宿命。教育实则是师生精神的相遇,是心灵深处精神世界的共享。因此,交往乃至深入交往对于教育的发生尤为重要。主体间性理论所倡导的交往式教育,要求师生是以言语交往为基本活动、以情感互动为深层内涵的全方位交往活动。
作为一种教育性措施,教育惩戒寻求的不是在压抑或对抗中利用武力使学生屈服,其更多地指向和谐氛围中学生主动承认并纠正错误。因此,这就需要师生通过交往在彼此理解中实施温和的惩戒。交往式教育所寻求的师生交互,有利于师生双方的互感互知,以深化教育惩戒的本真意味。其一,交往式教育要求师生表达并感知彼此的差异性,通过对话来彼此理解,明晰彼此的所作所为,在交往中达成“互识”;其二,交往式教育要求师生在交往中和谐共存,并形成双方认同的行为规范,达成彼此的统一性,在交往中达成“共识”。
3.和谐共生:教育惩戒的应然指向
每个生命都是独立存在的,拥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轨迹与个体价值。但由于享有着“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4],生命个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与碰撞,使得个体在各自的成长与生活中相互影响。世界向来是“我与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9]。自我与他者共同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以相互独立的生命形式各自存在,又在“自我”与“自我”的交互中产生联结,形成人与人的“自由联合体”,人类社会由此形成。师生共同存在于教育场域中,师生的“共在”见证着彼此的“此在”,师生的“此在”在交互中反映并成就着师生的“共在”。师生不是以自我为圆心的封闭式个体,教师和学生以一种共同体的方式存在于教育过程中,其交互作用影响着共同体中每一个主体的发展。因此,师生不应该互为彼此心灵成长的壁垒,而应作为彼此知识与情感的“生长元”。由于“先验”的不同,师生在异质性基础上彼此发展,又在交互中诱发共生。
教育惩戒是一种训诫性的教育措施,这种训诫性所指向的失范行为,很多时候不是由学生单方面造就的。教师言行的不妥所带来的学生心理上的排斥,也会增添或加剧学生的失范行为。因此,教师应明确与学生的共生状态,在动态交往中形成师生相得益彰的共生体。其一,创设“公共领域”,通过言语交互实现价值共感,取得共识的主体间性关系;其二,营造“情感场”,通过情感共鸣营造和谐氛围,形成师生的共生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