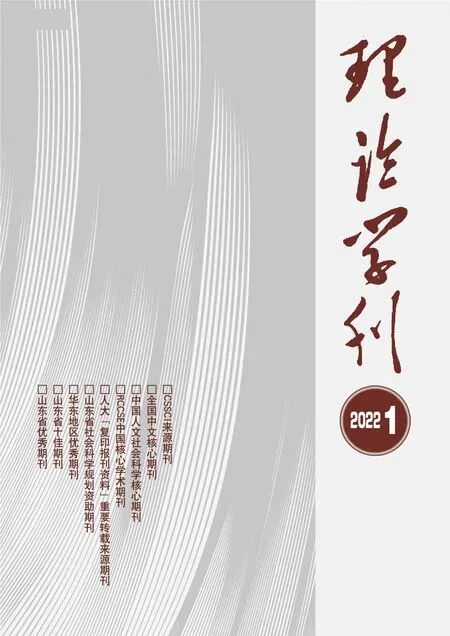五四前后郭沫若对孔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之思考
张 明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20世纪初叶,当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日本、苏俄辗转传入中国的时候,此时的不少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这里所谓的现实,既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具体社会状况,也包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实际地发挥思想指导作用,除了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的革命实践外,还必须紧密联系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不少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同时,对儒家文化却采取了或批判或质疑、或否定或回避的方式,并没有认真思索二者之间的会通与转换,而郭沫若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和认真探索的学者之一。在郭沫若看来,孔子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沟通并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基调,就为其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重要的价值支撑。
一、尊孔与反孔:五四时期郭沫若面临的文化抉择
20世纪初,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国粹派大力倡导国学,认为它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因此拒斥其他外来文化。国粹派的核心人物邓实就明确提出:“学者何?亦唯学吾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无汉学,无宋学也,无东学,无西学也。”(1)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政艺通报》1903年第24号。然而历史实践表明,国粹派盲目推崇国学,缺乏发展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必然会走上开历史倒车的复古之路。而与此同时,另外一批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激进学者却展开了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史无前例的清算。陈独秀指出:“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9页。另一位五四干将吴虞则直接将矛头指向儒家的宗法观念,视之为“洪水猛兽”,其云:“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是则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3)《吴虞文录》,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4页。鲁迅也在《狂人日记》中尖锐地指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就是礼教虚伪的面具,其实质就是“吃人”。这些说法确实切中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要害,揭示出了封建制度的弊端,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但是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无疑会助长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也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与上述两种文化立场不同,同样受西方先进文化影响的郭沫若,既没有像国粹派那样盲目推崇儒家文化,也不像当时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那样高呼“打孔家店”(4)按:目前学界对五四时期究竟有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存在争议。检视五四时期所有重要文献,除胡适在《〈吴虞文录〉序》( 《吴虞文录》,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中曾提出过“打孔家店”的说法外,尚未看到其他学者明确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具体争论可参阅王东:《五四精神新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杨华丽:《“打倒孔家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而是要求用一种“民主的待遇”(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3页。对待孔子。为此,郭沫若专门区分了孔子与后儒的不同。他批评汉代以来的儒家把儒学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了被历代统治者利用的一种政治手段,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他把这些“凝滞于小节小目而遗其大体”的儒家称为“拘迂小儒”(6)⑥⑧⑩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259、259、259、259页。。与对后儒的批评相反,郭沫若对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的学说极为欣赏。他称赞孔子是一位“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具有“圆满的人格”⑥的伟大天才,表明了自己对孔子的崇敬之情,希望也能像孔子那样做一个“球形的发展”(7)《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郭沫若原文如下:“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按:德语,《沫若文集》本作者自译: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形的发展是以他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如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这类的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底孔子,一个便是德国底哥德。”的人。在郭沫若看来,孔子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⑧。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文学家。仅就“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底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这一点而言,“孔子底存在”都是“断难推倒的”(8)《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0页。。不仅如此,郭沫若还表达了对孔子诗化理想的向往和赞誉之情,其云:“他闻音乐至于三月不知肉味的那种忘我ec-stasy的状态;坐于杏林之中,使门人各自修业,他自己悠然鼓琴的那种宁静的美景;他自己的实生活更是一篇优美的诗。”⑩总之,孔子那种完满的人性、圆满的人格、诗意的人生,正是郭沫若心目当中的理想追求,同时也是他为什么会觉得“孔子这种思想是很美的”,继而发出“我们崇拜孔子”呼声的根本原因所在。
综上,尽管郭沫若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不无主观情感的成分,但较之国粹派的盲目崇拜和激进学者的猛烈抨击,显然具有不少科学理性的因素。对于这样一种态度,成仿吾曾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20世纪初的中国学界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其“混沌”主要就在于新旧学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都存在很大的误解,具体表现为“旧的先入之见太深,新的亦鲜能捉到真义”,而在学界这种极为“混沌”的情况下,国内学者能做到“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的”,感觉“只有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9)④⑤⑥⑦⑧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296、294、292—293、293、293页。可以当之。实际上,这种“科学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也是郭沫若正确理解、合理吸收孔子儒学文化精神的思想前提。
二、“出而能入,入而大仁”:郭沫若对儒家入世人格精神的认同
虽然西方新学在晚清时期就已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西学的水平普遍低下,直接导致了对很多新文化人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并不是什么西学新知,而仍然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旧学。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小学里并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反倒是一些旧东西如国文、经学之类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其中,帅平均先生的《今文尚书》是他最喜欢的一门课(10)③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11页。;而到了中学时期,吸引郭沫若的仍然是经学,黄经华先生讲的《春秋》是给他印象最深的一门课③。这说明,儒家文化在郭沫若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对他今后文化道路的选择影响至深。那么,究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儒家精神决定了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呢?
1915年初,郭沫若到日本求学,同年6月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时由于学习压力过大,郭沫若患上了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一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记忆力几乎丧失殆尽,后来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就在患病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郭沫若接触到了王阳明的著作。就是这一次接触,不仅使他的内心慢慢平静下来,神经衰弱的病症渐渐消失,而且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和知行合一的伦理观也使郭沫若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对王阳明那种“努力于自我的完成与发展,而同时使别人的自我也一样地得遂其完成与发展”④的精神极为赞赏,认为“王阳明所解释的儒家精神,乃至所体验的儒家精神,实即是孔门哲学的真义”⑤。这种“孔门哲学的真义”在郭沫若对儒、道、佛三家思想进行的比较中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现。
在郭沫若看来,佛家的出发点就是“否定现实”,“他的伦理的究竟只是清净寂灭”,因此它“出而不入”;道家的宇宙观“本是活泼的动流”,但其人生哲学“却导引到利己主义”上面去了,因此它“入而不仁”⑥。而与道、佛两家完全不同,孔子追求一种积极向外扩充,由近及远、由下及上的人生态势,并与“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地、配天”的终极理想联系起来,因而他是能够“出而能入,入而大仁”⑦的。这表明,孔子不仅要实现个体一己之仁,而且还要实现与社会、与自然融会贯通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就与道家、佛家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儒家这种纵横天下、“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的人间“大道”,以及那种自我扩充、“四通八达,圆之又圆”⑧的积极入世精神,正是郭沫若所孜孜以求的,并且他声称要“把动的文化精神恢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11)《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正是出于对儒家这种“出而能入,入而大仁”精神的认同,郭沫若才最终从自我走向社会、从知识生产走向了革命实践。
三、“达则兼善天下”: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动力与契机
由于郭沫若始终怀揣着儒家那种积极“向外扩充”的入世精神,所以他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或者“纯粹的文学家”或者“纯粹的艺术家”或者“纯粹的思想家”(12)《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而是要走入社会,在社会中找到自我实现的方式。他心目中的这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就是参加革命斗争和社会政治实践。郭沫若走出的这条轨迹,其实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3)《孟子·尽心上》。的价值追求不无关系。
郭沫若青年时代就曾怀抱“以天下为己任,为救四海的同胞而杀身成仁”(1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页。的社会理想,而这显然与孔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舍生而取义”(16)《孟子·告子上》。的人生理念息息相关。郭沫若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道”具有一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因此他要求人们摈弃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思想观念,努力培养一种“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由此来“增进众人的幸福”(1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89页。。在郭沫若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民众的幸福以及社会的和谐。
正是儒家这种“兼善天下”的社会使命感和“杀身成仁”的笃定信念,使得郭沫若在接触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后,思想上发生了质的转变。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译完河上肇这位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所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郭沫若感觉自己像是从睡梦中被唤醒,对未来的人生道路不再彷徨和迷茫,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革命的认识也不再是仅凭“一味的感情作用了”(18)《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而是获得了一种理性的启蒙。可见,这本书不仅使郭沫若对社会革命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而且也为他今后指出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从此,他一改以往对自由个性的精神追求,转而直接投身于现实的革命活动。
1925年,郭沫若在一篇序言中又一次对自己的转变作出了明确表达,他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觉得在大多数人失去自由和个性的前提下,一小部分人却“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19)⑩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1926年,在写给成仿吾的一封信中,郭沫若也谈到这一点:“芳坞哟,我现在觉悟了”;“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20)《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按:“芳坞”系成仿吾的笔名。。在这里,郭沫若对自己早期追求的自由精神和个性解放作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认为个人的自由只有在全体的自由得到之后才能实现,所以他主张“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一部分已经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应该勇于牺牲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便是这个意思”⑩。
郭沫若的这些话语,一方面表明他早期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以及强烈的自我意识已趋弱化,而民族意识、救亡图存意识、建功立业意识则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他影响至深的儒家积极入世、“兼善天下”的精神理念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并逐渐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由此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实现实质性对接的可能性。
四、“马克思进文庙”:孔子仁学与马克思主义对接路径的文学书写
在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之后,郭沫若自称“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并坚信马克思主义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21)《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然而,自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以后,反对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像胡适、“研究系”、现代新儒家等,他们均声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应该另寻出路。而与这些质疑、否定的声音完全不同,郭沫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而且从文化精神上来讲又是与儒家思想相通的,因而完全可以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他认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相似,儒家不仅力求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而且也力求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比如,王阳明主张的“去人欲而存天理”思想如果放在社会发展的视域中来看,可以将其理解为“废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22)⑦⑧⑨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259、259、293—294页。。在这一点上,郭沫若认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对话的。
当然,王阳明“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学说本是就个体道德修养而言的,郭沫若把它理解为“废去私有制而一秉大公”显然是一种过度阐释,但是,抛开这一点,若就儒家的大同学说与社会主义思想而言,二者在精神上确有相通之处。马克思本人就曾明确地谈到,与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儒家的大同学说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点(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5页。。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似乎“更符合中国思想”,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儒家的大同观(24)参见[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572页。。郭沫若本人曾计划写一篇题为《马克思学说与孔门思想》的文章,以阐释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而搁浅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篇“带有几分游戏的性质”的小说《马克思进文庙》(25)⑩ 《郭沫若佚文集》(上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4页。。对于这篇小说,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就其思想价值来看,它或许是最早以文学的方式提出并探讨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儒学相结合并进行汇通的一个文本,因而其学术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文学意义。
在这篇小说中,郭沫若从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孔子和马克思虽然都为人所熟知,但实际上“真孔子”一直受到冷落,而马克思也被当时中国的学者们误解(否则孔子不会同众弟子在文庙里吃冷猪头肉,马克思也不会奔往文庙找孔子谈话)。针对这样一种思想现状,郭沫若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释和澄清。
(一)为孔子及其学说正名
郭沫若认为,孔子与后世的儒家并不相同,他只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且不说秦以后的儒家学说与其思想大相径庭,即便是同属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家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也与孔子不尽相同,因此,“总而称之曰儒,因统而归之于孔。实则论功论罪,孔家店均不能专其成”(2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3页。。郭沫若认为,倘若真用“儒家”来谈论孔子,让孔子去为后儒们的言论担责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华民族的堕落全归咎于孔子”⑦。针对人们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肆意曲解,郭沫若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种态度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他激进学者批孔、反孔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在郭沫若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孔子之所以被冷落、被批判,主要不是因为其思想中不具备促进社会改良、推动社会前进的内容,而是因为一方面后人“仅仅在名义上奉行他的教义”⑧,并未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后人所研读的儒家经典不是经典本身,只是经典的疏注”,所以“儒家的精神,孔子的精神,透过后代注疏的凸凹镜后是已经歪变了的”,于是“崇信”抑或“反对”孔子的人都只是看到了“一个歪斜了的影象”⑨,而非孔子思想的真实面目。因此,在《讨论〈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郭沫若就直言不讳地说,“孔子的思想也不见得就是‘谁也知道’的”⑩。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二)对马克思主义所受误解的澄清
郭沫若在为孔子及其学说正名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遭受的误解进行了澄清。在《马克思进文庙》这篇小说中,郭沫若就借孔子之口讽刺了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你的主义虽然早传到了中国”,但“你的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到中国来啦”(27)③④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162、163页。。事实上,由于五四时期国内尚且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完整翻译,因而导致国人对马克思的思想学说总是以讹传讹和产生误读。为此,郭沫若一直希望自己能用5年的时间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全部翻译出来(28)《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整个学界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准确、清晰、全面的把握,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承担起思想引导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避免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误解。
(三)孔子仁学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互补与汇通
在澄清了对孔子和马克思的误解之后,郭沫若便通过马克思与孔子的对话道出了“正解”。首先,郭沫若借马克思之口指出,他的思想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由于和孔子的学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些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③。对于这种论断,郭沫若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驳。他认为,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虽出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却可以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走上综合创新的道路,创造出一种新价值。
首先,郭沫若认为虽然孔子仁学本身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性,但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长处,因此可以用后者改造前者,使之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在郭沫若的小说中,孔子承认自己的思想不够系统,自己是一个不懂逻辑的人,因而在面对马克思时,他十分谦虚地说:“假如先把我的思想拉杂地说起来,我自己找不出一个头绪,恐怕也要把你的厚意辜负了。所以我想,还是不如请你先说你的主义,等我再来比付我的意见罢。”④在这里,孔子担心自己的思想缺乏逻辑性,一旦说出来,就会显得比较零乱,于是希望马克思先谈。这些话虽属孔子的自谦,但也是事实。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就曾指出,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29)[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但他并非哲学家;黑格尔则更为偏激,他认为在孔子那里,所讲的都是一些“常识道德”和“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因此,从孔子那里并“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30)[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0页。。这种论断虽然带有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但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孔子的思想表达方式的确不像西方学者那样具有严密的科学性与逻辑性,这可以说是孔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的短板。而郭沫若认为,孔子学说中存在的短板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长之处,因此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改造儒家思想,并使之具有严密的理论系统性。
众所周知,作为对整个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以及整体逻辑性是无与伦比的。从学科体系上说,它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方法论上说,它包括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理论基石;从知识结构上说,个体、家庭、社会、国家、自然等各个方面囊括无遗。这些均可以为整理孔子学说并最终将其改造成一种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论指导。这也是为什么郭沫若在小说中要让孔子用自己的思想去比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由此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处理二者之间关系时与其他学者在态度上的根本性差异:在郭沫若之前,五四时期的学者们基本上都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比附儒家思想;而到了郭沫若,则开始用儒家思想来比附马克思主义。这种颠倒后的态度恰恰表明了,郭沫若希望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进而实现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
其次,郭沫若认为孔子与马克思的出发点相同,都是立足于现世人生,注重民生,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马克思进文庙》中,马克思说他的思想的出发点首先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生是彻底肯定的”,随后又指出,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这个世界不断地适应民众的生存需求,从而使民众的生活获得一种最高程度的幸福。马克思的话音刚落,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迫不及待地接过话题,说自己的老师孔子同样也是重视民生之人,也追求一种人生幸福感的体验和满足。故而,郭沫若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和孔子一样,都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都立足于现世人生,都注重物质生产的发展,注重民生福祉,都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人民更幸福。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同的”(31)②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164、164—165页。。
再次,郭沫若认为孔子与马克思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构想与追求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相互趋同。接着上面的话题,孔子继续追问马克思对理想世界是如何设想的,人们是如何获得最高幸福的,马克思给出的回答是,只有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才能获得最高的幸福。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地去劳动,虽然不计报酬,但每个人的生活又都是衣食无忧的,他们的物质需求会得到充分的保障。孔子在听了马克思的描述之后非常激动,认为自己向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状态,与马克思追求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一致的②。
事实证明,儒家的大同理想的确是可以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对话的重要思想资源。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万国公报》华文主笔蔡尔康就将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学说相提并论,此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大同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陈独秀就是以儒家的大同社会来构想中国未来理想社会的,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是“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公同组织大同世界”(3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0页。;青年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也是大同世界,其云:“大同者,吾人之鹄也”(33)《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李大钊也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34)《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思想界热情高涨,都为之欢欣鼓舞、欢呼雀跃。中国学者之所以对俄国十月革命有如此之高的热情,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大同世界,创造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35)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0页。。
无独有偶,郭沫若也对儒家的这一思想特别看重,他不仅认为孔子与马克思相通,甚至认为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与孔子的大同理想也是不谋而合的(36)参见陈晓春:《从士的传统看郭沫若的人格》,《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1期。。可见,在郭沫若那里,孔子与马克思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构想与追求是趋同的,二者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对话性和关联性,这一点也使得他们在通往理想世界的途径选择上同样会存在着一些相通性。
最后,郭沫若认为孔子的“均贫富”与马克思的“公有制”在实现理想世界的方式与途径上彼此相通。近现代以来,许多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梁启超、胡汉民、梁漱溟等都认为儒家的“均贫富”思想与社会主义学说之间是相通的,二者可以相互转换。对于这种看法,郭沫若也是认同的,在《马克思进文庙》中,他就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这篇小说中,马克思认为孔子顶多只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并且竭力与孔子的思想撇清关系。他说,他的理想与孔子的空想不同,他的理想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一步步论证推导出来的。他认为,社会财富一旦“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中”,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对此,孔子不仅连连点头称是,而且还拿自己的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进行比附,而马克思却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孔子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而他主张“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他虽然反对财产集中制,但并不反对“产业的增殖”和物质的极大丰富,认为只有生产发展了,人们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才能获得“最高的幸福”(37)②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166、167页。,这和孔子所主张的“不患寡”“不患贫”是不一样的。
面对马克思的质疑,孔子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妥协和退让,反而进一步申明了其与马克思的相通之处。孔子说,自己也讲过“庶矣”“富之”,“富矣”“教之”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及“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之类的话,这些也同样是强调物质基础的重要性,由此可以证知自己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和马克思的学说是一样的,都是强调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相对公平的物质分配,同时反对利己主义,致力于营造公平的社会风气。在听了孔子的这番陈述之后,马克思终于被说服了,并且颇为感慨地说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②
通过小说中的上述对话,可以看出郭沫若找到了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点,由此也反驳了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在中国加以实施的观点。此后,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郭沫若又进一步提出了将孔子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接的方式与途径。在《王阳明礼赞》一文后面所附的“新旧与文白之争”中,郭沫若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儒家精神+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建设新构想,其基本思路就是在个人的修养方面可以借鉴儒家仁学精神,积极完善个体人格;在社会建设与发展方面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吸收各种先进经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促进个体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3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这种设想虽然还稍嫌粗疏,但却涉及到了如何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进行转化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可以说,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即一方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发扬优秀传统”(39)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第4页。,而郭沫若作为这个时代命题的较早提出者,在这方面早已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抹杀。
总之,五四前后,郭沫若以孔子仁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为基础来论证二者之间的转换和融合,一方面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参照途径,另一方面也满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落地生根的基本要求,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直至今日,郭沫若的这种探索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