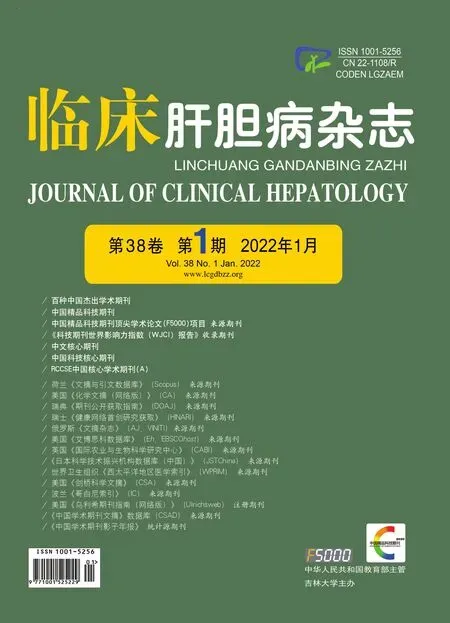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分子诊断研究进展
吴浩馨, 胡中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肝病中心一科, 北京 100069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是在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的腹腔感染,是肝硬化等终末期肝病患者常见并发症。肝硬化腹水住院患者SBP发生率为7%~30%[1],并发SBP患者的病死率高达20%~30%[2]。然而,SBP的早期临床诊断、早期病原学诊断及早期抗感染治疗仍是临床医师面临的巨大挑战[3]。如何快速诊断和精准治疗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综述分子诊断技术在SBP诊断中的研究成果及最新进展。
1 SBP的诊断标准及现状
所有腹水患者在入院时,无论是否怀疑有临床感染,均应进行诊断性穿刺。目前,SBP国际上的诊断标准为:在无明显的腹腔内、手术可治疗的感染源情况下,嗜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PMN)≥250/mm3[4]。
理论上,通过检测细菌本身来诊断细菌感染是金标准,但临床上往往很难实现。首先,样本细菌数量少,导致细菌培养的敏感度相对较低:有研究[5]报道,即使在感染性休克中,血液细菌的培养阳性率也只有69%。其次,Potgieter等[6]提出,在慢性病患者的血液中,存在大量有效休眠的微生物。这意味着细菌可以寄居在循环的免疫细胞中,无法被培养。第三,细菌培养时间较长,而抗菌治疗时机的延误可显著增加病死率。最后,部分细菌培养阳性的患者没有腹膜炎的相关临床症状,即所谓的细菌性腹水,在国际SBP的诊断指南中,腹水培养阳性也不是诊断SBP的必要条件[7]。
2 SBP的分子诊断原理及应用现状
近年来,细菌DNA(bacterial DNA,bactDNA)检测和测序已被应用于多种传染病的诊断,分子技术可以在4~5 h内检测出少量的细菌DNA[4,8-9]。特别是对生长缓慢的细菌和生物化学上无法识别的细菌,用分子技术进行鉴定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分子诊断技术的不断优化与发展,为SBP的诊断提供了机遇。
2.1 细菌DNA的诊断原理 细菌易位是肝硬化腹水并发细菌感染的重要病理机制,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当达到一个临界阈值可能易位进入肠系膜淋巴结、血液,最后进入腹水[10]。2002年,Such等[11]利用基于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首次在培养阴性的腹水和血液中检测到细菌DNA,并提出通过检测腹水或血液样本的病原体核酸来作为细菌易位的替代标志。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细菌易位可以是活菌,也可以是游离DNA[12]。因此,采用外切酶对样本中游离核酸进行预处理,可减少游离核酸对活菌DNA检测的干扰,能更准确反映样本中存在的具有感染性的活致病原[13]。然而,检测到细菌DNA是否便可以诊断SBP呢?
2.2 细菌DNA定性不足以诊断SBP 2008年,Zapater等[14]分析了156例非感染性肝硬化腹水患者在12个月内的临床转归,结果表明,检出细菌DNA的患者病死率较高,但bactDNA的存在并不能预测SBP的发展。2016年,Bruns等[15]在218例肝硬化合并感染症状的患者中发现,超过70%的肝硬化以及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的循环或腹水中存在bactDNA,但临床证实没有血流或腹腔感染。
bactDNA定性不足以诊断SBP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细菌易位时被循环免疫细胞破坏而暴露出bactDNA,使得细菌DNA片段存于血液或腹水中,但尚不足以引起感染[16]。第二,腹水通过调理作用、白细胞吸引作用抑制细菌活性或杀死细菌[17],在这过程中,细菌代谢产物可持续存在并被检测到。
2.3 细菌DNA的定量检测比定性检测可能更有助于SBP的诊断 2014年,Krohn等[18]提出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Q-PCR)来检测腹水中细菌量的问题。2019年,Alvarez-Silva等[19]通过Q-PCR定量检测bactDNA,发现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腹水bactDNA定量与SBP没有直接关系。Fagan等[20]在培养阴性的非中性粒细胞增高性腹水中发现,低水平细菌数量与炎症标志物关系不大,但bactDNA水平与中性粒细胞计数呈正相关。由此可见,SBP的发展不仅仅基于bactDNA的存在,也与其数量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SBP的发生中,消化道屏障是第一道防线,而腹膜免疫功能则是关键的第二道防线[17]。在肝硬化非感染性腹水中,宿主的腹膜免疫反应可以有效控制低水平的细菌,从而降低患者的SBP发病率和病死率。Q-PCR检测也有其技术局限性,需要标准品来实现绝对定量,而不同分子遗传学方法检测到的腹水bactDNA有很大的差异[15]。因此,分子诊断技术也需要不断地优化与进步。另外,肝硬化腹水患者临床病情复杂多样,腹水量的变化对细菌绝对数量的判断也可能有影响,但有关腹水量的变化和细菌数量之间的关系尚未有研究报道。因此,在检测分析bactDNA的绝对水平时,也要考虑腹水量的变化。
2.4 细菌DNA数量结合其种类能更精准地判断SBP 细菌易位后是否引起感染,与宿主的防御、免疫功能,细菌的毒力及数量有关。细菌的毒力取决于细菌的种类。从细菌培养的结果来看,革兰阴性菌、厌氧菌和肠球菌是造成肝硬化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21]。但随着侵入性操作在临床上的逐渐应用,外源性感染途径(如中心静脉置管、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也逐渐增多。近十年来,葡萄球菌的感染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2]。
2019年,Alvarez-Silva等[19]研究10例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腹水和血液的菌群特征发现,根据α-多样性指数,在属水平上腹水菌群多样性要高于血液。腹水中最常见的是紫色杆菌属、沙门菌属、皱纹单胞菌属。Chen等[23]发现,肝硬化腹水患者中,SBP发生率较高者,在门水平上以α-变形杆菌和γ-变形菌为主,尤其是莫拉氏菌和不动杆菌,这两类种群也是临床上重要的致病菌群。而病死率较高者主要以拟杆菌门和壁厚菌门为主,研究[24]表明这两类群在肠道中占主导地位,可能是此类患者肠道黏膜屏障严重受损,从而造成病死率较高。近年来,随着预防性抗菌药物的应用,因耐药菌感染导致病死亡率明显增加,尤其在亚洲地区[25]。最近一项关于全球耐药菌的研究[26]发现,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以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头孢菌素酶的肠杆菌科多见;法国以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多见;荷兰、英国等地以甲氧西林耐药葡萄球菌多见。在亚洲,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和鲍曼氏菌比较普遍[25]。但是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肠杆菌科仍然是近年来最常见的多重耐药菌。由此可见,检测特定种类的细菌DNA可能比仅仅检测细菌DNA的存在更重要。但分析特定细菌的种类和数量与临床结果及系统性炎症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SBP是肝病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终末期肝病的一个决定性分水岭。分子诊断技术为提高SBP的诊断效率提供了可能,2011年,Soriano等[27]采用PCR和测序技术检测16S rDNA基因的方法对SBP的诊断做了一些探索,然而从对SBP诊断标准的认识,连续标本的动态变化,以及分子检测技术的提高等方面的不足使得此技术没有真正应用于临床实践,在Gu等[28]运用分子诊断技术进行快速病原学检测的研究中,发现宏基因组测序(mNGS)技术对细菌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9%和91%,在12例体液培养或PCR阴性但临床判定最终确定了感染性诊断的患者中,60%的mNGS阳性。
因此,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SBP进行诊断具有巨大的潜能,通过对微生物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以及根据测序结果对细菌种类进行判定,能够更好的解释临床问题并服务于临床实践,所以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展望
(1)肝硬化细菌性腹水发生率逐年上升可能是细菌的短暂定植,需要更加精确的定性定量分子技术以及宏基因测序进一步研究。(2)需要新的生物标志物指导抗菌药物的应用,并评估抗菌药物的治疗效果。(3)通过细菌DNA的数量及分层从而准确地描述肝硬化腹水的菌群特征,提供新的诊断依据。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吴浩馨负责文献检索和论文撰写;胡中杰负责论文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