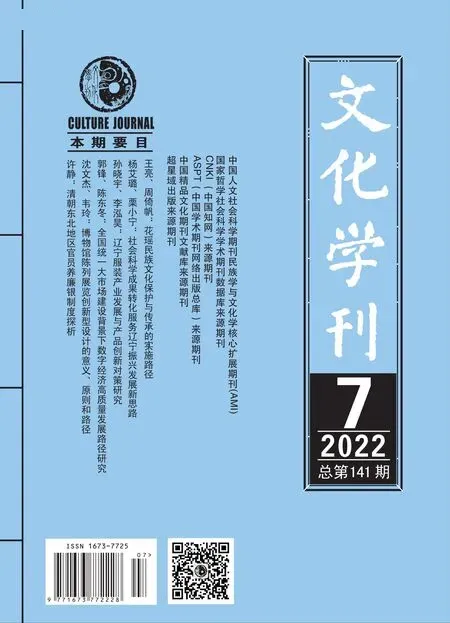欲望才是最甜美的酷刑
——尤瑟纳尔《东方故事集》阅读札记
刘晓晓
法国有两位著名的玛格丽特,其中一位是早已为中国读者熟知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而另一位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中文世界则知之者甚少。尽管她是法国20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亦是法兰西学院350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不朽者”。
余华在北大演讲时曾说:“尤瑟纳尔,这是我最喜爱的一个女作家,因为这个女作家非常地有力量。其他的女作家,像在中国比较受欢迎的另一个女作家杜拉斯,……她的力量当然也有,但是我喜欢的是尤瑟纳尔的那种力量,就是一把匕首刺进来的那种感觉。……尤瑟纳尔有一部很小的书,非常好的。”[1]余华所指的“很小的书”就是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
《东方故事集》初版于1938年,是尤瑟纳尔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最早的中译本是1986年漓江出版社的《东方奇观》(刘军强等译),还有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东方故事集》(罗芃等译)、2007年上海三联书店的《东方故事集》(郑克鲁译)。2021年2月,上海三联书店首度推出了《东方故事集》全彩插图本,译者为段映虹。
对读者来说,阅读《东方故事集》的体验应是美妙而艰难的。其美妙在于尤瑟纳尔用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和优美典雅、色彩感十足的语言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梦幻瑰丽的东方世界,即使这是一种想象的东方叙事,但它散发的流光溢彩仍能使东方世界的读者沉迷其中。而其艰难则在于尤瑟纳尔的写作是高密度的,无论是张炜还是柳鸣九,提及尤瑟纳尔时都深感其复杂性和丰富性,“她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容”[2]。《东方故事集》只有约8万字,表达的却是尤瑟纳尔对人类一些“永恒”问题的深切关照,蕴含着浓厚的思辨色彩,读者只有放慢脚步,才能理解其中的重量和密度。
一、欲望
(一)《马尔科的微笑》——“阿喀琉斯之踵”
罗芃在《东方故事集》“译本序”中指出,所有的故事“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作者对人生、对世界深沉的叹息,如果用一个字来说,那就是‘怨’”。在笔者看来,这本集子中所有的故事都充斥着“欲望”,这些欲望伴随着激情“狂暴而炽热地燃烧”。斯宾诺莎认为,人类驱动力的意识是欲望。近代以来,人类在欲望驱使下构建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欲壑难填,当欲望无法被满足时,人便会感到痛苦,这也就是罗芃所说的“怨”。
尤瑟纳尔借笔下人物指出,对人类来说,“欲望才是最甜美的酷刑”[3]42。这句话出自《东方故事集》的第二个故事《马尔科的微笑》。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部作品虽名为《东方故事集》(NouvellesOrientales),但法语中的“Orient”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指“整个亚洲、东北非部分国家以及埃及,从前还包括欧洲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所以作品不仅取材于中国、日本、印度的寓言和传说,还有希腊、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马尔科就是塞尔维亚历史传奇中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英雄。在这个故事中,斯库台总督的遗孀狂热地爱着马尔科,但马尔科对她已感到厌烦,遗孀遂引来士兵逮捕马尔科。马尔科为脱困跳入大海,却被遗孀的丝绸锁套拖上海滩,他只能装死以求脱逃。遗孀命令士兵对马尔科施以酷刑,马尔科经受住了种种酷刑,却在最美的姑娘哈依夏跳舞时露出破绽,“他的唇边浮现出一丝幸福得近似痛苦的微笑”[3]41。在这个故事中,所有的人都在欲望的旋涡中挣扎,马尔科可以承受肉体的极度痛苦,但禁不住色欲的诱惑,欲望就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同样的,遗孀对爱情的狂热其实是内心征服欲望在作祟,这也给她带来了死亡,最终她在士兵退去时被马尔科杀死。
柳鸣九曾指出,《马尔科的微笑》“把男人的一种共性或准共性浓缩在一个微笑里,堪称性格小说的佳品”[4]。笔者认为,《东方故事集》中马尔科不仅代表了“男人的一种共性”,更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性弱点,作为英雄的马尔科尚且无法摆脱欲望的纠缠,更何况普通人呢?
(二)欲望支配下的一幕幕悲剧
《王浮得救记》中,大汉天子拥有天下,“如同盛夏”一般。然而十六岁之后,他发现汉帝国并没有王浮的画那样美丽,只有王浮“通过千种线条、万种色彩进入的那个帝国,才是唯一值得统治的国度”[3]15,所以他恨王浮,要让他遭受酷刑。《源氏公子最后的爱情》中,暮年的源氏因察觉自己不能摆脱俗世的诱惑而陷入痛苦之中。花散里夫人执着于源氏的爱情,甚至隐瞒身份,两次假扮他人陪在源氏身边,然而源氏死前回忆时独独忘记了花散里夫人的名字,苦涩的泪水如骤雨般从她的脸颊上冲刷下来。《失去头颅的迦梨》中,女神迦梨被心怀妒意的天神们斩首,她的头颅滚落地狱,错误地和娼妓的身体结合。迦梨的思想如莲花般圣洁,身体却贪恋情欲,灵与肉的矛盾使她痛苦地游荡在印度平原上……可以看出,故事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欲望的手下败将,在欲望的支配下演出一幕幕悲剧。
(三)时代背景对尤瑟纳尔“欲望”书写的影响
叔本华认为,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欲望的短暂满足“就像抛向乞丐的施舍,今天维系了他的生命,这份痛苦又延长至次日”[5]。为了摆脱痛苦,人类的欲望不停地增殖,最终使欲望成长为吞噬人类的怪兽。当然,尤瑟纳尔并不否定一切正常的欲望,我们需要结合其创作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尽管尤瑟纳尔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常在世界各地漫游,离群索居,但任何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时代浸染。尤瑟纳尔曾说,《东方故事集》中,除了《失去头颅的迦梨》和《马尔科·克拉列维奇之死》,其余作品大多发表于1936—1937年。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役使于占有物质财富的疯狂欲望,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导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法西斯势力上台,整个欧亚大陆事实上已经笼罩在战争阴影下。尤瑟纳尔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九三八年,除了聋盲之人,哪个不晓战争即将爆发。”[6]442此时她已经预见到现代文明会遭遇一场浩劫,这将置人类于巨大的生存危机之中。如何才能走出这次危机呢?尤瑟纳尔将视线转向了东方。
二、东方之道
(一)尤瑟纳尔的世界主义观
毋庸置疑,尤瑟纳尔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童年的成长经历使她对东西方文化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她在同雅克·尚塞尔的访谈中曾提到:“道所传达的一切令我着迷——道家智者们互不干扰,……就某个事物长久地进行思索,并且尽力融入这个角落里的生命。”[7]尤瑟纳尔看到不同文化中的合理成分,认为人类应该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以解决面临的共同危机。在第六个故事《燕子圣母堂》中,她就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基督教修道士泰拉彼翁无法容忍异教徒,带领信徒对希腊的山林水泽仙女展开残酷猎杀,他不停地砍伐仙女们寄居的悬铃木,最终将她们赶到山洞中。为了赶尽杀绝,泰拉彼翁在山洞建了一座教堂,封死了出路。最终,圣母玛利亚将仙女们变成燕子救出。笔者认为,《燕子圣母堂》表面上是一个讲宗教迫害的故事,实际上暗指当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尤瑟纳尔借由圣母玛利亚之口表达了她对任何绝对化倾向与主义的不赞同:“可是你想不出一种办法,让仙女们的生命和信徒的得救可以两全其美吗?”[3]119尤瑟纳尔的世界主义立场,使她能够跳出西方文明的桎梏,以客观的态度发现东方文明的精粹,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尤瑟纳尔在《王浮得救记》中隐晦地给出了答案:到东方去,寻找那条解困之“道”。
(二)尤瑟纳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隐忧
《东方故事集》1978年重印时,尤瑟纳尔在后记中提到最后一篇故事《科内琉斯·伯格的悲哀》毫无东方色彩,说自己只是因为主角是一位荷兰画家,想将其与同为画家的王浮相对照。在笔者看来,这一安排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寓意。在这个故事中,随着时间流逝,画家科内琉斯的艺术创造力无情地弃他而去,尽管他仍善于分辨“色调上最细微的差异”[3]172,但是他已经丧失了将世间美好诉于画布的能力。故事结尾,科内琉斯呆呆地看着运河,发出苦涩的叹息。科内琉斯的遭遇实际上隐喻了当时西方社会在繁华的外表下潜藏的巨大危机,如人的异化、道德困境、战火纷飞等。尤瑟纳尔认为,这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有物质财富的疯狂欲望所导致的。她曾指出,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技术成果全部服务于贪婪,而这种贪婪则是一种邪恶。[6]484在这个故事里她表达了自己对现代文明的隐忧,这最后一个故事和第一个故事《王浮得救记》正好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隐含了尤瑟纳尔对东方文明中“道”的崇尚。
(三)“超脱”——解困之“道”
尤瑟纳尔说《王浮得救记》的灵感来自古老中国的一则道家寓言。故事中的王浮是一个“老庄”式人物,他摒弃了一切物欲需求,醉心于艺术的世界,“在王浮看来,除了画笔、颜料、墨汁、绢丝和宣纸,世上的任何东西也不值得拥有”[3]3,这使得他可以用纯粹的视角观察世间万物,从而窥探到宇宙的真谛。他看到了天地之间美与丑、生与死、具体与抽象的互相转化,所以王浮让弟子凌装扮成公主在柳树下抚琴,因为“没有一个女人不真实到可以充当他的模特儿”[3]8,每个女人都是具体的,所以不具有抽象性,而凌因为不是女人,反而具有普遍性。这里和《道德经》中“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精神实质相同。王浮参透了世间万物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奥秘,所以可以透过表象,看到内里的“雪山、春花和夏月”。他笔下的世界如此瑰丽,使弟子甘愿抛弃一切追随他,亦使大汉天子沉沦其中无法自拔。可天子不懂“道”,当跑遍整个帝国,也没有看见王浮画中那样的花园,当“活生生的女人的肉体就像肉铺挂钩上的死肉一样”[3]15令他反感时,天子震怒了,于是下令对王浮处以极刑。天子的痛苦来自贪婪,他对拥有的一切熟视无睹,却嫉妒穷画家笔下那个高山积雪永不融化、田野水仙永不凋谢的国度,无法得到时就要毁掉创造这一切的人。
相反,贫穷的王浮在精神上是无比富裕的,王浮参透了世间的“道”,在他眼中万物都是和谐共生的,甚至死和生也不是对立的,死可以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因此,王浮看淡了财富、名利,甚至也不惧怕死亡。在兵卒将手放在他的颈项上时,王浮并不畏惧,只注意到士兵衣袖的色彩跟袍子不相称;在弟子凌的头颅应声落地时,王浮竟然欣赏起凌的鲜血“在碧玉地面上留下的美丽的绯红色痕迹”。这不禁令人想起庄子在妻子去世时的鼓盆而歌。道家认为,生死的转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一样,得道之人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无欲无求无为,才能超脱俗世痛苦,寻得至乐。故事结尾,王浮畅游在艺术的天堂,真正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他和弟子凌乘坐着小船永远消失在“他刚刚画出来的万顷碧波之中”,正是王浮的“超脱”拯救了自己和凌,他也最终到达了毕生追求的至美世界。同样面对水面,西方的科内琉斯只能发出苦涩的叹息,而东方的王浮完成了自我拯救。尤瑟纳尔借助古老东方文明中的“道”,为正在经历现代性危机的人类寻找了一条解困之“道”。
三、结语
《东方故事集》写的是东方,却又超越了东西方之间的界限,尤瑟纳尔借由异域故事的外壳,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危机进行了深切思索。鲁枢元指出:“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在西方社会现代化启动之初,其实就已经埋设下最终致命的陷阱。”[8]《东方故事集》初版时,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欧亚大陆,如今,人类社会又正在面对疫情的冲击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困境。《东方故事集》中表现出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亦可给我们带来更多启发。同时,尤瑟纳尔的复杂与宏大也导致了她在当下这个时代的沉寂,翻译家袁筱一曾说,即使在法国,尤瑟纳尔也不属于进入了大众阅读领域的作家。
中国对尤瑟纳尔的译介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2—2003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史忠义主编的尤瑟纳尔文集。此后直至2007年,上海三联书店才推出郑克鲁翻译的《东方故事集》,但此译本的翻译和点评引起了些许争议。时隔14年,上海三联书店再次推出段映红翻译的《东方故事集(插图本)》,段映红的翻译既忠实于原著,又有东方的含蓄蕴藉,受到读者好评。奥姆松在法兰西学院接纳尤瑟纳尔的典礼上说道:“能在您现在所在的这座古老而名声卓著的建筑物里欢迎您,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您当然不是第一位院士,但您是第一位女院士。……您本人就构成一个悠久光荣的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9]今天,能在文学的世界再次与尤瑟纳尔相遇,对每一位中国读者来说,亦是一种“莫大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