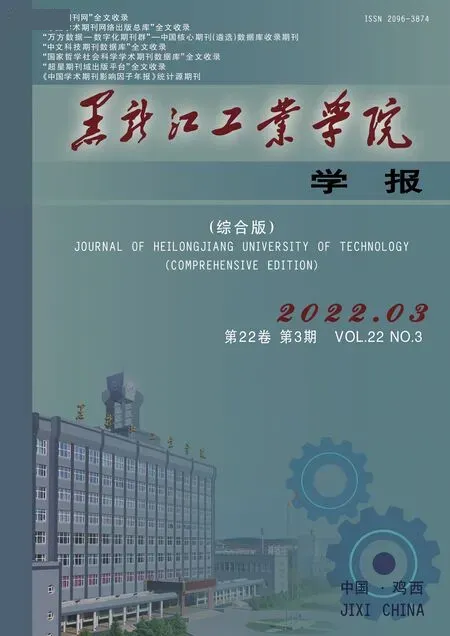以疼痛传达生命的原乡记忆
——从作家、地域、时代视角解读萧红《生死场》
王晓晨,宋依洋
(1.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2.沈阳科技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6)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的崛起给文学界以特别的震撼。萧军、白朗、舒群、李辉英……这些作家执着地发掘这片白山黑水间血染的民族灵魂,书写着关东地域的民族史诗。而在他们中间,从呼兰小城走来的女作家萧红,在小说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以其独特的乡土叙事和艺术魅力赢得了文坛的青睐,鲁迅称她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以悲壮苍凉的笔调咏叹着苦难沉痛的黑土地,用郁结沉痛之笔呼喊着女性解放与人格独立,以凝重深刻的哲思探寻着存在的生命体验。
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认为,文艺创作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强调了地域、时代与环境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如果说,迟子建是以一部优美的诗意剧作,在淳美厚朴的雪国之乡掀起了浪漫主义的旋风,那么萧红则是以一枝沉痛悲壮的巨笔,在愚昧落后的黑土地上打开了现实主义的闸门。《生死场》呈现了一个乡村荒野式的景观,一幅在历史进程中生和死的图景,一段关于民族伤痕的记忆,情节跌宕多姿而格调悲壮苍凉。这里,既有琐碎的家庭怨怼,又有伟大的民族情感;既有沉重的人生忏悔,又有深刻的生命思索,在北国的血与泪中听取民族的呐喊。
一、作家:跌宕人生的悲凉书写
罗兰·巴特认为,我们总能在小说文本中找到叙事者,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立场与态度。《生死场》呈现了对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然而,萧红的人生亦是如此。她是一个深受着封建家族制度的沉重压抑,被故土沦丧的历史洪流冲入苦难深渊,却又不曾停止过其敏锐透视与深刻思考的惊世才女。在小说中,她不仅传达了对生命意识的哲学思考,更发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压迫的深沉呐喊,这与她最早感受这世间的凄苦风雨和人情冷暖密切相关。
从“知人论世”说切入,坎坷的人生经历对萧红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地主家庭,在那个古老的封建意识尚未瓦解的旧社会里,重男轻女的观念深入人心,萧红从小就在父亲的谩骂、母爱的缺失、祖母的冷漠中度过。只有在宽厚善良的祖父那里,她才能体会到人世间的爱与温情。然而,祖父的离世却“把人世间的爱和温暖都带走了”。可以看出,童年生活中爱的缺失与创伤对日后萧红的人生、爱情以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在《生死场》中有明显体现,她在叙述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融进亲身经历和感受。在小说中,她把女性亦隐亦显的思绪描刻得纤细入微,行文渗透着悲凉的命运感,潜藏着作家对人生的深刻体悟。
小说是作家心灵的外化,它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体悟。萧红以其深刻的社会观察、文化省视的眼光以及苦难的人生经历,探索着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悲苦命运。她以亲身经历企图挣脱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少女时期,面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出走与之反抗。原以为逃离封建家庭,她就可以奔向自由的天地,然而女性的天空是低沉的,羽翼是稀薄的。在那个局势动荡、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她颠沛流离、饥寒交加,先后奔波于北平、西安、上海、香港等地,一生漂泊、居无定所。而她的爱情之路犹如布满荆棘的原野,给她带来了无尽的苦痛与伤害。先后经历了未婚夫的抛弃、男友的家暴与出轨、丈夫的冷漠、两次分娩的痛苦经历……最终在病痛的折磨中悲惨地逝去。在《生死场》中,她把乡村社会的愚昧思想容纳进历史文化心理的男女、家庭与婚姻问题之中。
在萧红笔下,女性的生存环境是压抑的,乡村女人的生育和死亡是卑贱的。如同《生死场》中所描写的那般凄凉:
“光着身子的女人象一条鱼一样趴在那里……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1]
生育的疼痛与恐惧无异于女人的灾难。萧红书写时的焦灼、不安,像闷罐子一样透不过气,这种苦难书写都源自于她本人的亲身经历,她那痛苦的生育经历也是这样一种无偿无味的纯肉体的苦难经历。因此,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自传色彩。在这里,她将女性的生育视为一种刑罚,是毫无尊严的受罪,是如同猪狗一般的动物性生产,是男性权力和欲望话语的投射。
在《生死场》中,她以女性的生育作为透视整个乡土生命本质的起点,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对宗法家族与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进行抨击,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戕害,表达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小说的艺术风格是凝重的、粗豪的,她在沾满血与泪的苍凉灵魂中,毫不心软地剖析着封建社会男性的粗劣面目,腐朽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的压迫、暴力与摧残,传达出撕心裂肺的痛苦。她几无剪裁地把封建社会的怖慑,男性的摧残铺天盖地地袭击着女性的肉体与精神,通过一种绝望的挣扎,达到女性对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与追寻。
“个人历史”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高度一致性。灾难沉重的社会和漂泊不定的生活折磨着她,在人生的隐痛与文化的忧愤下,她谛视着封建意识笼罩下的中国女性的苦难生活、顽强地挣扎和悲惨的结局。《生死场》中的那个渔村最美的女子月英,在瘫痪的痛苦和丈夫的摧残下,被折磨成可怕的怪物。善良温柔的金枝在华信之年,身体和灵魂遭到中日两国男人的蹂躏。男人为了性可以无偿去享用女人,将暴力施加于女人,而女人却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她以幽深略带抒情的笔调,深刻地描绘出女性命运的磨难与辛酸,而这种悲楚与辛酸的人生又带有种种沉重的枷锁,难以挣脱。满纸悲凉,使人们沉浸到暗夜深沉而凄凉的社会中。
萧红严峻地解剖着男权思想的痼疾、对女性个体与生育权利的无情践踏。她以一枝沉重而苦涩的笔,呕心沥血,描刻了封建男性社会的千形百态,使人们仿佛看到了百年以前中国大地上千万妇女的悲与泪,反省到残存的男权社会给女性的肉体与心灵造成的双重折磨。《生死场》中游荡着一个个属于中国女性力求挣脱压抑的坚定而痛苦的灵魂,笔端悲壮苍凉。通过对一群备受压抑与残害的农村妇女的心理状态和浮沉悲凉的命运遭际,探讨了女性生存的主体价值,饱含着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妇女出路的探寻。
马克思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经历的环境造成的。萧红一生所经历的苦痛与灾难异于常人,她的三十一年的生命几乎都在受难中度过,正是在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下形成了她的性格,也成就了她的创作。她奔突于布满血迹泪痕的苦难旷野,以沉重的心理倾跌去考验生命的力度;她撕开人间温情的伤疤,传达了时代风暴下女性生存的艰难。在小说中,她表现了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与思考,潜藏着她的爱与怜、哀与怒、深沉而又真挚的情感。
二、地域:苍茫北国的原乡记忆
“地域文化小说是以地域文化为审美对象,在文本构成上有着明显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现象。”[2]因此,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文学创作的内在特征。萧红以苍茫的北国风情,地域色彩与曲折的故事为躯壳,潜藏着对地域文化性格的探索与思考。在《生死场》中,她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独具特色的田间图景、民情风俗与地域色彩相融合的东北地方画卷。
美国批评家赫姆林认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萧红以广阔的审美视野,把人们带进苍茫荒寒的冻土之地,带进那些带有地域色彩的东北乡间,于平常生活的描绘中透视出深厚的生命思索与艺术韵味。《生死场》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独具匠心地在人物的对话、行为、作派中,灌注了东北地域的人文气质,灌注了北方人民粗狂豪迈的野性,从而在一幕血泪交织的揭竿而起的反抗中,叠现出黑土地上的农民千古承袭的文化性格。
地域文化影响作家创作,关东风物给萧红以深刻的熏陶。这个从冻土之地走出来的东北作家,得于乡土的滋养,展示着苍茫辽阔的北国大地和强悍朴实的乡村父兄的粗犷性格。萧红总是在纯朴和谐的自然风景中寻找人文变迁,这种山川草木间孕育着的健谈爽朗的地域性格。她在东北旷野的慷慨豪迈中寻找元气充盈的美学风格,其源于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黑土地。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东北乡村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她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自然古老、宁静纯朴的田间地方画卷。她沾染着乡土民俗的尘埃,作品中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东北的自然地理风光与人情风俗,这里的林荫树叶、青稞菜园、高粱玉米,洋溢着纯朴的乡土气息;这里的土屋篱墙、生活方式、田间劳作呈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情。
“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着榆树的根端。”小说的开头通过山羊与榆树的描写展现了农村社会的自然景观,奠定了乡村写景的基调。她将叙事隐藏在写景之中,通过对自然景物的书写,呈现了这片贫瘠而荒凉的土地上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群体心态,表达了她对东北乡村农民生存状态的思考,即改变这种原始古老的生活方式与麻木愚昧的国民心态。萧红通过故土的回忆魔匣放出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生命灵魂,从不同的取向拓展了地域人文的张力,在暗夜弥天的环境中不时闪烁着地域风情与民族生命的色彩。
迟子建曾说“对于生活,我觉得庸常的就是美好的。平常日子浸润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让你能尽情品咂”[3],《生死场》延伸至平凡的生活层面,给人以关东土地的独特的旷野乡村气息,展现了东北乡村的自然与文化、世相与人情。生活细节的运用,使故事颇为充实。萧红以圆熟的文笔,潇洒自如地伸向农民的日常生活,带有浓郁的风俗色彩和地方性诗情。她把人物性格渗透在景物和场面之中,疏密有致,展示了北方土地的生活画卷,质朴平易之中洋溢着乡土气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语言学家萨丕尔提出,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萧红的小说也并非全用普通话写作,其笔端也洋溢着浓郁的东北地方乡间俗语。《生死场》中糅合着北方语言,质朴中不失刚健,浅白不流于俚俗。以富有人情味和地域性的语言,展现了北方人民的性格。冬日里,乡村妇女在王婆家满炕坐着,人物之间的对话是自然纯朴的,那些毫无雕饰的口语絮絮道来,即活生生地描绘了东北人民的善良纯厚,又使人体会到语言中那热情豪迈的洒脱之气,从容调动方言,使平易的文字散发着独特的地域风情。小说中人物的举止言谈是简朴的,以自然的话语书写着乡村男女的厚道朴实。因此,地域文化氤氲着作家的乡土情怀。宽阔厚重的东北土地,负载着萧红的童年记忆,这里有欢乐与悲哀,苦难与诗情,寄予着作家的乡土情怀。而《生死场》这部小说呈现了鲜明的东北地域风情,萧红笔下的这一个农夫、这一个农妇、这一个故乡无不在静静地诉说着在时间长河里静止不动的黑土地上的故事。
三、时代:民族觉醒的奋起抗争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在1927年掀起了带有沉重历史感的一页,参与历史与战争的文学,并不曾孤独和寂寞。举凡民族危亡、国事蜩螗之际的作家,站在历史界碑之旁,负有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身处时代动荡、山河沦丧的硝烟岁月里,萧红以透彻的视角审视着国民灵魂在民族危亡之际的麻木与觉醒。她反思民族肌理的痼疾,揭露国民性的荒唐与麻木,由一往情深地恋慕故土,到省视着农民的觉醒与反抗,从特定角度透视出国民的社会文化性格与民族精神。
利哈乔夫认为,作家要想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与外部现实发生深刻联系,要看见人们眼中的泪影,听见他们内心的哭泣。萧红怀着理解而又焦虑的心情体验古老国土上那些痛苦的心灵。昔日的山河故土在日寇侵占的恶雨阴霾之中跌入泥塘水潴之中,东北大地陷入了它最苦难灰暗的时期。她在血泪交织的土地上呼唤着奋起抗争的倔强灵魂,在坎坷不平的辙痕上,探索民族的出路,从牵动人心的故事中,烘托出忧愤与悲悯的格调。
深沉的眼光与厚重的杰作,使萧红突破了女性文学的狭小格局。如果说,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是把握空间上的跨度,横向地展示以呼兰小城为缩影的北方社会的整体性,那么《生死场》是把握时间上的跨度,纵向地展示社会的历史性,她力求展现和探索在国破家亡之际东北农民乃至整个民族命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小说描写了九一八事变时期,东北乡村底层人民的生存与死亡。萧红关心田夫农妇在历史变动中的生活与命运,关心他们的文化环境、行为方式和国民心理。她以严峻苍凉的笔法写下了北方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面对日寇侵略,所做出的觉醒与抗争,表达了她对于国民性与民族性的探索。
《生死场》展示东北乡村的生活图景以及北方底层人民在生死场上的生存与挣扎,于质朴苍茫的格调中显示着动物般生生死死的生命形态。赵三、二里半、王婆、月英、金枝……萧红冷峻地叙述着这群乡村儿女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被践踏尊严的生活。日寇的烧杀抢掠、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的残酷暴行,激起了这片黑土地上的乡村儿女的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空前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无论男女老少,皆发出了反抗侵略、誓死卫国的呐喊。
萧红从悲凉的乡土中弥散出忧愤,具有熔民族命运与农民心态于一炉的历史格调。通过李青山等农民自发形成的“镰刀会”奋起反抗,发出了东北人民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呼喊,揭示了中华儿女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可摧毁的民族意志。他们在强悍中有正气,在民族危难之时能揭竿而起。赵老三流着泪说:“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帜插在坟头,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以王婆为代表的乡村妇女为了支持男人们抗日更发出了是“千刀万剐也愿意”的口号。这群乡村男女在悲怆的土地和山川的寂寥中,发出旷野里的呼喊。
叙事视角决定文本的叙事态度。萧红以冷隽、深刻,甚至有点刻毒的眼光,凝视着那片沦丧的山河故土的鬼影兽行。她通过独特的视角以女性经历的苦痛与灾难撕开了荒凉土地上的屈辱伤疤,揭露了外来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小说写了女人如何间接地经历战争,日军的兽行使乡村的年轻姑娘日夜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残酷的魔鬼凌辱着脆弱的生命,艰难的生存困境压迫着她们,贫饥与苦难折磨着她们,她们不断地逃离故乡而奔向城市,但却终究逃脱不了厄运的魔爪。她写战争的残酷,写血的反抗,渗透了她对生死、人性的体悟与思考。
历史的痛苦教会民族进行清醒的自我反思。《生死场》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人的心灵史与民族苦难史。萧红所描绘的人生图景复杂地交织着时代的迫力、民族的苦难与人民的创伤,是东北土地上悲与愤交融的历史画卷。她展示了乱世中北方农村的黑暗荒凉与血迹泪痕,在国家、社会与家庭的空间维度上,探索着死亡与求生、战争与人性。
结语
贾剑秋在《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提出,文学是文本影像。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萧红的小说中看到了苍茫北国的古老画卷,民族苦难的历史印记,《生死场》是一部对黑暗的愤懑和对光明的渴慕的民族启示录。传奇的人生经历、故土的地域风情与动荡的战乱岁月深深地影响着萧红的创作。在小说中,她以苍凉严峻的笔法控诉着封建社会下女性命运的悲苦,审视着历史进程中国民灵魂由麻木到觉醒,她勘探着民族精神的坚毅正气,执着地探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意识和蕴藏在社会底层的生命强力。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