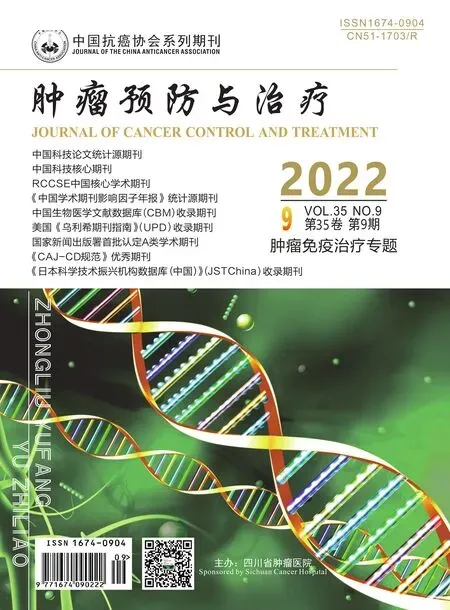肿瘤放疗联合免疫治疗之回顾与展望*
辇伟奇,许文婧,王佩,孙建国
400021重庆,重庆市中医院 肿瘤科(辇伟奇、许文婧、王佩);400037重庆,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肿瘤科(孙建国)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阻断剂为代表的单抗药物在多种晚期/复发转移肿瘤中被证实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使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简称免疫治疗)成为研究的新热点。不过,单纯免疫治疗的肿瘤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仅10%~30%,在不同瘤种存在疗效异质性,免疫治疗相关性不良反应(immune-rea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也不可忽视,因此,大多数肿瘤患者不能从单纯免疫治疗长久获益。免疫治疗与其他治疗策略的联合,已成为当前免疫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中,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更是被寄予厚望。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显著提升免疫治疗的疗效,ORR可达50%甚至更高,部分患者可出现远隔效应,被誉为革命性时代的来临[1]。然而,仍有部分患者不能从放疗联合免疫治疗中获益,即使已有获益患者仍存在较常见的免疫耐药现象,仍有大量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采用何种恰当的放疗模式,如何采用最佳放疗剂量和照射方式,哪种免疫治疗方案是最优的,都是现阶段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1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理论基础与研究
放疗可以造成DNA损伤诱导的肿瘤细胞死亡;可以通过触发促炎(和抗炎)介质释放来调节肿瘤细胞免疫原性和佐剂性,增加肿瘤浸润免疫刺激性细胞和增强新抗原表达,总体而言,在阳性免疫刺激表现中,这些现象常被概括为使免疫“冷肿瘤”转化为免疫“热肿瘤”[2]。
1.1 放疗增强肿瘤细胞的抗原释放与呈递
放疗已被公认为能够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ICD)的抗肿瘤方法之一。ICD 是一种细胞死亡,可促进由 T 细胞介导的对死亡细胞抗原的免疫反应[3]。肿瘤细胞基因突变可能产生新抗原从而激活T细胞反应,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与免疫治疗疗效正相关。放疗本身导致许多 DNA 损伤,包括碱基修饰、单链断裂和双链断裂,辐射产生的这些 DNA 改变可能是增加免疫监视的新抗原的丰富来源[4]。肿瘤细胞通过下调MHC-I的表达产生免疫逃避,避免被免疫系统所清除,而放疗可以上调癌细胞表面 MHC-I分子的表达,树突状细胞等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将抗原递呈给细胞毒性 T 细胞,使后者更好地识别抗原并活化杀伤肿瘤细胞[5]。放疗还可以促进抗原呈递细胞对受损肿瘤细胞的吞噬作用,导致肿瘤特异性T细胞的启动增加。辐射的促吞噬作用是由辐射后肿瘤细胞释放损伤相关分子模式介导的,包括内质网伴侣钙网蛋白易位至细胞膜,释放高迁移率族蛋白B1和三磷酸腺苷,它们共同促进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作用[6- 7]。这一作用伴随着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如 CXCL10 和 CXCL16,与放射线促进的肿瘤血管正常化过程一起,可以增强活化 CD8+T细胞的浸润[8]。当放疗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时,放射治疗的这些免疫调节作用会进一步增强[9]。
1.2 放疗启动免疫相关信号通路
除了增强肿瘤相关抗原的释放和呈递外,放疗还可以通过触发干扰素基因刺激物(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STING)介导的 DNA 感应途径来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STING通路是保护宿主免受 DNA 病原体侵害的先天免疫反应的一部分,不仅在病原体检测中很重要,而且在检测肿瘤细胞和垂死细胞释放的自身 DNA 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0]。放射后肿瘤细胞出现损伤,将核 DNA 释放到细胞质中,细胞质中突变 DNA 的存在导致细胞周期蛋白 GMP-AMP(cGAMP),即环状 GMP-AMP合酶(cGAS)的产物,通过 STING-NFκB 信号转导上调IFN-I基因的转录途径[11]。STING 和 I 型 IFN 激活也可以通过 ATM 和 IFI16 以不依赖 cGAS 的方式发生[12]。此外,由放疗触发的线粒体外膜透化使线粒体 DNA 能够暴露于胞质溶胶,也可以引发cGAS 驱动的I型IFN合成[13]。cGAS-STING 通路对于树突状细胞感知受辐射的癌细胞并诱导适应性免疫反应至关重要[14]。
1.3 放疗调节肿瘤微环境
放射线除了直接杀死癌细胞外,还可调节和重编程肿瘤微环境,使肿瘤微环境从免疫抑制表型重编程为免疫刺激表型。放射线增加CD8+T细胞的浸润,低剂量辐射能促进肿瘤脉管系统的正常化和 M2型巨噬细胞向 M1型 iNOS+表型的极化,iNOS+巨噬细胞诱导 Th1趋化因子的表达,这些趋化因子将 CD8+和 CD4+T细胞募集到肿瘤组织中,促进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作用[15]。放射线还会诱导邻近未受辐射的癌细胞或组织产生氧化应激和 DNA 损伤——即所谓的“辐射诱导的旁观者效应 (radiation-induced bystander effect,RIBE)”[16]。RIBE可能通过辐射的肿瘤细胞释放微粒(RT-MPs)介导,其表现出独特而广泛的抗肿瘤作用,此外,摄取 RT-MPs 的肿瘤细胞容易被活化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隔离,从而容易被免疫细胞杀伤。RT-MPs 的内化导致 TAMs 中PD-L1表达显著增强[17]。此外,放射线也有负性调节肿瘤微环境的一面,如诱导免疫抑制细胞因子的分泌,转化生长因子-β在辐射后不久就会上调,其抑制 CD8+T细胞的杀伤功能,并促进调节性T细胞(Treg)聚集,从而导致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18]。
2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临床研究进展
2.1 同步放化疗序贯免疫治疗
近年来,随着放疗介导抗肿瘤免疫原性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由于放疗后免疫抗原的暴露,可能提高免疫应答及持续时间,局部放疗后序贯免疫治疗成为研究的热点。PACIFIC研究报道了Ⅲ期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同步放化疗后行度伐利尤单抗巩固治疗获得突破性进展,放疗和免疫治疗的联合可以使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提高到40个月以上[19- 20],2020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和2021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更新的4年、5年生存数据再次证实该方案在OS及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都有明显获益[21],带来了“里程碑”式的进展。此后,一系列研究验证了该治疗模式的有效性。KEYNOTE-799研究[22]探讨pembrolizumab联合诱导化疗+放疗或同步放化疗治疗Ⅲ期不可切除NSCLC,队列A(卡铂+紫杉醇+pembrolizumab)的客观缓解率ORR为71.4%,队列B(顺铂+培美曲塞+pembrolizumab)的ORR为75.5%,队列A的中位PFS为30.6个月,队列B中位PFS未达到。队列A和队列B中分别有8.0%和6.9%的患者发生了3级以上的肺炎。AFT-16研究评估了免疫新辅助诱导+化放疗+免疫辅助治疗Ⅲ期不可切除NSCLC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3]。64名患者先接受4周期阿替利珠单抗诱导,再接受紫杉醇+卡铂的同步胸部放疗,和紫杉醇+卡铂巩固化疗,最后是1年阿替利珠单抗巩固治疗。中位PFS达23.7个月、12个月时的PFS率为66%、18个月的PFS率为57%,18个月OS率为84%,中位OS尚未达到。GEMSTONE-301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Ⅲ期研究,旨在评估舒格利单抗作为巩固治疗在同步或序贯放化疗后未发生疾病进展的、不可切除的Ⅲ期NSCLC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4]。其中33.3%的患者接受序贯放化疗,舒格利单抗组和安慰剂组的中位PFS分别为9.0个月和5.8个月,舒格利单抗显著降低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36%(HR=0.64)。基于这些研究结果,ASCO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等临床指南都将放化疗后免疫巩固作为Ⅲ期不可切除NSCLC的新标准。
2.2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激发远隔效应
远隔效应最早由R.H.Mole于1953年提出[25],近年来引起医学界的强烈关注。2012年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报告,1例晚期黑色素瘤的女性患者,在免疫治疗进展后接受胸部转移病灶的姑息性放疗,未经放疗的转移灶也出现缩小[26]。2015年Reynders[27]对23例单纯放疗诱导远隔效应的临床病例进行回顾,发现大多数发生在免疫原性较强的肿瘤,如肾癌、黑色素瘤和肝癌。随着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兴起,在增加肿瘤局控的同时,更增强全身抗肿瘤反应的效果。Theelen等[28]报道了PEMBRO-RT(2期)和MDACC(1/2期)试验的结果,试验分为单纯pembrolizumab(单免组)和放疗+pembrolizumab(放免组),在PEMBRO-RT试验中,第1剂pembrolizumab在末次放疗后不到1周内给予(放疗剂量:24 Gy/3f);而在MDACC试验中,pembrolizumab在第1次放疗时给予(50 Gy/4f或 45 Gy/15f)。148位患者被纳入汇总分析,其中76位为单免组,72位为放免联合组。单免组与放免组对比:最佳远隔病灶缓解率19.7%vs41.7%(P=0.0039),最佳远隔病灶控制率43.4%vs65.3%(P=0.0071),中位PFS:4.4个月vs9.0个月(P=0.045),中位OS:8.7个月vs19.2个月(P=0.0004)。该项研究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在转移性NSCLC患者中,有望通过选择安全区域的转移病灶进行放免联合治疗,以达到良好的全身肿瘤控制,同时避免发生放射性肺炎,为无法耐受胸部放疗的晚期肺癌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2.3 晚期肿瘤放免联合模式的探索
2022年1月《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杂志上最新报道了一项针对Ⅲ~ⅣB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的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29],1周期的“顺铂+多西他赛+durvalumab(D)+tremelimumab(T)”后再活检并筛选其中肿瘤内CD8+增加或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的患者进入后续去化疗放免治疗(radioimmunotherapy,RIT),后续行3个周期的D+T双免治疗,最后序贯8周期的D药单免治疗。共纳入80例患者(排除1例),其中23例患者为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口咽癌。诱导免疫化疗后41例患者达到pCR,31例肿瘤内CD8+免疫细胞增加。RIT队列进入满足80%的可行性预设值,1年和2年的PFS率分别为78%和72%,1年和2年的OS率分别为90%和84%。HPV(+)的口咽癌患者从RIT中获益更大,2年PFS率为94%,而HPV(-)的口咽癌和其他患者为64%。大部分3~4级副反应与化疗或放疗相关,未出现5级副反应。该研究结果提示局晚期头颈部鳞癌患者通过新辅助免疫治疗改善疗效,提升后续局部治疗疗效。
2021年5月,《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报道一项单臂、开放标签、I期的创新性试验[30],探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复发IV级胶质瘤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患者首先接受静脉注射低剂量环磷酰胺以清除调节性T细胞;24小时后依次接受颅内和全身佐剂给药:颅内免疫佐剂为poly I:C(合成双链RNA,激活先天免疫应答,刺激适应性免疫应答),注入手术腔或脑室;系统免疫佐剂由poly I:C和GM-CSF组成。在给予颅内佐剂前3针时,行颅内病灶小剂量放疗(DT:6 Gy/3f)。观察终点是疾病进展或出现无法忍受的毒性作用。共纳入30例患者,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发热(66.7%)、呕吐(33.3%)、头痛(30.0%)和乏力(23.3%)。仅有1例患者出现3级发热,未观察到4级副反应或治疗相关的死亡。30例患者中,CR 1例(3.3%),PR 5例(16.7%),SD 9例(30.0%),PD 15例(50.0%),客观缓解率为20.0%。整个队列的中位PFS为 88.0(61.0~254.0)天,中位OS为362.0(197.0~601.0)天。将患者分为有反应组和无反应组,两组患者在生存时间、T淋巴细胞亚群、CDC27突变频率、CD15、CD68表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该研究再程放疗剂量仅有6 Gy,主要是调节免疫微环境作用,激活免疫治疗疗效,为复发的IV级胶质瘤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思路。
3 放疗方式优化方向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协同作用优势,在临床上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治疗组合。放免联合策略的探索中,放疗方式有很多值得优化的地方。
3.1 放疗与免疫治疗的顺序优化
放疗与免疫同步、先放疗后免疫、先免疫后放疗,三种模式都有成功的远隔效应案例。Aboudaram等[31]报道了在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中免疫治疗同步放疗较不同步放疗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远隔效应更加明显。另一项研究显示先免疫治疗(pembrolizhumab)后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的序贯治疗模式较先SBRT后序贯免疫治疗的效果更好[32]。先放疗后免疫的治疗模式,可以使免疫治疗一定程度上克服肿瘤的放疗耐受,增强其放疗效果;先免疫后放疗的治疗模式,利用免疫治疗激发免疫微环境,还可以使肿瘤血管正常化,减轻肿瘤缺氧的状态,增加肿瘤对放疗敏感的可能性,增强肿瘤控制率。因此,三种顺序模式均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和临床证据,孰优孰劣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3.2 放免联合治疗的放疗分割方式优化
放疗分割方式对免疫激活具有重要影响。Demaria等[33]的研究结果显示,局部放疗联合CTLA-4抑制剂可抑制小鼠肿瘤模型肺转移的发生,而超分割放疗联合CTLA-4抑制剂产生了更明显的疗效。有研究显示:对比20 Gy的单次照射,多份次大分割方案(5×6 Gy或3×8 Gy)联合CTLA-4单抗产生的远隔效应更好[34]。SBRT的大分割方式能明显诱发抗原特异性T细胞和B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当联合免疫治疗时,重编程肿瘤微环境,增强免疫刺激效应,促进肿瘤抗原呈递,增加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进入肿瘤[35]。
3.3 放免联合治疗的放疗靶点、放疗部位、放疗剂量的优化
对比单一靶区的放疗,进行多靶点SBRT,联合免疫治疗能更好地控制多发转移患者的肿瘤负荷[36]。研究发现: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时,对大血管和引流淋巴结的照射会影响免疫细胞的功能和迁移[37]。至于放疗总剂量也需要考量,过高的放疗剂量也会影响免疫细胞功能和免疫系统激活。有研究显示:低剂量全身照射(low-dose total body irradiation,L-TBI)可促进多种免疫效应,包括NK细胞、巨噬细胞激活和T细胞增殖,改善免疫荒漠。对肿瘤免疫分型的研究较多,其中比较受研究者广泛认可的就是肿瘤的三大免疫分型:免疫浸润型、免疫排斥型、免疫沙漠型;免疫沙漠型肿瘤中很少有CD8+T 细胞的浸润,肿瘤免疫应答反应较差,L-TBI可促进多种免疫效应,包括NK细胞、巨噬细胞激活和T细胞增殖,改善免疫荒漠,通过小鼠实验表明,L-TBI可促进APC的成熟,同时低剂量照射后早期会出现CD28上调和CTLA-4下调[38-40]。近期的一项利用SBRT联合伊匹姆单抗(ipilizumab)治疗晚期恶性肿瘤的临床试验发现,暴露于低剂量散射线的肿瘤(由于它们接近SBRT靶向肿瘤)比远离靶向肿瘤的病灶更容易对治疗响应[41]。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免疫效果,是更好地追求远隔效应,还是起到免疫调节作用,放疗不同的分割及剂量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3.4 放疗射线性质的优化
目前,免疫放射治疗的研究大多基于光子放疗,光子放疗的缺点在于其免疫抑制机制,因非增殖性外周血淋巴细胞对放射非常敏感,在放疗期间可能会出现淋巴细胞减少,这通常与不良预后相关[42]。而更先进的放疗技术(如质子或重离子等射线照射)对免疫微环境的影响与光子照射存在差别,使用质子或更重的离子,由于射线物理性质和计量学优势,放疗过程中可以保留更多的正常组织,同时保持肿瘤的剂量适形性,这能减少循环T淋巴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的暴露,对免疫治疗具有优势[43]。质子的应用不仅可以增强放射治疗的免疫效应,而且可以减少这一负面影响[44]。临床前研究支持这一假设,体内研究正在进行中。
3.5 放疗免疫佐剂的优化
放疗具有将肿瘤转化为个体化原位疫苗的能力,其远隔效应具有免疫介导性,然而临床上这种现象的发生率很低,原因是肿瘤微环境中存在许多免疫抑制因素。免疫佐剂可促进抗原呈递、减少免疫抑制因素,两者联合可进一步增强肿瘤特异性免疫效应。免疫佐剂包括TLR9激动剂SD-101、GM-CSF、Flt3L、IFN-γ等[45]。如之前的临床试验介绍,免疫佐剂联合放疗可能起到较强的免疫调节作用[30],因此有望通过放免治疗联合免疫佐剂,增强疗效,提高肿瘤控制率。例如SHP-2是一个结构和功能相对保守但普遍表达的酪氨酸磷酸酶[46],过去的许多研究报道,SHP-2是一个可以激活RAS-ERK通路来促进肿瘤细胞存活和增殖的癌基因[47]。在髓源性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中,SHP-2会降低干扰素γ介导的转录激活蛋白1的磷酸化,从而抑制抗肿瘤的免疫原性[48]。研究发现,联用PD-1抑制剂和SHP-2抑制剂会进一步激活抗肿瘤的免疫原性并提高免疫治疗的疗效。在PD-1耐药的NSCLC模型中,在使用SBRT联合PD-1的基础上,SHP-2抑制剂的加入会显著克服免疫治疗抵抗并提高免疫治疗的响应率[49- 50]。
4 挑战与展望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带来了更多的抗肿瘤效应和临床获益,为肿瘤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发展,当前也面临诸多争议与挑战,值得未来更多的探索。
4.1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所致不良反应
多项研究的安全性分析显示,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将增加irAEs发生率。自2017年至今,ESMO、CSCO及NCCN指南相继推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毒性的管理指南,以应对临床上的irAEs,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1)irAEs与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疗效的相关性;2)预测放疗联合免疫治疗产生irAEs的生物标志物。
4.2 精准治疗与生物标志物的探索
精准、个体化治疗是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如何准确识别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最佳获益人群,寻找影响预后的生物标志物是未来探索的领域。对耐药和复发进行预测,继续精细化管理,减少治疗毒副作用可能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由于放疗改变肿瘤表型及免疫微环境,许多被广泛研究的潜在标志物(如PD-L1、TMB等)与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疗效相关性还有争议。通过细胞、分子、基因组学、影像组学的筛选和确定,对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精准人群选择是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潜在标志物包括循环肿瘤细胞、外周血循环肿瘤DNA等指标也在研究进行中。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进步也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手段。
4.3 探索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综合治疗
“综合治疗”是肿瘤治疗的特色理念,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基础上,是否有必要加入抗血管生成治疗或其他新型免疫治疗药物,这种多样化的综合治疗模式是否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及不良反应都有待未来研究的证实。
4.4 更加深入的机制研究
尽管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协同机制已积累了一定的证据,但免疫治疗耐受仍存在。如何平衡放疗对免疫系统的活化作用和抑制效应,既促进肿瘤抗原释放和T细胞活化,又避免诱导调节T细胞增殖,值得更加深入的基础研究。
4.5 国内临床研究数据的积累
大量临床试验数据来自欧美,而不同人种、不同基因差异会影响不同研究的结论。中国牵头的多中心Ⅲ期放免联合临床研究正在开展,将为我们带来更符合国内人群的研究结果。通过科学严谨的试验设计、执行与数据分析,寻找最适应国内人群的治疗模式,尽可能积累临床经验,从而为国内患者提供更贴近人群的证据支持和治疗指导。
4.6 基础与转化、临床研究的协作
基础、转化及临床各层面研究者间的协作是亟需加强发展的。由国家或区域性医疗中心组织成立多机构、多研究团队参与的免疫-放疗研究协作平台,研究者间的多组学数据管理与资源共享非常有必要。不同团队在协作组的指导下,依据各自优势背景,通力合作,及时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至临床,并通过标准化的患者信息收集,获得数据库规模性的结果反馈,建立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新型研究生态,实现科研力量的协同作用,以将基础研究发现迅速转化至临床实践中,真正使患者受益。
5 总 结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由于局部放疗亦可引起机体免疫抑制,放疗联合免疫治疗能否有效激发远隔效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放疗联合免疫的临床实践中,针对不同肿瘤类型应有个性化的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策略和思维。当前,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时机和顺序、放疗分割方式、放疗靶点、放疗部位、放疗剂量等均有待进一步优化,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处理、生物标志物预测、多样化综合模式等还需进一步探索。随着国内外更多临床与基础研究证据的更新,放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将更加规范、安全与精准,为中国患者带来更加可靠的临床指导与全新的治疗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