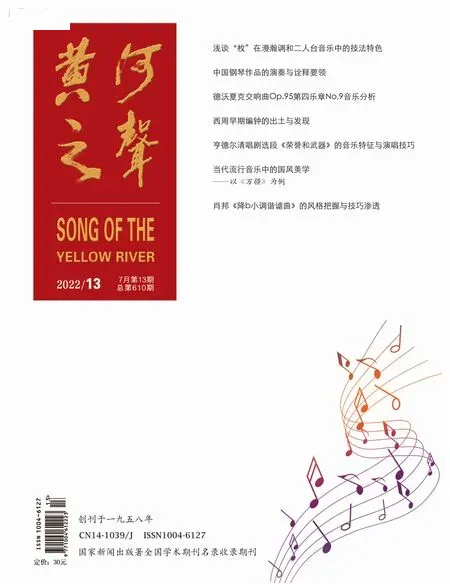戏曲题材二胡曲的戏曲化理解
宋华丽
引 言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乐器,是从戏曲伴奏乐器中孕育出来的。现代二胡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独奏乐器,有自己的曲目和成熟的训练体系。但多年的专业化发展使二胡与旧有戏曲音乐逐步分离。如今戏曲题材的二胡曲又作为二胡曲目的一个分项出现。二胡作为戏曲伴奏乐器的这份渊源本应该对这类曲目的表达有着天然的优势,但现在的演奏者主要以标准化训练体系作为基础训练,因此缺失了部分二胡演奏戏曲题材音乐时本因拥有的优势。本文主要由简述二胡戏曲曲目的发展、论述戏曲与二胡相关的各个部分的内在价值逻辑,最后总结成结论等几个部分组成。
一、二胡戏曲音乐的发展历史
二胡源于戏曲伴奏乐器“胡琴”族乐器,与中国戏曲有着广泛而深远的联系。胡琴家族遍布于全国各主要戏曲中。从剧种来看豫剧用二胡、京剧用京胡、评剧用板胡、黄梅戏用高胡。从地域来看秦腔用二胡、晋剧用二股线、花鼓用花鼓大筒、昆曲用提琴。总结起来看胡琴家族各个乐器各有特色,但都是胡琴系的拉弦膜震(板震)筒制扩音乐器。而二胡从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走上系统化专业化的乐器,说明二胡具有比胡琴家族其他乐器更强的乐器性能和可操作性。
民国时期二胡的发展主题逐步脱离戏曲音乐,作曲家们开始为二胡写作专门的器乐曲,二胡也作为主奏乐器登上舞台。二胡的演奏技巧、曲目、以及训练方式都逐渐远离原有的戏曲伴奏乐器道路。这一时期的二胡曲目大多采用中西方结合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其中就包括刘天华为二胡写作的“二胡十大名曲”。
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二胡音乐发展的主流,这也是当时的时代大趋势。当时西方文化相对发达且强势,东方文化圈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走上了取长补短学习和消化西方文化的道路。
但在建国后,受到当时党对艺术的指导意见的影响。音乐也要与人民大众相适应。而当时,群众对于音乐艺术的要求和欣赏主要集中在各种地方戏曲。这样出现了一批致力于写作戏曲和地方音乐这种曲目的音乐家。刘文金先生的《豫北叙事曲》(1958)、鲁日融先生的《秦腔主题随想曲》(1958)黄海怀先生移植的《江河水》(1962)都是这一类的优秀作品。同时戏曲原有的活力也孕育出一些很好的戏曲题材二胡曲。
到了八十年代后戏曲题材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逐步从尝试阶段走向专业化,创作了《长城随想》(1981)《乔家大院组曲爱情》(2007)《曾侯乙传奇》(2013)等作品,这一时期的由戏曲乐思写作的二胡曲在篇幅、复杂程度、结构上都有所突破。对于中国音乐的句段结构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应用,也发展了中国音乐的理论和实践。
二、戏曲音乐与二胡相关的内在逻辑
了解戏曲音乐的内在逻辑,就是了解戏曲音乐为何会呈现出现在这样的艺术形态。掌握和理解这些内在逻辑也与掌握西方形式曲目写作的美学观点有着一样的作用,可以让演奏者更好地理解曲目。
(一)胡琴伴奏音乐
戏曲中的胡琴音乐主要作用有两点:1、戏曲演唱时的伴奏,一般也是按照曲牌体的曲牌或者板腔体的板眼来框定的。这就导致几个现象,首先音乐一定是同质化的,这是需求决定的。其次长期的重复演奏一定会让乐师对于伴奏的每一个部分的句间关系,每一个音的强弱、音色在律制上的融合度都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和试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乐师的伴奏无限接近唱腔的一个完美匹配的状态。这与规范化训练的二胡演奏者不一样。规范化的演奏者在演奏曲目的时候主要靠的是:规范化训练的基本功和从专业副科学来的对曲目的处理规范以及美学理解来演奏。在有限的时间内这样的方式能让演奏者迅速掌握曲目的演奏和基本表达。
2、引子、过门、尾声:引子、过门、尾声部分胡琴通常起到的是补充没有人声时的空缺,保持音响效果的平衡。这时胡琴充当的是主奏部分,要与前后的人声形成很好的承接效果。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与前后人声一致的音色、演唱方法和处理。
(二)戏曲的人声唱腔
戏曲的核心是唱腔,唱腔的核心是音色和腔调。腔调的形成又来自几个方面。主要有1)方言对唱腔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咬字和旋律特征,比如南方很多方言比较多平声,南方的地方戏曲旋律也多为弹词一类较为平缓。而北方地区的方言多升降调,所以秦腔一类旋律中喜欢用较为夸张的颤音和大跳音,且极具个性化。2)地域环境和地域文化对腔调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戏曲风格句子中,比如甘肃的陇剧就喜欢用长腔,大句子都比较长,每个吐字也都拖长处理且喜欢夸张的演唱。但伴奏则是快速的,总结起来就是紧打慢唱。这和甘肃地方环境地广人稀,人与人之间关系真诚而热烈有关系。福建南音虽然也是慢唱拖腔,但是咬字变化缓慢,细节处理相对丰富。而且伴奏与唱腔附和也是缓慢推进。
三、二胡处理戏曲性乐曲的观点
二胡演奏者现在实际上要演奏的是一种既包含戏曲伴奏音乐又包含戏曲唱腔的综合性的现代二胡独奏曲目。使用的方法也完全基于规范化的和声曲式的分句分段处理,然后将其标准化。但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这种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处理戏曲性的曲目。对于如《曾侯乙传奇》这一类曲子在大结构和逻辑上还可以基于西方的标准曲式来分析。但对于《一枝花》这一类与戏曲紧密结合的曲子,完全西化的分析方法是失效的。
核心问题出在曲目逻辑不同。戏曲题材的曲目,大部分都是使用的戏曲唱腔和伴奏旋律作为曲目的题材。而这些材料主要都是由上文所论述的几种方式被组织起来的。而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现代作曲法所归纳的“模进、重复、倒影等”材料发展。以此为基础来看待戏曲题材曲目就要摒弃一些西式分析曲目的概念。
(一)偏音的游离性
在山西梆子腔“三度间音”的问题中,律学学者多次对不同艺术家的“三度间音”进行音准测量。发现不同艺术家的表现互相都有较大的出入,且每位艺术家在不同的地方的处理唱出的音也不同。说明了戏曲音乐甚至传统地方音乐中一大特点,特色音或者特色音程的宽窄是随着音乐的情绪和需求变动的。而大部分二胡演奏者在学习《秦腔主题随想曲》时都被告知,曲目中首调b7音是三度中立音是小三度等分音,很多学生也去寻找和练习将小三度等分音拉准确,对于标准化的训练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戏曲音乐来说这并不符合其本身的逻辑,这样演奏也无法演奏出曲目的精髓。
首调唱名下京剧中的Fa游离音也是同样的原理,在京剧中不管是演唱者还是伴奏都会使用较为偏高的Fa音。但这个音本身的偏高缘由比较复杂,但与燕乐调的清角有关。在各地戏曲中,用民族七声调式的偏音音高游离来达到丰富音乐感受的例子有很多,京剧作为一个融合多个地方戏的戏剧有这样的使用方法也容易理解。在《长城随想》中也要使用同样的思路来考虑,不应该将Fa看作调内的四级音,而应该看作是中国七声调式的偏音,也不要以某一版的京剧唱的偏高的Fa作为样本,而应该以感受京剧中名家对偏音的处理特质作为切入点来处理曲子。同样我们还会在曲目中遇到#F音,比如《追梦精华》的第四章中的慢板部分。曲目中有多处使用了#F到E音的滑音。这种滑音有个重要的目的是增大滑音的滑动距离,带来北京地区音乐风格的听觉感受。
(二)滑音和揉弦
在戏曲风格的二胡曲子中滑音与揉弦是模仿唱腔最好的两种手段。在二胡曲目《一枝花》中大幅度的压揉、鲁揉、回滑音、垫指滑音、大滑音都是作为模仿润腔的手段使用的。如果将鲁揉幅度要多大,大滑音要滑到哪个度数、压揉的频率是多少,这一类的问题用标准化的训练方式来解决的话,和戏曲滑音的实际效果要求则逻辑不符。其中大滑音主要是模仿甩腔这种手法,甩腔的运用主要是为了增加戏剧性效果,通过突然的大幅度音高变化加上突然提高音量来实现。其音乐表达的核心与要滑多少度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而应该学习其突然提高音量和变化音高带来的音响效果。
而《一枝花》引子的第一句使用的压揉揉弦与下滑音则是模仿梆子戏中的哭腔。重点也不是揉弦频率或者下滑音要滑多久,而是哭腔本身的艺术特点。所以在演奏时更多的是要感受和模仿戏曲的感受,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
(三)句和段
戏曲音乐有着自己的分句分段逻辑,戏曲类曲目虽然也能用标准化训练的曲式分析划出小句子和段落,但这是音乐的共通性,其内部的逻辑结构却不能仅仅用西式的曲式分析来解释。比如《一枝花》中53-77小节的快板。如果用西方曲式来分析就会变成前四句是一个方整的乐段,后面又多出一句。而从戏曲的自由逻辑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赶五句。而且赶五句本身有自己的律动逻辑。其重点落在第五句的赶句要强调处理,如果按照一般曲式来分析,最后这句就好像是多余的一样。
戏曲题材中,分句也有一些自己的逻辑。比如在金蛇狂舞中的主题。如果按照传统的分段分句是无法分割的,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倒宝塔形的段落样式。这段主题记写在2/4的拍号下。前三段每两小节是一句;这两个句子的时值时是4+4拍;占四个小节长度。第三段则缩减为3+3拍的两句,共占三个小节。第四段的时候已经缩短为2+2拍的两个小句子了,长度占两个小节。第五段与第四段完全一样,但在演奏时此处的速度在加快所以实际上的听觉长度也在继续缩短。每次重复动机时句子就会被缩短。形成一个倒着的宝塔形的曲式结构。这种方式在《秦腔主题变奏曲》中也有应用,在曲目中很多细碎的句子不能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就像不能把这里的最后四小节看作一个整体一样,就算是一个小节甚至一个音,该分句的还是要分句。
(四)戏曲节奏
在现代戏曲音乐中,对节拍形式的称呼通常叫做板式,这与西方音乐逻辑中的拍号的概念类似,但在实际运用中则有一些出入。在戏曲中板式一般与句子之间有着比西方拍号逻辑更强的关联。通常一个循环的板式内就有一个完整的句子构成,虽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在音乐的处理上则要比西方逻辑中拍号律动的强弱处理起来更加的激烈。而且戏曲中的板式有着相对固定的环节:比如西皮中的二六板式,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慢二六—流水板—快板。如果用拍号的概念表示则是(2/4)-(1/4)-(1/8)。我们不仅要在音乐处理时处理板式内部的结构,同时也要注意三个部分之间的强弱和速度关系。这里可以看出第三个部分的快板全是重音,是全曲最激烈的部分。而中间的流水版虽然看上去是(1/4)拍,但流水版更加接近无重音的概念,而不是全是重音的概念。
另一个重要的戏曲节奏概念则是散板。中国音乐对散板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戏曲音乐也不例外。而且不同于古琴音乐等其他音乐的散板,戏曲音乐的散板有自己独有的特征。戏曲的散板一般不是指无规律的自由发挥,而是一种有规律的渐快,渐慢的形式。这种有规律可循的散板需要的不是演奏者自行感悟之后规划的节奏和气口,而是遵循戏曲音乐的演唱逻辑而进行的。在进行演奏之前演奏者应该了解其运用了什么戏曲音乐元素,然后使用对应的处理方法。
结 语
二胡演奏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程度,对于不同的曲目有细分的思路和处理方式,这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精确到戏曲题材的二胡乐曲,我们也要再细分。如果曲目里使用了西方曲式结构,也使用了戏曲题材元素的,要分别按照西方曲式分析大框架,按照戏曲音乐分析旋律特征和演奏手法。如果是完全中国戏曲式的曲目则应该按照中国传统曲式的逻辑从大结构到小结构依次分析,最后按照戏曲的旋律特征来确定演奏手法。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感受到“胡琴”长期作为戏曲伴奏乐器所优化出来的很多特点。这些特点在演奏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中最难做的并不是分析或者学习中国戏曲式逻辑,而是无法转变标准训练所带来的惯性思维模式。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思维的转变而不是抛弃。比如说音准,京剧中的Fa音确实可以向上漂移,但这不代表没有标准可以随意乱拉。只是在这里音准的要求变了,从要求演奏确定的稳定的音高,变成了要求演奏确定的稳定的感受。感受不能度量所以不是一个准确的标准,但美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要达到的就是在求变中找到一个确定的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