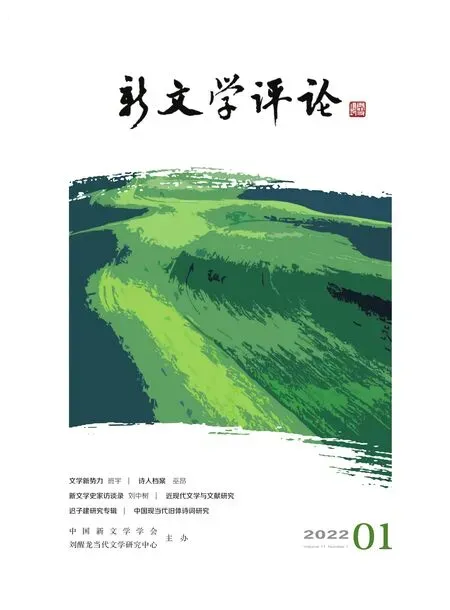在虚构与历史之间的“文心”
——王尧小说《民谣》论
□ 房 伟
2020年末,著名批评家王尧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民谣》,成了一个令文坛瞩目的事件。近些年来,批评家从事小说创作,已逐渐增多。然而,王尧的小说的创作,依然引发了众多期待。这种期待有几个层面,一是王尧给当代小说界带来什么?二是王尧的批评实践,对他的小说创作有何影响?三是王尧的小说创作,和其他批评家小说有何不同?这也许是我们解读《民谣》独特价值的重要思路。
一
有的学者说,批评家小说是一个无效命题,小说必须回到小说本身。王尧也反对“批评家小说”的提法。这样的判断,有其合理性。小说创作,有自身的艺术规律,不等同于批评,而感性和审美能力,对于一个批评家,也同样重要。王尧同时也承认:“批评家的身份,让我在语言、形式、结构上有了更自觉的意识,让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在意故事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含量。”①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小说艺术高度发展,其文体意识的内涵和类型外延,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学者小说,批评家小说,虽然数量不大,但也有着相当的文学辨识度和文体特征,即鲜明的哲学意味和较强的知识性,注重小说文体和语言的探索。《民谣》发表之前,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王尧发出倡议,倡导新“小说革命”。他表达出对当下小说创作的不满:90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历史表明,“写什么”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怎么写”没有真正由形式成为内容。这样的蜕变与小说家和现实、历史之间失去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有关——个人主义话语被庸俗化后,暗渡为单薄自伤的“我自己”的故事,广袤的世界被缩减成为极逼仄的“一隅”。我不是以崇高和宏大叙事的名义质疑其他写作的合法性,而是担心久而久之丧失了“我与世界”的连接能力②。理解这个发言,有助于理解“批评家王尧”与“小说家王尧”之间的隐秘联系与不同面向。
《民谣》发表之前,王尧的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都在文学界有着重要影响。他的当代文学批评,缜密睿智,又有着敏锐的洞见,同时他又以“文革”研究著称,继而在当代文学史、散文史等领域建树颇丰。他提出“扩大的解放区”“文学史关联性”“过渡状态”“无作者写作”等概念,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他还积极参与21世纪以来“重返80年代”等一系列学术热点的研究。理解王尧学术思想的核心关键词在于“关联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难题在于,各种意识形态观念左右着文学史写作,断裂不仅是摆脱影响焦虑的艺术创新冲动,也体现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干预性,以至于“重写文学史”“回到纯文学”等提法,也不可避免地被意识形态化,难以形成权威经典体系,加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矛盾重重”(王尧语)的复杂性,也使得“历史化”还是“在场化”问题,长期困扰学科建设。王尧的“关联性”灵感,让他摆脱“左/右”“启蒙/革命”等诸多意识困扰,建立了一种兼具复杂性与概括性,历史化与批评化的综合态模式。他提出的“过渡状态”“关联性”等概念,有效地对当代文学史不同审美意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进行描述,且能在“历史的反复”等不同文学史发展逻辑层面,解读种种思潮和运动的生成结构,重新考量诸多作家和作品的价值。这种思维模式也能有效避免文学史解构产生的对文学史本身的消解。比如,新时期文学之后,我们通过重建五四想象,重建了现代文学标准,并试图以此改造当代文学经典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关联性,在新时期文学之后消失了,它依然在主旋律文艺等概念有着诸多发展和变异。无视这种“关联性”,就无法建立起科学客观的文学史描述。“关联性”思维,让王尧的学术研究有了新思路,也使他有着一般批评家没有的,强烈的历史建构意识与现实介入感。他对“新小说”的呼唤,无疑也是看到目前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弊病,即历史感的消失。
同时,王尧和同时代批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虽有丰厚的理论修养、史料功夫和阐释能力,理性的学术岗位意识,但又是一个始终强调“文心”的批评家。他对批评家的限度有着清醒认识。他愿意在批评家语言不能及物之处,用另一套笔墨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正如萨义德承认:“用某一理论来认识、解释历史情境可能会有效,但是这种理论不可能‘涵盖、阻隔、预言’本质上杂乱无章、无法驾驭的多元历史情境。批评家既要明白理论不可避免,同时务必意识到它的局限,也得学会抵制理论,向着历史现实、向着人类需要和利益开放。”③他在《收获》和《钟山》开设《沧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两个散文专栏,前者写“陪都”重庆的文化人,后者写西南联大教授,都表现出知识分子对历史的介入性。通过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描述,他也写出了学术研究没有表达,或者说,没有得到淋漓尽致表达的情感和思考。这里有传统文人人格修养的继承,也有对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品质”的反思。这一点而言,王尧的小说《民谣》,也不同于很多当下的批评家小说。他不是借助批评语言的越界,制造一种“批评化的小说”(如吴亮的《朝霞》),而是试图在广义的中国文学传统中寻找精神滋养和书写方式。他对中国古代文章学颇为青睐,除了严谨的学术论文,他愿在广义的文章范畴之内,表现创作者的观念、经验、志趣、人格和信仰。虽然王尧从散文创作转向小说创作,但由散文生出的“文章之心”,依然是他创作的重要支点。他曾在访谈中说:“我一直心仪中国的文章传统,也主张恢复和传承文章传统——我们现在缺少这种能力,这也是很多优秀小说家但没有好语言讲故事的原因之一。”④
二
对于“文心”的强调,最终让王尧走到创作前台,写下了精彩纷呈的《民谣》。表面上看,该小说四个正篇部分,以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与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交叉,以个人化视角形成对1970年代江南大队的追忆与重构。这期间交织着王家与胡家的兴衰,革命历史与地方记忆的交融,个人情感与时代的碰撞,残酷的历史记忆与温暖的地方伦理书写。这种以家族故事与个人叙事结合的先锋表述,似乎没有超出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叙事经验。然而,仔细阅读后,我们发现,那又是“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王尧注重文体修养,他的文学语言,呈现出淡雅节制的散文化风格,小说创作的内在结构,人物构造,也都呈现出自然行文的松弛状态。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在《民谣》中表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学观,都有着很强的“文章学”痕迹——既能杂取日记、书信、文件等各种文体熔铸为小说(《民谣》正篇与杂篇外篇的结合方式,隐见着中国子部的文学传统)而不显文体混乱,又表现出对“自我与世界联系性”的思考。这里包含着个人的记忆、经验和情感,也隐含着拒绝戏剧化的历史理性态度。如海登·怀特所言:“历史就是将某一个事件置于一个语境之中,并将其与某一可能的整体联系起来。”⑤所有人与事的纠葛,生离死别,斗争与合作,都表现出历史的存在语境。它们处于独立之中,更有着彼此之间的隐秘联系。也正是因此,《民谣》的故事不是因果情节式的,而是网状的,以人物和事件为节点,以彼此之间的联系为经纬,共同呈现出1970年代特殊历史时期的风貌。而《民谣》又不是完全空间化的小说,几条故事线索,比如胡鹤义的子孙、独膀的秘密、村庄的权力变迁,都潜聚在水底,时隐时见,牵引着阅读兴趣。阅读之后,有一股氤氲的水汽,神秘而忧郁,弥漫在文本之间,有散文的韵味悠长味道,又能表现小说的深刻主题性。
言至于此,必须谈谈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历史叙事,经历了不断解构的过程,先是从革命叙事之中剥离,继而不断从民族国家叙事、启蒙叙事之中剥离,从《红高粱》《灵旗》到周梅森的《大捷》,再到先锋小说家苏童《我的帝王生涯》的抽象暴力史景观;从余华的具有日常与民间意味的《活着》,发展到李锐既反思启蒙又反思革命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莫言的民间史狂欢的《丰乳肥臀》,韩少功以民间词典形式解构大历史的《马桥词典》;从刘震云充满权力黑色幽默的《故乡天下黄花》,张洁充满强烈女性主义精神的《无字》,迟子建以自然书写介入历史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到阿来的少数民族史诗《尘埃落定》,李洱的哲学气质反思历史的《花腔》。我们还有以家族秘史解构中国现代史的《白鹿原》,阎连科充满强烈反讽解构气质的《坚硬如水》《四书》等优秀作品,都在表现对抗大历史的解构思维。而以文学对抗历史,似乎成了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家的惯性思路。比如, 米兰·昆德拉就认为:“一种艺术的历史的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⑥
然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中国小说界历史叙事的突破,明显感觉乏力,更令人忧虑的是,伴随着历史叙事退潮,历史意识的空洞化,带来了现实感的淡化,也就是王尧说的“我与世界的联系性的退化”。人无法在文学中想象自我与过去的关系,也就无法完整地理解现实的存在状态,进而做出有效的主体建构。搁置网络文学形态不谈,当下中短篇小说创作,轻小说化,琐碎化,粗鄙化,伴随着中产趣味化等问题,使得作家满足于趣味故事的精巧讲述。一种封闭的内在性挖掘,正让小说丧失严肃探讨社会现实的能力。长篇小说也不容乐观,小说越来越厚,故事越来越晦涩,人物越来越抽象,除了可怜的史诗雄心,只能看到单薄的故事和符号化人物,以及思想贫乏导致的历史与现实的焦虑。新时期发轫,经过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事,其启蒙化隐喻批判结构与解构性冲动,没有导致有效的历史影响力,反而日益走入语言实验怪圈和虚无的历史意识解体。
由此,当下文学的历史意识问题,不是批判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批判,不是个人私历史对抗大历史,而是历史意识消逝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交互性空前增强,地域性和历时性,都变得越来越具有平面化共时性,进而消除了历史的时间魅惑性与空间的陌生诗化。我在海南岛,可以通过互联网,观看格陵兰雪景,听B站的朋友介绍其历史,并在游戏和美剧中体验维京海盗入侵英伦三岛的历史故事。而历史本身的残酷性和当时蕴含的结构性感情和意识形态对抗性,则可能被消费时代沦为符号狂欢与冒犯的经济量。历史蕴含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性,则可能成为快速流动的现实所拒绝的深度表达。这种巨大的断裂,成为当下文学历史叙事的巨大危机。当下最火爆的历史叙事,并不是来自纯文学界,而是网络历史穿越文学。而这个历史文学的亚类型,最大的特点,即在于对历史的虚拟性。这解放了文字的想象力,也更彰显了历史意识的合法性危机。
三
因而,重建自我和历史的联系,首先就是要有一种相对个人化的,又摆脱了意识形态规定性的文字态度。这就要求将个人记忆与情感打开,冷静地应对大历史。这里的小说结构,就不再是抵抗与压制的结构,而是游走在断裂与非断裂之间的结构模态。90年代以来小说的历史意识,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以个人性形成与大历史的对抗关系,借以隐喻意识形态对抗性,以此建立人性叙事内在规定性。例如,阎连科认为,《民谣》的价值在于,真正拥有个人立场、个人视野和个人方法去面对历史与大事件,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道德与才华。甚至可以说,最个人的记忆史和历史观,才是最有效的文学观⑦。然而,《民谣》也许不是一篇彰显个人历史叙事的私化历史小说。王尧凸显的,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历史与大历史的“联系性”。正如王尧所说:“我不是写‘我’的历史,是写‘我’在历史之中。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⑧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王尧的苦心孤诣所在。个人面对历史的疼痛与恐惧,激情与欢欣,不再是崇圣心态,或解构心态,而是既看到大历史对个人的压迫,也看到大历史与个人的联系。第一人称个人化回忆视角,让个人情感记忆与历史产生了感性的关联,而亲历者的体验性视角,则在当下的角度,让个人的理性思维具有了历史的审美距离,批评家的隐含作者身份,则对前二者又形成了观察与评述。
悖谬的是,尽管有“重建自我与历史的联系性”的雄心,这篇以1970年代江南大队为基本时空的历史小说,又有着巨大的文本分裂,即四个部分正篇与外篇和杂篇的分裂。王尧解释说:“我想呈现曾经的分裂的语言生活。卷一至卷四的叙述和‘杂篇’的注释是我今天的文字表达方式,‘杂篇’和‘外篇’则残存了另一种语言的状态。我尝试写作杂篇和外篇,既想还原我们曾经的语言生活,也想探究我们思想的来源。”⑨他谈到了60年代人的人生体验的分裂,进而谈到江南大队的语言演变史,“风”与“雅”的传统与“颂”的意识形态语言的分裂。我想,也许正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断裂、碰撞、耗散和不断的反复,才造成中国当代作家历史表达上的“巨大焦虑”。王尧执着而清醒地对“关联性”的寻找,也就变成了对于历史整体性的意义塑造与主体建构。由正篇和外篇、杂篇形成的小说文本之中,我们看到了对分裂的历史记忆书写的“颠倒”:正篇主要写王厚平十四岁到青春期经历的“文革”中后期的个人化历史记忆,用的是节制干净的第一人称叙述语体;杂篇与外篇的零余部分,以第三人称客观视角出现,却是时代占据主流形态的语言,又与注释部分的第一人称叙事,形成了相互印证或解构的关系。
然而,这种颠倒不仅有批判意味,也有着“联系性”。这种“联系性”表现在艺术形式上,首先是每个部分的文本内部,应对个人与历史的方式。正篇之中,个人化视角穿起诸多人物和事件,却在凝视与回顾之中,将理性反思寄托于浓浓的人情。少年王厚平的记忆,串起从时堰镇到江南大队的历史变迁、地理沿革、资产变化。革命斗争、土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不是淡化成背景,而是成了一个接一个纷繁复杂的人物出场的节点,这些人物穿梭在历史中,通过厚平的视角,不断演出着悲欢离合。这里有婚丧嫁娶、风土人情、快乐的农村戏剧节,也有生死离别和残酷的斗争,比如,收听敌台被抓的张老师,为了证明清白割伤生殖器的余明。小说开头那一幕,更具有隐喻性:“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码头离不开水,也离不开岸,这是一个水与陆地的分界线,也赋予了叙事者“少年大头”独特观察视角。“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的比喻,既有化虚为实的灵妙,也通过隐喻表达时代记忆分裂的痛楚。正篇之中,在声音和气味的回忆里,独膀子、外公和王二大队长等前辈的革命往事,成为1970年代前史,却暗自镶嵌在时代背景之中。而勇子哥放弃前途与爱人结合,钻井队和村庄的人事纠葛,少年厚平的几段深深浅浅的恋爱,这些个人体验,在大时代之中,又在大时代之外。这些过去的记忆,又和第一人称“我”的当下体验(如对莫斯科先贤公墓的拜访),形成某种“关联性”互文。正篇部分也未回避大历史的残忍,它为我们铺陈出一个个令人惊悚的死亡,比如,王二大队长被还乡团杀死,大少奶奶悬梁自尽,房老头吊死桥头,三小吐血而亡,网小出车祸。小说还写到李先生的死,曾祖父的死,外婆的死,四爹的死,胡鹤义的死等等。但是,无论隐含作者,还是叙事者,都在非常节制冷静的笔调中,将死亡和痛苦展现出来。最终,死亡和痛苦,没有形成阎连科式狂欢奇观,反而变成历史星空中大大小小,闪着光亮的星。它们一个个地亮起或熄灭,共同联结出对于历史的反思。文本中还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充满悬疑的历史黑洞,比如,到底谁放走了胡家少爷?到底是谁出卖了王二大队长,是独膀子,还是胡鹤义?这些记忆与语言的“黑洞”,镶嵌在历史的星空,带着谜一般的诱惑,指引我们去思考。
四
相对于正篇对个人记忆的彰显(吊诡的是,正篇个人记忆的呈现话语,并非历史语境实有,乃是当下回忆话语重构的结果。而这种重构,今天也未必具有完全合法性,这又形成历史与个人的新分裂),外篇和杂篇则更多展现历史时代主流话语文本中的个人状态,在诸多历史文本的仿真中,形成返场般“穿越效应”。之所以说是仿真,一是这不是真实历史档案;二是在作者对于历史文本的模仿中,又有着无限逼近的真实感;三是这种无限逼近的真实感,又形成对当下的某种质询,即当下语境中,历史真实感和深度感的消失。文学的作用,不在于意识形态的某种建构,而是通过个人情感结构和思想结构的唤起,形成新的审美陌生化效果。那些曾活生生地,镶嵌在我们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我们遗忘。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无论伦理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它们还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着潜在影响,巨大的断裂和遗忘,无疑也令人担忧。因为它会让我们丧失历史的时间存在感,进而丧失现实反思能力和未来的探索能力。
在这里,正篇的讲述,形成了与外篇和杂篇的互文性,外篇和杂篇对历史的抚摸和介入,也成为重建历史联系的某种强有力的凝视。所有悲伤与愤怒,沮丧与疼痛,都像曾经的欢乐与理想的激情,有了理解的宽容和再次出发的勇气。被打捞的历史能指被再次擦亮,却因为所指本身的断裂和消失,反而更暴露了虚构行为本身的意义,即文化实践的延续。这些能指符号,有些已彻底消失,如“批林批孔”、学黄帅批师道尊严、小靳庄典型;有些还活跃在主流语言中,但王尧通过将它们盛行于民间的历史语境的重新回溯,无疑也让我们看到这些符号能指在当下晦暗不明的状态。江南大队图书馆建立的报告,入团申请书,毕业留言,这些或官方或个人的文本,都带有浓浓的时代气息。对儿时作文的仿写,烈士墓前对王二大队长的怀念,又和注释部分王二大队长牺牲事件,形成了补充,甚至是冲突。表姐的来信,许玲和王厚平的约会通信,也有着长长注释,进一步对正篇中个人的情感体验,进行解释和补充。对于王厚平在校政治表现的介绍信,仿写的揭发信,既让我们看到时代政治对个人的粗暴介入,也勾连起当下语境中尚未完全消失的政治文体的晦暗体验。杨网小控诉未婚夫变心的信件中,我们看到“文革”末期,伴随高考恢复导致的剧烈社会变动,通过对历史细节的仿真,我们重新回望这种社会变动对个人的影响。又比如,对检讨书的仿写,我们看到了70年代末期,个人以应对“文革”运动的方式,应对计划生育国策。外篇对杨老师未完成的小说文本《向着太阳》的仿写,不是一个简单的后现代“戏仿”,而更近乎充满历史同情的“重返”。“未完成状态”是历史焦虑的隐喻。无论对错或贤愚,历史与个人的紧密关系,在历史感消失的今天,却诡异地成为某种陌生又熟悉的体验。杂篇第十二小节,更具有隐喻意义的,是四首对民谣儿歌的仿写。中国古代社会,有以童谣为“风”,甚至为谶纬,传递民间疾苦和怨恨的做法,如“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为诅咒董卓而作。中国近现代历史,随着现代性的渗透,民谣也变异为意识形态文体,“风”只能以残存的状态,被结合进“颂”文体,如第四首“催眠歌”。然而,在当下历史语境之中,这些民谣也已变成“记忆的化石”,展现出几代人艰难的“自我的确立”过程中的分裂与痛楚,彷徨与沮丧。如何在当下语境之中,通过记忆的呼唤与质询,形成个人与历史有效的联系性,进而更好建立真正的历史理性主体,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个人成为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个体,让历史更富于情感、宽容和理性。王尧的这些意图,令人动容。
五
“历史的光影,破碎地散在了他们身上,他们本身是微小的存在,而不是我把他们碎片化了。”⑩阅读《民谣》,在重返历史现场时,让我们看到了种种微观历史细部,这些重返之中,虚构的想象热情与非虚构的真实逼近,同样激活着我们的阅读欲望。读这部小说,仿佛让我找到阅读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的感觉。《民谣》既是时堰村庄史、江南大队大队史,更是革命时期生活史与心灵史,包含着很多微观记忆,比如,个人文学阅读史与写作史,个人成长史,村民恋爱史,阶级斗争史,村民死亡史,村庄财富史,村庄婚丧嫁娶的民俗史。《民谣》不是一部个人主义碎片化之作,相反,却是一部将记忆的彩陶碎片重新凝结成大历史的诚心之作。它既是一部写给同时代人的记忆唤起之书,让他们在断裂、批判与遗忘之后,有了重新检视的可能,也是一部写给当下青年的未来之书。王尧将历史的结构纹理,再次呈现在了当下语境之中。《民谣》也呈现出现代性意义的历史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当大历史笼罩一切,文学的抵抗性拯救人性;当历史意识颓败,文学的审美则拯救历史,进而为人性重塑历史精神。
由此,我们也可说,《民谣》是一部在当下历史意识颓败之际,重新呼唤历史建构精神的诚心之作。有学者指出:“如何在尊重个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在漂移的甚至碎片化的现实中,重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有效关联,并为这一关联寻找有效的文学表述,是现时代文学所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和难题。”《民谣》是在延续至今的新历史主义解构思潮之外,当代小说界的重要收获之一。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言,一切历史书写,都在于历史与现实的永恒的,不间断的对话之中。《民谣》以先锋的感觉结构,结合节制典雅的语言,既有历史的虚构,又蕴含着更深层次的非虚构努力。虚构历史的想象,来自真实性的诱惑,也来自对“历史终结”的反思。而非虚构的努力,则蕴含着重建真实感,重建历史与现实联系的热情。这种双向的努力,不仅是“批评家王尧”的学术理想寄托所在,也表现了“小说家王尧”的文学雄心和境界。当然,这可能还有一层意义,即历史呈现出悲剧性的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理解,以及毛茸茸的历史复杂性,而对复杂性的呈现,不仅是颠覆和解构,也蕴含着建构的热情与野心,包含着同情与思考。《民谣》对中国当代小说历史意识的突破,值得文学界去研究。
注释:
①白雁、王尧:《王尧访谈:我不能把大历史强加给他们》,《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20年12月28日。
②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020年9月25日。
③陆建德:《世界 文本 批评家.序言》,爱德华·W.赛义德,李自修译:《世界 文本 批评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13页。
④王尧、牛煜:《未尽的问题与方法——王尧访谈录》,《当代文坛》2020年9期。
⑤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186页。
⑥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112页。
⑦阎连科:《重筑小说的根基——我读〈民谣〉》,《扬子江评论》2021年1期。
⑧王尧:《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扬子江评论》2021年1期。
⑨王尧:《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扬子江评论》2021年1期。
⑩白雁:《王尧访谈:我不能把大历史强加给他们》,《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20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