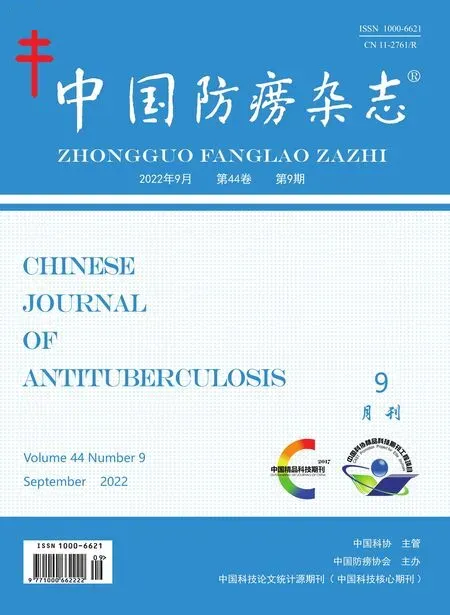抗结核药物贝达喹啉的耐药情况及其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姚蓉 陆宇
2020年,全球共报告耐药结核病患者157 903 例,其中包括132 222例耐多药结核病(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MDR-TB)/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ifampicin-resistant tuberculosis,RR-TB)患者,25 681例前广泛耐药结核病(pre-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pre-XDR-TB)和广泛耐药结核病(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XDR-TB)[1]。耐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治愈率低、病死率高、不良反应明显,价格昂贵。Bdq是一种新型口服二芳基喹啉类药物,通过影响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合成酶质子泵的活性,导致ATP合成受阻,从而阻止MTB中ATP的能量供应,发挥杀菌作用[2-4]。
2012年12月,Bdq成为首个获批用于治疗成人MDR-TB的新药[5], 在背景方案中纳入Bdq已被证明可以显著改善治疗结局并降低MDR-TB患者的死亡率[6-7]。截至2020年底,已有109个国家使用Bdq作为耐药结核病治疗的一部分[8]。然而,Bdq作为一种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抗结核药物,仍无法避免耐药性的出现和发展[9]。因此,有必要采取恰当的表型药物敏感性试验(phenotypic drug sensitivity test,pDST)和耐药性监测,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产生耐药性的风险,并最大程度地提高治疗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对Bdq耐药情况、可能机制、检测手段以及与临床的相关性进行综述,以提高临床对Bdq的认识,并为合理应用该药提供理论依据。
Bdq耐药现状
一、 原发性耐药情况
原发性耐药是从未接受抗结核治疗的患者对某种或某些抗结核药物发生耐药。一项基于人群的回顾性研究探索了中国台湾地区2008—2019年中从未使用过Bdq的898例MDR/RR-TB患者中的初始MTB分离株对Bdq的耐药情况。采用琼脂稀释法(agar dilution,AD)进行Bdq的药物敏感性试验(DST),发现其耐药性断点≥0.25 μg/ml,故中国台湾地区的Bdq耐药率为3.1%(28/898)[10]。在这28例患者中,RR-TB、MDR-TB、pre-XDR-TB和XDR-TB患者含Bdq耐药分别占2.5%(5/202)、3.3%(20/608)、4.1%(3/74)和0.0%(0/14)[10]。2015年中国11个省份的回顾性研究纳入了1603 株既往未接触过新型抗结核药物的菌株[11],1407株(87.8%)来自新发患者,196株(12.2%)来自复治患者。检测到6 株(0.4%,6/1407)菌株对Bdq耐药,提示对Bdq有耐药性的菌株可能存在密集的社区传播。与2007年中国第一次全国耐药性监测结果一致[12],在102株MDR-TB菌株中,只有1株(1.0%)对Bdq耐药,这也是唯一对氯法齐明(Cfz)耐药的菌株[11]。中国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277例接受Bdq治疗的患者,2.2%(6/277)MDR-TB分离株发现初始Bdq耐药,其中包括5株MDR-TB分离株和1株XDR-TB 分离株[13],其基线Bdq耐药率与南非报告的数据(2.3%)相似[14],但高于法国(1.0%)[15]和俄罗斯(1.3%)[16]。因此,不同地理区域的初始Bdq耐药性可能不同。
一项为期5年(2015—2019年)涵盖11个国家的耐药性监测研究评估了5036株MDR-TB分离株的Bdq初治患者对Bdq和其他抗结核药物的敏感性[17]。7H9微量肉汤稀释法(broth microdilution,BMD)显示Bdq的耐药率为0.6%,而7H10/7H11琼脂稀释法(agar dilution,AD)提示Bdq的耐药率为0.4%。在MDR-TB人群中,Bdq和Cfz之间的表型交叉耐药率为0.4%,在pre-XDR-TB/XDR-TB人群中为1%。MDR-TB患者对Bdq和利奈唑胺(linezolid,Lzd)共同耐药率为0.1%,pre-XDR-TB/XDR-TB患者为0.2%。在未接受过Bdq治疗的人群中,Bdq的耐药率较低。
二、获得性耐药情况
获得性耐药是指抗结核治疗达到或超过1个月的患者发生的耐药。Mallick等[18]检索识别出866篇论文,最终纳入13项研究。其中,11项为队列研究(5项前瞻性研究,6项回顾性研究),2项为随机对照试验。表型和基因型获得性Bdq耐药(acquired bedaquiline resistance,ABR)的中位频率分别为2.2%和4.4%。这与Kunkel等[19]的模型估计结果一致。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的耐药相关变异(resistance-associated variants,RAVs)都会产生耐药性[20],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表型和基因型ABR频率的差异。在巴基斯坦队列中,仅包括接受Bdq治疗后培养转阴延迟的患者,而其他队列包括所有最初培养阳性的患者,以及在Bdq治疗期间早期培养转阴的患者。这可能是 27.6%(表型)和 36.7%(基因型)的 ABR 频率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21]。此外,Mokrousov等[22]检测到基因型ABR频率显著升高至50%。据估计,在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患者中,获得性耐药约占MDR-TB新发患者的38.7%[23],这些个体在复发时发生复杂耐药模式的风险可能更高。由于Bdq的半衰期较长,失访受试者发生ABR的风险特别高。因此,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对预防获得性耐药至关重要。
三、Bdq与Cfz交叉耐药
Bdq 和 Cfz之间的交叉耐药性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24]。一些研究报告了对Bdq或Cfz表型耐药且已知耐药基因中没有可识别突变的分离株或体外进化菌株的比例[25]。有研究者鉴定出24株临床MTB分离株中的2株,治疗后Bdq的MIC增加了2倍,未鉴定出mmpR、atpE、pepQ或Rv1979c基因突变[26]。也有研究者鉴定了5株分离株中的1株,其对Bdq和Cfz的MIC增加2倍,而未检测到atpE、mmpR或pepQ基因突变[27]。
Ismail等[14]发现Bdq和Cfz的MIC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当存在Rv0678 RAV时,相关性更强。这表明它们可能具有共同的生化途径进而发生交叉耐药。在Cfz耐药分离株中,30%(9/30)对Bdq耐药,而在Bdq耐药分离株中,9株(100%)均对Cfz耐药,大多数(8/9)携带Rv0678 RAV。因此,Bdq耐药性可能对Cfz产生完全交叉耐药性,而在Cfz耐药性患者中,1/3将产生交叉耐药性。RAVs的发生率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所以,持续耐药性监测十分重要。
Bdq耐药基因突变类型
一、atpE基因突变
atpE基因编码Bdq的靶点(ATP合成酶亚基C)的第81位氨基酸。Ghodousi等[28]报告了从肺结核患者中分离的pre-XDR-TB菌株在18个月含Bdq方案治疗期间的微进化。治疗3个月内,与高水平Bdq耐药相关的atpE_Ala63Pro突变一过性出现,提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耐药性扩增的风险。然而,其在含Bdq方案治疗9个月后完全消失,这可能与这种突变体的适应性成本增加有关。因此,在MDR-TB 高负担国家,发展最低抑菌浓度(MIC)检测、pDST和全基因组测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WGS)至关重要。
Bdq耐药相关位点的遗传多样性研究显示[29],在atpE基因中发现25个新突变,大部分(15/25)是非同义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其中9个通过SUSPECT-Bdq预测软件赋予其耐药性。在这些突变中,只有I66V突变存在于参与Bdq-atpE相互作用的残基中;E44D存在于北京分离株(谱系2.2.1)中,它可能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多态性,导致该菌株对Bdq的固有MIC升高[29]。
大多数atpE基因突变发生于体外分离株。然而,atpE D28N、E61E、A63V和I66V各发生1株Bdq临床耐药分离株。atpE基因突变可引起MIC增加的范围从8~133倍不等[25]。
二、mmpR(Rv0678)基因突变
mmpR编码一个由165个氨基酸组成的非必需转录抑制因子,该抑制因子通过mmpS5-mmpL5泵影响Bdq的外排。Omar等[30]提到mmpR基因的非靶向突变越来越多地与Bdq耐药性相关。2015—2019年,共有7%的分离株被鉴定出对Bdq耐药。对大多数分离株(130/199)进行WGS分析,发现所有分离株均携带Rv0678突变,未发现atpE基因突变。对其余的分离株(69/199)进行了Sanger测序以鉴定Rv0678基因突变,发现所有分离株均携带Rv0678突变;未进行atpE基因测序[30]。共鉴定出297个Rv0678突变,大多数突变为插入或缺失突变。突变遍布整个基因;但是,5个密码子(46至49和67)突变在297个突变中占了114个(38%),在199株分离株中占了87株(44%)[30]。
在mmpR5中发现163个突变(116个非同义SNP、29个插入缺失和18个启动子变异),其中32个与MIC增加有关,14个与MIC无变化相关。3个SNP被翻译成终止密码子(E13*、W42*和R156*),这可能会改变蛋白质功能。此外,3个移码突变(192_193insG、193_193del、141_142insC)大量出现,均与较高的Bdq体外MIC相关[29]。
12项研究确定了66个独特的mmpR突变,突变广泛分布在密码子1~145之间。与耐药性相关最常见的突变是nt192-198处的6-鸟嘌呤均聚物的移码(Bdq 11株)或nt138-144处的低序列复杂度区域(Bdq 7株)或nt212-216(Bdq 4株)。在nt138-142和212-216的移码突变中,Bdq的MIC至少增加了8倍,但mmpR突变通常与Bdq的MIC适度增加2~4倍有关[25]。
三、pepQ基因突变
编码Xaa-Pro氨肽酶的pepQ基因突变也与低水平的Bdq耐药有关,推测可能通过外排发生。在pepQ基因中发现的120个新突变包括117个非同义SNP和3个插入缺失,其中2个导致单个分离株中的移码,这些移码可能参与pepQ基因的功能丧失[29]。
据报道,外排泵抑制剂可使pepQ突变体对Bdq的敏感性恢复到其野生型亲本的敏感性。体外进化的3个功能缺失突变(L44P和密码子14和271处的两个移码)导致Bdq和Cfz的MIC适度增加4倍[25]。
Bdq表型耐药检测
一、常规pDST检测方法
基于固体的7H11琼脂比例(agar proportion,AP)试验被认为是检测Bdq对MTB耐药性的参考方法[31]。应用生长活跃的突变菌株制备MTB混悬液,将混悬液接种到含不同浓度Bdq的7H11琼脂培养基(含10%OADC增菌液和0.5%甘油)上,作为实验组,而混悬液接种于无药物培养基则作为对照组。将平板置于37 ℃、含5%CO2的培养箱中孵育,1周后检查污染情况,然后在4~8周进行计数[32]。
与BACTEC MGIT 960相关的分枝杆菌生长指示管是目前DST使用最广泛的液体肉汤自动化系统。该系统可显著改善全球MTB DST的检测时间、符合率和性能[31]。将MTB混悬液接种于含不同浓度Bdq培养基的BACTEC MGIT培养管中并在 BACTEC MGIT 960系统中培养,以等体积接种生长对照管。由于MGIT系统是自动化的,可连续读取所有试管,使用荧光传感器以60 min间隔测量生长单位(growth unit,GU)水平,最长持续28 d[32]。如果含Bdq管的GU值>100且生长对照管的GU值≥400,则结果判读为耐药[33]。
二、Bdq的MIC关键浓度
Bdq 表型耐药的关键浓度目前尚未完全确定。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系统地审查了Bdq pDST的可用数据,暂定7H11 琼脂比例法、分枝杆菌生长指示管法的Bdq临界浓度(critical concentration,CCs)分别为0.25 μg/ml和1 μg/ml[34-35]。欧洲药敏试验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e on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EUCAST)在7H10和7H11琼脂比例法中采用0.25 μg/ml作为临床临界浓度(clinical breakpoint,CB)[36],高于抑制90%分离株或菌株的MIC(0.125 μg/ml)。然而,有证据表明,即使DST结果在关键浓度以下仍有可能导致治疗失败[17, 21, 32],这可能由于关键浓度的选择以及治疗过程中菌株对药物敏感性的变化引起。
Bdq耐药与临床的相关性
一、 Bdq表型耐药与Rv0678、atpE、pepQ和Rv1979c基因突变的相关性
Ismail等[37]首次评估Bdq表型耐药与Rv0678、atpE、pepQ和Rv1979c基因突变间的关系。按照检索标准共检索到1367项研究,最终40项(2.9%)研究符合纳入要求。系统文献综述的结果证实了atpE基因突变可导致高水平的耐药[38],但证据主要来自体外和动物实验,临床病例很少。研究结果显示,Rv0678基因中突变体数量众多并分散在整个基因中,大多数SNPs、插入和缺失发生在表型敏感的临床分离株中。虽有假设pepQ和Rv1979c在Bdq耐药性发展中发挥了作用[39-40],但通过对相关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其在耐药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很小[37],这项研究采用标准方法证实两个单突变体(atpE187G→C和Rv0678 138_139insG)与耐药性相关。然而,这一认知对临床不会做出实质性贡献,因为在过去13年中,临床分离株中仅报告1次atpE187G→C突变和3次Rv0678 138_139insG突变[37]。总体而言,Bdq耐药尚缺乏明确的基因型与表型关联。
二、Bdq耐药与临床结局的相关性
为监测耐药结核病患者使用Bdq期间该药耐药谱的变化,从13家研究中心的患者中收集阳性培养物,发现277例接受Bdq治疗的患者中,MDR-TB患者的初始Bdq耐药率为2.2%(6/277),5例痰培养阴转,138例在2周内痰培养阴转。另外,初始低水平Bdq耐药(0.25~0.5 μg/ml)的MDR-TB患者在接受含Bdq方案治疗时可实现痰培养阴转[13],这可能是由于对这些患者给予Bdq可以克服低水平的Bdq耐药性。
俄罗斯78例Bdq暴露患者的188株MDR-TB分离株,证实了Bdq治疗可能导致Bdq MIC升高[16]。同样,中国的一项研究显示,94例产生系列分离株的患者中,11例表现出Bdq敏感性降低,而5例获得性耐药患者中的3例未观察到痰培养阴转[13],这表明相对于Bdq原发性耐药患者,获得性耐药的MDR-TB患者治疗失败的风险更高。序列分析发现,11株Bdq耐药分离株中有6株携带Rv0678基因突变,其他3个Bdq耐药相关基因未检测到突变。痰培养阴转时间未见明显组间差异。
南非一项Bdq耐药性监测项目收集2015—2019年间所有开始接受Bdq治疗的患者的3份痰液样本:基线样本、治疗2个月和6个月的样本,共8041例患者提交监测样本,其中2023例纳入横断面分析,695例纳入纵向分析[41]。结果显示,基线Bdq耐药率为3.8%(76/2023),这一数据略高是因为pre-XDR 或 XDR-TB患者是在发病时接受基于Bdq方案的主要人群。在无Bdq或Cfz既往暴露史的人群(1987例)或未知暴露史人群(17例)中,Bdq耐药率为3.6%(72/2023),而在既往有Bdq或Cfz暴露史的人群中,耐药率为21.1%(4/19)。这一发现表明,Bdq耐药性与既往耐药结核病治疗之间无相关性。然而,如果患者既往暴露于Bdq或Cfz,则在基线时发生Bdq耐药率更高[41]。2.3%(16/695)的患者在治疗第90天时出现治疗引起的Bdq耐药情况,预计这些患者大多发生在 pre-XDR 或 XDR-TB患者的治疗早期。所以与RR-TB患者相比,pre-XDR和XDR-TB患者Bdq耐药率显著更高。此外,服用Bdq的患者若在第2个月仍保持培养阳性或培养状态逆转,应重新检测Bdq耐药性[41]。因此,表型Bdq耐药与较差的结局相关。
总结和展望
总体而言,Bdq耐药率相对较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Bdq耐药的遗传基础尚未完全阐明,目前已知的耐药机制包括atpE、Rv0678和pepQ基因突变。快速检测和有效治疗是控制Bdq耐药的关键。诊断上,开发准确的分子检测方法需要深入了解Bdq耐药性相关的基因突变,但由于数据稀缺和研究异质性,目前尚不足以开发一种快速的分子检测方法。因此,为提高对Bdq表型-基因型相关性的了解,需报告全面的基因型和表型数据及治疗结局信息,特别是治疗失败的患者。治疗上,科学合理应用新型抗结核药物及设计有效的联合治疗方案将有助于减少耐药性的出现。其次,在制定方案前,对MDR-TB患者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有利于指导临床是否将Bdq作为其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另外,当存在Bdq与Cfz交叉耐药的情况时,必须收集相关突变的基因组数据并重新考虑含有这两种药物的治疗方案,以降低患者治疗失败的风险和此类菌株在社区中的传播[21]。因此,充分了解Bdq的耐药特征及相应的耐药机制,以期开发Bdq耐药精准诊断方法,对于临床合理应用Bdq及减少耐药性产生至关重要。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姚蓉:数据的采集及整理、初稿撰写和修改;陆宇:研究指导、批评性审阅、文章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