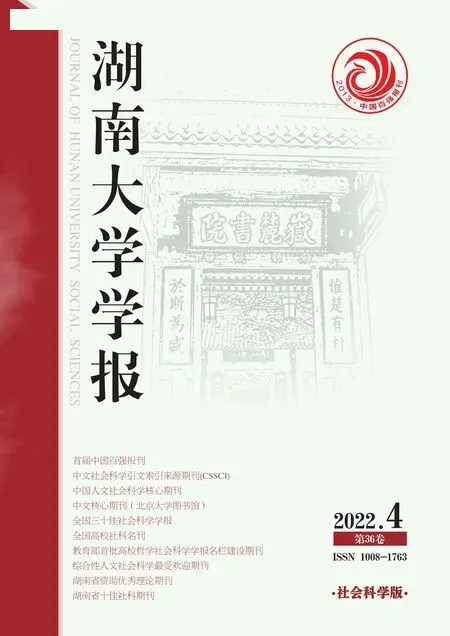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宋乾道九年(1173),张栻完成《孟子解》,后与朱熹多有讨论并加以修改。淳熙四年(1177),朱熹完成《孟子集注》。淳熙七年(1180),张栻去世,朱熹后所撰《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中赞赏张栻的义利之辨。因此,朱熹《孟子集注》讲义利与张栻《孟子解》应当有着密切的关系。问题是,朱熹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不仅引入了天理人欲概念,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将理欲与义利相对应,由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而讲仁义与利心的对立。同时引述程子语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1]202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包含了对于利的一定程度的肯定,又讲“利心”是“人欲之私”,“以利为心则有害”;既讲“不求利”,又讲“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不求利并非排斥利,而在于反对唯利是求、见利忘义,并且认为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在于“拔本塞源而救其弊”。
一 从胡安国“利者,人欲之私”说起
程朱理学讲天理人欲,依据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此,程颐作了解读:“‘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2]126又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2]312显然,在程颐那里,“人欲”即是“私欲”,而与“天理”相对立。关于义利,程颐解《孟子》“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说:“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2]176在这里,程颐不仅把孟子所讲“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解为“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把“利与善之间”改为“义利之间”,而且由此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义”指的是舜之大义,“利”指的是盗跖之利,是损人利己之利。然而,这种表述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将义与利等同于公与私而对立起来。
据《朱子语类》载,二程门人杨时曾与门人廖刚(廖用中)说义利事。廖刚说:“义利即是天理人欲。”杨时曰:“只怕贤错认,以利为义也。”[3]2598可见杨时已经将义利与天理人欲对应起来。后又有杨时门人张九成说:“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欲之间而已。然天理明者,虽居利势之中,而不为人欲所乱;人欲乱者,虽居仁义之中,亦无一合于天理者。”[4]1216
胡安国与二程门人谢良佐、杨时、游酢三先生“义兼师友”[5]1170,继承程颐天理人欲观。他所撰《春秋传》,认为《春秋》一书“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6]《春秋传序》,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同时又将天理人欲与义利对应起来,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说:“利者,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夺攘而后厌;义者,天理之公,正其义则推之天下国家而可行。”[6]43显然,胡安国所言是根据孔子所言“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以及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来。胡安国之子胡寅也说:“义者,天理之公也,华夏圣贤之敎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小人蛮貊之所喻也。”[7]430可见,胡安国、胡寅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是根据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来。需要指出的是,胡安国所言中的“利”是“放于利而行,多怨”之利,是“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之利,是就私利而言。胡安国《春秋传》讨论宣公十一年(前598),“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说:“《左氏传》:‘楚子为夏氏乱故,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征舒,轘诸栗门。’而经先书‘杀’,后书‘入’者,与楚子之能讨贼,故先之也。讨其贼为义,取其国为贪,舜、跖之相去远矣,其分乃在于善与利耳。楚庄以义讨贼,勇于为善,舜之徒也;以贪取国,急于为利,跖之徒矣。为善与恶,特在一念须臾之间,而书法如此,故《春秋》传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6]276可见,胡安国《春秋传》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其中的“利”,如盗跖之利,都是就私利而言。同时,胡安国还解《易》乾卦“元亨利贞”,说:“四德备而后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贞。’一德不备,则乾道熄矣。”[6]23显然,胡安国也讲《易》乾卦“元亨利贞”之利,讲《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之“利物”,肯定“利物”之德。可见,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实际上只是反对私利,将义与私利对立起来,而不是完全排斥利,不是笼统地讲义利对立。但不可否认,胡安国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将义与利的关系等同于天理人欲关系、公私关系而讲义利对立,是对利的否定。
胡安国撰《春秋传》,继承程颐所谓“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对《孟子》“王何必曰利”多有引述,并与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相结合,提出“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但或许未曾读到《程氏遗书》“‘利贞者性情也’,言利贞便是《乾》之性情”。因问:“利与‘以利为本’同否?”程颐说:“凡字只有一个,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顺理无害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2]249从这一语录可以看出,程颐解《孟子》“以利为本”,而讲“君子未尝不欲利”,同时解《孟子》“何必曰利”,而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仁义未尝不利”,并非讲义利对立,而只是反对“以利为心”。程颐这一语录,为程颐门人、杨时长子杨迪(杨遵道)所录,后来为朱熹编成的《程氏遗书》收录。
程颐不仅解《孟子》“何必曰利”而言“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反对“以利为心”,并特别强调“仁义未尝不利”,而且解“子罕言利”而言“计利则害义”[2]1150,并且说:“‘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盖人不当以利为心。《易》曰:‘利者义之和。’以义而致利斯可矣。”[2]383不是要“去利而就害”,而是反对“以利为心”,并强调“以义而致利”。显然,在程颐看来,利与害相对立,“以利为心”则是有害。程颐还说:“理者天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其公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2]917-918在程颐看来,“利者众人所同欲”,人人都想要利,但又不可“切于好利,蔽于自私”,不可自私自利,不可“以利为心”。可见,程颐将“利”与“利心”区分开来,将利与害对立,利并不是不好,所谓“利非不善也”[2]1170;而“利心”则是有害,是不好的。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虽然与程颐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相一致,都反对私利,但是胡安国所言中的“利”是就私利而言,“利者,人欲之私”,是不好的,因而与程颐对利的理解“利非不善”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
二 朱熹对“利”与“利心”的分辨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又讲“仁义未尝不利”,并非讲义利对立,为朱熹所继承。朱熹《孟子集注》的解读也没有明确认为该句是讲义利对立。尤其是,朱熹解该句之后所言“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明确说:“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又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明确说:“此言仁义未尝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之意也。”显然,在朱熹看来,孟子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要由此讲“求利之害”,讲“仁义未尝不利”,并非讲义利对立。为此,朱熹又说:“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则其下化之,自亲戴于己也。”进而指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而且还将程颐所谓“君子未尝不欲利”与“孟子言‘何必曰利’者,盖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合为一句,改写为:“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1]201-202明显是对利有较多的肯定,而只是反对“以利为心”。也就是说,在朱熹《孟子集注》中,孟子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非讲义利对立,并非要排斥利,而是讲“求利之害”,讲“仁义未尝不利”,反对“利心”,反对求利之心。这样的解读虽然讲天理人欲的对立,讲仁义与利心的对立,但并没有讲义利对立,并非排斥利,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在文字表述上多有不同。
朱熹《四书或问》就“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作了进一步说明:“仁义,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义,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义得于此,则君臣父子之间,以至于天下之事,自无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谓‘利者义之和’,正谓此尔。”[8]920在朱熹看来,居仁由义,“天下之事,自无一物不得其所者”,其间并无求利之心,这就是《易传》“利者义之和”之意,显然是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反对求利之心。
可见,在朱熹看来,“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仁义并非与利相对立,而是与利心相对立。他还说:“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然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3]1218这里所谓“才说著利,必害于义”,似乎是讲义与利的相互对立,但这只是就利心而言,是讲利心与义的对立,因此“不可先有求利之心”。也就是说,利由义而来,害由“求利之心”而来;“求利之心”不仅与仁义之心对立,而且与利相对立。
应当说,朱熹讲“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将义利与天理人欲相对应,在文字表达上无疑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朱熹讲“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与胡安国讲“利者,人欲之私”,又将其中的“利”解读为私利,而与义对立起来,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一,胡安国讲“利者,人欲之私”,朱熹讲“利心”为人欲之私。程朱讲天理人欲,讲的是心性修养;而他们讲义利,实际上讲的是社会生活。二者是不同的。胡安国把社会生活的义利与心性修养的天理人欲混为一谈。朱熹从心性修养的天理人欲看待义利,讲仁义之心而为天理,讲求利之心而为私欲,强调“利”与“利心”的不同,讲仁义之心与求利之心的对立,并非由此讲义与利的对立。
第二,胡安国讲“利者,人欲之私”,是要去除私利。朱熹讲“利心”为人欲之私,是要去除“利心”。胡安国讲“利者,人欲之私”,虽然实际上是要去除私利,但很容易被理解为是要排斥利。朱熹要去除“利心”,讲的是“不求利”,实际上是要去除对于利的贪欲,不主动求利,并没有完全排斥利之意。同时,朱熹反对利己,强调“利物”与“自利”的对立。他还说:“梁惠王问利国,便是为己,只管自家国,不管他人国。义利之分,其争毫厘。”[3]1220也就是说,义利之分,并不是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讲义而排斥利,而是在于利人还是利己。去除“利心”就是要去除利己之心,就是要去除私利。
第三,胡安国讲“利者,人欲之私”,只是要去除私利。而朱熹去除“利心”,则是要达到“不求利而自无不利”,避免“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根本就不是要排斥利。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只是从理欲讲到义利,进而排斥利。朱熹则不仅从理欲讲到仁义之心与求利之心,而且进一步从义与利的相互关系中,从利与害的相互关系中,肯定利的重要性。
三 张栻“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
朱熹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引入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讲“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虽然有别于胡安国所言“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但却非常推崇继胡安国而后张栻的义利之辨。
从现存的著作看,张栻研究《易传》而撰《南轩易说》,对《系辞》多有研究,但缺少对于《文言》的专题论述,因而也没有直接对于“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的解读。对于《系辞下》所言“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张栻说:“乾之德有利有正;变动以利言,非正也。人之生有性有情;吉凶以情迁,非性也。……六爻之变动,将以图利而免害也;六爻之吉凶,无非以情而感物也。”[9]55这里所谓“乾之德有利有正”,实际上就是讲《文言》所谓君子的“元亨利贞”之“四德”;利,即“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讲的是“利物”之德。可见,张栻讲“六爻之变动,将以图利而免害也”,实际上是对“利物”以充分的肯定,并非完全排斥利。
就义利关系而言,张栻说:“嗟乎!道二,义与利而已矣。义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逵;而利者犯荆棘、入险阻之私径也。”[9]991他的《孟子解》解孟子所言“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说:“此章论善、利为舜、跖之分,……盖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也,此不过毫厘之间,而有白黑之异,霄壤之隔焉。故程子曰:‘间云者,谓相去不远也。’夫善者,天理之公。孳孳为善者,存乎此而不舍也。至于利,则一己之私而已。”[9]603应当说,张栻的这一解读,讲“出义则入利,去利则为善也,此不过毫厘之间,而有白黑之异,霄壤之隔”,与程颐的解读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基本相同,因而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也多有一致,都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当然,张栻这里所谓“利”,为“一己之私”,为利己,为私利,并非《文言》所言“利物”,所以他实际上讲的是义与私利的对立。
重要的是,张栻《孟子解》还对义利作了进一步的界定,说:“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9]311又说:“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9]1007-1008认为“无所为者”是天理,为“义之公”;“有所为者”是人欲,为“利之私”。也就是说,张栻所谓私利,指的是“有所为者”。他还说:“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终日之间鲜不为利矣,非特名位货殖而后为利也。斯须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则一而已。如孟子所谓内交要誉、恶其声之类是也。”[9]311也就是说,张栻所谓私利,不只是指名位财利,“凡处君臣、父子、夫妇以至朋友、乡党之间,起居话言之际,意之所向,一涉于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虽善,而内交要誉,恶其声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9]973因此,张栻讲义利,不仅实际上是讲义与私利的对立,而且其意在于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而“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就是指行为动机上是否为了谋利的对立,也就是朱熹所谓“不求利”与“求利”的对立,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而不只是行为效果上的是否有利,或是利人与利己的对立。
张栻《孟子解》不仅把义利解读为“无所为者”是天理,为“义之公”;“有所为者”是人欲,为“利之私”,还进一步由此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且说:“惟其以利为先,而不顾于义,则其势必至于不夺则不厌。……欲利反所以害之也。若在上者躬仁义以为本,则在下者亦将惟仁义之趋。仁莫大于爱亲,义莫先于尊君。人知仁义之趋,则其有遗其亲而后其君者乎?此其益于人之国,可谓大矣。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9]314显然,张栻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是要反对“以利为先,而不顾于义”,反对义与利的相互对立;而他讲“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与朱熹讲“仁义未尝不利”,又讲“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只是讲仁义与利心的对立,而不是要把义利对立起来,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张栻《孟子解》不仅认为孟子所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讲的是“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而且还进一步讲“其所以反复警告者,深切著明,王道之本实在于此”,[9]314认为孟子所言王道,并非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在于行仁义而利于百姓,从而阐明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真正原因在于王道。
朱熹在《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中对张栻的义利之辨予以很高的评价,并且说:“盖其常言有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后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呜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谓扩前圣之所未发,而同于性善养气之功者欤!”[10]4140肯定张栻的义利之辨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以及对于“有所为者”的反对。
应当说,朱熹讲“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虽然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胡安国所言中的“利”,只是就私利而言,而且在张栻那里,是“有所为者”,是谋利的动机,即朱熹的“利心”,因而又与朱熹所言多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经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可以引伸出朱熹讲“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这也许就是朱熹讲“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虽不同于胡安国讲“利者,人欲之私”,但并没有明确对胡安国所言提出批评的原因。
四 结 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张栻,还是朱熹,他们对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解读,都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但并非由此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要反对私利,反对唯利是求,讲义与私利的对立。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由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讲行为动机的“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反对“有所为者”;朱熹则讲“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明确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张栻讲“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朱熹讲“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都不是要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而是要通过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而反对私利,反对“有所为者”,反对“以利为心”。
应当说,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朱熹讲“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二者是一致的,所以朱熹对张栻所言予以高度评价。就这一点而言,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与朱熹是相同的。
然而,就义与利的相互关系而言,虽然张栻反对“以利为先,而不顾于义”,反对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又讲“欲利反所以害之也”,讲“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朱熹讲“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与张栻如出一辙,但是,朱熹将程颐解《孟子》“以利为本”而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改为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言,较张栻更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对于利以更多的肯定。相比较而言,张栻即使能够接受程颐所言“仁义未尝不利”,但也未必能够完全接受以程颐所言“君子未尝不欲利”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由此亦可以看出,在义利之辨问题上,张栻要较朱熹更为谨慎。
尤为重要的是,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不只是停留于义利之辨上,而是由此认为“王道之本实在于此”,把义利之辨与王道、与造福百姓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从而展示了儒家义利之辨的更为广阔的论述空间。与此不同,朱熹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既肯定“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同时又对孟子为什么在当时“言仁义而不言利”作了解释,说:“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1]202一方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义利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又承认社会现实生活中义利的相互对立,而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正是要应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唯利是求、义利对立,而不是要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样的解读,使得程颐所言“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达到学理上的融洽一致,从而展示了儒家义利之辨的更为深刻的思想逻辑。
朱熹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讲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又讲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相互对立,这一思想为后来的王夫之所阐释。王夫之《四书训义》解《论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引述朱熹的注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并且说:“夫子曰:君子小人之分,义利而已矣。乃君子之于义,充类至尽以精之,而利害非其所恤;小人之于利,殚智竭力以谋之,而名义有所不顾;则皆以行其所能知者而已。……故君子之于义,终身由之而不倦;小人之于利,寤寐以之而不忘。人未有不喻之而能专意以为之,亦未有喻之而可禁其不为者也。斯则君子小人义利之辨,辨于其所习而已矣。”[11]381-382这里虽然讲“君子小人之分,义利而已矣”,似乎是讲义与利的对立,但实际上讲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喻于义”与“喻于利”,所谓“君子小人义利之辨,辨于其所习而已矣”,并非讲义与利的对立。当然,王夫之又进一步对义利关系作了深入分析,说:“要而论之,义之与利,其途相反,而推之于天理之公,则固合也。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事得其宜,则推之天下而可行,何不利之有哉?但在政教衰乱之世,则有义而不利者矣。乃义或有不利,而利未有能利者也。……故曰: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欲为之而即谋之也,斯为小人而已矣。”[11]382,王夫之明确认为,义与利虽然“其途相反”,但归根到底其本身是相合的;义为天理之公,“正以利所行者也”,义而有利,义利相合。同时,王夫之又认为,在政教衰乱之世,“义或有不利”,义与利相互分离,甚至义利对立,这就是胡安国所谓“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所以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无所争以养其和平”[11]772。显然,王夫之的解读,既讲义利相合,又讲义利相分,是继承朱熹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程颐、胡安国,还是张栻、朱熹、王夫之,他们对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解读以及对于义利的论述,虽然只是要反对私利,反对利心,反对唯利是求,而并非完全排斥利,但由于对“利”缺乏定义,利与私利、利与利心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因而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以及在现代学术的研究中,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解,甚至被解读为是讲义利对立而排斥利,在所难免,所以还需作更多的分析研究和学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