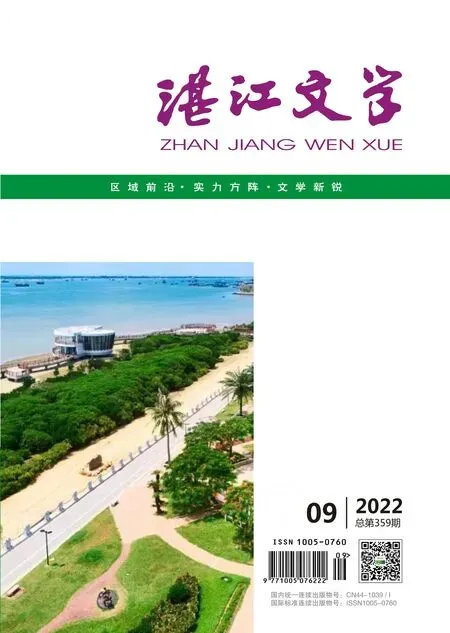村口有大树(外一篇)
◎ 胡海燕
当我们走近,一群大树微微欠身。枝叶扶动,沙沙有声,仿若客人来到作出的欢迎词。
满目绿意。走进去,人都绿了。樟树枫树以及其他,体格健壮,姿态优美。立夏节气。绿树阴浓夏日长,是一棵树遇上了美好时光。它们热热闹闹的,挨挤着,交错着,繁茂成一片绿意葱茏的小森林。
午后,在潘庄村口的大树下,静静地坐一会儿,便想起了泰戈尔的诗:“喂,你站在池边的蓬头的榕树,你可会忘记了那小小的孩子,就像那在你的枝上筑巢又离开了你的鸟儿似的孩子。”仰望大树,仿若真成了归家的孩子。
几乎每个村口,都有这样的大树。有时一棵,独木成林,一树一世界。有时三三两两,沿着入村的小路错落地排列过去,仿若树也会散步,走着走着就走进了人们的生活里。有时规规矩矩集于一处,上百年上千年时间过去,便形成颇有声势的林子。这样的地方,大都还有一脉生养万物的生命之水。于是,风光格外好。村人喊它“水口”。
但不管以何种方式出现,村口的大树似乎从来不属于自己。它们为一座村庄而生,为一座村庄而长。它们是巧妙安排在村口的伏笔。绿意掩映下,村庄羞羞答答地打开自己。越往里头,越是敞亮。而漫漫时间长河里,大树一刻不停地修炼自己,直到修炼成符合村庄气质的样子。村庄古老的,它们便也遒劲沧桑,仿若阅尽红尘万千,从容而潇洒。村庄崭新的,树也新。初生牛犊一般,凡事一副无畏态度。只是一个劲儿地,活泼泼地往天空生长,日日不同模样。
初夏的风吹起来,绿盈盈的凉,浸润草木清香。被草木包容,与草木对话,仿佛我们也生长出草木之心,恬静而淡然,安宁而知足。树木之外,是小桥,是流水,是村庄。以这样的方式打开一座村庄,似乎也有了不同寻常的况味。
几年前,朋友说要带我去看一个很美的村庄。于是,来到了潘庄。只见西流的溪水在村边拐了一个大弯,仿若怀抱,轻轻拥村入怀。踩着溪面上的石埠步入村中,石墙夹道,老屋俨然。巷陌幽深,曲曲折折地通向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人们或忙碌,或闲坐,拥有最自在的生活状态。而绿树斜在村口,仿若点睛之笔。那一刻,我似乎懂了,这便是村庄最美好的样子。
与一个村庄的缘分,也许一辈子就那么一两次。一晃多年,出于偶然,再次踏进潘庄。只是,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事物,都不见了。村里腾出几片空地。有些空地上长杂草,有些长出崭新的房子。唯有水依旧,桥依旧,树依旧。
大概,树比任何事物活得长久。在另一个村口,我见过一棵香榧树。长了几百年,空了心。却仍是神气十足,年年开花,年年结果。人走进去,世界安静,往事安静。风雨挡在树身之外,烦恼俗事挡在树身之外。又仿佛走进一棵树的灵魂深处,彼此交了心。触摸斑驳的纹路,犹如触摸百年光阴。和树对话,犹如和数百年的光阴对话。小小天地竟有了大大内容,是真正的虚怀若谷。
一棵树的胸怀,足以让人托付终身。听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原始森林里,生活着一群与世隔绝的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居住在树屋里的部落。他们的房屋建在西米棕榈树上,依靠西米棕榈树干做成的梯子爬上爬下。因此,这个部落的人被称为“树屋人”。他们的世界只有树。对一棵树的信任,就是对一整个世界的信任。
我老家村口也有几棵大树。两棵不结果的香榧,一棵长红豆的红豆杉。不知道什么时候在的。听爷爷说,他的童年也是大树给的。它们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大,长着差不多的模样。初来乍到的人,总以为是三胞胎。只有住久了,才能分清彼此。三棵差不多的树站在村口,共同撑起一片天。我们却厚此薄彼,对每到秋日便挂满红玛瑙的红豆杉青睐有加。我们不成熟的眼光里,常常以貌取人。谁好看就喜欢谁,谁实用就偏向谁。而树们不管这些,一味放任我们的态度,除了生长还是生长。
大树撑起一个乐园,仿佛撑起最美好的家园。在树下,我们从不吝啬时光,大把大把地抛掷。我们不知疲倦地沿着裸露的树根爬上爬下,在攀爬中一次次感受树木的温度。我们稚嫩的手脚千遍万遍抚摸过树根,直到树根散发油亮的光。老人无所事事。久久枯坐。看看前方,看看树,似乎和树无声交谈,但不知谈了什么。老人的世界和树的世界一样,喜欢用沉默作出最巧妙的回答。青壮年不常出现在这里,他们太忙了,总有忙不完的事儿。偶尔来了,也是夕阳西下,呼唤孩子们回家。
时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滑过去。蓦然回首,渐渐模糊的底色上,总有那样几棵青翠的大树,枝丫上挂满我们最美好的故事。我们忘了村子里发生的很多事,却不会忘记大树下生发的细枝末节。曾经,我们陪伴了它们,它们也陪伴着我们。我们陪过它们短暂的一瞬,它们却陪伴我们整整一生。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相较而言,大树更长情。它终究不离不弃,成了我们最亲的亲人。
树的世界,是一个玄妙的世界。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树是神物。谁同他们交谈,谁能倾听他们的语言,谁就能获得真理。”也许读懂了树,就读懂了人生。而后,当你少小离家老大回来,即便变了乡音又老了容颜,一眼望见村口的大树,故乡的记忆便拉开序幕。往事一幕一幕,沿着时光的纹路往前走,往后走,那样熟悉而亲切。有时,村庄生长太快了,一代代不停地改头换面,像翻书一样倏忽而过,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也曾慌张,彷徨,感受无以言表。但大树,终究能抚平所有忧伤。
树在,根就在。
尖山老街
某一日,你发现门板旧了,有的地方被磨得薄透了,却不知是什么将它磨透的。也许是形形色色的手,是隐匿其中的虫子,或者,只是时光。事物的老去往往悄无声息,却又理直气壮。
甚至开了一个洞。一束光走进屋里。光在扩大。孩子调皮的手伸进伸出,猫猫狗狗跳来跳去。门板差不多名存实亡了。又有一天,屋子开始倾斜。一开始是带头的一家斜了,旁边连在一块儿的赶紧过来帮忙,用尽全力想把邻居扶正。不曾想,不仅没扶正,反而自己也被带斜了。如此,被带斜的还有邻居的邻居。不知多少年过去,一整条街都斜了,像一个老人终究敌不过时间,歪歪扭扭的,任凭十二分努力仍是站不直。在这样的歪斜中,老屋越来越单薄。风大雨大的日子,身子骨差不多要散架了,摇摇晃晃的,令人担心。
人们不得不另寻去处,一个一个地走出去,一家一家地走,最后差不多都走完了。商铺走了,吆喝声跟着走了,讨价还价声也走了。寻常烟火走了,无赖小儿走了,嬉笑怒骂也走了。
一条街,就这样老去了。
后来,一块石头立在了入口处,上面写着:尖山老街。石头不容易老。刻进石头里的四个大字,青蓝色,依然新鲜。相比之下,建于明清时期的老街就沧桑许多,颇有“岁月易逝,容颜易老”之感。岁月面前,世间万物皆如泡影,一个不小心便稍纵即逝。尖山地处金华、台州、绍兴三地市交界地带。三州交汇,各地百姓频繁往来,或偶然经过,或短暂停留,或长期从事某项买卖,于是,商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人潮涌动,繁华街景随之形成。据说,在清代,尖山老街是商铺重地,卖盐的商家众多,有“日销千担盐”之说。那些盐大概自天台来,或从绍兴来,或从更遥远的海边来。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斑斓的文化。
人们喜欢跟着指示走进去,找一找无处安放的闲愁。或者,漂泊半生的游子归来,一眼望见老街仍在,仿若故友久别重逢,一时惆怅满怀,忙忙地找寻曾经的记忆去了。
一切,恍然重现。这个屋檐下我避过雨,那个店里买过东西,在那里吃过最好吃的点心。而小伙伴们成群地追逐在街上,即使路面全用大小不一的玄武石铺成,凹凹凸凸,又被来来去去的脚磨得滑溜溜的,也总能跑得稳当而飞快。他们自小奔跑在老街,早已对它知根知底。当奔跑在后的铆足了劲加速,伸手一把抓住前头的,几个小小的身体便拉扯在一处。侥幸逃脱的,也凑过来看起了热闹,哇啦啦的喊叫声此起彼伏。而快乐,不经意间早已传遍了整条老街。就这样跑着玩着,不知何时,小伙伴们都长大了……
温暖的阳光洒下来,老街的一半晾在阳光里,一半躲在阴影中。狭窄的街道,面面相觑的两层木楼,手挽手肩并肩地站立姿态,稍显局促的生活空间,都是原来的模样。几个人站着聊天。有人从阳光中走来。有人骑着电动车颠簸着过去,砰砰啪啪的声音跟了一路。有游客驻足,心事重重的样子,仿佛寻找什么,思考什么。
三两家店已开张。鞋铺卸下窗户上的木板,在窗口的旧桌子上摆出一排雨靴,高筒的,中筒的,深蓝,大红,迷彩,都是小时候常见的款式。越过窗口往里瞧,老式木头置物柜,老式柜台,各色毛线,老棉鞋,解放鞋,摆得满满当当,是80年代的样子。以前在供销社常见这样的场景,只是这儿一间房子大小,略显局促罢了。
隔一段路看见门口立着个人头模特,长发披肩,边上一个架子,挂满蓝色毛巾。望进去,一个男子躺在理发椅上,理发师拿着剃刀给他刮胡子。理发师老了,大概五六十岁。大概叫亭兰,一个好听的名字。门口上方的招牌上写着“亭兰理发”。又隔一段路,是一个裁缝店。没有招牌,门窗上分别贴着一张白纸,写着“修裤脚、换拉链”以及联系电话。主人不在。
一种繁华落尽的静默蔓延开来。老街低沉沉的,不吭一声。其他人家都上了锁,有的锁生了锈,有的锁新着。几道门上落了好几重锁,似乎要长久离开,想着要多加一把才放心。而我们呢,看到那么多锁,坚硬又冰冷,仿佛看到一种生活戛然而止,似乎下定决心要与过去彻底割裂开来,心里头不免怅怅然的。
想起之前,沿着老街走下去,会经过周氏宗祠,会走到尖山小学。那时,我是学校里的一名老师,先生是卫生院的医生。我每日几回地往返于两点之间,而连接这两点的正是尖山老街。每日在老街上来来回回,以为关于老街是熟悉的,却也是忘了具体样子。我们往往急于赶路,而忘了留意路旁的风景。唯独记得那时总忙忙地奔赴在路上,奔赴书声琅琅的学校,奔赴成立不久的小家,似乎都是怀揣梦想奔赴美好未来,满心里皆是暖意融融的欢喜。
一晃十八年过去。学校觅了新址,搬去狮峰山脚下,建成更具规模更现代化的校园。老校舍差不多拆完了,一座漂亮的酒店拔地而起。所幸,角落里的老四合院被留下来了,建成乡贤馆。走进去,虽面貌崭新,却似乎看见那个窄窄的讲台上,我默默地奉献过青春。这些年,我虽过得起起伏伏,但也算令人满意。今日重走老街,恍如看见当年的自己,跌跌撞撞从老街出发,一时感慨万千。而被展示在馆内认识的不认识的乡贤,一生诸多成就,却也曾是这里的稚嫩学子。即便他们走得再远,仍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地方等着。岁月,能给我们留下一些痕迹已是眷顾。
老街上方挂满了新颖的灯笼,明媚而张扬,仿佛架起一座彩虹桥。门上的对联红彤彤的,是新年贴上的。一群工人对着老屋修修补补,破旧的门板被拆下,换上了崭新的,白花花地泛着光。也许会做仿旧处理,看起来恍然回到了从前。也许顺其自然,任它在时光里慢慢老去。
老街不急呀。它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