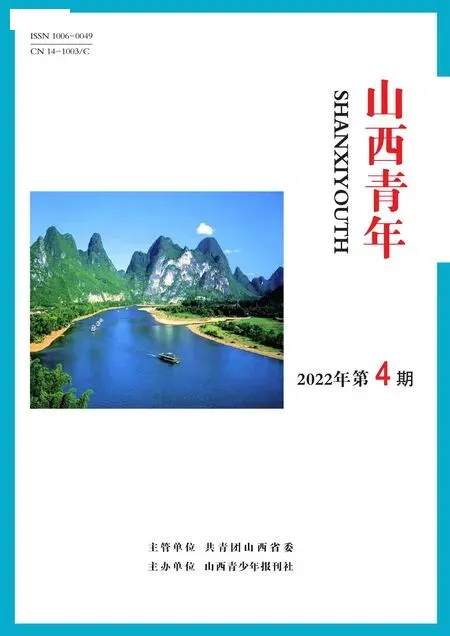王尧《民谣》的文学异质性
张亚萍 曹瑞雪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新世纪文学”逐步成为一个外延明确的概念,即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改革、发展、智能、数据、矛盾、危机等等元素相互交错交融,使得一种既承接着现代性又粘连着历史性的新世纪素质逐渐形成,并且在逐日得到强化与突出。在这种新质氛围的影响下,文学家们开始文学创作的探索与创新性书写,在文学文本的呈现方面,则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异质性特征。
一、“我”与“历史”的重建意识
“文学既不是政治观念的注脚,也不是思想发展史的解读。文学就其实质而言,是形象和意象的结合,作家主体意识及社会现实的结合与呈现。”[1]作者王尧在《〈民谣〉的声音》里说过:“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种重建意识着重体现在“我”与“历史”关联的一种主动性和选择性。“我”并非完全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进行人物发展与命运的书写;也并非完全将“历史”缀连到“我”的身上,然后以个人的生存境遇为中心展开关于宏大历史的讲述。“我”与“历史”双方之间的连结是在“相关性”意识下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的选择、自然的契合。
(一)革命与现代化的延续性
“村中有庄,有舍,舍围着庄转,庄围着镇转,镇围着县城转,这就是通常的社会秩序。有一天,我们村庄的秩序被打破了。”[2]这句话点出了整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即一个秩序被打破的时代。当传统乡村社会安土重迁、停滞不前的秩序遭遇革命,那种稳寂与封闭注定是要被“打破”的。小说写的正是在这种被冲击、被“打破”的历史时期下乡村的人与事。文本借助主人公返回少年记忆的通道打开了一个村庄的现代蜕变史图,通过回忆、现实、梦境、幻觉、虚构与真实杂糅交织的不同声音呈现了一首多声部式的革命史诗。
“现代化”的历史视野将中国19世纪以来不断引进和发展现代新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和这一过程里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化正式放入了历史考察。庄东头那边的“广播”在钻井机器的轰鸣声中再也听不见了,稻床在脱粒机的工作声中被放置一旁,庄前大桥上乘凉的人群待在家中吹着空调的冷气,曾裸泳的河流在工厂废气废水的排放中发烂发臭……现代文明的血液不断地融入和内变着这座古老乡村的内核,时代残存的瘢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渐渐淡化,整座村庄也在改变和被改变中起伏。作者的笔调审慎又理性,他站在历史圈子的外围,既看到了这场大运动里的“收益”,也指出了这个过程中的“亏损”,表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复杂性的深入理解和关怀,呈现出作家与现代中国变革之间少有的互动景观。在那座村庄里,革命与现代化都是绵延不断的存在。社会文明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新旧介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它们之间或消解或斗争的状态也将继续持续下去。
(二)碎片化与整体化书写的平衡性
小说的叙事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散碎”且“凝聚”的特征。作者通过回到过去和呈现当下的双线并轨式的交相叙述话语,建构起一个分层复杂的事件网络。不同的人物个体和历史片段在主人公王厚平的回忆中,轮番上场。它们看似并未遵循任何严格的时间或者空间顺序,只是随着主人公意识的流动随机跳出。实际上,这些碎片化的呈现逻辑恰恰是整个文本内在的核心叙事框架。所有记忆碎片共同作用,不仅勾勒出了相关历史背景的大图景,理清了事件的发展经过,还描摹出了处于社会洪流中翻腾起伏的个体人物的人生世相。
“许多人都向往回到失去的童年世界中追寻记忆中的生活残片,或表示依恋,或表示愤恨。只是艺术家更执着于在梦中和神经疾病中回顾,因为艺术可以提供回归过去的最佳途径。”[3]小说巧妙地对回归过去这一环节进行了艺术策略的加工处理,通过充满个人特色的童年视角,夹杂着神经衰弱病理的加持,借助呓语般的讲述,将大量历史中出现的片段浮现在现实的纸上。但同时,各个碎片化片段又以有机的排列方式,以极强的自洽性镶嵌在整体的书写过程中,作品整体的展开像是一张充满玄机的拼图,看似分散,实则具有很强的内聚性。每个波澜不惊的小故事以其真实性和不加雕饰地呈现,与整体书写达到了一种碎片化和整体性相统一的平衡状态。
二、从“小把戏”到“大结构”的叙事艺术
(一)形式实验的探险与“小把戏”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小说中的空间是重要的叙事承载体。空间的外延可以不断扩大,直至无限广阔,其内涵可以不断细分,直至个人知觉视域局限下无限可分性的极限,就像一张纸被撕裂成为无数的碎片。”[4]空间是人类感知世界和体悟世界的重要因素,平面文本通常借助不同多维空间的塑造,从而增加审美内蕴和艺术感受的立体张力。小说《民谣》尤其擅长对本土空间的艺术重构,通过详细的方位介绍和布局描写,凸显出作品鲜明斧刻的画面感。“庄子的东西两侧分别是东泊和西泊。如果用线条表示,这个庄子是在南北两条线、东西两个圆圈之间。”“庄后的河也就是北河,西边融通了西泊的北水面,东边拐了个弯子向东北,流到吴堡大队,拐向东南,便是东泊。”[5]……像这样关于详细描写空间的情节片段在不断拼贴、交错的过程中逐渐组合出一个立体、丰满的江南水乡模样。在弯弯曲曲的河泊交界处,有一块土地忙碌蓬勃、生机焕发,人们在河里做工,从桥上走过,在田埂上看鸟,有时候蹲在码头上用淘箩戏鱼,有时候趴在土墙上捉蜜蜂。作者真挚且具有地方感的叙述将发生在不同地点的片段关联起来,让各个情节部分之间具有了空间关系中的联结点,点绘出了一幅展开着的立体图景,给了小说横向上叙事发展的动力。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杂篇中将书信、新闻报道、政治通报、申请书等材料拼贴进来,将这些看似仿佛独立于正文之外的静态书面材料与作者不断流动着的回忆性意识材料相嵌合,形成了“动态”与“静态”的两种组合形态,彼此穿插,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了横纵不同空间维度的叙事结构。
(二)形式实验的冒险与“大结构”
形式和内容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无论是活的动物,还是任何由部分组成的整体,若要显得美,就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即不仅本体各部分的排序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体积,因为美取决于体积和顺序。”[6]在《民谣》中作者尝试了“形式”如何成为“内容”这一形式实验,将“杂篇”和“外篇”加入整体内容中,是一次充满冒险精神的文体尝试。
《民谣》是一部村庄的记忆追溯,它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一部回忆录,回忆的对象是一个村庄以及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的祖孙三辈,通过不同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命运走向讲述着发生在这段历史区间的历史文明进程。但同时,这部作品又不仅仅只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纯小说文体结构。“杂篇”和“外篇”作为最后附录的小部分,内化在小说整体的“大结构”之中,“‘杂篇’不仅是补充了前四卷的细节,它还是‘我’与‘时代’的语言生活。”“外篇”则以小说中杨老师的名义,写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向太阳》,也算是了结了杨老师的一个心愿。这个部分用不同的语言叙述了小说中“围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三、“似散实聚”的散文化意象隐喻
如歌德所说,从什么方面出发向知识和科学靠近,或者说,通过哪扇门进来,会有重大的区别。在写小说之前,王尧素来以散文研究著称,其曾凭《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批评奖。散文清新、恣肆、漫卷、素远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进入小说写作的语言和体式,加之其深受汪曾祺先生作品的影响,因此在《民谣》中多次出现运用意象来进行深层次隐喻内蕴阐发的现象。
(一)太阳:自我求索的精神揭示
先秦奇书《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夸父与日逐走的传说,很早地表现了个体对于光明追求的精神求索历程,夸父到渴死都在追逐的太阳即是一种理想的化身,文学家萧兵先生称夸父是“盗火英雄”,为了给人类采撷火种,使大地获得光明与温暖。小说《民谣》中借“太阳”意象表征作者对时代境遇的认知与慨叹,具有强烈的感召性和新奇性。
卷一第一小节里,“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7]小说的第一句话在开篇就奠定了小说的“调性”。用“一张薄纸”来形容太阳,一瞬间便将炽热的意象单薄化,“垫在屁股底下”带有些慵懒和随性,将全文的氛围和基调拉在一条较为“温和”的水平起点上。卷一第十二小节里,“外公说:安葬王二大队长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说太阳像鲜红的血。”[8]“鲜红的血”作为极有震撼力的意象,令人肃然生穆,深刻地暗示了王二大队长牺牲时的悲壮,表现出了对于反革命力量的愤怒,同时也暗含着革命战斗的艰苦与惨烈,这个基点开始上升到临界点状态。在卷二第十小节里,“胡若愚在夕阳下沿着石板街向西。少年将墨镜打开,双手扶着镜架向西望去,眼镜里的夕阳已经没有了刺眼的光芒。”[9]此时的太阳光芒与胡若愚自身的精神气融为一体,胡若愚的政治道路出了问题,前途未卜,之前光鲜亮丽的少爷光环逐渐褪色,这个基点又开始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卷四第八小节里,“阳光没有颜色,阳光贴近大地贴近庄稼贴近少年鼓胀的胸脯时才有了颜色。阳光只有照在向日葵上时才是金子。”[10]阳光由先前的红色逐渐褪色归为无色,总体基调又回归一种平缓的状态,并揭示出阳光与土地、少年和生命之间强有力的共生关联。
(二)麦子的霉味:回望中虚幻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中,麦地承载的是一种无声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人在麦地上活过又死去,麦地是他们的生命之根,生命之始,亦是生命之终。麦地给他们带来生的希望,却又不能完全驱散他们对生的迷茫。它所表征的伟大质朴、智性深沉的地母形象便是作家隐喻的精神家园,令人神往却又虚幻缥缈。在小说中,麦秸的霉气是一种凝结着的精神皈依,也是一种带有余味的旧质符号。
卷一第一小节里,“浑浊的潮湿抑制住了麦子的霉味,阳光下,发酵出来的味道慢慢地扩散着。”“凡是空地都铺满麦秸,霉味肆无忌惮地冲出来,钻进所有人的鼻孔,我们这个村子里的人在一个季节都失去了正常的嗅觉。”[11]麦子的霉味是一种依附和归属,麦子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村庄里最为重要的生存资料,它给予生活在庄里的村民极大的安全感和崇高的迷恋感。卷三第十八小节里,“他感叹地说:老厂长不在了。一阵风从河道上吹过来,我似乎闻到了1972年麦子的霉味。”[12]这里的“麦子的霉味”是另一种精神上的依恋,亲情上的归属。那一年我坐在码头等的是外公,外公就是我在亲情上的牵绊。卷四第七小节里,“在一顿晚餐上,我终于被弥漫着的麦子霉味呛到了。”“整个村庄都发霉了,腐朽了。晒干的麦秸因为腐朽已经断了筋骨,我们无法再用麦秸编制草笼子。”[13]此处的霉味则是一种旧质的象征,旧时代固有的生活秩序和生存模式所带来的混沌蒙昧的状态,恰似作者所言的阴郁的废墟。
巴金先生有言:“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人类的感情是共鸣的,带着感情创作出的作品,它的调性才有可能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需要。在当下文学创作急需拯救小说调性和文学性的境遇之际,王尧降低速率,减缓节奏,用十年时间、马拉松式的写作,以一个果决坚毅、雅致且谦逊的“回身”,重新阐释了学者小说的写法和意义。小说《民谣》不唯有故事,有情节,更有漫漶的情绪、饱满的情感、翱翔的情怀,其以特殊的调性为当下滞碍的小说创作注入了一脉新鲜的清流。同时,作品中透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展现了作者作为苏人的气质和性情,不仅呈现了江苏东台本土村庄的风貌变迁,更呈现了历史长河中蕴含着的内在精神和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