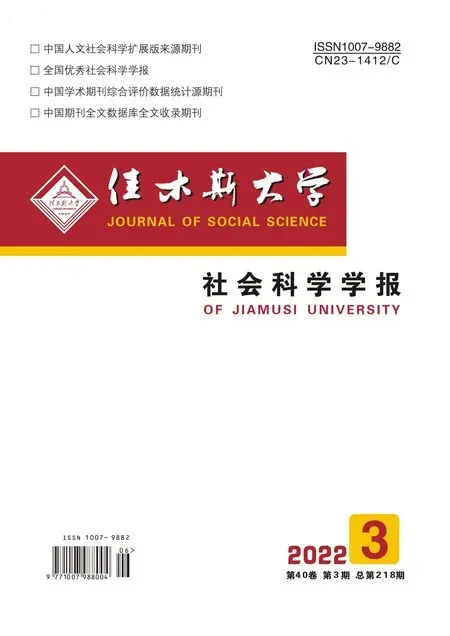后殖民下背景的“孤独”*
——牙买加·琴凯德《我母亲的自传》赏析
陈秋芳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教师教育系,福建 漳州 363000)
现阶段,除了一些著名的非裔女作家和亚裔女作家等,还有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少数族裔作家,便是加勒比裔美国女作家。其曾被殖民者的精力创作出另一个视角,并利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发出抗议的声音,其中,牙买加·琴凯德尤为突出,她利用最坦率、直接的方式控诉殖民主义,并构建出独特的写作风格,其中《我母亲的自传》被称为她最好的作品。
一、后殖民孤儿的独特存在
牙买加·琴凯德是一名著名的美国作家,创作《我母亲的自传》这篇小说的背景以英法前殖民地多米尼克为主,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角度为读者阐述雪拉的经历,描写主人公70多年间痛苦、孤独且传奇的一生,也是一部经典的关注后殖民主题的传叙作品。主人公的遭遇与作者琴凯德在境遇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将其成为是作者的自传叙事书籍,但是从整体层面来分析,琴凯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书中的虚构人物雪拉与作者的现实身份也存在一定的距离,使得故事富有普遍性,可以将其作为每一个后殖民女性的故事,牙买加·琴凯德的小说《我母亲的自传》重点写出一个黑人女性痛苦的人生,主人公没有受到爱情、友情及亲情的爱与眷顾,她独自一人思考自己的生命真谛,主人公的人生也是后殖民时代背景下广大女性的现实映照,作品在虚构与现实的拉扯中彰显了讽喻的力量。
自传叙事类小说的开篇通常以讲述自己的身世开头,《我母亲的自传》的开头便是关于“我”的身世的叙述:“我的母亲生下我就死了”“我的身后总是吹拂着一股凄寒而又晦暗的风”。因缺失母爱,使得“我”在刚出生那一刻便失去了堡垒和庇护,因此形成脆弱无助的心理[1]。母亲也成为雪拉在成长道路中濒临绝望中的一缕光,“我”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在心里描绘出母亲的样貌和脾性,虽然雪拉拥有父亲与继母,以及继母生下的弟弟妹妹,但是雪拉并没有在此环境中获取到应有的亲情。父亲不但没有起到补偿和替代的作用,甚至在雪拉年幼时期,将雪拉交给帮他洗衣服的尤妮丝,雪拉仿佛一件脏衣服或破包裹被主人随意丢弃。雪拉的继母所提供的食物全都长满了霉,发酸发臭,继母将雪拉视为这个重组家庭中的多余之物。雪拉在童年时期可以称之为“孤独”的童年,从没有体会到爱的温度,也从来没有处于被爱的位置上。
因失去亲情的照料与爱护,雪拉在友情上也存在一定的空白。雪拉与很多同学共同上学、学习、放学,但是她并没有收获一个知心的朋友或知己,彼此之间并没有构建出诚信的桥梁,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来源自双亲的指导和教育,父母要求孩子谨记不要轻易给予其他人过分的认可,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他人,书中提到“互相怀疑仅仅是我们彼此怀有的许多心理感觉之一,所有这些感觉都与爱相对,都占据着爱的空间”。雪拉被学校一名男性同学背叛并举报,在此情况下,主人公受到全班同学以及老师的侮辱,而那个被雪拉视为友情的莉莎,却只是一味地欺骗并利用雪拉。
阐述自己的家庭根系是回顾性叙事的重要环节,雪拉也希望可以完整地说明自己母亲的故事,奈何奈拉的母亲也是一个遭遇双亲抛弃的孤儿。雪拉的自传也被称为孤儿的自传,这种自传形式的小说书籍不会追溯过去的寻找与发现,因为过去的内容一片空白。雪拉母亲去世后,留给雪拉的只有面对世界的茫然与无措。在此作品中,除了主人公雪拉是孤儿以外,总欺侮她的尤妮丝乳母的孩子们,与她的境遇不相上下,他们失去了父亲,虽然有母亲的存在,但是她没有为孩子带来一丝一毫的母爱与庇护,在成长过程中母亲的位置始终是空缺的。死亡、驱逐、遗弃全部归属于殖民霸权的影响,这种不正常的后殖民社会导致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与亲近之人、家乡、文化及土地逐渐远离,并在此基础上沦落成没有归属、没有依靠的孤儿。传统自传的书写主题主要注重挖掘家世的渊源并在此基础上书写个体朝向主流群体发展的认同与归属,而《我母亲的自传》则是展开创造性的叙述个人历史,并将其作为自身的造物主。雪拉对于自己身份的确立,这不单单对所有殖民地孤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是殖民地重新塑造自我独立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象征。雪拉缺少亲人的呵护、朋友的关怀以及爱人的眷顾,在文中所描绘出的“我”是无比孤独的,这种孤独也渗透于身体和骨头中,文中提到“我坐在床上,我的心在破碎,我想哭泣,我觉得我是那样的孤独。我觉得危险,觉得恐惧。”这是在父亲家中,一个仅有七岁的女孩对人生和生命的感悟和体会。
二、后殖民境遇下女性的抗拒
拉巴特与其妻子莉莎二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是最普遍且常见的一种殖民地男女关系。雪拉在成年之际,父亲将雪拉视为利益方面的交换物资送给拉巴特先生,但是拉巴特对雪拉的到来毫无感觉,甚至呈现出一种麻木状态,他对贪婪的心理表现出极度热爱和倾向。拉巴特并不想与任何一位女性组建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莉莎通过自己的方法让拉巴特与她结成婚姻,虽然拴住了拉巴特的人,但是他始终不会成为莉莎侵占的“战利品”[2]。莉莎倾尽自己的精力为拉巴特展现自己的爱,但是拉巴特只知道一味地索取,毫无一点回馈的思想。然而在莉莎的生命完全枯竭的阶段中,她想养育一个属于自己和拉巴特二人的孩子,并对这个孩子产生幻想,希望孩子可以对她付出的爱与关怀给予一定的回报。但是她并不具备生育的能力,所以她便萌生了一种邪恶的想法,试图逼迫雪拉帮助她诞下一个拉巴特先生的骨肉。
雪拉与莉莎二人的相识与相知,为雪拉带来唯一一次可以深切体会的友情,但是莉莎不具备生育功能以及她对雪拉的欺骗,这也让雪拉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和命运展开了透彻的认知。这个企图将雪拉作为生育工具替代品的想法,让雪拉呈现出下意识地反抗,雪拉明确知道如果在此环境下诞下生命,自己便会与莉莎一样完全沦陷于物质上、精神上和感情上依托拉巴特的境遇,然而这个男人只是一个攀附物质财产的奴隶,不具备情感和爱的空壳。雪拉在莉莎的影子里显现出自己的未来,而且雪拉并不愿意将一个纯净的生命带到这个没有爱和关怀的社会环境当中。当她察觉到自己怀孕以后,便立刻采用古老的堕胎偏方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通过这种极端、残忍的措施独自更改了命运的安排。并在身体素质恢复差不多后毅然决然的离开了拉巴特家庭,凭借自己的体力劳动支撑着后续的生活。在雪拉依靠劳动养活自己的过程中,她逐渐获取了全新的力量,也明确自己选择的含义,也下定了决心。
雪拉之所以不愿意成为一名母亲,主要原因是她意识到自己没有母亲,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无法为诞生下来的孩子提供应有的母爱和教育,与其让他们生活在如此残酷的世界里,让他们在凌辱和鞭挞的日子里走向死亡,或者如同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生存在孤独的困境中,倒不如将其扼杀在自己的子宫中。雪拉做出的决定没有一丝顾虑,但是在读者的角度看是十分有道理的。在成为“我自己”前,雪拉没有资格成为母亲,然而在成为“我”以后,孕育便成为了一件自然且神圣的事情,雪拉奋力抵抗,也代表着自己未出世的孩子们做出抵抗,其主要原因是为了付出各种代价致力于维护自己可以拥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雪拉拒绝生育的这种举止行为,不单单表现出与现实不合作的态度,其更凸显出对自我民族历史生命的悲壮。
三、黑人女性的困境
因处在父权压迫的社会环境下,性别是歧视的重点要素。雪拉的父亲将她作为一件礼物送给朋友拉巴特,而拉巴特只是一个痴迷于收集财富、积累财富的人,所以,与拉巴特在一起也是一场灾难,他们并没有呈现出爱情该有的原貌,而且在男人的眼里,雪拉及其他女性只不过是一个生育或用来泄欲的工具[3]。男人们因雪拉拥有孕育孩子的生理功能而渴望拥有她,这种情感是不公平的,也正如雪拉所论述的,她不断遭受着来自父亲、情人和白人三方的虐待。被殖民地俘虏的国家将会抹去与原故土相关的一切,多米尼加人并在失去一切的同时还被强制性接受征服者所带来的事物。小说作品中,多米尼加人强忍着白人种族的歧视和侮辱,这便造成其沦入无身份的耻辱和痛苦当中。雪拉在成长过程中第一个会念的字是“大英帝国”,在学校的课堂学习过程中也被强制要求用英语展开交流,因为他们原本的语言被称为“编造的、虚拟的”。
雪拉的老师,本应是一位德高望重、为学生授予启蒙教育的教师,为这些失去关爱的孤儿指引正确的方向,但因其自身为非洲裔种族而时常觉得卑微,并逐渐形成一种厌恶心理。当看见雪拉后,她便看见了失败加勒比劣势种族的各方面特征,并将其认定为邪恶的反派,便在此情况下不断折磨、憎恶、蔑视雪拉,并将她个人对雪拉的负面态度传递给其他学生,在这位老师的不良影响和熏陶下,孤儿学生也逐渐踏上了殖民文化帮凶的不归道路。书中有很多女性人物,无论白人或黑人都成为父权制压迫下的受害人群,遭受着父亲和丈夫的侮辱与虐待。
另外,书中的白人—菲利普的妻子莫伊拉在公众下对雪拉表达了歧视,莫伊拉因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她认为与她有所区别的事物都是可憎可恶的。所以,她棕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以及正宗的英式口音都是她所为之喜爱的,而雪拉是一个可以随时得到的黑人女性。在普遍的白人眼中,黑人女性显示出“性感”“诱惑”的典型象征。生活在黑人女性身份由帝国殖民主义和父权制掌控的环境下,雪拉经历了来自父亲和情人双方的压迫,作为黑人,雪拉被降低至下等人民,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耻辱和偏见。另外,因缺失父爱和母爱,导致雪拉无法认清自己的位置,经历着不知“我是谁”的痛苦时光,所以其自我身份的遗失是雪拉一生的主要基调。
在《我母亲的自传》作品中,雪拉的父亲是一个黑色皮肤却长期佩戴白色面具的人格分裂的人,他虽然是苏格兰与非洲裔的混血,但是他将自己放置于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地位中,拒绝承认自己流淌着被征服者的血液,他戴着虚假的面具度过每一天,面对身边的同胞遭到侵害和凌辱,他并没有显露出一丝怜悯之心和同情之心,但是对那些殖民者却展现出卑微一面,唯命是从。可以将他划分为殖民统治的帮凶和叛徒,他完全丧失了正常人的热情、自由和爱。
四、因民族和历史等原因形成孤独人生
造成雪拉孤独的主要原因来源自民族和历史,雪拉出生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岸,在构建期间分别遭受英国和法国的侵占,现在被称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多米尼克岛国。这部小说作品采用主人公雪拉悲惨的一生描绘着后殖民时代背景下弱势民族群体的记忆痛点,为读者显示出殖民负面的影响和罪恶的一面。雪拉的母亲原是加勒比族裔中其中一分子,在诞生之际便被双亲遗弃,她并不处于征服者地位,也不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没有过去,更是没有未来一说[4]。加勒比族裔的母亲除了自己的身体处在故乡土地之上,其余的所有特征都被完全抹杀。然而站在故土上的双脚也无法支撑她的生命,对于这孤独、悲伤且坠落的生命,父亲在短时间内便消灭了她仅存的生命力。
雪拉的一生充满着压迫和统治,殖民主义使得某部分人群因自己白皙的肤色而占据着主导地位,获取了一切事物,也造成另外一部分具有黑色皮肤的人始终处在低级层次中,并失去了一切。琴凯德通过愤怒和讥嘲的语气写出“一个以他的苍白肤色自豪的男人,无比珍爱他的皮肤”“他的皮肤让他在一切事情上都享有等级方面的特殊优先权”,他们以一种征服者的身份和口吻疯狂压榨并迫害那些被征服者们。琴凯德针对自己出生的地区安提瓜怀着一种爱憎交织的矛盾心理,安提瓜不但缺少抵抗殖民统治的勇气,也无法脱离愚昧落后的状态,在后殖民时代背景下,安提瓜像一张任凭殖民主义乱涂乱画的纸张,呈现出遍体鳞伤的窘态。琴凯德对殖民的屈辱和压迫有着切身的感悟和体会,并极度厌恶殖民者。在琴凯德的小说作品中完全写出了其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以及对故国的哀痛和缅怀,这两种情绪相互交错,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怒火。
琴凯德的作品主要通过愤怒的情绪描绘生命的成长,并重点突出殖民主义征服者和统治者的残酷,她所论述的是长期受到后殖民残酷手段鞭打的人群在后殖民背景下的回忆。由于殖民统治的出现而造成更多的民族濒临沦丧,也造成整个民族中的人民群众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丧失了一个人生来具有的爱的能力,在贫困的生活中彼此伤害,无论是戴着白色面具的父亲,还是自私的继母,亦或是谋求利益的拉巴特先生、莉莎等等,他们都是如此。琴凯德作为一个作品的“局外人”,以一种泰然自若的状态去剖析着书中的一切。
在琴凯德的小说作品中,经典的人物形象会以一种意象化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比如作品中提到的“母亲”便是关键的意象。作品中的“我母亲”与“自传”形成了一个悖论,雪拉的母亲在雪拉出生的时候去世,而“自传”是雪拉七十多年人生的记录和回忆。在此期间,母亲这个角色也可以被象征为被打压和侮辱的弱势群体—加勒比民族,而雪拉的一生只不过在讲述“母亲”在殖民文化中所遭遇的迫害和欺凌。所以,雪拉便决定不会再繁衍出与自己境遇相同的生命[5]。在小说里,“母亲”只是一个空洞的文本,母亲的缺席代表着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缺席,也是为故土的追溯而构造出历史。殖民统治和压迫带给加勒比女性—雪拉难以言表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以一种孤独、残酷的形式彰显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一种愤怒。愤怒是雪拉自我保护和存在的最佳方式,也是她主动出击、自主反抗的方法。琴凯德的愤怒主要来自于对殖民统治和文化侵略的抗议。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分析雪拉面临的困境与孤独,揭示父权制和殖民压迫下给殖民地女性带来的深重灾难。《我母亲的自传》是一部在后殖民历史境遇下针对传统自传叙事的创新,也是一种新颖的自传叙事模式。琴凯德的作品主要关于性别、阶级和种族方面的抵抗文学,这种文学的特点也促使其超越了“女性作家”的标签,促使她的作品更富有批判意义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