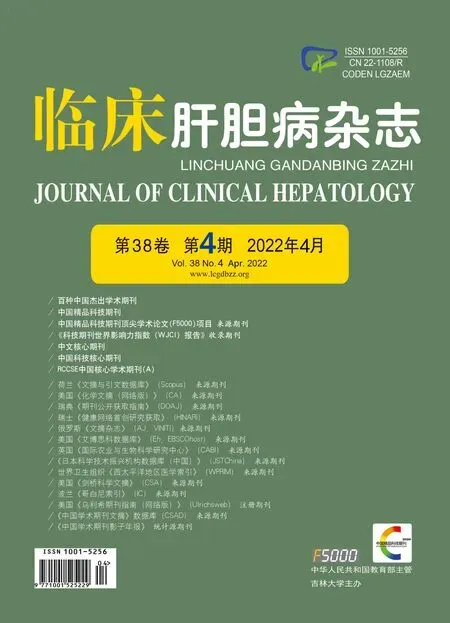后GWAS时代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遗传学研究
邱 方, 王 婵, 张明明, 史兴娟, 刘向东
1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检验科, 南京 210031; 2 扬州大学 转化医学研究院, 江苏 扬州 225009;3 东南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南京 210096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肝内胆汁淤积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常见抗线粒体抗体M2亚型(AMA-M2)阳性,血清生化指标ALP或/和GGT等异常升高。PBC是最早确定自身抗体靶抗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其组织特异性和易于确诊的特点,决定PBC是研究者理解人类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模型。PBC病因至今尚未明确,通常认为是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PBC家系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PBC患者兄弟姐妹相对风险率(λs)高达10.5,同卵双胞胎PBC发病一致率高达0.63,并且发病年龄较一致,表明遗传因素在PBC的发病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几十年来,PBC遗传学研究经历了小规模的家系研究、候选基因研究、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等阶段。继2017年本研究团队发表汉族人群PBC的GWAS分析结果后,全球主要人种的PBC GWAS分析已基本完成[2-5]。近几年,多种群全基因组Meta分析进一步发现,一些PBC易感的相关位点,尤其是针对X染色体的Meta分析,挖掘出多个新的PBC易感基因,对阐明PBC的发病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6-9]。后期GWAS分析将主要针对PBC的不同临床亚型、药物应答以及对系列GWAS数据的精细挖掘,包括药物开发和转录、蛋白、代谢等多组学整合研究。
1 PBC易感性的GWAS研究
GWAS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对数十万到数百万个多态位点(SNP)进行分析,是研究复杂疾病和性状遗传易感性的一种有效手段。2009年起,多国学者相继发表了PBC的GWAS研究结果,所有的研究均表明HLA Ⅱ类基因,尤其是DRB1、DQA1、DQB1基因位点与PBC遗传易感性关联最强[2-5]。欧美团队研究[10-12]表明,采用GWA数据推演的等位基因关联信号主要位于DRB1,包括DRB1*08、DRB1*11、DRB1*13和DRB1*14等。不同于欧美人群中DRB1*08∶01与PBC的强关联性,汉族人群基本没有等位基因DRB1*08∶01,而DRB1*08∶03与PBC紧密关联。此外,DPB1*17∶01是中国汉族人群PBC中又一独立关联位点[13-14]。但相比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PBC患者的HLA关联性相对较弱,70%~80%的PBC患者并未携带HLA区域主要的PBC易感基因[14],这也意味着非HLA区域基因可能在PBC的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共发现了近50个非HLA区域的PBC易感基因位点,多为免疫调节因子和免疫调控信号通路相关的因子,提示HLA基因和非HLA基因协同参与PBC的疾病进程。GWAS研究结果揭示包括JAK-STAT、IL12-IL12R、NF-κB、TLR/TNFα、IL21-IL21R和CCL20-CCR6等多个免疫调节通路与PBC的发病相关。
GAWS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种群PBC的易感基因及位点会有所差异。在欧美白人中发现的22个非HLA区域PBC易感基因中分别有10个和5个在中国汉族人和日本人中被证实。值得关注的是,被认为与PBC发病有密切联系的IL12A在欧美白人和中国汉族人群均有很强关联性,但在日本人中并无显著性,而汉族人群与欧美白人IL12A的易感位点并不相同。日本人的两次PBC GWAS研究发现的3个新的PBC易感基因中POU2AF1仅在日本人中有显著性,而TNFSF15和IKZF3在中国汉族人群中被同样证实是PBC的易感基因[2-5,15]。笔者对中国汉族人群的PBC GWAS研究发现了包括IL21R、IL21、CD58、ARID3A、CD28-CTLA4-ICOS、IL16在内的6个新的PBC易感基因,研究还显示中国汉族人群易感性最强的HLA基因和非HLA基因位点分别位于DRA内含子-1的rs9268644位点和TNFSF15-TNFSF8的rs4979467位点[2]。
2 PBC易感性的后GWAS研究
由于多数PBC患者出现临床症状较晚,多代家系样本较难收集,因此通过大规模家系样本进行PBC的连锁不平衡分析的难度较大。Wang等[16]近期发表了对30个PBC核心家系的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未发现在GWAS找出的易感基因中存在严重的新生突变(de novo mutation),这一结果表明PBC的遗传易感性主要反映在群体中常见多态位点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的免疫稳态的失衡。对近50个PBC易感位点或基因的精细定位和功能SNP的鉴定是目前PBC遗传学研究的重点之一。通过对易感基因功能SNP的分析鉴定,确定功能SNP的调控机制,对研究PBC发病机制有重要的提示作用。目前发现的PBC易感基因TNFSF15、IRF5、IRF8、TYK2、MMEL1-TNFRSF14、IL7R、IL12B、TNFAIP3和IKZF3-ORMDL3等的关联SNP,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现的关联SNP是一致的,说明不同自身免疫疾病的易感性存在共性。同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共同易感基因中,也存在功能SNP的差异。CD28-CTLA4-ICOS位点的SNP与T2D、RA、PSC、MS和PBC等易感性相关,但在这一区域,PBC的关联SNP与其他疾病的关联SNP没有连锁关系,说明CD28-CTLA4-ICOS位点参与PBC发病的作用机制有其特异性[2]。在目前发现的易感基因中,IL21、 IL21R、IL16和ARID3A等不仅表现出种族的特异性,也表现出PBC的疾病特异性,针对这些位点的功能SNP的分析,有助于探讨PBC特异的发病机制。
尽管GWAS研究发现了大量与PBC相关的基因变异,但是还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这些基因变异影响PBC的病理进程。由于对复杂的基因调控网络的理解尚不完善,因此也导致对GWAS结果的解读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将免疫遗传学与免疫表型联接,阐明PBC易感性相关的免疫调控分子在其发病及病理进程中的作用。目前基于GWAS研究取得的数据,一些具有PBC典型血清学、生化和组织学特征的基因敲除动物模式如IL12 p35-/-、IL12 p19-/-和dnTGFBRII小鼠模型被建立,并在PBC的免疫病理机制研究方面取得很有价值的成果[13]。
3 PBC特定亚型和表征的GWAS研究
与其他自身免疫疾病相比,PBC表现出疾病的组织特异性,但其临床表症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PBC患者在发病年龄、起病表症、疾病进程和治疗效果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目前95%以上的PBC患者AMA-M2阳性,在<5%的AMA-M2阴性的PBC中,可能有部分患者是AMA弱阳性,或仅识别目前AMA-M2抗原中被掩盖了的表位,或完全是AMA阴性。对AMA完全阴性的患者,PBC的发病机制与阳性患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但目前要收集到大量的AMA完全阴性的患者进行GWAS分析,有很大的难度,需要从数十万的PBC患者中加以甄别,要完成这样的分析,需要大规模的协作。除AMA-M2外,PBC患者还出现PBC特异的抗核抗体,主要是抗gp210抗体和抗sp100抗体,二者的阳性率分别为30%~40%和20%~35%。抗gp210抗体仅识别gp210的C末端突出到细胞质的部分,目前尚不确定抗gp210抗体是否仅识别单一表位。抗sp100抗体识别多个抗原表位,包括线性和构象表位。Wang等[17]对抗sp100抗体阳性组和阴性组的GWAS队列分析发现,MHC区域的rs1794280和rs492899位点与抗sp100抗体相关联,并鉴定出HLA DRβ1-Asn77/Arg74、DRβ1-Ser37、DPβ1-Lys65是决定抗sp100抗体产生的关键位点,该结果揭示抗sp100抗体具有强烈的遗传倾向,其产生与HLA分子对sp100表位的呈递密切相关,提示分子模拟可能是抗sp100抗体产生的原因。但对抗gp210抗体阳性组和阴性组的GWAS队列分析未发现任何显著的SNP位点。目前抗gp210抗体是如何产生的尚不清楚,但抗gp210抗体阳性患者在临床表征和熊去氧胆酸(UDCA)治疗的应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抗gp210抗体的产生机制对PBC的有效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
PBC患者在AMA抗体产生、发病年龄、发病表征、无药物干预的疾病进展,UDCA治疗的药物应答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和个体差异,针对这一系列异质性的GWAS分析有助于了解PBC的发病机制和个性化的治疗。这类研究工作需要建立在大规模临床样品和正确、可靠的临床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目前针对特定PBC亚型的分析已在国内外的部分实验室展开。
4 基于GWAS数据的药物开发
GWAS研究结果揭示了多个与PBC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的信号通路,为治疗PBC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潜在的靶点。单克隆抗体优特克诺(ustekinumab)的靶向位点是IL12/23 p40亚单位,可作用于IL12/Th1和IL23/Th17通路,但在一项对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良的PBC患者应用优特克诺治疗的临床试验中,没有患者在Ⅱ期临床试验中达到预定主要生化应答终点[18]。PBC患者激活的T淋巴细胞靶向针对肝内胆管,用CTLA-4抗体阻断CD80/CD86可能具有治疗作用。阿巴西普(abatacept)是CTLA4分子的细胞外功能区,与人IgG的Fc段结合而成的可溶性融合蛋白,但目前临床试验采用阿巴西普联合UDCA治疗UDCA应答不良的患者,发现阿巴西普联合UDCA治疗并不能改善生化应答和临床疗效[19]。在PBC的易感基因中,与TNFα信号通路相关的有TNFRSF1A、DENND15、TNFAIP2,目前已证实TNFα抑制剂在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中有明显的疗效,但是否对UDCA治疗效果不佳的PBC患者具有疗效尚不明确。利妥昔单抗(rituximab)是B淋巴细胞表面分子CD20的嵌合型抗体,初步临床试验已证实利妥昔单抗可以明显降低UDCA无应答PBC患者体内的自身抗体水平,但对PBC的疗效非常有限[20]。Moritoki等[21]认为可能的原因是患者出现针对利妥昔单抗的抗体(anti-drug antibodies,ADA)和研究中纳入的UDCA疗效不佳(难治型)的PBC患者比例较高。鉴于此,Moritoki等[21]通过小鼠PBC模型发现,抗CD20抗体治疗需要在PBC发病的早期进行,才能广泛抑制PBC的效应通路,但对产生ADA的小鼠,治疗效果有限。Cordell等[9]基于PBC的GWAS数据的分析结合计算机生物学技术的药效分析,建议将多个针对GWAS靶向基因或位点的单克隆抗体或小分子药物作为潜在的PBC治疗药物。期待后期的动物实验和临床测试能够为PBC的治疗提供更多的手段。
综上所述,尽管PBC的遗传学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与多数复杂性疾病遗传学研究面临一样的困境,即不能有效地解析遗传变异如何调控效应蛋白表达,效应蛋白分子又如何对细胞、组织产生影响,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近年来基于GWAS结果,开发的多个针对PBC治疗单抗药物临床试验结果均不理想,可能是目前困境的具体表现。随着多组学整合研究的深入,单细胞测序和代谢分析等研究手段的发展和普及,必然将PBC的遗传易感性跟分子病理机制紧密联接,为PBC的遗传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邱方、王婵、张明明负责完成初稿撰写;史兴娟负责初稿的修订;刘向东负责文章的思路、审核及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