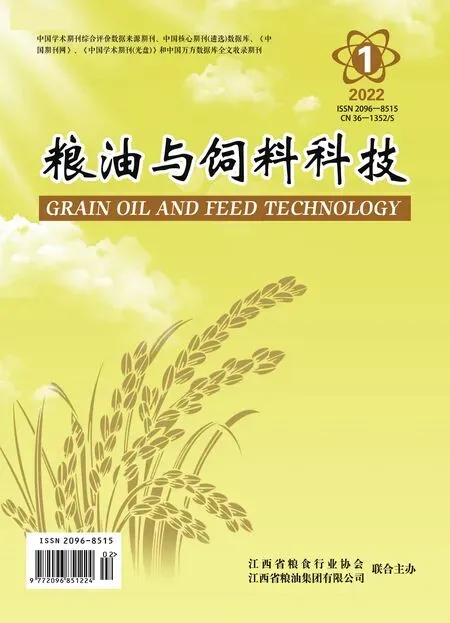我与稻米的情结
王水良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种的是稻谷,吃的是稻米,稻米伴我成长,相比于城里人,对稻米的情结我更亲、更深、更浓。
我出生于1966年,极其匮乏的物质生活伴随我度过了儿童、少年的美好时光。虽然我未曾经历过饥荒年代,但吃不饱、穿不暖的艰难时日却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时代记忆。
在生产队期间,由于家里男劳力少,就我父亲一人,家中吃饭人口有8人之多(父母和6个小孩),虽然有三个姐姐能上生产队挣点工分,但毕竟是女工,挣得工分比男工少,每到年底全队决算时全家人一年辛苦下来挣得的工分总是入不敷出,年年都是超支户。超支户,年内分得粮食少,还得从案中倒拿钱到生产队上去。尽管我母亲很能干,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最难过的莫过于每年上半年5月至7月青黄不接的缺粮季,要度过这段时期,办法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借粮”,向生产队借,或是向亲戚、邻居等借;另外一个就是吃杂粮度日。杂粮中吃得最多是红薯。有时一天要吃两餐红薯稀饭,稀饭易饱,但不经饿。没有稻米的时日是难熬的,忍饥挨饿的日子是痛苦的,有时还是很尴尬的。时至今日我对饥饿还存有深深的恐惧感。“多挣工分、多打稻谷”成为我儿时的最大梦想。毕竟“民以食为天”,千事万事吃饱饭是头等大事。
1982年分田到户了,按1000m2/人的标准,我家分得0.8hm2田。父亲很高兴,因为我家从此不再做超支户了。那时种水稻成本较低,产量也不高,平均250~300kg/667m2。一年两季下来,我家能产稻谷5500kg左右,除去交公粮、定购粮外,剩余的粮食可作种子粮、口粮、饲料粮等,口粮年年有余。分田到户的政策,解放了农民的劳动生产力,解决了种粮农民吃不饱饭的大难题。
父亲虽然体型有些瘦,但不弱,做起农活是个精干的行家里手,浸种、育秧、栽禾、打药、收割、做田等诸多农事样样在行。作为家中的长子,我从小就担当着父亲的小帮手,协助父亲完成各项农活。在缺少机械的时代,大多农活都是繁重的体力活,干农活头顶烈日时间长。一年中最辛苦的时候要数每年的“双抢”季,早稻要及时收割、整晒、收仓入库,晚稻又要马上栽下去,这段时期天气又特别热,太阳又特别毒辣,在太阳下炙烤劳作的人们一天都不知道要出多少汗、湿多少身衣服。“春争日夏争时”,要争分夺秒地去劳作,每天天不亮就要下田,晚上要做到八九点才能收工,中午偶尔可休息2h左右,如果天公不作美,中午都不得休息,要到晒场去收稻谷,以免稻谷被雨浸湿发芽。休息时间少,劳动强度大,许多人经过一个“双抢”季的折腾,轻则消瘦一圈,重则要病一场,最轻的要数我们这些农家的学生娃们,一个暑假下来,每年都是白皮肤回村,黑皮肤返校。“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粒粒粮食都是农民滴滴汗水的结晶。
在未有外出打工之前,农民主要的劳作范围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种粮是全家的主业和主营收入,养猪、鱼和些许家禽等就是全家的副业和副业收入,卖粮的收入是我读书经费的主要来源,种粮支持着我顺利完成学业。
到粮管所交粮那时是全家的大事,每到交粮季我都会陪同父亲一道去交粮,一则是当当父亲的下手,另则可打打牙祭,能吃着平时难以吃着的包子和馒头。交粮最难熬的是排队,最恐慌的是交过夜粮。我父亲是个地道农民,老实、本分,拉去卖的粮都是挑家中最好的稻谷:水分低,谷粒饱满,杂质少。在我的记忆中,我家交粮一般都比较顺利,但偶尔也交过过夜粮,在粮管所自家谷包上数过星星。交过夜粮是难熬的,一方面晚上太热,二是蚊子叮得难受,最担心的是怕露水、地面返潮和晚上下雨,这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天交售稻谷的水分,如果水分不达标就得在粮管所翻晒稻谷。好在老实人不吃亏,交过夜粮时我家从未发生过第二天翻晒稻谷的事故。当交过夜粮时,我也曾幻想过,如果上级能出台不留过夜粮的便农举措,该多好!多年后终于盼来了这一便民举措,我对此从心底里是一百个赞成。正因为我知道农民交粮的不易,后来工作了,有幸每年战斗在收粮一线,能直接服务粮农,我都很珍惜,工作间隙或工作之余,都会尽可能为粮农提供些帮助,或抬包,或帮助老弱粮农扛包,或帮助过风等等,虽然在收粮期间的我很辛苦,但我更知道农民交粮的不易,帮助粮农我义不容辞,这也是我农家子弟的本分。
交粮最有趣的是发生在1986年,当时高考刚结束,粮管所的工作人员平时都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就开玩笑地说,你以后有可能会做我们的领导,不能得罪你,所里还破天荒邀请我与他们一同用餐。最后我真的被江西粮校录取,1988年分配到县粮食局机关,成了基层粮管所的直接管理者。
在粮校学习期间,我对稻米有了全新的认识。了解了它作为主食的营养成分,了解了它属国家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了解了它的储藏特性,了解了它的商品特性。如果说作为农家子弟之时的我对稻米的了解只是开了一扇窗,那通过粮校的学习对稻米的了解可说是敞开了大门。角色不同了,关注点也不同了。原先只关注产得好、售得出,是单环节的问题,现在关注的是收得到、收得好、储得好、售得好,是全产业链的问题。
1988年9月我从江西粮校毕业直接分配到横峰县粮食局工作,从“农村人”变成了真正的“粮食人”,以“粮食人”的身份再次与稻米结缘。在局机关从事过购销、物价、计统等岗位,从科员一步步干到副局长,30多年从未离开过粮食行业,一直在从事着“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管住、管好“天下粮仓”的工作。我想稻米作为粮食流通行业的传统产业,也是我们南方地区的最大宗粮食商品,如何传承好、呵护好,需要我们“粮食人”去坚守。无论历史的轮回,还是市场的波动,无论机构怎么变化,我们“粮食人”都要始终不渝地去坚守粮食这块阵地,因为只有坚守,才有希望,这也是我们粮食人应该有的信念和应该承担的责任。
虽然我从“农村人”变成了“粮食人”,身份变了,角色变了,但我身上的泥土气味从未改变过。父亲当家时,每年我都会抽空回到家一如既往地当父亲的大帮手,做各种农活,见事做事,乡亲们都夸我“未忘本”。后来父亲退居“二线”后,弟弟长大当家了,他们以外出务工为主,家中的田地都被他人承租了,我回家做农活就少了。由于种田收益少,外出务工收益多,农民纷纷外出务工,在家全职种田的少了,田地撂荒也在所难免。
2002年,为了推动乡亲们种粮,我在产粮大乡莲荷乡莲荷村承包了8hm2农田。从选种、浸种、耕地、插秧、耕田、施肥、收割等环节,实行精细化管理,稻谷产量高、收成好,许多种田的老把式都当面夸我,说我有两手,每亩田的稻谷产量平均达550kg。虽然地处丘陵地区,机械化程度不高,加上当时插秧全靠人工,种植成本高,但最终每亩年纯利润也达到了580元。由于当地人看到我种稻谷能赚钱,第二年老乡擅自毁约不再出租稻田,从此我的种粮梦没能延续。
田地的撂荒、农民无端践踏田地,常常会使我感到痛心疾首,但最让我扼腕叹息的是对稻米的无端浪费,饭桌上、垃圾桶里,白花花的米饭赫然可见。微观地看,可能在某些地区,某些人眼里,稻米再不是奢侈而难求的,有时甚至是多余的,然而从宏观的地域角度来看,也许在世界某个角落,温饱还是难题;从时间角度来看,粮食更不是永远可以一直充足的。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同时也是个农业大国,多年的粮食工作实践经验无时无刻不在警示着我们:中国的粮食少不得一点,所以请珍惜种粮的田地,请珍惜手中的粮食!
稻米,从我一出生就开始与您结缘,从“农村人”到“粮食人”,一路走来,平平淡淡,实实在在,这兴许就是一种缘分和永远忘不了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