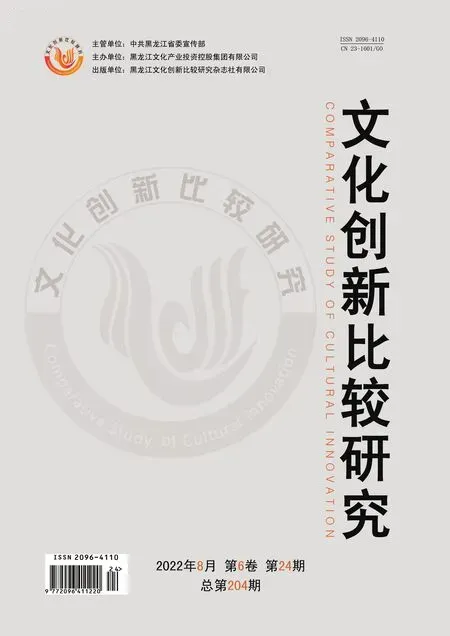狂欢式表达:从戏谑到认知镜像建构
——重读米兰·昆德拉《玩笑》
何卫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400030)
1967年, 米兰·昆德拉出版了历时三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无一例外引起了又一次轰动,在欧洲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一部政治小说。从表面上看, 小说包含了昆德拉小说的所有特征, 如隐喻、音乐的叙述节奏、基本词的使用、背叛主题、孤独意识及“梦境叙事”等。若从情节架构来考察,就可以发现随着叙事的展开, 主要线索是主人公路德维克的命运沉浮变迁和情感波澜呈现出 “升-降-升……”的结构走向,并且形象多重性和诙谐的风格反复出现,显现出文本的独特之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让狂欢化在小说中发挥核心的作用, 并将其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表达。
狂欢化和其体现典型的加脱冕结构, 由俄国文论家米哈伊尔·马赫金提出。他从历史诗学的角度对狂欢体文学在欧洲的历史形成、 发展过程及特点进行研究。 认为狂欢式,即狂欢节的生活,深刻影响人类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精神领域, 对文学更是存在关键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就属于狂欢体这一体裁,是狂欢体的变体。这种文学中的狂欢化,其显著表现是加、脱冕仪式及其象征性、诙谐和戏谑的特征、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复调性等。巴赫金列举关于狂欢化的所有一般特征,如人们之间随便、自由不拘的接触、语言、大笑、庆贺、游艺的路线、易位和换装等,其中,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影响的,就是加冕脱冕的仪式,即狂欢国王戏谑地被脱冕随后再被加冕, 而小丑即位加冕当了狂欢节的国王,后来又被剥夺王位脱冕这样一个转换过程。这样一个降格或易位的过程可以是循环往复的。“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 ”[1]
从狂欢的角度进行解读, 在昆德拉小说的智慧中,不仅存在着“文类的复调性”,即将各类不同的文体,诸如哲学(论文)、评述、故事、寓言、散文、通信等统一在一个文本之中, 以不断变换的多种视角去展现存在[2],还表现出明显的狂欢式倾向,作为隐性的叙事进程。这一点在《玩笑》中体现在:运用加脱冕型结构形成叙述线索的推进和逆转, 建构起人物形象的两重性,围绕着幽默讽刺的氛围,来表达狂欢的世界感受。
1 狂欢式结构
《玩笑》的主要叙事构架是主人公路德维克的命运进程, 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是他经历中的数次升降格、易位和换装,本文且称为主脱冕结构,除此之外并存着另外3 个局部而相互平行的脱冕型结构,表现在路德维克的3 次感情历程中, 将这3 个较小的脱冕型结构称为“次脱冕型结构”,它们一起构成了文本的叙事框架。
1.1 主脱冕型结构:路德维克的命运进程
《玩笑》采用的是线性的时间顺序叙事。 小说在3 天的时间范围内展开, 事件几乎是按照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单元来进行, 其中又不断穿插着人物以回忆的形式对于过去的回顾, 时间跨度达到了几十年。视点虽围绕在几个不同的人物身上,但主要的中心事件还是讲述了一个玩笑,并由一个玩笑,又繁衍出一串串的玩笑, 这些玩笑均是在主人公路德维克身上发生的。
在1948年2月, 当20 岁的路德维克给他的恋人玛凯塔寄了一张写着“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气。 托洛茨基万岁! ”的政治玩笑明信片后, 大祸临身, 立即被解除了在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勒令退学。他的命运从此改变,成了一个偏远地区兵营的成员,其实也就是苦役犯。在路德维克一生的历程中,这是他所遭遇的第一次脱冕,他由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二年级党员学生干部,易位为一名众叛亲离的苦役犯, 狂欢节的国王换装成了“小丑”。经过漫长的降格化处理,生活的现实和感悟给十七年之后的路德维克重新加冕,“我觉得我的一辈子,从头到尾,充满了皮影人和皮影物,而现实本身反倒没有它应有的地位。……时至今日,报仇雪恨已经成了充饥的空想,自己孤家寡人的信仰,一个和当年的各个参与者越来越不相干的神话。 ……我一面切着盘子里那块大大的裹着面糊的肉块, 一面听着那伤感的、隐隐的‘咳呀、咳呀’的声音飘荡在村子房屋上空, 我的脑海里又出现戴着面具的国王和他的马队, 不禁为人类行为的不可理喻而感动”,伴随着众王马队的游行及至终点的伴音, 路德维克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一生由明信片玩笑开场, 又引出许多牵涉众人的糟糕玩笑,是实实在在的,属于历史的范畴,不涉及对错的程序本身,任何人无权收回,寻求解脱、复仇也是枉然。 “到了这时,我明白了,我根本无法取消我自己的这个玩笑,因为我就是我,我的生活是被囊括在一个极大的(我无法赶上的)玩笑之中,而且丝毫不能逆转。 ”[3]这时的路德维克,与装扮成国王的雅洛斯拉夫的年轻儿子符拉迪米尔一样,重新加冕,再次戴上国王的面具,化装舞会结束。
文本的基本叙述框架建立在这种脱冕—加冕型结构之上。 路德维克,这个狂欢节之王,其地位的升降浮沉、命运的转折腾挪、情感的波澜周折、心灵的煎熬超越,均附着在这个狂欢载体上面。伴随着换装和易位的循环,主人公置身于一个新的处境,地位与命运迅速改变,情节得以继续发展,闭环的结构走向开放,显现出狂欢节交替更新的精神。
1.2 次脱冕型结构:路德维克的3 次感情历程
在主人公路德维克这个主脱冕型结构之外,文本另外还设置了3 个次要而相互平行的脱冕型结构,体现在路德维克的3 次情感历程中。 本文把这3个局部的脱冕型结构称为“次脱冕型结构”。
学生时代的玛凯塔是路德维克的初恋, 但是由于她的“幽默不协调”,将他政治性玩笑的明信片公布出去,这种类似出卖的行为,致使他“在生活中第一次沉了船”。 正是这种行为,将路德维克对于玛凯塔的印象由一个体贴、美丽的“王后”降格成一个冷酷令人不快的“小丑”。 他第二段感情是他在兵营生活中遇到的唯一“绿色”,露茜成为他心灵的慰藉。即使她从来没有满足他作为男人最基本的需求, 但他总是对她怀有最美好和最强烈的情感。 随着视角的加深,显露出来一个真正的露茜:在少女时代与一群流氓少年长期厮混的心影阴影, 一直影响露茜的生活。而这种形象的转变,在路德维克看来也是一种形象的降格和易位,直至她选择与考茨卡同居,成为一名理发师后,他们之间从此形同陌路,则是她脱冕的完成。第三段感情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路德维克为了报复将自己开除出组织和大学的泽马内克, 他主动并故意勾引其妻子埃莱娜疯狂爱上他, 在他自认为得手以后, 并且沉浸在这种报复的畅快感之时他并不知道, 此时的泽马内克已经喜欢上一个叫波洛佐娃的新欢。 而埃莱娜已经被排除在泽马内克的情感世界之外了。 当路德维克发现这点后,无尽的失望、懊恼一起向他袭来, 尴尬之中他犹如一个从神坛中跌落的茫然“小丑”。 特别是埃莱娜寻求自杀(未遂)后,他更是承受着内心无尽的折磨。在这个复仇的玩笑中,路德维克由复仇的“王子”换位成徒劳的“傻瓜”,使用了降格和易位处理手法。
可见,一个主脱冕型结构,再加上3 个次脱冕型结构,共同支撑整个文本,将路德维克的生活、情感、思想画面完整展现出来。
2 形象的两重性
《玩笑》是以特定的环境时代作为背景的,透露出主人公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冗繁的哲理性思考,其中一些形而上的思索意义十分深远。但是,思想讨论似乎是模棱两可的, 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和统一的答案。路德维克的苦闷和烦恼两方面,既有他自己的挫折、降格,也有与恋人的复杂关系,体现了狂欢化结构中人物形象的两重性和象征意义。
路德维克的生活,充斥了种种玩笑。这些玩笑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狂欢游行。生活把他抛上高空,装扮成“国王”,又把他摔向谷底,易位为“小丑”。如此反复,完成一次次地加脱冕仪式,展现了他非同寻常的经历。这种与常规生活相异的生活方式,打破了所有构成常规生活的必然因素。 而这种超乎正常的生活最初因玩笑引发,最后也由玩笑结束。在他的身上结合了嬗变与危机两个极端。 明信片玩笑使他由“国王”脱冕为“小丑”,这既有悲剧性,又有一定喜剧性。 他聪明,能说会道,才华横溢,鹤立鸡群;他愚蠢,爱开玩笑,冒当时环境之大不韪,作茧自缚。脱下“面具”之后的路德维克,又经历了多重的玩笑而完成了加冕的逆转。这其中,那张可怕的明信片玩笑是一个转折,代表了“换装”的节点。要不然他的生活将按部就班地走下去,或许像泽马内克那样,前程无量。在这狂欢游行的叙事场中,路德维克被赋予了聪明的“傻瓜”、悲剧的“小丑”的特性,后来又成为理性的“智者”、真理的“国王”。现实的格格不入引导其进行深入的思考,既是对本质的叩问,又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投降。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偶然性,又蕴含必然性, 路德维克的形象便建立在这既肯定又否定的二合一复合体中。
他的两个最爱,玛凯塔和露茜,身兼高贵与低俗的两重性,一个外表十分可爱却是一个告密者,一个被赋予最纯洁的理念却实际上阅历无数男人。 她们实际上是美与丑、希望与绝望的混合。从起点又回到开始的地方, 这就是命运给他开的两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借助于狂欢化结构中降格处理的力量,文本展示了现实中更深的层次和更重要的方面。
有意思的是, 路德维克与他的两个最爱最终都没有肌肤之亲, 反而他带着玩笑心态搞到手的埃莱娜却狂热地爱上了他。埃莱娜之于路德维克,包含了玩弄与想念、厌弃与同情的两重性,并最后使他重新加冕,达到了狂欢化感受的认知。 在这点上,巴赫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脱冕型各形象中失去了狂欢式的两重性, 那么这些形象便要蜕化为道德方面或社会政治方面的一种完全否定的揭露, 变成单一的层次,丧失自己的艺术性质而转化为单纯的政论。 ”这种形象两重性的意义,是为了表现尼采所言的“永劫回归”的思想。
3 讽刺戏谑:狂欢感受的回声
昆德拉的小说都有着严肃的主题, 但常常用戏谑和幽默的处理方式使其变得喜剧化。《玩笑》中,路德维克的命运肇始于一个无意义的玩笑, 这个玩笑却有意义地造就了他一生的悲剧。 他最终陷入由无意义报复导致的尴尬境地是值得讥讽的, 但大笑之后, 人们会不由得对由一张明信片中的无意识政治玩笑演变的一连串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后果进行反思——在“极权政治”横行的特定时代里对人尊严的极端藐视显得多么荒谬可笑和残酷, 而这恰恰是作家意欲通过戏谑和讽刺揭示给读者的真相。最后尽管路德维克仍然处在由玩笑造成的实实在在的困境之中,但他认识到,那个时代的严肃本质上不过是滑稽,细节上的严肃是以总体的玩笑为基础的。这样一来,精神上的痛苦得到释放,历史的庄严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滑稽和幽默与严肃平行,是针对世界、历史,针对全部社会和世界观的。
戏谑幽默与狂欢式存在着密切联系。 据巴赫金考证, 狂欢节在中世纪大城市持续时间达3 个月之久,狂欢节的广场上全民参与,暂时取消了人们的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的一些规范和禁令,人与人之间变得亲昵起来。 人们努力摆脱自己的身份,从狂欢节诙谐和幽默的角度,从狂欢式世界感受的角度去观察和表现世界。这是一种既现实,又理想的特殊生活方式,处于生活和艺术的交界线上。这种诙谐和幽默对多样性和变化性的感受永远保持活力,它涉及不断变化的四季、日月相位、草木荣枯等。这是全民性的喜剧和盛宴。 它与自由保持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 反映了人们追求身心的自由和解放的本性。人们在笑声中回到自身,并进入乌托邦的自由王国[4]。国内学者对小说的戏谑和严肃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详尽阐述。 认为狂欢式诙谐是一种特殊的、包罗万象地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切入生活的另一种表达, 世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有诙谐才力所能及。 滑稽的本质是严肃,它与严肃同等重要[5]。
昆德拉选择用喜剧的幽默形式构成其哲理小说的外壳,这是一种智者的狂欢式彻悟。他主张小说的基本精神就是幽默戏谑,“小说并非诞生于理论精神,而是诞生于幽默精神” 。小说的娱乐性与严肃性同等重要。 认为相较于悲剧,喜剧更加残酷。 前者向读者展示安慰和幻景, 而诙谐和幽默揭示不为人知的区域。与严肃性一样,历史有着喜剧性的一面[6]。在分析了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后,作家继续指出,不能信任悲剧,要把悲剧的帷幕撕裂,只有幽默和笑能够照亮生命的本质[7]。
4 认知镜像建构
戏谑幽默与形象两重性是狂欢式一个重要表现,而加冕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世界感受这个核心所在, 它蕴涵了交替和变更、 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狂欢理论认为,人们存在着两种生活的概念,一种是日常、正规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式,即狂欢节的生活。这两种生活贯穿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它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 “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礼仪、形式的总和)的问题,实质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的深刻根源, 包括在阶级社会中的发展, 以及异常的生命力和不衰的魅力——这一切构成文化史上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 之所以说这种狂欢式世界感受根植于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 是在考察分析希腊罗马、 中世纪、文艺复兴及以后各阶段的文学发展后,巴赫金指出狂欢化逐渐融入欧洲各民族的生活和语言之中,认为语言中整个层次和各个方面都渗透了亲昵的广场语言和狂欢体的世界感受。 在这狂欢式世界感受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复杂的文艺复兴世界观。时至现在,狂欢化成为文学的一种传统,也成为文学体裁的一种传统。 “狂欢化有构筑体裁的作用,即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和艺术思维中, 便出现了一些作为标志的狂欢式。
狂欢节庆活动彰显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内核,建构起小说基本的表述路径。 从时空体叙事学理论来说,狂欢节庆活动与时间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并且被置于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意义上来认识。“正是认知化了的题材构成了最初的叙事草案类型”[8], 也构成了最初的叙事脚本。“认知化了的题材”即“狂欢节广场的狂欢”。 它是严肃的,蕴含着一种对对象的认知形式,“有真正深刻的东西”。 通过这种认知形式,形成叙事场上的时间和空间。 狂欢式叙事的实质是耕植于文化历史传统之上的认知方式,加脱冕型结构、模糊性和戏谑讽刺正是这种狂欢的世界感受的投射, 在文本中则内化为叙事者认知图式中建构的文化的历史镜像。通过对这种历史镜像的解码,可以重塑文本文化结构和历史认知语境。
5 结语
作为“存在的勘探者”, 米兰·昆德拉以其独特的小说方式和艺术特质, 形成多维的艺术个性与不同情感空间的并列, 最终指向对存在的多向度思索。《玩笑》中,路德维克的生活的换位推动着情节发展,丰富其叙述维度,引导故事由此走向高潮,建立起小说的狂欢式表达。 正是借助于这种历史文化镜像形式, 作家显现的是他洞悉人的存在和世界形式的哲学思考,以此审视生命的轮回,展露他深藏于心的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