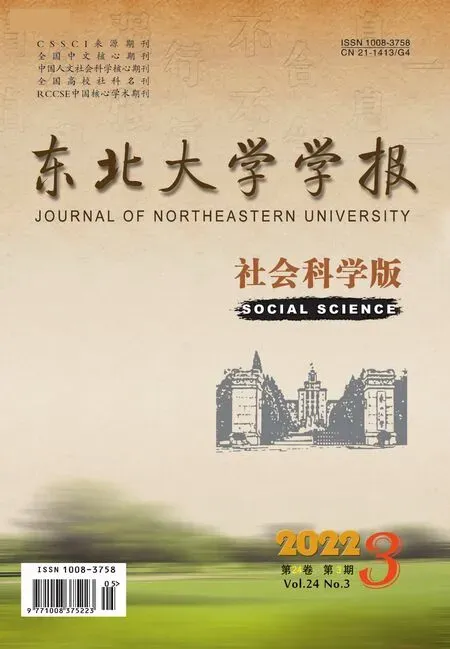论视觉体验中的“虚拟在场”及其存在论意义
索 引, 文成伟
(1.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2.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理想中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简称VR)技术涉及与身体多感官的协同交互体验, 但由于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现阶段较为普及的VR 技术应用仍然是以视觉体验为主导, 其他如听觉和触觉体验等在其中多为辅助性因素, 而嗅觉和味觉等方面的体验则尚未成熟。 然而,由于人所接收到的外部信息80%以上都来源于视觉, 视觉模拟的逼真程度对于VR体验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1], 即便现有的VR技术不够理想, 其确实已经能够给人带来相当程度的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 或者说一种仿佛自己“在那里”, 置身于那个虚拟环境之中的“在场”(presence)感受。那么,VR环境中的视觉体验究竟如何影响了这种“虚拟在场”的形成? 以及这种“虚拟在场”是否具有存在论层面的意义? 这将成为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
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 Gibson)的生态光学(ecological optics)理论与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现象学思想展开相关论证。虽然吉布森的理论并非专门的现象学理论,但其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有着十分相似的精神内核,即对身体知觉重要性的强调。正如斯科特·里士满(Scott C. Richmond)指出,吉布森和梅洛-庞蒂都“旨在将知觉作为一种现象层面的运作,进而对其进行整体的理解……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知觉是感知者与世界之间的一个持续的、相关的术语”[2]。国内学者薛少华同样认为吉布森与梅洛-庞蒂的理论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即反对知觉研究的二元论立场,而强调知觉与行动之间的耦合性[3]。从这种以身体或肉身知觉为核心的视角出发,将可以看到,VR环境中的视觉体验并非一种孤立的感觉活动,也并非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审视,而是发生在人以身体的方式与VR环境的动态交互之中,牵涉着人与VR环境所构成的一种相互纠缠、交织的存在关系。这种视觉体验既涉及VR环境对感知者的显现方式,也关系到感知者对VR环境的视看方式。这两方面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共同促进了“虚拟在场”现象的形成,并使得这一现象具有了一种存在论层面的意义。
一、 VR环境对感知者的显现
虚拟现实的视觉体验,首先关涉到VR环境对感知者的显现方式,这种显现方式对“虚拟在场”现象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从吉布森的生态光学视角来看,VR光环境对感知者的显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环绕光”(ambient light)信息的模拟还原呈现,而这种呈现方式使人与VR环境不再处于经验主体和经验客体对象间的对立关系,能影响感知者的自我在场知觉,增强感知者的“在场”沉浸感。VR技术对于现实环境模拟的逼真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充分地还原出现实环境中环绕在我们周围的光线信息。例如,“光场”(light field)技术,被认为是未来VR技术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目的就是通过在VR环境中尽可能地还原呈现出三维世界中完备的光场信息,从而使感知者获得相应的三维立体视觉[4-5]。对此,从生态光学的角度看,在VR环境中模拟出人在光场中所知觉到的这些光线,恰恰如同模拟吉布森所谓的“环绕光”,也就是三维世界中,环绕在我们周围,并被人实际知觉到的光信息。“环绕光”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辐射光,而是光照所映射的环境在感知者的身体知觉层面的具体呈现状况,它是“对原初的知觉世界特征进行描述所获得的内容”[6]106。“环绕光无法就其自身而言构成环境。对于吉布森来说,环境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它首先是针对某个知觉者和行为者而言的环境。”[6]108可见,吉布森通过“环绕光”的概念,实际上反对人与环境之间基于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对立关系。人并非处在环境的对立面,而总是处于一个具体的环境之中;环境也并非是一个绝对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是人所知觉到的实际具身性环境,并伴随着人的身体活动,在知觉现象层面显现出相应的变化。人与环境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这种不可分割性能够直接体现在环境向人显现的光信息的变化中。在VR环境中,模拟光信息具有与环绕光类似的显现特征,而这些显现特征能够使感知者对自身存在的知觉和对所处环境的知觉相互关联、相互协调,消解人与VR环境间的对立,以此增强感知者的“在场”沉浸体验。
首先,在VR模拟环绕光的显现中,光结构具有梯度(gradients)变化特征,其能够使感知者知觉到内在自身与外在环境的延伸关系,从而打破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对立。例如,从吉布森的视角来看,距离信息可以通过有关地面延伸的光信息而具有可见性,并体现在地面特征之尺寸大小与纹理密度的梯度变化中。这种梯度变化在远端方向的地平线处到达极限,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则以感知者的鼻子、四肢等身体部位所显现的位置为近端的界限[7]109-110。这意味着,在视觉经验上,这种光结构的梯度变化使感知者以虚拟化身(avatar)的方式所处的“这里”与VR环境中其他事物所处的“那里”,在一个连续的表面布局上构成了一种相互延伸的补足关系,从而打破了感知者内在自我与外在环境间的界线,消解了二者的对立,增强了二者的协同关系。在这方面,大卫·惠廷希尔(David M. Whittinghill)等[8]和卡罗琳·维恩里奇(Carolin Wienrich)等[9]所做的“虚拟鼻子”实验,可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支持了上述观点。实验通过在被试者的VR视觉场中添加一个虚拟的鼻子,减轻了被试者在VR体验中的眩晕感,增强了他们的适应性。从生态光学的角度看,虚拟鼻子的加入使得VR显示中的光信息更符合人在正常视觉下所感知到的环绕光结构,而且虚拟鼻子的位置实际上是视觉立体角(visual solid angles)所能呈现出的可能的最大化位置,其在光结构的梯度变化中,代表了有关距离的绝对“零点”,代表着被试者自身所在的位置。以此零点为基准,被试者能够以更自然的方式去把握VR环境中其他事物相对于自身的位置与距离,知觉到“这里”与“那里”的延伸关系,从而产生更好的适应性与沉浸体验。
其次,在VR模拟环绕光的显现中,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光信息间具有可逆性转换特征,其能够使感知者在环顾四周的视看中,以非对象化的方式将VR环境知觉为一个自己“在之中”的,与自身存在相关的处境。在VR环境中,感知者的视觉场(the field of view)具有一定边界,这使得当一部分可见光环境向感知者显现时,总有一部分光环境被遮蔽,成为不可见的。这些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光信息,会伴随感知者头部的转动而呈现出可逆性的转换。例如,当头向右转时,新的光信息会随着视觉场右侧边缘的移动被逐渐添加进来,而已经进入视觉场中的光信息又会随着视觉场左侧边缘的移动被逐渐删除,反之亦然。同时,任何当头向右转时从视野中移出东西,都会在头向左转时重新进入视野[7]110-111。头部的上下转动与左右转动所呈现出的光信息的变化规律类似。虽然进入感知者视觉场中的光信息会随着感知者头部的运动不断变化,但是这种可逆性的变化特征本身是不变的。光信息的这种变化规律,一方面,会使感知者知觉到一个向其敞开着的、全景式的、围绕他周身的整体VR环境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会使感知者知觉到,在一部分可见VR环境向其显现的同时,有另一部分内容因其身体在环境中所占据着有限的位置而被遮挡。也就是说,通过这些被遮蔽、被隐藏的光信息,知觉到自身在VR环境中的在场。正如吉布森所言:“当你眺望这个世界时,隐藏在你视看周围的环境,肯定不是黑暗,也不是空气,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自我。”[7]105总之,VR环境在此不再作为对象图像,而是作为与感知者有关的处境而存在。
再次,在VR模拟环绕光的显现中,光流信息的方向变化同样具有可逆性特征,其能够影响感知者的自我运动觉,在知觉层面打破静止和运动的绝对区分,使感知者在知觉到VR环境变化的同时,知觉到自身的在场运动。吉布森认为,在感知者的身体相对于环境的运动中,环绕光结构会呈现出连续流动的变化,形成所谓的“光流”(optical flow),而光流反过来也影响着感知者的运动觉,即感知者对于自身在环境中运动的知觉。光流的变化特征能够在VR环境中得到还原,这在GTS和《神力科莎:竞速》等赛车游戏的VR模式中表现明显:当驾车向前行驶时,感知者前方视觉场中所呈现出的模拟环绕光会从中心向四周流动,而当从后车窗向外看时,视觉场中所呈现出的模拟环绕光则会相反地从四周流向中心,在倒车的情况下,原先的光流变化则会发生逆转。与此同时,这些光流的变化并不会影响模拟环境中代表稳定不变环境整体的光结构信息,例如模拟环境中陆地和天空在地平线处的对比,以及地表整体纹理等。如此,通过这种变化的光信息与不变的光信息的对比,感知者产生了一种相对于环境的运动感,仿佛自己真正在驾车行驶。正如吉布森所言:“如果说一个人在环境中向前移动时,感知到前方世界的流出和后方世界的流入,这种说法是相当错误的。一个人体验到的是一个刚性的世界和一个流动的阵列。环绕的阵列的光流几乎从未被感知为运动(motion);它仅仅被体验为运动觉(kinesthesis),即自我运动(egolocomotion)。”[7]115
最后,在VR模拟环绕光的显现中,光信息的变化具有“可供性”(affordances)特征,其能够使感知者知觉到VR环境与自身在价值和意义层面的关联性,并能在实践层面对感知者的行为活动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吉布森用“可供性”的概念来表达环境中能够对动物的生存实践活动提供正面支持或产生不利影响的特征或特性,它“一方面属于环境中所具有的一种刚性属性,但另一方面又根据知觉和行为主体的意向或需求而发生变化”[6]102。吉布森认为,环境的可供性已经蕴含在环绕光信息中,这意味着感知者能够在视觉经验中直接把握到一个具体环境对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可能的实践效用、价值与意义。这同样适用于VR环境。例如,丹尼尔·弗里曼(Daniel Freeman)等的研究表明,VR技术的应用对于治疗患者的恐高症具有良好的效果[10]。从生态光学的视角来看,VR环境能够模拟出真实环境中影响患者高度知觉的环绕光结构变化,也就是说能呈现出让患者感到“可坠落”的高度信息,从而为患者提供一种逼真的“危险”情境。以此为前提,通过完成任务以及相关心理辅导的方式才能够有效地去减少这一“危险”在患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总之,这说明,VR环境对于感知者来说,并不是与自身无关的外部图像,而是具有一定价值属性并能够对感知者的知觉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实践情境。这种实践性的影响,增强了感知者的“在场”沉浸感,正如帕维尔·扎霍里克(Pavel Zahorik)等认为,虚拟“在场”意味着VR环境能够对感知者的行为产生相关影响[11]。
综上所述,VR环境对感知者的显现,从吉布森的生态光学视角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环绕光”信息的模拟还原呈现。VR环境中的模拟光信息具有与环绕光类似的显现特征,而这些显现特征能够加强VR环境与感知者在身体知觉层面的联系,使感知者对自身存在的知觉与对所处环境的知觉相互关联、相互协调,消解其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使VR环境向感知者敞开,成为后者置身于其中并在活动中实际知觉到的处境,从而增强感知者的“在场”沉浸体验。
二、 感知者对VR环境的视看
虚拟现实的视觉体验不仅涉及VR环境向感知者的显现,还与感知者对VR环境的视看方式密切相关,而这种视看方式同样对“虚拟在场”现象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梅洛-庞蒂认为:“我的身体同时是能看的和可见的。”[12]36也就是说,人在具身性的视知觉活动中不单纯是一个内在性的主体。实际上,由于人具有“能见-可见”的反身性或可逆性肉身存在结构,因而兼具主体性与客体性、主动性与被动性。在虚拟现实体验中,这种可逆性的存在结构,使得感知者在对VR环境的主动视看过程中,同时具有一种对于VR环境的被动可见性,从而使感知者不仅能够知觉到自身被卷入了可见的VR环境之中,而且能够知觉到自身在VR环境中也是可见的。这种反身性或可逆性的视觉活动,在知觉层面更深层地消解了人与VR环境间作为主体与客体对象的二元对立,使感知者知觉到自身与VR环境的共在关联,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感知者的“在场”沉浸体验。
首先,“能见-可见”之间的可逆性,意味着感知者在视看活动中能够知觉到自身被卷入了其所见的VR环境中,这在知觉层面消解了人与VR环境的对立关系。梅洛-庞蒂认为,肉身是一种镜子现象,它揭示出“我”的视觉活动中存在着一种“看-被看”的双重感知,也就是说,我既是一个能够主动视看的能见者,也是一个被动的可见者,并且我的能见与可见之间存在着一种可逆性的回环。在虚拟现实体验中,感知者“能见-可见”的可逆性,通过虚拟化身在VR环境中得到了延伸。一方面,虚拟化身给予了感知者一个锚定在虚拟世界中的视看位置,其视域跟随着感知者的目光而变换,以具身化的方式延展了感知者第一人称的视觉活动,使得感知者具备了在VR环境中的主动视看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虚拟化身诞生于VR环境之中,因此它实际上使感知者在VR环境中获得了与虚拟的诸事物相同的可见性,也就是说使感知者在VR环境中获得了一种被看的可能。因此,在视觉活动中,感知者与VR环境并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作为可见的能见者,感知者并非以视觉主体的身份,面对着作为客体对象的虚拟事物,而是由于通过虚拟化身具备了与诸虚拟事物相同的可见性、可感性,因此能够被卷入可见的虚拟环境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在多姆纳·巴纳寇(Domna Banakou)等利用VR技术研究身体归属感幻觉的实验中,成年被试者在VR环境中的一个虚拟镜子面前看到自己化身为一个4岁的孩童,并同时产生了虚拟世界中的事物偏大的错觉[13]。从梅洛-庞蒂的立场看,虚拟镜子向被试者显现了其可见的(虚拟)身体,揭示了被试者在这一视觉活动中的能见和可见的二重性。虽然被试者能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4岁的孩童,但可见的虚拟化身却已经将视看着的被试者带入到了那个孩童的虚拟世界中。被试者对环境中事物大小所产生的错觉,恰恰说明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那个4岁的孩子,并在以孩童的视角主动观察着其所在的虚拟世界,而虚拟世界相对于感知者这个可见的虚拟化身(孩童幼小的身体),也就显现为一个变大了的世界。总之,当感知者视看VR环境的同时,其通过自身可见的(虚拟)身体也同样进入并被包含在了VR的整个景象之中,也就是知觉到自身被卷入其中,而VR环境对于感知者来说也就不再是一个对象物,而是感知者所处的可见世界之整体。
其次,“能见-可见”之间的可逆性,还意味着感知者能够知觉到自身在VR环境中是可见的,这使感知者的自我不再封闭于内在意识之中,而是能向着VR环境敞开,与VR环境构成了一种差异中的同一关系或共在关系。在梅洛-庞蒂看来,我的能见与可见之间并非完全重合一致,相反,总是处在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相互转换之中。这使得我在主动的视看中同样有着被看的可能,这种可见性并不在于我的身体被谁看到,而在于我是被看者,在于我的视看中始终预设着一种他异性的目光,一种潜在的、匿名性的目光[14]。这种他异性目光并非局限于来自某个具体的他人,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源于所见的事物、环境以及世界,也就是可见者的整体。正如梅洛-庞蒂所引用的画家被事物注视的体验:“在一片森林中,我有好多次都觉得不是我在注视着森林。有些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注视着我。”[12]46因此,能见与可见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écart)或者说“间距”“分裂”[15],实质上意味着感知者的自身知觉并非源于某种通过意识反思而获得的内在同一性,相反,对自我的知觉中已经包含了一种他异性的目光,或者说,自我的主体性中已经包含了他异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视觉活动中的主体自我实际上不能脱离其所见的他异性存在者而单独存在,二者之间是一种共在关系。同理,从梅洛-庞蒂的立场出发,在虚拟现实体验中,由于虚拟化身延伸了感知者的能见性与可见性,因此感知者在对虚拟事物的视看中,同样会产生一种在那里被看的感受。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诸如《生化危机7》(ResidentEvil7)VR版等恐怖类的VR游戏中,玩家能够获得十分沉浸的惊悚体验。也就是说,当玩家通过虚拟化身,注视着虚拟环境中那些恐怖的场景,并察觉到那些景象会回应自己目光的变化时,便会有一种自己在那里能够被看到的感受,感受到自己在那场景中是可见的,随时有可能会面临某种未知的风险,或被未知的鬼怪所发现,由此产生压抑、害怕的情绪。当那些鬼怪真正出现并朝着玩家的目光走来时,玩家的可见性就充分曝光在了鬼怪那可怖的凝视中,这时玩家也就会因感受到自己“被发现”而不由自主地发出尖叫。总之,感知者在主动的视看活动中,同时知觉到自身在VR环境中的被看或者说可见,意味着感知者对自身主体在场的知觉总是与对他异性VR环境的知觉不可分割,或者说主体自我的存在只有在与他异性环境的共在中才能获得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区别于抽象意识的内在同一性,而是与VR环境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差异中的同一性关联。
综上所述,从梅洛-庞蒂的视角来看,视觉活动所具有的反身性或可逆性特征,使感知者对于其所见的VR环境具有一种可见性。这种可见性使感知者在视看VR环境的同时,不仅能够知觉到自身被卷入了其所见的环境中,而且能够知觉到自身在VR环境中是可见的。这在知觉层面消解了人与VR环境的对立关系,使感知者在知觉VR环境的同时,也知觉到自身与VR环境的共在,也就是共同“在场”。
三、 “虚拟在场”的存在论意义
如上文所述,虚拟现实的视觉体验既涉及VR环境对感知者的显现方式,也关系到感知者对VR环境的视看方式。一方面,VR环境通过模拟“环绕光”而向感知者显现的方式能够影响感知者的自我在场知觉;另一方面,感知者视觉活动所具有的反身性或可逆性,能够使感知者知觉到自身与VR环境之间的共在关系。这两方面的耦合,在知觉现象层面打破了VR环境与人之间的对立,使人对自身存在的知觉与对VR环境的知觉,就像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相伴而生,不可分割,并使VR环境与人形成了一种共在关系,从而促进了“虚拟在场”现象的形成。从梅洛-庞蒂的立场来看,这种在身体知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内感知与外感知的不可分割性,这种内在与外在、主体与客体的含混性,正是以“肉身”(flesh)存在为基础的。在梅洛-庞蒂的肉身存在论中,“肉身”并非停留在物质性的身体或实体层面,也并非抽象的意识或精神存在,而是在广义上表达着人与诸事物、环境以及世界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相互交织的普遍存在结构或存在原则[16]139。也就是说,从梅洛-庞蒂的视角看,在虚拟现实的视觉体验中,人所获得的“虚拟在场”感受,实际上揭示出了人与VR环境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相互关联性,即二者并非构成经验主体和经验客体的二元对立,而是形成了一种肉身性的前反思意义上的相互“交织”(chiasm)的存在关系。
一方面,VR环境中的模拟环绕光可被视为一种“肉身化的光”,其显现离不开感知者肉身性的视知觉活动。作为一种在感知者身体知觉层面所实际显现的光,吉布森的“环绕光”概念响应了梅洛-庞蒂对于光的现象学立场。“梅洛-庞蒂将光理解为一种伴随着知觉变化的现象”[17],他认为光与我们的肉身知觉经验是不可分割的,与我们知觉到的现象共存,是具身化的,“只有当它已经散布于(我们也身处其中的)肉身之中,只有通过我们,这种光亮才能汇聚于一个核心意义之上”[18]。同理,由于VR光环境模拟了环绕光的变化,因此它的显现同样与感知者的肉身性知觉不可分割,其显现总是预设着感知者肉身的目光,它显现在这目光之中,并随着目光的变化而变化,它并不阻碍目光,而是对目光的延伸与缠绕,成为了肉身化的光。
另一方面,感知者在视觉活动中的自身可见性,建立在肉身可逆性的基础上,离不开其所视看的VR环境。梅洛-庞蒂将肉身的存在原则表达为“可见者(the visible)在正在看的身体之上的缠绕,可触者(the tangible)在正在触的身体之上的缠绕”[16]146,而视觉活动中所蕴含的“能见-可见”的二重性,正是对此的体现。肉身的可逆性使得感知者在主动的视看活动中,同时具有被动的可见性。这种可见性通过虚拟化身的中介,被延伸至了虚拟世界之中。因而当感知者视看VR环境时,就已经被卷入了其所见的VR光环境之中,与VR环境相互纠缠,共同在场。
VR环境与人所形成的这种肉身性的“交织”存在关系,进一步来说,在现象学存在论的意义上,“虚拟在场”现象中,可被视为是对肉身性“此在”(Dasein)“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d)生存论结构的扩展和丰富,以至于指向着可能的虚拟生存。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即存在者的自身显现,而存在者的自身显现也就是存在者的存在。此在的存在或自身显现作为一种最为原初的现象,一方面是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自身显现的前提,另一方面同时意味着世界的自身显现,因而揭示了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实际生存方式[19]。梅洛-庞蒂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赋予了此在以肉身性,认为此在的自身显现必须以肉身为基础,其生存论结构也只有在肉身存在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从这种现象显现的角度出发,“虚拟在场”现象可被视为是VR环境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肉身”为基础的双重显现过程,即在VR环境向感知者显现的同时,感知者也以可见的方式,在VR环境的显现中显现自身。在这种双重显现过程中,一方面,VR环境中诸事物的显现必须要以处在实际肉身知觉活动中的感知者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感知者的自身显现,基于肉身的可逆性,总是同时意味着VR世界的自身显现,它总是显现在VR世界的显现之中,也就是说,以VR世界的存在为其应有之义。如此可以看到,在“虚拟在场”现象中,VR环境与感知者以肉身为基础而形成了一种在显现中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的存在关系。这种存在关系实际上可被视为是肉身性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在虚拟维度的延伸,即人“在-虚拟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a-virtual-world)[20]。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现实世界中的活动对人而言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感官刺激体验或图像游戏,而是一种可能的在世存在方式。
四、 展望:虚拟生存的可能
如上所述,“虚拟在场”现象揭示了人生存论结构中的虚拟性维度,表达了虚拟现实活动作为一种人在世存在方式的可能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可能性将在未来“元宇宙”(metaverse)的建设和发展中逐渐得到彰显。
“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它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21]在此,虽然虚拟现实技术,或者更广泛来讲,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 简称XR)技术只是构建元宇宙技术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知觉现象层面,元宇宙是作为一个虚实相结合的世界向人显现的。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存在论事件”[22],被视为人类未来的数字化生存方式。
元宇宙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而非单纯的虚拟游戏,在于它兼具了实践性与境域性。一方面,实践性是元宇宙作为人生存方式的必要前提。它意味着元宇宙中拥有完整运行的社会和经济系统,使人在虚拟的环境中能够以独立的身份自由地进行工作生产、社交娱乐等活动,而这些虚拟活动能够产生相应实际的价值与效益,并对现实生活造成切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境域性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属性,是元宇宙成为人生存方式的重要保障。在梅洛-庞蒂的意义上,人的生存是发生在一个具身的境域之中的生存,因此,只有以由人肉身知觉活动所展开的存在境域为基础,虚拟实践才可能具有生存论的内涵,反之若是缺乏这一境域性,虚拟实践活动就只能算是附庸于现实生活的手段。就元宇宙而言,其境域性恰恰生成于由虚拟现实乃至于扩展现实技术给人带来在场沉浸体验之中。正如上文所述,虚拟的在场沉浸体验意味着人在肉身性的知觉活动中与数字化的虚拟环境相互交织。人不再隔着屏幕,而是以虚拟化身的方式置身于元宇宙的数字化网络环境之中;后者也不再被当作一个有待于去“操作”的数字系统,而是在人的知觉活动中被把握为具身的多样化时空场域和实践情境。如此可见,元宇宙之为“宇宙”的意义,并非指向一个另类的客观物理世界,而在于它所呈现的是一个能让人置身于其中,“在场”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一个有待于人去亲身经历、实践的生存境域,因而能够作为未来人的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
总之,由“虚拟在场”现象所揭示的虚拟生存,将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未来逐渐获得一种实践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已经在“元宇宙”的建设中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