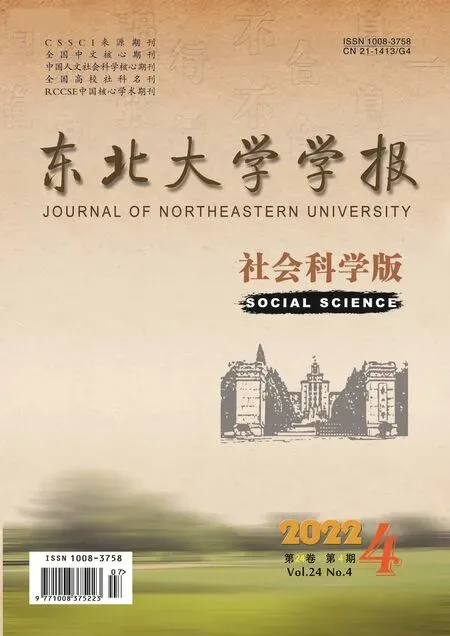CISG在我国法院的适用
----兼论后民法典时代的条约适用问题
张 普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4)
经历40余年的发展,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The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Contracts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 简称CISG)已经成为国际贸易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条约[1],缔约国高达95个(1)数据来源: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salegoods/conventions/sale_of_goods/cisg/status。。准确适用CISG是缔约国条约义务的应有之义,也是彰显各国涉外司法水平的重要体现。然而在CISG的适用问题上,我国法院的审判实践尚存诸多不足,学术界亦常论常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实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自此废止。《民法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均未对条约的适用问题进行规定,这就使得民商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局面。以反思国内实践知不足、以考究国际实践求补正是提升我国条约适用能力、完善条约适用制度的重要方法,因此本文旨在剖析CISG适用规则、评析国内外司法实践,这对于我国司法系统清晰认知和准确适用CISG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一、 CISG在我国法院适用的依据和方式
条约的适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为条约自身的性质与设定,二为缔约国国内法中对条约适用方式的选择与规定。
1. CISG的适用依据
我国法院在适用CISG时应当遵循该条约自身的规定,同时还应当依据我国国内法中有关条约适用的规则。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对CISG的适用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作为缔约国,我国法院依据CISG规定适用该条约是条约义务的应有之义[2]。CISG的第一章(第1条至第6条)即为该条约的适用规则,其分别就适用条件、管辖事项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在CISG的适用中,这些适用规则具有一定的逻辑层级性。第一步应根据CISG第2条至第5条判断涉案合同是否在CISG的管辖事项范围内。如果涉案合同的性质与内容落入CISG的调整范围之内,再依据CISG第1条进行判断。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的CISG缔约国或根据法院地冲突法规定适用CISG缔约国的法律,则再依据CISG第6条判断当事人是否排除了CISG的适用。如果合同当事人并未有效排除CISG的适用,CISG应最终得到适用。
其次,我国法院应当依据我国国内法的规定适用条约。目前,我国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并未明确条约的法律地位,也未规定条约的适用方式。长期以来,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被视为我国法院适用民商事条约的国内法基础和一般原则(2)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其也是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条约、国际惯例的直接依据[3],但该条款并未在新制定的《民法典》中得以保留。《民法典》实施后,《民法通则》自此废止。这也就导致我国法院适用民商事条约基本依据的缺失。目前,就民商事条约的适用问题,我国民商事关系的基本法《民法典》与统一规定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法律《法律适用法》均未规定。从法律规定层面看,条约的适用确实处于“无法可依” 的局面,但《民法典》实施后,民商事条约仍会在我国得以适用。一方面,适用条约是我国作为缔约国应当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另一方面,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可适用条约是我国法院的一贯实践,而且这一实践也无理由不持续下去[4]。不只如此,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所体现的“条约优先”的适用方式也将会得以坚持。目前,该条款的相关规定在其他民商事法律中仍然存在,并依然有效,如《海商法》第268条、《票据法》第95条等。基于我国的这种司法传统,在合同领域也将保持“条约优先”的态度。可见,虽然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并没有被《民法典》所吸纳,但我国长期基于该条款所形成的条约适用习惯将会得以延续。具体而言,这种适用习惯大可包含以下两方面:其一,民商事条约可以在我国法院直接得到适用[5-6];其二,当民商事条约与我国法律规定不同时,应适用条约。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我国法院适用条约具有指导意义。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发布的《转发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3)《通知》中规定:我国政府既已加入了公约,也就承担了执行公约的义务。因此,根据公约第1条(1)款的规定,自1988年1月1日起,我各公司与上述国家(匈牙利除外)的公司达成的货物买卖合同如不另作法律选择,则合同规定事项将自动适用公约的有关规定,发生纠纷或诉讼亦得依据公约处理。故各公司对一般的货物买卖合同应考虑适用公约,但公司亦可依据交易的性质、产品的特性以及国别等具体因素,与外商达成与公约条文不一致的合同条款,或在合同中明确排除适用公约,转而选择某一国的国内法为合同适用法律。与1989年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明确对CISG在我国法院的适用进行了说明。两文件思想一致,内容相仿,均明确了CISG“自动”“直接”的适用方式。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的理解存有诸多争议,尤其是在目前被废止后,以上《通知》与《纪要》对于CISG在我国法院的适用更不乏价值,其直接明确了该条约适用方式,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CISG的适用方式
依据CISG的适用设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其存在直接适用、间接适用和约定适用三种适用方式。
直接适用是指法院依据CISG第1条第1款a项(以下简称a项)对其进行适用。如果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缔约国,且当事人并未排除CISG的适用,我国法院就应当适用CISG。根据前文所述,我国法院判定CISG是否得以适用时应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判定涉案合同是否属于CISG的适用范围,然后判定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否位于不同缔约国,最后判定当事人是否排除CISG的适用。在对CISG的直接适用进行外部证成的过程中,前两次判定都是基于客观事实的认定,法院只需要根据CISG的规定进行比照裁量即可。而对“排除适用”的判定则要求法院形成对当事人排除CISG适用的确认[7],这种极具主观性的判定在CISG制定时就饱受争议[8],实践中也的确给法院适用CISG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如果涉案合同的客观因素完全符合CISG的适用条件,对于当事人有效排除CISG的判定就成为CISG能否直接适用的关键。实践中,合同当事人排除CISG适用较为妥当的方式有以下三种:其一,明确排除适用CISG[9];其二,约定适用非缔约国法律[10];其三,约定适用某国特定法律[11],例如约定适用中国《民法典》。而当事人在合同中仅笼统地约定适用某缔约国法律则难以达到有效排除CISG的效果,甚至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为某联邦国家的一个州法律时,也不能排除CISG的适用[1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也采用该观点(4)参见:“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四终字第35号判决书。,更有学者直接将如此约定称为对CISG的“间接选择”[12]。
间接适用是指法院依据冲突法规则对CISG进行适用。根据CISG第1条第1款b项(以下简称b项)规定,如果法院依据本国冲突法应适用的是某一缔约国法律,则该条约应该得到适用。我国在加入CISG时对该条款进行了保留。基于此,传统观点认为我国法院只能依据a项的直接适用规则来适用CISG,只要存在一方当事人营业地在非CISG缔约国,我国法院就应依据对b项的保留完全排除CISG的适用[13]。笔者认为,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并非都在CISG缔约国时,CISG也有适用的可能。此时,我国法院理应排除依据a项对CISG的直接适用,就法律适用问题应该由《法律适用法》来决定。如果根据《法律适用法》应适用对b项进行保留的缔约国法律(包括我国)或非缔约国法律,CISG当然不能得到适用。如果根据《法律适用法》应适用没有对b项保留的缔约国法律,此时b项在该缔约国内发挥“分配条款”的作用(5)“分配条款”,也称“法际私法”,指解决一国现行法律中不同规定之间冲突的法律。对于该条款作用的详细分析,参见张普:《国际民商事条约在我国法院的可适用性及其适用模式》,《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105-116页。,其不但将该缔约国的实体法分为国内买卖合同法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14],而且在该缔约国为准据法国时CISG将取代其国内的买卖合同法而优先适用。我国法院此时适用CISG并非基于我国作为CISG缔约国的条约义务,而是基于《法律适用法》的指引和对该缔约国在CISG下条约义务的尊重[15]。
约定适用是指法院依据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而适用CISG。CISG第6条规定了当事人的私法自治(6)CISG第6条: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其也明确了CISG的任意性。就内容而言,该条款只是明确了当事人可以排除适用CISG、部分适用CISG和在不违反第12条的前提下对CISG的条款进行修改或变更。至于当事人能否约定适用CISG,该条是没有规定的。条约能否基于当事人约定而成为准据法不仅取决于条约的自身设定和性质,更取决于一国国内法的规定。对于该问题,国际上尚无定论。而在合同领域,我国涉外立法和实践对于私法自治一直采取肯定态度,但是,当事人能否选择条约作为合同的准据法,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法院普遍承认当事人对CISG的选择适用,但就适用时CISG的性质而言,法院实践不一。笔者更倾向于将其认定为准据法,而非合同内容[16]。
二、 CISG在我国法院适用的弊病
从立法实践来看,CISG对于我国国内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合同法》和当下的《民法典》合同编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CISG。但是反观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尚存许多弊病。
1. 立法的缺失与我国法院对规则理解的偏差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尚缺乏有关条约地位及适用方式的明确规定。就民商事条约在我国的接受方式,学界普遍承认“当然纳入说”[17]。虽然在《民法通则》废止后,我国法院依旧会延续第142条所载明的方式对民商事条约予以适用,但《民法典》对该条款的放弃的确造成了条约适用规则的缺失。就目前来讲,我国民商事条约适用的理论体系完全是基于原《民法通则》第142条而建立起来的。不论是民商事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基础理论还是CISG等条约在国内的具体实施,均是依据该条款而展开。当下,该规则的缺失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
就CISG的具体适用,应当认为CISG虽然并非中国立法机关“亲生”,但其“纳入”我国法律体系后便如同“亲生”,因而在我国具有了法源地位。我国法院在适用CISG时是在适用属于我国法源的规则而非是在适用我国法源之外的规则[5]。因此,我国法院在直接适用CISG时无需任何指引或依据其他法律。然而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依据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适用CISG的案例比比皆是,甚至成为了主流意识。这足以反映我国法院对于条约适用规则理解的不足。目前,《民法通则》已经废止,《民法典》也并未有如此规定,我国法院自然不会再依据该条款适用CISG。但是,该问题并非只是法律条款的存废问题,而是法院对民商事条约适用规则理解的偏差。
作为我国司法机关适用CISG的重要依据,《通知》与《纪要》的价值不容小觑。两文件不但明确了CISG在我国法院的适用方式,而且展示了我国法院积极适用CISG的态度。但是,两文件就CISG的适用规定也存有一定偏差。就具体内容来看,两文件均以当事人“不另作法律选择”作为我国法院适用CISG的条件,这难免给人一种“我国法院适用CISG需要以当事人不作法律选择为前提”的错觉。正如前文所述,对于客观因素完全符合CISG适用条件的合同,法院最终能否直接适用CISG应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有效排除CISG,而并非“另作法律选择”。“另作法律选择”并不等于“有效排除CISG”,如果当事人只是笼统约定适用某缔约国法律,我国法院并不能以此排除CISG的适用,而是应当直接适用CISG。
此外,《通知》与《纪要》只明确了我国法院对CISG直接适用的方式,而未提及间接适用的方式。这显然说明了我国法院对CISG适用规则理解的不足。也正是这种对CISG适用规则的片面理解导致了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忽视CISG间接适用的倾向。可见,对于CISG适用依据与适用规则理解的不足与偏差严重制约着我国法院准确适用CISG的能力。
2. 我国法院对CISG 适用排除不当
我国法院时常在当事人未约定法律适用时错误地排除CISG的适用。在CISG的直接适用中,当事人是否有效排除CISG是法院最终能否适用CISG的关键。如果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法律适用,则当然不能视为排除了CISG的适用,法院应当依据a项直接适用CISG。在“恩拓进出口商行与‘波德拉谢’安杰·克利维克商业公司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纠纷案”中(7)参见: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7)浙0782民初字第2064号判决书。,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中国和波兰,当事人也并没有就法律适用作出任何约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应当直接适用CISG。但是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对涉案买卖合同的法律适用没作出约定,本案中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货物交付发生在我国境内,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裁判。”可见,该法院显然忽略了CISG的适用问题,而直接依据我国冲突法规则进行了准据法的选择,这种作法是错误的。究其原因,在于我国法院适用条约的意识并不强。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法院最通常的做法是依据我国的冲突法规则去确定准据法。这就导致法院在处理一些满足CISG适用的案件时经常习惯性地根据《法律适用法》来确定准据法,而完全忽略CISG的适用。
此外,在当事人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我国法院也时常错误排除CISG的适用。无论是直接适用还是间接适用,当事人基于约定阻断CISG适用都要达到“有效排除”的标准。有效排除CISG需要满足的形式要件为当事人达成合意[18],实质要件为形成法院对当事人排除CISG适用的确信。如果当事人并没有达成排除CISG的合意或只是笼统地约定适用某缔约国法律,则并不能产生有效排除CISG的效果。在“The Moneycon Consultant Inc.与宁波布利杰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8)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甬商外初字第209号判决书。,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美国和中国。就法律适用问题,The Moneycon Consultant Inc.主张适用中国法,而布利杰公司表示:“若CISG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冲突,则优先适用CISG”。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中国法律与CISG并无冲突”为由,最终依据我国冲突法规则适用了我国法。本案中,当事人对于法律适用的主张看上去十分复杂,并且从法院的最终判断来看,不能说当事人的主张对其毫无左右。但如果法院能够把握当事人有效排除CISG的形式要件,情况也就会变得明了。本案中,当事人并未达成排除CISG的合意,当然不能形成对CISG的有效排除,应直接适用CISG。另外,在“寿光木可多经贸有限公司与奥斯特派克化工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9)参见: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外初字第23号判决书。,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中国和澳大利亚。案件审理中双方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此适用了原《合同法》。本案中,当事人的约定虽然满足了排除CISG的形式要件,但笼统约定缔约国法律(中国法)尚不满足排除CISG的实质要求(10)司法实践中,如果能够证明当事人有意将缔约国法律与CISG区别开来,如明确区分中国法和CISG,则当事人约定适用缔约国法律的做法可以被法院认定为是对CISG的有效排除。。在此后的二审中(11)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第1141号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纠正,适用了CISG。至于当事人约定适用的中国法被当作CISG未涉及事项的准据法,应当认为二审法院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3. 我国法院对CISG适用不准确
我国法院在适用CISG时常存在逻辑颠倒的问题。CISG不但存有直接适用、间接适用、约定适用三种方式,而且每种适用方式都是基于不同的法理基础和逻辑推理。因此,法院在判断是否适用CISG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就CISG的直接适用而言,法院应该首先对涉案合同是否属于CISG的管辖范围进行判断,而后对涉案合同的国际性进行判断,最后对当事人是否有效排除CISG进行判断。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经常会首先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判断。这种逻辑颠倒往往会导致CISG的适用错误。在“意大利采埃孚帕多瓦有限公司与宁波市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等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案”中(12)参见:宁波海事法院(2016)浙72民初第1539号判决书。,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意大利和中国,庭审中双方均同意适用CISG。一审宁波海事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CISG,根据《法律适用法》第3条的规定,本案依法适用CISG。”虽然一审法院在案件中适用了CISG,但其基于当事人约定而对CISG的适用存有一定的逻辑错误。法院首先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逻辑颠倒将会导致两个层面的错误。其一,就CISG的适用方式,一审法院显然肯定了当事人对CISG的约定适用。然而在CISG能够得以直接适用的前提下,法院不应肯定对CISG的约定适用。因为直接适用的基础是缔约国对条约义务的遵守,若无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有效排除CISG,CISG应该为法院强制地予以直接适用。其二,就当事人约定适用的行为性质,一审法院显然认为是《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然而在CISG本应得到适用的前提下,当事人对于CISG的约定仅能视为对适用CISG的宣称与强调,并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13)该观点在此案的二审判决中得到应正。虽然在双方已有适用CISG的约定,但二审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销售合同中,买卖双方未约定适用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也未通过明示的方式排除该国际公约的适用,故本案合同纠纷应适用CISG,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123号判决书。,更不可能起到选法的效果。
我国法院在适用CISG时还时常存在路径错误的问题。CISG一经纳入,即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具有了法源地位。如果满足CISG直接适用的条件,法院应当“自动”“直接”适用CISG。所谓“自动”,主要体现为CISG的优先适用性。所谓“直接”,主要体现为法院应该像适用国内法一样适用CISG。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时常会依据我国国内法的指引来适用CISG,而导致适用路径上的错误。下面以一则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来分析我国三级法院在适用CISG路径上的差异,以窥视我国法院适用CISG路径上的偏差。在“C & J金属板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晨兴机械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C & J案”)中(14)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温商外初字第340号判决书。,一审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C & J公司与晨兴公司的营业地不同且所在国均属于CISG的缔约国,在双方未排除公约适用的前提下,CISG优先适用于C & J公司、晨兴公司所订立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该案中,法院适用CISG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其依据原《民法通则》第142条适用CISG实无必要。随后,该案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样根据原《民法通则》第142条,“同时,根据CISG的规定”确定了CISG的优先适用地位,继而适用了CISG(15)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商外终字第144号判决书。。最后,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的法律适用也作了阐述:“C&J公司与晨兴公司的营业地分别位于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美两国均是CISG的缔约国,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未排除该公约的适用”,故本案应适用CISG(1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66号判决书。。对比以上三级法院的裁判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CISG适用路径的论述不仅言简意赅,也完全符合“直接”“自动”适用的要求。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基于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的指引而适用CISG的做法实属画蛇添足。需要重视的是,如此适用CISG的案例在我国司法审判中不在少数。
此外,我国法院在适用CISG时还存在CISG与其他法律适用混乱的问题。CISG是由不同法系、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协商而成,是各国就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问题所达成的最低限度的意思统一[19]。因此,CISG与国内法必然会存在一定的重合。但同时,CISG也并不能像国内法一样尽可能详尽地规范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的所有问题。我国法院在适用CISG时必然会遇到CISG与我国国内法竞合时的法律选择、CISG就某一或某些事项未规定时的法律确定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基础是CISG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缔约国法律体系内,CISG起到“定向替代”的效果。所谓替代,一方面表现为CISG就某一问题有具体规定而国内法并无规定时对国内法的补充,另一方面表现为CISG和国内法均有规定(不论规定是否一致)时对国内法的取代。但这种替代并非是对缔约国国内法的绝对排斥,其以CISG的管辖范围为限,故而称为“定向替代”。CISG的优先适用就是其对国内法替代的后果。对于CISG并无管辖的“外部漏洞”,法院还应当根据本国冲突法规范进行准据法的选择[20]。以“Universalmarbles公司与厦门成伟鑫工贸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为例(17)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初字第277号判决书。,案中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意大利和中国,双方并未约定法律适用。就法律适用问题,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中、意两国均是CISG的缔约国,且双方均未排除适用该公约,依据《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之规定,本案优先适用CISG,CISG无约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可见,法院以CISG“定向替代”了相应的国内规则,但其在CISG“外部漏洞”直接适用我国国内法的思路是错误的,此时法院应当依据《法律适用法》来确定准据法,而并非直接适用我国法。
三、 CISG在我国法院适用的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纠纷也必将激增。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完善涉外法律体系,不断提升司法机关司法能力,以保证条约在我国法院得以适当、准确地适用。
1. 补正CISG适用依据
我国法院难以准确适用条约的首要原因是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宪法及其相关法未就条约的法律地位和适用方式进行明确,各单行法对该问题也是语焉不详,《民法典》更是整体放弃了原《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无论《民法典》是基于何原因放弃了该规定,对于条约的地位与适用方式的明确都确实是我国法院适用条约时不可回避的关键性和基础性问题。因而,在立法层面通过法律明确的方式解决条约的适用问题是最为根本的方法。就具体做法,可在宪法或相关法中明确条约的适用规则,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此外,也可以在《民法典》等基本法中明确某一领域相关条约的适用规则,从而改变条约适用无法可依的局面,以减少司法实践中的困惑、误区和分歧。
然而考虑到修改法律的困难性和条约适用问题的迫切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不失为一剂良方。通过对近年来我国法院的相关司法文书进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起到了积极作用。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例,对比“C & J案”与其之后案件的裁判文书(18)如“杭州奥斯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德米里克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商外终字13号判决书;“宁波市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诉意大利采埃孚帕多瓦有限公司等船舶物料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128号判决书。可以发现,“C & J案”之后的裁判对于CISG的适用更加规范和准确。相信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将“C & J案”的再审当作典型案例进行公布和示范不无关系。然而,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CISG适用的指导性案例只有1个(19)参见:指导案例107号“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能够查询的典型案例也仅有3个(20)分别为“埃及 ELBORSH公司与耿群英、石家庄赛德贸易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402 号裁定书;“C & J 金属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晨兴机械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66号判决书;“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四终字第35号判决书。参见http:∥www.court.gov.cn/wenshu.html?keyword=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aseid=&starttime=&stoptime=。。这远远满足不了我国急速增长且形式各样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需要。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发布更多高质量适用CISG的司法案例,以指导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条约,进而提高我国司法系统对条约的理解能力和适用水平。
此外,在《民法典》缺失条约适用规定的情况下,《通知》和《纪要》以及指导性案例等对于CISG适用的指导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在其他领域的条约适用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指导性文件或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明确和统一法院对具体条约的适用。
就CISG本身的适用规则,我国的确应当考虑撤回对b项的保留。诚然,正是对b项的保留使得CISG的适用更为复杂,我国司法界对于b项认知的缺乏也造成适用CISG的不足。如果撤回对b项的保留,CISG的适用将变得更加明朗。目前,我国《民法典》合同编深受CISG影响,当初“内外有别”的经济管理体制也不复存在。因此,对CISG替代国内法的担忧已无必要[21]。相反,实现CISG与我国《民法典》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完善我国合同规范体制,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化。另外,随着CISG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不断加深,商人们对于CISG规则更加了解,也能更好地依据意思自治实现对法律的选择与对合同的预期,这将导致我国对于该保留的预期价值的降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外贸管理体制早已时过境迁,对于b项的保留值得重新审视和评估。
2. 统一CISG分析范式
考虑到从立法、司法指导等方面补正CISG适用依据和适用示范并非易事,因此遵循CISG内部逻辑,结合我国法院司法习惯,形成统一的CISG分析范式,以供法院系统参考和使用是另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在准确适用CISG的过程中,大可经过以下三个环节,且每个环节都有着各自的内在逻辑。
首先,理清CISG与传统冲突法方式的关系。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可以通过冲突法方式和统一实体法方式。CISG作为典型的统一实体法,在解决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纠纷时与冲突法方式是两条并行的路径(21)虽然依据b项对CISG进行适用也要优先考虑我国冲突法,但如此适用冲突法也是CISG规则的一部分,最终还是回归到CISG来解决纠纷。。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时习惯于优先考量冲突法方式,这种习惯需要得以纠正。法院应当优先考虑适用CISG,这是条约目的使然,也是对条约义务的遵守。
其次,进行CISG的外部证成。在法院处理案件时,CISG的“准入”规则具有严格的逻辑层次。就CISG适用的三层次关系,前文已经论及,在此不作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CISG的外部证成中,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查验应放于最后。法官切不可在法律选择时首先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免落于冲突法方式的惯性思维。另外,允许当事人选择条约所体现的私法自治并不等于CISG第6条所规定的当事人意思自治[22]。当事人选法或另作法律选择并不必然构成对CISG适用的有效排除。如果经过三层判定最终CISG“准入”失败,则应回归冲突法方式,否则,应直接适用CISG。
最后,实现适用CISG与冲突法方式的良性互动。虽然说适用CISG这一统一实体法与冲突法方式是两条并行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在依据CISG处理案件时就绝对排斥冲突法规则的适用。由于CISG管辖范围的有限性,在涉及CISG“外部漏洞”时,应当承认冲突法方式的回归,直接适用我国国内法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以上CISG适用的分析范式可以帮助我国法院判断CISG的适用以及处理好CISG与冲突法方式的协调。
3. 提升适用CISG的说理能力
囿于对条约适用规则理解的不足与条约适用实践的生疏,我国法院错误排除CISG适用、不能准确适用CISG也必将导致在案件中适用CISG说理能力的不足。因而加强法院系统对于条约适用的学习能够实现在案件中外部证成与内部证成能力的同步提高,从而提升法官运用条约处理案件时的说理能力。
有关CISG权威的、正式的解释和说明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贸易法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汇编》(以下简称《摘要汇编》)。目前,《摘要汇编》不但就CISG的具体条款进行了解读,还配有国内外案例说明,可为我国法院系统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料和参考依据。《摘要汇编》虽然不是CISG的一部分,对缔约国并不具有当然约束力,但法院在适用CISG时应当对其予以足够重视。在《摘要汇编》中,就CISG的排除、间接适用、与国内法关系等问题都有一定的说明。我国法院裁判文书中对于CISG排除问题的分歧、适用路径的错误等问题足见法院系统对《摘要汇编》学习的不足。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中明确要求:“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应当依法引用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这对我国各级法院运用条约进行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条约内容来看,其与国内法最大的不同在于条约往往规定了较为明确的适用条件,该特征在民商事条约中尤为突出。因此,在案件中对条约的“准入”不只是法官在逻辑上的外部证成,更是一个适用法律的“释法”过程。这就要求法院在适用条约时也要示明其援引的具体条款并以此进行说理。然而,我国法院的司法文书中往往缺乏对此的论述。例如,我国法院多依据a项适用CISG,而在裁判文书中对援引该条款并适用CISG的论证寥寥无几。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三个典型案例也均未就CISG的适用规则进行示明和分析。此外,在案件审理中我国法院常以“注册地”标准对管辖权问题进行审查后,进而以“注册地”“住所地”等取代“营业地”来判定CISG的适用(22)如“国民沥青株式会社与浙江嘉悦石化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540号判决书;“Universalmarbles公司与厦门成伟鑫工贸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初字第277号判决书。。如此进行法律证成是不严谨的,甚至是错误的。反观国外司法判例,法院对于CISG适用条款的示明、论证,以及对于当事人“营业地”的判定则更为规范,说理也更充分(23)参见: “Nucap Industries, Inc. v. Robert Bosch LLC”,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 (29 August 2016)15-cv-2207 ; “Zintix Pty Ltd. v. Olitalia s.r.l.”, Italy District Court of Forli, (26 Mar 2009) 2691/2009.。因此,适当借鉴国外法院判决也是提升我国法院说理能力的另一种方式。在这方面,贸易法委员会所建立的“判例法数据库”和佩斯大学建立的“CISG数据库”可为我国法院提供世界各国的相关案例。
综上,我国法院系统可通过对《摘要汇编》和对案例数据库的运用更好地理解和掌握CISG,从而提升适用CISG的说理能力。
四、 结 语
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CISG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民法典》对于条约适用规定的缺失使得我国条约适用问题更为突出。后民法典时代,我国法院依旧会对民商事条约予以适用。至于对CISG的理解与适用还不够完善的问题,我国法院应当拓展国际视野,借鉴外国相对成熟的适用经验以补正自我之不足。只有积极看待CISG才能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也只有准确适用CISG才能够展现我国的司法能力,从而树立大国司法的形象,营造公平、正义的国际商事新秩序。